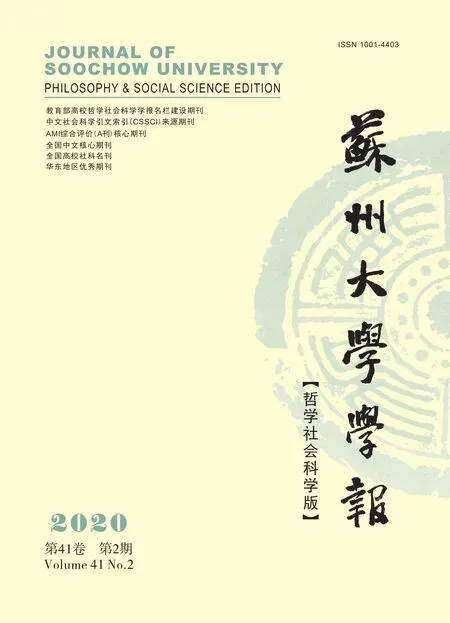优益权的另一面:论法国行政合同相对人保护制度
李颖轶
(华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41)
基于公共服务原则与二元司法体制,法国行政法院判例造法为行政主体保留优益权既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亦有现实的制度摇篮。[1]在行政法语境下,优益权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在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外,还必须符合“比例原则”要求(1)比例原则,如同“不用大炮打麻雀”的经典比喻,要求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和幅度以问题解决的必要为限,即手段与目的必须相符,否则可能构成权力滥用。,以确保优益权行为既合法也未越权或滥用权力,由此在实定法上不具苛责性。但在合同法视角下,无论行政主体如何审慎,在非必要情况下不得行使,优益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合同约束力的削弱。这些无法通过合同约定排除的,亦不通过一般合同规则调整的、固有(2)De plein droit,即拉丁文 de plano,根据《法兰西学院辞典》,系指无论是否受到质疑,无论是否须经司法或行政手段实现,都当然存在的权利或权力。本文译作“固有”。V.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t.1,1835,6e éd.的合同履行风险,必然要求法国行政司法系统也创设出一套同样不依赖合同约定产生的,亦不通过普通合同法规则调整的、固有的相对人保护制度(3)在新近论著中,已有学者开始采用“行政相对人优益权”(Les prérogatives des cocontractants)来描述行政合同相对人特殊保护措施,如 LOMBARD M.,DUMONT G.et SIRINELLI J.,Droit administratif,Dalloz,10e éd.2013.,并最终以此独特的公法进路平衡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代表的公共利益与相对人合法合理的私人利益。
一、行政合同履行原则:财务平衡
“财务平衡”(l’équilibre financier)与其说是一项相对人保护措施,毋宁说是一项行政合同(4)鉴于法国公、私法合同都采“contrat”为术语,本文仍以“行政合同”指代中国法语境中的“行政协议”。履行基本原则。(5)在经典行政法教科书与行政合同法教科书中,财务平衡原则均作为与王子行为理论、情势变更理论、不可抗力等具体保护措施的平行措施加以论述。鉴于优益权行使的补偿标准,与下述三类具体保护措施的补偿标准均围绕财务平衡原则展开,其实质乃是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笔者因此将其单独论述。它借鉴自法国私法中的“合同(经济)均衡”(l’équilibre contractuel)制度,意指 由于实务中常常无法实现经典法律格言所期望的“约定即公平(Qui dit contractuel dit juste)”[2]410,因此有必要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外赋予立法者和法官一定权限,以控制和调整合同内容上过于悬殊的失衡状态。(6)如法国旧《民法典》“合意瑕疵(les vices du consentement)”“约因(la cause)”等债法制度。
公法合同中的财务平衡原则最早出现于1910年最高行政法院“公共工程部长诉法国轻轨总公司”判例。(7)CE.11 mars 1910,n 16178,Rec.216,concl.Blunm.本案涉及公共服务特许合同,公共主体主张直接针对合同行使单方变更权。政府代表表示“所有合同本质上都是寻求与实现平衡‘许诺给相对人的利益’与‘强加给相对人的负担’的可能方式;所有行政合同都内含相对人获益与损失真正均衡之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财务与商务平衡,即特许合同的财务平衡”[3]6。自此以后,经过学者们的解读和阐释,财务平衡逐渐成为整个行政合同制度中的履行基本原则。(8)由于法国行政合同制度的判例造法特点,行政法学者对判例中出现的“财务平衡”术语阐释并非完全一致,本文主要参考René CHAPUS教授、Laurent RICHER教授与Laurent VIDAL博士的观点。为与前述私法“合同均衡”原则区分,行政法官和公法学家们有意选择了“财务平衡”作为术语。它意指在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在双方均不具法律苛责性时,行政主体必须维护相对人在“预期收益”与“现实损失”之间的经济平衡,要在“承诺给相对人的利益”与“强加给相对人的损失”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如无例外,合同双方均不能破坏这种合同经济上的目标,甚至立法者和法官也不能随便打破这种合同经济目标。
然而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为适应公共服务的可变性需求,政府必须随时监督和调整由相对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改变、增删行政合同权利义务条款来要求和敦促相对人回应公共服务需求,即行使监督指导权、单方变更权甚至单方解约权等行政优益权。由于公共服务的持续性要求,相对人不能中断公共服务的提供,即使意外增加的义务明显加重了履行负担、破坏了合同经济平衡,相对人依然只能继续承担。[1]在这个过程中,合同双方均不具苛责性,但由于合同行政主体一方同时身兼为社会大众组织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法定行政职能,而相对人只是这一行政职能实现的辅助人,前者就必须支付和偿还后者在初始约定之外增加的义务履行支出,以确保合同能够在经济上继续保持平衡的状态。因此,这本质上是公法视角下,以公法进路重新阐释,如何维护“公共(服务)利益”与“相对人利益”之间经济平衡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公益与私益兼顾的“公法上的公平”。
需要强调的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财务平衡很大程度上是指公共主体行使优益权时必须维护相对人“预期收益”和“额外损失”之间的平衡,前者由行政合同约定在先,后者却往往不能在当事人之间达成共识,而行政合同在公共服务持续性的要求下必然不能只因为无共识而终止。因此,这又是一个基于双方当事人诚实信用、需要自证的司法技术性事项。实践中,行政法官有权对此酌情处理,数额争议时有权主动决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结果。[4]234
毫无疑问,由于财务平衡最初是针对行政优益权提出的,因此财务平衡原则的首要价值便是在行政合同的框架下平衡行政优益权。如果说出于公共服务、公共利益要求,优益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行为中贯穿始终、不可或缺的法定权力,那么在公共服务、公共利益之后,财务平衡就必然是相对人在参与行政合同“辅助行政”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的最有力武器。出于平等与私权保护等宪法原则,在行政法官们的阐释下,它同样也是一种不依赖于合同约定产生的法定义务与责任,由此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实现行政合同内权利-义务、合同外权力-责任的总体平衡。因此,“财务平衡”与“行政优益权”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政府行使行政优益权,必然要承担财务平衡的义务;相对人服从行政优益权,必然享有财务平衡的权利。参照下述“王子行为”与“情势变更”等相对人具体保护制度的适用效果也是要将已被打破的合同经济重新回复到财务平衡的状态,我们甚至可以从补偿原因角度将“财务平衡”重新命名为“行政优益权”以丰富和充实后者的法定内涵。(9)由于判例解读和理论归纳广泛来自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概念术语命名呈多样性。本文参照主流学者观点将财务平衡与王子行为、情势变更、不可抗力作为四种平行的政府补偿理论加以阐释,但仍需提请注意,前者的命名指向补偿效果,后三者的命名却指向了补偿原因——但补偿效果却仍旧是“财务平衡”。总而言之,财务平衡原则是法国行政合同制度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法定或意定苛责事由时,必须适用的一条基本履行原则。
二、公法上的“王子行为”
法国法上的王子行为(le fait du prince)理论源于私法合同法,系指由公共机关做出的、合同当事人缔约时无法预见的、当下亦不能避免的、足以造成债务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的行政行为。它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也包括抽象行政行为。(10)如行政机关发布政令导致合同正常履行受阻。作为不可抗力的主要情形之一,王子行为在私法合同法中是一项无可争议的法定免责事由。(11)法国旧《民法典》1148条,新《民法典》1218条。然而在行政合同制度中,王子行为被行政法官与公法学者们赋予了更多的内涵。
首先,王子行为依然针对合同履行受其影响而言,也依然是指公共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但不是任何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都足以构成公法上的王子行为。判例显示,如果行为主体是受影响合同的行政缔约方以外的其他行政主体,最高行政法院拒绝适用王子行为理论对相对人进行损失补偿。(12)CE,20 octobre 1971;CE,29 décmbre,1997,本案中最高行政法院拒绝适用王子行为理论,认为国家虽为行政合同当事人,却不是造成合同履行干扰事由的《城市规划法规》的制定者。换言之,只有合同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才“可能”被司法认定为王子行为,即王子行为的适格主体只能是合同行政主体。
其次,王子行为虽然必须是合同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但其直接指向的对象却不能是该行政合同事项本身。它只能是出于行政职能需要,行政主体对其他事项做出的行政行为影响了该行政合同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多为发布政令等规范性文件等单方行政行为。[4]262因此,它区别于合同行政主体出于公共服务需要,无论有无约定均可直接对合同内容进行的单方干预,即行使行政优益权的行为。
最后,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合法有效,即内容上和程序上都不得被司法评价为违法或越权等无效行政行为。唯有如此,相对人才能援引王子行为理论向行政行为主体——同时也是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主张补偿全部损失。(13)否则可直接依公法进路就违法行为或越权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主张行政赔偿。
例如,某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合同授权某公交公司特许经营当地公交运营服务,嗣后,(1)该地方政府要求公交公司更改运行路线、增加运营车辆,由此直接加重了相对人的义务负担,此时构成优益权——单方修改权——的行使,地方政府必须根据财务平衡原则进行全部损失补偿(14)CE 21 mars1910 Compagn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de tramways,Rec.p.216.;或(2)该地方政府出于公共服务需要行使警察权在一定区域内设立通行禁止,由此间接导致公交运营负担加重,则足以构成公法上的王子行为,相对人有权据此主张全部损失补偿(15)CE 4 mars 1949,Ville de Toulon,Rec.p.197.;甚至(3)行使警察权创立通行禁止的是国家中央政府,则进一步涉及公法上的情势变更规则。(16)CE 15 juillet 1949,Ville d’Elbeuf,Rec.p.358.
出于公共服务的持续性要求,公法中的王子行为不再作为当事人义务法定解除的不可抗力:如果王子行为对合同造成的影响是履行成本增加,则相对人必须继续维持义务履行;如果影响是部分履行不能,则相对人只能遵照此种禁止对义务履行的方式和内容进行调适和改变;如果影响是全部履行不能,此时相对人得主张合同终止。(17)此时全部履行不能是否构成公法上的不可抗力尚存争论。单从补偿效果看,虽然都是财务平衡原则的具体适用,但依“王子行为”理论补偿的范围往往大于依不可抗力补偿的范围。但无论何种情况,只要合同行政主体的合同外行政行为导致合同相对人履行成本增加或预期利益减少,后者均有权依据“王子行为”理论要求行政主体给予全部损失补偿。这种行政主体必须维持合同相对人“期望获得的利益”与“额外增加的负担”之间的经济平衡的客观效果,本质上也是“财务平衡”原则的具体落实。(18)但主流学者们依然严格区分财务平衡与王子行为,认为是不同的行政合同相对人补偿规则。
由此可见,王子行为的核心价值是要平衡合同行政主体的非合同行政行为。在一个行政合同关系中,如果说财务平衡是针对行政主体对合同事项本身行使优益权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那么王子行为就是针对行政主体合同事项之外的其他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两种补偿理论双管齐下,有力地调节了合同双方责任承担的风险分配。行政主体无论是合同行为还是非合同行为都被法律预设了相当的成本付出,相对人的合理预期也有了更为周全的保障。而且,行政补偿的效果旨在重新恢复合同的经济平衡,因而也有效贯彻了财务平衡原则,既有利于行政权行使、实现公共服务职能,也有利于维护合同相对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
值得讨论的是,这种损失补偿的性质是否应理解为合同责任?(19)CAA Paris,23 juillet 1991,Société COFIROUTE,n 89PA01566.本案中,法官将王子行为理论下的行政补偿解释为行政主体承担合同责任(即中国法语境下的违约责任),引起学界讨论。诚然,王子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合同行政主体的行为干涉了合同正常履行并造成了相对人损失。但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并非遵循完全相同的理论基础与分析进路:前者一般基于违法、越权、不符比例(原则),以及无法苛责时兜底的职能责任;后者一般依据违约、侵权,以及归责原则上的过错责任为主。与中国合同法归责原则上采严格责任不同,法国《民法典》规定私法合同归责依然以过错责任为主,完全无过错的合同当事人完全免责。而如前所述,王子行为与“违法”“越权”“不符比例”等情形不同,属于无法苛责的行政职能正常行使行为,无法被解释为是行政主体的“过错”。(20)关于国家与行政主体等公法主体的“过错”问题,法国大革命前坚信“国王不能为非”而主张无责任政府;大革命后,随着国家赔偿理论的繁荣,法国逐步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行政赔偿制度。较为主流的学说/制度包括行政法治、越权无效、比例原则、行政风险理论、公共分摊理论等。但无论依据何种理论学说,公法责任都不是基于私法债法上的“过错”导致,因此极少有诸如“行政违约”与“行政侵权”的表述。因此,此时的补偿只能被看作是一种不基于过错责任理论的、公法上的行政职能责任。
三、公法上的“情势变更”
王子行为理论排除了合同行政主体以外的其他行政主体的行为。而在实际生活中,对行政合同履行的干涉却往往来自其他行政主体、立法机构等第三方。此类事项对合同主体而言属于“风险”范畴,其发生完全独立于当事人行为与意图之外。由此造成合同相对人损失的,适用法国行政合同法的原创规则:情势变更(l’imprévis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波动,波尔多市煤炭价格比战前上涨五倍,彼时以煤气为能源的公共照明公司损失巨大。波尔多市政府不愿意补偿照明公司承受的巨大损失,还以特许经营行政合同合法有效为由,要求后者继续提供公共照明服务。照明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案件最后诉至最高行政法院,经过综合考量,最高行政法院并未采纳各方当事人诉求,而是自主创设了全新的“情势变更”理论,判决政府补偿照明公司的大部分损失,后者继续提供公共照明服务,以满足公共服务的持续性要求。这就是著名的“波尔多煤气案”(21)CE,30 mars 1916,Gaz de Bordeaux.。自此以后,情势变更理论在行政司法上得到广泛适用,范围也从特许合同扩展到一般行政合同,特别是政府采购合同领域。
依据情势变更理论的构成要件,变更的“情势”应为:(1)合同缔结时,各方当事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无法合理预见的异常风险;它有别于合同当事人必须承担的合同本身的正常风险。后者是合同主体根据其身份、经验、专业与信息等能够综合预料到的、合理范围内的输赢赚赔经济风险。(2)发生于当下,亦非各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甚至有意为之。如果是合同行政主体所为,要么归于优益权行使,要么归于王子行为,甚至可能是违法或越权的无效行政行为,都无法适用情势变更。(3)对合同的影响必须彻底,无论依据何种计算方法都造成履行成本大幅增加要求相对人继续履行会彻底破坏财务平衡的程度。如果只是一般波动,则只能由合同相对人自行承担。由此可见,并非任何程度的风险都足以构成情势变更,只有在合同经济平衡已被彻底打破的异常风险面前,相对人才能主张情势变更理论获得行政补偿。[4]246[5]656
由此可见,只有内容上一锤定音的不可磋商合同才可能因其不能适应重大情势变化,而需要适用情势变更理论来重新分配风险损失。由于《1974年11月20日通知》明确政府采购合同的行政主体必须补偿相对人因情势变更遭受的损失,大量诉讼纷至沓来。面对数额纠纷,司法机关还需结合各方当事人意见自主判定具体金额,原则上行政主体承担90%。(22)根据Laurent CHAPUS教授总结甚至可能高达90%~95%。目前,根据ROCHER教授评述,“鉴于判决作出的社会背景,今天的相对人要依据情势变更理论获得补偿非常困难”[4]248。显然,随着合同缔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政合同,特别是政府采购合同,开始广泛采用“浮动计价条款”和“定期更正条款”以控制双方当事人预期之外的风险。[6]15一旦当事人有了类似约定,嗣后就不得再主张适用情势变更理论获得损失补偿。[4]426因此,随着风险变得越来越可控(23)如国际商会发布的情势变更示范条款(clause modèle de hardship de ICC)。,近年来行政司法实践中相对人主张情势变更理论获得补偿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公法上的情势变更制度建立在公共服务的持续性原则之上。[1]即使变更之情势造成合同履行异常困难或代价过大,只要尚未达到履行不能的程度,同王子行为理论类似,合同相对人也得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以保证不间断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对行政主体而言,新情势下行政合同继续履行成本往往低于解约再重新缔约的成本,解约不必然是经济上的最优选项。此时行政法官适用情势变更理论主动调整合同经济均衡,维护合同继续履行。同时,相对人本质上被视作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辅助人,真正的组织者和最后的保证人是肩负此种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因而具体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不能归咎于双方当事人的风险损失,相对人只需承担缔约时合理预期内的正常部分即可,余下的都必须由政府基于职能责任亲自承担。(24)CE.4 mai 1949,Ville de Toulon,Rec.197.同前述王子行为理论类似,这依然是公法视角下、行政合同财务平衡原则所代表的、公法上的“合同公平”。
显而易见,依公法合同情势变更理论要求行政补偿,并非要求行政主体承担合同责任,也与损害赔偿无关,因为它根本不涉及各方当事人行为。换言之,情势变更理论仅针对重大异常风险,即那些不能归咎于当事人、造成了合同履行严重困难的意外法律事实。此外,无论新情势是暂时的还是彻底的,只要履行遭受影响、合同严重失衡,相对人都可以主张情势变更理论获得行政补偿。此时行政法官对行政合同的内容变更与行政补偿的数额计算都必须视具体情况具体判断,并在判决中做出充分合理的论证。
除此之外,行政合同判例法上还存在一种特别适用于公共工程合同的类似风险补偿理论——“意外限制”(25)CE,30 juillet 2003, Commune de LENS, n° 223445.本案提出了公共工程“意外困难”的构成要件:(1)合同履行时遭遇了实质困难;(2)是合同缔结时不可预见的例外情况;(3)由合同当事人之外的原因造成。,意指公共工程合同缔结之时,虽然双方都已秉持诚信原则进行了充分的信息调研与能力评估,但实际施工过程中依然遭遇了意外困难,尤其是技术壁垒。它可能是施工难度异常、技术限制(26)CE, 7e et 5e sous-sections réunies, le 30 juillet 2003,n° 223445; 旧《公共采购法典》第19条。,或发生新情况造成实质履行困难——如发现地下结构不宜施工(27)CE,1/4 SSR,le 30 juin 1976,n° 96266.,或持续恶劣天气无法施工(28)CE,13 mai 1987,Soc.Citra-France,Rec.t.821.,这都让相对人债务履行负担大幅增加。此种“意外限制”一旦出现,除非满足下述不可抗力构成要件导致合同解除,相对人都必须在公共服务持续性要求下克服或规避困难,继续履行公共工程合同;同时有权根据本理论要求行政主体增加工程造价,补偿意外损失。而且,不同于情势变更的补偿范围,此时行政主体必须承担公共工程施工合同的全部风险,即全额补偿相对人的额外支出。判例明确这是一种“合同外责任”。(29)CAA Paris,le 20 juin 1991,Société AQUITECH,n° 89PA01543.即中国法语境下的“非违约责任”。究其原因,大抵在于建设工程合同带有加工承揽合同性质。而参照法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加工承揽合同中定做人承担全部风险,承揽人只承担过错责任,即不因承揽事务在无过错时遭受意外损失。(30)法国旧《民法典》第1787条、第1788条,与第1792条第2款。
四、公法上的“不可抗力”
与私法合同制度类似,不可抗力在公法中也是法定合同解除(31)由于行政合同多为持续性履行合同,公法不可抗力下的合同解除主要指合同终止(résiliation),即效力面向将来丧失,不溯及既往亦不涉及已履行之返还。事由。(32)参见法国旧《民法典》第 1148条。但在公共服务持续性要求下,行政合同基本不得解除,于是行政法官便将公法上的不可抗力进行了最狭义的解释和最谨慎的适用。由此,在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除了仅适用于公共工程领域的“意外限制”理论,同样是风险,同样是意外之情势:(1)那些时间上临时的、程度上非绝对的、严重性仍然可以克服和修复的情况,秉承公共服务持续性原则,一般适用情势变更理论补偿损失,合同在经济重新平衡后继续履行;(2)那些时间上永久的、程度上绝对的、严重性不能避免也无法克服的情况,造成合同事实上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经济再难恢复平衡[7]184,或者继续履行成本畸高、已经超出解约补偿和重新缔约的成本之和(33)学者们对公法上的不可抗力构成要件做了细致而周密的总结与讨论。但由于判例造法,行政法官们实质上掌握着最终决定权与解释权,因而实践中不得不考虑可量化的经济学成本分析,以便将政府支出所代表的公共财政损失降至最低。,此时才可能被行政法官判定为不可抗力要件满足,合同才得以终止。[4]250[5]1211
在1932年瑟堡轻轨案中(34)CE,9 décembre 1932,Compagnie des Tramways de Cherbourg,Rec.1050.,通过特许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轻轨公司负责提供公共交通服务并获得了自由定价权。嗣后随着电力新能源的应用与电费高昂,票价上涨已达极限,轻轨公司仍然欠下大量电费。政府以已授予自由定价权为由拒绝补偿损失。行政法官认为,政府不能因已授予自由定价权而免除其在情势变更时的损失补偿义务;而且,本案电力代替煤炭和高昂的电费已经“绝对地”改变了合同履行的经济环境,即使合同仍能履行,实则已经构成不可抗力,因此判定合同终止;同时,政府必须基于其公共服务职能主体的身份,依照情势变更的标准,补偿相对人从意外情势开始到合同解除之时承担的、超出合理预期的额外费用。
在2000年的Staffelfelden自来水案中(35)CE,14 juin 2000,Commune de Staffelfelden,Rec.227.,水源意外遭受严重化学污染,自来水公司不得不从更远的其他水源取水,尽力满足该市供水公共服务的持续性要求。由此成本增加三倍,政府拒绝补偿特许合同相对人的意外损失。行政法官认为,水源的严重污染短期内无法消除,即使自来水公司能利用其他水源勉强保持供给,但已不是原特许合同的缔结条件,因此已经构成不可抗力,合同应该终止,相对人供水义务解除。但政府仍需补偿从水源污染开始到合同解除之时自来水公司新水源取水所承担的意外支出。
由此可见,公法上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同适用效果与私法规则也不尽相同。首先,它并不强调意外困难无法克服、合同已达履行不能。判例只要求“彻底”“绝对”“永久”的改变,且未涉及暂时不可抗力之情形。(36)如CISG79条第3款,法国新《民法典》1218条之规定。其次,合同终止后的利益调整适用公法上的财务平衡原则,即依据不可抗力终止合同时双方主体义务随之解除,但相对人在合同终止之前遭受的意外损失,行政主体仍需基于公共服务主体的职能身份,比照情势变更理论补偿绝大部分。最后,笔者注意到,无论判例如何论证,公法上的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行政法官权限巨大,完全可以依据具体情况自行选择适用。
例如波尔多煤气一案,战争使得照明原料煤炭价格上涨五倍,法院判令政府偿还照明公司损失、公共照明合同继续履行——适用情势变更理论;法院也完全有理由判定合同解除,因为战争导致履行障碍是最少争议也最常引用的不可抗力之一,煤炭价格因战争上涨五倍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经济背景。如果适用不可抗力解除合同,政府也可以在新的煤炭价格下另觅其他有相关资质的公司(甚至与原公司、原班人马)重新签订公共照明服务合同,只要经济上更为合理。(37)囿于篇幅,此处只作理论上的比较与讨论,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采取私法中尚未承认的情势变更理论要求政府补偿损失已是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们的一次大胆创举。
再如瑟堡轻轨一案,电力代替煤气投入城市轻轨运营造成了能源成本的巨额增加,虽然彻底改变了轻轨公司履行公交服务合同的经济背景,法官判定不可抗力终止合同之后,政府重新组织公共交通服务——城市轻轨依然使用电力,还是要缴纳巨额电费——经济环境已然如此,也许行政成本更高、效率更低。因此法官也可以判定为适用情势变更理论,城市轻轨服务合同继续,政府补偿轻轨公司的绝大部分损失。
又如Staffelfelden自来水一案,原来的水源虽然遭到彻底污染,但城市供水服务并非完全不能维持。如果自来水公司额外增加的三倍成本低于合同终止后政府重新组织供水服务需要付出的成本,相较之下,维持合同继续履行才是经济上的理性选择。在此前提下,本案法官也可能适用情势变更理论,判决政府分担自来水公司的绝大部分损失,以保证其继续提供城市供水服务。[8]137
由此可见,行政合同中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的识别,理论上虽然遵从学者们从判例中提炼的“不可抵抗”“彻底的”“永久的”等标准,但本质上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面对超常风险带来的意外损害时,只有行政法官拥有足够权限来具体分析和判断,哪些情况适用情势变更维持合同继续履行,什么时候适用不可抗力终止合同。但无论做出何种判决,基于财务平衡原则与公共服务职能,合同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损失补偿必不可少。
五、结论
综上所述,法国绝对的司法二元主义成就了其独特的行政合同制度。公、私法分立的语境下,行政合同本质上从未被视作一种所谓的“公法之债”,完全超越了私法合同制度的债权、债务阐释模式,救济上也不遵循私法债法中的违约、侵权制度。在保留优益权这一行政裁量权以保障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公法学家们从公法理论、制度本身出发,创设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合同相对人保护制度。大量借鉴私法合同的规则、制度,历经行政法官与行政法学者的阐释与重构,在公法领域亦被重新赋予了特殊的意涵,从而成为有别于私法的公法规则。即使近年来受欧盟统一法制进程影响,法国行政合同制度也从未丧失其独立性,甚至积极寻求以其特色制度影响欧盟立法。
司法实践中,由行政合同引起的争议类型纷繁复杂,但所有行政行为都必须经得起合法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检验。本质上,是否违法(广义)、越权,是“行政行为”与“法(广义)”“权限”之间的相对关系。但在无法直接适用私法违约责任制度的行政合同关系中(38)鉴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必须讨论归责原则,而公法语境下是否仍有讨论“过错”或“无过错”的必要与价值?于此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论述。,行政行为因“合法”“合比例”而不具法律苛责性,尚不足以保障本质上只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辅助人的合同相对人的合法合理权益。本质上,它是相对人“为公益损失的私益”与合同行政方“公共服务职能责任”之间的相对关系。[9]这与行政行为的性质,甚至与行政行为本身无甚关联。正是有了这一套公法特殊保护制度,即使不适用私法责任,合同行政方仍然必须依照财务平衡原则的要求补偿相对人非因自身原因造成的意外损失。
一言以蔽之,在保留优益权的法国行政合同制度中,相对人权益受到行政法一般规则与行政合同法特有制度的双重保护。这不仅与私法合同理论、制度不甚相关,甚至与公法普适的赔偿理论、制度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在大陆法系公、私法二元分立语境下,中国行政合同研究者与立法者如希望继续保留行政优益权,则应尝试改变现有的研究范式。大量精力如果继续倾注在诸如“行政侵权”“行政违约”甚至“行政之债”等完全寄生于私法债法制度的范畴研究上,必然会导致“旷日持久的争论给行政契约留下的太多皱褶”继续“怎么努力也烫抚不平”[10],甚至会造成一代公法学者辛勤耕耘而来的行政合同独立性逐渐丧失,最终真有沦为“伪命题”之虞的严重后果。有鉴于此,在优益权模式下,本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着重讨论如何创设一套公法上的合同相对人特殊保护制度。只有从公法原理、公法视角出发,在充分结合中国行政法既有救济制度的基础上,参考私法债法相关规则[9],以一套公法自有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规则体系重新阐释与构建公法上的合同制度,我们才能最终探索出一套既有利于政府公共服务与行政效率,也能充分有效保障相对人合法合理权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行政协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