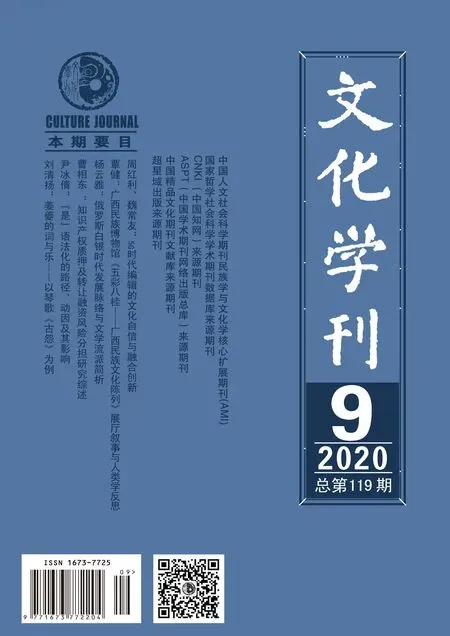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网络狂欢”
胡 鑫
一、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到“网络狂欢”的思考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的俄罗斯电影《西伯利亚的理发师》里,有一幕令人记忆深刻。在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节日“谢肉节”中,平日里威严的将军在狂饮后野蛮地咬碎酒杯,在众人狂笑和呼喊中追赶扮演拿破仑的小孩,忘我地挥舞火把并点燃舞台,绘就了一幅在冰天雪地的寒带风光中,人们肆意欢呼、赤膊混战、狂吃豪饮,灵魂在雪地间炽热翻滚的图景。短暂的狂欢节欢愉中,人的阶级地位或日常生活身份几乎无从显现,每个人都能成为任何活动的参与者,快速完成角色的切换。
电影里狂欢的感官感受与精神更新,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里有更加深刻全面的阐释。狂欢化理论主要来源于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理念,并演变为两种不同的狂欢层面,前者是身体的释放和狂欢,后者是精神的更新和宗教式的狂欢。
在以教会为权威的中世纪,社会等级森严,戒律严明,人需要小心翼翼地按照既有规范活动,难以脱逃日常生活的藩篱。暗灰的第一生活底色里,狂欢节作为火光似的亮色,使得人们有机会第一生活之外的生命体验,也就是第二生活。在第二生活里,人们在现实世界里的身份角色、阶级地位等日常都突然消解,取而代之是身体和精神的崭新建构,出格的举动可以被欢呼和认可。如巴赫金所言:“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的再生和更新。”[1]人们暂时遗忘了日常生活的身份、地位等,跳脱到另一种崭新的自我存在中,进行自我的创造和认同。
所有人在一个平等的广场上,纵情宣泄和设定自我,无需在脑袋里进行程式化的考虑与抉择。从头至尾都是对崭新自我的觉察和展现,现时的新生与历史的消亡同时发生,自在的哭与自在的笑具有同样自由的精神内核。“自由在笑”是巴赫金从自由意义上概括的一个重要主题,“它的特性在于‘与自由不可分离的和本质的联系’,它显示了人们从道德律令和本能欲望的紧张对峙中所获得的自由”[2]。这样一个肆意的广场空间,使我们联想到网络。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人介入网络空间十分便捷,成本也低廉,每个人都可以非常迅速地打开这样一个脱去现实触感的平面出口。
二、“狂欢化”特征在当代“网络狂欢”中的呈现
网络传播方式的普及和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已经使它成为十分大众化的体验。无论身处都市还是偏远的小镇,无论是何种身份地位,人人都可以依靠镜头与麦克风,在网络空间中呈现自我。人们可以通过鼠标和键盘,在无数区域内进行自我的建构。这种人与人的互动十分容易和开放,免除了日常现实中自我身份或角色的约束,现实中很难有交集的人可以彼此进行对话、角色的互换和重建。
(一)网络的狂欢化空间
每个人自出生就拥有身份角色,在社会中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定与准则,很难承担逾越日常的代价。而在网络中,人有更大的自由来对操控自我要建立的角色或话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出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相较于日常生活,传播的中心感弱化,言语的表达和传递更为简单快捷。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大多数人是单向度的接受媒体过滤的信息,交流反馈的成本较高,受众和媒介之间的地位固定而鲜明。自媒体的产生极大冲击了传统媒体,人们可以开通公众号,公众号并非官方独有,官方或个人都可以采取同样的传播方式表达观点。网络直播更是消解了其中的界限,平民也可以获得数万人的注视,进而构建自己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角色。
狂欢化的广场舞台上,演员和观众并不是固定的身份,体制或环境中的固有身份界定在这里得到了消弭,不再有明确的区分。人们可以主动地参与其中,而不再是被动地或是放在既定框架中的消极客体。
(二)网络的狂欢化语言
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更加实际的面对与联系都使得话语本身受限。巴赫金强调了狂欢的仪式中面具的必要性,面具使得参与者成为异名者或匿名者。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各种角色,恣意建造自己的人格,以这种语言来布置自己的场景。
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物理属性,网络使得各种感受趋向于平面化。尽管未来可能会出现如电影《头号玩家》中的触感外衣,使得游戏等系统中的受伤、绝杀等触感更接近于实际体验,但这无法抹除特定语言对于用户感受的加持。相同的游戏、论坛或各种平台系统都构成了独特的圈子,进而发展成圈子文化,而群体共通的语言或符号便是形成文化的标志因素。
弹幕作为一种新的匿名形式,使影像的制作完成并不再是其诠释的终点,而是参与到了一场语言的狂欢中。例如一些直播形式,其中的重头戏并不只是主播本身,一样重要的还有弹幕。弹幕作为另一种网络话语方式的实践形式,即时性和同时性使其话语的建构与作品本身获得了持续的建构和更新。每个观众都可参与到弹幕中,每个弹幕又都与视频共同构成了新的存在形式,输出和影响着播放者本身。借助弹幕这种语言形式,人们嬉戏玩笑或模仿讽刺,使得影像最终不仅仅是创作者的原始输出,而是创作者与观众共同参与的文化缔造。作品由以前的封闭变为敞开,弹幕以松散的只言片语参与其中,观众也不再是沉默地面对单纯的成品本身。
三、“网络狂欢”与“狂欢化”的本质区别
与单向度的网络狂欢不同,巴赫金“狂欢化”非常强调脱去现世的外衣后,自我精神在释放中所得到的更新与再生。人在狂欢体验中暂时避开了现世的约束,并且体验本身与现世并不分离,而是给人以新生的生命力量。或者至少,现世中阶级感或是身份感的压迫紧张,会在狂欢后得到实在的松弛。
而大众的狂欢很多时候只是精神的松弛与感官的片刻愉悦,是在文化产业下的一种消费与狂欢。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重生和更替在这里并不重要,大众甚至只是消费主义或符号价值的追随者,得到的只是在这样的追逐中获得的片刻满足,精神的独立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发无聊与寻找快乐。
法兰克福学派所言的“文化工业”等正是这样乘虚而入[3],想方设法以各种载体形式或营销方式,找到大众的“嗨点”或“痛点”,以赢利为目的尽可能获得大的流量和关注度。沉浸在轻松和快乐的氛围中,人们得到了时间的消遣,让位于严肃和深刻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各种罪恶的娱乐机器以法西斯式的侵占来渗透意识形态,自我持存的理性与精神自由的放置也变得愈加困难。
四、对网络“狂欢世界”的反思
福柯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话语关系,话语不再是表情达意的符号,而是有着自身的规则,用以建立秩序及言说之物的界限[4]。由于社会既有的秩序和体制,人们因地位不同而分,有了不同的话语权。大多数人只是作为普通的受众,很难将声音传播出去。决定权总是掌握在拥有更多资源的人的手里,他们决定着市场的导向,甚至作为媒体的过滤器和发出器,控制着话语的输出与导向的建构。自媒体等网络平台的产生,使人们可以自发为自己搭建各种舞台,进行自己的文化生产。
弗罗姆曾说:“唯独当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时,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力才有意义。”[5]网络平台的话语权门槛降低的同时,意味着质量的危险与有目的闯入和操纵的便捷。比如网络直播的丑闻、小型平台对于谣言的传播和对大众的误导,充满了各种不良价值导向传播的危险。故而,在敞开的网络空间中,如果只是单纯沉溺于其中的开放式的话语狂欢,那终究是空虚和虚弱的。在网络狂欢中,没有思考所介入的自由是丧失意义的,这种自由下的人终究还是被动者,偏离了狂欢化理论的初衷,这也是巴赫金谈及民间狂欢时所表达的,对于民间化的狂欢仪式逐渐狭窄化、贫瘠化和庸俗化的担忧。
同时,所谓的“狂欢化”只是作为一种体验为日常生活做补充。狂欢化理论的流行很大程度也得益于现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心理,它们为此提供了良性的土壤。不可否认,这种狂欢将人类从现世的无奈与纷繁中脱身而出,获得了精神的释放与社会压迫感的消解。但这种狂欢化常常还是与现实分割,无法实在解决现实问题。
故而,尽管网络所带来的大众狂欢化有其意义价值,但缺乏反思能力与自由精神的人,终究不能在这场狂欢中得到自我的更替与再生,只是疲于逃避,甚至再度被操纵。只有在这个敞开的平等的空间内掌握真正话语权并沉淀出思想的人,才能够在其中找到平衡。同时,这些在网络中获得自我更替与精神新生的人,是良性运转的网络狂欢中真正需要并反过来能够推动其建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