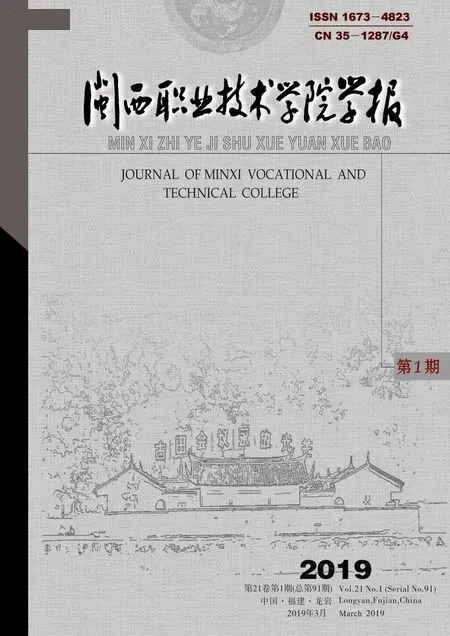《心灵外史》的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思考
汪晓雅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石一枫是近年来暂露头角的优秀小说家,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感,题材广泛,叙事语言风趣幽默。出版于2016年1月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是他创作的一个巨大转折,石一枫一改之前小说中的“犬儒主义”和插科打诨的心态,更加果敢地挖掘作品的深度和主题意义。发表于2017年《收获》第三期的《心灵外史》是石一枫继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之后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心灵外史》绝不是对生活的简单观察和描摹,而是对生活的思考和关照,而这种用心关照和思考主要体现在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思考这两个方面。
一、作家的人文关怀
童庆炳说:“文学家是专门在人的情感生活中耕耘的人,人文关怀是他们的基本‘地盘’。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都毫无例外具有悲天悯人的品格的原因。”[1]《心灵外史》这部小说也不例外,小说戏谑并带有痞气的语言风格,并无法掩盖作家石一枫对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角色都投以极大的人文关怀。
一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非常重要,往往彰显作家的创作意图和重点。《心灵外史》的开头直接写“大姨妈”的故事,结尾最后一句写“对了,我的大姨妈,她叫王春娥”[2],可以看出,石一枫的创作重点在人物身上。“大姨妈”一生的经历和遭遇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感到可悲。她的一生都在为自己身上的罪而忏悔并试图赎罪。但是又囿于其自身的缺陷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她的赎罪之路屡试屡败,最终走向自我灭亡。对于作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这种典型女性的情感生活和人性的变化,从中书写人物命运的悲剧,体现作家的人文关怀。
“大姨妈”的赎罪之路源于“文革”期间揭发杨麦母亲藏着姥爷手稿这一事件,由于揭发而致使杨麦母亲被流放西北,因此而带来的愧疚感让“大姨妈”走上了漫漫的忏悔长路。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大姨妈”相信“革命”是正确的,她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认为杨麦母亲将手稿藏在柴房里这一行为是破坏“革命”,这种认识是她建立在“革命好,为我好,为所有人好”这种信仰上而形成的,并不是为了她个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不检举这件事,那么她就是“革命的罪人”。王达敏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原罪”的背景,但是中国文学并不是没有忏悔文学,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忏悔意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所谓原罪,多指极左年代由阶级论及暴力政治强加于人的一种‘无罪之罪’”[3]。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亲密朋友之间互相检举的情况很平常,小说中杨麦母亲关于为什么没有因为被揭发而恨过 “大姨妈”,有这么一番自述:“多简单啊,那年头人人都这样过。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的多了,你姥爷就是被跟他一起赏菊花吃螃蟹的人举报的。他被定了性以后,我也必须表态和他划清界限”[2]。但是“大姨妈”并没有将她的罪归结于时代,而是自我反思,她主动插队下放到河南农村,作为她赎罪的方式:她以为自己主动下放,就算是对杨麦母亲最好的补偿。“大姨妈”自身想法过于狭隘,无法看穿这种相互检举的背后,其实是人们在极左年代残酷的阶级斗争下,为了生存而被迫作出的决定。因此,“大姨妈”走不出自己内心的“灵魂法庭”,心中的愧疚感和自我耻辱感无法使其获得人生的超脱,以及人性的新生。
“大姨妈”因为无法怀孕而沉迷于练气功,没有练出来孩子也练跑了丈夫,人生重大失败后的迷惘与困顿让她陷入传销组织“虫宝宝”而无法自拔,以为自己在这份事业中获得了成功。又因为对杨麦母亲的愧疚,热心地将杨麦母亲和杨麦都拉进这个荒唐的致富之路。最后在杨麦的帮助之下,“大姨妈”意识到所谓的公司项目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之后,她的精神世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她以为的“好心”差点让杨麦被害死,也让杨麦母亲失去10万元的全部财产。“大姨妈”的一生忙忙碌碌,为了让自己好也让别人好,总想弥补因为她而受到伤害的杨麦、杨麦母亲以及她的丈夫,反过来却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所谓的“革命、气功和虫宝宝”事件,她也怀疑过,但是由于其自身认识的缺陷,以及悲剧生活给她带来的苦痛和自责让她不敢质疑,因此她无法从一个个显而易见的骗局中走出来。“我觉得只要信了他们,就能摆脱世上的一切苦——生不出孩子,被男人揍,觉得自己没用……他们那些人对我说。信了吧,信了吧,这其实并不足以说服我,但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也在说,信了吧,信了吧,信了就能越过越好。一到这时候,我就顶不住了……”[2]最后处于心灵崩溃边缘的“大姨妈”和矿区中生活同样分崩离析的刘有光等信众一同烧炭自杀了。
石一枫专注于书写 “大姨妈”的悲剧命运。“大姨妈”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罪,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赎罪,整部小说就是“大姨妈”走向灭亡的忏悔之旅。“大姨妈”只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圈子里,心怀忏悔意识生活在痛苦里,即使已经得到杨麦和杨麦母亲的原谅而不自知,最终还是走不出她给自己画的牢笼。
正如孟繁华所言 “当下许多作家都在积极面对道德重建这一精神难题。道德困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困境”[4]。石一枫的人文关怀也不只是落在“大姨妈”这一个角色身上,石一枫关注到小说中每一个角色的精神困境,书写每个人物命运的悲剧。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自己的心灵困境所压迫,都有自己隐藏起来的痛苦。小说中作家安排了一个很巧妙的情节映照作家的观点,杨麦的母亲在向杨麦控诉“大姨妈”是如何将她的10万元钱骗走的时候,他同母异父的妹妹出现在母亲背后说“有病,你们都有病”,结束了这一场控诉。
夸张一点说,小说里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杨麦母亲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和儿子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她的一生都带有受到“文革”运动迫害的阴影。杨麦的父母之间没有爱情,杨麦不被重视和疼爱,一直缺爱的杨麦一段时间受到“大姨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爱护。成年之后,杨麦的生活并不开心,在单位不温不火不受重视,做生意又失败。由于父母的不幸婚姻,杨麦不相信爱情和婚姻,流连于各个女性之间,最后却一直孤身一人。当儿时“大姨妈”带给他的温暖被唤醒,“大姨妈”式的照顾便成了杨麦的追求,他想要回到有“大姨妈”照顾、能够体会温暖的日子。这种过上正常人生活的愿望是人的最基本、最正常的需求,是人的人性所急需的,这正是作家所要表达的终极人文关怀。
二、面对现实的历史理性思考
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会驱使他关注社会、思考历史。《心灵外史》中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总是穿插在故事背景的叙述中,寥寥数笔却鲜明地表明作家的立场和看法。
从《心灵外史》的命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有关心灵与信仰的作品,小说所要透视的正是当时社会的信仰危机问题。很多像“大姨妈”那样无知而盲信的人都在寻求气功大师发功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都是生理上的病症,“大姨妈”希望大师可以解决她不孕的困扰以及“我”(杨麦)发育迟缓的问题,而得了冠心病、糖尿病和坐骨神经痛的病人们不去寻求正常的医疗手段,竟也寄希望于气功大师发功来帮助他们摆脱病魔。小说描写了信众们集体练功时的滑稽场面,“她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却不下地,而是盘起了双腿,腰背挺直……有规律地开始转动,上三下,下三下,左右各三下……”[2]而当气功大师因为要“攒着功力”去别处发功而使很多信徒没有获得大师 “授功”时的崩溃场面也让人忍俊不禁,“群众浩大地哭爹喊娘起来。那我的冠心病怎么办?还有我的坐骨神经痛。我可是重度糖尿病啊,重度的,撒尿都招蚂蚁了”[2]。作家对于这些盲目无知的信众,先是觉得滑稽可笑到可怜、悲悯,最后是质疑与思考。小说传达出作家对古今中外的怪力乱神在中国大行其道以及“不问鬼神问苍生”这种原本蕴含在我们民族骨子里面的信念流失的强烈不满,作家运用讽刺的手法将国人仍然处于混沌与迷茫的丑态尽情展现。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经历的是经济狂飙突进的时代,小说中的“我”(杨麦)在这种时代的影响下也经历了疯狂追逐金钱的阶段,“在既百无聊赖又声色犬马的日子里,我渐渐地混宽了腰围,也混成了某些圈子里的‘熟脸儿’,于是我开始尝试着做生意”[2]。杨麦在朋友“李无耻”的组织下,做起了“信仰生意”,他们开寺庙挣香火钱,不料庙里的主持因为贪婪敛财而触碰法律红线,因此变成经济犯罪嫌疑人,本来“德高望重”的高僧在佛教界变得臭名昭著,杨麦的“信仰生意”也因此赔得血本无归。作家借助小说主人公杨麦的经历向读者传递这样一种思考:国民群体无意识的盲信,并不是因为那些神棍的吹嘘和洗脑能力多么强大,而是经济至上原则带来人们心灵的异化,一些人抓住另一些人的弱点,通过编织美好的假象,创造一个个所谓的“教”,贪婪地敛财。
而当作家继续深入地观察和分析社会,作家发现人们的心态已经从盲信到无信最后发展为只畸形地信仰金钱。小说中关于传销的描写,十分贴近现实,许多人抱着发家致富的心态加入“虫宝宝”公司的传销活动,并被洗脑深陷其中,很多人为了奖金分红而失去理性,为了不让所谓的“奸细”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他们可以随意限制别人的自由,甚至杀人灭口。作家意识到小部分人因为狂热追逐金钱而失去理智还可以控制,但是如果社会的上层也犯这种错误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作家不仅将锐利的批判笔锋对准社会上唯利是图的一部分人,更勇敢地转向一些地方“带血GDP”政绩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度依靠透支自然资源来获得,环境污染成为人们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大姨妈”家住的村子变成了矿区,过度以及不当的开采方式使得这个地方的地下水受到污染,人们不断得怪病去世,最后村子变成鬼城一般的地方。但是当杨麦提出要去“大姨妈”住的村子看看的时候,警察却支支吾吾,并且这个村子竟然还被黑恶势力封锁起来。一些因为污染身患重病而没有及时撤出的村民,在这个布满密密麻麻白对联的鬼城苟活,而活下去的唯一支柱是一个双目失明叫刘有光的人带来的“福音”。最后因为矿区要被清空、拆迁,留守家园的七个村民被逼上绝路。这篇小说后面有一个附录,附录中大姨妈、刘有光和信众们烧煤气自杀了。一群信仰基督教的信徒,放弃所谓主的救赎,竟然自杀了。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不顾人的生存而大肆破坏环境,最后将在艰难中仍然苟活的人们也逼上自我灭绝的道路。石一枫把自己尖锐犀利的社会批判锋芒对准了“带血的GDP”。
石一枫面对国人的信仰危机,一步步抽丝剥茧,理性地分析社会问题,挖掘出中国社会深处的隐疾——金钱至上欲望下人性的扭曲,那些滑稽的盲信、亲情友情的冷漠以及社会的混乱等问题都是隐疾的社会表征。这也体现出作家在贴近现实的同时,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历史理性思考。
三、结语
《心灵外史》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而作。社会转型期千姿百态又充满变化的现实生活给文学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创作天地,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石一枫选择描写人物的情感生活和人性变化,思考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隐秘而又深刻的震荡。《心灵外史》展现了传统观念与现实生活、感性与理性的深刻相悖下,作家深刻的历史理性精神。2018年8月11日,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不仅证明了石一枫创作优秀小说的能力,而且说明作家如果沿着传统现实主义的道路进行创作,心中拥有人文关怀并对社会现实具有清醒的认识和思考,那么一定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