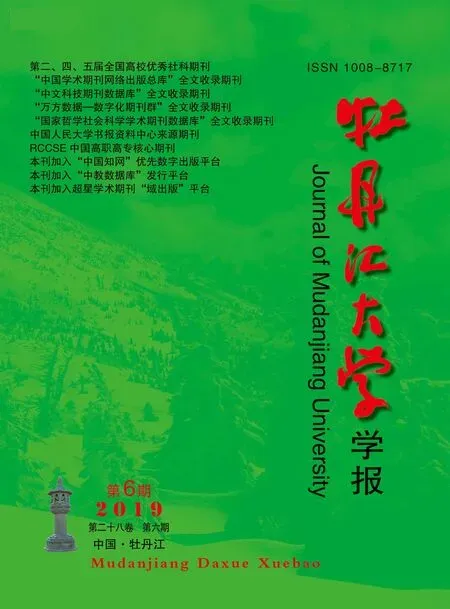执着的家园寻觅
——论刘庆邦的乡土小说创作
蒋 丽 云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广东 东莞 523960)
家园,泛指家庭或家乡,既包括物质层面的生存空间,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归属和情感归依。在乡土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始终是社会的基石,家园意识也是作家们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乡土中国急遽变迁,对乡土中国的重新审视,对精神家园的构建已成为当下中国作家的使命与担当,对于深切关注底层大众的农裔城籍作家刘庆邦而言,家园是他安放身心的地方,亦是他写作素材的来源,追问生命意义的原点。
一、追忆家园
刘庆邦的家乡在河南豫东平原,19年的生活经历早已让那里的草木亲情如血液般在记忆的血管里流淌,赋予了他长久的精神慰藉。在时代浪潮的席卷下,传统农耕文明逐步走向衰落,并艰难地完成着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蜕变中的家乡并不符合作家的理想,与许多乡土浪漫派作家一样,刘庆邦也是以深情的目光,回望的姿态表达着对美好故乡的依恋和传统价值的赞美,以记忆中的豫东家乡为蓝本,用温婉细腻的笔墨勾画出一个和谐宁静的乡土世界。
(一)说不尽的乡村诗意
1、谐美的生态景象
刘庆邦笔下多次呈现了悠远明净、令人神往的乡村自然风光,柳条摆动,麦苗起伏,花蕊微颤,春风捎香,《曲胡》中,寥寥数笔便为读者勾画出了一幅柔美温馨的乡村春景图。乡村的美好不仅在于风景的优美,更在于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和谐共生,万事万物都充满着灵性,无论是与梅妞心意相通的羊还是陪伴猜小成长的倭瓜,都被赋予了人性化的色彩。在这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里,人也保留着自然人性的淳朴坚韧,在小说《听戏》《响器》《遍地白花》中,戏、大笛、绘画等民间艺术焕发出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唤醒了姑姑、高妮、小扣子对艺术的执着,点燃了他们生命的激情,也使得平凡的底层生命氤氳着诗意。除了对艺术发自内心的追求,连日常循环往复的劳动也散发出生命的美感,《拾麦》中的方奶奶在土地和劳作中,方才体会到人生的价值与乐趣。《谁家的小姑娘》中,年纪尚小的改居然帮娘完成了颇费力气的攉水,扬洒的水花在阳光的投射下发出缤纷的七彩光芒,劳动的美感给生命增添了一抹亮色,自然与人性的纯美,构建出至情至美的浪漫家园。
2、淳朴的乡土人文
世代相沿的民风民俗凝聚着民间文化的基因,是解读乡民日常生活的密码,也是寄托思乡情怀的载体。刘庆邦的乡土小说生动刻画了故乡的人生仪礼、传统节日和世态人情,他笔下的民风民俗古朴悠远,洋溢着生命的诗情,宛若一幅幅乡情浓郁的民俗画卷,点缀着自然纯净的乡土世界。在乡村,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相应的民俗仪式,如青年男女结婚成家需历经相亲、相家、订亲、结婚、闹洞房、回门等一系列程序,相亲是择偶的主要方式,主角自然是男女双方,相家则是由女方父母出面帮女儿的婚姻把关,婚礼前亲朋好友需用“添箱”的方式表示心意,婚礼中最热闹的自然是闹洞房,而婚后回门新女婿总免不了受村人的取闹,每一个步骤都灌注了真情,牵动着心灵的波澜。死亡作为人生的落幕也需遵循丧葬礼俗,挑选小姑娘在死者的鞋上绣上菊花(《黄花绣》),请响器班子吹一吹(《响器》),长子需扛引魂幡,摔碎恼盆(《葬礼》),生老病死的人生仪礼,大多寄托了人们的美好祝愿,让底层生命的平凡生活充满了仪式感。传统节日也是乡民日常生活的一道亮光,每年三月三的庙会,集上商品琳琅满目,家家户户打扮一新,听大戏、看电影、观唢呐班子打比赛,热闹非凡,气象万千(《春天的仪式》)。过春节放大炮,闹元宵点花灯,还要蒸灯碗子,据说孩子若偷吃掉别人家的面灯,就会一辈子心明眼亮,失明的小连专门蒸好灯碗子,预备别的孩子来偷(《灯》)。古朴纯净的民风风俗中弥漫着朴实醇厚的人间烟火味儿,折射出乡土人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也营造了和谐有序的家园感。
(二)褪不去的悲凉底色
1、物质上的贫乏
透过回忆的面纱,刘庆邦略去了乡村生活的单调与无奈,倾情捕捉着日常生活的诗意,用审美的眼光描绘出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家园,但纵使经情感美化后的乡村也掩盖不了生活艰难的暗沉底色。喜如在地里扒红薯至忘我之境,但初衷只是想用卖红薯的钱买一条能为自己相亲增色的红围巾(《红围巾》)。改在攉水时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力气,惊喜背后却是无尽的苦涩:爹外出务工不幸身亡,娘已劳累至晕,不满周岁的弟弟饿得哇哇直哭,积水的玉米地急需抢救(《谁家的小姑娘》)。现实的艰难与心酸已然存在,只不过在回忆的净化下披上了一层诗意的外衣,从而淡化了现实困境带来的焦虑与苦涩。
2、精神上的未开化
传统的风俗在刘庆邦精致细腻的描述下涂上了诗意的色彩,别具一番风情,但透过这道理想折光,不难发现习俗约束下衍生出的诸多规矩对人的束缚,以传统婚俗为例,《春天的仪式》里,星采与“张庄那孩子”定亲已半年,仅在相亲时见过一面,因为“没有理由相见,找不到机会相见,也不敢相见”[1],只能在人头攒动的三月三庙会上苦苦寻觅,期待偷偷看上一眼。《夜色》中,定亲后的周文兴不舍得对象高玉华干脱坯泥这等重体力活,但是碍于规矩,只能趁着夜色偷偷替她翻坯,将自己柔软的关爱寄托在生硬的泥坯里。淳朴善良的青年男女满怀对爱情的憧憬,含蓄中不失热烈,相对于现代社会的速食爱情,却有一种美好,但传统的规矩也让这里的青年男女失去了爱情的自主权,但他们不会对被动的爱情婚姻进行抗争,甚至连一丝抱怨都不曾有过,因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早已在乡间深深扎根,身处其间也唯有认同后的顺从。受压制而不自觉何尝不是一种更深的悲哀,但乡村传统文化观念残酷的一面在刘庆邦的柔美小说中并未铺陈开去,只是作为低回的颤音暗藏在美好的乡村恋曲中。
二、直面家园
市场经济的席卷,现代文明的突进,使得乡土社会面临剧烈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土社会在走向脱贫致富,摆脱愚昧落后的历史进程中,昔日的生态家园、精神家园却遭致前所未有的侵害,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象已不再,乡村文化的美好习性不断丧失,乡土世界的宁静被无情打破。将关心民间疾苦视为作家良知所在的刘庆邦并未一直沉浸在记忆中的理想世界,而是又拿起现实主义的大笔,满怀忧患意识地关注着转型期乡土世界的现实境遇以及乡民们在时代变革下的痛苦与迷惘。
(一)回不去的故乡
1、凋敝的生态图景
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向前,并不断向农村进军,开发热潮随之而起,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开发掠夺资源,致使自然环境恶化严重,曾经的生态乐章俨然沦为生态悲歌。《红煤》中宛若世外桃源的红煤厂村在矿场的疯狂滥采下短短几年就变得满目疮痍,水位下降,树木枯死,地基下沉,古塔开裂,最终导致煤矿特大透水事件。传统的耕作方式也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大片土地被荒废,《摸刀》就叙述了一块肥沃土地七八年间的五段式变化:庄稼地、砖窑场、养鱼塘、垃圾坑、化粪池,读来令人痛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亲密走向疏离,乡里人不愿再“土地刨食”,将目光转向了土地以外的世界,外出打工成为潮流,以至于年轻小伙子要是呆在家里,村里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往日热闹的村庄转眼成为萧条的“空心村”,人们不再勤于耕作,而是将大把时间消耗在搓麻将等娱乐上。环境恶化,人气涣散,文化颓废,凋敝的乡村失去了往昔的诗意和魅力。
2、冷漠的现世人情
传统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无疑是熟人世界和谐交往的重要纽带,平日里,拜访问候,互赠礼物;他人遇事遭困时,则施与关怀,尽心帮助,亲如一家的乡土情谊便在礼尚往来中形成,然而城市文明的入侵、商品经济的渗透,使得质朴美好的人情观被侵蚀,温暖和谐的情感秩序被打破。《秋风秋水》的李开梅担心醉酒的丈夫失足坠河,想请管事的三叔帮忙打捞,不料三叔竟百般推诿,直到李开梅提及酬金,方才答应替她扒几网子,还不忘带上鱼篓子。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原有的同情心、同理心荡然无存,自私冷漠的金钱观消散了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助的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所剩无几,心灵的家园难觅踪迹。
3、失范的乡村秩序
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激发了乡民对金钱、权利、欲望的渴求,在城乡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传统乡村文化无声落败,淳朴的乡村伦理道德面临崩塌。《风中的竹林》中,朱连升以进城找了三回小姐为荣,百般炫耀,还在庄上卖起了性用具,方云中呼吁乡民抵制乱象,大家却反过来劝他跟紧形势转变观念,一气之下郁郁死去,更为讽刺的是,出殡之时女儿却用彩纸为他扎了三个小姐。基层干部也腐化堕落严重,《黄泥地》的方良俊不过当了芝麻大的官,就在当地威风八面,无恶不作。金钱开始成为政治的媒人,钱权勾结加剧,乡村权力趋于失衡,传统的乡村秩序濒于失范,和谐的乡村走向溃败。
(二)到不了的城市
1、都市里的异乡人
面对乡村的凋敝和城市的繁华,无数不甘于命运的农民告别乡土、涌入城市,试图开出一条新路,然而要想真正获得城市的认可又谈何容易呢。由于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知识能力有限,又缺少经济资源,只能居于城市的最底层,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活计,他们或是成为矿场煤窑里的走窑汉,终日在暗黑天地里顶着致命危险艰苦劳作,但在窑主眼里却是牟取利益的工具,毫无生命价值可言(《红煤》《福利》)。或是成为一名城市保姆,辛勤工作之余时常遭遇雇主的戒备与刁难(《说换就换》《后来者》),甚至遭遇男性雇主的性骚扰或侵害(《习惯》《找不着北》)。或是成为拾荒者,在城市楼群间四处扒垃圾、捡破烂,就连吃喝穿戴也大都取自垃圾(《到城里去》)。或是在诱惑、逼迫下走上堕落之路,物质富足下难以掩盖的却是精神上的屈辱和心酸(《兄妹》《家园何处》)。文化程度和农民身份的限制也使得他们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难以真正享受城市社会福利,也融入不了城里人的圈子,弃农进城的他们还是摆脱不了外来者的身份,只是作为低端劳动力栖居在城市的边缘,无法安身立命,“而远方那个乡村,他们又回不去或不愿回去了”[2],因此只能成为都市里的异乡人,失去家园的漂泊者。
2、徘徊于城市文明之外
由乡入城者中,也有少数人拥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居所,过着相对富足安逸的生活,如《城市生活》中的田志文,尽管物质生活无忧,但忙碌无趣的工作,周围冷漠疏离的面孔,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让他无法入心、深陷寂寞,于是在空虚无聊中煞费苦心地与一辆废旧自行车连番开战,劳神费力的挪车竟让他感觉到了久违的快乐,但一想到废车的主人或许也是因为无聊,将挪车当成了一大乐子始终奉陪着,顿觉索然无味,可见精神空虚已经成为现代都市文明的一大通病,这也代表了由乡入城者的另一类处境,虽然能在城市立足,但心灵深处依然存留着乡村赋予的特质,回旋着对美好的乡土人情的渴望,无法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同样置身于走出了乡村却又走不进城市的迷茫中。
三、追问家园
(一)矛盾的创作心态
自现代文学起始时代,乡村叙事就充满着悖论,一方面,乡土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另一方面,乡村又是诗情画意的所在,这种矛盾的乡村想象一直延续到当代。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激烈冲突,让许多乡土作家游走在审美乌托邦与现代性批判之间,陷入价值思维的惶惑之中,这在“农裔城籍”作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刘庆邦曾坦言他的乡土小说创作犹如在矛盾中自己跟自己干仗,时常陷入两难的精神困境,小说也呈现出“柔美”和“酷烈”两幅截然不同的笔墨,建构理想家园时是柔美的、出世的、抒情的,直面现实家园时却是酷烈的、入世的、批判的,然而两个极端的书写却一致地表达了对家园的追问与探索,展现了底层生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迷茫。经情感美化后的乡村固然美好,但潜藏在诗意下的低回颤音也流露出了对乡土家园的困惑,当乡村家园无法依托时,乡民们“由乡入城”追寻新的家园,寻觅到的不过是精神的荒原,但回望家乡,面对的同样是不堪回首的记忆,城市是他乡,故乡也成了异乡,淳朴的乡民们又该去何处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呢?因此刘庆邦诸多小说的结尾留下了“我这是在哪里呢?”[3]、“他们会到哪里去呢!”[4]等追问,事实上底层民众对“家园何处”的困惑又何尝不是作家和时代本身的困惑呢?刘庆邦通过“路在何方”的反复追问向读者袒露着精神无处扎根的迷茫以及对精神家园的无尽追寻。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面对多元的文化环境,无根的焦虑已成为现代人心中的隐痛,因此对家园的寻找与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向后看的价值取向
刘庆邦酷烈小说中阴暗的现实、冷酷的人性让人震愕,柔美小说中谐美的状态、美好的人性又令人心醉,作者也正是在理性现实与感性理想之间左右摇摆,两种风格看似迥异,“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指向:即对文化原乡的精神守望”[5],呈现出“向后看”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对故乡充满感恩和眷恋的远方游子,刘庆邦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视为理想的生存方式,他隐去了乡村的历史性发展,淡化了对现实苦难的体认,通过心灵深处的家园记忆构建了一个经情感美化后的理想乡村家园,通过对乡村的诗意书写,礼赞传统农耕文明,发掘人性的真善美,重建精神的栖息地和避难所,借由精神性的故土安顿疲惫的心灵,缓解现实的困顿,但这只是想象中的乌托邦,并非真正的理想家园。作为一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刘庆邦也清醒地意识到诗意田园是远远滞后于现代文明进程的,因此又以冷峻的态度探寻转型期农民的生存之路,然其笔下无论是现实乡村,还是城市生活,亦是作为城乡结合部的矿区都是以理想乡村生活作为参照,几乎不见现代世界的光芒,仍然“以传统的价值立场和文化心态应对现代文明困境”,[6]将人性的淳朴善良视为家园的救赎之路,在酷烈小说中虽然书写了人性在欲望下的扭曲和变异,但农民生命的底色总存在一丝亮光,如赵上河最后的恻隐之心(《神木》),马海州出于本能的救助(《走窑汉》)等,作者正是要用这道人性的亮光提醒乡民要坚守本性,守望家园,然而“怀旧意味的家园找寻往往难以提供一种崭新的家园图景。”[7]相对保守的家园意识也使得作者在家园探寻的征途上难以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