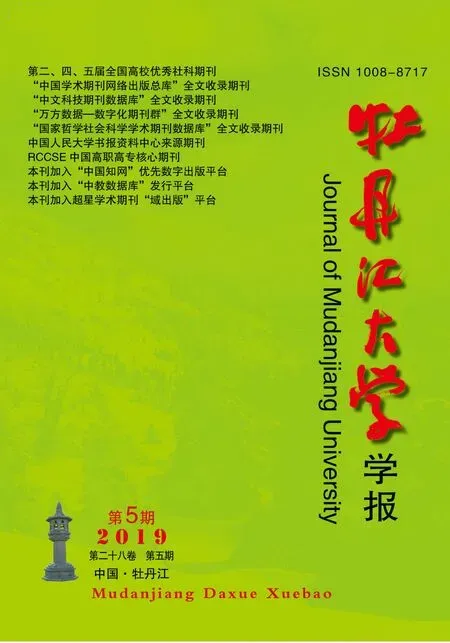社会认同下译者身份的翻译伦理
谭 素 琴
(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引言
在人文学科领域,身份作为一个重要概念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由于身份问题的复杂性,要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具体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总体说来身份概念有三种:启蒙主体的;社会学主体的和后现代主体的。第一种以启蒙哲学为基础,认为人是一个完全中性化的、整体的、有理性、有意识和行为能力的个体。这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强调身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第二种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认为身份在自我和社会的交互中获得多重属性,且主体的内核并非是自主的、自足的。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身份理解注重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间的交互性;第三种概念是建立在少数族话语基础上的后现代去中心身份,是“碎片化的、分裂的,是在差异中多重建构的,往往也是交织对立的话语、实践和位置。它们在激进的历史流变中产生,持续不断地演进和变化着”(Hall,1996:17)。身份从本质主义的单一“自我身份”,发展到后结构主义下的多重身份再到后现代视域下的碎片化身份,仿佛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人与社会的动态发展进程。
对译者文化身份的讨论,不仅实现了由语言学向文化研究的过渡,脱离了以往研究中“翻译主体”和“译者主体性”的话题窠臼,而且将译者置身于宏大的社会历史空间,开启了新的研究维度。遗憾的是,随着学界对翻译文化转向的批判性反思,译者主体的社会性研究刚刚萌芽就戛然而止。译者身份的多重性、译者主体身份与社会间的交互性、社会视角下译者主体的“受动性”等问题都还缺乏系统界定和全面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将社会认同引入译者身份研究中,从社会认同的视角重新界定译者身份的内涵和类型,将社会认同与翻译规范整合起来,阐释译者的群体主身份认同和角色身份认同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二、社会认同下的译者身份界定
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是英国心理学家塔菲尔(Tajfel)和特纳(Turner)在最简群体实验范式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身份是在三个层面上构建起来的:基于群体的群体身份,基于角色的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群体身份强调从认知、态度和行为三条主线实现个体的社会归类;角色身份关注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个体的某一角色与该角色相对应的行为之间是否匹配;个体身份则是将个人归属为区别于他人的,独一无二的实体,其行为往往根据个人意愿来进行(Stets &Burke,2000:226-228)。从角色认同的观点来看,个体的多重身份按照一定规律由高到低排列起来形成身份等级(identity hierarchy),在某种情况下等级较高的身份最可能被激活,也最“能从心理上提升个体在所属群体中的认识影响力和行动影响力”(Oakes,1987:118),造成身份突显(identity salience)。身份突显的潜在意义,就是等级越高的身份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关系越大。
从社会性的视角来看译者,译者身份只是他在特定情况下选择的一种角色身份。李文静将译者身份分为角色身份、群体身份和个体身份。角色身份指的是以译者所担任的社会角色为基础,包括译者角色和其他与翻译相关的社会角色;群体身份以译者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如国家、民族或性别身份;个体身份是译者不同于其他译者的独特的个性风格(李文静,2011:9)。尽管李的分类为译者身份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维度,但尚未在认同与译者行为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关联,缺乏一种可资参考的描述体系。换句话说,她并未触及到“身份凸显”“主身份”和译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是最本质的缺陷。谭载喜认为,译者身份存在“主”“次”之分,“主身份”是指译者作为“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转换的人”,即个体从事翻译活动时的身份,“次身份”是指译者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角色时的身份(谭载喜,2011:120)。
将译者角色身份定义为“主身份”,其他身份定义为“次身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前提基础上的:即译者最本质的、最稳定的身份是语言转换者。然而,如果把译者看成是一个社会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那么译者“主身份”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他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把自己认同为主要所属的社会群体成员时具有的那种身份。这个身份限定了他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社会活动和社会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通俗的说,“主身份”就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在社会中的主业,“次身份”是副业。就拿林纾来说,他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主身份不是翻译家,而是桐城派古文学家。这是因为:其一,译者是双语转换者,而林纾不懂外语;严复就曾说,“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钱钟书,1985:6);其二,林纾本人也认为对自己的评价,“第一该讲自己的‘古文’,为什么倒去讲翻译小说”(同上)。林纾不审西文但却能以“翻译家”的身份与严复享誉晚清译坛,凭借的是他优秀纯熟的古文功底和文学审美力,其作品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对文学或美学的重视超过一般猎奇式的译者”(朱志瑜,2016:30)。
三、社会认同下译者身份的翻译伦理
1.社会认同与翻译规范
在翻译学中,图里将其界定为一个用来描述分析翻译现象的范畴,把翻译规范分为三种:预备规范、初步规范和操作规范。预备规范确定翻译文本的选择和总体翻译策略;初步规范引导作者的文化心理;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行为的真实决策过程(Toury,1995:58)。图里有关翻译规范的描述,主要从原语和译入语的语言规范系统出发,采取的是文本语言学视角,而“先入为主的观念”“特定社群共享价值观”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社会身份的定义。因此,我们不妨把翻译行为看成是译者与其他社会群体主体、翻译主体间的身份建构过程或者是服从译者的身份认同伦理的过程。
就译者而言,他在翻译中受到的认同伦理无外乎以下几种:译者的“主身份”即主要认同的那个群体内部的社会规范;译者作为双语转换者这一群体认同下所要求的行业规范或译者伦理;译者作为个体的自我认同规范如性情素养、审美偏好等。群体主身份构建了译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心态,起着预备规范和初步规范的功能,决定了翻译目的、文本选材和大体的翻译策略;译者角色身份规定了译者“双语转换”的本职,决定了他作为主体的“忠实”与“叛逆”,“能动”与“受动”的二元属性;译者个体身份则赋予了译者个性化创造的原动力。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的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所属社会群体身份的约束,其次才是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的约束。当然,译者三种身份与三层伦理之间并非截然分开,在特定的时候有可能会相互重合。
2. 译者身份的规范伦理
(1)译者群体身份的规范伦理
作为社会行为的翻译实践,本质上是译者根据特定历史时期下确定的主要群体身份同自己的其他身份、其他翻译主体间主身份协商的过程。根据社会认同的观点,个体通过社会归类会对我属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通过实现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对应到翻译中,译者通过对群体主身份的社会认同,自觉自愿地接受该群体内部的思想观念、原则规范并内化为自我身份的一部分,忠诚并服务于该群体,增强我属群体的凝聚力。这一群体主身份下的认同伦理,类似于图里的“预备规范”,为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奠定了总体基调。同一时代的不同译者,其群体身份的主身份是不同的,也决定了他们翻译过程中遵循的伦理不一样。
以五四时期的瞿秋白和鲁迅为例。虽说两人是挚友,有着相似的革命思想和文学观念,但两者在翻译目的、具体选材、翻译策略和表达方式上却存在明显分歧,说到底也是由于两人群体主身份、次身份的认同差异决定的。尽管鲁迅或间接或直接地参与了政治活动,但无论怎样,他总是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一个实务的政治家,相反,虽然瞿秋白自认为参与政治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但他终究是一名职业政治家。总之,“鲁迅是文学家,旁涉政治;瞿秋白则是政治家,兼顾(管)文学”(王宏志,1999:81)。“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体主身份,表明其一切社会实践的出发点是服从革命需要,服务于政治需要。这一身份同时隐含着这样的认同规范即信仰共产主义,坚持革命事业,解放劳苦大众,传播革命思想等。受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之前强调个体身份历史价值的瞿秋白,这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更加看重社会对个人的塑造作用,突出个人发展应融入到社会历史进程中去。
实际上,从材料的选取,到翻译思想的确立再到翻译策略的应用,瞿秋白都配合了这种群体主身份的认同规范。他的翻译文本选材带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倾向,绝大多数作品都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马列主义经典有关。在翻译方法上,他既反对赵景深“牛奶路”(milky way)这样“宁错而务顺”的硬译,又反对鲁迅力求保留原作丰姿的“宁信而不顺”思想。他“既信又顺”的翻译主张,同样与其主身份密切相关。译作要信,就是为了要原原本本地介绍马列主义思想,不能使之歪曲走样;译作要顺,就是表达要符合普罗大众的阅读需求,要用绝对的白话,以此增强译作的可读性,促进革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比较而言,鲁迅的群体主身份是无产阶级文学家,其翻译活动的认同规范便是从文学出发,以文学为根本,以文学为镜子反射出社会与人生。与瞿秋白强调集体意识不同,鲁迅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认为应“任个人而排众数”,大力彰显个体身份。他的许多小说都塑造了十分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痴癫疯狂的“狂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的阿Q,勤劳质朴但命运悲惨的祥林嫂,穷困潦倒,落魄迂腐的孔乙己等。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清楚说明了其翻译目的是“改造社会”,之所以选择东欧如俄国、波兰及巴尔干等小国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是因为五四青年可以借那些呐喊和反抗的作者来表达新时期的身份诉求。相应地,他主张“宁信而不顺”,认为翻译既该“保留原作丰姿”,又该尽量“保存洋气”,提倡异化的翻译方法,注重输入新的文学内容和文学表现手法,改造“实在太不精密的”中国文字或话语体系,进而改变中国人的思维。
一般说来,译者的群体身份是积极社会认同的结果。它会随着时代需要和社会环境自觉改变,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群体主身份下的认同规范与个体身份中的认同规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为前者已经内化为个体的一部分;不过,在极权社会或某种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中,译者有可能无法自主实现积极社会认同而产生社会认同威胁。这时,主导译者行为的规范就不是译者的角色身份规范,而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那种群体身份规范了,译者受到来自社会外群体的强制性规范和约束也更加明显。
(2)译者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的翻译伦理
如果说译者群体主身份认同从宏观上限定了译者翻译目的和文本选择的准则,那么角色身份认同则在中观上限定了翻译的性质和译者主体性中“创造性”自由的限度。译者角色身份的认同规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译者对自身作为双语转换者这一角色身份的认同,必然使其受到这一角色伦理的规范;二是译者角色作为一个主体,会受到主体性哲学有关受动性和能动性的规范。第一层规范与翻译规范的语言学和文本-语言学途径紧密相关。虽然译者的群体主身份在总体上决定了他的文化心态和翻译策略,但双语转换者所固有的职业伦理却从根本上规定了他生产的文本性质是翻译而非创作。译者角色身份的第二层规范力,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主体性问题有关。一方面,传统的译者主体身份认同把译者看成是隐形人,过于强调文本客体或作者主体身份的限定性规范。另一方面,翻译的文化转向又过于突出译者主体规范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而将原文或作者主体的“限定性”置之不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是在为不负责任译者的误译、错译、烂译提供理论支持。作为“双面人”的译者天然地将“受动性”和“能动性”融为一体,既要受到原作者的限制,又要用另一种语言创造出译本。
译者角色身份定义了翻译是“忠实的创造”,而译者个体身份则带来了更多个性化的创造自由。每一个译者,都是宏观社会环境、微观家庭生活、教育经历和个人气质的产物,差异化的家庭、教育等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才情学识和诗学观。译者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对翻译行为的影响,类似于图里翻译规范中的“操作规范”。译者对这两种身份的认同,决定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忠实和译文生产时的创造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作为专业人士所具有的审美力和诗学观,决定了译作的品质。
四、结语
身处社会现实的译者,并非如规定性理论假想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转换者,就该忠实地再现原作,而是在各种身份认同下按照相应地规范伦理进行翻译实践的。社会认同强调个体在群体关系中获得对我属群体的认同,并由此建构起个体的社会认知结构和规范伦理。如果将翻译看成一种社会行为,那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任何选择,与其说是“各种历史、社会、文化、政治、个人审美和艺术风格等种种外力交织形成的”(许均,2002:63),还不如说是他多重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译者的群体社会身份从总体上建构了译者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文化心理,属于“首要的”、较高层次的宏观规范,那么其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则平衡了“忠实”与“创造”,属于较低层次的具体规范,是以译者的文化心态和翻译认知为前提的。译者翻译行为的身份伦理,就是他在自己的群体身份、角色身份和个体身份间以及他的多重身份与其他翻译主体间的身份相互协商和制衡的认同伦理。只有译者以翻译为职业或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时,其主身份才等同于译者角色身份,才会更多地从职业眼光上注意到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忠实”与“创造性叛逆”。 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不再是双语转换者或语言活动者,而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翻译为手段的社会活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