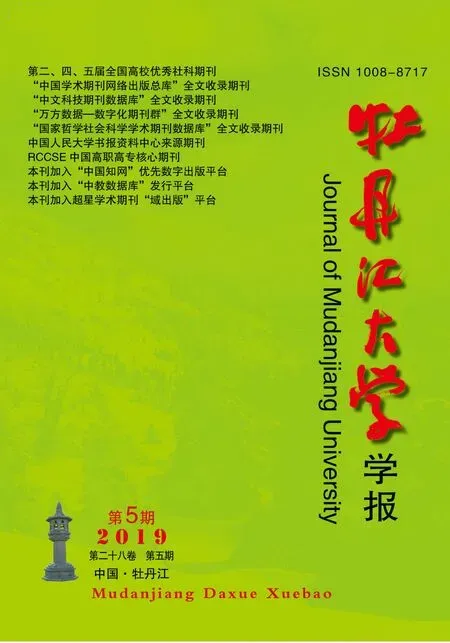“边缘性”理论视野下的《橘子红了》
陈 文 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台湾作家琦君(1917-2006)作为一个当代文学中的散文家、小说家和儿童文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1991年,长篇小说《橘子红了》出版。2002年该小说由导演李少红改编成电视剧,一时引发两岸人民的关注。作品讲述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江南小镇,一户封建世家为传宗接代而纳一年轻女孩为妾,畸形的婚姻关系最终将女孩毁灭的悲剧故事。
《橘子红了》是作者以年少时的经历为灵感、以故乡环境为背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而创作的小说。作者琦君化身为文中的叙述者秀娟,向读者讲述了一段自己曾经参与的往事。20世纪在西方学术界呈现出交叉学科研究的趋势,西方学者对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层面研究人类历史,从而衍生出“边缘性理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在1928年发表的《人类的迁徙与边际人》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这种边缘人是文化混合的产物。帕克指出“新的文化接触会引起道德混乱,可是这种道德混乱最具体的表现在边际人的思想中。如果我们要对文明和进步的各种进程做最深入的研究,文化变迁和融合在进行的边缘人思想就是最好的研究对象。”[1]2因而研究秀娟以及作者琦君的边缘性特征对客观了解时代更替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变革有着积极意义。
一、秀娟的边缘性特征
《橘子红了》中的秀娟一直游离于封建家庭的道德规范和自我内心价值判断和反抗意识之间。美国社会学家罗布特帕克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指的是“身处两种文化交界处,远离中心文化的人。他们在文化的开放、交流和选择中往往徘徊于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体系之间,因为不能完全融入任何一个文化体系当中而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并常常伴随精神上的困惑。”[2]分析秀娟的边缘性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秀娟面对秀芬事件时的态度以及面对时代传统与更新的复杂情感。
(一 )封建家庭中的养女
《橘子红了》的第一章节被命名为“乡下的家”,与之对应的是大伯在“城里的家”,乡下的家是整个大家族地位的象征,文中描写这个家的整体环境和氛围时用词多为沉闷、古老,如第一章中对书房的描写,“书房壁上的古老自鸣钟,有气无力地敲了四下,我抬头看,指针却指的是五点。”[3]3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家庭让人倍感压抑,在昏暗的书房里,“我”感受不到任何乐趣,只是觉得时间难熬,只好乘着近来生病的先生在昏暗的四方帐里打瞌睡的间隙偷偷溜出书房。在这个家中唯一让人感到有生机和活力的地方,莫过于橘园。“从走廊边门一溜烟跑到橘园里。顿时眼前一亮,一股清新的空气直透心肺,古战场凄凄惨惨的景象马上消逝了。”[3]4整个家庭沉闷、无生机的氛围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掌管乡下大宅的大妈无子。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极度让大妈抬不起头来的事。受过传统礼教的大妈也将自己无子当成自己的罪过,对于大伯冷漠的态度毫无抱怨。不仅如此,还对大伯没有以无子为由休妻报以感恩之心,故而一直寻找机会弥补自己无子的缺憾,以报答丈夫对自己所谓的“宽容”,这也是后来造成秀芬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之一。
正因为整个家庭中缺失“孩子”这一角色,所以成为大妈女儿的秀娟在整个家庭中备受宠爱,但秀娟依旧只是以一个养女的身份存在,秀娟的到来并没有将大妈从无子的负罪感中解救出来。简而言之,秀娟虽然被承认、却没有被接受,但她只作为这一封建家庭中的养女,由此造成她在整个家族中的边缘性地位。
(二 )新旧思想的接收人
秀娟比同龄女孩子更加幸运,因为这个封建大家庭给予了她接受教育的机会,虽然不是大伯的亲生女儿,但是却在这位封建大家长的坚持下为秀娟请来了先生。教书先生虽然知识渊博,但作为深受中国古代价值观念影响的儒生,其保守的思想和所坚持的价值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作为学生的秀娟。秀娟的新思想多来源于六叔,这位六叔与秀娟的年纪相差无几,在城里接受教育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新的思想。每次当六叔回到乡下的家时,总会给这个在家里接受传统教育的小侄女带来新的书籍,例如《模范青年》。在新旧思想的交替影响下,秀娟对于在家中发生的一系列古怪事开始有了复杂的情绪。一方面秀娟对于大妈心甘情愿帮着大伯纳妾的行为深感困惑,明知秀芬和大伯之间的关系是畸形的、不符合新思想价值导向的,却只能成为一个悲剧的旁观者。带着些许的歉意和期盼,希望秀芬在大妈的照顾下能过上比在哥嫂家更好的日子。
在“伤逝”一章中,秀娟谈及秀芬的悲剧性命运,“秀芬来我家,短短不及半年,却像挣扎了一生一世。她怀过希望,领受过一丝丝虚无缥缈的爱,却尝尽了生离死别之苦,最后付出了微弱的生命。这究竟是谁的过错?”[3]51由此可看出,对于造成秀芬的死因,秀娟内心是复杂的,她既不相信秀芬的死来自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封建大家庭,不愿意承认自己深爱的大妈和尊敬的大伯是造成秀芬悲剧的直接凶手,但先生所说的“命数”又过于虚无缥缈。秀娟一直游离于封建家庭的道德规范和自我内心价值判断和反抗意识之间。只能将这份哀怨的感叹指向当时不公平的世界以换来自己内心的平静。
作为生活在封建礼教价值观念和平等自由的新时代观念碰撞时代的边缘人,秀娟身处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交界处,她不同于完全认同旧时代社会秩序的大妈,也没有融入到新的社会价值导向中心。不论与位处旧时代价值体系中心的大妈还是接受了新思想、在不断靠拢新道德的六叔都有着一定的距离,秀娟自身面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的矛盾、困惑的情感也伴随着这种边缘性而来。
(三)畸形婚姻的旁观者
秀娟对于大伯、大妈和秀芬之间的畸形关系所持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可怜大妈为大伯和家庭所作出的牺牲,希望劳苦的大妈长久以来的心愿可以达成,希望大伯能真正回到乡下的家中,而并非像是一个普通的过客,仅仅用“贤妻妆次”四个字联络与妻子的关系。对于大妈和秀芬之间的关系,秀娟更希望她们是母女而不是共侍一夫的可怜女人。
“秀芬、秀娟,我们相差只有两岁,真像姐妹。她要跟一个像她父亲一般老的男人过一生一世。也有点怪大妈,她一厢情愿地制造这么一件古里怪气的事,安排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命运,究竟是怜悯她,还是害了她呢?”[3]11
由这段描写不难看出,秀娟认识到这段畸形关系终究会将这个年轻的女孩毁灭,而事情的主要推手却是百般疼爱“我”的大妈,同样是旧礼教下被压迫的可怜人,秀娟无法将矛头直接对准大妈,而只是微微地表达了对这件古怪事情的看法。秀娟没有全盘否定大妈以及整个大家庭所坚持的那套道德准则,而又十分清楚这样的关系是畸形的、不符合时代新思想、新道德的。
秀娟的自述以及之后一系列的行为符合斯通奎斯特所论述的“边缘人发展阶段”的第二阶段特征,即“个人由于自身的经历开始察觉到文化的冲突和自己人格内部的矛盾感——分裂的自我以及不安定性。”[1]2她的自我已经感觉到畸形关系将给整个家庭带来的伤害,但却有意识地选择回避问题,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渴望悲剧的延缓发生以及不发生,从而实现自我内心的安定。
二、作者的边缘性特征
谈及秀娟就无法跳过作者琦君本人,在《关于橘子红了》一文中,作者琦君说“这里面的我——秀娟,不完全是我,我十六岁时还没有那么通达人情,对人如此体贴。”[3]257由此可见,秀娟这一人物形象或多或少带有作者的自述色彩,如果说儿时的琦君对于当年这一大家庭中所发生的故事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触和较为客观的认识,那么秀娟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是琦君本人的重生,其目的便是完成对往事的“再参与”以完成对往事的客观性重述。而今要探讨秀娟的边缘性还得从作者琦君的边缘性说起。
从琦君自身的角度来看,出生于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琦君,成长于时代的新旧交替之中。她早年的家庭环境以及人身经历与其边缘性密不可分。
(一 )家庭环境——旧式家族中的新生儿
从小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熟读古今中外之经典。成长在传统封建大家庭之中,琦君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同时又因饱读新文学,新旧思想观念难免在她的意识形态中产生碰撞。父亲虽然对她疼爱有加,但是父亲的再娶、母亲的哀愁使她对那个从小养育了她的家庭环境产生了十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她怀念旧时生活秩序的恬静与美好,追忆着故乡的山水与人文;另一方面,她深刻同情被旧式思想禁锢了的劳动人民,特别是长期生活在父权制价值体系下的中国妇女。在她的作品中,“母亲”形象占了很大比重,如《佛心母心》《橘子红了》《髻》等。父亲纳妾使得父母原本和谐的关系破裂,琦君也自然陷入对父亲既崇拜又批判、对母亲既怜悯又同情的情感之中,她无意于批判旧封建旧道德对人的荼毒与压迫,但字里行间浓浓的哀怨色彩使得每位读者都能触碰到其中那份不经意的哀怨与清欢。
(二)时代边缘——新旧交替中的边缘人
琦君,本名潘希真,1917年7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大户人家,父亲潘国纲喜好书籍、信佛行善,母亲叶梦兰慈祥贤惠、温柔敦厚,因家庭环境的熏陶及启蒙教师叶巨雄的严格教诲,琦君熟读诗书,饱看新文学作品及外国小说,文学功底深厚。经历1949年大迁徙的琦君同其他从大陆渡海赴台的作家一样,追忆和怀念成为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成为琦君作品中最魂牵梦绕的地方。琦君的几篇小说大都以追叙的方式将儿时的经历一点点呈现出来,与其说是小说,更像是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式记录。成年后的琦君虽然有着诸多游历异乡的经历,但对祖国山川的思念使其作品中常常带有哀愁的色彩。
(三)故土边缘——迁徙台湾的乡愁者
1949年中国发生了社会政治大变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纷纷跨过海峡抵达台湾。琦君也随着家人远离祖国大陆到达台湾,开始了她对故乡无限的追忆和思念。在琦君的作品中,故乡永远是无法割舍的地方,梦中的故乡和故人常常出现在她作品之中,故而很多人说读琦君的作品就像是在看过去的老照片。在她的散文《家乡味》中写道:“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土的一事一物。”[4]73这种对故乡炽热的思念,也正是作家热爱祖国的表现。“对于故乡的眷恋与热爱不只是她个人的思想情感,同时也反映了许多流落海外的中国人的心理、心态。”[5]
琦君虽然已远走台湾,但大陆对她从小产生的影响却难以磨灭,以琦君为代表的台湾作家生活在怀念大陆和适应新环境的时空夹缝之中,既回不到过去,又无法预测未来,最终成为那个变革时期的边缘人。
三、边缘性的探寻与追溯
边缘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是中心与边缘并存。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的中国正处于整个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带。西方世界在工业化的不断进步中愈发富强,自然科学的发展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西方国家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开始向世界推广符合其自身价值导向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西方世界日新月异,东方世界满目疮痍,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与中国人也正接受着来自遥远西方的新思想的冲击与洗礼。民国初期,整个中国的古老价值体系正接受着人们的追问与质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生长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两个文化体系之间,一方面,被新知识新文化所开导、启发;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旧式社会价值体系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之中,他们往往处于这两者的交界地带,既不认同旧式价值体系,又无法适应新的价值导向,从而造成个人与社会大众间的巨大间隔,如俄国19世纪文学中所描绘的“多余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零余者”。
(一)探寻秀娟的边缘性
秀娟是生长在民国时期的新女性,其“新”在于在传统旧式家庭中接受新教育。虽父母双亡,却受大伯大妈宠爱,在大伯的支持下请了先生开始识字学习。“上午教过的《论孟左传》统统温习一遍,自己喜欢的《吊古战场文》更是背得滚瓜烂熟。”[3]3在那个年代能正视女子教育,甚至不惜重金单独为一个女孩子在家中聘请老师,足可见大伯对秀娟教育的重视程度。与之相比,与秀娟年龄相差无几的秀芬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如果说秀娟在家中接受的教育是传统教育,所学思想是传统思想,那么六叔所带给秀娟的教育资源则是她接触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门。“我还有个六叔,礼拜天总回来陪我聊天,带许多新文艺小说和杂志报纸给我看,他说这样思想才跟得上时代。”[3]4通过六叔带回来的书籍,秀娟逐渐与新时代、新价值体系接触,在一系列类似于《模范青年》等书籍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旧式传统婚姻观念的荒谬,当大妈告诉秀娟即将给大伯纳妾时,秀娟在对大妈的行为感到极度不理解的同时,又十分心疼大妈,埋怨大伯对大妈的冷漠。但是即使知道这种畸形的婚姻关系会毁灭大妈和秀芬时,秀娟的内心极其矛盾。“这件事,只有我和六叔,心头总像有个解不开的结。……我心里竟萌起一种奇妙的念头,却又像犯了大错似的,立刻打消。”[3]19秀娟逐渐察觉到六叔和秀芬之间微妙的关系,她所接触到的新小说、新文化中也极力倡导自由的爱情,明知大伯和秀芬之间即将成为夫妻,可还是喜欢六叔和秀芬在一起的时光,因为这个时候的秀芬开始美丽活泼起来。秀娟明明不认同秀芬与大伯的畸形关系,却无法鼓励秀芬为自己的命运而向传统价值导向反抗,因为所要反抗的直接对象是同样受到父权价值观念影响的大妈和疼爱自己、给予自己良好生活条件和学习机会的大伯。面对这种两难抉择的情况时,秀娟选择了保持中立,既同情秀芬的不幸人生,又尊重大妈所作出的牺牲,由此形成秀娟的边缘性特征。
(二)追溯琦君的边缘性
由于亲生父母早逝,琦君被过继给伯父一家,由伯母叶梦兰代替生母卓氏扮演琦君一生中重要的母亲角色。大伯潘鉴宗作为封建家庭大家长,给予了琦君良好的教育,但由于纳妾一事给伯母叶梦兰所带来的痛苦使琦君印象深刻。这种畸形的家庭婚姻制度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在琦君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如《橘子红了》中的大妈和秀芬,《鬓》中的母亲与姨娘。琦君作为这一悲剧的观者,是典型的边缘者,她深知这种畸形关系对家庭成员所造成的伤害,却只能在抑郁无助中消耗自己的情感,既不愿意全盘否认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又对部分封建价值愤愤不平。只保持着平淡冷静的客观态度,将往事娓娓道来,而故事的悲剧根源从何而来,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态度。琦君像是一个冷静客观的时代旁观者,只是把这些往事一一成列出来,而不做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批判。既不宣扬旧式社会秩序,又不对它进行彻头彻尾的否定,更不求改变传统价值体系,是实实在在的旧式价值体系的边缘人。
1949年北京人民政府成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到达台湾,大批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带领着自家人举家台迁。据统计,由大陆迁徙往台湾的人数达到200万人,其中包括作家琦君。从此以后,大批台湾作家的作品有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乡愁。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浙江人,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以及不尽相同的风土人情,在努力适应台湾的同时也在无时无刻地怀念故土,成为身在异乡的异客。生活在大陆生活文化和台湾生活文化的两个不同体系之间,既无法摈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又无法完全融入台湾社会秩序之中,成为异乡的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