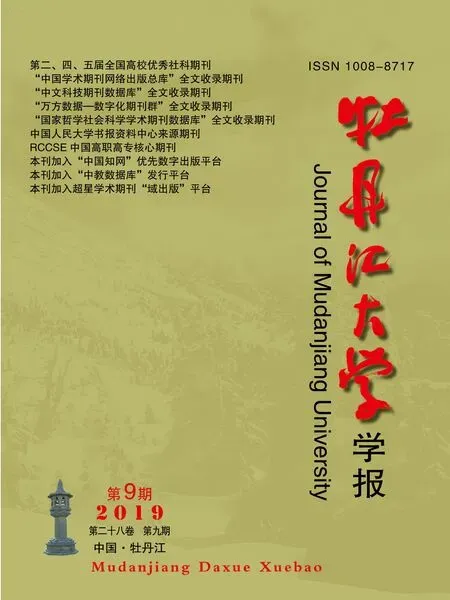论中华民族的“虚化”与建构
马 宇 飞
(榆林学院政法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一、中华民族的“虚化”
(一)中华民族虚化的历史惯性
王朝国家“家-国”同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是王朝国家的臣民,其政治社会化的生成逻辑,亦是“国”的家族化,即“国”之“公域”与“家”之“私域”之间无泾渭分明的“群己权界”,而是二者重叠互构。“王朝国家,实际上是家庭所有制的扩大,即由财产的家庭占有扩大至‘国家’,形成‘家-国’体制。‘国’是‘家’的放大,而‘家’又是‘国’的缩小,……国家成为某个家庭的私产,即‘家天下’。”[1]“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原子化的王朝国家的臣民个体与政治权力中心保持相当距离,他们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愿或能力,有的往往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集体无意识的间或顺从。“臣民意识到专业化政府的权威,其情感上取向于它,或许不喜欢,或许感到骄傲,其评价它为合法或不合法。但这种关系……是对着该政治系统中输出、行政或‘向下流’的一面,……尽管存在符合臣民文化能力的有限形式,但基本上是一种消极关系。”[2]同时,异质化、碎片化、“家天下”的传统社会,王朝国家的“国”之聚合力低下。及至清廷,所谓“皇权不下县”,族权与绅权的“乡土秩序”将大量家庭、宗族的纠葛矛盾消解于基层,个体从属于家庭、宗族,其政治社会化被家庭、宗族、村社等区隔,所谓“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这割裂、遮蔽了臣民对更高政治共同体的认知与关联。“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其常言‘天下’,以‘文化中国’之‘天下’兼称‘国家’,可见其缺乏国际对抗性,折射出其完全不像国家(指民族国家)。”[3]
秦汉之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观照天下的层次主要有三:层次一,中原王朝直接统辖的郡(县),比如,清朝在关内地区设置直隶省、江苏省、安徽省等内地十八省。层次二,以羁縻、册封、土司等制度间接统辖的边疆区,比如,明朝中叶在西藏、云南等西部和南部,在府、县流官管辖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等地方行政机构,委任当地民族头人为长官,即为‘土司’。层次三,与中原王朝以经济关系——贡物与回赐;礼仪关系——封典为主的两国间礼仪形式;军事关系——互相求兵或出兵等为表征的朝贡国,例如,朝鲜、安南、琉球等。这三个层次即为华夏文化泽被的“化内之地”,即为“天下”。但“天下”并非“世界”,因为,“世界”尚有中华无法企及的“化外之地”,例如,异域的大食等。而且,“化内”与“化外”二者之间的界线是相对的,即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因此,王朝国家的疆域边界时有盈缩、模糊不定。作为社会存在的“王朝国家”自身就模糊不定,而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生者不远别,……坟墓多绕村”的王朝国家臣民个体的“认知地图”里,何谈国家认同,何谈中华民族的认同?
由此,对于王朝国家时期的“中华民族”,一方面,笔者赞同:晚清之前中华民族的非实体性,即处在由“自在”向“自觉”的过程中,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是晚清之后的重新建构;另一方面,诚如史密斯所言:“现代的民族主义‘国族’非凭空而来,而是在原有族群传统基础上‘显影’的‘重新建构’”,即王朝国家时期各个民族事实上“自在”同存共生。因为,晚清之前中华民族的虚化,所以,“国族”,即中华民族的“建构”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国家建设,即国家政治组织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二是,国族建设,即在不同族属的国民中间建构一体性的“国族”共同体。
(二)中华民族的日常性虚化
“中华民族”的主要理解之一是:支撑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作为一个族体单位“国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其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形塑而形成,而且,是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中流砥柱功用的“政治民族”。但是,中国当下的实际:“则是更多强调‘国族’中的各个民族,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的族体意义与族性,迟滞了国族建构,导致国族建构的虚弱甚至虚幻化。”[4]“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众鲜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直接体会到‘中国公民’的现实意义,而且,在国内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优惠政策与民族制度,使得少数民族身份的现实意义显著,结果客观上‘中华民族’被架空和虚化。”[5]例如,我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课堂上、期刊上、报纸上等宣讲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介绍斯大林的“民族”界定,导致一些人产生如下“民族意识”:(1)希求培育和发展“本民族经济”;(2)力促本民族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3)排斥其他“民族”成员迁入本民族的“自治地方”;(4)力主通过风俗、宗教、历史教育等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与“民族意识”。以上这些又直接吻合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如此宣教的直接结果就是将国人的“民族观”定位于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而非包含所有国人的“中华民族”。
同时,在党和国家的官方文本(文件)中常见的政治语言是:中国人民、各民族公民、各少数民族、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中国各族人民、中国(全国)各民族等的表述。而在学界,“现行之民族理论大体都是围绕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展开,而相关中华民族的论述却付之阙如,……吊诡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理论中无中华民族理论。这种民族理论(政策)长期施行,渐成一种特殊政治文化:凡是增益少数民族权益之言行,皆支持、鼓励,甚至纵容;凡是损益少数民族权益的言行,哪怕是学术探讨,皆压制、批判,甚至打击。”[6]这导致:其一,原本为“文化民族”“中华民族”的主体构成,即56个族群的“政治民族”意涵日益突出;其二,“国族”之中华民族的概念和实体地位遭到质疑,悖反的是代之以“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统称”的观点;其三,原本于新中国初期基本解决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问题,在时下的国家建设中反倒又成了问题。此外,从汉族、各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关系角度区划的“族属民族主义”的分裂势力,例如,“疆独”“藏独”的身心之游弋。 “一中为忠,两中为患”,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之间的角力,加之“中华民族”的虚化、悬空,这将进一步引致中国国民的身份归属感、政治归属感等不同程度上的弱化,这又将加剧族际间的“离散化”倾向。总之,“中华民族的虚化倾向明显,中华民族被解构的风险在增加,任由其发展,中华民族将无法规约各民族群体的诉求,无法发挥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支撑功用。”[7]
二、中华民族的建构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以维护祖国统一为根本原则。这是因为,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族际团结、社会安宁是全体国民的最高福祉。“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乱是祸”,正如,“在亨廷顿看来,如果美国不能首先在国内解决‘我们是谁?’这样一个美国特性(美国国家认同)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充满‘文明冲突’的世界中,美国不仅将无法匹竞其他文明,甚至自己都会面临‘解体或根本变化’之虞。”如果中国国民缺乏统一的“身份意识”,没有明晰的国家认同,国家将如马克思语境下的“一袋马铃薯”,最终结果,甚至陷于四分五裂。基于“千年、百年来,维护并拓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如既往地是中华民族甚于一切的政治愿景、道义情感与精神寄托,一如既往地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对此,笔者认为,时下维护祖国统一、族际团结,“谋篇布局”的体现之一,即是“五个认同”的中国话语。
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要弱化中华民族虚化的历史惯性。通过回溯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景深反推“如何理解中华民族”。例如,“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即是于历史过程中的各个族群交往、交流,通过“去族群身份”的交融,“滚雪球”般地逐渐形成。亦要消减学界的理论斑驳:即溯源中华民族如何从原生性族群的事实性共生,而且,在此基础上,顺应世界体系“国族”之趋势,保持“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连续性”。共性地历史叙事、共性地集体记忆,彰显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属性意义上的多个民族、政治属性意义上的同一个国族”的政治共同体,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饱经岁月洗练后全体国人共同的价值守望。各个民族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但是,又非凝滞固化,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迁徙流动、通婚互融,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器物制度等方面持续地交相渗透,继续“交往、交流、交融”。即建构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相应地弱化各个“民族”的个体“民族意识”,以“中华民族”为共性“民族意识”,以此进一步强化各个“民族”之间的互为认同。
(二)同质性“国家建设”
其一,理性吸纳“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安东尼 •史密斯将源起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归类于‘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其强调领土、法制与公民权;而将亚洲等国被动仿效的民族主义归类于‘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其强调血缘、语言和传统文化。”[8]而在苏联解体前夕,其主体族群俄罗斯族同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发展落差。引致少数民族受歧视的联想,俄罗斯族亦因为倾斜性民族政策而心怀不满。一旦苏联解体,所有族群竟都欢呼雀跃!因此,“要在不同人群之间凝聚共同的国家意志,就要保障全体公民不分阶层、族群,皆能均等地参与国家生活,均等地享有公民权利。……现代国家成为民族集合体的关键,就在于人和人之间打破任何身份限制,通过互相让渡主权订立契约,平等拥有并行使公民权,并由此形成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9]由此,同质性“国家建设”的出发点,就是由“族群模式的民族主义”理性吸纳“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
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其基础的政治属性是“国民身份”,与“国民身份”相对应是法律属性的“公民身份”。因此,拥有一国国籍之“国人”个体,往往是“国民”与“公民”的二重角色。作为“国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享有,不是基于其“族属”身份,而是基于同质性的“公民”身份。因此,吸纳“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每个国民都应该享有人人享有的,与最广泛基本自由体系相兼容类似自由体系相一致的平等权利。“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即不能忽略每一个“公民”个体,保障其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语言权、文化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基本公民权。推进“法治”,完善个体公民权的保护。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安排,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这种不平等可以合理地被期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这要求,我国在保障全体国民个体“公民权”的同时,并非完全排斥“族际主义”的民族政策取向,而是要务实考量疆域内各个族群之间事实上的发展差距。例如,契合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布局政府间横向资源配置的“对口支援”政策等(“政策”,一般蕴含着特定价值取向与社会设置的规则)。但是,其政策制定之依据,不是基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而是不同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占有社会资源不同所引致的“社会分层”,以及合作共赢的“区域伦理”等,从而,跳出基于“民族身份”的窠臼。
其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加之,“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由此,“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中华文化自信。时下,中华文化的内部,其历史谱系、神圣记忆正在借用新的符号系统,完成时代特色的重述、重构。“汉族认同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少数民族亦认同汉族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诚然,不可沙文式的强制性认同,但列宁说,自然发生的同化过程是一种进步。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例如,在教科书中,以及调整法律、法规、政策中不利于“五个认同”和“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本符号。比如,教学内容上,我们尊重族群(个体)间的异质性,但我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国族”是“中华民族”,我的“民族”是苗族或藏族等,这类似于我的“省籍”是某省,但并不相斥我的“国籍”是中国。再如,以“语言之同质性符号”为例,在民族地区按照现代化教育标准,建设“双语”(汉语为“国语”)师资培训学校、职业学校、中小学和双语幼儿园等;建设“双语”学习智慧教室与远程信息化平台,打造“四个中心”,即“双语”课程教材研发中心、教学研究中心、教育质量评估中心、教育成果推广中心。以“教学内容”“语言教育”等为抓手,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享中华民族共有历史记忆、共享现代文明的发展“红利”、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屋顶”之下。借用柏拉图“知识就是回忆”之喻,即唤起并清晰于历时性上,早已存储于中国“公民”心灵中同质性中华民族的“认知地图”和“心理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