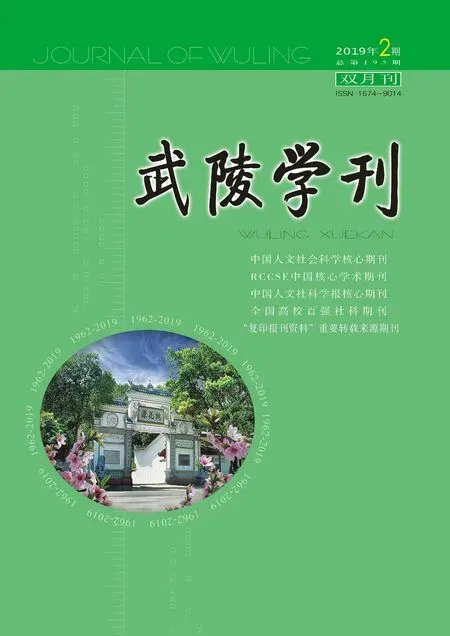赵必振笔下的自立会起义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34)
1900年的自立会起义是20世纪初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近代改良与革命的转折点。又由于这次起义动员了湖南、湖北与安徽等地的哥老会参与,因此在中国近代会党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史学界对自立会起义多有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蔡少卿的《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①。关于与此次起义有密切关系的赵必振,过去史学界研究的并不多,主要有田伏隆、唐代望的《马克思学说的早期译介者赵必振》②、田伏隆的《赵必振传略》③、曾长秋的《赵必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④等。这些文章的重点在于介绍赵必振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的史实,但是对于他与自立会起义的关系尚无专文研究。笔者以岳麓书社1983年出版的《自立会史料集》内赵必振本人写的回忆文章与人物传纪为主要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还原他与自立会起义的关系,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
赵必振(1873—1956),字曰生,号星庵,湖南常德人。早年在常德德山书院、长沙湘水校经书院求学,深受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赵必振在1900年与何来保积极参加自立会活动,共同主持常德地区自立军的组织工作,曾经在德山乾明寺召集哥老会首领大会,设立机关,因此对于自立会以及该会在湖南常德的活动十分熟悉,他的记录有相当的可信度。
赵必振在《自立会纪实史料》中论述自立会起义远因时说:“鸦片烟战役以后,外交失败,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无不割地赔款,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懔中国之危亡,叹民生之多艰。而满清政府帝后争权,盲目排外,致引起八国联军之祸。吾辈目击心伤,因愤而急谋自立,以冀自存。”至于近因则是:“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惨被诛锄,唐才常愤国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因戊戌保国会之基础,改组自立会,又称国会,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集全国之官绅士庶,先设总会于上海,继设分会于汉口,以唐才常为督办南部各省之首领,而自立军之规模具焉。”[1]34
赵必振的上述论述可在《汉口中国自立分会启》中得到印证。《汉口中国自立分会启》宣称:“现因端王、荣禄、刚毅暨一概骄横旧党,暗中主使劝助拳匪滋事,……我等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不特为中国造福,且为地球造福。”“合今日上等才识,议易国家制度,务使可为天下表式。本会之宗旨,系使百姓保有自主任便议权。”[1]37
自立会的“声明借尊皇权以伸民权”之语,赵必振解释说:“当时风气未开,囿于数千年君主之习,故表面仍不能(不)借尊君之论,避免一般奴隶之纠弹。及改为自立会之时,仍不能不为遮语,以便吸收多数之民众。……内则以改君主为民主相鼓励,而对一般愚人,则又以保皇复辟等语以引其入我范围,徐徐再以民主之说开其智识。”但如此自相矛盾,势必造成政治思想上的混乱。赵必振自己承认:自立会“其名不正,又不能见谅于后世”[1]35。
我们认为,赵必振对于自立会起义远因、近因的分析涉及对中国近代基本矛盾的看法,这些看法连同他对自立会起义在政治思想上自相矛盾的揭示都是基本正确的。在一百多年前就有此认识,应当说是比较先进的。
二
赵必振是自立会起义的亲历者,还是自立会在常德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对于在起义中牺牲的三位同志兼同乡何来保、蔡钟浩及陈应轸充满了兄弟之情、同志之爱。
何来保是庚子年间“坚决策动革命者”[1]260之一。赵必振(化名民史氏)在《何烈士来保传略》中透露,戊戌年九月,“余自外归,……访君,君握手,遽谓余曰:‘国事至此,中国之亡将在眉睫,奈之何?’相与注目视,不能作一语。居里中,郁郁不自得,恒太息圣主之幽废也,新政之隳弃也,中国之危亡也……庚子七月,始知唐烈士勤王之举,将集义兵于汉镇,招三江两湖之壮士以成劲旅,君大喜,偕余共襄其事,以常德之事自任。……汉镇事败……捕者至,事急,同志之武人被捕就义者,已二十余人,余皆惊溃。君与余谋,且避其锋。蔡烈士钟浩亦在常德(蔡烈士本与汪烈士镕以全湘之事共任,其至常也,盖因巡察,非仅专任一郡者),共谋避乡间亲友之家,少解再出,且谋后图。……君病未尽愈,坐卧榻,与余握手商别。……余居乡间,捕者尾至,余急走得免死,奔命海外”[1]266。
赵必振在《何烈士来保传略》回忆说:“往者君尝谓余暨某君曰:‘吾先死,汝两人,必为吾祭文一、传一、碑一、挽诗数章。汝两人先吾死,吾亦若汝两人之待吾者。’某君者,君之密友,合余三人,皆总角交,同订生死者也。今年六月,君患病几死,病愈,时已闻唐烈士勤王之事,因慨然曰:‘吾已死矣,今之余生,今上之赐也;今上为民变法,几死,吾当以死助唐救君,不复恋兹体魄矣!’……盖君自办勤王之事之始,已置此身于度外矣。”[1]266
《何烈士来保传略》文末称:“今请泣告于君曰:君之仇,公仇也,天下之人,皆欲为君复之。请言其私,万一不死,生入国门,君之妻,吾嫂事之;君之子,吾犹子之;君之父,犹吾父也。知我幽冥,有如日暾日。”[1]267
由赵必振校补的《自立会人物考》何来保条说,常德人何来保“在邑中时,必振自广西归,一见如故,遂订总角交,与同邑胡有业三人皆莫逆,同治诗、古文辞,时相唱和。甲午中日战事后,湖南有志之士,懔国家之危亡,急谋救国之大计。……时外寇逼鲁,侵入孔庙,毁子路象。来保尤悲愤,著《悲孔》上、下两篇,以告中国之士大夫。两文皆在《湘报》中发表,来保之名,更为同志所重。及戊戌政变,……一切新政,概行毁灭。来保亦遁归常德。适赵必振亦自广西艰归,与来保重见,更感志同道合之谊,愤时嫉俗;来保、必振、胡有业等,悲歌慷慨,日事吟咏以消遣。来保遂取岁寒三友之义,定名为‘寒社’。既而杨概、汪镕亦以邮寄参加。蔡钟浩、蔡钟沅从唐才常自日本回湘,亦加入吟社,来保又戏称为‘寒社七子。’”[1]301庚子“陈义卿因事来常,暗中联络,为必振所闻,走告来保。遂由来保、必振联名致函于汉口总机关。适蔡钟浩、蔡钟沅兄弟亦到汉,证明函件之真伪,遂由汉口总机关分函常德各同志,将常德自立军事,交何、赵主持。既而蔡钟浩、蔡钟沅亦来常德指导。龙山唐桂林(字仰吾)亦至常。乃租小西门城湾之废磨坊为驻常之机关”。武汉总机关被破坏后,“湖南巡抚俞廉三,乃派湖南候补知县沈瀛,密赴常德,按名缉捕。来保、钟浩先后在桃源、汉寿捕获,均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1]302。
关于蔡钟浩,赵必振(化名民史氏)在《蔡烈士钟浩传略》中介绍说,蔡钟浩“闻独立自由之义,集同人开自立党于长沙,刊章程,编会籍……湘乡人之唱言自立,实以君为始。政变,君归里,郁郁不自得,慨然思远游,……游学于日本。时顽固柄政,国事日非。复偕诸烈士归国,谋所以救者。义和团事兴,中国之危如累卵。唐烈士效日本覆幕尊王之举,君始终与其谋。林烈士暨□君□□主持汉镇事,君赞襄之,推广于湘中。君遂以全湘事暨汪烈士镕共任”。不久自立会起义在湖南遭到镇压,“常德武人之死者已二十余人,城中不可居,始与何烈士来保及余谋,君遂归,潜伏于乡间别墅。途次遇陈烈士应轸来探常德之事,君告以事不可为。及闻同志□君□□至龙阳,居陈烈士宅,君潜至龙阳,将更有所谋,而捕者尾至,遂被获。逮至长沙,酷刑三昼夜始就义”。赵必振在文末说:“己亥始识君,君欲以兄事余,余谢之,君怏怏不乐。历庚子,勤王事起,君再归常德,共事日久,余讶君之年少而才,心折之。君又申前说,余大喜。君责余曰:‘向者固请而不得,何自居之亢也。’余急谢罪,相与订约,将登堂拜母,未果而事败,君竟死,……吾辈流血救世,已有所成,而余尚未知何所底止,敢不自励,以负死友?若夫兄弟之约,再世相期,既种前因,必结后果。”[1]263
由赵必振校补的《自立会人物考》钟浩条称,蔡氏兄弟在时务学堂为高材生“闻民主民权、自立自主之言论。戊戌政变,时务学堂停办,钟浩兄弟皆归武陵,始与必振相识。唐才常为友雠国变所激刺,联络江湖志士及门下通才,欲办大事,组织自立军。钟浩、钟沅参加其事。武陵为钟浩桑梓之地,而在武陵组织之陈义卿同志急须返汉,无人主持。适何来保、必振有函到汉,钟浩兄弟证明非伪,汉口总机关始以武陵之事委托何、赵主持。钟浩兄弟负往各县任指导之责”[1]304。
在自立会中,陈应轸(字小沅)是“为国民流血者”之一,他与赵必振既是同志,又是同里[1]279。《陈烈士应轸传略》披露:“癸巳乡试,居长沙,与君同旅舍。君负奇才,气势虎虎,……己亥之冬再一见之。庚子勤王事起,君与其事。蔡烈士钟浩屡为余言君之为人。未几,君以事赴澧州,过常德,一宿即去。蔡烈士告余曰:‘小沅昨日至,短衣匹马,大有燕赵豪士之概。’余心识之。以为君返当复见,而君又自澧州折而赴汉镇,始终不复得见云。汉镇事败,君遁归里,……由间道出海外。……居无何,君又赴沪,将有所谋,为捕所获。……急逮至鄂,酷刑严讯毕,遂就义于武昌唐、林诸烈士成仁之所。”[1]278
另外由赵必振校补的《自立会人物考》陈应轸称,陈应轸“居岳麓书院,与必振订交。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应轸亦自立会会员。武汉自立总会失败,各县机关皆不能自存。应轸犹骑马至常德,欲谋抵抗。既知势不能敌,始亡命赴沪,为反水者所卖,在沪租界被捕,解至南京,转解湖南,已无生望矣!忽有夙不相识之湘人,询知应轸之父与张百熙为同年,乃自出电费,电百熙乞救。百熙既(即)电湖南当局,乃释”[1]308。
赵必振写的上述文字叙事清楚,文笔流畅,有血有肉,爱憎分明,充满情感。他刻画的人物笔墨不多,但有细节,真实可信,栩栩如生,使人读后留下深刻印象。这说明他的国学功底很深,完全胜任文字宣传鼓动工作。
何来保、蔡钟浩及陈应轸与赵必振一样,年龄“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2],与封建官场较为疏远。他们具有爱国情怀,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在自立会起义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三
赵必振关于自立会起义的叙事较早论述了这次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他说自立军计划“先组织五军……以湖北为中军,安徽为前军,湖南为后军,河南为左军,江西为右军”,在湖南的势力主要分布在长沙、岳州与常德等地[1]36。而“湖南夙为哥老会之巢窟,其会员约十二万”[3],对此基本省情,自立会领导人不会不知道,于是“在湘以长沙为中心,以保卫局为基础,舒菩生、李虎树诸子领导之,结纳会党首领马福益,率其群众,部署于浏、醴一带为策应”[1]260。
为何要引入哥老会的力量呢?赵必振解释说:自立会成立后“皆文人无武力,不足以集事。乃推唐才常为东南各省之分会会长,林锡珪副之,设中、左、右、前、后五军;更联络东南各省之江湖豪杰担任军事。又仿江湖豪杰秘密会中之票布为富有钱票,给江湖中各兄弟。平时则与票布同效,成军时,则如今日士兵之符号,佩以为证。清吏官书,误以为持此票者即为首要,此妄说也。在武汉三镇,皆有总机关,各县郡县,皆有分机关,假旅舍之名,以掩人耳目,所谓‘某某公’(即公寓之意)者皆是也”[1]302。长沙机关称“招贤公”。清朝官员的奏折也证实了这点。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擒诛自立会头目折》中称,自立会“入会者亦不尽康党……两湖会匪又最多,……其军名曰自立军,勾煽三江两湖等处哥老会,纠众谋逆”[4]。湖南巡抚俞廉三也在奏折中说:“大抵此项匪徒中有二等:一系文人,皆在各处学堂肄业;及曾经出洋学生,与康有为等交往素密。一系痞匪,即内地旧有之会匪痞徒。”[5]撇开其中的污蔑之词,是符合自立会有文事会员、武事会员的基本构成的。时任湖南按察使幕僚的李莲航(名昭慈),“缉捕者至臬幕搜查,得未经散布之富有票数簏,昭慈因是被杀于长沙之浏阳门外”[1]303。
参加自立会起义后在长沙被刑毙的谭翥“为会门中之忠实者。参加自立军后,在长沙进行甚力。武汉总机关失败,长沙组织中有反水者秘报清吏,遂被捕,就义于浏阳门外。翥为长沙靖港人。既就义,清吏以其头解至靖港,悬于河干之路灯柱,观者纷集其下,议论纷然。必振适亡命过靖港,以发太长,至河干剃之,因知其事”[1]309。赵必振还指出湖南哥老会著名首领“辜万年,字鸿恩,长沙人,被捕死于鄂狱。”[1]315。另有“石竹亭,湖南武陵人。为会门之健者。殉难于常德”[1]331。
所有这些都为后人研究会党与自立会起义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史料。自立会纲领本身的不彻底性以及与下层会党联络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这一起义势必失败的结局,何来保、蔡钟浩等百余人在湖南殉难。
四
赵必振本人写的有关自立会起义的回忆文章与人物传纪,同时也披露他本人在这次起义中的作用与地位。由于他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在常德地区重要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因此自立会起义失败后,遭到了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列名通缉。赵必振经桂林、澳门,逃亡日本。亡命日本期间,赵必振曾任《清议报》《新民丛报》校对/编辑等职,常以“赵振”“民史氏”等笔名撰文。其中何来保、蔡钟浩、陈应轸三篇传略就是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他在《清议报》社论《说动力》中论及自立会起义,认为“虽败犹荣”。另外赵必振在解放前有《自立会纪实史料》一稿(湖南省图书馆藏),全文共九章,约三万余字⑤。其中有一篇是非湘籍烈士《沈荩略传》。又有《自立会志士事迹略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解放后赵必振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1年他又对林绍先写的《自立会人物考》进行了补订,增添了自立会人物传略若干篇,提供了有关当时两湖死难诸人的一些资料,弥足珍贵。他在晚年写的《自立会人物回忆》中又透露了自己在1909年以两广总督袁树勋督府文案的身份“奔走期间”,参与营救被捕的自立会同志龚超的故事。由此可见,自立会起义给赵必振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历时半个多世纪,他一直念念不忘,在不同的场合写下了大致如一的回忆文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
不过,赵必振的论述也有不尽人意之处。首先,史学界通常认为自立军左军统带是桃源会党首领陈犹龙,起义之前他还在武陵县接纳了宋教仁等人为富有山堂的会员[6]。赵必振对陈犹龙并不生疏,起义失败逃亡期间还与陈犹龙等人在澳门共同赁房居住过。不知何故,赵必振对陈犹龙的事迹讳莫如深。究竟谁是自立军左军的负责人,有待进一步的考订,赵必振的论述难以成为定论。其次,赵必振对哥老会的制度并不熟悉,他说哥老会某某公即公寓之意是不对的。某某公实为哥老会分支组织某某公口的简称,辛亥革命云贵川三省光复后完全公开,挂出了牌子。再次,有人认为常德自立军的密谋实则毁于哥老会成员石竹亭的多嘴饶舌,此人“在外张扬特甚,大有逢人遍告之势”[7],因而走露了起义风声。赵必振对此没有提及。淡化处理殉难者的失误虽是人之常情,但无助于吸取经验教训。
自立会起义失败后,一些有觉悟的幸存者另找出路,再显身手,赵必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日本期间他从事日文翻译,先后译书三十余种,最著者是日本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版)、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刊行),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者之一。联系到他1900年参加自立会起义,其思想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进步脉络还是有迹可寻,决非偶然。
注 释:
①收入《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载于《求索》1983年第1期。
③载于《常德县文史资料》第三辑,1987年。
④载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⑤其前七章后为岳麓书社1983年出版的《自立会史料集》所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