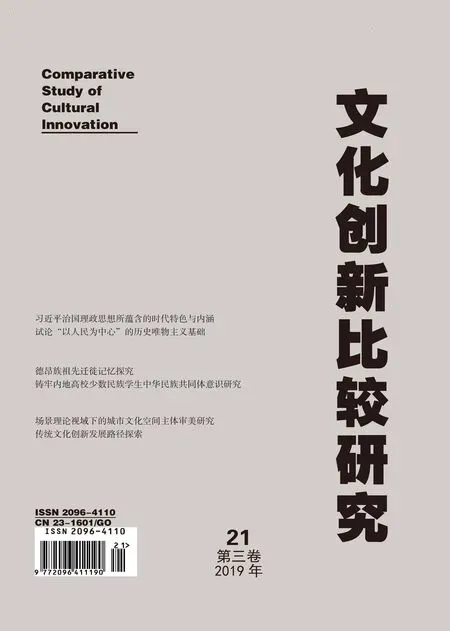透视小说《应物兄》中的“情”
光同敏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应物兄》是一部全面透视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长篇叙事小说。小说的叙事如王鸿生先生在他的评论中所言:“小说从来不追求着一条线讲述,而是不断地脉线头,不断地丢下这个线头又岔到开去捡起另一个线头。”[1]作家从人物写到动物、植物、器物、玩具等,仅动物就近百种,植物数十种;从生活写到工作、闲暇、应酬、偷情,小到家庭琐事大到社会时局无所不包。内容涵盖了多门学科,如历史、生物、文学、艺术、医学、风水、流行文化等,可称谓一部“百科全书”。行业跨度大,涉及了工、农、商、学多界,时空涵盖广,从国内写到了境外,谈古论今。
研读时常常会深陷“局”中,仿佛自己就是“局”中某个“符号化”的人物,应物兄?费鸣?陈明亮?还是……。尽管这个“局”是“虚设”的,但“局”里发生的一切仿佛是那么的“真实”、“贴近”,又那么的“荒诞”、“无聊”,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把现实生活透射出来,把当今知识分子的遮羞布扯得一干二净,让它完全“裸露”在读者面前。这部抓人小说的起、承、转、合围绕着建“太和院”展开的。所有的人物关系盘根错节,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复杂的知识分子社会。“名利”、“排挤”、“乱情”尽收眼底。小说可评点之处非常之多,本文仅就“情”展开论述。“情”是贯穿整篇小说的一条线,许多小说均靠“情”抓人,没有“情”作品就索然无味,所以“情”是叙事小说绕不开的。小说涉及到了“爱情”、“亲情”和“友情”,以及男女之间的“乱情”。以下笔者就从“乱情”说起:
1 肆意妄为的“乱情”
A、在叙事小说中,男女的性爱描写不可或缺,因为“性”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孟子.告子上》中告子曾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2],孔子也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3]所以“性”是人之本能。似乎多数读者也乐意从小说中找出点“性”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男女的“性”描写古来有之,早期的《金瓶梅》、《红楼梦》,现当代的《围城》、《废都》、《活动变人形》等中均可见出。比如,贾宝玉与袭人,方鸿渐与鲍小姐,庄之蝶的多次风流韵事,倪吾诚与刘小姐等等。在“乱情”的描写中,作家的言说技巧也各有千秋。如钱钟书寥寥几笔就交代了方鸿渐与鲍小姐在船舱中“偷情”;王蒙描写倪吾诚找刘小姐的情节也很含蓄,贾平凹《废都》中的“性”常常是在此处省去几百个字。而《应物兄》叙事的特别之处体现在语言的“精细”上,过于精细的词汇紧紧抓住读者,使眼球寸步难离,甚至是无法抗拒,但这种“琐碎”的难免让人生厌,甚至是愤懑。于是疑问产生:“偷情”真是这样吗?作者的亲身体验?这种“赤裸裸”的描写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
A、小说中关于“偷情”叙事发生在以下人物身上。第一是主人公应物兄与朗月;第二是混血卡尔文的“乱性”;第三是程刚笃与易艺艺。应物兄仅有两次和朗月的乱性,在第七节“滑稽”中,“…捶向他的拳头…搂住了他的腰。隔着毛衣,她小小的乳房贴在他的胸口…没有把她推开……让他陷入了迷狂”,
第二十七节,…但是她很快就脱得一丝不挂…那颤抖的、滚烫的、多汁的肉鞘。她的腰弓起来,扭向一边…抬眼看了看她,发现她的头高高仰起…
在这两段描写中,可以见出应物兄在“应人”时,也处于“折中”状态,这样定义也许不一定贴切,但从生理角度讲,人具有动物性的一面,“性”是本能。情节中应物兄似乎不非主动的,而是“屈从”,这或许是作家的故意,但这种故意实则是一种嘲讽。作为男人的应物兄是一个深受儒家教理洗礼的知识分子,在行事时当然要保持一种儒家伦理下的“矜持”,恪守着“学者”的形象,行事是还默念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绝不了。如果真的有第三次?又会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作家把“道德归罪”的尺度留给读者,足见这种“反讽”手法的高明。从朗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女性“性”观念的变化。她是新女性的代表,她抛弃了儒家的“三从四德”,变得异常“主动”,偏偏喜欢和一个老男人“做爱”,反观社会当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B、小说中另一个“乱情”就是混血留学生卡尔文 ,在第十一节《卡尔文》…卡尔文尤其对她的私处赞不绝口…需要助跑才能插进去…“是啊,她的要害,就是对我的致命诱惑。”…小说中还有好几处卡尔文和女性“乱情”片段,这里就不一一举出。卡尔文受教于西方文化,他的“性”观念与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从行文中可以看出卡尔文就是一头喜欢“滥交”动物,但为什么会在中国有这么好的土壤?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女性愿意投怀送抱,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学问题。笔者以为当农耕文明被工业文明打败时,剩下的只是屈辱,文化上的自卑造成对西方的“盲崇”,“盲崇”通常使人迷惑,扰乱人的思维和辨别力,对于西方蜂拥而至的“精华”与“糟粕”无抵抗地接受,包括性观念。“纵情”与“滥交”成了一部分国人追逐的时鬓。小说没有对卡尔文的“乱情”作任何评价,但值得思考的是当下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好西方伦理与我国传统伦理的关系,保留什么?剔除什么?
C、第三对“乱情”的是程刚笃和易艺艺。在第84节“太和春煖”中…程刚笃就和易艺艺…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易艺艺翻过来翻过去,并且推拉着易艺艺的屁股,用她的阴部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脸…在这一段“乱情”中,程刚笃是大儒程济世的公子,依仗着他父亲的“名头”在外胡作非为,然而,恰恰有些女性喜欢迎合,像易艺艺。这透露出怎样的信息?为财?不是,为名,更谈不上,只能是心灵的空虚和生理上的需要,这是当下中国社会“乱性”的实情。小说在“偷情”叙事情节中着实用了不少笔力,辞藻运用的非常“赤裸”,把“性”“暴露”那么的“直白”,甚至让人“瞠目”和“生厌”。
2 复杂的“畸情”婚姻
在叙事小说中,作家往往会用大量的笔力描写男女的婚恋情感。通过对话和场景描写招人眼球,遣词造句往往催人泪下。在这部小说中确有纯真的爱情,这里无需赘述。笔者要评说的是几对非正常的“婚恋情感”。这几对婚姻严格意义上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因为他们“情感”的基础是“虚”的。比如应物兄和乔珊珊;乔先生与巫桃;栾廷玉与豆花。尤其是主人公应物兄与乔珊珊没有任何情感基础,也可以说是一种“屈从”。乔珊珊研究的是女权主义,她就是当下的一个女权主义代表,在她身上呈现的是 “蛮横”和 “自以为是”。此种性格的形成一部分是她对女权思想的曲解,另一部分来自他父亲的地位。她的初恋情人是郏象愚(敬修己),后来她又与别人搞“婚外情”,而应物兄对于妻子的出轨却“视而不见”,甚至是“麻木”,这种恰好对社会现状一种反讽。
前段时间的一个讲座说现在欧洲的男子有百分之三十不能生育,上海已达百分之二十。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这说明了什么?是“女权主义”的扩张?还是快节奏的社会使得女性越来越“彪悍”,男性越来越“娘炮”?这个问题很复杂。当今传统礼教的那个“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事务需要女子的参与。自五四运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了家门,成为了真正的“半边天”,这是社会的进步。
小说中第二对人物乔老先生与巫桃,他们的年龄相差很大。第三对是栾省长与豆花,豆花先是家政的老板,后来到了栾家,最后终于入了“正堂”。从小说中似乎看不出什么悲情,婚姻相对“稳定”。巫桃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豆花的手段也很“高明”,婚姻的男方一个是德高望重的知识泰斗,另一个是位高权重的政界大员,但假如男方不是有社会地位的乔先生和政界大员栾省长,这种所谓的“幸福”还会存在吗?这几对婚姻中多少有一种“嘲讽’意味,一种对当下社会婚恋的讽刺,爱情本该是神圣和纯洁的,但掺杂着目的就会变味。而以上婚姻恰恰如此,当然是我一家之言!
3 仍有余温的“亲情”
任何小说无论对情节和人物性格如何的夸张,对阴暗面的揭露与批判采用何种艺术手法,总能见出“真情”,否则就无公共的社会伦理了。亦如小说中程济世所言:“一个儒家可以节欲、寡欲,但不能寡情、绝情,更不能无情。”[4]《应物兄》中的“乱情”与“畸情”着实让人生厌,但还是在市侩的生活中见出了“真情”。其一是主人公应物兄和他的女儿应波,如:…只要应波一哭,不管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满足…,其二是到美国和女儿应波在一起短暂的两天,从他们的对话中能够体会一种久别“亲情”。世上最难割舍的莫过于“亲情”,父母对儿女的爱永远是无私的,俗语说‘虎毒不食子’。小说中体现出父爱如山,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应物兄勉强地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婚姻。
另一处是栾庭玉给他母亲刷马桶。可以见出栾省长对他母亲的“孝”,这段描写有点让人有点生厌,但确实富含真情。当下人们的道德观与价值观着实扭曲了,好的伦理习俗正在消亡,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如何传承良好的伦理习俗是当下必须面对的话题。
4 “情”背后的思考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也有写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但如此深刻地透视知识分子的非《应物兄》莫属,小说的“起、承、转、合”中无不见出“情”字。作家把三种“情”呈现得淋漓尽致,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使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与世界接了轨的同时,却忽视了人文,从而导致了功利主义的抬头,“钱”成了社会的价值标准,致使物质与精神的发展发生了错位,从而导致“乱情”和“畸情”现象的发生。《应物兄》像一面镜子一样透视了社会实情,这种嘲讽式的纰漏提醒该是重新建构正常伦理体系时候了。
注释
[1] 《收获》,长篇专号,王鸿生,《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 事心事之间关系》,2018年;
[2] 孟子及其学生著,《孟子.告子上》,查自360网页;
[3] 曾子等著,(汉戴圣编篡),《礼记》,查自360网页;
[4] 《收获》,长篇专号,李洱《应物兄》,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第7节,第11节,第27节,第84节。
——论李洱《应物兄》的空间叙事
——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