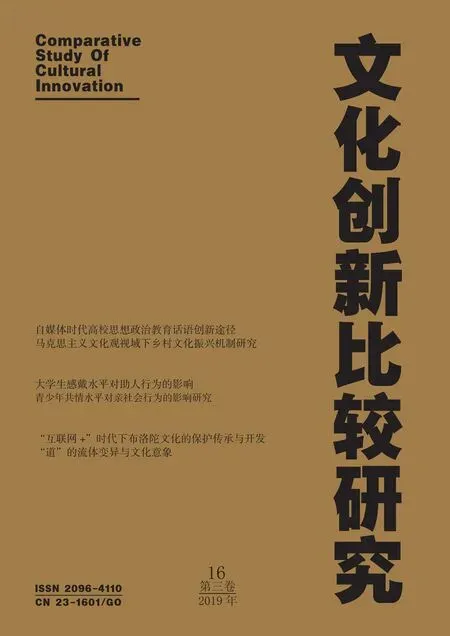“道”的流体变异与文化意象
李静
(1.辽东学院,辽宁丹东 118001;2.辽宁省文化社会学学会,辽宁丹东 118001)
中国文化滥觞于先民宗教文化时代,铁证在于道现象和道文化的出现。道现象认知衍生的道文化,避免了西方中世纪的文化倒退,也奠定了东方文化的基础。然而,道文化容括的内涵丰富,范围庞杂,使得道文化在虚实、交葛、界域之间飘忽地游荡。不难发现:在中国文化研究中,“道”“道家”乃至“道教”研究,可谓蜂飞蝶舞。始于古代文论而大兴于传统文化的道文化研究“成果”,更堪称著述如林。然万般景象之于道、道家、道教的解析,笔者所见不多,且语义界定的芜杂,乃当下“国学”研究中一种普现的“通弊”。事实上,道之谓道,乃中国文化时代的先人感悟并知觉对象世界的结果; 道家之谓道家,乃老聃、庄周体认道、膜拜道之“天理”的创化性结论;道教之谓道教,实乃如“程朱理学”之于儒家的极致性图腾处理。故,清厘道文化本源,界说道家与道教对道文化的承、认、括、结及教化性处理方式,乃解说道文化至今被崇尚的合律本质与道哲学融古今而通世界的价值逻辑。但是,目前围绕这一点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其研究意义也鲜为人们重视。因此,该文立足中华文化视野,以“百物崇拜”、道家、道教、多元文化激荡为背景探讨意象。
1 “百物崇拜”历程的意象答案
“百物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界一般被理解为近存原始社会的宗教,其研究即根据对原始民族宗教崇拜的考察; 而通过考古发掘所证实的、 在成文历史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远古原始宗教则被称为史前宗教。二者实质相同,其基本特点都包括对食物、繁殖、祖先、死亡、自然万物以及社会群体的神秘观念和祈求敬拜,并由此发展出对超自然体之神灵的信仰及崇拜。” “百物崇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自然崇拜。自然崇拜时期天神、土地、星君、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山神、河神等是人们的崇拜对象;二是图腾崇拜。“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因此,有了如龙、凤、熊、虎、玄鸟,花、槐等崇拜对象。在中华文化历程中,“道”是中国人摆脱恐惧与建立希望的思维产物,其意象由直接和间接两个层次构成。
1.1 直接意象:寻找一种信心
约在公元前5世纪,人类处在智能大奠基阶段。为了满足需要,人们把不能理解的一切归结于神秘,“百物崇拜”就是人类先民的共同特征。事实上,“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这种反映,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进一步发展,不同的民族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复杂的人格化。”这一时期,关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先民有了自己的感悟,道字的创化就是具体呈现。通过考古发现:“道,金文(行,四通的大路)(首,代表观察、思考、选择)(止,行走),表示在叉路口帮助迷路者领路。有的金文加‘又’(抓),表示拉住迷路者的手引路。有的金文则加‘又’加‘爪’,同时加‘曰’”(说明),表示领路者且牵且讲,帮助迷路者弄清方向。”什么是方向? 其实就是可以获得心理慰藉的追求对象,有学者直接解释为路,笔者认为,这只是表象,深层次的意象实际上是指生存的信心。
1.2 间接意象:寻找一种思维
“生存的信心”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既表现出意愿,又表现出对行为的规范,还表现出对存在意义的探求,这一点可以从“道”的金文字形的形成看出。起始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殷金文),经历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西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东周金文),至前221年~219年(秦汉金文),前后约496年,占卜龟甲上的甲骨文被学界称为可以识别的最早的中国象形文字。虽然,我们至今仍未发现甲骨文中的“道”字,但金文的“道”已经可以说明。“道”的“中间下面是人的头部,头的上方是一个气路象意符,几条脉络与天相通。四边外围的几笔,象征四通八达。会意:人通过头顶的气路,与自然相感,四通八达,毫无滞碍,明明白白。天人合一的状态,就是道。……中间一根柱子,外面像DNA 的双螺旋一样,直通天上。当能够保持与大道相通、与天相连,源源不绝获得天德的能量滋养自己的肉体和身心时,这个时候就会处在道中;而且,这种能量还可以向四周散发,帮助四周,使这些人能够飘起来。”这实际上是在回答“生存的信心”应该来自哪里,答案是人的意愿要符合天的意愿,人的行为要符合天的规范,人的意义是天赋予的。应该说,这是古老的道家思想的主体意境,呈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也开启了中国人认识天、地、人的实践。
2 道家总结历程的意象答案
时至春秋,“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老子,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正式成型。从此成为古往今来治国治家的至尊宝术。以黄帝、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管子、鹖冠子等等为主要代表,主张‘无为、璞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等等。”著有《道德经》《道家易学》《文子》《庄子》等著名道家经典。其中,《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此为背景,“道”因此又有了直接和间接两个层次的文化意象。
2.1 直接意象:路
人们对“生存的信心”和“生存意义”的寻找,需要一个载体来实现,它便是路。什么是路? 路在哪里? 这在“百物崇拜”时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而“道”在经历了道家对这一时期的系统总结之后有了最为直接的认知。春秋战国之后,“篆文基本承续金文字形,省去‘又’和‘曰’。隶书将篆文字形中的‘辵’写成;将篆文字形中的写成。当‘道’的‘向导’本义消失后,篆文再加‘寸’另造‘導’代替。”《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从辵从。一达谓之道。古文道从寸。徒皓切。”“‘首’,代表人的头面部。头上的三竖,表达头顶之上三缕气流,冉冉而上与天相通。就表明还是要与天相连,要把自己的天门敞开,获得天德的能量,那么自身的能量场才能扩展开来,影响和帮助别人。”寻道的原因在于“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1]。”不难发现,这一时期,“道”的意象已经超脱了“生存的信心”的范畴,聚焦于“生存意义”范畴中的思维之路。
2.2 间接意象:天路
沿着“生存意义”的思维之路,即如何思维自身的意义?关于“道”字的间接文化意象,可以依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汉字构造原理阐述(六书),并将“道”字的演变与时代背景有机结合起来。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对“道”的总结是以世袭制为依托的,以“敬天法祖”为正统信仰,于是有了姜子牙、姬昌、姬发等描绘世袭制的神话与人们获得思想自由愿望的交织。于是有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的思想主旨,有了“道法自然”“为而不争”“清静为天下正”、虚其心和“正言若反”五个基本原则。由此不难看出:道家对“生存意义”的思维中“道”的意象内涵既有了“获得思想自由”的神仙境界,也有了以世袭制为内容的社会思维,所谓的“天”实际上是自然和社会崇拜的混合体,此即天路之意象。
3 道教历程的意象答案
汉朝后期,春秋战国时期的以崇拜诸多神明为形式的以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为宗旨的方仙家,在这一时期有了教的团体,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以道为至高信仰,认为无形无象、玄之又玄、无法言说。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散则为气,聚则为神。”以此为背景,“道”的直接和间接两个层次的文化意象又有了新意。
3.1 直接意象:德为贵
秦汉时期道教、儒学、佛教盛行。期间,道教成为东汉时中国主要宗教之一,把“道”作为最高信仰。它基于最初传统神学建立的神仙谱系,即天神、地、人鬼的崇拜系统,逐步转换为对圣贤的崇拜,如孔子、孟子、关公等。如成书于东汉中晚期的《太平经》就有“圣人、贤人” ,《上清众仙真记》、《真灵位业图》、《无上秘要》等就列有尧舜禹三王和诸子圣贤孔丘、颜回、墨翟等。不难发现:这些崇拜对象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就是“德”,以德为贵因此成为其最直接的文化意象。
3.2 间接意象:天德与人德合一
“道”与“德”是道教教理的核心内容,“贵德”透视出“道”的间接意象。我们注意到:在公元前221年至1956年,高度集权的国家制度逐步形成,儒释道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家国一体化意识成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同一存在,巫术、神学逐步成为文化附庸,“道”字的直接文化意象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道教把与道合一看作是人智慧解脱的唯一路径,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道因此成为天地万物的产生过程,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个‘道’,……看上面两点‘丷’,拉开一点就成了个阴爻;下面一横,就是个阳爻,代表了阴卦和阳卦组合,不停地组合就形成了64 卦。这里面含着人生的许多道理,所以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就喜欢去求签问卦,实际上就沿自于这种外求的方式,自己都已经不再主动去跟天相通来开发自己的大慧,而依赖于别人的帮助,依赖于方法的运用。”本质上是在求得“天人合一”,即天德与人德合一。
4 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历程的意象答案
在当代,“地球村”的逐渐形成推动了各民族的文字改革,中国也如此。“从字体上看,繁简明确区分始于一九五六年,之前主要是繁体…繁体符合六书规则,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凡是韵母相同的绝大多数都具有相同的偏旁或部首。中国1971年进入联合国后,全面推广简体字。”我们注意到:虽然这一时期短暂,但就中华文化发展而言在质上的变化和面临的挑战是从未有过的,其直接和间接意象也随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而不断被深化。
4.1 直接意象:为谁
始自1978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一直在作用着国人对“道”的思维,围绕什么是道?许多人正在颠覆其传统意象。有人甚至认为,“简化到最后,把‘道’的这个‘首’旁,化成一把‘刀’子,写成了‘辺’,拿着刀子走遍天下,”虽然这种说法缺少学理根据,但问题指向却是命中要害的。我们不难发现:在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作用下,财富开始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富足成为多数人的依据,钱成为良心、脸皮、的代名词,也时刻成为支配人们思维的工具。因此,“道”有了以个人得失为中心的红、黑、白之分,为谁? 客观上成为“道”的直接文化意象。
4.2 间接意象: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
事实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就逐步成为中国人人生观、 世界观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道”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体现在社会主义这个‘器’之中,社会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手段,要为大众谋福利,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这个价值理性也一直处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制高点,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理’。”然而,这个“道”在当代面临着挑战: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道”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的“道”(资本)的挑战;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在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欲望空间的同时也无限地增强了欲所不能感。上述两个方面相互交织,致使许多人对“道”的理解处在功利、浮躁的怪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