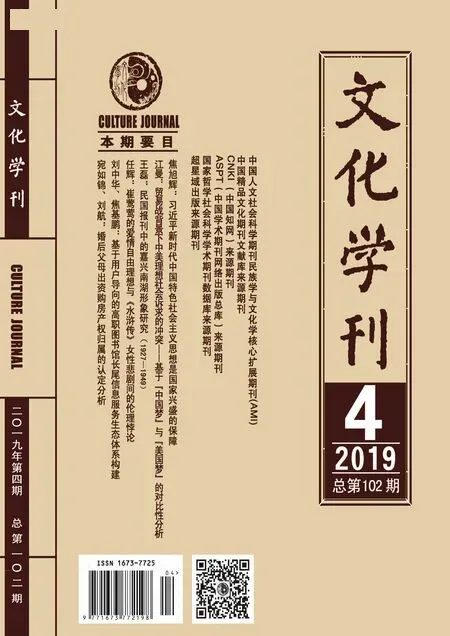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
盛百卉
知识社会学创始人卡尔·曼海姆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终其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一、学术研究轨迹
布达佩斯、海德堡、伦敦三座城市标记了曼海姆生平、学术研究及社会活动的轨迹[注]在三座城市的生活、学术研究及社会活动的时间段分别是1893—1920、1920—1933、1933—1947。。
曼海姆早年师从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这一时期的学术生活和社会活动所形成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及价值体系也成为一种底色和基调,影响了他一生的理论思索。海德堡阶段是他理论研究的最重要时期,《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后者也使他成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在这部著作中,曼海姆指出:在社会群体中,不仅宏观上每一个阶级的意识是由它在社会中的位置所决定的,甚至从微观上讲,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信奉的“知识”都是由他赖以产生的社会情境所决定的。流亡英国期间,他更加关注社会现实,聚焦于战后重建问题、民主社会的规划和教育等问题。《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自由、权力和民主规划》和《教育社会学引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二、知识社会学创立的时代语境
曼海姆认为,社会文化中的问题并不像自然科学问题那样遵循某种内在纯粹逻辑,它们仅在有限的层面遵循一种内在性,因此,知识社会学的创立是对以下问题的回应:“是什么知性的和生命(Vital)的因素使文化科学中的特定问题可能出现?这些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该问题的解决?”[1]曼海姆始终坚持“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力图通过对“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帮助人们找到可以信奉的新的“逻各斯”。
曼海姆所设想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通过个案在纯粹的经验层面探究知识与其产生情境之间的关系,同时把知识社会学与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他批判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只把各种观念的变化仅仅看作个体内部观念发生变化的陈旧方法,指出这种方法妨碍了人们对社会过程渗透学术领域的承认。他认为,个体的思想并不完全属于个体,个体在更大意义上是他所处“社会群集”的代言人和思想先行者。他同时指出,传统的认识论哲学忽略了“真理”和其原生土壤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真理”和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真理”被当作一株空中的植物悬置起来,供人膜拜。他尝试通过对“真理”有效性的研究避免其走向自身的反面——“谬误”,希冀建立一种知识社会学视野下具有建设性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并不忽视经验中那些无法量化的甚至含混的潜在力量对“真理”的影响。
三、核心问题
在阐发知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时,曼海姆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思维的孤立个体”和“社会群集”的关系,二是“思想的论战”与“政治势力的较量”之间的同一性问题。
曼海姆认为,虽然只有个体才能够思维,但是个体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发源于其自身内心世界,主导个体思维的是其背后那更广大的与其地位类似的“社会群集”。他提出:“从意向角度来说,知识社会学的探讨并不是从单一个体及其思维过程开始,之后便以直接运用哲学家的方式继续研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种种抽象高度为目的。毋宁说,知识社会学所试图领会的,是出于某种历史——社会情境的具体背景之中的思想。”[2]曼海姆的思索并不仅限于指出“个体思维”与“社会群集”的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各种不同思想之间的论战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具有高度同一性。“各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是人们通过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各种一目了然冲突而进行斗争的前哨阵地。”[3]现代社会政治斗争可以理解为争夺世界观阐释权的斗争。为了使自己具有正当性,它不遗余力地破坏对手的社会生存和知识实存所具有的基础。
如果说“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曾经一度作为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独有武器,那么现在,任何一个群体都会用它反对其他所有的群体。一旦认识到人的思想并不是在社会真空中产生和发挥作用、所有的知识都是与主体的地位、情境密切相关,人们就不会把一个时期内所谓的“真知灼见”当作终极真理来接受,分析这些“真知灼见”中哪些是“虚假意识”,哪些是“实在”,便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重要任务。曼海姆为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找到了两个主旨概念作为切入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四、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曼海姆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内部存在细微差异,而“更加精确地陈述这个概念的各种意义变化,可以对它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和历史学分析铺平道路”[4]。他将意识形态划分为“意识形态的特定观念”和“总体性意识形态观念”。“意识形态的特定观念”和“总体性意识形态观念”的联系在于:为了理解对手的真实意图,人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对手说了什么,而在于分析这种“言语”背后的各种社会条件。“意识形态的特定观念”同“总体性意识形态”的差异在于:持“特定意识形态观念”的人只把对手的一部分“断言”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而持“总体性意识形态观念”的人则把对手整个世界观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五、结语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上勾勒出“知识”与其“社会情境”“意识形态”以及与“乌托邦”之间的有机联系。为现代人重新审视“知识”“真理”等提供了新视角。在曼海姆那里,“知识”“真理”不再被悬置起来,它们产生于社会意识、政治生活的土壤中,并反过来对人类的社会意识、政治生活起作用。曼海姆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呈现一种中性色调,而乌托邦则呈现出一种积极色调,这对我们思考“知识”在建构现代性思想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