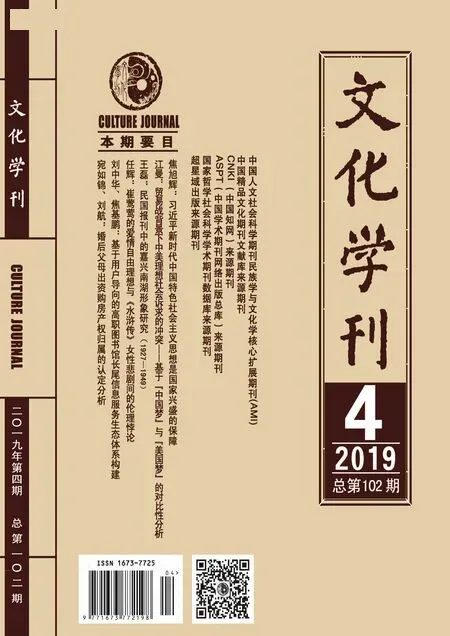王思任诗歌创作理论探微
董书研
作为明代的文学大家,对王思任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其小品文上,对其诗歌创作思想鲜有提及。其实,王思任的诗歌创作量也是极为丰富的。他的诗集有《尔尔集》《避园拟存》《律陶》《庐游杂咏》四种,《谑庵文饭小品》卷二中另存一部分,共计八百余首。在他的诗歌内容中不仅能窥测到公安派的影子,也有竟陵派的因子。王思任的诗歌创作理论没有系统的专门论述,但其许多诗学观点在他为朋友诗集所写的序文当中有所体现。作为明代晚期的一位诗人,王思任的诗学思想虽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但又彰显出自己的独特个性。
一、“真情”与“正旨”的融合
王思任在诗歌的内容创作上讲究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认为诗歌应该是最直接抒发胸臆的手段。在《袁临侯先生诗序》中,王思任言:“而临侯遇境摅心,感怀发语,往往以激吐真至之情,归于雅含和厚之旨,不斧凿而工,不橐籥而化,动以天机,鸣以天籁,此其趣胜也。”[1][注]文中所引王思任诗文均出自《王季重十种》。这其中的“激吐真至之情”便是“情真”,即诗歌讲究情真意切,不追求过分地雕琢修饰;“归于雅含和厚之旨”便是“旨正”,即是指不违背诗歌原有的“雅”的特点;“不斧凿而工,不橐籥而化,动以天机,鸣以天籁”便是“巧妙融合,自然天成”。王思任在《王大苏先生〈诗草〉序》说:“唐人之诗,韵流趣盎,亦只开口自然。莫强于今日之诗,玄深白浅,法度文章,何如捏作,要不过恶墨汁之图传也。”[2]他对唐诗高度认可,并对晚明诗歌创作中过度讲究诗歌技巧而放弃真情流露的创作观念予以批判,认为晚明的诗歌创作过于造作扭捏,忽略了诗歌的原始美感,而没有生动自然的妙处。
对“真情”与“正旨”的践行,王思任的抒怀言志诗中最能体现,其诗内容比较丰富,复杂多样的情感在一字一句中或强烈或平缓地流露出来,形成一股若隐若现的力量,牵扯着人们的心。而它在艺术性上也有着异于其他的独特之处。首先,抒怀言志诗与其他几类诗相比较而言,在整体上是风格最为悲苦与辛酸的一种。王思任的诗歌历来多谑笔,多乐处,即使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诗,也不过是愤懑与嘲讽,描写隐居生活的《律陶》一集中的诗,虽亦有苦味,但诗人总能主动地自寻解脱之道。然而,此类抒怀言志诗却是王思任内心极苦极酸处的直接呈现,并且诗人根本无法释怀自我和解脱,只好说些无奈的话聊以自慰。年华老去,孤独漂泊,家国蒙难,命运坎坷,王思任将这些人心里面最苦的东西一一展示出来,其诗又怎能不苦不酸?[3]《广福寺题壁》写诗人“谒官不得见”后的心理,既悲自身际遇之酸楚无奈,又叹家国危难的忧愁苦闷,令人不得通脱。其次,抒怀言志诗在情与景的巧妙融合方面较其他类诗更为突出。如《还罕山》一诗,诗人将自己的人生遭遇与山中景色联系起来。往昔青春年少,山寺是一番“妙香生清心,四时听鸟舌”的“饰洁”气象,如今却“荒云堕崩风,短篱补恒缺。空庭阒天僧,旧犬亦逃绝”。其实,这是与诗人后来坎坷悲戚的人生遭遇紧密相关的,正因为后来诗人经历的种种坎坷,有感于此,他才会选择这样的景象来加以描绘。“凄切”“昏惨”的景物正好能表达出诗人悲苦的情感。此处,情与景的融合十分巧妙,读来真切感人,撼动人心。
二、“韵”“趣”“秀”的统一
诗至明代,以“趣”“韵”论诗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明人手中,“趣”与“韵”已经成了诗歌审美的核心范畴,并有着不同以往的时代特征。王思任从接受学的角度,将明代的“趣”“韵”发扬光大。他认为,诗歌要具有“趣”与“韵”,自然不能仅含字面简单的意思,而应该由语言文字所构成的独特情境生发出更多更深的意旨,即言近旨远。在《〈方澹斋诗〉序》里,王思任讲得甚为具体:“吾尝谓太白终在少陵之上,即其寄托游仙泳女,一再读之,飘淫恍惚,而别离短促之景具是矣。”即通过诗歌的表面文字而感受到丰富的深层情感,《〈郁冈诗自选〉序》中也说:“诗之为道,大类于此,情境所触,语言文字不足以尽之,而尽之于一二韵语,第语在韵先,韵从触发,诗乃佳耳”。这仍然是谈蕴藉之美[4]。
当然,尽管王思任笔下的“趣”与“韵”在审美特征上具有一致性,但它们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审美范畴,仍具有它们各自的独特之处。首先,王思任将“趣”标举为诗歌审美的最高范畴,“弇州论诗曰才曰格曰法曰品,而吾独曰一趣可以尽诗。”“趣”是位于“才”“格”“品”之上的。其次,王思任论“韵”更强调“音”方面的特点,指声音的和谐、顺畅,各种不同的声音混在一起也同样能达到和、顺的美学效果。“诗有声口,一开即得,若复苏援塑捏,如何而诗,则诗之韵去久矣”,这即是王思任直接的观点。除此以外,王思任还提出了“秀”这一概念,在《〈李大生诗集〉序》里说:“而大生为之,趣盎味流,不啻镜花盐水,至其五言清矫,乐府之古澹,绝句之飘骚,汉唐兼用,元宋亦来,而总之一字曰秀。”在此,王思任认为“秀”是诗歌带给读者的整体审美感受,非一字一词所能涵盖,也就是李大生诗歌体式的不同艺术特征的总体表现。
三、反“拟古”,主“言己”
复古思潮在明代中后期是人们绝对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理想激荡着同时代的每个读书人。反对拟古拟人的观点在王思任的文章中直接出现的就很多,《〈何龙友先生诗集〉序》就言:“近目操管家谭诗,拳釱于法裁,削棘于品格,梦诡于澹玄,刀圭于韵字,闪倏逃寄,无可奈何,而诗道遂大苦。”与此相应的是,在给友人诗集所写序文中他常常褒扬对方不拟古,不拟人。如《袁临侯先生诗序》中说临侯之诗“新彩异光,不尚比拟”,《〈茵花馆诗〉序》言祝金阳之诗“不蹈古,不逐今”。王思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诗要“言己”“各任其性情之所近”。简而言之,诗歌应表达诗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和自己的独特个性及心理。在给朱宗远诗集写的序文中,王思任直言:“造物者既以我为人矣,舌自有声,手自有笔,心自有想,何以拟之议之。”人既为人,便有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为诗即是将这种个体自我的独特感受与体验抒写出来,若必拟之,则我何为我?“诗以言己者也,而今之诗则以言人也。自历下登坛,欲拟议以成其变化,于是开叔敖抵掌之门。莫苦于今之为诗者,曰如何而汉魏,如何而六朝,如何而唐宋。古也今也,皆拟也。人之诗也,与己何与?李太白一步崔颢语,即不甚为七言,杜子美竟不作四言诗,亦各任其性情之所近。无乐乎为今诗而已。”王思任以己之“性情”为立足点,批评今人为诗“皆拟”“言人”,未能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故“无其诗”。
四、结语
王思任的诗歌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不是仅囿于竟陵派诗人的忧苦孤寂。其诗歌在风格上或凄凉悲悯,或雄厚浑圆,或柔和秀蕴,或忧思感伤,各尽其态。在题材上,或小桥流水,或国破家亡,或茶酒书画,才情可见一斑。他的诗歌创作正是才情、才思的完美体现。在诗歌创作理论上较“公安派”“竟陵派”也是有许多创新,给诗歌带来别样的灵性与趣味,对当时刻板厚重的诗风予以改观。这就是王思任在中国的诗歌历史上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