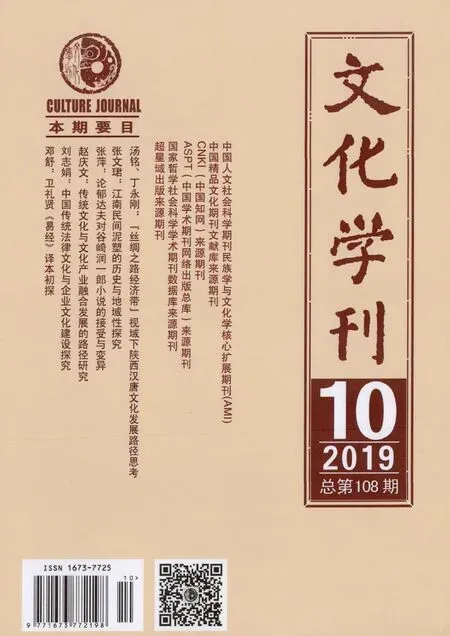日本近代文学对莫高窟藏经洞的文学形象建构
张 冰
敦煌是古代的绿洲城市,象征着富饶、和平、稳定,也是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之地。敦煌在古代丝绸之路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20世纪初期,西方探险家从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掘出大量古经文物备受世界瞩目,17窟因此得名藏经洞。人们对藏经洞的由来以及藏经洞中的古籍文物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与此同时,深受中国汉文学影响的日本东方学者和普通民众也对敦煌以及藏经洞产生了巨大的向往和热情,甚至出现了以藏经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了近代日本对丝绸之路认知的一个重要侧面。本文选取松冈让的《敦煌物语》、井上靖的《敦煌》、陈舜臣的《敦煌之旅》三部不同时期创作的日本文学作品,深入探讨文本中对莫高窟藏经洞的文学形象建构,结合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在横向的文学描写中探究作品的异同,进而透视日本近代文化中丝绸之路的形象特征。
一、“百科全书”式的小洞窟的相同认知
三部作品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形象建构的相同点主要为对藏经洞位置、大小及洞内古籍文物的描述。
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关于藏经洞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洞窟曾经颇受争议。之所以有人认为藏经洞不能成为独立的洞窟,大概与其位置和大小有关:“从藏经洞与16窟相对的位置来看,这是16窟的附属洞窟便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了。”[1]学界普遍把大洞窟旁附属的小洞窟看作是耳洞。三部作品对藏经洞位置的描述与普遍的观点相似,均提到藏经洞位于通往16窟的通道的右侧,即位于北壁一侧。通道右侧有一个“宽两尺高五尺的狭窄洞口”[2],即为藏经洞的洞口。关于洞窟狭小的特点,陈舜臣在《敦煌之旅》中是通过听闻的“小”与自己亲身体验的“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描述的:“虽然之前就听说17窟是狭小的耳洞,没想到却是如此之小的洞窟。我们从兰州来的包括陈家四人,甘肃省的老刘、小刘,还有北京旅行社的一位女性一行七人,再加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三位女性共十人进入17窟,就已经达到满员的状态了。”[3]陈舜臣通过亲身体验,生动形象地描述出藏经洞实际空间之小的程度。井上靖则是通过具体的数字进行藏经洞大小的描述:“洞穴大概是十尺四方的方形洞窟。”[4]松冈让虽然未具体描述藏经洞的大小,但通过对里面堆满经书场景的叙述已经能够反映出藏经洞洞内体积之小。“(藏经洞)是四角都涂过的石仓库。比前面的石室低了半米,靠着住持带来的小灯看向昏暗的内部时,忽然闻到一股古文书独特的味道。仔细观察,洞内是成束堆积且高达三余米的卷物。因这些如小山一般紧紧堆积在一起的卷物占尽洞内空间,所以人们一旦进入洞内便动弹不得。”[5]由此可以看出,洞窟内异常拥挤狭小。
尽管藏经洞十分狭小,但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物内容却异常丰富。松冈让的《敦煌物语》中描述藏经洞为“古代文明的宝库”,洞内包含多种语言和民族的古籍以及众多绘画作品,堪称古代文明的“百科全书”。由此可以看出,藏经洞虽小,价值却不可估量,对学术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其中,藏经洞中的佛经典籍超过总文物的90%,因此,三部作品对藏经洞之中的内容叙述离不开对洞窟内堆积如山的经书的描述。《敦煌》中描述洞中的典籍是包裹成束再进行存放和堆积,《敦煌物语》与《敦煌之旅》则是描述了藏经洞中的典籍在未被西方列强盗取之前在洞内整齐地堆积如山,在被盗取以及被清政府将剩余的物品保护起来之后,洞内仅剩一尊雕像及北壁上的壁画。这些藏经洞相同形象的构建体现的是作家们对藏经洞基本形象的共同认识。藏经洞内的文物由堆积如山到空空如也这一形象的变化,实则体现了藏经洞成为了近代西方列强“文化争夺的古战场”。“19世纪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开始将目光投向敦煌,这里宛若列强们的争霸场所,每年都会有一两个国家的探险队在这个地域的某一处挥动锄头挖掘文物。”[6]近代帝国主义国家打着科学探险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为了在偏僻的中国西北内陆进行地理考察,为实现自己侵略扩张的目的积极谋划,反映出近代西方列强的勃勃野心。狭小的石窟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引起热潮,不仅因为其中的文物内容丰富,还因为它是丝绸之路之上多民族文化与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与发展历史过程的体现。一个小小洞窟展现了横跨古今、连接东西的文化历史画卷,凝结成丝绸之路的一个缩影。三部不同时期的日本文学作品不约而同地关注藏经洞,突出其空间狭小与重要价值之间的反差,正是因为敦煌石窟藏经洞是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史上当之无愧的代表。
二、背景和经历影响下的藏经洞的不同认知
不同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人生经历的不同使得他们对莫高窟藏经洞形象的认识有所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但却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对藏经洞乃至对丝绸之路的文化认知。
1938年之前,敦煌仅仅停留在学者的认知范畴,日本关于敦煌的书籍资料大多是史书及敦煌学的学术成果,文艺界中却鲜有涉及。因此,要创作敦煌题材的作品,需要参阅史书文献资料和敦煌学学术资料,《敦煌物语》就是在此基础上创作的,成为了后世文艺界中创作敦煌题材作品参考性的小说。作者松冈让也在1943年出版的《敦煌物语》后记中表明,小说是“文化史式的作品”[7]这些都构成了该文本“知识性”的特点。也正是极具“知识性”特点的《敦煌物语》的出现,使得“敦煌”进入了日本普通民众的视野。松冈让出生于日本长冈县的净土真宗本觉寺,后因看清其中的黑暗而走上作家的道路,但其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一身份并未动摇。由于他掌握大量佛教知识,并且热衷于考古学,在《敦煌物语》中侧重于对藏经洞中的佛经典籍内容的描述自然不难想象。小说中提及伯希和在洞内翻阅整理古籍时,对佛经属于六朝写经还是唐经等内容与考古价值进行了分析等的内容描述,体现了小说描述佛经典籍内容这一侧重点。此外,松冈让创作《敦煌物语》之前有幸目睹了敦煌出土的写本,这也给了他一定的创作动力。自身的佛教知识与相关专著书籍的知识储备适逢藏经洞写本的出现,三者交织碰撞出文明发现的火花。
《敦煌》的创作时代背景可以分为两点:一是战后(从日本结束战败状态的1955年开始)大众社会文化的形成,历史题材成为大众文学的主流,井上靖开始转型创作历史小说并取得成功,《敦煌》是继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后的又一部力作。二是战败后的文化空白期,日本民众对文明的探索与溯源产生兴趣,某种意义上,井上靖的历史文学作品也起到战后精神救赎的作用。《敦煌》通过虚构的手法,将大众文坛的潮流与战后的现代人意识有机融入历史题材之中,其中不乏现代的“爱情”“执着”“无畏”“民族抗争”等因素。所以说,《敦煌》是富有近代人意识的虚构性历史小说。井上靖“在少年学生时期就学习中国的汉文学知识,并对中国的西域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在阅读相关文献史书的过程中,他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成因产生了较大的疑问,这一疑问也一直伴随着井上靖。直到1954年,他才决定着手准备构思小说《敦煌》,查阅诸多古籍经典并拜访敦煌学学者藤枝晃。”[8]此外,井上靖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曾担任过杂志社报纸宗教栏的编辑,这为其后来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一定的宗教知识与收集材料的能力。与松冈让的《敦煌物语》不同,井上靖称其创作《敦煌》的动机为虚构藏经洞的成因,因此,作品整体具有浓厚的虚构色彩,如作品侧重于对藏经洞不受战火侵袭也不易被他人发现同时是一个极佳藏身之处的特点的描述,这些特点既有利于藏经行为的叙述,也有利于突出作品虚构藏经洞成因的主题。虽然分析小说中的文本可以得出,“藏经洞的出现,是为了避免经书在西夏入侵沙州(敦煌旧称)时遭到战火的侵害与回教徒的破坏”这一内容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小说中的主要藏经人赵行德和他深爱的回鹘女、与他并肩作战的朱王礼,还有贪婪无耻的尉迟光,都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体现了小说史实与虚构相融合的特点。
陈舜臣的《敦煌之旅》诞生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个时期,一部分日本人可以进入中国西北进行旅行探访,这其中包括井上靖、司马辽太郎等。实地探访与文献叙述相印证,形成了这一时期敦煌书写的实证性特征。陈舜臣自幼就对中国历史抱有极大兴趣,成为专业作家伊始,就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创作作品,同时,陈舜臣本身也对美术作品有着较大的兴趣并且掌握相关知识,所以陈舜臣在《敦煌之旅》中侧重写藏经洞的历史由来和故事,并用大量笔墨描述洞中北壁的壁画《树下供养者图》。介绍壁画时,陈舜臣并非单纯地介绍壁画的构图及内容,而是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壁画具有写实性的特点以及指出这幅《树下供养者图》与其他洞窟内的壁画截然不同,评价壁画留白尽可能多的占用墙壁空间可以使观者身心得到放松。此外,陈舜臣对洞窟内张大千留下的字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与批判。这是另外两个作家所没有提及的。陈舜臣亲自到藏经洞内参观,才得以将藏经洞的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井上靖和松冈让则因为时代原因,作品创作时期未能亲自参观藏经洞,又因为藏经洞不断发生着的认识变化与史书资料未能完全同步,所以二者仅停留于史料的收集与虚构。藏经洞的成因至今仍无确切定论,但这并未消减人们对其进行探究的热情。陈舜臣叙述自己在藏经洞的所见所闻之前,对当时学界中得到普遍认可的两个藏经洞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成因之一是在宋朝时期敦煌受到党项族的入侵也就是西夏的入侵之时,为了防止佛经典籍受到战火的破坏故藏匿于此,又因其中没有值钱的金银财宝,所以逐渐被人们遗忘。另一成因是众人根据藏经洞的古籍经典中有许多残缺破损的佛经写本而推测,当初这里是被当作垃圾场来堆积废弃纸张的洞穴。”[9]对此,陈舜臣通过对藏经洞内具体形象的描述,否定了藏经洞为“存放废弃纸张的垃圾场”一说,并否定藏经洞是耳洞这一观点。陈舜臣这种实地访问后创作的方式,一方面真实展现了藏经洞的形象,另一方面体现了这个时期日本人研究敦煌以及丝绸之路文化较为重视实证性的特点。
三、结语
长期以来,日本都把中国的丝绸之路当作遥远的梦,提及敦煌、丝绸之路、西域等词汇时也都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近代以来,日本人对敦煌以及丝绸之路形象的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国民心理和意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这三部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可以看出,日本人对藏经洞的认识逐渐加深并摆脱了原本的神秘色彩,对其认知的方式经历了“想象—虚构—实证”的变化过程。藏经洞虽异常狭小,却成为跨越七个世纪之久的丝绸之路史的历史缩影。在日本近代作家笔下,它有着既包罗万象又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变换的形象特点。松冈让笔下的藏经洞是“世界文明的宝库”,井上靖笔下的藏经洞成为爱情、友情故事虚实相交的舞台,陈舜臣笔下的藏经洞则是艺术的瑰宝和历史事实的陈述者,这些形象特征共同反映了日本人认知的敦煌形象的独特特征。此外,对藏经洞乃至敦煌的文学形象的探究也在我国“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实施的过程中,对了解他者“丝绸之路”的认知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