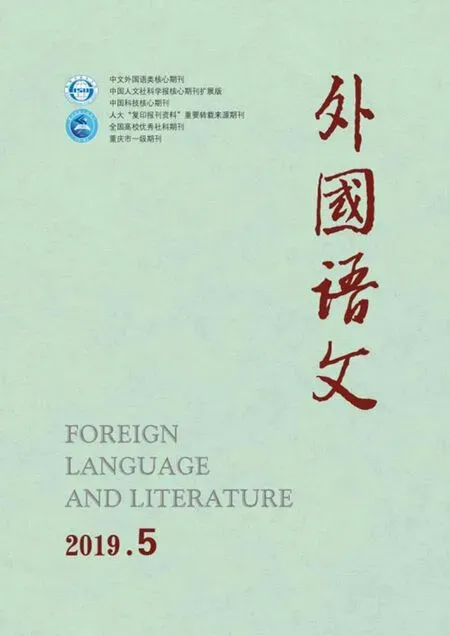计划化和组织化与翻译秩序建构(1949—1966)
林红 李金树
(1.四川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2.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1949年以降,中国迈入了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为荡涤旧社会遗留的“文明垃圾”,构筑新型的国家政治文化生态,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翻译活动被纳入国家体制,成为国家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轨道上有序开展。“计划化”和“组织化”成为翻译批评话语中的核心叙述,“建构起严格的翻译行为规范和翻译操作模式”(廖七一,2017:102),对彼时的翻译和翻译批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话语的梳理,以“十七年”(1949—1966)政治文化语境为背景,考察此一话语生产的原因、实施途径及其产生的效应,审视特殊时代语境下主导批评话语与翻译秩序重构之间的互动和勾连。
1 新中国成立前翻译乱象的批评
翻译活动“计划化和组织化”问题的提出,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渊源有自”,是有一定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的。从表层上看,是对新中国成立前翻译“乱象”的一种政策回应;从深层上看,是新中国整饬文化市场、厘清文化秩序、服务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翻译界公开提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组织化应肇始于沈志远。沈志远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他在《翻译通报》创刊号上发表《发刊词》,对解放前的翻译提出了尖锐批评:
旧中国的翻译工作,正如旧中国的其他一切事业部门一样,完全是无组织、无政府的。每一个翻译工作者,都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来进行;每一个出版家,也都把翻译书刊当作普通商品来买卖。译作者是为了生活,出版者是为了利润,私人的利益推动着一切。该翻译什么样的书,该怎样进行翻译工作,该采取怎样的方针来译书出书,哪类书该多译多出等等,这一切都是翻译者或出版者个人的私事,谁也不能去过问,市场的情况决定着一切。这种情况到今天自然就不能再容许其继续存在了。适应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转变:从散漫的盲目的状态转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状态。(沈志远,1950:2)
沈志远对旧中国翻译工作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1) 翻译出版机构“各自为政”,无组织、无政府、无纪律,整体呈现出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2)出版社(或出版家)把翻译书刊当作普通商品,追求的是“私人利益”,罔顾其“社会价值”;(3) 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翻译者或出版者“自己的私事”,缺乏“社会公益性”。显然,这些 “乱象”背离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必须得到纠正和治理。因此,翻译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便是情理之中的“大转变”了。
沈志远的《发刊词》“一语惊起千层浪”。随后,《翻译通报》发表数篇文章,声讨1949年前的翻译乱象,强调现今翻译工作计划化和组织化的必要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在批评者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翻译,“乱象”丛生,秩序紊乱,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对翻译工作认识出现偏差,缺乏正确的立场,对翻译的社会政治功能感知不足。禾金(1950:19)批评道:“翻译工作离不开政治,脱离了进步的政治立场而把翻译工作看作是一种‘纯技术性’的事情,这是愚昧!”大多数翻译工作者把译品当作一种商品,为了赚稿费,谋取私人利益,而不是为着大众的文化提升而翻译。谷鹰(1950:20)批评道:“过去的翻译工作,如像单纯商品生产一样,是独立的、零碎的、散漫的,各个工作者之间没有联系,好像大家都生产同一种商品一样,完全是自发的、无政府状态的。”这样一来,大家“疯狂竞争”,“组织和计划是不可想象的”,翻译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话也就落了空”(张荫槐,1950:19)。
(2)翻译者各自为政,缺乏组织性和必要的联系。导致的后果是:其一,翻译内容缺乏甄别,“泥沙俱下”,“谁高兴译什么就译什么,谁有机缘,谁就胡乱出版,致使好多不必要介绍的东西也介绍了来”(王子芸,1950:33),随意选择翻译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许多“不必要的书籍”,“一译再译”,另一方面,“很多名著至今尚无译本”(张子美,1950:34)。更为严重的是,还有“相当数量的译品,却传播着英美资本主义不健康的思想”,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群众的审美阅读,还“大大地伤害了我国文化”(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秘书处编译科,1950:34)。其二,翻译界缺乏统一的翻译公约和共同遵循的翻译标准,对广大译者没有统一的约束力。因此,翻译选材随意性大,翻译界缺乏沟通,抢译、重译现象严重,浪费了人力和物力,出现“劣译”驱逐“良译”的现象。
(3)翻译态度不端正,不负责,不认真,不严谨,因此,译品错误百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翻译状况最为诟病的“乱象”。沈志远(1951a:11)就曾批评道:“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作风,在我们翻译界中至今依然严重地、普遍地存在着。这是今天翻译工作的一切病态中最严重的一种,因而也是最急迫需要加以纠正的一种缺点。”
(4)为赶工期,抢译、复译甚多,缺乏必要的审校制度,因此译者对于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内容多采取删节,翻译既不忠实,又晦涩难懂,让人不忍卒读,生产出了一批粗制滥造的译品。申伏对此“乱象”有生动的描述。他写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翻译“草率从事,选译不精,粗制滥造。在这时期的翻译书,许多是既不信,也不达;或信而不达,或达而不信,就达的另一意义说仍是不达。有的甚至错误百出,流传谬种,不可卒读”(申伏,1951:32)。
简言之,在批评者看来,1949年前的翻译,无论是观念上的翻译认知还是现实中的翻译选材、翻译态度、翻译制度等,都存在事实上的秩序紊乱和观念上的认知错位。这些紊乱和错位的根源,“一言以蔽之,可以说就在:无组织、无计划、非集体的”(申伏,1951:32)。因此,要清除这些根源,建构新的翻译秩序势在必行。
2 新中国成立之后翻译秩序建构:途径与效应
随着旧社会的解体和新中国的成立,旧的翻译工作赖以生存的政治和文化土壤已不复存在。为适应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建立新的翻译秩序已迫在眉睫。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组织化呼之欲出。无论是舆论批评,抑或全国性翻译刊物的创办与翻译出版机构的成立,还是全国性翻译会议的召开,都围绕“计划化和组织化”展开论述,服务于新的翻译秩序的建构。
2.1 翻译批评话语的“计划化和组织化”
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开启了翻译批评话语“计划和组织”之门。各路人士纷纷为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献言献策,凡涉翻译批评,几乎到了“言必谈计划和组织”的地步。计划化和组织化成了翻译批评话语的核心叙述。兹摘录几段如下:
(1)针对目前翻译界无组织、无计划、无政府的客观现实,我们要解决三个根本问题,即“成立翻译工作者自己的组织;编制全国性的翻译计划;建立翻译工作的统一领导”(董秋斯,1950c:4)。
(2)一些精通翻译的专家,“多数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来搞翻译,没有从人民、国家的需要出发”,“翻译工作需要管理,不是依靠翻译的兴趣和主观判断来决定翻译什么,而应该有审查”(1)语出胡乔木在1951年8月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的讲话。这似可视作高层领导人对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释放的积极而强烈的信号。这一信号,一是强调了翻译需“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社会功能;二是强调了翻译的组织纪律性,暗含政治对翻译的规训。(邹振环,2000:284)。
(3)未来的翻译计划必须切合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有系统有重点地介绍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作品;对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亦须加以批判地介绍(阎庆甲,1951:15)。
(4)为了更好地做好翻译工作,也就是更好地完成翻译工作者的政治任务,把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统筹计划是极端必要的,单靠个人孤军苦斗是不行的(吕德本,1951:42)。
(5)适应时代把翻译组织化、计划化、集体化、规律化,而绝不机械化。今日翻译要好,要让人满意,要效率高,第一必须建立组织,编制计划,彼此连贯,互相配应,集体执行。一个口号就是翻译的计划化。在翻译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申伏,1951:32)。
(6)为解决组织问题,建议编译局可以采取六个步骤:1)调查翻译人才;2)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3)各专门委员会议定翻译书目批次、完成时间、译文标准等;4)编译局规划书目,征求承译人;5)编译局聘请专业人士审校译稿,并印行;6)编译局设立长期委员会,终审译书,定为国订本(袁昌英,1951:50)。
(7)希望在各地建立起翻译工作者的组织,设置够用的参考书(吕叔湘,1951:8)。
(8)我们的翻译计划里应当包含的几件比较重大的工作内容如下:1)总结经验建立理论,可先以编撰“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为中心工作;2)编撰辞典统一译名;3)翻译各科学术名著;4)审定经典著作译本(罗书肆,1951:15-16)。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批评者既包含政府文化官员(如胡乔木),也包括专业批评家(如董秋斯、吕叔湘),还包括一般翻译同行(如阎庆甲、申伏等),由此形成批评的“多声部”。不同的批评者基于自身立场,对翻译工作“计划性”和“组织性”的目的、实施途径、意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论者的表述各异,但话语内涵基本一致:均认同翻译工作“计划性”和“组织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期望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论者的批评话语选择和翻译政策倾向性形成了某种“话语共鸣”,使“组织性和计划性成为主流批评话语中频率最高、最核心的关键词”(廖七一,2017:98)。毫无疑问,批评话语的聚焦,为翻译秩序的建构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和充分的批评空间。
2.2 《翻译通报》的创刊和翻译出版机构的成立
翻译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充分的舆论批评空间,还需要可观可视的实体支撑。因为,翻译工作的 “计划化和组织化”,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全新”的观念存在于批评者的话语之中,它还必须落实到现实的“物化”之中,成为秩序代言的实体存在。这一“物化”的表现形式就是《翻译通报》的创刊和全国性翻译出版机构(中央编译局、外文出版社等)的成立。
《翻译通报》于1950年7月1日创刊(2)创刊日与党的生日相同,笔者手头上虽没有相关资料证实,这是偶然为之还是有意为之,但从沈志远的《发刊词》中,我们可以窥见,这样一份刊物的诞生,是党和新政府领导下的结果。,是新中国第一份翻译工作者专业刊物,其中心任务就是“使全国的翻译工作能够逐渐走上有组织有计划的道路”(沈志远,1950:3)。在其正式公开发行的第一期,沈志远(1951b:1)又重申了《翻译通报》的办刊动机与使命:“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把翻译工作“从无组织无计划的状态逐渐推进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状态”;“通过批评、研讨和经验交流”,提高翻译作品质量,“担当起人民中国和人民世纪所赋予它的时代任务”。显然,沈志远着眼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给予《翻译通报》庄严的“时代任务”,为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呐喊助威并身体力行。
《翻译通报》在其《发刊词》中就旗帜鲜明地确定了刊物的四项宗旨:加强翻译工作者间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每期都辟有“翻译界动态”“翻译计划”“翻译计划调查”等栏目,通报全国翻译工作者的工作和翻译局的翻译计划。饶有意思的是,1951年第2卷第1期的尾页,编者设计了一个“全国翻译工作调查表”,以出版总署编译局的名义致“全国翻译工作同志”,调查以下内容:原著外文书名、原著者姓名、原书译名、原书出版者名称、原书出版日期、原书版次、译介进程,其调查目的为“编制全国翻译图书目录,了解全国翻译工作情况,使全国的翻译工作逐步走向计划化”。虽然,因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翻译工作者填写并反馈了此表,但可以想见,这份唯一的、全国性的翻译刊物,在传递“国家声音”,推行翻译工作“计划性、组织性”所发挥的作用。
《翻译通报》的创办,意义非凡,它“引导当时中国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健康有序发展”(穆雷 等,2016:39),在建构新的翻译秩序中,其“耳目”和“喉舌”作用显著。其一,作为国家级刊物,很好地充当了国家翻译政策计划化和组织化的舆论宣传阵地。赞助人通过刊物用稿要求、栏目设置、编辑方针等,限制和规约刊发论文的内容,引导翻译工作者,从而把控和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翻译观。其二,发表翻译批评文章,展示不同声音,通过学术争鸣,整合翻译秩序。无论是对翻译选材,抑或翻译操作流程,还是译作评价规范,众多翻译同行都积极撰文,倡导翻译秩序的嬗变。如袁桂生(1950)、王宗炎(1950)、范之龙(1950)、江心(1950)等都呼吁,要积极翻译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的进步作品;周华松(1951)、裘景舟(1951)、徐永煐(1952)分别探讨了译名统一、合译模式、集体翻译等问题;吴文金(1951)、金满成(1951)、石宝瑺(1951a;1951b)等探索了译作的评价模式和标准问题;董秋斯(1950a;1950b)、焦菊隐(1950)、汤侠声(1951)、赵少侯(1951;1952)等发表翻译批评研究文章,阐释翻译批评的目的、原则、标准、方法及态度,建构翻译批评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发表的关于翻译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大多是翻译秩序文字技术层面上的探讨。但在后期(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之后),翻译批评有时甚至上升至政治叙事高度,由翻译秩序的整合引申至政治秩序的规范。其三,《翻译通报》犹如“公告板”,力主和助推翻译秩序的计划化和组织化,起到了翻译信息互通有无的媒介作用。自1950年第2期始,《翻译通报》每期均辟有“翻译界动态”“翻译计划”或“本刊小广播”等栏目,刊载相关单位或个人的翻译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重译、抢译、浪费翻译资源的现象。如《翻译通报》在1951年第1期第34页的“本刊小广播”中列举四例来信,皆因见该刊翻译计划信息而停译或终止翻译相关书籍。
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还体现在翻译出版机构的创立上。1949年后,为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式,呼应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组织化,有关部门相继成立了两大翻译出版机构,即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外文出版社。限于篇幅,本文无意讨论这两大机构的翻译出版详情(3)具体详情可参读倪秀华、滕梅、吴菲菲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只简要论述其在新的翻译秩序形成中的作用和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首先,翻译出版机构的成立从根本上保证了翻译工作的组织性,确保翻译选材的目标性和体系性。这从有组织、系统地翻译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便可知一二。毛泽东曾在1953年1月29日做出批示:“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二单位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俞可平,2010:6)据王子野(1993:58)统计,截至1956年,已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241种,印行了2700多万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共印行25.6万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共印行了近40万册。马、恩、列、斯的三大全集也开始翻译出版,至1956年,《斯大林全集》13卷全部出齐;《列宁全集》(39卷)出版了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出版了第一卷。毫无疑问,上述经典著作翻译出版秩序的形成,中央编译局功不可没。
其次,翻译出版机构的成立,不仅体现了新政权对翻译工作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组织的形式,将一大批翻译人才(翻译家)纳入体制,给予工资和行政级别,进入体制化的运作空间,从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译者秩序的整合。正如李洁非(2014:26)所言,其着眼点与目的,“是构建、定位文学的行政秩序”,“保证文学事业与党和国家整个政治的一致性”。这即列斐伏尔所说,用赞助的形式,影响或主宰译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译者的身体“被纳入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作为一个驯服的生产工具进行改造”(汪民安、陈永国,2003:20-21)。此举一方面是对译者物理空间的身体规训;另一方面,通过体制内的大会、文件学习、规章制度贯彻等等对译者进行精神空间的思想塑造。
最后,国家体制的翻译出版机构,一方面凸显了集体的资源和人力优势,群策群力,发挥集体翻译的长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遮蔽翻译审美和翻译批评的个体差异性,较易导致翻译行为的单一性和翻译主题的泛政治化。1949年伊始至1958年,这十年对苏联文学译介的热宠,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青睐,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简言之,翻译者或批评者职业化了,批评话语的生产也“体制化”了。批评者的思维和视点受政治的制约渐增,很大程度上都要接受主流政治话语的召唤。因此,翻译或翻译批评中的“我”就不由自主地或潜意识地被“我们”所代替,实难发出个体或“个性”的声音。
2.3 翻译会议的召开
为扭转新中国成立之前翻译“乱象”丛生、秩序混乱的局面,响应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组织化,促进翻译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交流,统一思想,协调各方声音,召开全国性的翻译工作会议势在必行。
1951年11月5日至12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胡愈之致开幕词,对“目前翻译出版物的质量低,重复浪费,翻译工作缺乏计划性”等“最严重”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同时号召代表同志们共同努力,使“以后翻译出版物逐步消灭错误,提高质量,走上计划化的道路”(胡愈之,1951:4)。沈志远作了题为《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主题报告,不仅总结了目前翻译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4)这些缺点包括:第一,缺乏严正的政治立场;第二,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作风;第三,抢译乱译,重复浪费;第四,混淆黑白,歪曲原意;第五,死译硬译,文理不通;第六,任意增删脱漏,破坏原著体系;第七,不通业务,杜撰译名,剽窃他人,据为己有。沈志远.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J].翻译通报,1951(5):10-12.,还提出了有计划、系统地开展翻译工作的七个具体任务和两个基本政治任务(5)今后翻译工作上的一些重要的具体任务:一、制定全国翻译计划;二、确立必要的工作制度;三、逐步建立专门性的工作组织;四、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五、统一译名与编撰各科辞典;六、研究和整理翻译经验、确立翻译标准;七、培养专门的翻译干部。两个基本政治任务:有计划、有系统地、认真严肃地大量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科学著作,来推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和“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的领导地位”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实现,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翻译工作的基本政治任务。我们的翻译工作必须有计划、有系统地、认真严肃地介绍外国先进经济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秀著作,首先是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伟大友邦苏联的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经验和优秀科学技术著作。因此,为适应国家的建设需要,介绍外国,尤其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来武装全国建设干部,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乃是今后我们翻译工作的另一基本政治任务。详见沈志远.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J].翻译通报,1951(5):14-16.。叶圣陶致闭幕词,强调“翻译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提高翻译品的质量,使翻译工作走向计划化”(叶圣陶,1951:5)。这次翻译工作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吹起了“计划化和组织化”的“号角”,对翻译工作者翻译认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调适作用。我们可从译者的字里行间窥见一斑。《翻译通报》曾在1952年第1期发表吕众等集体执笔的《我们对翻译工作的新认识》一文。文章高度赞扬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称之为“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为拥护会议精神和决议,吕众等对过去的翻译工作做了自我检讨。错误的原因在于“任务繁重”“能力有限”和“重量不重质”,翻译工作会议以后,认识到了过去“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决心提高中文和俄文水平,“在中央翻译机构的正确方针指导之下”,“在全国读者的监督之下”,改进工作,提高翻译质量,“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吕众 等,1952:18)。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这次会议的很多计划措施都无法充分落实,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仍然没有真正实现计划化,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孙致礼,1996:191)。
1954年8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作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长篇报告。报告不仅对1954年以前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回顾,提出了他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即“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和实现翻译目标的具体步骤(即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体互助和培养翻译人才),而且还以文化官员(即国家翻译的统一赞助人)的身份对文学翻译工作提出了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刚性要求。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开篇,他就指出当时的翻译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状态”(茅盾,1984:5)。为消除这种混乱状态,他提出:“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切经济、文化事业已逐渐纳入组织化计划化的轨道”,“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茅盾,1984:7)。口吻之严厉,态度之坚决,远非一个纯粹的翻译学者所能承载。此外,茅盾还对如何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站在文化部长的角度,茅盾对翻译问题的指摘和对翻译工作计划化和组织化的倡导,已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表达,而是代表官方对翻译秩序的批评和建构。历史早已证明,茅盾讲话后不久,私营翻译出版和发行机构逐渐国有化。这从侧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艺官员话语政治的建构力量。
除茅盾外,在此次大会上,郭沫若发表了《谈文学翻译工作》的讲话,老舍、叶圣陶、郑振铎等人也纷纷就文学翻译工作问题发表了讲话。这次会议对文学翻译工作高度重视,还就如何组织和壮大文学翻译队伍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这次会议为文学翻译工作确定了方向和目标,在其推动下,国家对翻译出版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整顿和改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真正走上计划化和组织化的道路。
2.4 翻译选材秩序:“苏俄转向”
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对翻译选材影响深远。建国伊始,在“政治认同”和“诗学认同”的召唤下,苏俄文学独占鳌头,“苏联译作占据了中国译坛的中心”(赵稀方,2015:39),现实主义作品“一花独秀”。这一翻译选材秩序的形成有其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相关学者如陈南先(2004)、卢玉玲(2007)、吴赟(2012)等有过深入解读,本文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秩序也间接验证了“计划化和组织化”的政策效应和话语张力。
在全国翻译界一片“计划化”和“组织化”的“运动浪潮”中,各种层级的翻译组织纷纷建立,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计划。《翻译通报》1951年第4期曾在“翻译界动态”栏目中,发表“天津市翻译工作者互助组”座谈会决议后的事项。该翻译互助组列出的译述工作计划,从某种程度上可大致反映1949年后前十年的译介趋向。该计划包括:(1)介绍苏联的马列主义思想与学术方面的文章;(2)介绍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先进经验,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发展的情况,介绍他们的英雄人物;(3)介绍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科学(要深入浅出的通俗科学)与科学家;(4)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脆弱以及他们制造战争的阴谋,及其必败的道理(这方面,以改写、节译为主);(5)介绍苏联与世界进步的文学艺术方面代表性的短小作品,尤其是关于争取和平的文艺作品、抗美援朝的前线报告等(天津市翻译工作互助组,1951:45)。
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表面上是规范翻译行为,实质上是配合主流政治审定翻译的政治方向和思想内容。这一政策的显著效应之一,即是翻译选材秩序的调整:由新中国成立之前“题材不限,国别自由”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现实主义独尊”和“苏俄转向”。此一规范的表征和结果即是,较1949年以前,翻译出版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比过去有显著的进步”。沈志远对这一“进步”有过细致的描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30年间(即1919—1949年),译自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占全部译书的67%,而译自苏联的仅占9.5%。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前者退到了20.5%,而后者却升到77.5%。苏联书的译品已占到绝对的优势了。过去30年间所出版的全部俄文译本总共不到700种,而1950年一年内出版(包括再版)的俄文译本,已多达1600余种(沈志远,1951:9)。而卞之琳等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时也写道,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止,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旧俄)文学艺术作品共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种数的65.8%强(总印数82005000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印数74.4%强)(卞之琳 等,1959:47)。
种种迹象表明,翻译工作的有序开展和翻译选材的“唯苏独尊”,都直接或间接性地得益于翻译“计划化”和“组织化”的倡导。正如崔峰(2013:39)所言:“翻译工作的组织化成为翻译质量——包括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保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新政权对翻译选材秩序进行了再整合,由苏俄转向了亚非拉国家。因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表。
3 结语
作为“十七年”间主导的翻译批评话语和核心的翻译政策概念,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是特殊时代语境中各种张力作用下的复合产物。翻译界人士纷纷建言献策,积极响应此一政策。政府也通过创办翻译刊物,创设翻译出版机构及召开全国性的翻译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该项政策。上述举措对翻译秩序的重构发挥了积极作用。
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的提出,表面上是出于实践层面的考虑,意在遏制1949年前的翻译“乱象”,整饬翻译市场,旨在回答“翻译如何选材和翻译如何进行”等翻译技术秩序问题,形塑新型的翻译生产规范和模式。实质上,此一问题的提出,有更深层的政治战略谋局:重点关注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通过对翻译作品的思想甄别和文化过滤,对翻译活动进行政策引导和干预,对译者进行体制规训,从而建构社会主义的翻译话语秩序和翻译价值观,完成了从翻译秩序→文化秩序→政治秩序的嬗变。换言之,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已将翻译工作上升为国家行为,成为建构新中国文化生态,保障新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