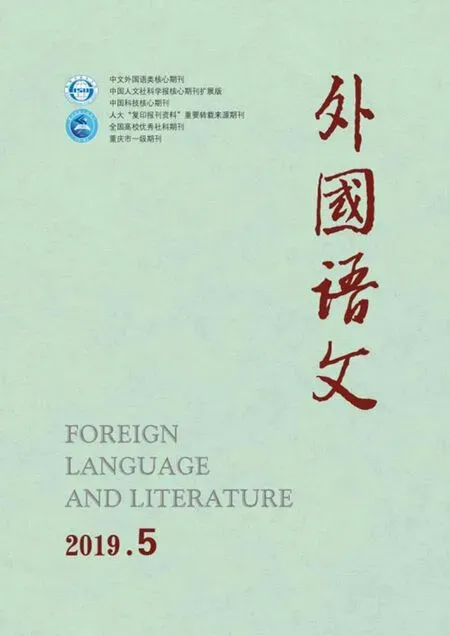波德莱尔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影响
——以柏桦为例
文雅
(四川外国语大学 法意语系 400031)
波德莱尔作为象征主义的先驱和现代派鼻祖,对整个中国新诗发展以及诗歌创作都起到了较为重要的影响。近几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日趋增多。国内学者所关注的受波德莱尔影响的中国作家与诗人主要有:鲁迅、李金发、闻一多、卞之琳、穆木天、艾青、戴望舒等。在这份名单里面,我们注意到国内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还停留在现代诗人身上,当代诗人是缺失的。然而,波德莱尔的影响并不止于现代诗人,稍后成长起来的当代诗人,他们仍然在波德莱尔诗歌的阅读中体会到感动和震撼,并在其影响下进行诗歌创作。
柏桦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代表诗集《表达》中的多首诗歌被译为英、法、日、荷兰语,在国际文学界知名度较大。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顾彬十分肯定柏桦在中国诗坛的特殊地位:“真实就是不说谎不出卖,诗歌同样。这样的真实,历经寂静的艰难岁月得以被识得与表达,里尔克是这种诚实写作的典范,柏桦同样是。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不可能在别处。”(1)该评论出现在柏桦诗集《秋变与春乐》封面。
柏桦在他的文学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以下简称《左边》)以及其他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及第一次阅读波德莱尔作品时所体会到的振聋发聩的感受。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受到波德莱尔那种奇特、深沉的艺术感染,柏桦才坚定地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而多年后的今天,柏桦再次被问及波德莱尔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时,他仍然毫不含糊地说道:“影响很大。从最初的李金发到多多再到我无一幸免。”(2)为完成该研究项目,笔者通过邮件与柏桦老师进行了访谈,主要内容包括他对波德莱尔的阅读体验、波德莱尔诗歌地位的评估、波德莱尔对他以及年轻诗人的创作影响等。因篇幅原因,该访谈录不附于文末,但主要内容会概括在本文内。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波德莱尔对诗人柏桦创作中的影响,窥探波德莱尔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1 醍醐灌顶的阅读体验
学者徐学清在《文学创作的抄袭与互文性》一文里面谈到阅读经验对于作家创作的重要性:“文学作品的高下,作家成就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作家是否善于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启发,汲取养料,丰富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创造出新的作品。”(2011:39)正是因为早年间阅读了波德莱尔的诗歌,柏桦作为诗人的灵性被唤醒,从此全情投入到诗歌创作里面。
在《左边》这本书里,柏桦详细描述了他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在“决定性的年龄”(柏桦,2008:53)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这本书上,他第一次看到波德莱尔的肖像,他说自己在这位法国诗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邂逅的亲切感。肖像下面配着一行字“吸食大麻、鸦片之后的诗人波德莱尔”(柏桦,2009a:46),柏桦用诗意的语言充满感情地描述了这幅肖像给他带来的震撼:
大麻、鸦片、诗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这位诗人。他深思漂浮,温驯的眼睛略带一丝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于激动的内心,一滴清泪欲从他的眼角无言地滴下;他倦怠而优雅,一只手纤细地支着头,轻柔地瞧着我。……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可泣的忘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 《美的历险》。(柏桦,2009a:46)
《露台》这首诗歌对柏桦产生了至深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他整个生活方式。在书中,柏桦说他爱上了波氏诗歌中咏唱的女人,“回忆的母亲,情人中的情人”(柏桦,2009a:77)。一个集母亲、情人、女王于一身的女人,她的身上既散发着家庭的温暖,又涌动着夜晚的魅惑,既有美丽的胸部,又有善良的心,她既是香水,又是毒药,让人尝尽欢乐,也付出所有。柏桦认为,唯有这种女人才能“与我那来自左边的热切相吻合,那种充满激情和反叛的热切”(柏桦,2009a:77)。然而,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并不足以说明这首诗带给柏桦的思想颠覆,让柏桦更为着迷的是波德莱尔那包含独特定义的美。这是一种既热烈痛苦又自由朦胧的东西,总是给人以揣测和想象的空间,这种“热烈与痛苦的相互依赖”(Jauss,1978:201)最能让敏感的心灵产生共鸣。在多年后的访谈中,柏桦再次谈及对这首诗的情有独钟:“瓦雷里先生认为《阳台》(3)《阳台》与《露台》系同一首诗,早期倾向于翻译成《露台》,后来更多使用《阳台》这一翻译名词。是波德莱尔最美的诗歌之一,我也这样认为;这首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观念,但也有点别的东西:对某种在人际关系中不能有而又只能通过人际关系获得的东西的追求。事实上,在浪漫派的许多诗歌中,悲伤是由于利用了这一事实:人类的关系永远不能满足人类的愿望;而且同样,他们不相信除了这些人类不能满足的愿望外,人类还有更加深远的目标值得追求。通过《阳台》,波德莱尔写出了一首人类经验中存在但却无人表达过此种经验的诗,因为真情与晦涩的分寸在这首诗里是那样难以精确地把握。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是一次突破;对于所有诗人同道来说,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向往。”(4)此段文字为柏桦访谈的原文。时隔多年,柏桦对波德莱尔的理解多了一层哲学的意义,那是超越文本之上,对人类普遍情感经验的一种凝练。柏桦提到的这种“不满足”,本雅明也有相似的领悟:“《恶之花》中,凡是有人目光出现的地方,几乎都有这样的象征。这就是说,人目光唤起的期待并没有得到满足。”(本雅明,2012:155)其实,这种“不满足”也是美学的本质,对“无法穷尽”和“无法到达”的永恒追求是文艺作品的创作源泉。接受美学大家Jauss认为,接受者的生活背景、社会层次及阅读品味都会决定他对作品的阐释和理解(Jauss,1978:13)。作为诗人的柏桦,拥有更强的洞察力和对情感的感受力,他比普通读者更能体会到波德莱尔的精妙之处。这让人想起普鲁斯特对波德莱尔的挚爱,本雅明认为:“普鲁斯特作为《恶之花》的读者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同气相求的东西。不了解普鲁斯特对波德莱尔的感受,也就无法理会波德莱尔。”(本雅明,2012:143)这种“同气相求的东西”,柏桦也深有感悟,作为读者,在《恶之花》中读到了满足其期待视野的别样诗意。
柏桦带着狂热和一丝忧伤反复诵读这首诗歌,他生气自己曾经的散漫,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用自己有限的词语,投入到无限的诗歌世界里:“悬置、断点、暴烈、晕眩、不幸与危险”(柏桦,2009a:77),他不遗余力地学习波德莱尔“神秘的诗歌法则”(柏桦,2009:77)。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及自己曾经写过的一首诗,最后一句是:“这一夜/猫终于死了。”(柏桦,2009a:236)他用“极差”来形容这首诗的质量,但是我们仍然能窥见在写作初期,波德莱尔对他的直接影响。“夜”“猫”“死亡”,都是波氏诗歌里最常见的意象。如同普鲁斯特通过阅读波德莱尔所认识到的:“成就一个伟大作家的因素不仅仅在于用词和表达手法上的标新立异,更在于从新颖的角度发现和重建寻常事物之间不为人知的联系,这种新颖的发现和重建才是作家达成表现形式的创新和整体风格的独特的基础。”(刘波,2013:225)作为诗人的柏桦不断成熟,波氏对他的影响不再停留在词句的模仿或者意象的重复上,而是渗透到自己的诗歌观念,并启发他寻找到专属自己的诗歌语言,若仅论诗歌形式和语言,他的创作与波氏风格已相去甚远。
2 诗歌观念的契合
早年受波德莱尔诗歌启发走上创作道路的柏桦,后来所持的诗歌理念与这位法国诗人高度默契:偏爱短小精致的诗歌形式,突破性继承诗歌的传统美,不懈追求用词的深刻独到,重视诗歌理论,强调诗人的特殊使命。
众所周知,波德莱尔诗歌创作独辟蹊径,诗歌主题惊世骇俗,其美学理论无不呈现出反叛、独到的特点,但是,波德莱尔却对传统、严谨的商籁体情有独钟。在一封写给朋友阿尔芒的信里,他谈及自己对这种西方经典诗歌形式的特殊感情:“在形式的束缚下,思想的爆发更加有力。商籁体里一切皆可:滑稽、时髦、激情、遐想、哲思。那里有精心雕琢的金属与矿物质之美。你是否曾经透过地下室的窗户,壁炉的烟囱,高耸的岩石缝,或是拱廊……观察头顶那一方天空,相比从一座开阔的大山看到的天空全景,这是否会让你产生更加深邃的、无穷的感觉?”(Bertrand,2006: 70)波德莱尔十分重视诗歌的形式,总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加独特、精美、准确的表达方式,因此,他格外看重诗歌技巧的锤炼。他认为只有那些不会写短诗的人才会求助于长诗,但诗歌却只有在凝练的形式里,才能爆发出最强有力的思想。戴望舒在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时,也把波德莱尔的诗歌形式看成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他这样解释自己的翻译意图:“这是一种试验,来看波德莱尔的坚固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在转变成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曹万生,2003:149)
对此,柏桦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观点:“诗永远必须短,长以至于史诗乃诗家之大忌也!”“我是一刹那的‘小诗人’,这也是我的诗歌理想。诗在我的笔下一写长我就惊恐,一短小我就有信心。”“我对长诗从无感觉,也从未觉得不写长诗会感到自卑。我只写短诗,也只推崇短诗人。”(柏桦,2006:269)柏桦未必读过波德莱尔关于偏爱短诗的言论,他们这种共性源于各自对诗歌本质的深刻领悟。对他们而言,诗歌形式的束缚,有助于他们克制浪漫主义式的抒情。其实,在这段柏桦评论他的同时代诗人崔卫平的文字中,也表达了对诗歌形式的执拗追求:“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柏桦,2009a:42)
波德莱尔对商籁体的情有独钟和柏桦对短诗的偏爱,都反映出诗人在追求诗歌现代性的同时,对传统美和古典美的尊重。正如Jauss的观点:“就美学意义而言,与‘现代’相对应的,并非是‘古老’或者‘过时’,而是‘古典’,一种永恒的美,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Jauss,1978:162)波德莱尔也认为现代性的美是两者的结合:“所谓现代性,就是过渡的、瞬间的和偶然的,这构成艺术的一半,而艺术的另一半,便是永恒的和不变的。”(Baudelaire,1976:695)因此,在姚斯看来,波德莱尔诗歌的独到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保持了亚历山大体严谨的格律而且运用自如;另一方面,这一纯粹的古典诗歌的结构的对称原则又不断被抒情运动不对称的伸展与收缩所打破”(Jauss,1978:202)。这一立一破之间,波德莱尔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柏桦为自己第一本诗集《表达》撰写的小传,被视作可以“开启柏桦诗歌的秘密天窗”:“23岁时,读了波德莱尔的《露台》后开始认真写诗。受梁宗岱教授的影响至深,恪守‘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这一名言并坚持‘一首好诗应该有百分之三十的独创性,百分之七十的传统’这一信条,为提高诗艺不懈地努力着。”(黄梁,2000:307)这就是柏桦自己所说的“互文性”,他的诗歌语言虽然新奇独到,却也总是渗透着汉语诗歌的抒情传统。
波德莱尔的诗歌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恶”的词汇,他不仅不避讳,还能用高妙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并不诗意的词语。他就像一位语言的炼金术士,给平凡的词语赋予象征的感召力。柏桦的诗歌同样不排斥那些粗俗的语言:“诗人之任务便是用词。词不分大小,也不分美丑,皆能入诗也。”(柏桦,2006:269)在柏桦的诗歌里,我们读到这样的诗句:“不成熟的死刺激一辆飞驰的火车/可耻的棺材像空气升腾”(《一个有病的男孩》)(柏桦,2009b:4),“一具优美僵直的尸体”(《震颤》)(柏桦,2009b:9),“忧伤的梦游的妓女们”(《春日》)(柏桦,2017:56),“在沙上建筑你的语言之墓”(《诗人病历》)(柏桦,2009b:12),“不幸的青春加上正哭的酒精”(《未来》)(柏桦,2009b:134)。在阅读波德莱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惊叹诗人对词语有超强的驾驭能力,一些普通的词经过他的排列组合,就散发出特殊的魅力。而柏桦的诗句,也往往展示出这种惊人的能力,词语被他赋予一种深度,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柏桦相信,每一个词语都蕴含着深层的意义,他总是通过魔法般的排列组合,赋予这些词崭新的意义。他的诗句在我们的头脑里唤起新奇独特的意象,让我们感叹词语之间的奇妙关联,产生匪夷所思的阅读感受。“可耻的棺材像空气升腾”,用“可耻”“空气”“升腾”来形容“棺材”,既赋予这个词人的灵性,又消解了它质的重量,诗人炼金术般的语言魔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的,用“优美”修饰“尸体”,用“忧伤的妓女”点缀“春日”,在“沙上”建筑“语言之墓”,处处充斥着悖论的矛盾力量,让人感到一种眩晕的强烈诗意,在读者心里开出一朵朵致命的“恶之花”。
柏桦反对诗歌情感的自由抒发,他很早就进行了诗歌理念的“严肃”思考。这是一种韦勒克所说的“审美的严肃性”和“知觉的严肃性”(Wellek,1971:43-44)。1984年,经过了三年的深入阅读与思考,在体会了波德莱尔“心灵与官能的狂热”(柏桦,2009a:2)、梁宗岱的“以诗歌抗拒死亡”(柏桦,2009a:2)、吴少秋的“神秘和气氛”(柏桦,2009a:2)以后,他正式写下了自己的诗歌理念,命名为《我的诗观》,包含三段内容。柏桦称之为“一个典型的象征主义诗观”:一种敏感、神秘、感召的诗歌。柏桦认为,象征主义是他早期诗歌的“土壤、水、空气和灵魂”(柏桦,2009a:93),他声称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也曾尝试过“坚实简练的意象派、解放潜意识并更加革命的超现实主义,以及菲里普·拉金的反对狂热呓语和暧昧朦胧的后现代冷峻诗篇”(柏桦,2009a:93),甚至也尝试过“将叙事、民俗、古代生活内容及现实的日常细节移入诗歌”(柏桦,2009a:93),但象征主义已经深深融入他的血液,所以一直到2008年,柏桦都称自己是一个“‘古老的’象征主义者”(柏桦,2009a:93)。
两组扫描范围均从肺尖至肺底部,其一次屏气后再连续扫描。HRCT采取薄层扫描,其扫描参数为200mA、140kV,轴距扫描矩阵为512×512、层距为10毫米、层厚为1毫米,并使用骨算法展现、重建图像细节,择取合适的宽窗位改良诊断结果。常规CT扫描矩阵为256×256、准直为1.5毫米、螺距为1、层厚为10毫米、160mAs、120kV。
柏桦呼吁应该把注意力从诗歌转移到诗人,因为他认为诗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真正的诗人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触须,并以此来感知世界……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证明了这一点。”(柏桦,2009a:93)他说:“诗人的一生是他的诗篇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这个注脚当然要比诗更能让人怀有浓烈的兴味。如果说《恶之花》是一本让你在一小时内活得比20年还充实的书,那么波德莱尔生命中的一小时就等于你生命的全部。”(柏桦,2009a:93)同样,波德莱尔也从未停止过对诗人身份和使命的思考,并体会到一种强烈的诗人责任感:“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只能描绘他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所感。他应该忠实于自己的自然,像躲避死神一样,躲避别人的所见所感,哪怕这个人是一个伟人,因为用别人的感受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谎言而不是真实。”(Baudelaire,1976 : 620)打开诗集《恶之花》,通过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开篇的几首诗歌,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波德莱尔对“诗人”的严肃思考。“宁静的诗人举起虔诚的手臂,/他看见天上有一壮丽的宝座,/他那清醒的头脑啊光辉无际,/把愤怒人群的场面替他掩遮:∥‘感谢您,我的上帝,是您把痛苦/当作了圣药疗治我们的不结,/当做了最精美最纯粹的甘露,/让强者准备享受神圣的快乐!∥我知道您为诗人保留了位置,/在圣徒队的真福者行列中间,/您请他参加宝座天使、力天使/和权天使的永远不散的欢宴’。”(波德莱尔,2013:11-12)(《祝福》)“诗人啊就好像这位云中之君,/出没于暴风雨,敢把弓手笑看;/一旦落地,就被嘘声围得紧紧”(《信天翁》)(波德莱尔,2013:14)“远远地飞离那些致病的腐恶,/飞到高空中去把你净化涤荡,/就好像啜饮纯洁神圣的酒浆,/啜饮那弥漫澄宇的光明的火。”(《高翔远举》)(波德莱尔,2013:15-16)“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应和》)(波德莱尔,2013:17)。波德莱尔通过诗句表达诗人的追求、力量、荣耀、耻辱、苦难、使命和命运。“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诗人之使命在于坚定地面对当下生存的自我关照,从每一个在历史长流中无所依傍的瞬间夺取可以与永恒对话的美。”(龚觅,2000:82)这种对诗人身份的关注和自省,让波德莱尔和柏桦成为更为纯粹的艺术家。
3 一种超越形式的解放性的影响
在笔者对柏桦的访谈中,关于波德莱尔对中国诗坛影响的问题,柏桦是这样回答的:“波德莱尔的影响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一是观念的冲击,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一种现代性的震撼;二是感受力的刷新,即诗竟然可以这样写,主观的、意志的、象征的。”(5)此段文字为柏桦访谈原文。从整体上,柏桦肯定了波德莱尔对中国诗人创作的影响力,“观念的冲击”“感受力的刷新”高度概括了波氏的诗歌成就,以及在他启发下形成的一种主观、象征,带有现代性震撼力的诗歌表达。“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柏桦,2009a:102)是柏桦最欣赏波德莱尔的诗句,因为这句诗体现了波德莱尔秘密感受的痛苦与至福。这种“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他在海子谈论荷尔德林的文字里体会过:“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是沉醉的,没有尽头的,因为后来生命经历的痛苦——痛苦一刀砍下了——,诗就短了……像大沙漠中废墟和断头台的火砖……”(柏桦,2008:9)柏桦说,这段文字虽然是谈论荷尔德林的,他却读出了“波德莱尔式的冰和铁”(柏桦,2008:9),他说海子更像是一个“争分夺秒燃烧的波德莱尔”。正如刘波教授所言,诗歌永远来自于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老老实实反映自己感觉到的事物,对他所表现的事物要怀有感同身受的情愫,并从个别的、偶然的感觉中发现具有永恒价值的省悟。”(刘波,2013:225)他认为波德莱尔身上就有着某种“表现痛苦经验诗人的品质”(刘波,2013:225)。这种“痛苦经验”在当代诗人那里得到了深度共鸣。柏桦在读北岛《雨夜》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这种波德莱尔式的疼痛和欢乐。“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沾湿了你的手绢/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柏桦,2008:5)柏桦(2008:5)说:“《雨夜》带着一种近乎波德莱尔式的残忍的极乐,以一种深刻饱满的对抗力量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他认为“这种痛苦中的欢乐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深切地体会”(柏桦,2008:9)。这或许是现当代诗人们的一种群体特征:不能在现实和社会中获取减轻痛苦的力量,被迫在诗歌中表达整个人生的沉重和难以释放的饱满激情。之所以波氏诗歌在中国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诗歌中这种矛盾、纠结和撕裂契合了现当代诗人们的内心情感体验。
当我们在访谈中提及波德莱尔对当代诗人创作的影响时,柏桦的回答是波德莱尔对更年轻的诗人的影响力已经不大,但自波德莱尔以降的现代性诗歌观念,他认为还是有影响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柏桦的态度是既客观又肯定的。应该这样理解:波德莱尔对当代诗人创作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一种诗歌观念上,而不是在诗歌形式、诗歌意境或者修辞手法上的简单模仿和重复。柏桦曾经谈起当代诗人尹丽川,并以《郊区公厕即景》一诗为例提及波德莱尔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强力影响(《波德莱尔在中国》):“蹲下去后,我就闭上了双眼/屏住呼吸。耳朵没有关/对面哗哗地响,动静很大/我睁开眼,仰视一名老妇/正提起肥大的裤子/气宇轩昂地,打了个饱嗝/从容地系着腰带/她轻微地满意地叹了口气/她的头发花白/她从容地系上腰带/动作缓慢而熟稔/可以配悲怆的交响乐/也可以是默片。”(柏桦,2008:10)正如柏桦所说,这首诗的表达手法、书写技巧及诗歌语言都与波德莱尔带有浪漫主义余绪的象征诗相去甚远,但是,他认为:“就像波德莱尔在诗中书写过开天辟地的新题材一样,如拾垃圾者、腐尸、恶魔、蛆虫、苍蝇、粪土等,尹丽川同样以厕所这一最能体现中国现实的意象,为我们展示了同样令人震惊的一幕,她通过厕所书写了普通中国人的沧桑、麻木、荒凉,这正是一首波德莱尔所一贯追求的深度现实主义之诗。”(柏桦,2008:10)刘波教授曾经非常深刻地探讨过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的历程:“波德莱尔在他的巴黎诗歌中实践的‘深层模仿’实则不是用诗歌来模仿现实,而是用诗歌来置换现实。而且这种置换不是对现实的简单移植,而是体现出艺术活动和精神活动对现实的提升或深化作用,换句话说,当波德莱尔通过诗歌创作活动把城市置换为图画之际,他其实是把物的价值置换为了精神的价值,把属于城市生活的日常经验置换为了具有普遍价值的美学经验。”(刘波,2016:486-487)从这个角度看,尹丽川和波德莱尔的共通之处,便在于两位诗人都在现实生活中深刻感受到生活的意图,用写作的意义置换生存的意义,用不同的诗歌语言表达诠释出各自理解的生活真谛。即便写作的技巧、形式有异,他们作为诗人的使命却是契合的,犀利地将世界“恶”与“丑”的底蕴和盘托出,让现代社会的客观真实样态一览无余。
在访谈中,笔者问柏桦,尹丽川本人是否承认受波德莱尔影响,他回答说,这是他的大胆推测,诗人自己可以不承认受其影响。比较文学专家查明建认为,我们学者在进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时,常常使用狭隘的影响研究方法来处理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国作家作品中的主题、创作手法、情节、意象与外国作品相似点着手,寻找影响的证据,以证明外国文学对中国某个作家的影响为目的”(查明建,2000:35)。如果我们使用这种局限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在中国当代诗人的创作中,并无多少波德莱尔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接受者的主体性,包括他所处民族本身的发展,我们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查明建强调在影响接受中,绝不可忽略作家自身的创造性:“任何文学影响和接受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与接受主体所处的文学环境和作家自身的审美倾向有很大关系。可见,影响并不否认民族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因。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内在作用才使得文学接受成为可能。没有接受主体的接受,也就谈不上影响。影响或超越影响,都是这种内心积淀的先结构作用的表现。所以,接受影响并不必然意味着是放弃创造个性的机械搬用和模仿,而是指通过作家创造性的吸纳和转化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从而有融入自身文学的发展进程之中。”(查明建,2000:38)中国当代诗人对波德莱尔的接受,正是诗人们在经历社会变迁以后,在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结合中国自身的语境,对外来、内在的诗歌经验进行整合、归化,从而形成具有个性化的诗意表达。
查明建还提到另一种影响的可能性:有的作家根本没有读过外国作品,他接受的“影响”只是当时共时性的文学氛围和风气,或者是受到接受过影响的作家作品的更为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波德莱尔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从李金发、徐志摩、陈敬容、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到后来的海子、北岛、柏桦,无一不曾被波德莱尔的诗歌和诗学深深震撼。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是这样理解“影响”的:“特定意义上的 ‘影响’,是一种创造性的刺激。”(大塚幸男,1986:119)。而法国批评家朗松也说过:“外来影响不止一次地起着解放我们的作用。”(朗松,2009: 78-80)波德莱尔诗歌的现代性,满足了现代人复杂情感的倾诉,正是这种现代性刺激着中国当代诗人,他们在波德莱尔的诗学影响下,追寻诗歌本身价值,挖掘诗歌本质,而这种外来影响也让他们从中国的传统诗歌中得到解放,创造出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特质的当代诗歌,反映出在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中国诗人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的文化哲学观和思想价值观。
在阅读中得到解放,并在此刺激下创作出具有主体意识和风格的作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表达》便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强势而生。“一个影子、一朵花、一棵树、一阵风、一段流水、一块石头、一个声音”(柏桦,2009b:5-7),物体、意象、感官如同一首交响乐,歌唱波德莱尔式的“精神与感官的狂热”(Baudelaire,1999:55)。这首诗跟波德莱尔的诗歌一样,态度严谨,经得起推敲,犹如一个冷峻的生活旁观者,却智慧又激荡地表达出时代最震撼人的声音。“这是我早期诗歌的第一声部,它解放了我,并让我获得(或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的胜利。”(柏桦,2009a:91)这种影响的刺激和解放,在柏桦的这段话里得到完美的诠释:“一首诗的成功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莫名的契机、必要的训练和阅读、信仰的偏爱和执着、与某个决定性的人相遇、偶然的天意、打开的诚恳与幼稚的心、对内心不厌其烦的倾听、不断地返回到童年、返回到自己的先辈的某一个细节、长时间地沉醉于痛苦或幸福的周而复始的折磨、回忆或突然勇敢的舍弃、懒散的阅读时碰巧的专注或停顿、对一个词或一句话形骸俱释的敏感和陶醉。”(柏桦,2009a:91)柏桦的这段话形象地诠释了一个诗人走向成熟,塑造自己个人风格的历程。
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柏桦几乎是在决定性的年龄,接受了波德莱尔诗歌的洗礼,走上一种全新的、现代意义的诗歌创作道路。由于所处时代、哲学背景的不同,两位诗人呈现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比较文学专家史忠义在《中西比较诗学新探》一书中,指出中西诗学诗性的内涵大不相同。西方的关键词是灵感、激情、天才和想象,而中国诗性诗学的关键词是缘情、意象、意境和性灵等。从审美性来看,西方诗学追求崇高,中国诗学追求自然。史忠义高度概括的中西诗学特点,在波德莱尔和柏桦的诗歌中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
波德莱尔一直认为诗人是通神性的,诗人需要激情与天才,才能通达崇高。对波德莱尔而言,诗歌是一种具有暗示性的魔力创造,他诗歌里的想象力,有一种魔性,他的梦呓、他的幻觉、他的灵感,全部被他转化成艺术品,一种人工的迷醉,其中蕴含着非凡的力量和强度,带着神性的犀利。
在西方诗学的观照下,柏桦的诗歌仍然坚守着“诗缘情”这一不变的中国诗歌法则,他有反抗的姿态,也有怀旧的情调。和波德莱尔一样,柏桦也曾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波氏的激情是一种持久的、对美和崇高的不懈追求,柏桦的激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青春的激情。从激情、反叛到平和,身为大学教授的诗人柏桦表现出一种与生活握手言和的姿态。但波德莱尔坚信诗歌与反抗有着不可断绝的联系,他是坚定的反抗者,有着决不妥协、粉身碎骨的决心。
与波德莱尔一样,柏桦也试图在可见世界,寻找可描述内心世界的隐喻,但与波德莱尔追求绝对的精神性不同,青春激情过后的柏桦对生活更加亲近,他从现实入手,从细节出发,冷静地诉说诗人的幽微敏感。柏桦的诗歌有一种叙事性,而波德莱尔的叙事有一种抽象性。
柏桦认为,事实上,中国新诗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深深打下了西方文学的烙印,并且用十年一变的时间,把西方近百年的诗艺重新集中学习了一遍,这是不争的事实(柏桦,2006:289)。80年代中期,中国新诗的发展呈现出群魔乱舞的狂乱之势,各种流派层出不穷,各种论战此起彼伏,“非诗”“非抒情”的叫嚣使得当代新诗几乎是集体性诗意流失。在这样的诗坛语境中,柏桦保持了他的清醒与独立,与波德莱尔一样,始终坚持着一种纯粹的、神圣的诗歌创作。董洪川教授在研究艾略特的时候引用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伟大的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董洪川,2006:123)柏桦在波德莱尔影响下的诗歌创作,超越了形式、技巧的相似,把握住自己的时代特征,自由地表达了一个现代诗人的感觉方式和经验模式。
——柏桦诗风之变
——柏桦诗歌的先锋意识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