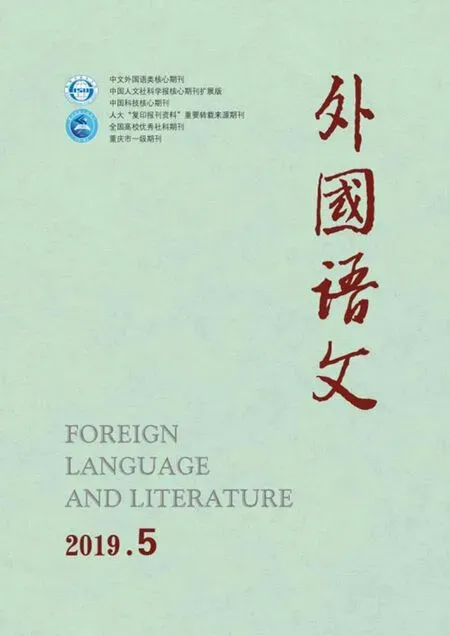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与“二战”时期的美国
任虎军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在人类历史上,美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因为它的历史是从反对欧洲大陆(特别是英国)的各种奴役、迫害和压迫开始的。17世纪初,当首批英国人离开母国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上帝派他们来到的地方。兴奋不已之余,在感谢上帝的同时,他们也痛恨英国政府对他们的统治与束缚。这种痛恨与日俱增,最终促使他们向世界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其中写道:“我们认为这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上帝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幸福追求。”(Baym, 1989: 640)基于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独立宣言》还写道:“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而且有权利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州……它们有充分的权力发动战争,宣布和平,缔结联盟,发展商业,以及其他独立州有权做的事情。”(Baym, 1989: 643-644)《独立宣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文件,其反复强调的“独立”“自由”“平等”与“和平”之主张,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团结起来合力反抗英国统治走向独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成为美国人建国的理想与生活目标。在美国人看来,“自由”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不仅属于美国人,而且属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美国人摆脱英国统治,追求自由,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所以,托马斯·潘恩在其《常识》中说:“美国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的事业。”(Baym, 1989: 618)
如果说《独立宣言》为美国追求自由与平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圣约翰·德·克利夫科尔的《美国农夫的来信》为美国的自由与平等做了现实宣讲:“这儿没有占有一切的大地主,也没有一无所有的平民。这儿没有贵族家庭,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宗教统治,没有可见的赋予极少数人的权力,没有雇佣数千人的大雇主,没有极其奢侈的享受。富人与穷人之差距没有欧洲那么大……这儿,人是自由的,就像他应该自由一样,这种令人欢喜的平等也不像许多其他平等那样转瞬即逝。”(Baym, 1989: 559)所以,欧洲人来到北美大陆之后,“一切都使他们再生了。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制度。这儿,他们是变化了的人。”(Baym, 1989: 560)他们不再是欧洲人,而是“一种新人”(Baym, 1989: 561)。在这个由“新人”组成的“新国家”,“很少有人犯罪……他不迫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迫害他”(Baym, 1989: 564)。这个“新国家”有着诸多欧洲无法相比的“诱人之处”,因为“如果你诚实、节俭、勤奋,你就有更大回报——自由与独立”(Baym, 1989: 567-568)。
无论是《独立宣言》的理论辩解,还是《美国农夫的来信》的现实宣讲,都凸显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什么?在美国缔造者看来,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因为它是“上帝选出来的国家”,是一个倡导自由与平等、反对奴役与暴政的国家;换言之,就身份而言,美国应该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应该奉行《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来平等”的真理;然而,写进《独立宣言》的“人人生来平等”的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到了美国现实生活中却成了令人费解的谬误,因为美国社会从未实现“人人生来平等”的理想,美国绝非反法西斯主义者。正因如此,凡有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美国文人,都不失时机地将目光投向美国,通过书写再现美国的各种言与行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竭力让美国看清自己。诺曼·梅勒便是这样一位文人,他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1948)通过再现美国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向我们展现了“二战”时期美国的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
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说,他写作的目的是“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发起一场革命”(Mailer, 1959:17)。虽然梅勒从未明确表明他要革命的“我们时代的意识”是什么,但他革命“我们时代的意识”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社会”。梅勒在《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中说:“我记得曾在1958年说过,‘我要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发起一场革命。’……那时候,我想我脑子里有几部别人没有的书,一旦把它们写出来,社会就会发生变化。”(Mailer, 2003:62)从梅勒进行文学创作的历史语境来看,他所说的“我们时代”正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进入冷战的时代,这个时代美国社会意识除了帝国主义意识,还有性别歧视意识、种族主义意识和极权主义意识。梅勒在《存在主义差事》中说,美国“处于十分可怕的时代,患有十分严重的疾病。”(Mailer, 1972:341)他认为,“美国依靠生产破坏性资料获得繁荣”,因此“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出美国人生活中健康的方面。”(Mailer, 1959: 189)他在《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中说,美国作家的失败在于没有写出一部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拉尼娜》和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能使一个国家看清自己的伟大作品”(Mailer, 2003:300)。梅勒回忆说,每当失望之时,他都会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挽救苏联(Mailer, 2003: 162-163)。由此可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梅勒力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挽救“患有十分严重疾病”的美国。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说,如果美国社会再次出现危机,那就不是“来自经济中心,而是来自上层建筑”(Mailer, 1959: 215),因为美国社会的帝国主义意识、性别歧视意识、种族主义意识和极权主义意识的存在已经使美国社会“处于十分可怕的时代”,使“我们生活在灭绝威胁之下”(Mailer, 1959: 382)。梅勒认为,“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跟他们的社会相对立”(Mailer, 1959: 190),他要以与美国社会相对立的姿态通过自己的写作革命美国社会的这些意识,以阻止美国社会朝死亡方向前进。
虽然梅勒革命时代意识的写作动机于1959年公之于众,但他革命时代意识的意识在成名作《裸者与死者》中已经存在。《裸者与死者》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好小说”,它真实再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普通士兵在整个战争中所受的身心伤害”。因此,它被视为反战小说(Kinder, 2005: 190-191)。作为反战小说,《裸者与死者》跟其之前的许多战争小说完全不同,因为它“没有试图赋予战争和那些参战人任何浪漫色彩”(Kinder, 2005: 194);相反,它比较真实地再现了部队内部的种族冲突、猖獗的反犹主义以及军官与士兵之间的阶级对立等美国社会的黑暗面。有评论家认为:“梅勒写《裸者与死者》的部分目的是要提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读者:什么东西正在从美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中删除。”(Kinder, 2005: 191)梅勒于1946年夏天开始创作《裸者与死者》,当时他刚从海外服役期满回国,如果说他当时发现“什么东西正在从美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中删除”的话,那么,他要通过他的小说恢复这种“正在从美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中删除”的东西:“二战”并不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参与战争的美国并不是民主与自由的乐园,而是各种权力意识与反权力意识之间进行激烈争斗的竞技场。因此,《裸者与死者》努力恢复“二战”之残酷性的同时也“没有试图将制度种族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中消除”(Kinder, 2005: 194)。不仅如此,小说也没有试图将当时比较猖獗的性别歧视意识以及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极权主义意识从美国人对“二战”的记忆中消除。事实上,《裸者与死者》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二战”的残酷性及其对参战士兵的身心伤害,而且在于它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各种权力意识与反权力意识之间的战争,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战争期间美国的国内法西斯主义行为,从而使美国人看清了战争内外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真面目,这是这部“战争”小说书写战争的真正用意所在。
1 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
《裸者与死者》是一部战争小说,也是一部再现“二战”期间美国国内性别问题的小说。小说再现“二战”的同时,也再现了战争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战争,这种战争通过小说中男性人物谈论女性的话语、男性人物谈论自己妻子的话语以及男性人物与妻子的对话得以充分展现。小说开始不久,布朗(Brown)和斯坦利(Stanley)就女人问题展开激烈的唇枪舌剑。布朗对斯坦利说:“你不能相信他们任何人,没有女人你能够相信。”斯坦利回应说:“我不知道,情况不完全那样,我知道我信任我妻子。”布朗反驳说:“信任女人是不值得的。你占有我妻子吧,她很漂亮。”斯坦利回应说:“她的确是个美人。”布朗又说:“她是美人,你以为她会坐着等我吗?不,不会。她正在外面鬼混潇洒啦。”斯坦利则说:“我不那样说。”(1)Norman Mailer, The Naked and the Dead.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8.下文中凡出自该版本的引文,均在引文后的括号内注明引文出现的页码。布朗和斯坦利谈论女性的话语和口气表明,他们对女性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性别歧视者与反性别歧视者之间的对话,他们的话语分别体现了性别歧视意识与反性别歧视意识。布朗的话语表明,他不仅是一个性别歧视者,而且是一个性别歧视意识的传播者与推广者;他不仅自己对女性抱有极大偏见,而且竭力使自己周围的人也对女性产生偏见。在他看来,“干净像样的女人不再有”,“没有一个男人一看就可以信任的女人”(120)。然而,不论他怎样竭尽所能说服斯坦利,斯坦利都没有跟他站在一起。斯坦利对布朗的对抗是反性别歧视对性别歧视的对抗。布朗和斯坦利对话中体现出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也体现在布朗、斯坦利、普拉克(Polack)和明尼塔(Minetta)等人谈论女性的话语中。布朗认为:“没有女人你能够信任。”斯坦利回击说:“我不知道,我信任我妻子,有各种各样的女人。”布朗不认输,仍然坚持说:“她们都一个样。”明尼塔反驳说:“我信任我女友。”但普拉克却站在布朗一边说:“我一点都不信任那些婊子。”布朗觉得自己有了支持者,便说:“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很不服气地问明尼塔:“你信任你女友,哼?”明尼塔回答说:“那还用问,我当然信任她。”但他的回答使普拉克再次站到布朗一边:“他就是信任那些婊子。”布朗再次很得意地说:“我告诉你,明尼塔,她们没有一个你能够信任的,她们都会欺骗你。”普拉克也随即附和说:“该死的女人没好的。”但他们没有折服明尼塔:“我不会担心。”斯坦利也从另一个角度反驳布朗说:“我可不一样,我有孩子。”但布朗认为:“有孩子的女人最糟糕,她们最不容易满足现状,最需寻欢作乐。”普拉克再次支持布朗说:“我很高兴,不用担心那些婊子中有人会欺骗我。”但是,明尼塔还是没有被他们折服,他回击说:“去你的,你们以为你们好得不得了。”(184-186)这个众声喧哗的对话中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性别歧视的声音,另一种是反性别歧视的声音。布朗和普拉克的声音显而易见是性别歧视的声音,他们的话语体现了他们的性别歧视意识。斯坦利和明尼塔的声音明显是反性别歧视的声音,他们的话语体现了他们的反性别歧视意识。斯坦利和明尼塔与布朗和普拉克的对抗是反性别歧视者与性别歧视者之间的对抗,体现了反性别歧视意识与性别歧视意识之间的对抗。布朗和普拉克的话语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意识也在卡明斯(Cummings)和罗斯(Roth)等人物谈论女性的话语中体现出来。卡明斯认为:“一般的男人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看自己的高低,其中没有女人的角色,她们只是一个索引,一个[男人]用以衡量优越性的尺码之一。”(322-323)罗斯认为,“女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孩子,以及所有更为琐细的东西”,因此,“很多事情是不能告诉女人的”(56)。
布朗、普拉克、卡明斯、罗斯以及斯坦利和明尼塔等男性谈论女性的话语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也体现在卡明斯、布朗、罗斯和戈尔德斯坦因(Goldstein)等男性人物谈论自己妻子的话语中。对卡明斯来说,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不是他的情感与精神伴侣,而是他的生活助手与家庭保姆。“她忙于料理家务、处理愉悦和游玩账单。”(416)不管她为家付出多少,在卡明斯眼中,她都不是什么贤妻。他毫无顾忌地对副手霍恩(Hearn)说,“我妻子就是一个婊子”,因为“她想尽一切办法来羞辱我”(182)。与卡明斯不同,罗斯虽然认为“很多事情不能告诉女人”(56),但身在海外,他“努力想起他的妻儿,似乎在他看来,没有比回到妻儿身边更为美好的生活”(119)。跟罗斯一样,“晚上,在帐篷里,戈尔德斯坦因总会……想自己儿子,或者努力想象他妻子此刻会在什么地方。有时候,如果他认为她可能在走亲访友,他会试图想他们在说什么,想起家人的玩笑,他会带着应有的高兴摇摇头”(205)。卡明斯、罗斯和戈尔德斯坦因对待妻子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对待女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和性别意识,这两种不同态度和性别意识也体现在布朗和戈尔德斯坦因设想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家对待妻子的态度中。小说末尾处,布朗和战友想象着战争结束后回家跟妻子见面的情景:“我会跟某个娘们同居。我什么都不干,只玩女人,喝酒,整整玩两周……然后,我会回家找我妻子,我会让她知道我回来了,我会让她感到惊讶,我会让上帝见证。我会把她踢出家门,让人们知道你如何对待一个婊子。”(710)布朗始终是一个性别歧视者,他对待妻子与其他女人一样,因为在他眼中,她们只是性的玩物,只是男性满足性欲的对象。但是,梅勒显然要告诉我们,“二战”期间,美国社会也有不同于布朗的男性,他们对女性比较友好,具有明显的反性别歧视意识,戈尔德斯坦因就是他们的代表。与布朗不同,戈尔德斯坦因这样想象战争结束后回家与妻子见面的情景:“我清早就回家,从格拉德(Grand)中心站搭乘出租车,一路直奔弗拉布什(Flatbush)公寓我们的家,然后上楼,按门铃,娜塔莉(Natalie)会猜是谁,然后她会前来开门……”(710)戈尔德斯坦因与布朗迥然不同的想象,体现了他们迥然不同的性别意识。梅勒将戈尔德斯坦因的想象置于布朗的想象之后,目的是为了告诉读者,性别歧视意识尽管想独揽天下,但总是受到反性别歧视意识的对抗。梅勒在小说末尾处再现士兵想象回家的情形,旨在告诉读者,美国即使结束了海外的军事战争,却无法结束国内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战争。
小说还通过威尔逊(Wilson)与妻子艾丽斯(Alice)的对话再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小说中出现过两次威尔逊与艾丽斯的对话交流,一次是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次是书信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发生在艾丽斯在医院生产后不久。一天,艾丽斯发现威尔逊在自己住院期间外出找了女人,而且花掉了她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她非常生气地对他说:“伍德罗,我觉得你实在太卑鄙,没有比一个男人对他妻子撒谎、在她和宝宝住院期间花掉他们的所有积蓄更为低劣的事了。”(378)但威尔逊却反驳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艾丽斯,我们不说这个好吧,我多数时间都是你的好丈夫,你没有必要那样对我说话。我只想开心一下,我现在开心了,你最好不要把我的心情搞得一团糟。”(378)艾丽斯与威尔逊的争吵是两种性别意识之间的争吵。威尔逊是性别歧视者,是男性至上主义者,他只知道自己享乐,却不知道为妻儿承担义务和责任。在他看来,男人不可以向女人(特别是妻子)袒露心声,因为“你告诉女人的越少,你就越幸福”(259)。他很像卡明斯,却没有遇到像玛格丽特那样百依百顺的妻子。他妻子艾丽斯具有强烈的反性别歧视意识,但遗憾的是,艾丽斯最终被威尔逊的糖衣炮弹所蒙骗,她的反性别歧视意识暂时被淡化,失去了最初的强度。威尔逊虽然暂时平息了艾丽斯的反抗,但他的性别歧视意识使他始终未改过去的做法,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欺骗妻子,因而引起了艾丽斯的再次反抗。威尔逊海外参战期间,一天晚上,他收到妻子艾丽斯的抱怨信:“我不会再忍受了,我一直是你的好妻子,而你不是我的好丈夫……我已经烦做你的妻子了,因为你不理解……”(258)面对妻子的抱怨,威尔逊毫无愧疚之感,反而恼羞成怒,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告诉你,你最好有个像样妻子的样子,不要再唠唠叨叨;否则,我肯定不会回到你身边……有很多女人愿意跟我在一起,你是知道的。”(258)艾丽斯对威尔逊的愤怒是反性别歧视意识对性别歧视意识的直接宣战,但威尔逊对艾丽斯的强硬回应表明,“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意识十分猖獗。通过再现威尔逊与艾丽斯之间的剧烈冲突,梅勒再次表明,“二战”期间,美国国内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战争,就其剧烈程度而言,毫不亚于国外的军事战争。
2 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
除了再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之间的战争,《裸者与死者》也再现了“二战”期间美国国内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之间的战争,从而再次证明,《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来平等”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到“二战”时期已经完全成了令人费解的谬误。小说中,除了男性人物谈论女性的话语、男性人物谈论自己妻子的话语以及男性人物与妻子的对话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意识与反性别歧视意识之间的冲突和对抗,种族主义意识与反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也比较明显,这可以在少数族裔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以及白人谈论少数族裔的话语中看出。
首先,小说通过明尼塔的生活经历再现了“二战”之前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意识与反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明尼塔是墨西哥裔美国人,他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小时候就开始做欧裔白人的美国梦,但自始至终过着少数族裔的生活。小说这样描述他的经历:“墨西哥小男孩们也吸收了美国的寓言,也想成为英雄、飞行员、情人、金融家。”(63)“在圣安东(San Antone),一个墨西哥男孩能干什么?他能干廉价餐馆的收银员,能做敲钟者,能在合适季节采摘棉花,能开杂货店,但他就是做不了医生、律师、大商人和领袖。”(65)“墨西哥小男孩们也吸收了美国的寓言,如果他们做不了飞行员,成不了金融家或军官,他们仍然能成为英雄……只是这不能使你成为坚定而冷漠的白人新教徒。”(67)在描述明尼塔的生活经历时,梅勒使用了“也”“但是”和“只是”等加强表达语气和表达效果的词语,旨在表明,像欧裔白人一样,明尼塔也可以做自己的美国梦,但他不可能像欧裔白人那样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小说从第三人称视角揭示了阻止明尼塔美国梦得以实现的种族主义意识,同时也通过温和的“抱怨”揭示了明尼塔内心深处的反种族主义意识。
其次,小说还通过犹太人罗斯和戈尔德斯坦因的生活感受再现了“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罗斯是犹太人,大学毕业,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但“他觉得凡事格格不入”(51)。罗斯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不是因为他与他们有年龄差距,而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歧视和排挤的对象。戈尔德斯坦因也是犹太人,他比罗斯年轻,但对非犹太人歧视犹太人的感受却比罗斯更深。在海外服役期间,他亲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几个士兵跟一个卡车司机开玩笑,卡车司机给他们说哪个连好哪个连不好。他换挡准备离开时回头喊了一句:“只希望你们不要到F连,那是安置犹太仔的地方。”他的话引起一阵哈哈大笑,有人甚至在他身后喊道:“如果他们把我安置在那儿,我就从部队退出。”随后又是一阵哈哈大笑(53)。这件事使戈尔德斯坦因颇受伤害,他“一想起来就气红了脸”,“他甚至在愤怒中感到一阵无望”,因为“他知道这于他无益”。他虽然“希望对那个回应卡车司机的男孩说点什么”,但“问题不在那男孩”,因为“他只是想耍点小聪明而已,问题在于那个卡车司机”(53)。戈尔德斯坦因知道,那个卡车司机之所以口出此言,并且能得到他人认可,是因为在他们身后,“所有一切都是反犹太人的”(53)。戈尔德斯坦因不明白为什么非犹太人要歧视犹太人,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允许反犹主义存在;所以,他反复责问上帝:“他们为什么这样呢?”(53)“上帝为什么允许他们这样?”(54)他对同胞罗斯说,“我就是不明白,上帝怎么能视而不见听由他们这样?我们应该是上帝的选民。选民啊!选出来受苦!”(54)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因此,当罗斯说:“我觉得你对这些事忧虑过多,犹太人对自己忧虑太多,”他回答说:“如果我们不忧虑,没有别人会忧虑”(54)。戈尔德斯坦因的话语表明,他不但具有强烈的反种族主义意识,而且具有很强的民族忧患意识;然而,他对这种猖獗的种族主义束手无策,不得不接受它的“合法”存在。因此,当罗斯抱怨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却找不到好工作时,戈尔德斯坦因说,“我的朋友啊,你就别跟我说了,我总是有工作,但有些工作不可一提啊,抱怨有何用?总体上看,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有老婆有孩子。”(55)
再次,小说通过白人谈论少数民族的话语再现了“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意识与反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白人军士克利夫特(Croft)认为,“有好的墨西哥人和不好的墨西哥人,你不能打击好的墨西哥人”(62)。白人布朗认为,犹太人罗斯“懒惰,无精打采,凡事都无兴趣”(119)。在白人看来,“你可以像杀死一头大象那样迅速从头部杀死一个黑鬼”(159)。显而易见,克拉夫特和布朗以及他们的白人同胞都是种族歧视者,他们谈论墨西哥人、犹太人和黑人的话语体现了他们的种族主义意识,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在威尔逊等人伤害戈尔德斯坦因的话语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一天,威尔逊跟战友聚在一起喝酒,戈尔德斯坦因在他们旁边给妻子写信。威尔逊邀请他一起喝酒,戈尔德斯坦因谢绝加入时,“他们都表示蔑视”,尤其是克拉夫特,他“吐了一口痰,不再看他”;加纳格(Gallagher)毫不掩饰地说:“他们没人喝酒”;威尔逊甚至骂道:“戈尔德斯坦因,你是个小屁孩,这就是你”;里德(Red)指责说,“人如果不能照顾自己,就一文不值”;威尔逊甚至说,“试图对他好真是一种错误”(203-204)。威尔逊等人有意伤害戈尔德斯坦因的话语是其种族主义意识的体现,加纳格的话——“他们没人喝酒”——清楚地表明,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成见由来已久。面对威尔逊等人的侮辱,“戈尔德斯坦因突然转身走开”,但他的行为并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喝酒的那帮人凑得更近了,他们之间现在有一种几乎可以摸得着的纽带”(204)。戈尔德斯坦因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大发怒火?”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恨我?”(204)因为“他努力成为好士兵,从未溜走搭乘便车,跟他们任何人一样强壮,比他们大多数人工作更卖力,站岗放哨时从未擦枪走火,不论这些多么诱惑他,但从未有人注意到这些,克拉夫特从未认识到他的价值”(204)。他思来想去,最后才明白,“他们是一群反犹主义者”(206)。他因此“讨厌跟他们做朋友”,因为“他们不想跟他相处,他们恨他”(206)。遭受威尔逊等人侮辱之后,戈尔德斯坦因突然意识到,“他恨所有跟他一起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他不记得过去什么时候他有几乎不喜欢的人。”(206)戈尔德斯坦因的生气以及心理变化体现了他的反种族主义意识,表明了他与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这种冲突与对抗也在白人伤害罗斯的话语中得以体现。克拉夫特率领的侦察连准备攀登安纳卡山(Mount Anaka),罗斯体力不支,数次跌倒被战友扶起,最后实在无力坚持,任凭战友怎样催促,他都拒绝爬起,气急之下,加纳格对他说道,“起来吧,你这个犹太讨厌鬼”。对罗斯来说,没有什么比“你这个犹太讨厌鬼”更能伤害他,也没有什么比“你这个犹太讨厌鬼”更能表达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憎恨。因此,一听到加纳格说他是“犹太讨厌鬼”,罗斯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一时间所有的疲劳都消失殆尽:“那种打击、那句话本身,就像一股电流一样激起了他,罗斯感觉自己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那样骂他”。“他不吭不声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努力接受这种震惊”,因为“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真正很愤怒,愤怒刺激着他的身体,推动着他走了几百码,又一个几百码,再一个几百码”(658-662)。加纳格的话语体现了他的种族主义意识,罗斯在加纳格种族主义话语刺激下做出的非常态反应体现了他的反种族主义意识,也表明了他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最后,小说还通过戈尔德斯坦因的童年经历和他对犹太人本质的理解再现了“二战”之前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意识与反种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戈尔德斯坦因七岁那年,在放学回家路上,一群意大利小孩打了他,叫他“犹太人”。他哭着回家,向妈妈讲述了自己被打的经历,从爷爷那儿知道了他被打的原因:“他们打你,因为你是犹太人。”他还从爷爷那儿知道,犹太人受苦的原因:“我们是一个被折磨的民族,被压迫者所困扰。我们必须从灾难走向灾难,这使我们比其他人更为强壮,也更为弱小,使我们比其他人更爱更恨另一个犹太人。我们受的苦那么多,我们知道了任何忍耐,我们总会忍耐的。”(483)年幼的戈尔德斯坦因虽然不太理解爷爷的高谈阔论,但他从此知道了“受苦”这个词的含义。爷爷将犹太人与“受苦”和“忍耐”紧密联系,不是为了叫戈尔德斯坦因向种族主义低头,而是叫他通过坚守自己民族的传统去对抗种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进行斗争。这个意义上讲,爷爷的话语体现了他的反种族主义意识。像明尼塔一样,年幼的戈尔德斯坦因“有抱负,他在读中学时就有诸多关于上大学、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的不可能梦想,在仅有的闲暇时间,他阅读技术书,梦想着离开糖果店,但当然了,他离开糖果店,便进入仓库干起了装船工的活,而他母亲又雇了一个小孩做起了他以前做的事”(484)。此处的“但当然了”不仅表明戈尔德斯坦因的梦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且表明戈尔德斯坦因难以实现梦想似乎理所当然,因为他生活在种族主义的控制之下,“但当然了”还表明了戈尔德斯坦因的反种族主义意识。
3 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
除了再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裸者与死者》还再现了“二战”期间美国社会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这种冲突与对抗体现了“二战”期间美国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这可以在卡明斯将军与其副手霍恩、美军士兵与军官以及克拉夫特军士与其领导的侦察兵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中看出。
卡明斯与霍恩是上下级关系,但非一般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因为霍恩是卡明斯精心挑选出来的副手;然而,卡明斯从未视霍恩为具有完整个性的人,因此,他们之间不断发生矛盾与冲突。在霍恩眼中,“将军身上有很多矛盾,他本质上对自身舒服有一种完全冷漠,但生活中却具有一个将军至少所必需的奢侈”(77)。虽然“他事先就被广告为营队里最有同情心、最和蔼的军官,他的魅力众所周知”,但霍恩发现,“他是个暴君,一个带着鹅绒般柔软声音的暴君”(78)。卡明斯认为,霍恩的一切权利都是他给予的:“你作为一个人的所有权利完全取决于我一时的性质……没有我,你只不过是个二等军士。”(82)因此,跟卡明斯谈话时,“霍恩一直处于防守状态,掂量着他的话语,说话时毫无自由可言”(84)。虽然“他害怕过的人不多”,但“他害怕将军”(170),因为他必须接受卡明斯的权力理论,成为其权力实施的对象;然而,他的本性使他走向反抗。卡明斯对霍恩说:“作为美国人,他们大多数都具有我们民主的特殊体现,他们脑子里不断放大他们自己作为个人应该具有的权利而对他人作为个人应该具有的权利毫无概念。农民正好倒过来了,我告诉你,造就了士兵的是农民。”(175)因此,他要“镇压他们”,因为“每次士兵看到军官得到一点特权,他都会受到一次打击。”(175)但霍恩回应说,“我不明白这个,在我看来,他们会更加恨你。”(175)卡明斯回答说:“他们会恨我,但他们也会更怕我。我不管你给我什么人,只要他在我手下时间足够长,我会让他怕我……我要告诉你,罗伯特,要让部队工作运转,你不得不让每个人在惧怕之梯找到合适位置……当你惧怕上司而轻视下级的时候,部队的作用就会发挥得最好”(175-176)。卡明斯认为:“二战”是“权力集中营”,“政治跟历史无关,就像道德规范跟具体个人的需要无关一样。”(177)他认为,“在部队,张扬个人个性的思想是一种障碍。”(181)卡明斯关心的不是善与恶的问题,也不是爱与恨的问题,而是上级与下级、有权与无权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权力的分享。他是权力追求的偏执狂,甚至连众人眼中至高无上的上帝也低他一等,他不认为他像上帝,而认为上帝像他(182)。如果没人敢挑战上帝的权威,卡明斯的意思显而易见:他绝不容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因此,霍恩试图挑战他的权威时,他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惩罚,“掷烟头”事件就是明证。霍恩本能地知道,“不能将火柴梗丢在将军的地板上”(314),但卡明斯对他的压制使他做出了违背自己本能的举动。“他将火柴梗扔在将军的脚柜旁,然后,随着心脏的快速跳动,他小心翼翼地将烟头扔到了将军干净地板的中间,狠狠地踩了几下,带着惊讶而受困的自豪,站着看着它。”(314)他这样做,目的是“让卡明斯看见,让他看见”(314)。看到原本干干净净的地板上霍恩丢下的火柴梗和烟头,卡明斯的第一反应是,“要是此刻他手中攥着一只动物,他会把它捏碎”(318),因为“霍恩所做的就等同于士兵的手伸到了他本人身上。对卡明斯来说,这是他部队独立的一个象征,是对他的反抗”(318)。卡明斯认为:“他的士兵对他的惧怕和尊敬,现在是理性的,是对他惩罚他们的权力的承认,这还不够,还少了另一种惧怕,这种惧怕是不可推理的,它包含了他的极大权力,从效果来说,是挫败他的种种渎神的东西。地板上的烟头是一种威胁,是对他的否认。”因此,“他不得不直接而无情地应对”,因为“你越滞留反抗,反抗就会越厉害,不得不毁了它”(318)。卡明斯对霍恩进行了严厉惩罚,但也受到霍恩强烈反抗。卡明斯与霍恩进行激烈的舌枪唇战,体现了极权主义意识与反极权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卡明斯对霍恩阴险毒辣的惩罚以及霍恩的败退表明,“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意识极为猖獗。
卡明斯与霍恩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所体现出来的极权主义意识与反极权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也体现在美国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之中,这可以在比纳上校(Major Binner)与卡明斯将军对拉宁军士(Sergeant Lanning)的恐吓中看出。拉宁军士巡逻作假被发现后,比纳上校问他:“你巡逻期间有多少次这样不负责任?”他回答说:“这是第一次,长官。”比纳上校又问他:“你们连或营还有其他军士也一直做虚假和错误巡逻报告吗?”他回答说:“没有,长官,从未听说。”听到这样的回答,卡明斯将军威胁说:“拉宁,你想回到美国还是想烂在这儿的罪犯集中营?”他回答说:“长官,我这身制服穿了三年,而且……”卡明斯将军进而威胁说:“就是你跟我们一起二十年,我也不在意。还有其他军士也一直做虚假巡逻报告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长官。”卡明斯将军换用另一种方式威胁说:“你有甜心[情人]吗?”他回答说:“我结婚了,长官。”卡明斯将军继续威胁说,“你还想看到妻子吗?”他回答说:“她一个月前离开了我,长官,我收到了绝交信。”(315)从这样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尽管比纳上校与卡明斯将军竭尽全力对拉宁军士实施权力,但拉宁军士始终没有就范。拉宁军士的行为体现了他对压抑性权力的反抗,也体现了他的反权力意识。拉宁军士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反权力意识也体现在明尼塔的话语中。在明尼塔眼中,所有军官都是“他妈的讨厌军官”,因为“他们是一帮狗杂种”(367)。霍恩从司令部调出之后,接替克拉夫特成为侦察连连长,对克拉夫特的“提升构成威胁”(李公昭 等,2003:68)因此成了克拉夫特的“敌人”。然而,霍恩跟卡明斯和克拉夫特完全不同,到了侦察连之后,他告诫自己“应该很快形成这样的思想:他们[侦察连士兵]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434)。他将手下士兵看成“不同个人”的思想显示了他的反权力意识,使他成为读者心目中卡明斯与克拉夫特的对立者。但是,当他强迫克拉夫特为杀死一只小鸟而向罗斯道歉时,他却发现自己也成了卡明斯,因为“他服从命令捡起地上的烟头时卡明斯可能也是这样的感觉”,因此,他突然“很反感自己”(532)。霍恩的自我反感体现了他的反权力意识。
小说中极权主义意识与反极权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还体现在克拉夫特与加纳格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中。加纳格与克拉夫特同在一个侦察小分队,长时间侦察跋涉使他们身心疲惫。加纳格希望克拉夫特放弃登山计划,带领小分队踏上归途;然而,克拉夫特却没有丝毫踏上归途的念头,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登上安纳卡山(Mount Anaka),将它踩在脚下,从而征服它。但在加纳格和明尼塔看来,登上安纳卡山几乎不可能,如果强行去登它,就等于白白送死。因此,加纳格与克拉夫特之间发生激烈争吵。加纳格质问克拉夫特,“你究竟为什么不返回?难道你还没有得到足够奖章吗?”克拉夫特以命令的口气说:“加纳格,闭上你的臭嘴。”但加纳格毫不惧怕地说:“我不怕你,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克拉夫特再次命令加纳格:“闭上你的嘴巴。”但加纳格回击说:“你最好别跟我们作对。”(691-692)加纳格对克拉夫特的抗拒是他对权力的抗拒,他们之间的冲突是权力意识与反权力意识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表明,“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Foucault, 1978: 95)。
4 结语
通过再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裸者与死者》再现了“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在种族、性别及阶级等方面的各种法西斯主义思想与行为,表明虽然美国打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号参与海外战争,却无法遏制并消除国内十分猖獗的各种法西斯主义意识与行为。小说为什么要再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说:“艺术的最终目的就是强化,甚至,如果必要的话,深化人们的道德意识。”(384)梅勒说:“我们感觉非常圣人般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许是邪恶的。我们觉得最邪恶因而最终是腐化的时候,我们也许,借助上帝的惊讶判断,被视为圣人般的。”(Mailer, 2003: 151)梅勒所言表明,他绝非生活在真空中进行纯艺术探索的唯美主义作家,而是具有强烈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梅勒认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他必须要有一种不安意识、一种冒险意识、一种善于洞察的意识(Mailer, 1959: 276)。1955年,梅勒接受《独立报》(Independent,原名Exposé) 编辑利勒·斯图尔特(Lyle Stuart)采访时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想接触人,通过接触人,对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产生一点影响。”(Mailer, 1959: 269)1963年,他接受斯蒂芬·马尔库斯(Steven Marcus)采访时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作家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就能影响自己时代的意识,从而间接地影响后来时代的历史(Mailer, 1978: 26)。梅勒传记作家希拉里·米尔斯指出,梅勒的这一思想源于欧洲思想:“作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他必须参与政治。”(Mills, 1982: 99)但评论家迈克尔K.格兰迪(Michael K. Glendy)认为:“梅勒早已接受了更早的影响,即认为艺术根植于政治。”(Glendy, 1995: 7)尼格尔·雷(Nigel Leigh)指出:“至少在1948年选举之前两年,梅勒慎重地接受了华莱士(Wallace)的预言:美国已处于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危险中。”(Leigh, 1990: 6-7)迈克尔K.格兰迪认为:“《裸者与死者》的政治语境充满的正是这种确信。”(Glendy, 1995: 8)可见,梅勒再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的性别歧视与反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以及极权主义与反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梅勒熟知美国社会各种权力意识对人性的压制和束缚,倡导自我与他人自由,倡导人人平等、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倡导通过理解、宽恕、忏悔和同情等人类美德消除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从而达到和平共处、自由平等的理想状态。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说,他憎恨“拥有权力而无同情心的人,即那种连简单人类理解都没有的人”(271)。他还说,“我认为黑人与白人结成配偶是黑人的绝对人权。”(Mailer, 1959: 356)梅勒在《总统案卷》中说:“如果犹太人和黑人能获得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和爱尔兰天主教徒一样的平等,美国则会完全不一样。不管它会成为什么,肯定跟我们能够想象的任何情况完全不同;相反,如果黑人和犹太人被同化到现在美国人生活的那种毫无声息、毫无想象的水平,美国则会跟现在完全一个样,甚至更糟。”(Mailer, 1963:188)
梅勒认为,伟大的小说能够对社会的自由发展做出贡献。他说:“如果伟大的小说消失了……我们将会更加远离自由社会。”(Mailer, 2003: 161)他还说:“一部伟大的小说具有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新的意识”,但是,“我们在欣赏这部作品之前,必须被这种新的意识所鼓舞”(Mailer, 2003: 287)。《裸者与死者》无疑是一部意义深刻的小说,它能够带给“二战”后读者一种新的意识;然而,只有被这种新的意识感染之后,读者才能真正欣赏它的深刻意义。作为一部“战争”小说,《裸者与死者》力图再现的不是“二战”本身,因为它只再现了战争的一个切面,它真正力图再现的是“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各种权力意识与反权力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通过再现这些权力意识与反意识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梅勒不仅表达了他对人类平等、自由与和平的倡导,而且告诫人们,真正威胁人类自由、平等与和平的不是军事战争,而是各种权力意识。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