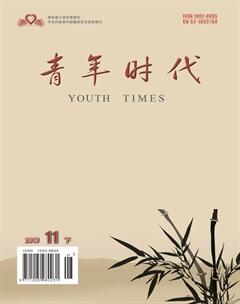小组社会工作介入受欺凌儿童的思考
摘 要:校园欺凌问题一直是中小学校园中的棘手问题,卷入任何形式校园欺凌的学生身心健康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小学高年级这部分儿童。受欺凌儿童作为直接的受害方,常表现出自我认同感低下,将失败归因于自己,低自尊、低自信等特点,在生理、学习以及社交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作为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小组社会工作可以减少小组成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其他压力反应,增强自尊,减少抑郁和孤立,并促进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本文结合目前的研究和理论,探讨了小组社会工作介入受欺凌儿童的可行性和优势,同时提出了社会工作者在具体实务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
关键词:受欺凌儿童;小组社会工作;情感
一、小组社会工作方法与受欺凌儿童
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对象的方式有3种,即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以及社区社会工作。受欺凌儿童被迫处于一种社会应激状态,生理和心理方面均承受着不同寻常的压力,自我认同感低、缺乏社交信心和活力,他们通常不会向老师和家长求助,此时最好的朋友或者和他处境相同的人群是其最容易接受的倾诉对象。小组工作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工作方法,属于社会工作中观层次的实践,被视为“没有家人的互动关系亲密,却比组织或机构更有意义的关系”,在这种群体中,成员之间存在着多种关系,通过互助和赋权,实现成员之间相互援助的目的,小组工作方法被认为特别适合于满足有创伤病史的个人治疗需要。
二、受欺凌儿童的特点
欺凌事件的参与对象包括欺凌者、受欺凌者以及旁观者,并且绝大多数小学生在面对欺凌事件时选择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学习生活中,欺凌事件对于受欺凌儿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生理方面
儿童正处于建立认知图示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遭到欺凌使儿童被迫进入社会应激状态,弹性儿童在面对威胁时会很好地调节自己的注意力和情感,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而缺乏弹性并且外界也没有及时介入帮助的儿童,长期持续的欺凌会使其恐惧、不安、焦虑、抑郁,患精神疾病的概率会增加,更严重的会威胁生命。
(二)学习方面
受欺凌的儿童会封闭自己的内心,难以和家长老师叙述自己遭受的困难,内心的情感压抑会影响学习行为。学习兴趣降低、课堂上难以集中注意力、不主动发言、不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方面有疑惑,害怕寻求老师同学和家长的帮助,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三)社交方面
受欺凌的儿童缺乏自信,害怕与别人交往。他们对人际关系较敏感,对他人的主动亲近和关心产生抵触,对陌生人存在戒备心理,容易被集体排斥在外,难以建立友谊。
三、小组社会工作介入受欺凌儿童的优势
受过创伤的人一般被认为缺乏“自尊调节的精神结构”,因此培养独立、有凝聚力和稳定的自我意识是非常必须的,Foy和他的同事指出,小组模式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治疗干预,功能在于尽量减少、改善并补救创伤。研究发现,小组参与可以减少小组成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和其他压力反应,增强自尊,减少抑郁和孤立,并促进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这与社会工作介入受欺凌儿童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实务过程中,小组工作介入受欺凌儿童具有以下优势。
(一)小组活动具有多样的活动形式
小组活动包括互动游戏、情景模拟、集体分享等。将专业的社会工作方式融合在多样的活动中,一方面能够吸引儿童,提高活动参与度,获得更好的活动效果;另一方面,在小组活动过程中,小组工作者的目的正是根据每个组员的能力与需求促进个人成长,使个人与团体、团体与社会之间达到适应,促使每位组员发生改变,同时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与独特性。
(二)小组工作是一个符号互动的场域
小组中的成员可以互相影响。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个体通过感知他人对自己的反映和评价,从而建立起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形象和自我评价。通过小组活动的形式介入受欺凌儿童,将相同经历的儿童聚集起来建立安全的环境,增加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通过同伴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从而建立起自我认同,促进个人成长。
(三)小组工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小组工作的目的不是在一两次的活动中对服务对象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改变,而在于在过程中依托与同质个体之间的信任,建立集体意识,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四、介入过程面临的挑战
在受欺凌儿童小组的活动过程中,我们应当更注重成员之间的互助、力量和赋权,而社工者的职责就在于促进这一互助进程。受欺凌儿童群体的独特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强调受欺凌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不同,介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以下3个挑战。
(一)成员之间稳定的关系
个别成员对其他成员的不信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孤立倾向可能会影响小组顺利开展。在进入小组之前,成员无论是否知道其他组员和自己有类似的经历,个别参与者可能会以自己当前的认知来看待其他人,认为他们是不同的。在被欺凌儿童小组工作的开始阶段,工作重点在于帮助成员之间建立信任感,从而进行舒适顺畅沟通。个体成员的性格、处事风格以及在小组中的舒适度创造了一种与小组成员的联系感,并决定了他是否能够全身心地到小组活动中。因此在小组组建之前,社会工作者需要通过量表和问卷进行初步筛查进入小组的人,确保每一个小组成员没有被孤立或者被强化。
(二)小组中的情感表达
在小组互动中,受欺凌小组的成员随时都有可能宣泄自己的感情,社会工作者要为这种强烈的表达做好准备,小组成员也可能会被这种情感宣泄所吓倒,并在之后的活动中暗示自己不再进行表达,但是情感表达在小组活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社工需要通过物理环境和群体文化支持两个方面来推进小组成员表达。
在小组工作中,社工需要关注的是运用哪些情感表达方式有助于小组成员的成长和发展,而不是花全部精力去关注小组成员表达出来的情绪。此外,小组社会工作者必须警惕小组和个别成员再次遭受创伤,对于一些受创伤很严重的儿童,社工应当主动去接纳并抑制这种表达,而不是鼓励他将这种强烈的情感表达出来,因为持续地进行强烈的情感宣泄对年幼的儿童来说也许并不是好事,每一次倾诉都在回顾自己经历的创伤。van der Kolk指出,“当病人获得稳定、控制和洞察力时,治疗就可以终止。如果病人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足,挖掘过去的创伤没有内在价值”。因此,情感表达是为了促进成员问题解决并给他们赋权,而不是令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感到束手无策。除此之外,社工还应该注意小组成员之间情感的互相传染性,避免个别成员的回忆对别的成员造成影响,在儿童的大脑中受欺凌的那段经历会随着时间推进,主动添加新的想象进行重组产生改变,记忆本身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三)小组过程的阶段性
组织推进小组活动中,社会工作者需要认识到每个小组成员的经历不同,因此他们每个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这同时体现了社会工作中的个别化原则。这就要求小组活动需要循序渐进,分阶段实现各个目标。在小组工作的开始,目的是使小组成员意识到自己的这段经历和感受是正常的,进而理解他们被欺凌的经历。只有在小组情感和结构稳定之后,才鼓励这部分儿童深入探索經验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和反应。因此,对于受欺凌小组而言,社会工作者需要分阶段、持续进行介入。对于刚进入小组的成员来说,任务清晰、时间明确更容易给他们带来安全感。通过彼此之间的了解,自己和其他成员的倾诉使经历正常化,减少了他们的孤立感和不同。在我们的小组中,我们要介入的是这些症状的共性,而不是每个组员的受欺凌情况,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任务重点在于帮助小组成员建立共性和个性经历之间的联系,参与小组对于受欺凌儿童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小组的结构形式给他们提供了安全保障。
对于受欺凌的儿童来说,他们不会同时关注自己的欺凌体验和其带来的情感反应。在整个小组活动中,社会工作者要通过容易接受的方式使小组成员学会宣泄和表达,通过这种方式学习新的、更有效的方法来应对创伤及其带来的负面情绪。
参考文献:
[1]林菲.4~6年级小学生受欺凌与自尊、焦虑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7.
[2]Stolorow R D,Lachmann F M.Psychoanalysis of developmental arrests[J].Theory and treatment,1980.
[3]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崔艳丽(1995—),女,汉族,山西吕梁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青少年发展与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