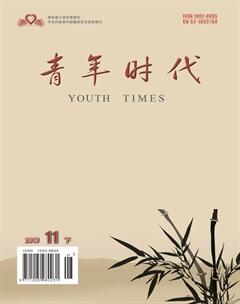迟子建长篇小说中的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迟子建长篇小说中对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世界、萨满教文化与殡葬习俗这两方面的描写,关注小说中异文化所表现出的民俗学色彩,解析作者潜藏于文本中的精神诉求,进而从异族形象塑造的文学意义这一角度对迟子建的长篇小说进行整体性思考。
关键词:日常生活世界;萨满教文化与殡葬习俗;精神诉求;异族形象
一、引言
在迟子建的家乡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均系东胡民族分支,在活动区域、信仰、习俗方面大同小异,从小耳濡目染的迟子建在长篇小说中综合这两支民族相似的生活习惯、自然崇拜和发展命运,塑造了许多能同时体现这两支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形象。《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跋就是迟子建对这两支民族进行综合创作的佐证。在生态观念和发展观念的影响下,相较于其他人物形象,她笔下的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也更接近东北地域文化的原生形态,并作为汉族作家小说中的异族形象,表现出了独特的文学意义。
二、日常生活世界
风土人情是一个地区文化资源的最外在表现。在长篇小说中,迟子建立足于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聚居地的环境特征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习惯,通过衣食住行的诸多细节,在小说中生动地建构了鄂伦春人与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呈现出了专属于这两支东北边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图景与生存状态。
在迟子建的笔下,鄂伦春人与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迥异于汉民族居主体的外部世界。因为这处异世界的存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方式的惯常认知被打破,强烈地感受到了大自然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这两支民族被大自然包容的幸福感和生命得以昂扬绽放的喜悦感。然而这处异世界并不因自身生活方式的原始质朴与外界隔离,他们需要用猎物换取枪支、盐、面粉等不能自给的物品,这使他们有了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通过小说中提到的换物细节,我们得以对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的性格进行更全面地审视。如果他们的性格里多一些精明与算计,那他们的生活水平定能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活世界也就不再那么令人向往。在《伪满洲国》中,虽然作者的创作主旨就是呈现小人物平实的生存状态,但鄂伦春人的生活世界显然比其他人多了几分无忧无虑。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最后一任酋长的女人质朴恬静的生活方式让城市中的很多人羡慕不已。在《树下》里,正是因为有那些鄂伦春的小伙子,历经苦难的七斗才有了一种内心的慰藉,才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在《群山之巅》里,绣娘不仅为边地小镇带来了几分异域情调,她身上的率性与纯真也通过她的儿孙得到了宝贵传承。
在这处异世界里,不仅人可以免受或少受世俗侵扰,就连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驯鹿、白马等动物都有了独立的思想和与人类平等的地位。而迟子建也正是以这些生活细节为基础,确定了她在进行异族形象描写时的叙事基调,在逐步接近东北地域文化原生形态的过程中,含蓄地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以此为镜,反观人类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从而进一步展开了对这两支民族发展命运的思考。
三、萨满教文化与殡葬习俗
东北地区由于纬度较高,自然环境恶劣,经常受到暴雪、野兽和外族入侵的威胁,农业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关内地区。在生产力相对低下、人们思维水平较低的年代,生存本能促使居民借助神力來维系自己的生存。此外,由于东北地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又受到北亚和西域等多民族文化的影响,始终没有形成地域的主导文化,所以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萨满教文化一直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取向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
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受到科学民主等思想的影响,传统的萨满教文化被视作愚昧与落后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政策的取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萨满教文化中的相关神事活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萨满教文化作为东北地区的原生文化,已经在人们心中形成了永久的文化记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和新一代东北作家渴望借助地域传统文化资源构建真正东北文学的诉求日益强烈,文学作品中开始越来越多地看到萨满教文化的相关描写。在长篇小说写作中,迟子建推进了郑万隆等人对于萨满教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观念这一合理因子的肯定。从对文化符号的缅怀升华到了在地域原生文化的内核中去反思当代社会的种种价值观念的高度。在作品中她通过打猎后的祭祀、日常生活中的禁忌等细节对萨满教文化进行了生动刻画。其中,她对萨满教文化观念影响下的风葬习俗描写着墨最多。
在《伪满洲国》中,迟子建借紫环希望乌日楞死后能被风葬,向读者呈现了鄂伦春人风葬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不过她在小说中对于风葬习俗的认知似乎更多地停留在了民俗层面的了解,她对风葬过程的细腻刻画也主要侧重于民俗学方面的意义。但是在小说《群山之巅》中,迟子建对于绣娘风葬的描写则鲜明地体现出了她对人生终极追求的思考。通过绣娘燃烧的骨灰,作者试图重新激荡起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业已经麻木的神经,激发我们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她想唤起我们对大自然的归属感,带着我们开始一次追问生命终极意义的灵魂之旅。
不仅是对殡葬习俗认知的升华,从《伪满洲国》到《群山之巅》,迟子建对彰显萨满教文化力量的核心人物萨满的认知也实现了自我超越。在《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塑造了3位萨满形象。在认可萨满身上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同时,她也用充满温情的笔触书写了萨满们在获得神力时所承受的巨大苦痛。在小说《伪满洲国》中,迟子建想表达的只是救回除岁的老萨满身上所具有的神力以及跳神招魂这一事件所体现出的神秘色彩。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则有意识地关切到了萨满身上所体现出的“大爱”力量。为了让对神力持轻蔑态度的吉田认识到萨满的力量,尼都萨满用生命作为代价跳了人生中最后的神舞,履行了一位萨满能为民族尽到的最后责任。另一位萨满妮浩也是如此。大兴安岭火灾那年,妮浩用生命完成了神舞,为鄂温克人求来了雨水。和尼都萨满一样,妮浩也是用生命履行了萨满对一个民族最后的责任。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不以评论文化的优劣为目的,而是为了展现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人物性格与人生追求。通过上述2部小说中的3位萨满,作者表达了对生命自然状态和敬畏神性精神的追寻,为读者树立了永恒的人道主义精神旗帜。
四、作为异族形象的文学意义
在长篇小说中,迟子建自下而上地构建了专属于这两支民族的文化体系,生动地呈现出了这两支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生存哲学,与作为现代化象征的汉族主体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由于迟子建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与视角去书写这两个民族的命运变迁的,一方面,她能够突破这两支民族传统文学的界限,而且不受情绪偏见左右,正视不同民族的现实关系差别;另一方面,无论她具有怎样博大的悲悯情怀,都无法彻底掌握这两支民族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诉求。加之迟子建在写作小说前就已经深谙汉民族占主体的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弊病,这使她对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的书写在潜意识中就带有了一种借他山之玉以攻己之石的目的,即从文学的层面通过鄂伦春人与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理念为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东北乃至整个社会提供了一处永恒的精神家园。
这种民族互补性的初衷是好的,但不能因此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民族在刚刚开始改变既有生活方式时,都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依莲娜和索玛那样因为不适应现代化生活而产生的悲剧固然值得惋惜,但这毕竟只是个案。作家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去思考当一个民族被迫进入现代化的浪潮后,应该进行怎样的自我调适,才能适应新的生活。很明显,作者更多地沉浸在鄂温克人原始生活的质朴,她希望这处城市化的对极能够永远存在,而忽视了对他们中大多数人新生活的思考,作者对鄂温克族如何取汉民族之长而补己之短的书写明显不足,这使得广义上的汉民族与这两支少数民族的关系变成了单向度的借鉴与参考。这种凝聚了作者感情的创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让鄂温克族成为了小说中的背景化存在,他们独立的文学意义被削弱,而更多地成了城市化过程的对照者。
这种背景化的处理方式在另外3部小说中同样体现了出来。在《树下》中,马背上的鄂伦春小伙子们“来无影去无踪”,他们神话一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给处于困境中的七斗提供一定的心灵慰藉,就连他们的白马也都成了精灵一样的存在。在《伪满洲国》中,山林里的鄂伦春人也仿佛与整部小說的叙事节奏相脱节,他们的存在似乎更多的只是为了让摆脱了往昔痛苦生活的紫环有了一定的心灵寄托并与胡二的生活形成一定的交集。虽然鄂伦春人所处的大兴安岭地区受抗日战争的影响相对较弱,但与鄂伦春人有关的生活细节和宗教细节基本都是通过胡二和紫环的视角呈现出来的。在这部没有明确主角的长篇历史小说中,鄂伦春人完全成了陪衬,作者甚至没有提到一个鄂伦春人的名字。在《群上之巅》中,作者对绣娘孟青枝进行了鲜明的文学加工,她带有奇幻色彩的辞世与风葬场面更与松盏镇中其他人为了权益的勾心斗角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结语
虽然作者外来者视角的先在缺陷与反思现代化进程的情感投射,使小说对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如何实现传统游牧生活与现代城镇生活之间转变的思考不够深入,让这两支民族与他们必将面对的现代生活形成了一定对立。但迟子建以汉族作家的身份与这两支少数民族之间进行了近距离接触,掌握了丰富的生活资料,深化了小说的民俗学色彩,为读者提供了东北边地两支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生活图景,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参考文献
[1]迟子建.伪满洲国[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迟子建.伪满洲国[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迟子建.树下[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方守金,巧子建.自巧化育文学精灵——旧子建访谈录.[J].文艺评论,2001(3).
[6]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06(2).
作者简介:丁安琪(1997—),女,满族,辽宁本溪人,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东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