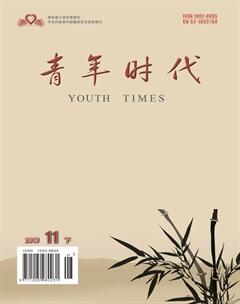以宇文所安的追忆观与碎片说解读潘岳的《悼亡诗(其一)》
摘 要:宇文所安的《追忆》一书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复现的现象,将“回忆”当成创作者的“殿堂”,让历史历代的文人骚客在这块领地上不断复写、审视。本文借鉴宇文所安对“回忆”的观点和碎片说,试对潘岳的《悼亡诗(其一)》进行解读,潘岳的悼亡诗通过写妻子的遗物,用碎片化的意象重建回忆场景,侧面勾勒出了妻子的活泼动人、未经男性道德化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悼亡诗;宇文所安;追忆
一、宇文所安的“追忆”观与碎片说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利用西学背景对唐诗展开了视角独特的研究,其著作《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下文简称《追忆》)《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等著作在中国广受欢迎。
《追忆》一书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视为一种核心主题:由于对于“不朽的期望”,诗人希望后人能像“我”記住前人一样记住“我”,因此“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同往事千丝万缕的联系”。宇文所安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分析了回忆与传统、死亡、历史的道德性和机械运转的关系,展现了隐喻法和举隅法两种诗法在诗人追忆往事中的运用,进而分别以沈复的《浮生六记》和李清照的《金石录序》为个案,提出了沈复“微观世界”和“入侵式”的回忆复现模式,认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看似美满的婚姻中,实际上潜藏着汹涌暗潮。后者也呼应了国内学者对此的争议和探讨。
宇文对“追忆”的阐述独辟蹊径,在《复现:闲情记趣》一文中,作者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他对“回忆”的界定:回忆不是故事,但“回忆可以是进行大量沉思和回顾的场合”;虽然回忆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可视的形象,但是它又“不同于展现在我们肉眼前的形象。我们眼中的形象有细节作为背景,在生活世界中有它的延续性;在我们的回忆中,背景是模糊不清的,出现的是某种形式,故事、意义、同价值有关的独特的问题等,都集中在这种形式里”。
此外,作者提出了贯穿全书的观点:回忆来自过去的断裂的碎片;“它闯入正在发展中的现实里,要求我们对它加以注意,我们‘沉湎于其中”。诗人只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碎片”,周围环境的丰富细节以及对他个人所具有的意义,就全涌现在诗人的心头,所有这些都凝聚在一个形象、一个名字或者某一时刻里。宇文提出了重要的“断片说”:
在我们同过去相逢时,通常有某些断片存在于其间,它们是过去同现在之间的媒介,是布满裂纹的透镜,既揭示所要观察的东西,也掩盖它们。这些断片以多种形式出现:片段的文章、零星的记忆、某些残存于世的人工制品的碎片。
一块断片是某件东西的一部分,但不只是整体的某一成分或某一器官。假如我们把各种成分组合在一起,得到的是这件东西本身;假如我们把全部断片集拢起来,得到的最多也只能是这件东西的“重制品”。断片把人的目光引向过去;它是某个已经瓦解的整体残留下的部分:我们从它上面可以看出分崩离析的过程来,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它那犬牙交错的边缘四周原来并不空的空间上。它是一款“碎片”:它同整体处于一种单向的、非对换的关系中。
这些碎片起到了“方向标”的作用,把我们引向某种失去的东西。
二、抚存追忆:悼亡诗中的意象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类反复出现的抒情诗,悼亡诗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抒情诗的规定性。首先,悼亡诗一般指悼念亡妻而作的诗;其次,“生离死别”成为最常见的主题,并且意象的使用多与家庭生活相关;最后,悼亡诗为中国诗人提供为数不多的能够公开谈论甚至歌颂婚后爱情的场所,抒发对妻子的赞美或哀思。
例如《追忆》所示,出于对留名千古的期待,诗人反复追忆先人、历史事件、传统,让回忆成为了一个容纳的场所,一个“殿堂”,让“已经物故的过去像幽灵似的通过艺术回到眼前”。这种回溯代表了诗人想要不断跨越记忆鸿沟的努力,触发点可能是一件物品,可能是只言片语,虽然不能代替往事,但它能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让人们跟着诗人走向已经消逝的、不复存在的场景。
这在悼亡诗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面对亡人旧物寓寄情思似乎成为一个判断该作品是否为悼亡诗的一个重要标志,睹物思人,抚存悼亡,故妻不在,她留下的妆台、一撮头发,甚至曾经寓居的房间,都成为了故人的一部分,让诗人深深地怀念。例如,《诗经》中的《葛生》被认为是悼亡诗的发轫之作。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恫千苴屠!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在郝懿之前都将此诗解为征人妇思夫之作,然而诗中的“角枕”“锦衾”为收敛死者所用,因此郝懿判定其为一首悼亡诗。因此将最后两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理解为“谷则异室,归于其室”式的誓言,才比较说得通。
在悼亡作为诗歌类型形成的过程中,西晋文学家潘岳是标志性的人物,被认为是悼亡诗的之祖。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秋,爱妻在洛阳去世,潘岳悲痛欲绝,写下《哀永逝文》《悼亡赋》《杨氏七哀诗》等一系列哀悼之文,其中最动人的就是三首《悼亡诗》,后来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而“悼亡”也约定俗成为追悼亡妻的专称,不可用于悼念他人。《悼亡诗》其一: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怳如或存,回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诗人从时光流逝说起,妻子不在的岁月里,季节交替如白驹过隙,时光流逝而不易察觉,由此引出了诗人此时与亡妻人天永隔的怅惘,甚至生发出独留在世上有何益之感,只是在勉力应对朝廷的职责而已;然而回到家中,面对昔日两人共同生活的房屋里,却再也看不见亡妻的音容笑貌。
9~14句详尽写了诗人“望庐忆亡妻”的情景:帐帏和屏风上已没有妻子的形迹,只有生前的墨迹尚存,衣服上还残存昔日妻子的香味,生平玩用之物还挂在壁上。诗人把读者带入了他如何回忆亡妻的场景,仿佛能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自己家的屋檐下,寂寂地环视房宇,跟人们细细诉说哪些事物是妻子生前就如此放着,哪些东西现在已找不到踪迹。妻子虽然亡故,与诗人生死两隔,但是遗留的物品:帏屏、翰墨、流芳、遗挂……如同她留在这里的细小碎片,诗人努力想把这些碎片拼起来,以此营造一种故人仿佛还在的情景。
但遗憾的是碎片不能代替整体,也无法將往事重现。“怅怳如或存,回遑忡惊惕。”诗人恍惚间心中五味杂陈,惶、忡、忧、惕,四种情绪在他心中交替翻沉。置身这房间里,四处散落的妻子的碎片,如影子一般,给诗人一种亡灵隐现其中的错觉,但是诗人及时醒悟,他明白无论如何回忆,甚至努力保持能让他唤起追忆的场景,他都不能跨越时间和生死给他们之间设下的鸿沟,一时间惶恐忧惧不已。
诗人用“同林鸟”“比目鱼”这种经常象征爱情和相守的比喻来控诉生死相隔的残酷和往事不能复现的怅惘。往日应对朝堂之事后回到家里,还能看到妻子在帏屏游走,或者在桌前挥毫的温馨场面,而此时,这反而成为一种人生的缺失。对妻子的思念,让诗人寝食难忘,对孑然孤存于世的忧惧,也不会随着停止回忆而褪去。
《悼亡诗》其它两首与第一首章法大体相同,只是在不断改换情景和陈设的细节,以多方面展开被唤起的记忆,形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也有研究者认为,潘岳的所有悼亡诗都集中在“塑造一个笃于夫妻情谊的丈夫形象,让我们看到他多么痴情地眷怀亡妻,沉溺在无尽的追思中不能自拔,可是妻子的形象却没在诗中出现”。确实,在潘岳这几首悼亡诗中,诗人着重表现的是悼亡主体也即作者自己,而非悼亡对象,对妻子的形象、性格或美德未着笔墨,仅以物品作为意象出现来指涉妻子生活的场景,虽然情感真切动人,不免有对妻子形象的物化之嫌。
然而,仔细分析“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几句,随着诗人回忆的思绪,在帐帏和屏风间留连的妻子,握笔挥毫的妻子,采新花熏衣衫的妻子跃然纸上,这些碎片传递着众多有关女主人的讯息,诗人甚至没有为妻子施予道德的装饰,也未将其女性模式化。比如在追忆之时,诗人选择墨迹而未提及女工之类代表女性刻板印象的闺中物品,而将亡妻塑造成一个跃然活泼、活色生香而不乏才情的女子。因此,可以说,潘岳即使将亡妻形象隐藏在其遗物碎片的后面,也并未遮盖住她作为怀念对象的魅力,在曲折隐约中更显男女婚后情爱的细密和质朴。
三、结语
宇文所安的《追忆》一书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复现的现象,将“追忆”这一文学从中剥离出来,在哲学、历史和审美向度上作了详尽的阐释。其中提出了将“回忆”当成创作者的“殿堂”的看法,赋予这种主题以空间感和仪式感,历史历代的文人骚客从无到有地撰写出精妙的诗篇,引领读者走向更远古的往昔,复刻出精彩的独家记忆,给人们展现出他们在这块领地上独特的视角。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中,其西方丰富的理论资源和严谨论证逻辑为人们解读唐诗提供了他者视角,这种陌生化下的再审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多义性和丰富性,也大大拓展了古典文学的意义阐释空间。
参考文献:
[1][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蒋寅.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3):1-10.
[3]杨周翰,王宁.中西悼亡诗[J].外国文学评论,1989(1):109-113.
[4]吴思萌.谈宇文所安的“断片”说:读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有感[J].北方文学,2015(7):95-96.
作者简介:许松雪(1991—),女,回族,山东淄博人,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