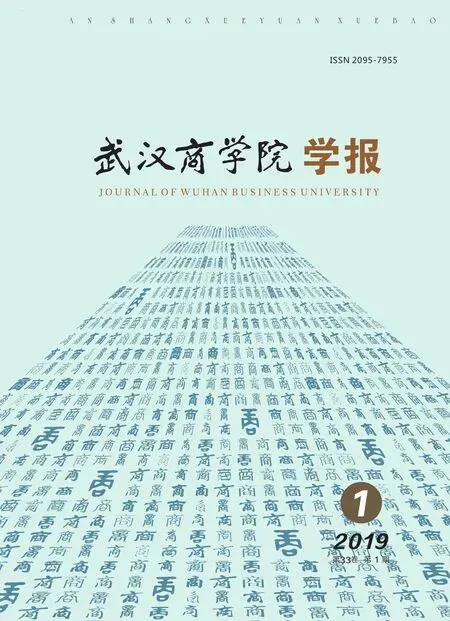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现状与展望※
刘晓慧 刘西国
(济南大学,山东 济南 250002)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期。伴随着政府确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重点,国家对创新活动越来越重视,企业作为研发投入主体的地位也日益凸显,企业是国家创新的主体,因此探求影响其创新水平的因素,对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一)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
战略控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是支持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的三个必须的条件,而高管作为上市公司战略决策和实施的主要内部人,如何激励高管重视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资源的配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Jensen和Meckling早在1976年就针对高管激励问题展开了探索,研究发现,对代理人实施股权等形式的激励,能够使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趋于一致,能够促使代理人关注有利于上市公司实现长期价值的活动。Dong和Gou(2010)关注到了转型经济中公司治理特征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之后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力度与上市公司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投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李春涛和宋敏(2010)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对CEO实施薪酬激励能够显著促进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并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上市公司较为显著,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促进作用。马文聪(2013)、李秉祥(2014)、尹美群(2018)等学者也都通过研究得出了高管激励能够抑制投资不足、提升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结论。
而根据利益趋同效应(The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Effect)与壕沟防守效应(The Entrenchment Effect)来看,高管激励契约往往具有双重效应,这种双重效应使得高管激励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徐宁,2013)。Lazonick(2007)通过对动态的创新过程展开研究,得出结论:不完全契约几乎存在于整个创新过程中,适度的高管激励能够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如果对高管实施过度的激励,会使高管权力过于集中,加之创新项目风险较大,反而会使高管减少在创新活动等利于实现上市公司长期价值项目的投入。徐宁和徐向艺(2012)则从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转化能力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效率三种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对高管实施激励的程度达到临界值之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趋于递减。
(二)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
伴随着现代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代理问题日益显现(Jensen、Meckling,1976)。股权结构作为衡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程度的指标,自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Francis and Smith(1995)关注到了管理层持股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经过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大于30%的上市公司,其研发创新能力要显著高于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小于15%)的上市公司,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高股权集中度降低了由研发活动给上市公司带来的代理成本。Lin et al.(2011)以我国私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经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研发产出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刘伟(2007)、刘运国(2007)、杨德伟(2011)等学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高管持股与否和持股比例是影响上市公司经营效率和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并且高管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文贵(2015)则利用中国工业上市公司数据库,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考虑创新效率,经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非国有股权比例较高能够显著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水平,并且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来自于经理人观,而不是在政治观。陈习定(2018)则认为认为管理层能持股将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捆绑,使管理层有动力基于上市公司长期利益积极投资创新项目。因此,管理层持股利于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提高。
还有部分学者研究股权结构和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陈隆、张宗益等(2005)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技术创新水平之间为“U型”关系,这意味着绝对集中以及较为分散的股权结构都会对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Beyer et al.(2012)将比利时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经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达到一定临界值之前,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而在临界点之后,再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反而对抑制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朱德胜和周晓珮(2018)通过对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10-2013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能够降低代理成本,督促他们更好地为股东服务,选择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创新项目,但过于集中的股权又会抑制创新,应当对高管实施适度股权,给予管理层一定经营管理的自由。
(三)政府补助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完全的市场竞争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但外部性问题的存在使得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效应,因此政府有必要在经济活动中实施干预。政府补助作为上市公司研发资金的重要来源,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关于政府补助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Leyden et a1.(1991)指出,在公共部门中政府在研发方面的补助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研发创新效率,但在私人上市公司中,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政府的研发补助反而会阻碍上市公司对研发的投资。Changet a1.(2006)通过对我国政府研发支出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包括政府创新补助在内的政府各类促进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建设的措施,都对于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的增长和创新效率的提高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也有学者得出与上述结论不同的观点,洪嵩(2015)利用SFA(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展开研究,发现政府的研发支持反而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认为这可能与政府技术偏好、可能会滥用创新补助等原因有关。宋来胜和苏楠(2017)、李平和刘利利(2017)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陈旭东等(2018)认为政府补助保障了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环境,为创新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促进了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提高,激发了上市公司的创新动力。而余菲菲和钱超(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创新效率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他们以我国科技型中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政府补助对科技型中小上市公司不存在挤出效应,而是存在着明显的激励效应。然而,随着政府科技补助强度的不断增大,这种激励效应逐渐降低。
(四)融资约束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
现有关于融资约束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文献观点分为两派,一派学者认为融资约束会阻碍上市公司技术创新项目的进行,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有抑制作用。Savignal(2006)认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意愿较低,融资约束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Silva(2013)的研究同时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创新投入和产出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况学文(2010)通过构建LFC和DFC两个融资约束指数,发现融资约束程度降低了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并通过投资-现金流验证这一的正确性。卢馨(2013)以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限制了研发投资。王书珍等(2016)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具有研发周期长、研发所需资金大等特点,资金不足将导致研发终止或失败,影响上市公司的创新进程。秦娜等(2018)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出发点,利用CFK指数衡量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实证研究发现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高保密性,使得创新项目信息无法传递给投资者,投资者往往要求上市公司支付更高利率才对其进行投资,增加了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不利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项目的推进。周开国等(2017)、周凤秀(2017)、张璇等(2017)学者都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融资约束抑制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观点。
另一派学者则持有相反观点,他们认为融资约束能够帮助上市公司提高创新效率。顾群等(2012)通过Logistic回归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少,能够抑制管理者进行无效投资的动机,特别是在创新项目上,管理者倾向于低风险的创新项目,增加创新项目的成功概率。代理理论认为,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上市公司管理者有动机利用在职消费、过度投资等方式实现“自利”,而当上市公司面临融资约束时,上市公司可利用的资金有限,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管理者会充分考察包括创新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项目,谨慎投资,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刘桂香等,2017)。
(五)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
内部控制作为上市公司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与上市公司资金的利用和风险的控制密切相关,会对投资者的创新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杨清香、廖甜甜,2017),经典的管理学文献认为这一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内部控制悖论”和“内部控制促进论”。“内部控制悖论”假说认为,过于严格与制度化的内部控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僵化问题,而上市公司的研发创新项目作为灵活性较高的项目,必然与死板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相互冲突(Kaplan&Norton,1996)。过于严苛的内部控制制度也会使上市公司员工和管理者感到束缚与压迫,降低员工和管理者的创新热情(Ribstein,2002)。Zhang(2007)则从上市公司高管的角度出发,认为严格的内部控制不仅增加了高管的风险暴露率,还降低了高管的隐形收入,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管理者的创新积极性显著降低。内部控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降低代理成本,然而内部控制很可能因为抑制公司的整体创新活力,从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实现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张娟、黄志忠,2016)。
与上述观点相反的“内部控制促进论”同样由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Dougherty et al.(1996)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成熟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把上市公司的组织资源、经营流程和战略相结合,从而利于上市公司持续创新能力的提升。刘新民(2006)从上市公司内部战略控制和内部财务控制两方面入手,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内部战略控制与上市公司的突变创新正相关,上市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则与上市公司渐变创新正相关。李萍(2015)认为内部控制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实施的控制体系,对降低R&D投资操作层面的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起到重要的抑制作用。杨清香等(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降低财务报表中研发投入项目的信息风险,提升创新活动的价值相关性。张晓红(2017)认为内部控制可以通过风险评估的方法,来有效规避与防范创新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经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内部控制和创新效率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发现内部控制程度高低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成正比。张娟和黄志忠(2016)也得出了类似的支持“内部控制促进论”的观点。事实上,较多的研究考察的是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许瑜和冯均科(2017)证明了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促进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林钟高和张天宇(2018)则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增强了董事会行为对挖掘式创新战略的积极影响。
二、文献述评
经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和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均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方面;关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国家经济政策因素,包括政府支持、政府创新补助等;二是微观层面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融资约束、高管激励、股权结构等。
关于内部控制和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融资约束和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丰富,现有研究多将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并且现有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并不一致。因此,研究内部控制、融资约束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旨在为上市公司提高创新效率、优化上市公司治理提供一定专业借鉴。创新作为决定上市公司生存、支持上市公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基本要素,关系着上市公司的长期竞争优势与持续成长。增强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上市公司自身生产经营水平,提高上市公司运营能力,突出上市公司竞争优势,帮助上市公司抢占市场份额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规模小、行业新、发展速度快、市场竞争激烈等特点,技术创新水平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所处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分析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其内在作用机理,对优化研发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上市公司平稳运行和长期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进而对促进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提升国家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往往伴随着风险,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探索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公司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不同风险承担水平下,公司创新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公司的创新效率分为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研究不同创新模式下公司创新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