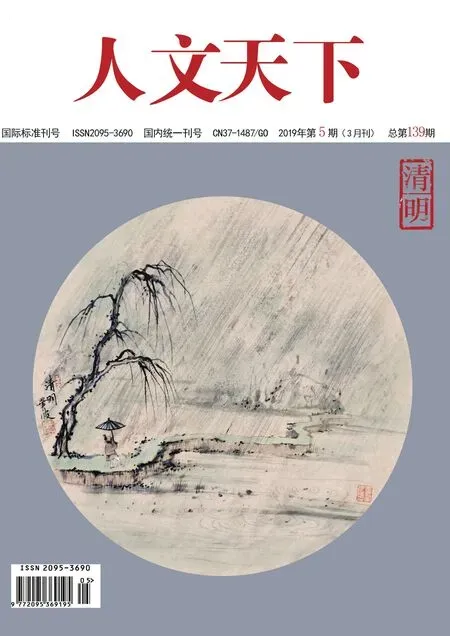袁枚尺牍文略论
车振华
袁枚是清代文坛的多面手,他不仅以诗歌创作和“性灵说”的诗学理论名世,同时他又是杰出的散文家,其尺牍文创作在清代已经为人所重视。袁枚虽退隐于小仓山之随园,但这仅仅是“市隐”,而非与世隔绝,他的社交面依然很广。上至达官贵人,中有亲朋同侪,下到山人晚辈,袁枚无所不交,由于彼此之间需书信来往,因此他所作尺牍的数量自然不在少数。他生前编有《小仓山房尺牍》十卷,存尺牍二百多篇,以散文的形式实践了他的“性灵说”。
一、酬朋答友,款诉心曲
尺牍文学作为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但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注重考据的朴学占据了上风,整个学术界都埋头于故纸堆,做着古籍的考订和辑补。当时文坛以炫耀才学“掉书袋”为创作标准,而以抒发性灵为主要特点的尺牍文学就自然走了下坡路,其独有的文学审美功能开始衰竭。袁枚的弟子洪锡豫为《小仓山房尺牍》作序说:“先生以四六为外集,其严画古文界限之意,业已了然。尺牍每况愈下,豫岂不知?”虽然“严画古文界限”,袁枚仍然以其出色的创作实践,为之作了较为完美的收底。他将横溢的才华倾注其中,使其作品成为中国尺牍文学的最后亮点。
袁枚的尺牍有长有短,长者如《答洪稚存论吴中行》(《小仓山房尺牍》,下文所引篇章,若无特殊注明,皆引自《小仓山房尺牍》),为两篇大论,议论可谓详尽,尽显其思辨能力。短者如《答唐静涵问坐位》,不满百字,文曰:“昨彭大司马坐朱观察之上,朱大不喜。蒙寄书问孰是孰非。鄙意以为皆是也。朱所执者,《孟子》‘乡党莫如齿’一言;彭所执者,《王制》‘一命齿于乡里,二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之义也。彭官一品,是三命矣,于父族尚不齿,而况于乡里乎?”袁枚没有直截了当地评判是非,而是用“两歧语”圆滑地应付了过去,显示了其聪明之处。
数量最多的是朋友间的问候赠答,谈论的也多是家常私事,如感谢对方的款待、酬赠,以及慰问多年未晤的老友等。如《与何献葵明府》:
菊有黄花之际,正相思命驾之时,蒙故人之情,委曲周挚。或极三更清话,童仆鼾呼;或听一部宫商,金灯灿烂。至于小艇将开,而呼驺又到;漏尽霜浓之际,握手依依,使我至今低徊不置也。访春痴兴,恃牛相公之保护樊川,几于微服野行,狎邪不顾,终无所获,命也何如!然新花之采折,与旧雨之周旋,孰轻孰重,静言思之,终不悔雉皋之跋涉也。
在苏耽迟四十余日,佳人信断,残腊将终,依旧抱空而返,未免揄才太刻,穷且坚矣!幸为小女择得一婿,楚楚不凡,差强人意。本求西子,翻得东床,想彼苍亦“与之齿者去其角”之意也。还山后,重兴土木,小有经营,日与都料匠攘臂握算,日昃不遑;故奉赠诗与游冒氏荒园之作,至今未能握管。才人觅句,荡子寻春,其间得与不得之故,想亦有数存耶?
文中只有对好友的体贴问候和自己近况的描述,琐琐碎碎,虽不登古文大雅之堂,却是尺牍之特质所在。
因为尺牍是个人之间的交流工具,具有私人化的性质,所以从作家的尺牍中往往能得到比个人作品更明晰的意见。读袁枚的尺牍,我们可以倾听到他的心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袁枚。如《再与西圃》即是对陶西圃表露自己对于入仕与归隐的想法,他说:“仆已挈家入山,随园构草屋数间,将栖鸡于阶,豢豕于牢,采山钓水,息影蓬庐,从此永赋遂初。虽韩、白按剑于前,苏、张巧说于后,必不出雷池半步矣。昔元微之以州宅夸于乐天,仆则以山房傲于西圃,故人交好,情在于斯。”密友之间,不必隐晦,袁枚的这份退隐表白可谓是推心置腹。
二、“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袁枚生性阔达,生活上喜欢潇洒飘逸,自由自在,而厌恶那些摆起面孔来教训人的道学先生,虽被人讥之为“佻达”却乐此不疲。在才力上,他才高气盛,用笔纯熟,气韵流畅,语言精警达意,让人读之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如《戏招李晴江》:
旧雨不来,杏花将去。仆此时酒价与武库争先,足下来车,亦须与东风争速。不然,则残红满地,石大夫虽来,已在绿珠坠楼之后,徒惹神伤。送行诗呈上,所以多用小注者,恐百世后,少陵与孔巢父交情,费注杜者几许精神,终未了了故耳。
足下去矣,所手植借园花木,交与何人?何不尽付山中,当作托孤之计?赠花如赠妾,不妨留与他人乐少年也;如不见信,可使歌者何戡,与花俱留。他年仆则曰:“璧犹是也,而马齿加长。”兄则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岂非一时之佳话哉?合肥可有诗人否?可将鄙作带往,教令和成,归而镌板,压之行李担中,较羊肉千斤,肥牛百只,轻重何如?
短短两段文字既用了数个典故,又做到恰到好处,不掉书袋,自有一股活泼的灵气。袁枚少年时即有超俗之举,山居多年,更以经史自娱,喜欢调笑戏谑,他曾坦言自己“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他的这一个性在尺牍中也有所表现。
《乞上元令李竹溪释枷犯》就是一篇奇文,这种文字在乾隆时代恐怕只有袁枚才能做得出。文中说自己过北门桥时遇见一位剃头匠因赌博而被带枷示众,其人“嫣然少年,饶有姿媚”。于是他动了恻隐之心,向县令求情道:“……可见天性好赌,自古有之。王侯将相且然矣,况里巷子弟乎?且造物虽巧,生人易,生美人难。谈何容易,于千万人中,布置眉目,略略妥当,而地方官不护惜之,反学牛羊,从而践踏之,忍乎哉?”并引用了唐人诗来为此少年说理:“休将两片木,夹杀一枝花。”
只因人貌美,而为犯法之人求情,已属奇矣,更有意思的是,该少年释放后被允许在袁枚头上一试其技,袁枚又写了一封信给该县令:
荷校者来,仆拥髻而出,急令沐剃,谁知奏刀茫然,发未落而头先伤,竟是以怨报德!方知彼固店家之酒旗,以貌招,以体荐,而非以伎奏者也。磁能引铁,而欲其牵瓦也,不亦难乎?且谛视之,貌亦不佳,自觉前书之无谓。虽然,彼虽伎不佳,貌不佳,而能遇雾里看花之老叟,又能遇肯听下情之好官,则其流年月建,固已佳矣!顺天者昌,于余心终无悔焉。特再布知,同为一笑。
此信是对上一封信的修正呢,还是要把这个幽默进行到底呢?以老叟之年而为自嘲之语,在随园行来,当不难矣。洪锡豫《〈小仓山房尺牍〉序》说袁枚的尺牍“信手任心,谑浪笑傲,无所不可”,让人“读之意趣横生,殊胜苏、黄小品”,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三、金刚怒目,哀民多艰
袁枚《题竹垞〈风怀诗〉后》(《小仓山房诗集》卷九)云:“尼山道大与天侔,两庑人宜绝顶收。争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头。”表明了自己不驯服的浪子情怀和强烈的反叛意识。他把这种思想灌注到他的尺牍中,使其中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复似村》中袁枚针对贾似村讥其“荐贤太滥”的批评,答道:“仆平生最爱武三思一语,道‘我不知世上何者为善人,何者为恶人。但与我善者即善人,与我恶者即恶人’。此种见解,今之大贤君子,往往皆然。即古之程朱,亦未免蹈此病,第不肯如三思之直捷说出耳。”
袁枚的这段话,虽有偏激之嫌,但可说是对传统是非善恶观念的一种颠覆。在他那个时代,袁枚能够毫不掩饰地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加以率直的表露,体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
袁枚由科举而入仕途,虽然只做过几任县令,但在任上却颇有政声。对于做官,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对当代官员的一些昏庸的做法,他在《覆江苏臬使钱玙沙先生》中批评道:“今人不明之是求,而先廉之是求;不知不明而廉,不如其不明而贪也。不明而贪,贪,即其医昏之药也,贫者死,富者生焉。不明而廉,则无药可治,而贫富全死于非法矣。今人不明之是求,而先勤之是求;不知不明而勤,不如其不明而惰也。不明而惰,惰,即其寡过之一端也,其所枉谬者,月不过一二事;不明而勤,则卤莽断割而枉谬者,日且千百事矣!”
袁枚对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反驳,反对官员以“清”字自我标榜,认为“不明而廉”不如“不明而贪”,因为“不明而贪”还有药可医,而“不明而廉”却是无药可医了。这种见解可谓是透辟独到。通常认为“清官害人”的理论最早由刘鹗的《老残游记》提出,其实袁枚在尺牍中已经导夫先路,刘鹗不过是用生动的事例为其作了诠释罢了。
袁枚曾做过几任地方官,深知民生疾苦。《与金匮令》就是他为遭受屈辱的小民所发出的正义呼喊。袁枚作此信的缘起是他从蒋士铨那里听到的一桩冤案:金匮令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不惜对一对相爱偷情的青年男女痛下杀手,“必使玉碎花残而后已”。袁枚认为金匮令的做法“大杀风景”,心里极为不平,于是作信痛斥之。在信中,袁枚将满腔的怒火喷薄而出:“足下不为佳人之仁君,而为恶棍之傀儡,是诚何心哉!须知男女越礼之罪小,棍役刁诈之罪大,足下重其所轻,轻其所重,不特无恻隐之心,兼且无是非之心矣!”
值得注意的是,袁枚不仅仅从个人感情出发,斥责金匮令的做法昏庸、不近人情,他还引经据典,列举了周文王、孔子、孟子等圣贤的例子,并直接引用律文“非亲属不许捉奸”来警告金匮令,说明金匮令此举与法有悖。文章极有说服力,相信那位金匮令看后定当哑口而汗颜。《子不语》卷十六中有一篇《全姑》,说的就是这个案子。在小说中,袁枚为那个昏官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其痛恨之心可见一斑。
四、冲破藩篱,怜香惜玉
对于女性美,袁枚有着与世人不同的审美标准。明清之世,正是礼教对妇女禁锢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女性流行缠足,这一残害健康的变态行为不但没有引起社会的反对,反而被一些无耻的文人奉为“三寸金莲”而津津乐道,成为当时女性美的重要方面。袁枚对此非常反感,《答人求娶妾》就是对这种荒谬审美观的批判与嘲讽。文章一开头,他就批评对方道:“甚矣,足下非真好色者也!凡有真好者,必有独得之见,不肯随声附和,从古诗书所载咏美人多矣,未有称及脚者。”接着袁枚嘲笑道:“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亦可谓小人下达矣。……可望其凌波微步,姗姗来迟否?”
对于女性,袁枚并不是只采取一种士大夫式的玩赏态度,而是用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她们身上体现出的美,对于那些有才气、有气节的女子,他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赞扬。被章学诚骂为无耻的广招女弟子一事,在袁枚那里却引以为自豪。在《与汪顺哉世妹》(《尺牍·辑补》)中,他说:“今岁清和之日,小住西湖。蒙诸女士不弃衰颓,香车问字,钗光峦翠,照耀书楼,如织女诸星,环聚老人星侧。”语气颇为得意。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仍念念不忘众女弟子,在《答秋帆制府》中回忆道:“居恒悒悒,自觉无俚,不得已而列子好游,来往于吴山越水间。竟有宋子、齐姜,终温且惠者,姗姗然湔裙捧贽而来,道韫尹堂,班昭问字,数年来竟得二十余人。”表达了他对才女的欣赏。明白了他的这种感情,就不难理解他在《金纤纤女士墓志铭》(《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二)中对女弟子金逸有才而早亡的深切痛惜了。
袁枚的妇女观在《答杨笠湖》中表现得也很鲜明。文中说杨笠湖(杨潮观)因为袁枚在《子不语》中写他梦到南明名妓李香君而暴跳如雷,作信相责曰:“所称李香君者,乃当时侯朝宗之婊子也。就见活香君,有何荣?有何幸?有何可夸?弟生平非不好色,独不好婊子之色,‘名妓’二字,尤所厌闻。”袁枚对杨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妓女地位虽低,但那些有气节的妓女应该受到人们尊重。他说:“然而香君虽妓,岂可厚非哉?当马、阮势张时,独能守公子之节,却佥人之聘,此种风概,求之士大夫,尚属难得,不得以出身之贱而薄之。”相反,越是那些自诩为清高之人越可耻,“伪名儒,不如真名妓”,他提醒杨笠湖道:“就目前而论,自然笠湖尊,香君贱矣!恐再隔三五十年,天下但知有李香君,不复知有杨笠湖。”这与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载的刻“钱塘苏小是乡亲”(《随园诗话》卷一)之章戏弄尚书的故事很相似,可见这种思想在袁枚的意识深处是根深蒂固的。或许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袁枚提倡男女平等,具有现代意识,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他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
五、文兼散骈,清雅可赏
袁枚的尺牍并非达意而已,而是在语言上细加雕琢,使人读来齿颊生香。他在《答相国》谈到自己所献的食物时说,“味浓则厌,趣淡反佳”,其实他的尺牍与他所献的食物有同样的风格,即清淡而有韵味。《答两江制府尹公》与《再答尹公》就是很好的例子。二作均为袁枚病中写给恩师尹继善的,态度不卑不亢,语句清雅可赏。文曰:
韦把总来,接寄怀诗二章;知夫子得句于风雨横舟之际,金丝引和,寄托深远。适窗前有绿梅一株,水仙数种;对之展读,正与古香冷艳同入襟怀。枚疟虽痊,而四肢无力,终日曳杖而行,未出柴门一步;借此闭门,与“廿一史”中古人相对,领现在可行之乐,补平生未读之书。昔有善用其短者,枚亦善用其病,夫子闻之,必为莞尔。(《答两江制府尹公》)
枚健饭月矣,起居幸如平时;惟形体未充,五十步外不能离杖而行。前蒙夫子遣使问疾,枚欲趋函丈。奈春寒逼人,毛发浙洒,且闭户半年,一作出山之云,则应酬如麻而起。是以旌旗两至白门,而野鹤孤眠,竟无迎送;自叹公门桃李,变作朽木难雕。倘节届清明,此身与草木同茂,定当先诣平泉,领略时雨春风,以捐除宿疾也。(《再答尹公》)
袁枚尺牍的语言之所以优美,是因为经过了精心打造和锤炼,熔铸了古文和骈文的优点,又使人读来而不觉,即如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所说的“披上了骈体的外衣,拽上了古文的尾巴”。“拽上了古文的尾巴”,这不难理解,因为袁枚是一位古文大家,他在创作尺牍时肯定会不自觉地用一些古文笔法。而“披上了骈体的外衣”,指的是在尺牍中加入骈体文的因素。准确地说,这既是袁枚尺牍的缺点,又是其优点。说它是缺点,是因为在尺牍中加入了太多的骈体因素,有“有意为文”的意思,削弱了尺牍自由挥洒的特点;说它是优点,是因为在尺牍中加入骈体因素,就增加了尺牍的文学可读性,使它看起来像是优美的小品文。
有学者认为袁枚尺牍的骈体外衣与当时的文学风气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是很有见地的。袁枚所处的清中叶,正是骈体文“中兴”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骈文大家,如胡天游、汪中、洪亮吉等。究其原因,清中叶尽除晚明习气,复古思潮炽烈,而骈体也是古文体之一种,于是就借此风气实现了大翻身。另外,当时文网甚密,造成了文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和行动上的畏缩,他们不敢率性而言,只能在形式上另辟出路,追求文章的形式美。袁枚是当时文坛极为活跃的人物,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其实从袁枚对待骈文的态度来看,袁枚让尺牍披上骈体的外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虽然也轻视骈文,以自己的骈文作品为“外集”,但与那些正统的文人相比,他的态度还算平和。他说:“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骈,文之道也。”(《书茅氏〈八家文选〉》)在《胡稚威骈体文序》(《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中,他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说:“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论者先散行后骈体,似亦尊干卑坤之义。”可见,袁枚并不反对骈体,他只是反对在古文中用骈体,认为这种用法有损于古文的纯粹,而在半私人化的尺牍中则没有那样的限制。尺牍不用担负载道的重任,适当的掺入一些骈文的因素,不但不会影响尺牍的表情达意,反而会增强它的美感。李英《〈小仓山房外集〉序》中评价袁枚的尺牍“古藻缤纷,大气旋转,足冠一朝”,可谓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