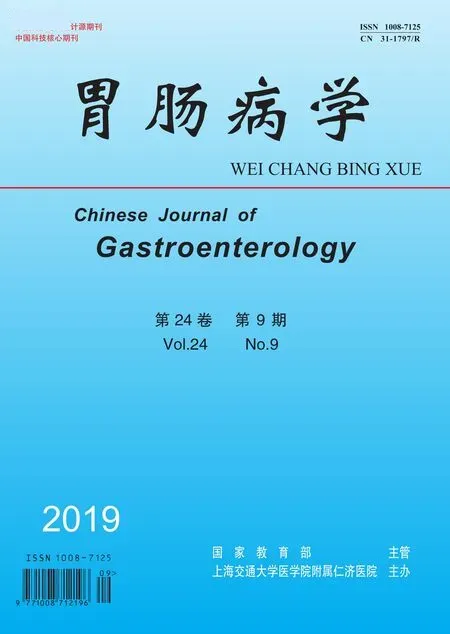Toll样受体与炎症性肠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燕 彤 张 军
南京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210000)
Toll样受体(TLR)是一类在天然免疫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蛋白质,能够识别病原体分子,如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s)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刺激下游信号转导分子,诱导效应细胞炎性介质表达,从而影响免疫应答,并在先天性免疫与后天性免疫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炎症性肠病(IBD)属于胃肠道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可分为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两大类。研究表明TLR可通过调节黏膜稳态、肠道菌群以及黏膜免疫等方面参与IBD的发生。本文就TLR与IBD相关性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一、TLR相关的信号通路
TLR信号转导通路可导致核因子-κB(NF-κB)激活,引起诸多促炎细胞因子的基因转录,如白细胞介素(IL)-1、IL-6、IL-12、肿瘤坏死因子(TNF)、趋化因子、急性期蛋白等,进而诱发一系列炎性反应。除TLR3通过TIR结构域接头分子(TRIF)途径发出信号外,其余TLR的信号均依赖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信号通路。TLR4可同时通过这两种信号通路发挥作用。
1. TRIF信号通路:TRIF属于TLR3的Toll/IL-1受体(TIR)结构域募集的一种接头蛋白。TRIF与TLR3结合后,TRIF可与不同信号通路下游的蛋白分子结合,激活转录因子和转录激酶,如NF-κB、干扰素调节因子-3(IRF-3),进而调控一系列免疫反应。
2. MyD88信号通路:当TLR与PAMPs结合后,受体与MyD88羧基末端相互作用,MyD88利用其死亡区募集下游同样含死亡作用域的IL-1受体相关激酶(IRAK)家族,导致IRAK自身磷酸化。磷酸化的IRAK脱离MyD88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6(TRAF6)结合,TRAF6活化引起两条不同途径的信号转导,即NF-κB和c-Jun氨基末端激酶-应激活化蛋白激酶(JNK-SAPK)。在IBD中发挥作用的转导途径以前者为主,NF-κB磷酸化导致一系列特定基因表达,从而产生原发性致炎因子如 TNF-α、IL-1、IL-6、IL-8、IL-10等,完成炎症信号转导过程[1]。
二、不同种类TLR在IBD中的作用机制
1. TLR对肠道黏膜稳态的调节:TLR在肠上皮中的表达具有空间、特定细胞类型以及时间上的差异[2]。肠上皮由一层极化细胞构成,将肠腔与固有层分离,可与肠腔内菌群相互作用并对其产生影响。肠上皮可通过模式识别受体,如TLR直接识别微生物成分,因而肠上皮TLR信号的激活在感应和响应致病性微生物以及维持黏膜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CD患者肠道黏膜受损时,血小板被激活,血小板上的TLR4暴露增加,其可与脂多糖(LPS)结合,进一步引起粒细胞激活和防御素产生。粒细胞激活可促进血小板激动剂分泌,诱导血小板活化并从循环中补充,此种正向循环可增强宿主防御能力[3]。在IBD中,结肠中脂质过氧化产物4-羟基壬烯醛浓度升高,其作用于全身可抑制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破坏肠道屏障功能,促进LPS和细菌产物从肠道进入体内循环,从而促使TLR4信号激活,诱发肠道炎症反应,加重IBD[4]。由此可见,TLR4可通过调节肠道黏膜稳态在IBD中发挥作用,具有双面效应。
2. TLR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TLR与肠道菌群的接触会引起肠道黏膜的局部免疫反应,且此种反应会因肠道微生物逃逸而传播至别处,进而引起器官甚至全身的炎症反应。此外,肠上皮TLR表达增加会干扰肠道微生物的构成,进而引起菌群紊乱,促使IBD的炎症加重。有研究[5]发现,TLR3可通过与病毒RNA或内源性mRNA结合,参与脂质运载蛋白(LCN2)的调控,进而影响肠道菌群稳态,使机体患IBD的概率增加。
TLR5在新生小鼠肠道上皮细胞中存在年龄依赖性表达,有研究[6]发现,TLR5表达对小鼠肠道菌群组成有显著影响,且TLR5多态性增强会破坏宿主-微生物的稳态,增加CD的患病风险。而某些TLR可通过特殊机制抑制肠道细菌移位。研究[7]显示,Paneth细胞特异性基因MyD88的表达可促进抗菌肽Reg3g产生,防止小鼠肠道菌群移位。
3. TLR对肠道黏膜免疫的调节:人体中肠道巨噬细胞可通过调节其表面TLR吞噬细菌、分泌细胞因子,从而维持肠道免疫功能。但此种调节机制出现紊乱,可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包括IBD。在TLR配体刺激较强的状态下,肠内巨噬细胞可下调TLR关键分子MyD88和TRAF6,以及上调负调节因子如IRAK-M、锌指蛋白A20来抑制免疫反应[8]。由此可推断巨噬细胞对TLR的适度调节可维持肠道黏膜免疫平衡以及抑制炎症。全基因组相关研究[9]表明,TLR1和蛋白激酶活化的α1催化亚基基因的遗传多态性与胃肠道慢性炎症、胃癌、幽门螺杆菌感染易感性增加有关。慢性幽门螺杆菌感染可通过作用于TLR1相关信号通路诱导系统免疫耐受和抑制炎症反应,从而预防IBD的发生[10]。由此推测,TLR-1对IBD可能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TLR6与TLR2形成异二聚体,参与Th17细胞发育,介导炎症反应。有研究[11]证实TLR6可刺激小鼠内脏相关淋巴组织细胞在体外诱导Th1/Th17应答,抑制由后者介导的肠道炎症。TLR7 是一种核苷酸敏感的TLR,可与病毒的单链RNA结合。研究[12]表明,TLR7与TLR8可联合作用,激活效应T细胞,清除肠道有害物质,从而抑制炎症进展。TLR9以同源二聚体的形式存在于胞内内质网中,主要识别细菌和病毒。TLR9被未甲基化的CpG DNA 激活后,可触发先天性免疫应答。研究[13]表明,TLR9-IL23-IL17轴在IBD的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TLR9通路激活可促进IL-23释放,从而进一步激活Th17通路,Th17细胞通过产生促炎介质IL-17介导炎症的发生。上述TLR均可诱发黏膜免疫反应,通过一系列免疫细胞和淋巴组织调节肠道功能,进而在IBD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作用。
4. TLR对肠道炎症反应的调节:Yokoyama等[14]的研究发现,TLR2可识别肠道内致病菌DNA,并在活化后表达升高,激活炎性因子,参与炎症反应的发生。该研究发现UC患者回肠末端炎症部位TLR2表达增加,患者出现肠道息肉的概率显著提高,可能是由TLR2激活抗炎因子引起肠道黏膜修复所致。TLR4亦有类似效应。TLR4是第一个被发现的TLR,其与CD14、LPS结合蛋白(LBP)、髓样分化蛋白22(MD22)联合作为模式识别受体发挥作用,可通过抗炎、促炎两种机制对IBD的进展产生影响。
①抗炎机制:通过对IBD伴肠息肉的小鼠肠道黏膜上皮TLR mRNA检测发现,TLR2和TLR4 mRNA主要定位于Ⅰ期病变的结直肠上皮和Ⅲ期病变的炎性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在Ⅱ期病变中两者均定位于上皮和肉芽组织。在炎性结肠黏膜中,TLR2和TLR4表达增加,通过激活IL-10抗炎因子和炎症局部细胞增生,发挥抗炎作用,修复肠道黏膜[15]。
激活TLR4通路可促进糖皮质激素合成,从而减轻消化道由于应激反应所致的损伤。TLR4基因缺失的小鼠体内糖皮质激素水平降低,胃肠道炎症加重,提示TLR4信号通路有抑制肠道炎症的作用[16]。
②促炎机制:环氧合酶-2(COX-2)是引起炎性反应的关键酶,可促进炎症反应,导致损伤。研究[17]指出,激活TLR4信号通路可促进COX-2表达,导致慢性肠道黏膜炎症,尤其在UC患者中多见。
三、治疗IBD的药物设想
1. TLR拮抗剂:间苯二酚是一种天然的TLR2/1抑制剂,可抑制TLR诱导的炎症反应。研究[18]表明间苯二酚可通过抑制TLR4激活的NF-κB通路,从而调节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的释放,使机体免受UC导致的肠道损伤。
研究[19]表明氯喹可通过TLR1/2和TLR9信号干扰先天性免疫应答,进而减轻结肠炎小鼠肠道症状。有学者通过测定抑郁症患者前额叶皮质中TLR表达,发现TLR2、TLR3 mRNA表达明显高于正常人,提示TLR抑制剂可能可缓解IBD患者的精神症状,提高生活质量[20]。
研究[21]显示,黏附侵袭性大肠埃希菌可通过抑制let-7b使肠黏膜细胞调控TLR4表达的功能受损,导致TLR4过度表达,激活NF-κB通路,释放大量炎性因子,加重结肠炎。提示let-7b可能是CD潜在的治疗靶点,尤其是伴黏膜侵袭性大肠埃希菌感染的CD。
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在细菌感染中有较强的关联。研究[22]表明肠道感觉神经元通过TLR4受体识别病原微生物,进而激活TLR4信号通路,使痛觉受体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受体1(TRPV1)表达上调,引起细菌侵袭和IBD内脏疼痛。TLR4拮抗剂在治疗IBD神经性疼痛中的应用亦被证实,其中吗啡衍生物是最强有力的TLR4拮抗剂,可增强吗啡镇痛的作用,但机制有待明确[23]。
单糖衍生品、蔬菜和水果中富含的酚类化合物阿魏酸[24]、白芍七物[25]、阿托伐他汀[26]等亦可通过抑制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发挥抑制肠道炎症的作用。
间充质干细胞(MSCs)移植在治疗IBD患者恶性血液病的同时可治疗IBD肠道症状,其可促进细胞增殖、加速损伤肠上皮的修复过程。有研究[27]表示MSCs治疗通过抑制LPS/TLR4信号通路,从而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改善IBD肠道症状并减少肠外并发症。
研究[28]显示,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服用香菇多糖后可抑制LPS刺激的TLR4过表达,从而减少下游信号关键蛋白的表达,抑制肠道炎症反应。此外,有研究[29]表明大黄素可通过调节鞭毛素-TLR5信号通路改善UC的症状。目前,针对TLR9-IL23-IL17轴的药物靶向性已在IBD中开展研究,针对p40的单克隆抗体作为IL-23的抑制剂已用于CD的治疗,抗IL-17A单克隆抗体AIN457在CD的治疗中具有有效性和安全性[30]。
2. TLR激动剂:研究[31]显示,脆弱拟杆菌多糖A(PSA)通过TLR2信号在动物结肠炎模型中诱导调节性T细胞产生抗炎因子IL-10,从而抑制胃肠道炎症。有研究表明,分布于外界接触皮肤黏膜的树突细胞可通过TLR2途径激活,从而释放调节细胞因子,如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同时移行至淋巴组织,与淋巴细胞相互作用,从而调控免疫反应。Maier等[32]的研究发现,肠道益生菌普拉梭菌可诱导树突细胞激活TLR2途径,产生高水平IL-10,并调节T细胞应答,提示其可缓解IBD患者的肠道炎症程度。
丁酸梭菌可显著提高Cajal间质细胞中TLR2、IL-6、IL-8的表达,从而通过TLR2调节后两者的表达,促进间质细胞增殖,改善肠道动力,抑制炎症反应。TLR2沉默会降低该菌诱导的IL-6、IL-8表达[33]。喹唑啉衍生物作为TLR7/8激动剂可触发MyD88依赖的信号通路,活化自然杀伤细胞并引起效应T细胞增殖,从而杀伤肠道有害物质[12]。Musch等[34]的研究显示,基于DNA的寡核苷酸cobitolimod(DIMS 0150)是一种TLR9激动剂,可通过激活淋巴细胞、树突细胞以及巨噬细胞的TLR9通路,恢复糖皮质激素的敏感性,可作为治疗严重、慢性活动性、难治性UC的化合物。
四、结语
目前对于TLR与IBD的关系尚未完全明确。人体多系统以及各免疫通路间存在关联,可从其他角度入手,找到IBD与相关系统疾病的联系,从而探索新的治疗思路。在实验日益精确化、科技逐渐进步的今天,多靶点复合生物制剂或小分子药物应用于临床IBD的治疗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