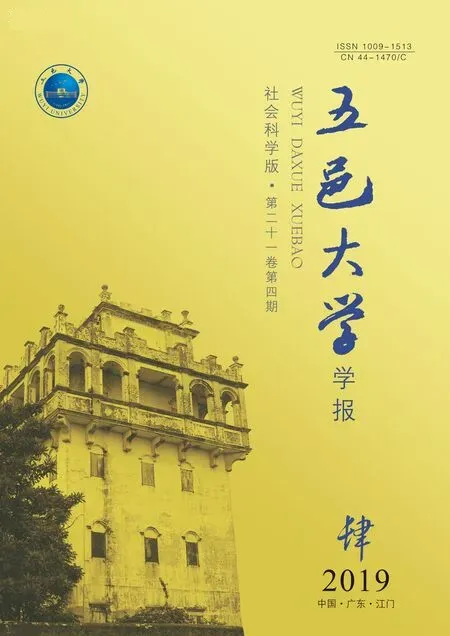从梁启超“四力”说之“提”力看其接受美学①
赵 楠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梁启超在岭南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文艺理论更是独树一帜,其中关于“趣味”“移情”“四力”说,以及小说的群体影响作用等等之论说,都极有研究价值。其中,“四力”说提出“熏、浸、刺、提”四个概念,被认为是其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结合读者心理探讨四力之关系、梁启超的接受美学理论,却至今少有人涉及。本文认为,在四力中,“提”可以集中体现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其针对他所一直关注的阅读群体,包涵着他一系列的接受美学观,因而是四力中最为核心的观念。由于“提”力的提出本身就是针对小说而言的,本文也主要结合小说这种文体进行阐述。
一、激发读者进入接受至高境界之“提”力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 884一文中提到了“四力”,即“熏、浸、刺、提” 。其中,“熏”“浸”是渐进产生影响的方式。“熏”使人“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扬,而神经为之营注”,而“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言其营造的是一种空间氛围;而“浸”,“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则说的是在时间上令读者不知不觉进入作品,沉浸其中。“熏、浸”共同构建多维时空的作品接受环境,采取和读者定向期待(为读者原来所具有的较为稳固的的综合阅读素养,它“按其已有的思想、文化、知识、修养、能力、经验、习惯等形成的阅读模式,来认识、理解、阐释作品所提供的信息或暗示的一种内在欲望;在功能上,则起着选择、求同和定向的作用”[2]206)对接的方式,令读者在心理对抗较小的情形下构建创新的期待视野,向“提”的境界慢慢靠近。
“刺”是进入“提”之境界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骤觉”,极言时间之短暂,并且读者有明显的感受。“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这是瞬间读者由自我的阅读经验,和作品经“熏、浸”濡染的氛围产生重叠,而生发的共振、共鸣心理,是一刹那的感受、猛然间的质变。读者把对作品的直观感受与自己的个性、经历、趣味等整合在一起,进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审美感受之中。“刺”对主客方的契合度有较高要求,很显然,是读者的定向期待得到了极大满足的缘故;同时,“刺”也是读者阅读接受中刺激强度最大的一种方式,说明读者也感受到了新力量的震撼,创新期待——即求异的需求(搜索原有视野之外的新事物之意识,可帮助读者跳出原有的思维桎梏,并获得新的审美快感)同样得到了极大满足。
应该说,由于“熏”“浸”的作用,而产生了“刺”,“刺”已经能让读者对作品为之动容、心有戚戚,但在四力中,“提”才反映了读者接受程度的至高点。“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和之前的被动接受不同,此时,读者的主观能动性被大大调动、激发,充分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文本融为一体,进入到文本的再创作当中,阅读不再是简单、纯粹的吸收活动,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解读,读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与书中主人公“俱化”,主体与阅读对象之间的界限已经无限消弭,两者进入了物我两忘的极致自由状态,阅读主体的自我价值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实现,而阅读视野也进入了全新的状态:
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1]885
所言正是“提”力产生的这种状态,此乃审美接受心理中的最高境界。这是因为,审美活动本身就反映了人对自我狭隘世界的一种对抗和超越,是沟通外界、感悟其他生命的一种方式。从最初的审美感知,到将在场与不在场的事物串联起来,经过联想、改造并获得审美想象,最后达到最高层次的审美感悟与体验——“提”力所致之境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精神得到激发,心灵世界得到开拓,可以“忘怀一己的利害得失,恣情享受生命自由舒展的乐趣,并在一定程度上更新生命的状态,激发生命的活力”[3]53。梁启超是一个始终关注国家民生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美学思想受到了康德和伯格森的影响。梁启超将伯格森称为“新派哲学巨子”,其关于生命与艺术、美的思考,多有伯格森生命哲学的印记,注重生命的价值、体验、自由。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的接受心理作出说明时指出:
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1]884
正道出了读者审美心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对自由的向往。“审美给予人以充分的选择自由,使人性的残缺,变成了人性的完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美对人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戏耍,而是人独有的一种生存形式”[4]。这是梁启超总结的小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它满足的是读者接受心理中突破现有生存状态的要求,符合阅读中的创新期待。另外,梁启超还认为:“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1]884,指出了小说接受心理中的另一种情况——对读者偏于定向期待的满足,这两种情况,梁启超也认为是“理想派”和“写实派”之差别。两种心理的满足,使得小说产生了良好的接受效果和社会影响。当然,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小说还具有趣味性、简易性、开放性,几点兼具使其接受效果更胜一筹,此点将在下文再作阐述。
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1]884。可见“小说”的接受效果多种多样,而“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最受欢迎,这些心理影响较大的效果就类似于“刺”“提”之力了。而从以上梁启超对小说阅读心理的描摹,“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无论是前者以自身来感受外在世界,还是后者所言文本中的情景托喻了自己的内心,很显然能够“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无疑是读者充分感受作品情境后产生的的阅读效果,主客体双方得以融合,文本影响深入而持久,所谓“无量”是也,这和短暂的“刺”有所不同。此种阅读效果,也就是“提”力产生的作用了。因此,从客观效果来看,“提”也是四力中影响最大的一种。
应该说明的是,四力在读者阅读接受的过程中,“熏”“浸”是前提,“刺”“提”的发生则并无必然的先后性,且有可能同时产生——因为阅读心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但是,它们对读者产生影响的作用和层次是从低到高排列的。
二、关注读者接受心理是“提”力产生作用之重要条件
如何能使读者进入“熏”“浸”的状态,再完成从“熏”“浸”到“刺”“提”的实现?使“提”力产生最佳的效果,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必须关注读者的接受心理。接受美学认为,作品最终意义的完成不能仅靠文本本身,而读者的参与程度亦十分重要,“阅读并非对作品简单复制和还原,在这一活动中并非作品单方面作用于读者,接受者与作品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单一的认识与被认识的因果关系。理解本身便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行为,包含着创造的因素”[5],“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6]。读者进入作品后,凭借既有经验以及想象力将作品文本还原为意象世界, 并调动感知、思维、感情,完成文本接受与补白的双向交流, 作品才具有了完整的意义。而读者通过创造性地参与建造从未体验过的意象或情景,获取新的审美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心理被调动的程度、参与的积极性如何,会直接影响到最终审美效果的获得,因此读者接受心理之特点不可小视。“提”的过程正是读者阅读兴趣被极大调动的过程,要激发读者这种心理,的确需要研究其阅读接受中的种种特点。
梁启超对于读者的接受心理,是十分关注的,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提过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1]884在多篇文章中,亦论述过作品与读者接受心理的问题。将其整理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品应该具备趣味性。上述一问,梁启超就自己回答:“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1]884。在此,“乐而多趣”实际上和梁启超后来提出的“趣味”说相通。“趣味”是梁启超整个人生哲学的重要理念,被认为是生命的根本价值和动力所在:“活动要有原动力——像机器里头的蒸汽。人类活动的蒸汽在哪里呢?全在各人自己心理作用——对于自己所活动的对境感觉趣味”[1]4010,“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1]4013,没有活力、激情、乐趣的人生如同“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1]4017,是极其可怕的。对于乐趣每个人都心向往之,这是因为在乐趣中人们更能体会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力量的释放。基于读者的这种心理,作品想要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加强趣味性,积极引导读者进行阅读:“文学是要常常变化更新的,因为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1]4927,“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戏谑。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1]172。在具有趣味的阅读中, 读者的心理自由度往往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针对作品的补白与互动积极性和创造力也较强,作品带来的体验可以弥补真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心理需求,“提”力的发生机率就会大大提高。人们对娱乐性、情节性强的作品更为喜闻乐见,小说恰恰具有很明显的这种特征,因此人之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1]885,小说也就成为梁启超在文学革新运动中极力提倡的一种文体了。
应该说,小说所产生的美感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其以艺术之美吸引读者,唤起读者的心灵愉悦,梁启超对其是加以肯定的,也正如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所言:“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7]64,以及休谟之言:“美是一些部分的那样一个秩序和结构,它们由于我们天性的原始组织,或是由于习惯,或是由于爱好,适于使灵魂发生快乐和满意”[8]330。虽然“趣味”的字面含义似乎带有世俗、感性的味道,但是,梁启超所言“趣味”决不包含着“下等趣味”,所谓“下等趣味”梁氏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解释为三种情况:一、要瞒人的;二、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三、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的,[1]3946作品中如果包含着“下等趣味”,便可能将读者引入歧途,无法产生美感,更遑论产生“提”力的作用了。同时,“趣味”的表现又具有多样性,有喜有悲有苦,不仅仅单指快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提到最受读者欢迎的是那些令人“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的作品,也说明“趣味”不能仅仅理解为作品的娱乐性,它还具有触及到读者审美心理的深层次多样性特征,美感“可能是痛而后快或又痛又快的复杂情绪,可能是包含人心深处的悲喜哀乐等多种情感因素的综合情感”[9]50,应该说梁启超对作品的接受效果之分析“已隐含了悲剧美的审美理念,他在价值取向上更偏重于痛而后快的崇高感”[10]164。可见,梁启超所言“提”的发生是有条件和方向的,是和趣味高尚、内涵丰富的目标相结合的。
“趣味”既是激发读者阅读兴味的具体方式方法,又是实现的目标,也就是说,“提”的整个过程是以“趣味”为本质思维特征的。前者是基于对趣味的一般的、浅表层次的理解,梁启超已经论及,它可产生“熏” “浸”“刺”“提”种种阅读效果;后者属于深层次对艺术本质的触及,梁氏虽已有所探讨,但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还未明确指出,“趣味”说他在后期的审美理论与人生、美的功能、价值相结合,才趋于完善,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实际上,此文已经谈及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于体会“趣味”的终极愉悦,唯有“提”力可以达到。
这是因为,在达到终极“趣味”的过程中,“提”力与“熏”“浸”“刺”三者不同,它激发了读者自我创造的力量,在文本中打上了自我生命的烙印,使得读者充分地感受到创造的自由和乐趣。结合读者自我经验,使得再造情境更为生动和逼真,无疑令文本的接受心理产生了前三者所没有的效果,“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1]885。梁启超这里提到的“移人”,便是“提”力所能达到的最终阅读效果,也即我们所说的物我两忘的境界。一般的实践活动,主体总是力求客体服务于自己,主客体之间往往有着占有与反抗的激烈冲突,而审美活动的主体却可以常常对象化,沉浸于客体之中,与其共命运、同呼吸,达到往复交流、“感而遂通”(《易·系辞上》)的境地,感受到极度的精神舒展、会心与畅神。而此时的读者不但有着感性愉悦,并且在审美理性方面也得到了升华,通过感同身受,发现宇宙生命本根上都是息息相通的,由此领悟、体证生命的真实意义,个人与群体生命融汇聚集,主客、客体被超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被超越了,“审美领悟正是要以其悟性的洞彻来把原先审美体验中所形成的物我同一的心理感受超升到天人合一、群己互渗的精神境界上去,这既是生命的自我超越,而亦是向着生命本源的返归”[3]51。由此唤醒、振奋、充实、提升自己的生命力,应该说是读者审美接受的终极意义所在了。“趣味”的此种力量具有驱动源之意义,心理上的乐趣与感悟,使人们从不厌倦,是一种内在且持久的的力量。由于“提”力的这种作用,梁启超认为文学正可以“专从事诱发以刺激各人器官不使钝”[1]4018,是与美术、音乐并列,使人从现实的功利主义中跳脱出来,保持精神追求的三种利器之一。
除了趣味性,如果想要更大范围的读者进入阅读,则必须关注文本的第二个特点:简易性。假如文本的语言平易,读者阅读的障碍较小,就可以很好地令读者消除畏难情绪,快速进入文本设置的情境,“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1]885,“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1]39。“而小说者,恒浅易而为尽人所能解。虽富于学力者,亦常贪其不费脑力也而借以消遣,故其霏袭之数,既有以加于他书矣”[1]2747,正指出了小说广受喜爱的原因。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交流顺畅无碍,就更容易进入“熏”“浸”的状态,所以,“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1]172,这又涉及了对读者阅读心理产生作用的第三个前提,即开放性。此点和简易性相关,小说因其平易,故传播效果佳,读者面广,无论上下,均可阅读,产生的影响力也超乎寻常:“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1]172。这种开放性同时还表现为面对每一个读者,文本所展现出来的姿态,即接纳、包容、迎合,这在小说表现最为明显,不是板起面孔进行教育,而是以“趣味”吸引,如此“作者只要把那现象写得真切,自然会使读者心理起反应”[1]3982,更容易贴合众多读者的的阅读期待心理而产生效果。
三、“提”力的发生以“崇高”为指向,注重社会功用
文本内蕴含着各种产生阅读效果的可能,而其必须和读者心理契合,才能发挥力量,所以,梁启超极为注重读者的接受心理。然而,这种注重并非没有原则,曲意逢迎,而有着鲜明的指向,这即是崇高美。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论及“提”时,梁启超列举了多部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花月痕》,诸多人物形象,如华盛顿、拿破仑、释迦、孔子,这些作品或人物,凸显的主要美学特征为抗争、冲突、理想、激情、豪迈、刚健等等,有一些还展现出悲剧美,令读者“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这和美学中所说的“崇高”之范畴基本吻合。梁启超虽然在其论著中从未明确提出“崇高”这一论题,但实际上他在作家研究、小说丛话、诗话等多处理论研究的文章中,都表现出对这种美学理想的向往。《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梁启超认为韵文表情方法中的“奔迸法”为“情感文中之圣”[1]3924,所谓“奔迸法”,展现的就是奔放刚健崇高之审美特征,梁启超对其显然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梁启超谈到秦汉时“有两首千古不磨的杰歌:其一荆轲的《易水歌》;其二,项羽的《垓下歌》”[1]4345,钦慕的正是诗歌中悲壮、慷慨等崇高的风格特点,其他如《情圣杜甫》、《屈原研究》等也提到崇高与悲剧等相关问题,高度肯定了其美学价值。对这种风格的提倡,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崇高相较于优美、滑稽等对读者的冲击显然更强烈,“是当情感突变时,捉住他‘心奥’的那一点,用强度写到最高度”,“令我们读起来,不知不觉也跟着到他那新生命的领域去了”[1]3925。由此,从接受效果来说,产生崇高审美的作品显然影响更深入和持久。
梁启超的这些观点,都和他对民族文化、国家历史和现状的思考紧密相联。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认为,文化启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要针对国民心理,改造、重建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识,“研究政治,最紧要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1]3695,要改变国人精神萎靡、感情枯竭,缺乏创造力、意志力等顽疾,应使艺术深入读者心理,启发其人性光芒,用审美的超功利性来“新民”,这正是“三界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因此,“崇高”一类的艺术尤为梁启超所提倡。而在各类艺术种类中,梁启超尤其肯定小说的社会功用, 对其给予十分的期望。他认为,小说的力量非常强大,和“群治”关系相当密切: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172。
“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而“四力”既有益于社会的一面, 又有“毒万千载”的可能:“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 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用之于恶, 则可以毒万千载”[1]885,所以,作品的导向性非常重要,小说如果过于低俗就会类似流毒,产生严重的后果,这是“群治”过程中不得不注意的一点。
通过这种倾向性,梁启超对阅读接受过程中所注重的一点,即作品之社会功用,也就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但是,这个过程不能以简单的口号宣传或者说教实现,而是通过趣味,使读者从心里自发地领悟文本之美,使小说通过其内在的力量作用于人的心灵,因而间接地产生教化作用,这即是艺术的情感性和愉悦性,“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1]3921,“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1]230,这种效果既不是文本的自我呈现, 也不是由读者建构而来的,而是两者以读者的心灵为中介,以“趣味”为动力引发而来的。可见,小说各种力量,尤其是“提”力生发作用都建立在读者心理特点的客观基础上, 是符合接受美学原理的, 其社会功用不是外力强制产生的结果。
如此, 梁启超以“提”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一、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相结合。其功利性在于强调小说与艺术的社会价值、教化作用,但同时,这种功利性超越了一己私利,注重以尊重读者的内在性情、心理特点、主体精神为前提,又带有反功利的色彩;二、强调接受群体的整体性,审美的愉悦,不应该只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而应该覆盖于广大人群,融入他们的人生,渗透在他们的生活、活动、思维各个方面,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求真向善,得到根本改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1]4070;三、以“趣味”为核心,以“崇高”为指向。梁启超承认小说的审美,由读者参与文本建构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提”的这一阅读效果,非有读者充足的自发力量不能完成,因而他注重读者审美的心理机制,提倡“趣味”;同时又认为作品对读者的指引作用也同样重要,这样就看重“崇高”。本质上,梁启超建构的读者接受的至高境界就是自由畅神与自我改造融合、激扬生命与理性领悟融合,激发个人活力、去除精神蔽障,进而达到国民素质提升和社会蜕变之效果。这些观点,可谓是梁启超作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化巨匠和思想家所提出来的先见,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