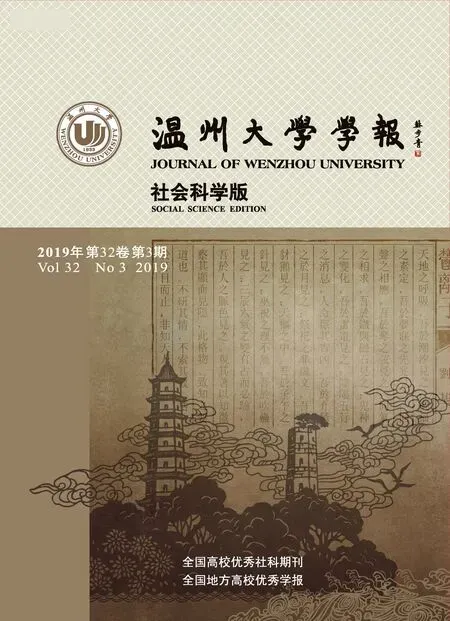从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看美国教育公平问题
谢天长
(福建工程学院法学院,福建福州 350118)
美国加州参议院提出的加州宪法修正案(五)即SCA5,SCA是Senat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的缩写。当地华人为了抗议这一修正案,通过使用脸书、微信等即时通讯手段宣传、在大众媒体撰文和发声、约见选区参议员、华裔组团到州议会和华盛顿抗议等多种方式表达意见,迫使提出修正案的拉丁裔参议员埃德·赫尔南德斯(Edward Paul Hernández)收回提议,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从中可注意到,美国社会存在比较深刻和难以调和的教育公平问题,并在不同州中产生了多个法案和诉争,特别是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案在2016年的最新判决,反映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平权问题所展现的模糊和踌躇。
一、美国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的提出及其核心问题
(一)美国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的提出
美国加州宪法修正案(五)具体表述为:“加州宪法禁止本州因种族、性别、肤色、族群、出生地,在政府机关、公立教育、公共服务合同签订方面歧视任何个人或团体或给予其特殊照顾。这个法案将会保证上述禁令不能阻止州立高等院校使用被美国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Ⅱ允许的学生选拔程序。”美国加州宪法修正案(五)就是想通过删除1996年加州议会通过的209提案中涉及的有关“公立教育”的文字,从而为加州公立大学系统在选拔新生时考虑种族、性别、族群等因素打开缺口,为加州公立大学乃至在加州的私立大学额定少数族裔招生比例提供制度根据。参议员埃德·赫尔南德斯提出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的理由是,需要公立大学录取学生时考虑种族背景来增加少数族裔的入学人数,实际是明确少数族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从而保障少数族裔享有平均受教育的权利。这似乎是一项能够照顾少数族裔学生利益且具有公正性的招生政策,充分考虑了少数族裔学生在教育资源获得方面的弱势地位,并给予相应的优待来满足其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愿望。
事实是,加州地区的华裔学生较多,且普遍成绩较为优秀,被录取进入加州大学系统就读的亚裔学生因此大幅上升。相对应的情形是,许多西裔和非裔学生因各种原因,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在缺乏刚性录取政策保护的情况下,进入加州大学系统读书的学生就大幅度减少。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截至2013年加州的人口总数为38 332 521人,其中,非西班牙裔或者拉丁裔的白人占39.4%,拉丁裔占38.2%,亚裔占13.9%,非洲裔占6.6%。虽然亚裔占加州人口总数不到14%,但他们在加州大学系统里却占了接近40%。资料显示,在加州大学系统中,录取的大学一年级亚裔新生比例从1995年的35.2%上升到了2005年的40.1%。在相同的时间段,非洲裔大一新生比例从1995年的4.2%下降到了2005年的2.9%,西班牙裔新生比例在加州大学系统里面从1995年的15.1%下降到了2005年的12.7%,白人新生的比例在加州大学系统里持平。200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9 348名大一新生,其中非洲裔新生有324人,占录取人数的3.5%,拉丁裔有1 660人,占录取总数的17.8%,亚裔有4 220人,占录取总数的45.1%。①参见:蒋琦琪.美国“平权法案”实施后教育公平理念的变化与启示:以“密西根大学案”和加州“SCA5提案”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2014。
在支持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的人们看来,是取消种族因素的录取政策,或者说缺乏对特定族裔的录取保护导致了特定人群进入加州大学系统念书的机会减少。加州宪法修正案(五)所表明的大学录取方向,是要根据人口比例而不是成绩来分配加州公立大学的教育资源,即每招100名学生,都须按照族群分配入学指标,学生在各自的族群内竞争入学名额。华裔乃至广大亚裔也是少数族裔,这一政策反而会限制亚裔学生的入学人数,况且主流白人学生根据高中阶段成绩的入学比率也不高。按照加州宪法修正案(五),对于普遍重视教育的华裔乃至泛亚裔来说,根据族裔人口分配入学指标也是一种歧视,而且非常不公平。
(二)美国加州宪法修正案(五)所体现的核心问题
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的支持者认为,通过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优待能促进社会平等。其理由是,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歧视,现有的政策不利于他们的平等发展,导致了少数族裔学生在受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少数族裔学生整体上不如其他族裔学生,尤其在考试成绩上处于劣势地位。通过录取比例上的底线照顾或录取分数上的适当照顾保障少数族裔学生享有同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促使少数族裔在未来发展中获得平等发展的机遇。
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的反对者提出了他们的理由:其一,不符合成绩标准。包括加州大学在内的美国大学一般以高中平均绩点(GPA)为最重要标准来录取新生,且加州居于前 9%的高中毕业生都已保证被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取。这意味着优秀的、家庭条件相对弱势的学生已通过这一录取比例获得了优惠待遇,再考虑所谓“族群”就是刻意倾斜给特定族裔,从而构成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其二,影响大学的教学。加州宪法修正案(五)使一些成绩不符合要求的学生不适当地被某个大学录取,这些学生入学后会因学习太过困难而大大增加了大学生的辍学率,并对他们造成辍学的伤害。如果硬性让他们毕业,那只能降低考试水平,或者按照不同的族群提供不同的及格率,这显然是荒唐且不可接受的。其三,影响公平竞争的社会风气。加州宪法修正案(五)也让某些学生更加没有努力学习的动力,因为他们成绩虽差但仍可通过照顾政策获得录取;反过来,亚裔和白人学生的勤奋则可能是徒劳的。这种劣胜优汰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整体社会公平性的维护和良好社会风气的构建。其四,可能会加重族裔间的紧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州宪法修正案(五)是以损害下层白人和亚裔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其他族裔某些中上层的需求,其间的利益博弈难以避免不同族裔之间的争斗与紧张。
在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的影响下,即使是那些完全靠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黑人和拉美裔人士,也被认为他们成功就读于名校源于种族,这对毕业于名牌高校的少数族裔学生也是很不利的。合理的做法是,对于某些少数族裔的学生,如果因为家庭收入低而造成学习困难,政府可给予这部分学生或其所在学区适当的经济补助,让这些学生能跟其他族裔的孩子在大体相同的环境下学习,以实现教育条件大体均等情况下的公平竞争,但录取标准则不能降低。
二、美国加州宪法修正案(五)与“平权法案”
(一)加州宪法修正案(五)的制度基础是“平权法案”
加州宪法修正案(五)源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本是指“平等人权在就业领域的体现”,其首要目的是杜绝因肤色、信仰、性别、族裔等引起的就业歧视。1960年代美国的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都致力于落实《民权法案》并实施对少数族裔的具体照顾政策。时任总统约翰逊赞同在大学入学、员工入职或晋升、政府招标方面给予少数族裔和女性优惠与照顾,在现实环境下努力消除历史上对少数族裔(如黑人、亚裔、拉丁裔)和女性的歧视,并通过招生、入职、政府合同等具体方面上的照顾,把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在历史上承受的歧视折算成现实的、具体的利益。①1965年6月,时任总统约翰逊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演讲中对“平权法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你不能把一个才从很多年的手铐脚镣束缚中解救出来的人,立刻将他带到与别人并肩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可以和别人自由竞争’,并且相信这样做是绝对公平的。因为对于打开一道公平的大门,我们要做的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全体公民都能够从公平的大门下通过,那么所谓的公平,不只是权力和理论,更是事实和结果。”转引自:刘丽丽.美国的教育平权[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6(11):35-38。“平权法案”实施后,其时有色人种和女性的大学录取率大幅提高,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也因之得到了一定的利益。1978年,哈佛的亚裔新生比例从此前的3.6%上升至6.5%,1985年又达到10.8%;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等大学中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也得以增加[1]。
为落实“平权法案”的要求,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普遍给予少数族裔学生一定程度的照顾,有的大学甚至明确采取给少数族裔学生加分或给予最低录取百分比的方式,照顾黑人、少数族裔学生顺利升入大学。亚裔家庭一惯重视子女教育,因而亚裔学生普遍成绩较好,在“平权法案”助推下,促成了美国高校中各族裔学生共同入学的局面,亚裔学生进入各著名高校学习的比例更是大幅提高。
(二)“平权法案”引发的两难选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反思“平权法案”并产生很大的争论,焦点在于“平权法案”实际已经矫枉过正,对某些少数族裔的过度保护已形成对白人的“逆向歧视”。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①1973年,巴克第一次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dical School at Davis)提出入学申请时,其基准分(benchmark score)高达468分(满分500分)。由于申请提交得过晚,并低于当年录取的最低基准分470分而未被录取。1974年,巴克再次提出申请。为吸取上次教训,他很早提交了申请,由于招生委员会主席Lowrey博士给出其最低评分而导致其再次未被录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巴克曾向Lowrey博士写信抗议特殊招生政策。参见:Regents of Univ.of California v.Bakke,438 U.S.265,320,98 S.Ct.2733,2763,57 L.Ed.2d 750 (1978)。成为公众反对“平权法案”的第一案。巴克是一名白人男生,连续两年都被同一所医学院拒绝录取。该医学院执行录取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让一些各方面条件比巴克差的黑人学生获得了升入该医学院就读的机会。巴克因而认为,定额制严重违反了公平竞争的社会规则,遂将该大学告上法庭,此案一直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原则上支持“平权法案”以照顾少数族裔的升学需求,但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则认为是违宪的。
由巴克案激发的有关“平权法案”的争论随即发酵,20世纪 90年代中期的加州州长 Peter Wilson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Peter Wilson利用自己处于加州州长位置的优势,极力推动废除“平权法案”。事实证明,这一时期取消“平权法案”的确给亚裔带来了福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中亚裔学生的比例迅速由20%左右上升至40%;华盛顿州中仅有6%的亚裔公民,而华盛顿大学的亚裔学生却占到了20%[1]。
20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了Grutter v.Bollinger案②Grutter v.Bollinger,539 U.S.306,123 S.Ct.2325,156 L.Ed.2d 304 (2003),Lee Bollinger时任密歇根大学校长。,“平权法案”再次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问题。白人学生、密歇根州居民Barbara Grutter申请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入学资格时被拒,Grutter女士发现,一同申请的有些黑人学生的平均绩点和法学院入学考试(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成绩比她低却获得了入学资格。因而Grutter女士就把密歇根大学告上法庭,这就是“Grutter v.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密歇根大学在本科生入学打分体系中给每个少数族裔申请者加 20分的政策是违宪的,但学校为了增加在校生生源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族裔申请者是合法的。这与 1978年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即原则上支持“平权法案”,但反对用量化的方式来确定如何照顾少数族裔的学生。
(三)“平权法案”争论的核心:程序正义抑或补偿正义优先
“平权法案”的核心是“程序正义”和“补偿正义”优先性的权衡与抉择问题。“程序正义”强调采取中立的同一程序来施用于一切社会群体,不论参与者的个体条件差异,只关乎是否完成既定的程序,由程序来筛选出结果。“补偿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经济条件等的差异而有偏向地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以保证在存有差异的不同族裔间寻求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合理且美好的价值追求,问题在于,落实“补偿正义”原则存在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的无限复杂性,基于这种无限复杂性而度量出来的结果,无论操作者如何费尽心思都会招致批评,实际是无法取得“绝对公平”而满足不同价值判断下的取向与行为抉择。更为要命的是,这种对所谓“补偿正义”的裁断权一旦被权力机器所劫持和把控,就可能沦为某些人的禁脔,并为其任意操弄。因此,在“补偿正义”本身不存在确定和统一认知的情况下,防止以“补偿正义”为名的权力滥用,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美国公众整体上是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差异性因素融入入学、就业等政策的考量当中,而不接受纯粹的“程序正义”,但对如何补偿相关族裔和个体所承受的损害却缺乏明确标准,其中不仅涉及社会因素的度量问题,还涉及不同族裔之间的平衡问题、同一族裔不同因素的差异性影响问题,根本而言,应该把这种差异性补偿标准具体换算在特定的个体身上,这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毕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计算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经济地位与政治资本之间、家境与社区环境之间、个性与教育环境之间的兑换率,在无法准确计算情况下的“补偿”和与之相对应的“补偿正义”,无论采取怎样的操作性补充行动,都会遭致诟病。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社会的“平权法案”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除了黑人和墨西哥裔等少数族裔,还包括很大部分利益实际受损的白人都支持和肯定“平权法案”。从更广泛、更深刻的范围看,减少阶层差别、促进社会融合、提升弱势群体的地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赞同和支持的社会理念。问题在于,“平权法案”所彰显的公平理念,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偏差,出现了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现象。比如财力雄厚、政治影响力强大的犹太人,从来都是选择性谋取自身利益。在大学入学问题上,犹太人把自己划入白人群体而不受“平权法案”的影响,弱势族裔如苗人却被划入亚裔中垫背。大学入学环节的“平权法案”,虽然在进入大学这一环节中对少数族裔实施了或多或少的照顾,但中小学教育阶段却任由弱势族裔的小孩在恶劣的基础教育环境中成长,实际上造成少数族裔在享受既有“平权法案”的照顾中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实际造成对少数族裔的另一种歧视。
(四)“平权法案”给亚裔学生入学带来困扰
依照“平权法案”的规定,所有公立大学在招收新生时,都有义务采取配额或加分的方式照顾少数族裔学生优先入学。毫无疑问,“平权法案”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少数族裔在升入大学时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保障了少数族裔不因种族、性别、信仰等因素而受到入学歧视。“平权法案”施行之初,华裔作为少数族裔也确实因之而获益,在升学、就业、政府合同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华裔学生在入学问题上并不因“平权法案”而获益。因为普遍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华裔学生的读书成绩普遍良好,在不歧视的情况下他们升入大学尤其是升入常青藤大学的机会很多,“平权法案”对少数族裔的招生配额反而成为对华裔的限制,华裔子女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优秀成绩在大大超出配额的幅度内获得进入优质大学就学的机会。
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常青藤各校针对亚裔高中生显然有不为外界所知的内定指标,但常青藤各校都不承认。据罗恩·鲁兹(Ron Unz)在《美国精英制的神话》中的统计披露,哈佛录取亚裔学生的比例在1993年达到20%之后迅速下降,此后十几年始终稳定在15%左右。①参见:Unz R.The Myth of American Meritocracy [J].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2012-11-28: 14-51。亚裔群体确信,哈佛大学等高校在招生录取中为了减少亚裔学生的数量,有意设定了一个隐密的、针对亚裔的“种族配额”[1]。1975年布朗大学的亚裔学生录取率为44%,1981年降至1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裔学生录取率从1979年的76.7%降至1984年的34.3%;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整体录取率为17%,亚裔为14%;哈佛大学整体录取率为15.9%,亚裔为12.5%;耶鲁大学整体录取率为18%,亚裔为15%。②转引自:孙碧.平权法案误伤亚裔?[J].比较教育研究,2018(2):96-103。
这种情况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并进行了专门研究。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托马斯·埃斯彭席德(Thomas Espenshade)和亚力山德里娅·沃尔顿·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通过对9 000名申请名校的学生进行分数统计和数据分析后发现,如果高中成绩大致相当,白人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要比亚裔学生大三倍。在有“美国高考”之称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亚裔学生必须比黑人学生高出450分(总分2 400分)才可能有升入大学的同等机会[2]。不言而喻,大学在录取新生时加入了种族因素,造成了对亚裔生源的招生歧视,这已经是很难否认的事实。
三、“平权法案”存废的最新发展及后续影响
(一)Fisher案:“平权法案”的最新发展
“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案①Fisher v.Univ.of Texas at Austin,133 S.Ct.2411,186 L.Ed.2d 474 (2013)。源于白人女生 Abigail Noel Fisher 和 Rachel Multer Michalewicz 于2008年申请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时被拒绝录取。她们发现,不少有色人种学生却以比她们低的成绩进入该校学习,因而她们认定自己受到了反向种族歧视,遂以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为据将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告上法庭。
这个官司经过漫长的审理现已作出判决②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579 U.S.(2016) (Fisher II)。后文中的法院意见源于判决。,因为法官Antonin Scalia于2016年2月13日去世,法官Elena Kagan申请回避,案件由剩下的七位大法官投票决定。Fisher案在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二次审理后出现了4∶3的裁决结果,Kennedy、Ginsburg、Breyer和 Sotomayor这四名大法官同意维持下级法院也就是第五巡回法庭做出的判决。判决书总结了Fisher案在最高法院第一次审理时设定的三项约束性原则:(1)严格审查平权行动的录取程序;(2)对于学校方为追求学生个体多样性而采取的录取政策所进行的合理解释,司法予以尊重;(3)大学在招生过程中纳入种族分布因素时是否经过仔细的设计则无需司法审查。裁决书说,德州大学综合采用排名前百分之十的招生政策是独创的,但该校说明学生个体多样性的数据并不足。裁决书要求该校应定期评估所获取的数据,“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方法,确保种族政策除了满足重大利益之必要性外,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作用。”
这个个案绝不会是单一案例,它还会波及其他高校。如果“平权法案”所体现的对少数族裔在大学录取中的照顾政策因此而终结,它不仅会在公立大学的招生政策中受到即时影响,同时也会波及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完全可能参照公立大学的做法而终止对少数族裔学生的照顾录取。因为“平权法案”被否决,对私立大学而言,它们和公立大学一样失去了适用“额定录取”的司法基础,任何照顾性质的大学录取政策都将被视为是一种种族歧视。基于美国的司法制度和判例法传统,在未来的类似诉讼中,学校很大可能要面临败诉的后果。
(二)Fisher案所体现的招生政策及其后续影响
法院驳回了上诉人Fisher反对招生政策的四个观点。首先,法院坚持认为,虽然缺乏相关数据佐证,但得克萨斯大学为实现“多样性”目标的理由是“足够充分的,可衡量的,对该政策进行司法审查,是可实现的。”其次,法院认为,得克萨斯大学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在 Hopwood一案判决生效到开始实施“结合整体学术招生政策”的七年间,种族中立政策及其推广力度不足以实现上述目标。再次,法院认为,种族因素对大一班级的“多样性”有积极的效应(虽然还是有限的效应)。这些有限的效应应成为“实现多样性的初步尝试而不是违宪的证据”。最后,法院认为,上诉人Fisher并没有提供切实可信的证据证明,该大学在实现种族多样性和种族中立目标中存在可以改进的具体方面,包括如何扩大“前10%规则”。多数法官强调:“大学有责任利用现有的数据来评估人口结构变化和是否已经摒弃了种族意识政策,并且从正反两面来识别必须采取平权措施所产生的影响。”
在冗长的异见书中,大法官Alito联合首席大法官Roberts和大法官Thomas写到,大学既定利益的多样性是不可衡量的,相比 Fisher案一审时,其背后的利益又有所不同,“大学的辩解缺乏说服力,有时也让人觉得甚至不够真实”。Alito同时指出,明确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高校的目标“既不具体也不准确”,“对种族偏好的使用也没有限制原则”。Alito由此质疑,“法院怎样才能够确定固有观念已被充分摧毁”或者“是否完全实现了种族间的平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大学仅仅通过一些员工就认为,种族偏好对完成这些模糊的大学目标是有必要的,就可以评判是否存在种族歧视,那么寻求严格审查的艰苦努力将是毫无意义的。法院将被要求听从大学管理者的决定,平权行动政策将完全与司法审查隔离。”Alito重申了巡回法庭中异议人士的意见:自动录取的少数族裔学生跟全面审查录取的学生相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同质化、更缺乏活力,而且更加固守陈规。Thomas大法官则重申了他在Fisher第一次重审时所表达的意见,也就是“高等教育招生中使用种族因素是平等保护条款明确禁止的”。
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第五巡回法院的判决,使得种族因素在大学录取政策考量中得以维持。根据惯例,20年内类似案件都不可再被讨论,大学录取中的种族区分将持续下去。
四、余 论
(一)教育公平是一个深具广泛性和复杂性的议题
教育平等是一个全球性话题,教育中的不平等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显现。美国“平权法案”以及由此引起的司法争议,关涉群体教育平等、个体教育平等的复杂问题,所涉及的人群不仅包括少数族裔,还包括广大白人家庭,不仅涉及社会底层民众,也涉及社会精英,是牵扯到社会各个阶层、行业、区域等不同人群的议题,其广泛性不言而喻。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则在于,不仅有当下的地域、个体、阶层、家庭、经济条件、培养方式、教育理念、利益群体影响等诸方面复杂因素的交织,还有文化背景、种族、教育资源布局等历史复杂因素的影响,更为难缠的是,承认这些差异却无法进行不同因素之间的确切换算,更无法作出精准的补偿。不同区域、不同侧面、不同个体之间都会有很多不同,任何“一刀切”的政策法律都会招致批评甚至导致新的不公,针对不同个案的处理则既无精准尺度,也无法承受高昂的管理成本。因此,教育平等注定是一个招致批评和争议的议题。从另一角度看,任何社会的公平从来都是相对的,在看得见的未来也难以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因而,需要社会大众更多的宽容与包容,只要在趋势上和整体上走向更为公平的教育环境,就应该予以认同和支持。
(二)促进教育公平:从消除显而易见的教育不公入手
尽管如此,对教育公平问题也并非无计可施,更不可以无所作为。无论处于何种社会中,教育公平之所以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这一问题关乎各个家庭、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之外,就是教育资源在分配中存在不少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抓手”。从社会管理的方面看,着力消除这些不公平因素就能下好不断促进教育公平的“起手棋”,即从反向来促进教育公平,通过消除诸如基于身份、区域、学习经历等的加分,控制招生名额在一定区域、族群、对象中的特殊安排和照顾,坚决遏止招生中的腐败行为等,从而达到正向促进公平的目的。从更为深远的方面看,则要增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避免优质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更要限制甚至禁止经济发达、教育资源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应该注重向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区域挹注资源。在招生、转学、转专业、名额分配等重要事项中强化正当程序要求,保持程序中立、程序公开和程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