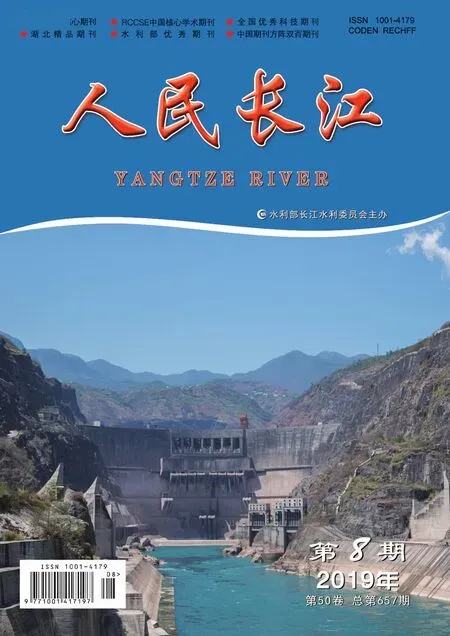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运行的环境问题及风险分析
黄 绳,农 翕 智,梁 建 奎2,邵 东 国,钟 华
(1.武汉大学 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2; 2.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北京 10003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为缓解我国黄淮海平原水资源严重短缺、实现我国南北方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 截至2018年10月16日,中线工程已累计向京津冀豫四省(市)调水175亿m3,从根本上改变了受水区的供水格局,改善了受水区城市用水水质,提高了受水区多座城市的供水保证率,受水区地下水位开始回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效益日益凸显。
然而,分析研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日常运营情况和输水调度过程发现,中线工程水源地、中线总干渠和汉江中下游都存在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潜在风险。雷沛等[1]讨论了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可能面临的支流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及生态风险;张乃群等[2]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水体浮游植物进行了调查,讨论了浮游植物对中线水质的影响;左海凤等[3]对南水北调中线沿线劣质地下水对输水水质的潜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典型渠段数值模型;刘丙军等[4]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汉江中下游地区水资源利用相互关系;钟华平等[5]研究了合理的地下水生态水位对南水北调受水区内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必要性;任仲宇等[6]对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水污染途径进行了研究,讨论了中线总干渠沿线地下水的水质保护对总干渠水质的影响;王光谦等[7]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老鹳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农业非点源污染的识别模型,对中线水源区的农业非点源污染进行了风险评价和污染源区的识别。另有许多学者从外界环境因子对水质的影响[8-10]、水质时空变化规律[11-13]和水质风险分析[14-17]等角度,讨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可能存在的部分生态环境问题和潜在风险。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中线工程的水质安全、生态系统健康和运行稳定,及时发现并解决以上问题具有重要的工程、生态和社会意义。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特殊性、区域性和封闭性,目前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运营的环境问题及风险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还需要对中线工程水源地、总干渠以及因调水引起的汉江中下游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潜在风险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1 水源地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为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多项针对性措施,严格控制水源保护区内工业、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物排放,丹江口水库水质目前较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但参考丹江口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的监测数据发现,该季度监测点的水质状况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说明水质存在恶化趋势。整体而言,水源地当前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农业面源污染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位于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周边大部分是农业生产区,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水源区水体氮、磷污染的主要来源。2017年实施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十三五”规划》指出:农业和农村的污染已成为库区主要污染源,对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氮排放量的贡献比例分别达到49%、43%、74%。丹江口库区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水产畜禽养殖、区域水土流失和化肥污染以及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等[18-20]。孟令广等[21]采用输出系数法计算得出,畜禽养殖业、耕地和农村生活污水导致的氮磷排放占水源区氮磷面源排放总量的70%以上。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加大了水产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力度,采取关闭搬迁养殖栏舍、取缔网箱养殖等措施,但库区仍有水产有效养殖面积约 6.2万hm2,且存在部分水域投饵性网箱密度设置过大、未充分考虑水体合理承载力等问题[22]。水土流失和化肥污染是库区面源污染的另一重要来源。“十二五”规划期间丹江口水库及其上游地区开展了一定的水土保持工作,但问题仍然突出。据统计,2017年丹江口库区水土流失面积为12 000 km2左右,占总土地面积40%以上,库滨缓冲带的水土流失比例高达69%[23]。由于库区所在流域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多数耕地位于坡面处,化肥容易随地表径流进入库区,坡地的水土流失增加了耕地农药化肥污染水质的风险。根据统计数据,2002~2014年水源地化肥施用明显过量且逐年增加,施用强度是我国生态县建设化肥施用符合标准的2.47倍[24]。另外库区内耕地施用方法不够科学合理,多为抛洒浅施,导致保肥性差[25],如丹江口市化肥利用率只有30%~40%左右。
1.2 重金属污染
丹江口水源地的重金属污染风险主要来自3个方面。
(1) 淹没区土壤中的重金属释放。丹江口大坝加高后,水库正常蓄水位从157 m提高到170 m,新增淹没区面积305 km2[26]。被淹没的土地成为新的水库底质,其中包含的重金属元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释放到上覆水体中造成水环境二次污染[27-29]。水库沉积物中,Cd,Hg,As,Zn,Cu,Pb等重金属均有一定程度的富集,尤其是Cd元素,快速解吸释放的风险较大[30-31]。
(2) 水库流域内的污水排放。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或间接性汇入,汉江流域和丹江流域的入库支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直接增加了库区重金属含量[32-33]。尹炜等[34]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16条主要入库支流,发现老灌河、泗河、天河的重金属污染相对最为严重。
(3) 流域内尾矿的淋滤和重金属的释放。丹江口水库及其上游地区多座尾矿库对水源地水质安全构成了较大威胁。据统计,水源区内有尾矿库300余座,且大部分建设时间较早,建设标准低,安全基础差,环保设施缺乏,尾矿废水可以通过渗流进入水体和土壤,这种污染不仅危害性大,而且作用时间长、不易被人察觉[35]。另外溃坝更能引起地表水体大范围的污染。栾川县近年来就发生了多次尾矿溃坝事件[36]。继洛钼集团大东坡三道沟尾矿库塌方事故后,2017年2月14日龙宇钼业有限公司尾矿库6号溢流井发生坍塌,造成库内循环水流入河道引起污染。
1.3 消落带生态问题
消落带处于水陆生态系统的过渡区,是周围泥沙、有机物和化肥农药等进入库区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是水库脆弱敏感、易污染、易破坏的地带[37]。因季节变化和运行调度的需要,丹江口水库水位涨落使库区周围土地在淹没和出露两种状态间交替[38],其中145~170 m区域为主要消落带,估算面积约540 km2。消落带的主要覆被类型即为耕地,淹没时土壤中氮磷和重金属等物质进入水体引起水质污染,出露时库区周围农户的无序开垦造成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同时水位变动也影响了土壤中黑炭对微量污染物的吸收[39-40]。调水人为地改变水库水文变化规律,消落带内诸如细叶水芹、狗牙根等物种受水淹影响较大,物种多样性受到破坏,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变得简单化[41]。目前丹江口水库的消落带尚未稳定形成,生物群落还没适应环境变化,消落带植被群落的恢复和构建也正在研究之中[42]。由于库区消落带具有狭长、横向延伸小等自然条件和干湿交替的水文条件,难以从群落尺度进行遥感监测[43],同时消落区诸多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还不能为人们所认识[44],因此对丹江口水库建立生态监测网络以长期关注其消落带演变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2 总干渠环境问题和风险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全线利用地形高差,基本为自流输水形式。由于输水距离长,总干渠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45]。为保障总干渠正常运行,必须重视以下环境问题和潜在风险。
2.1 藻类贝类增殖风险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水深较小,光照条件好,生物群落多样性相对简单,以菌-藻-小型水生动物为主。出现氮、磷等污染源扰动情况时,干渠生境容易改变,会使生物群落结构和优势种群发生变化,尤其是藻类、贝类等低等水生生物,在适宜条件下可能快速生长繁殖。由于干渠的营养元素、水温、光照、流速等条件均较适宜,2015年以来干渠硅藻、金藻等藻密度呈现自南向北沿程升高的趋势,也发现了淡水壳菜等贝类大量增殖的风险。藻类异常增殖不仅增加“水华”爆发风险,其残体沉降还导致底泥营养盐和有机物蓄积量增加,一旦释放将会产生二次污染。而贝类在输水管渠和水工建筑上附着生长,不仅增加糙率系数,降低输水效率,还可能堵塞管道,腐蚀结构,威胁工程安全[46-47]。
2.2 路桥运输事故和施工污染
总干渠沿线跨渠桥梁超过1 200座,运送危险化学品、石油和其他液体的车辆经过时,存在倾覆和化学品入渠的风险,导致突发性事故[48]。例如,2016年张石高速易县境内一辆拉运甲醇的车辆被货车追尾,使甲醇泄漏到下方中线干渠造成污染,由于干渠建有排水沟等防护设施且工作人员及时处理,事故未对输水水质造成严重影响。Wang等[49]基于贝叶斯网络进行风险评估,北京-石家庄段跨渠桥梁发生危险品运输事故的概率为0.08%,并且在最不利路况下事故最高可能性可以达到0.17%,并且事故发生后,往往造成输水干渠的大范围退水和断流,同时污染退水区,因此此类运输事故可能造成的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另外,跨渠桥梁在施工时存在泥浆、油污、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质[50]。桥面的粉尘、油污等污染物被雨水冲刷后,也可能通过伸缩缝等结构破损处进入干渠,造成潜伏性、长期性的污染。
2.3 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
中线总干渠沿线穿越上千条大小河流,河水水质较渠水往往差很多,有的甚至是黑臭水体,另外部分渠段所在位置是地表汇流聚集区,受到区域农业面源污染和垃圾堆放点等点源污染的威胁。工程设计时利用渡槽、倒虹吸、涵洞三大类交叉建筑物使河流与干渠不发生水交换,另外还布置截流沟拦截排污口和地面汇流[51]。尽管建筑物防洪等级较高,但长时间运行后,起初洪水计算的地形等条件变化较大,暴雨下污水漫溢风险仍然存在,如保定段西侧大清河浅山区就曾出现洪水漫溢串流。勘查发现,主要风险点包括个别低位渡槽、阻塞的截流沟、交叉穿越的排污廊道和建筑物等[52]。此外,工程设计时为防止地下水压力破坏,干渠附近地下水水质不满足Ⅲ类标准时通过自流或抽水的形式外排到相邻水系,以减小对渠道的压力;地下水水质满足Ⅲ类标准则通过单向逆止阀内排减压。但在运行过程中,逆止阀损坏或者强排井判断失误都可能引起水质不达标的地下水入渠的问题。即便是当时符合标准的内排水,由于沿线污染型企业废水滴漏和垃圾场淋滤液下渗,水质可能已经劣于Ⅳ类甚至更差,例如河北段就有40 km地段地下水水质超Ⅳ类[53]。
2.4 大气干湿沉降污染
我国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特别是华北地区已成为全球大气污染物沉降量最高区域之一[54]。大气中的污染物质以酸雨或降尘的形式落入渠中,成为总干渠水体污染的来源之一。黄河以北的中线总干渠沿岸分布着大量的燃煤发电、化工、制药、冶金等企业,大气干湿沉降带入氮、磷、重金属等污染物对中线总干渠输水水质的影响不容忽视。根据现场监测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换算污染负荷,按照最不利情况估算,顶宽取130 m,明渠长度按1 156 km计,加权平均过水量取47.5亿m3,则大气干湿沉降共引起干渠SS浓度增加1.440 0 mg/L,TN浓度增加0.209 0 mg/L,氨氮增加0.088 0 mg/L,TP增加0.001 3 mg/L[54]。
3 工程运行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后,汉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水量减少,水文情势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了汉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问题。近10 a来,汉江中下游爆发了多次硅藻水华事件。据调查,汉江下游东荆河几乎每年春季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硅藻水华问题[55]。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丹江口水库下泄流量不足导致汉江中下游流量减小、流速减慢是水华在枯水期爆发的重要原因。谢平等[56]通过定量计算(不考虑引江济汉工程)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后汉江水华发生概率高达13.6%。为改善汉江中下游河段生态、灌溉、航运等用水条件,建设实施了引江济汉工程,于2014年9月正式通水。但根据报道,2015年2月下旬和2016年3月上旬,汉江中下游干流仍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水华污染,采取水利调度措施下泄流量后才得以控制。谢敏等[57]采用观察流量法分析汉江得出结论,水华发生的临界流量约为500 m3/s,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与环境影响研究》专题报告的成果基本一致。因此,丹江口水库以下河段如何进行联合调度以控制水华的爆发,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此外,由于丹江口水库下泄水量减少而导致水环境容量不足,汉江沿岸的排污引起的中下游水环境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应引起重视。
4 应对问题的建议
(1) 对于丹江口水库水源区,首先要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升级和转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药化肥的利用率,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全面贯彻落实河长制,禁止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未经处理排入水源区,提高流域内尾矿库的安全性;构建水库的水质监测网络,加强各部门协调配合,严格把关入库支流水质,尤其是总氮和重金属含量。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和保障制度,指导农民有序合理开垦,保护水陆交错带生态。
(2) 对于输水总干渠,最重要的是构建水质预警及应急调控管理平台,实现中线总干渠全线水质监测,提高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研制渠道内快速高效去除污染物和藻类的技术设备,及时充分地应对藻类贝类异常增殖、化工品运输事故等污染事件。另外,既要提高跨渠建筑物施工技术,减少施工污染物进入干渠,又要完善跨区域多部门水质管理协作机制及数据共享平台,定期巡查并规范化管理周边垃圾堆放场、企业废气废水等污染源,防止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沉降的污染物长期累积。
(3) 对于汉江中下游,要加强监视汉江水量水情变化,联合调度汉江梯级枢纽,研究面向生态补水的最优调度方案,缓解工程引起的汉江水量减少问题,确保中下游水量满足生态环境需求,同时积极开展汉江中下游水污染防治工作。
5 结 语
综上所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运营过程中还面临很多环境方面的问题和潜在风险。流域内农业面源污染、因排污和尾矿所引起的重金属污染以及丹江口水库消落带的脆弱性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而总干渠输水过程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来自于跨渠路桥事故中污染物的排放风险及建筑物施工带来的污染,另外,因地表水地下水侵入、大气沉降等原因造成的污染物输入及渠道内藻类贝类增殖和水华风险也不可忽视。工程运行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汉江中下游流量变小所引起的富营养化和水质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当结合当前形势与政策,迅速有效地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切实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稳定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