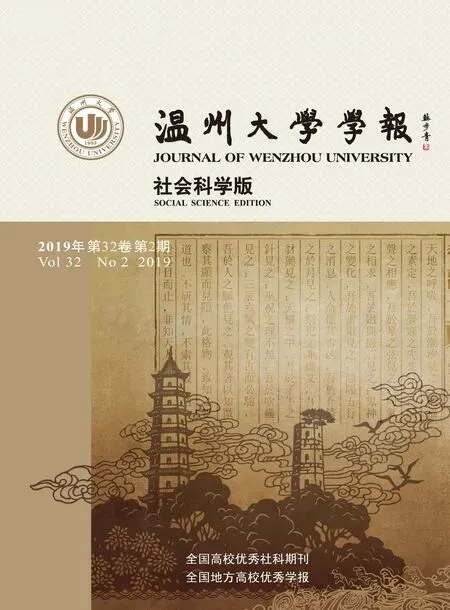“道”是无情却有情
—— 老庄情感哲学初探
萧 平,张 磊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丰富的情感表达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人类的情感不是一种动物本能性的情感,而是一种包含了社会心理、历史意识、文化意蕴在内的情感。中国古代哲学特别重视人的存在方式,认为“只有情感才是人的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1]。先秦儒家对情感的重视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事实上,早期道家对情感也十分重视,老庄对“情感的本质”“情感的作用及其局限”“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认知,本文尝试对老庄情感哲学的主要内容进行初步考察。
一、无情说
老庄情感哲学的首要特征就是“无情说”,老子和庄子在这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命题,如“圣人不仁”“天道无情”“人故无情”等等。如何理解这些命题的真实意蕴?究竟要如何看待老庄的“无情说”?下面我们逐一论之。
(一)圣人不仁
老子特别强调源自本心的真实情感,反对任何虚伪的感情,也拒斥对感情进行繁文缛节的规范与制约。这首先体现在“圣人不仁”的提法上①本文所引以王弼本为主,同时参考帛书本、郭店竹简本。: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2]13-14
历代注释很多,如河上公注曰:“圣人爱养万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任自然。”[3]18王弼注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2]15天地与万物完全按照各自的本性生存发展,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人格意志与情感,这就是“天道无亲”,效法天道的圣人也是如此。道家的圣人和儒家的圣人既相同又不同。相同之处在于两种圣人都有情感,绝非没有任何情感的人;不同之处在于两者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生存处世的态度亦不同。儒家的圣人满怀仁爱之心,心忧天下之民,故采取汲汲有为的治理方式,由此庄子批判道:“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4]382道家的圣人反对将这种爱民之情通过人为的方式来呈现,而是主张效法天道,尊重百姓的生活意愿,让他们充分展现自己的本性,达到自然的生活状态,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129。“不仁”是指不人为干涉,不以私情为准绳,任其自然发展。由此可知,“不仁”本质上恰恰是真正的仁爱之情,是一种无私之情,这是老子情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所辨析出来的各种情感及其规范对道家是不适应的,道家亦视之为附赘悬疣。道家崇尚自然,认为哪怕是再好的赞美与引导,对人而言也是一种限定与损害,从而也就斩断了其无限发展的根本途径——自然。老子在言说时往往会避免这一问题,从而采用遮诠的方式去诉说,以保全该事物最本初、最自然的样貌,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绳绳不可名”者,都是运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来呈现的,“圣人不仁”也有这种意味,这种“不仁”恰恰保有了“大仁”最本来的样子。在《道德经》中,老子对这种外在规范与制度所设置出来的、标榜为“名”的各种情感表达了一种拒斥: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2]43
此章通常被视为老子反对儒家的仁义,其实这种理解忽视了作为“名”的“仁义”与作为真实情感的“仁义”的区分。河上公的注比较准确:“大道之时,家有孝子,户有忠信,仁义不见也。大道废而不用,恶逆生,乃有仁义可传道。”[3]73实际上,老子认为“仁义”之名与“名”应所对应的那种真实存在状态出现了背离,这正是大道废弃之后人类社会的现实状态。作为纯粹至真的仁义状态是无名的,出现了“仁义”这种名,恰好表明人类社会在堕落,滋生了各种虚伪的情感,才不得不彰显与之相对的“仁义”状态。六亲之间的情感本身应是真实完美自然的,但正因为出现了不孝不慈之人,才出现了对作为名的“孝慈”的特别推崇。假设整个社会全部是实然的孝慈,那么作为“名”的“孝慈”自然不会彰显。因此,“孝慈”等“名”都源于人为的认知,庄子对此有深刻认知:“至徳之世……相爱而不知以为仁。”[4]451“至徳之世”并不是一个绝情的、无情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都具有一种自然之真情,而无半点虚伪狡诈。相爱意味着自然的真实情感的存在,而“不知以为仁”则表明释放自然真实情感的主体并不去辨析和区分情感的种类,亦不需要某一种“名”来规范、称谓。与此相反,道家反对各种矫揉造作之情,那种世俗之情只会损害个体的内在本性。只有从这个层面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老子的“绝仁弃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2]45
1993年出土的郭店简并不曾直接否定“圣”“仁”“义”等德行,而是反对“辩”“伪”“虑”等分别造作之情。参照郭店竹简不难发现,后世通行本《老子》中的“绝仁弃义”原作“绝弃虑”,据廖名春之见,“仁”的本字作“”,亦作“”[5]20。尽管“”“”俱从心部,但毕竟是意义差别甚大的两个字。关于“”字的训释,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刘信芳、陈斯鹏为代表。该字读作“化”,训为“教行”。[6]第二种说法以季旭升、廖名春为代表。该字读作“为”,作也。此处加“心”,表示此“为”系属心理活动,指心思、心计[5]20。第三种说法以裘锡圭、高明为代表。‘’可释读为“伪”,应理解为“背自然”的“人为”[7]。但不论采取哪种解说方式,都只能说明老子所反对的只是破坏了自然之情的后天说教,却不曾全盘否定仁爱,反而老子所强调的“复返自然,回归性命之情,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发展”才是最大的仁义。
总之,在老子的哲学中,圣人与百姓都是有真实情感的人,但老子对现实社会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尤其是从政治治理的层面进行了反思,他主张“圣人不仁”“绝仁弃义”“大道废,有仁义”等,都是强调圣人应当以无为的方式处世,反对人为创设与塑造各种道德规范来衡量情感,反对治理者将一己之私情强加于百姓之上,而是主张尊重百姓的真实情感和意愿,让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自由地生活。
(二)人故无情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对人的情感及其局限性有了进一步的反思与批判,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庄子与惠施关于有情无情的对话中。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4]225-227
惠施认为人必有情,他对“情”的理解大致指人的各种情感,当然也可能包括各种情欲、情志、意念等,惠施认为如果不将这些包含在内,则不能称之为“人”。这是纯粹从实然的角度来界定人,人必然有一定的情感情欲。而庄子只不否认人有各种真实情感,所以庄惠对话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即对“情”的界定不同。庄子所认定的“情”乃是非之情、好恶之情、情欲之情,这种“情”只会伤身损性,是应该排斥的,因为这不是人内在本性所包含的内容。人的完整界定是精神灵魂的超越与独立,而各种形体相貌等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形体相貌受之于天、道,与万物相比,这一点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有人能够拥有独立的精神,超越物我对待,不以俗世的各种是非之情、情欲来损害这个超绝的精神,故庄子主张“常因自然而不益生”[4]227,即顺从天与道所赋予之生命,不积极地增益生命本真之外的东西于其上。而惠施仍然不解庄子之情,认为不增益则无法保全己身,始终认为情感是肉身必须具备的,而庄子则指出惠施沉浸于是非坚白之辨中不知返,已经因为情欲而损害了生命。对这种情欲以及是非之情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外、杂篇中: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4]458
“失性”亦即因为各种情欲而损伤了本性,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2]27-28庄子所说的损性伤身的五者正是对老子这一思想的发挥,满足一己之私欲,在各种感性生活中寻求刺激,在杨朱看来乃是全生,而庄子则批判为损性,不是真正的“得”——“德”。由此可知,以老子、庄子为中心的道家,根本不曾有任情纵欲的思想[8]330。
总之,老庄的无情说,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无情是指摒弃各种私情、情欲,因为道家认为情欲的追逐只会伤害人的本性,使人迷失。庄子、惠施关于无情的对话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展开的。故道家的无情排斥情欲,无情是无情欲。其二,无情是指没有私情,恰好彰显了道家的至公之情。老子的“圣人不仁”即是这一观念的表达,它超越了儒家“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的狭隘认识,①在道家的自然主义立场看来,“至仁”境界是将自己和人间的一切关系剥离净尽(“至仁无亲”),一切形迹扫除净尽而完全地融入自然,致使“天下忘我”。所以对于达到这个境界来说,将人与人紧固地交缠在一起的人伦关系和以敬、爱为内容的“孝”等道德观念和行为,是相距太遥远了,“不足以言之”!参见:崔大华.庄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57。老庄认为圣人不应偏私于任何一个人或群体,对宇宙万物都应有一种普遍之情。由此可知,无情即是至公之情。其三,无情不是绝对没有感情或摒弃、压抑任何情感,相反,无情旨在推崇真实的情感,但真实情感的流露最终也建立在宇宙万物一体的基础上,因而达到上述第二层次的无情。故道家的无情恰好彰显了人的真情。最好的例证便是庄子妻死时鼓盆而歌,通常的理解只看到鼓盆而歌,却忽视了庄子的“我独何能无概”②“概”即“慨”,意即“感触哀伤”。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485。之说。其实庄子妻子死时,他首先是有感触而哀伤,这才是真实的庄子,是活生生的作为人的庄子,而不是作为神的庄子。但庄子这种至真的情感流露并没有一泻千里,不可收拾,而是最终入于“理”③庄子之“理”非外在礼乐制度之规范,而是源自对天道的领悟与对天地万物自然之理的通达。,可以说是“以情入理”,知“得”是“时”,知“失”是“顺”,一切人事变化都是“命之行”,即知其为理之必然,于是不动于情,而哀乐不入[8]473。道家的无情说不能偏离这三个层次,否则将导致绝对无情说,反而误解了道家的无情。
二、真情说
老子和庄子虽然都倡导无情,强调应自然无为,但这种“无情”只是针对会损害人本性的情欲、私情而言的,并非要人摒弃一切情感,使人落入徒具形骸的境地。非但如此,老子和庄子还倡导真情说,主张人释放真实的情感。
(一)以慈为宝
孔子倡导“仁”,老子则主张“慈”,并将“慈”视为三个最重要的德性与品质之首。老子曰:
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2]170
《说文解字》曰:“慈,爱也。”④参见:许慎.说文解字[M].和刻本:362;许慎.说文解字[M].汲古阁本:692。在老子看来,三宝中最重要的是“爱”,只有内心有爱才能真正地勇⑤这一点和孔子所讲的极为相似,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参见: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1987:161。,因为这种勇敢不是以杀人为喜乐,而是以保全生命为要务。没有爱的勇敢是残忍、残暴,是“乐杀人”,因而“不可得志于天下”[2]80。老子批判现实中的各种不正义战争,反对杀戮,主张“不以兵强天下”[2]77、“以无事取天下”[2]149,主张以慈爱来化解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他才会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2]173。面对不可避免的战争,即便取得了胜利,也不能去美化,所谓“胜而不美”[2]80。战争必然会有伤亡,必然会有生命的丧失,因此他遵循着古礼,主张以悲悯的心态对待战争: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2]80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2]173
高明认为:“杀人众则庶民殃,老则失其子女,幼则丧其父母,悲哀降临无辜。故此,战胜不可赞,亦不可颂,当以丧礼处之。以丧礼处之者,以示其残害百姓,荒废田亩,不祥甚矣,不可美也,不可以杀人为美。”[9]王弼注:“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胜。”[4]173劳健云:“王弼注云云,后人相承,多误解‘哀’字如哀伤之义,大失其旨。王弼注‘慈以陈则正’句云:‘相慜而不避于难,故正也。’”[2]173可见“哀”不是哀伤,而是一种慈爱,本质上是人发自内心的爱心、悲悯之情。这种“慈爱”超越了敌我的界限,是早期道家所宣扬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王安石又曰:“夫战,非得已也。非得已,则虽胜犹不足以为善。胜而为善者,乐致人于死矣。此所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也。”[10]世人常好胜而恶败,这实际是由后天人为的分别以及人自私性格被自身无限放大而造成的,老子此处反世俗而行之,胜不仅不善反而应该哀之,这实际是对人性的一种拷问和对人生命之情的一种回归,后天所附加的种种外在私欲真有自然所禀赋的内在生命可贵和神圣吗?显然没有,但是老子所处的时代已然是大道废弛、非得已而战的时代,人们争强好胜,此时老子之哀,正是他自然爱物的真情流露,超越了狭隘的一国一家的利益纷争。而“哀者胜矣”正是顺道爱物的效果,“哀者胜矣”我们大可以理解为“慈者胜矣”,“慈者”即为顺道爱物,以本性待人,不矫饰、不妄为,以自然之法则为行动之则,以此焉能不胜?
老子除论“慈”“哀”之外还谈“善”,老子讲“善”很多,且含义丰富,有心地淳厚、高超、幽玄、擅长等义,除却心地淳厚表达伦理情感之外,其它意义与本文所论无关,故先按下不表。老子以善表达伦理感情,如“与善仁”,意味着与人交往要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老子讲到: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2]129
河上公注曰:“百姓为善,圣人因而善之;百姓虽有不善者,圣人化之使善也。百姓德化,圣人为善。”即无论是对待善者还是不善者都要以善的方式对待他。另外“善”在这里作“德”的判断宾语,是对“德”做一种价值判断,“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4]95,“德者,道之舍”,“德”根源于道,法于自然,老子以为这种“善”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之情感,并主张圣人将这种自然之善推广于天下万物,无有偏薄之心,顺乎万物天性自然,自然化成。所以老子又说: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2]161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①帛书本作:“是以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2]71
均平地、真诚地爱戴每一个事物,却又不治理他、不约束他、不去妨碍他的自由,这才是老子善的真实内涵。老子主张爱人,反对弃绝不善之人,而是常常去救助人。
综上可知,老子推崇发自内心的慈爱与悲悯,反对狭隘的私情,这种泛爱万物的博大情怀,体现了老子哲学中的宗教精神。
(二)顺性任情
道家诸子基本上无意于对情作善与不善、恶与不恶、美与不美的道德判断,战国中后期,人性论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然而道家在这方面似乎保持一种超脱,即不主张性善或性恶,张岱年将道家的人性论称之为“超善恶论”[11]194。但道家对人性仍然有其看法,他们批判儒家的人性论,《庄子》一书谈论人性就体现了这一点。道家谈人性论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性”字使用较少,而“德”字使用较多。道家所认为“性”者,是自然朴素的,乃所谓“德”之显见。宇宙本根是道,人物所得于道以生者是德,既生而德之表见于形体者为性[11]194。徐复观亦认为,内篇的德字,实际便是性字[8]331。既然人生而具有的内在之“德”就是性,那么人的各种形体相貌都是天所赋予,无不正常,但仁义是否天赋呢?在《骈拇》篇中,庄子进行了深刻地反思:
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4]317
骈拇和枝指在通常人看来都是不正常的,不是人性天生所固有的,庄子借用俗世的这种观点,进一步批判仁义,认为将仁义作为人之本性,无异于俗世看待骈拇枝指,其实都是将无用之肉、无用之指添加到人性中。庄子尖锐的批评了以仁义为性的观点: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4]325-326
骈拇和枝指如果人为分开,必然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与庄子同时的仁人——主要是儒家学者,其对天下人性状态,就如同要断弃骈拇枝指一样忧虑,而那些不仁之人则放弃其生命本真之情,浸淫于物欲之中。庄子在这里提出“性命之情”的观念,张岱年认为,人之本性,道家亦名之曰“性命之情”。情者真实之义,性命之情即性命之真。其中不含仁义,亦不含情欲[11]194。道家的真情说体现了情与真的统一,性命之情表明这种情是人的生命天生所具备的,而非人为增加所成。
总之,庄子多将“性命”与“情”并提,所谓“任性命之情”“安性命之情”都是指性命之真,庄子学派所谓“贵真”亦指人情之真。由此可见“真”这一观念在庄子哲学中与人性、情感的主题紧密相关。通常“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与“伪”相对立,其实“真”“伪”对立的观念究竟形成于何时很难定论。我们认为在“真”出现的初期,它并不表示一个与“伪”相对应的观念,而在《老子》提出“道”的观念后,“真”才以根源于“道”为其价值基础与“伪”相对应[12]174-175。《老子》中的“真”主要有三处,如“质真若渝”等。这里的“真”都只表示一种对实存之性状、来源的描摹与肯定①陈静认为,老子中的“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断定物之实在为“真”;其二是肯定质之纯朴为“真”。参见: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52。。正是由于设定了一个“道”,“真”的意义才得以显示,即凡是根源于道的性状或实存即为“真”。换言之,“真”本身并不是一个实体性存在,而是对实体或性状之根源、价值所作的判定。正是由于“真”的这种判断性评价功能,故常常作形容词与其他词结合构成合成词,表达根源性、本然性的观念。当然也有名词性的“真”,如“贵真”。不过这个名词性的“真”本身并非表示实体性的存在,而是指代各种根源于“道”的性状、实体,如“德”“性”“性命之情”“身”等②钱穆认为:“庄周乃本此见解(指独化)而落实及于人生界,其由天言之则曰道,其由人言之则曰神,其由确有诸己而言之则曰德。此三者,皆可谓之真。”参见:钱穆.庄老通辨[M].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55。。关于这个“真”,《渔父》中有重要的论述: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屯,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4]1026-1027
“真”这一观念代表着生命的本源存在状态,“真”根源于“道”,“精诚之至”是对来源于“道”之性状的描述,也是对“真”的诠释。强哭、强怒、强亲都不是人真实本性的呈现,是不“自然”。而哀、威、和的形成则是因为哭、怒、亲等情感源于本真之道,不参杂任何的伪饰与雕琢。故而庄子反对各种乖离了“道”——“不真”的世俗活动,提倡不必拘泥于任何外在礼乐制度的纯然不杂的性情流露。从来源上看,“真”禀受于“道”,凡真性、真德、真情皆自然而成,不可改变。这里的“自然”强调“真”的根源性,即根源性自然,亦即自然本性,“道”的敞开与呈现就是“真”,换言之,天地万物等一切生命存在的绽放、延续、持存就是“真”。庄子批判世俗对“真”的矫夺,在《马蹄》篇中有所显现: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4]338
马有其真性,即自然本性,这种本性就在马的存续状态中。这个寓言的目的并非在于说马,而是以马喻人,其意蕴在于说明人被制度奴役化后个体自我精神丧失,不能自觉地保持自然本性。圣人能保持“真”,实际上就是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与自我意识。在《庄子》中,“真人”一词出现频率很高,“真”涵盖了“德”“性”等等根源于“道”的性状,凡保有这种“真”的属于“真人”。真人和至人、神人一样“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知说生,不知恶死”[12]176。
综上所述,“真”建基于“道”这个根源性的观念之上,是一切事物之本性的来源,即自然本性。道家的真情说旨在强调人性真实呈现,情感的真实流露,反对各种虚伪的、矫情的状态。
三、影响与意义
老庄的情感哲学对中国传统士人的情感与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后世学者对老庄的“无情说”“真情说”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发挥。
汉初黄老学兴盛,士大夫们多少都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尤其是道家的情感哲学思想。贾谊在《鵩鸟赋》中就表达了超越狭隘私情的观念:“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13]这正是对庄子不以私情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的发挥。作为文学家的张衡则曰:“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14]表明只有将心灵超拔出万物之外,才能不被世间的荣辱得失所牵制而损害人之真性。
魏晋时期,圣人无情说一时成为士人们辩论的热门话题。何邵《王弼传》曰:“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15]在王弼看来,圣人实际上与普通人有着共同的情感,但圣人独特之处在于能以其卓然独立之“神明”(理性精神)主导着五情①汤用彤先生认为,“圣人无情之说,盖出于圣德法天。此所谓天乃谓自然,而非有意志之天”,“与天地合德,与治道同体,其动止直天道之自然流行,而无休戚喜怒于其中,故圣人与自然为一,则纯理任性而无情”。参见: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0。,故能应物而不被外物所牵累,洒脱而不拘束,率真而不违礼。总之王弼对“圣人无情”的理解实发老庄之精义,成为当时的流行学说。何晏亦主“圣人无情”,而贤人则“动不违理”,“小人则为情欲所累而不能自拔”[16]。这种无情说发展到极端,则演变成嵇康、阮籍的“任自然之情”,直至放浪形骸、不为礼法所拘。可见“无情说”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真情说”,两者相辅相成。与嵇康、阮籍对名教大加鞭挞的做法相对的是向秀、裴頠、郭象,他们一方面承认情感是人的重要内在本质,是人性自由的重要内容,“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17];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情感本身具有恶的倾向,故不能放任情的发展,故主张以礼义节制情感,体现了儒道兼综的特点。老庄的“真情说”对魏晋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18]的命题,对“情”在文学创作中的关键作用作了理性表述。挚虞也指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19]钟嵘、萧子显都持同样的观点。钟嵘《诗品·序》开篇便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咏。”[20]萧子显则主张:“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21]对文学作品以“情志为本”思想加以深刻阐述的是刘勰,他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22]他力主“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这种“重情”思潮不仅大大提高了魏晋文学作品的价值,而且为魏晋美学畅情意识的形成和成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魏晋之后,受老庄“真情说”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家们。这一时期,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理学家内部掀起了对程朱理学天理人欲的反思与批判,文学方面则倡导“性灵文学”“至情说”。从王艮、何心隐、李贽等心学家到“公安三袁”、汤显祖等文学家,无不如此。在思想层面最有力的发声者当属王阳明,王阳明以人情来诠释天理,按照“心即理”的逻辑,认为人的各种情感无不是本心所发,由人的良知所主导的基本情感即是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在阳明看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23]。良知是本体,一切活动只要按照内在的良知去做即可,七情只需任本心之自然即可。王阳明的后学中当以泰州学派最重情感,如王艮王襞父子在自然人性论上发展了情感,将情理解为符合人性的自然情欲,人的自然欲求、自然情感是最真诚的,是“自然之则”,即天理,不是“人欲”。李贽则提出“童心即真心”“发乎情性,由于自然”“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仪”[24]等观点。在文学领域高谈“以情抗理”的是汤显祖,“反对传统的以理制情论,提出以情抗理、以情胜理,以本体化超越化的情感来反对权威化先验化的伦理理性和强制性的法制”[25],主张以个体之情感为唯一真实的存在。稍后的袁宏道则对情理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他明确主张“理在情内”[26],主张尊重合乎自然之性的真情。这些思想均是在老庄“真情说”思想上加以发挥的。
老庄的情感哲学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亦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层面上讲,老庄的“无情说”要求治理者尊重百姓的情感与意愿,反对强力干涉或将个人私欲凌驾于他人之上,体现了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尊重。从个体修养层面来看,“真情说”显示了老庄对各种强制性规范的反思与批判,对道德异化的反思。生活在快节奏的、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倡导道家的“真情说”,有利于释放人的精神压力,缓解人的情感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