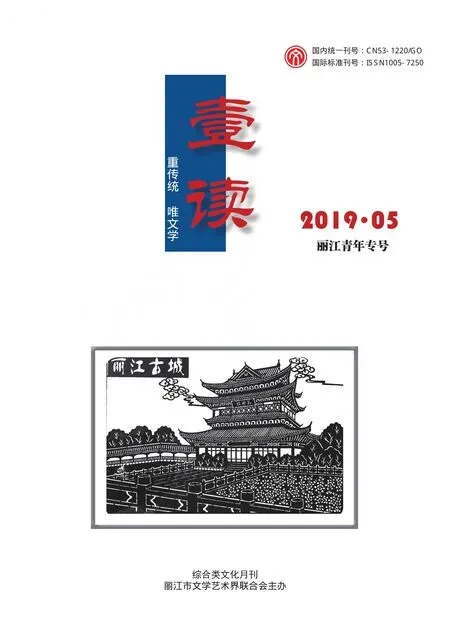给丽江
◆冯娜
出生地
人们总向我提起我的出生地
一个高寒的、山茶花和松林一样多的藏区
它教给我的藏语,我已经忘记
它教给我的高音,至今我还没有唱出
那音色,像坚实的松果一直埋在某处
夏天有麂子
冬天有火塘
当地人狩猎、采蜜、种植耐寒的苦荞
火葬,是我最熟悉的丧礼
我们不过问死神家里的事
也不过问星子落进深坳的事
他们教会我一些技艺
是为了让我终生不去使用它们
我离开他们
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
他们还说,人应像火焰一样去爱
是为了灰烬不必复燃
劳作
我并不比一只蜜蜂或一只蚂蚁更爱这个世界
我的劳作像一棵偏狭的桉树
渴水、喜阳
有时我和蜜蜂、蚂蚁一起,躲在阴影里休憩
我并不比一个农夫更适合做一个诗人
他赶马走过江边,抬头看云预感江水的体温
我向他询问五百里外山林的成色
他用一个寓言为我指点迷津
如何辨认一只斑鸠躲在鸽群里呢
不看羽毛也不用听它的叫声
他说,我们就是知道
——这是长年累月的劳作所得
陌生海岸小驻
一个陌生小站
树影在热带的喘息中摇摆
我看见的事物,从早晨回到了上空
谷粒一样的岩石散落在白色海岸
——整夜整夜的工作,让船只镀上锈迹
在这里,旅人的手是多余的
海鸟的翅膀是多余的
风捉住所有光明
将它们升上教堂的尖顶
露水没有片刻的犹疑
月亮的信仰也不是白昼
——它们隐没着自身
和黝黑的土地一起,吐出了整个海洋
石像
最难雕刻的部分已经完成
她的笑意是石头的
她的嘴唇和衣袖是石头的
她的哑默和心跳是石头的
当一个人伸出手,她的体温是石头的
她在石头里获得时间
在别人的眼光和抚触中获得生活
许多朝代后,还会获得新鲜的祷告
——如果人们还信奉神灵安住在石头当中
在她的石头的眼睛里
生命和死亡是同一只鸟
日出前起飞,在黄昏隐藏了脚迹
她的怜悯和遗忘是石头的
她的呼吸是石头的
她的不确定的名字是石头的
——最难雕刻的部分已经完成
博物馆之旅
没有声音的朝代,超过了后代的理解力
一代人的器皿,保存着他们的雨水和心智
我相信重复,也是创造历史的一种方式
——或者,是众多的重复延续了历史
献身于某颗星辰和它不可知的轨迹是愚蠢的
相信星象坦荡则更加愚蠢
一行经文获得无数版本的赞颂
如今,隔着冰冷的钟罩
我们活捉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祷告
那些在旷野里逃窜的、在海峡溺毙的
罕见的、庞大的白垩纪物种
想象它们和我们一样目光发烫
辨认着未知的来客
来自地心深处的背叛
繁衍出岛屿、密林、始祖鸟多余的翅膀
此刻灯光盘旋,为它们注入新鲜的死亡
时间的暗道和窄门,被推开、掩埋
一尊远渡重洋的雕像
眉宇与我们相仿
而我们
我们正在为尘埃和海水的重量,争论不休
粉红清真寺
为了他人的信仰,蒙住东亚的脸孔
为宽恕,找到黑暗中需要宽恕的名字
穿过玻璃中古老的颜色
是阳光,让我变得粉红
粉红的真主,并没有给我裸露皮肤的自由
一百三十年前的我,纺织着黑夜和长袍
鲜红的血流在别处
孤儿的悲泣,一个王朝分裂的爱
隔绝着我
积攒的箴言和顶针,缝补着一千零一个夜——
“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
有人谎称粉红的寺庙像情人的手指
他沉默地面向西方坐下 他听见
一个拥挤、失修的国度
我的声音,擦亮了它隐藏的遗物
他深信他的祷告
没有给我更多的自由,也没有将我变成新的
黑暗
寄北
用新习得的方言,穿过一枚顶针
一个北方的手印,用不多的力气
按在新鲜的盐粒上
坐在市集的背阴处,想与你说一说
李煜或苏轼
我在南方获得的宁静,是他们维持的气候
拂晓时,回味着出现林海的梦
你经历的北方,早有人述说
手艺人有时带来奇妙的新把戏
我尾随他,看见作坊里人们正把日子
一点点用旧
裁缝店里的学徒,裁寿衣就像裁一封家书
我熟悉那些哭声和交谈
熟悉那些滚边的丝绸衣裳
古人的信,藏着不想被识破的伤心
他们拣选尘灰覆盖的词,吹一吹
我把湿了的双手擦一擦
把它们重新放回你不能看见的地方
诗歌献给谁人
凌晨起身为路人扫去积雪的人
病榻前别过身去的母亲
登山者,在蝴蝶的振翅中获得非凡的智慧
倚靠着一棵栾树,流浪汉突然记起
家乡的琴声
冬天伐木,需要另一人拉紧绳索
精妙绝伦的手艺
将一些树木制成船只,另一些要盛满饭食、
井水、骨灰
多余的金币买通一个冷酷的杀手
他却突然有了恋爱般的迟疑……
一个读诗的人,误会着写作者的心意
他们在各自的黑暗中,摸索着世界的开关
寻鹤
牛羊藏在草原的阴影中
巴音布鲁克,我遇见一个养鹤的人
他有长喙一般的脖颈
断翅一般的腔调
鹤群掏空落在水面的九个太阳
他让我觉得草原应该另有模样
黄昏轻易纵容了辽阔
我等待着鹤群从他的袍袖中飞起
我祈愿天空落下另一个我
她有狭窄的脸庞,瘦细的脚踝
与养鹤人相爱、厌弃、痴缠
四野茫茫,她有一百零八种躲藏的途径
养鹤人只需一种寻找的方法:
在巴音布鲁克
被他抚摸过的鹤,都必将在夜里归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