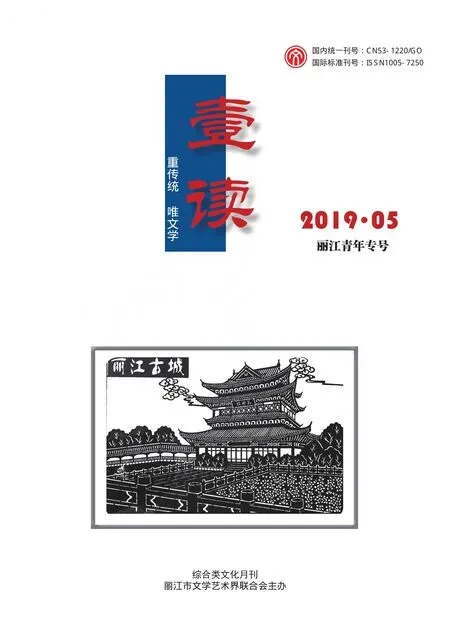B 面房间(节选)
◆黄立康
B1
“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孙燕姿《天黑黑》
我曾是一个怕黑的孩子。夜晚,大人熄掉灯,进入睡梦,我却被关在梦境之外,徒劳地睁着眼,看着黑暗吞噬房间,与外面世界的黑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整个世界的黑暗向我扑来,我的恐惧被献祭在黑暗的神坛上充当鲜活的牺牲。多少个夜晚,我——一只胆小易惊的兽,在黑暗的无风森林里惊惶觅食,我紧绷身体,将棉被拉到眼睛下方,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压低鼻息,防备着黑暗的突袭。不敢出声、不敢乱动,怕吵醒大人引来责骂,责骂意味着你将被推远、孤立、放逐到更深更黑的暗夜里。这会让我更恐慌更害怕,我只好依靠自己接近零度的胆汁,与黑暗对抗。
黑暗里到底有什么呢?我总觉得在我看不见的暗处,有一个鬼影正试图偷偷接近我。我闭上眼睛,因为用力过猛,整个眼幕泛起了闪烁荡漾的光圈。那光圈因黑暗而生,在黑暗里繁殖,一层又一层的叠加,如同增生的肉瘤,增加了夜的病情;那光圈随意的分开又聚合,画出夜行的百鬼,在黑色宣纸上悄声乱舞;那光圈随着我的心跳而跳动,它变成了黑暗的心脏,激出黑色的血。这是我醒着的噩梦。
黑是房间的另一道门。有这样一张画:一个人落进了光线暗淡的海里,深黑处,一只血口大张的海怪正隐在黑暗里。未知就是恐惧,当寒夜降临,黎明尚远,失去太阳和神明的庇佑,对黑暗的恐惧是人类共同患上的恐惧幽闭症。但是,人心对于绝望之物充满畏惧的同时,也充满迷恋,像至幻的药品,明知可能致死,依旧沉迷其中。我开始迷恋、依赖黑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少年,在大海的兽笼里,和一只饥饿的花斑虎隔船对望,要活下去,就得喂饱大虎,并驯服它。我试着驯服关在我身体里的恐惧,用我乏力的想象之鞭,讲故事是我对抗黑暗的方法,选择出现在我黑暗里的活物,虚构一些幼稚无害的情节,情节里有我,还有哥哥。我和哥哥在黑暗里编排故事,甚至躺着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表演。渐渐地,黑暗变成了故事,变成了夜晚的光。那些浪漫幼稚而温暖的讲述,来自于兄弟间的配合,这些时刻,有个双胞胎哥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我不知道哥哥是否也怕黑,他与我的默契是否也是受迫于对黑暗的恐惧。我们闭口不谈躲在各自黑暗里窥探的鬼怪,毕竟,我们只负责各自的成长,毕竟,没有一个男孩愿意被别人称为“胆小鬼”。夜幕降下盛宴的布帷,我们念着咒语通过幻想的密道前往虚构的世界。后来,我搬出哥哥的房间,那些生于黑暗的故事悄然枯萎,但我们没有感到任何不适,我们是各自幻想世界里的英雄,同床而异梦,一条船不必有两个船长。我带着那些黑暗里的想象,继续成长,某天,当我提笔写下那些故事,我突然明白,黑暗是菩提。
B4
“原谅我们,我们都还在找。”
——陈奕迅《Baby song》
酒杯如同房间,父亲将自己藏在里面。父亲在世时,总是往杯子里倒酒,后来酒杯空了,我心里某个地方也空了下来。我很想知道,在我的儿子心里我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但即便是父与子,也是两个人、两个世界,有些疑问终究会成为时间的谜语。我时常对镜自顾。镜子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酒杯,你往镜子中斟酒般注入目光,目光穿过水质的空间,当你到达自己时,总会产生一些迷幻的恍惚和失真的醉意。马尔克斯说:“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老,是源于他发现自己开始长得像父亲了。”于是我仔细地在镜中人的脸貌上寻找父亲的踪迹:卷发、日渐升高的发际线、浅淡的眼井、褐色的痣、坚硬的唇线、布满胡茬的下巴……像末日的预言得以实现,终有一天,我将与父亲重逢、重合:父亲是死去的我,我是活着的父亲。
如果我说“父爱如山”这一温情金句是文字自造的善意谎言和圆满假象,你是否会生出宿醉后的空虚和疲乏。我要像蒋方舟“审判童年”般审判文字,请相信我,我讲述的是另一种真相:父爱如刀。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父亲(包括我自己)其实并未具备世人所期许的父亲应具有的品质。包容、干净、沉稳、温柔、通达、智慧——这些精美的词语配在“父骑单车,儿倚父背”的画面下,父亲的背影,在柔曼的光辉里接近神圣。但真正的父亲们,其实是一群充满缺点的人,他们身上的缺点比母亲们多得多,破坏力也大得多。世界对于男性同等残酷,虽然在人生竞技场上,男性要比女性容易到达巅峰,但那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男性一场平凡,一生庸碌,甚至落于庸俗。多数男性无法活出从容、自信和气度。父亲们懒散、易怒、消极,毫无顾忌地吸烟、酗酒、赌博。男人们惊人地相似:大男子主义,自负又小气,狂妄却怯懦。
骆以军在《脸之书》里形容自己:“如同我童年印象里同样总一脸怒容的父亲。”总是一脸怒容,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形象,或许也是我留给我儿子的印象。儿子总是向我投来探寻的怯怯目光,好像我怒气隐现的脸是一杯倒满的白酒,他试图以目光猜测酒的度数和烈意。为什么父亲总是一脸怒容?为什么我总是一脸怒容?是因为父亲在爱哭懦弱的我身上看到了他孤儿的童年,还是因为儿子强行占去我的时间让我不得不安身于一种陌生的身份?父亲是我急欲颠覆的王权,儿子是我私心想要开创的时代,父与子,轮回的交迭,我们同时都一脸怒容,我们又同时忧心忡忡地偷望各自的父亲,看他脸上是否有黑色的云。
父亲嗜酒,母亲恨酒,如同地球的两极,生成了我两兄弟对酒截然不同的方向:哥哥滴酒不沾,而我喜欢小酌。初中时,某天下晚自习回家,刚进堂屋,便看见母亲拭泪忍哭,父亲尴尬讪笑,地板上一地的碎玻璃,半个酒瓶躺在酒液里,酒像黑暗伏地蔓延。浓烈的酒味暗示着曾发生过的激烈争吵,甚至还可能有打斗。我和哥哥悄悄地退出禁区,默默地洗脸洗脚。父亲跟了出来,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他喷出的酒气要浓过他的语气。酒是父亲的知音,却是母亲的仇敌,他们的战争殃及孩童。或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父亲的生命、母亲的幸福,像酒气那样开始快速地消散。
父亲的酒杯是寂寞的。酒杯在电视机后,和一个酒瓶放在一起。多数时候酒杯是空着的,是寂寞的。父亲会时不时到电视机旁找东西,借机将酒杯倒上酒,一口闷下。由于家人的反对,有所忌惮的父亲只好喝“快酒”,无法细斟慢酌,难得闲情雅致,喝酒,对于父亲更像是一次偷欢。快速麻醉,恍惚飘然,全然颠倒了梦境与现实。酒中的父亲是寂寞的。父亲倒映在酒中的身影,如同海上飘摇的孤岛。我希望父亲能原谅我,我只是无法向他解释我的世界,或许父亲也不知道如何向我解释他的世界。我不知道父亲的人生在追寻什么,甚至,我忽略了父亲也有他的人生,也有他的追寻。所幸的是,父亲他一直在找。他在找什么?找寻活法,找寻回家的路,找寻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意义,找寻“幸福”看它能否将自己融化,找寻童年源头的苦果将它连根拔起,又或者找寻祖先的归处暗暗扣响虚无的回音?我十四岁的心计无法猜透沉默的天机,我想,父亲没找到能让他安宁的事物,他心不安,他无法平和,他丢了魂,也失去了为他喊魂的人。父亲像铁笼里的困兽,一直在自己划定的距离里神经质地来回走动、低吼。
这时代太快,将一腔热血的人早早抛下。一个身陷在寂寞和困顿里的男人,他人生的际遇就像喝下的酒,回忆苦,今朝烈,和往事干杯,和梦想告别。当我站在三十岁的路口眺望父亲而立时的身影,恍然觉得那背影如同倒下的一线烈酒,我尝到了天地悠悠的悲怆,品出了欲说还休的苦涩,我甚至在父亲的背影里看到了同样焦虑暴躁的自己。我一直在找,也一直没找到让我安宁的事物。父亲,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总是一脸怒容?儿子,别怕,为什么我总是一脸怒容,因为我们目光游离、心事重重的父亲总在另一个地方,想着两三件后悔的事,想着一些未了的心愿,酒杯,变成了逃离世界的安全出口。酒杯盛放了一个男人的心事与怨怒,最后也将盛放这个男人的灵魂。
“被酒打了”——我们方言里有酒的妙趣。某次上昆明和朋友醉饮翠湖到凌晨,第二天我“被酒打了”。浓睡不消残酒,睡到中午的我头痛似裂,乏力欲呕。强忍着不适,头重脚轻地起身找到了正在吃午饭的家人。母亲不理睬我,而我五岁的儿子则偷偷观察我,他脸色苍白,目光忧虑。宿醉难受,还招人嫌弃,我决定换家餐馆吃一碗咸辣的肠旺米线刺激一下疲惫的胃。走了一段路发现儿子悄悄跟着我,我和他说话,他不回答,只是低头跟着。我点了米线,儿子骑在一张凳子上假装若无其事地玩,不时偷偷看我。我逗他说话,他小声说,昨晚他大声叫我,我就是不答应。他是在担心我,他担心有什么事突然发生在我身上,灾祸或是惩戒突然降临将我吞噬,他要看着我才安心。
儿子三岁的某天,他蹦跳着来到我的书房。我扬扬手里的酒杯逗他:来,喝一杯。儿子认真地看了酒杯一眼,眼神戒备,然后看向我说:爸爸不要喝酒了,喝酒会死的,像爷爷那样。我酒杯悬空,眼眶湿辣。
B5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
——《人质》张惠妹
猫醒来,钻进我的右手臂弯,为我讲述她的梦。她梦见我死了。她哭着去找医生,要医生将我的牙齿留给她,作为遗物保存。我抚摸她的头发,问她:为什么要保留牙齿?她悲伤的哭腔带着不可逆转的确信:因为牙齿硬,能保留很长时间,它可以代替你陪着我,直到我死。
为爱而生的感性女人,她们的可怕之处在于,即便是在梦里也能保持狂热而又清晰的强大逻辑。我抱紧她,左手放在她隆起的腹部。腹部平静。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正漂浮在充满羊水的子宫——温暖的房间——里安睡,那房间似乎有着很好的隔音效果,可以抵御一切侵袭,他(她)母亲的忧伤并没有惊扰到他(她)的美梦。几次产检,我都在B超室外等着。我想象着人耳听不到的超声波穿过猫的身体,转换为影像呈现在屏幕上。子宫——婴儿的天堂——以模糊昏暗的状态出现在我眼前,看上去如同静默漆黑、生命涌动的海底。猫一脸疲惫地走出房间,却压抑不住兴奋: 医生说看到小家伙的手和脚了,医生说看到孩子的脊椎了,医生说照到宝宝的五官了,医生说这孩子一动不动很安静,你说会不会是个女孩?医生说小家伙可调皮了,不停乱转,会不会又是个儿子?
我总是无法从那一片昏暗的影像中看到惊喜,不知道这和我的色弱有没有关系,但每次我都要做出热烈地回应。B 超的影像看起来像一团团翻卷的乌云,伴随着条形的闪电和圆形的滚雷,生命的雨就在这里孕育。后来照了一次四维彩超,小家伙的侧脸和他哥哥小时候十分相像,肉红色的画面,太阳高照,云层松软。
曾经的我也被这些松软云层、幽暗海水包裹着,我年轻的母亲带着担忧和期待,在疲惫沉重间,掰着指头数着每一秒钟,时间臃肿而笨拙。那时我还无法感受到父亲的存在。年轻的父亲坐在走廊里,带着尴尬和克制,正对着放射科照X 光的房间门,想象着人眼看不到的X 射线,穿过他妻子的身体,穿过他未来的孩子。1984年,小城的医疗条件有限,母亲简单的产检,听胎心时却听到了两个胎心音。年轻的父母肯定慌张而无措,最后决定照X 光,虽然明知X 射线会伤害身体。母亲说,当时以为怀着一个什么怪物,坚持要看个究竟。结果,体型比我略大的哥哥挡住了我的存在。医生安慰说,可能是双胞胎,问家族里有没有双胞胎基因。我的家族里没有双胞胎基因,我和哥哥是异卵双生子。我成长的岁月里,我总是费劲地解释我不懂的遗传学:我们不像,但我们是双胞胎,异卵双生,如假包换。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母亲的子宫是永远温暖的房间,温暖,安谧,甘甜,摆放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在她的子宫里,极速成长,那速度快得如同世界已等不及要看我们的模样。
生命之门,需要鲜血才能扣响。
生我和哥哥那天的情景,母亲轻描淡写的叙述,屏蔽了寒冷、恐惧和危险。母亲说,生下哥哥和我后,她大出血。时隔多年,母亲旧事重提的语气轻且细,那些逃离她身体的鲜红浓血,在当时,飞快地涌向死神,而现在,清淡得像一场安静落下的雪。那场薄雪在我的记忆中经久不化,毕竟,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母亲的磨难,是我的血地。三十二年后的初冬,天气转凉,树叶枯黄,我即将迎来我的第二个孩子,孩子的名字就叫“小雪”,我希望她平安地落下。
医生把我叫到前台,向我做术后反馈。医生说:“割开了七层。”(七层,用锋利的钥匙解开生命柔软的保险。子宫,保险柜最后的密码。)“子宫壁已经非常薄了。透明,可见婴儿头发。”(玻璃城堡,水晶鞋。)“母亲在33 周突发妊娠高血压综合症,34 周强行剖宫,早产儿。”(世界已然等不及要见她。)“是女婴。”(睡美人,白雪公主,长发姑娘。所有的女孩都应该有长发和花房。)“体重1.7 公斤,出生后送往新生儿科,在保育箱里进行专业护理。”(因为轻,才看得见轻盈的天使。)“请签字。”(谢谢。)
儿奔生,娘奔死,生死只隔一层。产前确认胎位,给猫打B 超的是个相熟的女医生,她对猫说:“你太拼了。”猫那时大概已经虚弱得没有力气炫耀她虚荣的幸福了,她只能疲惫地报以微笑。一阵眩晕袭来,猫晕倒在B 超室。医生赶紧找来轮椅,将昏沉的猫护送回病房。
为什么不顾生、不避死地生孩子?如果问男人,我猜测答案会是五花八门,甚至可能会出现茫然犹豫地说“不知道”的情况。如果问女人,你会得到坚决而肯定的答案:因为爱。为什么要为你怀孕,为什么要为你堕胎,为什么要为你生孩子?因为爱你,因为她是我的孩子,因为她是我们的孩子。在猫的词汇里,“我们”是一个万能词,像一个房间,围住了我和她,隔开了全世界。有时候,猫会因为“我们”的孩子在某个瞬间与我神似而高兴骄傲,全然忘了她自己。
童话,不止是写给孩子和成人看的,童话是写给世界的。《格林童话》的《糖果屋》,被继母丢弃的兄妹在森林里没有征得主人的同意,“拆下房子忘情地吃了起来。”这一情节隐喻了孩子对母亲的残忍掠夺。糖果屋代表着母亲,香甜,柔软,可口,你可以用她对你的爱,向她蛮横无度地索取。如果可以,母亲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血肉之躯。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她看自己儿子的眼神狂热而专注,见到一月未见的儿子时,全世界连同阳光空气都是多余的。
孩子有时任性而残忍,这或许是人类想要极力掩饰的丑恶。有一件事,我要向我母亲道歉。妈妈,对不起。我十岁那年,跟随父母去蝴蝶泉旅游。天气炎热,母亲买了三只甜筒冰淇淋,我一只,哥哥一只,她一只。我边走边吃,很快吃完,节俭的母亲是不会再给我买一只的。可我还想吃,我转身走向母亲,一把抢过她手里的半个冰淇淋。我一直记得这个情节,因为内疚,那时馋嘴的我残忍得像个魔鬼。我现在三十三岁,对世界充满了欲望和野心,那时年轻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是什么伟大的蛊惑,麻木了她,让她选择了隐忍与克己?因为身体的特殊构造让她们天生就有包容的特质?因为爱?
年轻的母亲喜欢一条蓝色牛仔裤,我曾陪她去看过好多次,但母亲一直没将它买下。每次,母亲都要比一比、摸一摸,也不好意思总是试,后来,母亲就只是进去看看。或许,很多次母亲路过那家店,都是匆忙走过,然后迅速地瞥一眼,或许,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母亲隔街眺望,仿佛看一场热闹。有一天,牛仔裤被人买走了,挂牛仔裤的地方空了。我想,母亲那时的心也空了,又或者,母亲没有失落,反而骄傲地舒了一口气,她又一次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引诱她的魔障。魔障消失了。无敌是多么寂寞。
猫陪我去买裤子。恰巧导购员是我教过的女学生,十八岁的女孩,正青春。女孩为我热情地推荐,殷勤地夸赞。她或许只是希望我买裤子,但却让猫如临大敌。女孩的热情穿越了火线,抵达了猫的战场。猫溃败了。我能明显地感觉猫情绪一落千丈。女人间天然而古老的敌意,无法帮助猫忽略时间的公正,猫在刷卡付完钱后,竟失神将钱包忘在了柜台上。我将钱包拿在手里,客气地和店员告别。这件事我从未和猫提起,她出于本能而浑然不知。七年一闪而过,现在,我们很少说“我爱你”了,因为我们默默认同了“我爱你”的局限,那三个字像一个狭小的房间。曾经我们是两个人,所以我们说“我爱你”,如今,我们是一个人,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在一首歌里,互为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