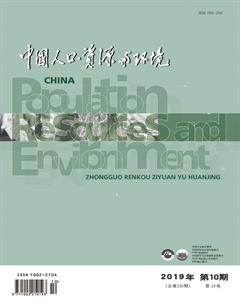论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的立法配置
摘要 合理配置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是《长江保护法》中法律制度体系建构及其展开的核心理论问题。作为以水为核心物质要素构成的空间,长江流域的事权具有特殊性。需要基于一定的空间观,从层级、内容、空间、性质四个维度,对这一特殊空间进行识别以确定事权的“范围”,进而在政府间进行事权立法配置。既有立法基于一元空间观,将长江流域视为“水系空间”。导致事权的立法配置存在流域层级事权虚化、弱化,仅针对单一“水”要素,对流域特殊性问题缺乏针对性事权配置,片面强调事权关系的单向服从等问题。当前,长江流域已成为长江經济带建设的空间基础和物质支撑。这为长江流域空间识别的重构理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驱动力。鉴于,国土空间布局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功能定位及各项任务的载体。本文认为,长江流域应从一元空间观下的“水系空间”,升级为多元空间观下“以水为核心要素的国土空间”。据此,《长江保护法》在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及展开的过程中:①为中央、流域、地方三个层级分别配置相应的事权,重点是重构长江流域管理体制,为流域管理主体配置相应的流域层级事权。②顺次建立流域规划、水安全保障、生态保护与修复、水污染防治、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五类基本法律制度。③针对长江流域特殊的“点”、“线”、“面”问题,设计流域特殊性法律制度对政府间事权给予配置。④在各级、各类政府间合理配置权威型、压力传导型、合作协商型、激励型等四类事权,形成配套法律制度。
关键词 长江流域;事权;水系空间;国土空间;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 D92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10-0024-06 DOI:10.12062/cpre.20190705
理论上,事权虽然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范畴,但其核心内涵无疑是政府的行政事权[1]。或言之,事权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具体化。现代“法治政府”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使行政权力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以防止权力滥用。这必然要求通过立法的方式,科学界定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并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进行权力分工,即政府间事权的立法配置。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可见,实现政府间事权的立法配置,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涵。
1 问题的提出
作为典型的公共事务,流域治理虽然离不开社会、企业、公众的参与,但政府作为管理者、组织者、决策者,其流域事权对流域治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对长江这样一个涉19个省(区、市)、12个部门(行业)的流域而言,没有任何一级政府、一个部门(行业)可以单独胜任全部流域事权。因而,在实现长江流域法治的进程中,必须通过立法对政府间的事权进行合理配置。当前,专门为长江流域制定一部《长江保护法》,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共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部立法如何通过构建及展开其法律制度体系,以真正实现长江流域法治。考虑到,立法是以各类法律规范集合成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基本内容,而法律制度本质上又以对相关主体权利(力)义务的配置为核心。其中,对有关政府主体职能的规定就是对政府间事权的立法配置;而政府之外其他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则需要通过配置政府间事权加以监管或保障。因此,如何对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进行配置,就成为《长江保护法》中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及展开的核心理论问题。
2 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立法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事权配置的理论基础是“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层次性理论”。即依据事权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或产品)的范围,首先将事权分为全国性与区域性事权。进而,对介于二者之间的事权划为准全国性事权,或作为混合事权由央地分享,或作为直管事权配置给专门主体;对区域性事权则再根据其具体范围,在地方各级政府间进行二次配置。可见,事权的“范围”是政府间事权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流域作为以水为核心要素构成的特殊空间,其事权的“范围”具有特殊性——“流域空间性”。这种特殊空间的事权“范围”,需要结合此特殊性从四个维度加以衡量:
(1)层级维度。流域空间划分的基础在于水,这与行政区域的空间划分并不完全重合,在空间上可能超越单一行政区域。因此,流域事权中既可能包括中央和地方层级的事权,还可能包括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全国性事权——流域层级的事权。
(2)内容维度。流域空间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流域事权在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内容上,相较医疗、教育等事权具有明显的涉水指向性。
(3)空间维度。“水”具有高度的“塑造性”与“可塑性”,由此形成了流域间差异化的空间形态。于是,每个流域空间内都可能存在流域特殊性问题,需要通过事权配置加以特殊应对。
(4)性质维度。以水为核心要素构成的流域空间具有价值(功能)的多元性,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生活、生态等价值,饮用、灌溉、行洪、发电、通航、养殖、景观等功能。但是,多元价值(功能)之间却是有限兼容的。这种有限兼容性一旦被打破,相关主体附着在相关价值(功能)上的权益将难以实现。这就要求,流域事权在性质上必须适应流域空间内价值(功能)多元、权益复杂的需要。
刘佳奇:论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的立法配置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10期即便如此,长江流域空间的事权范围仍不易确定。因为,“空间”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依据不同的空间观(识别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识别结果。这将直接影响上述四个衡量维度的实现程度和结果,进而影响流域事权“范围”的确定。既有立法沿袭的是一种“一元空间观”,将流域视为由“点”(湖泊、水库等重要水体)、“线”(干支流)构成的集水区或分水区,即“水系空间”。囿于这样的空间观和空间识别结果,给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的立法配置带来了以下问题:
2.1 层级维度——流域层级事权的虚化、弱化
鉴于长江流域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划,故其事权应当存在中央、流域、地方三个层级。但囿于“水系空间”的定位,流域事权长期附属于中央和地方的水管理事权。尽管现行《水法》确立了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将流域作为法定的事权层级。但事权层级的法定化仅是基础和形式,其目的和实质是将各层级的事权通过立法配置给相应的主体。根据既有立法规定,中央层级的事权具体分配给中央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地方层级的事权具体分配给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而流域层级的事權,虽然形式上依法配置给了“重要江河的流域管理机构”,但其具体事权配置的结果并没有实现充分的法定化。事实上,长江流域早已设有“流域管理机构”——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但“长委”仅是水利部的派出机构,虽名为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其事权实则源于水利部的“三定方案”和交办事项,缺乏充分的立法授权。故所谓的流域管理,本质上仍从属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水管理;所谓的流域层级事权,实际上处于一种虚化、弱化的立法状态。
2.2 内容维度——仅针对单一“水”要素
与域外流域立法的情况类似,我国的流域立法最初也是“单项立法”。其表现为,立法中的流域事权仅为“水利事权”,如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抗旱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流域管理要求的提升,立法中流域事权的内容升级为流域水安全事权,并增加了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等新的事权内容。亦即,流域事权从“水利事权”升级为“水管理事权”。但囿于“水系空间”的定位,虽然流域事权的立法内容不断丰富,却始终未超出单一“水”要素的范畴。诚然,流域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形成的,但域外流域立法综合化的发展规律表明,水不是流域空间内的唯一要素,流域事权也并不局限于水管理事权。例如,美国的流域管理就已从单纯的水管理,已扩展至与水相关的土地利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领域[2]。长江作为中国最大的流域,是一个复杂超大的巨型生态系统。目前这种“就水论水”的事权立法配置状态,没有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着眼,缺乏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统筹[3]。例如,当前长江沿线化工污染整治和水环境治理、固体废物治理之间明显存在关联,仅通过立法加强水污染防治方面的事权配置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3 空间维度——对流域特殊性问题缺乏针对性事权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病了”。从空间分布的角度看,长江的“病症”是:长江源头、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两湖”、饮用水水源地等“点”的问题不容乐观;沿岸“化工围江”,航道、河道安全存在隐患,沿江污染带分布广泛等“线”的问题较为突出;面源污染加剧,流域内河湖生态功能退化等“面”的问题长期存在。这些“病症”是在长江流域这一特殊空间存在的,属于流域特殊性问题。因此,《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中央立法难以进行特殊规制,流域内各级地方立法则是力所不能及,仅有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两部行政法规也不可能给予充分的事权配置。不仅如此,相关立法受制于“水系空间”定位下“点”和“线”的范围限制,对“面”的问题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而流域的问题“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上”,“面”的问题不解决,“点”和“线”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治。
2.4 性质维度——片面强调事权关系的单向服从
流域空间的整体性,是点、线等组成部分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故下级服从上级、区域服从流域、地方服从中央的“单向服从模式”,成为流域政府间事权立法配置的基本原则。但是,对于长江这样一个跨区域、跨部门(行业)的流域而言:①政府间事权关系中如果只有纵向服从,可能导致流域管理中地方投资和积极性下降[4]。不仅增加了中央、流域的事权负担,也不利于流域内各区域、各领域(行业)的均衡发展。②流域内相关部分间不仅有“纵向”关系,上中下游、左右岸、不同行业之间还存在“横向”关系。立法中缺少对于“横向”关系的考量,割裂了相关部分之间的天然联系。加之事权本就有行政边界性,地方层级的事权主体难以超越本区域或领域而考量其他区域或领域的事务。以致在长江流域管理中不同行政区域、部门(行业)的职能被“条块化分割”,职责交叉重复,“扯皮推诿”现象严重[5]。
3 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立法配置的理论重构 欲破解上述问题,就要重新厘定长江流域事权的“范围”,其关键是对长江流域空间的识别进行理论重构。但长江并非中国唯一的流域,既有立法中“水系空间”的定位虽有缺陷,但却高度凝练了各流域空间的“共性”,保障了事权立法配置结果的普适性。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驱动力,促使长江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流域空间识别理论。那么,理论重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均会受到质疑。当前,这种理论重构无疑已经具备了特殊的驱动力,其源于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
作为这一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空间格局。其实质,是以长江流域的“黄金水道”为核心,流域内相关要素在上中下游、东中西部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意味着,长江流域被赋予了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功能。为了下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先手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空间管控单元”。可见,国土空间布局是落实长江经济带功能定位及各项任务的载体。作为长江经济带的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对长江流域空间的判断必然要超越“水系空间”的范畴,升级为涵盖19省(区、市)全部空间范围的“国土空间”。显然,这是一种超越一元空间观的多元空间观。据此,长江流域应定位为一个以水为核心要素和纽带,由水、土、气、生物等自然要素和人口、社会、经济等人文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共同构成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复合性空间[6]。这就使得对长江流域空间进行重新定位,具有了一般流域不具备的改革需求和决策支撑。不仅对长江流域空间识别的理论重构形成巨大的驱动力,更为理论重构确立了一种新的空间观基础。结合域外流域立法相关规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上述改革需求和决策支撑亟需以长江流域专门法和特别法的形式得以实现。
3.1 重构长江流域管理主体,实现流域层级事权从虚化、弱化走向实化、强化 长江流域当前所处的特殊重要战略地位和功能,特别是国土空间的新定位,客观上要求加强全流域完整性管理。既有立法对长江流域层级事权的配置,特别是对“长委”的职能和定位,既非真正意义上的流域层级事权,也无法满足长江流域层级事权配置的新需要。这就要求,《长江保护法》应加强事权在流域层级的配置。重点是重构长江流域管理体制,明确长江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并为其配置相应的流域层级事权。显然,此“长江流域管理机构”非《水法》意义上的彼“流域管理机构”。①其定位不再局限于水利部的派出机构,而应是由法律授权、代表长江流域整体利益的法定事权主体。②其功能不再局限于技术服务,而是必须配置与其职能定位相适应的流域层级的法定事权。其内容不再局限于水利,而是涉及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甚至包括必要的非涉水流域管理事务(如工程建设等)。
3.2 充实法律制度的类型,实现事权内容从水管理走向涉水管理 从立法的角度讲,每一种事权的内容理论上对应一种法律制度的类型。囿于既有流域立法没有摆脱“单项立法”的状态,将事权局限于水管理事权。相应地,法律制度的类型也相对单一。如今,对长江流域这一特殊“国土空间”的管理,是对“涉水”要素载体的综合管理。从事权内容的角度看,立法中所涉事权的类型必然包括但不限于既有类型。由此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法律制度体系中应当包括哪些具体类型;其二,各类法律制度应以何种先后顺序形成体系。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结合长江流域涉水要素保护、开发、利用、管理现状,从内容的角度对长江流域“涉水事权”进行类型化及逻辑排序。具体而言:
(1)规划是流域管理的龙头,规划事权是各类具体事权的源头,故流域规划制度应是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起点。
(2)水安全保障始终是长江流域管理的“头等要务”,因而水安全类事权是其他事权存在的基础,流域水安全保障制度在法律制度体系中处于首要地位。
(3)“共抓大保护”是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长江流域一切活动均不得以损害生态环境为底线。鉴于生态环境保护类事权对长江流域而言特殊重要,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制度在法律制度体系中处于优先地位。
(4)保护和改善水环境质量,是长江流域以水为核心所构成的国土空间生态环境状况的重要保障。水污染防治类事权作为保护和改善流域水环境的核心抓手,是长江流域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事权内容。其应置于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制度之后,形成从“系统保护”到“核心要素保护”的递进式制度体系设计。
(5)“不搞大开发”绝非单纯保护,而是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开发。同时,开发利用的对象不限于“水资源”,而是长江流域的“涉水资源”。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涉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事权的存在,对于实现长江流域的绿色发展而言无疑是必要的。因而,在前述制度体系顺次建立和展开的基础上,流域涉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制度也是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专设流域特殊性法律制度,实现事权的空间维度从二维走向三维 “国土空间”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概念,是空间内各类要素的系统性载体。对于长江流域这一特殊的“国土空间”而言,不仅包括流域内重要水体等“点”、长江干支流等基本的“线”,还应扩展至流域国土空间的“面”。为应对前述流域特殊性问题,《长江保护法》应专设流域特殊性法律制度,从“点”、“线”、“面”三个维度进行事权配置。
(1)对于某些流域特殊性问题而言,需要超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从全流域的高度进行管理。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因其地位相对超脱且为流域整体利益的代表,应当由其对此类问题实施直接管理。
(2)另外一些流域特殊性问题,因其往往跨区域、跨部门(行业)而涉及的主体众多、利益关系复杂。故立法应当对所涉相关政府间的事权加以统筹配置,并建立利益沟通与协调机制。对于此类问题,长江流域管理机构虽不是直接管理者,但应当通过相应的事权配置,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3.4 建立配套法律制度,实现事权性质从单向服从走向互动协同 前文已述,长江流域空间内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以水为纽带形成的互动关系,决定了《长江保护法》中法律制度体系所涉事权性质上也必须是多元且互动协同的。①地方、下级事权的存在和運行,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上级事权的权威。因此,事权配置的过程中涉及央地关系、上下级关系的,性质上必然需要以权威型事权配置作为基础,如下级规划对上级规划的服从、流域统一调度权等。②中央、上级事权的权威性,不仅体现在立法表述中的“应当”和“必须”上,还必须通过目标考核、环保督查、约谈问责等压力传导型事权,对地方、下级事权进一步产生实际作用。③各级、各类政府事权主体之间,在流域管理中还需要通过协调议事、执法协作、联合执法、信息通报等进行必要的合作与协商。在此过程中,事权在性质上明显更加丰富,即在权威型与压力传导型事权之外,增加了合作协商型事权。④在合作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设定资金投入、生态补偿、行政奖励、基金等激励型事权,引导地方或下级主动、积极地实现流域管理的目标。权威型、压力传导型、合作协商型、激励型四种性质不同的事权在立法中的综合运用,共同构成了保障前述各类法律制度运行的配套法律制度。
4 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立法配置的具体路径 基于对长江流域从“一元水系空间”到“多元国土空间”的理论重构,结合“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层次性理论”,在构建和展开上述法律制度体系的过程中,长江流域政府间事权配置的具体路径为:
4.1 中央层级事权
长江不仅是跨行政区域的巨型流域,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支撑,其对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保障有重大意义。因此,长江流域事权中必然包括中央层级的事权。其主要包括:
(1)重大事项决策权。所谓重大事项,既包括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江流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如重大政策、战略规划等),也包括某些对长江流域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项目审批(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作为长江乃至国家的重大事项,其决策权应当且只能依法配置给中央政府。甚至,某些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政策、规划、项目,其决策权依法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以获得最大的决策合法性。
(2)重大流域性事务协调权。所谓重大流域性事务,是指涉及跨部门(行业)、跨省(区、市)的具体流域性事务。例如,跨省界水事纠纷的协调处理、流域干支流控制性水库群联合调度、流域内上下游邻近省级政府间建立水质保护责任机制等。此类重大事务也必须由中央政府(及其建立的相关协调机制)从国家和长江流域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在相关主体间进行必要的组织与协调,以推进相关事务的实施。
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某一类流域涉水事务的中央统管权。此类统管权,既包括本领域流域性事务的中央决策权、协调权(如各类流域专项规划的制定),也包括本领域具体流域性事务的中央监管权(如流域内重大项目的审批等)。此类事权是事权横向配置中的最高层级,也是流域治理“九龙争水”的根源。经过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事权已经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思路进行了整合与重新划分。在此情况下,《长江保护法》应避免纠结于部门间“主管与分管”、“统管与配合”之争。而应参考“水十条”的明确列举模式,逐项配置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长江流域某一类涉水事务的中央统管权,使此轮事权改革的成果法制化。
4.2 流域层级事权
对于某些前述流域特殊性问题,中央政府不可能也无必要直接管理;中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囿于事权分工难以实现流域系统性管理;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则限于事权的地域性无法实施流域整体性管理。为避免条块分割管理的封闭性、自利性给流域整体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此类问题交由流域层级的事权主体——长江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无疑是最佳选择。此类直管事权主要包括:①控制性水工程的联合调度,流域重要水域、直管江河湖库及跨流域调水的监测等流域性“点”问题;②长江干流的河道采砂,长江干流、重要支流的取水许可等流域性“线”问题;③跨流域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应急调度,流域干流岸线的管理与保护,重点防治区水土流失的预防、监督与管理等流域性“面”问题。
作为流域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对直管事权之外的流域特殊性问题,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则需要与所涉相关主体实施交互加以解决。由于交互过程所涉事权如前所述包括权威、压力传导、合作协商、激励等四种类型。故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在“交互”中的事权包括:
(1)权威型事权的议题发起者。虽然决策事权由中央政府行使,但长江流域管理机构作为流域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应当通过组织或参与相关政策、规划、区划、行动方案等制定的方式,成为相关决策议题的发起者。
(2)压力传导型事权的监督者。虽然目标考核等压力传导型事权应由中央组织,但长江流域管理机构长期具备的信息技术优势与相对中立的地位,决定了其有权参与对流域内地方涉水事权实施情况的监督。
(3)合作协商型事权的协调者。作为流域整体利益的代表,长江流域管理机构既可以通过会商、协商等方式组织相关区域、部门进行利益的横向协调,又可以通过征求或提出意见等方式参加其他流域性事务的协调机制。
(4)激励型事权的参与者。技术、信息等不仅是流域内压力传导型事权实现的重要依据,也是流域内激励型事权实现的必要基础。因此,对于流域性资金投入、生态补偿、行政奖励等激励机制的运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其中。
4.3 地方层级事权
虽然“水”是界定流域空间的核心要素,但土地是流域范围划分的本体[7]。而行政区域正是以土地作为划分依据,从而实施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的特定地域单元,具有比较稳定的地理界限和刚性的法律约束[8]。因此,各级地方政府是长江流域的基本管理主体。其要对本行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负责,必然要管理本行政区域的资源环境要素,包括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涉水资源[9]。鉴于此,《长江保护法》中流域事权在地方层级上的分配,首先需要“打包式”地交由各级地方政府[10],由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流域管理“负总责”。
同时,考虑到各级地方政府在流域管理中的职能差异,立法应对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进行差异化配置:
(1)省级政府的事权配置。在流域层面,省级政府是本区域權益的“对外”代表。对于涉及本区域的流域性事务决策事权,省级政府应当有权参与。在本区域内,省级政府不仅承担总体负责相关法律、政策以及中央和流域决策的执行事权,还承担本区域内流域涉水事务,落实各项指标,分解相关任务的组织和领导事权[10]。
(2)市、县级政府的事权配置。市、县级政府具有相关法定职能部门及相应的行政执法权。因此,与省级政府相比,除不具备参与流域性决策的事权外,其在本区域内同样承担着执行上级决策和组织领导本级流域管理的双重事权。
(3)乡、镇级政府的事权配置。作为一级地方政府,乡、镇级政府应当对本级流域管理负总责。但是,其既无法定的职能部门,又缺少法定的行政执法权。因此,立法应为其配置“协助事权”,即协助上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做好辖区内农村饮用水安全、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
在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事权的立法配置。在既有立法对各级、各类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流域事权已经完成初步配置的情况下,《长江保护法》的重心在于:①结合相关立法及长江流域管理的实际情况,通过区分事权的主体和级别(如“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各级、各类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间的事权进行精确配置,使其适时、适当、适度参与本级流域管理。②对各级、各类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相关事权之间存在的矛盾或冲突之处,提供解决矛盾或冲突的确定性指引。③对各级、各类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事权的范围仍存在模糊甚至立法空白的领域,进行充分、有效的弥补。
(編辑:于 杰)
参考文献
[1]刘剑文, 侯卓. 事权划分法治化的中国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2):102-122, 207-208.
[2]US EPA. Identifying and protecting healthy watersheds: concepts, assessments,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R]. Washington DC: US EPA, 2012.
[3]习近平.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 新华日报, 2018-06-14:1-2.
[4]邢利民. 国外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做法及其经验借鉴[J]. 生产力研究, 2004 (7):107-108.
[5]王树义, 赵小娇.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商共治模式初探[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8):31-39.
[6]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国际水资源管理经验及借鉴[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95.
[7]晁根芳, 王国永, 张希琳. 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建设研究[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1:2.
[8]汪阳红. 正确处理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J]. 中国发展观察, 2009(2): 24-26.
[9]高而坤. 谈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J]. 水利发展研究, 2004(4):14-19.
[10]吕忠梅, 张忠民. 现行流域治理模式的延拓[M]//吕忠梅. 湖北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报告(2014).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40.
Study on the legislative alloc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for Yangtze River Basin
LIU Jiaqi
(Law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how to realize the alloc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for Yangtze River Basin is the core theoretical issue for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gal system.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onsists of water as the core material element, and the authority of which has its own particularity. It needs basing on the space concept , from the certain space concept of hierarchy, content, spatial dimensions, properties, identifying for this particular Basin space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the authority, thereby to proceed the legislative alloc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Basing on single space concept,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regards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s the ‘river system space. That leads to legislative allocation of authority existing authoritys emptiness and weakness at basin level, and just directing at single ‘water elements, lacking of nichetargeting authority allocation for the Basin issue, onesided emphasizing on oneway obey of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has already become space base and material suppor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t provided the special driving for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recognition theory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pace. Whereas, territorial spatial layout is the carrier of implementing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the various task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hould be upgraded to ‘territorial space that views water as the core elements under multivariate space concept from the ‘river system space under the single space concept. Hereby, in the process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①Allocating corresponding authority respectively for three levels, which are the central, river basin and local. The key point is to reconstruct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deploy corresponding basin level authority for Yangtz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subject. ②Establishing five basic legal systems such as river basin planning, water security,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wading resources sustainable use in proper sequence. ③Aiming at the proper issues of ‘point, ‘line and ‘fac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designing particular legal system for the river basin to allocate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④Legitimately allocating four types of governance such as authoritativeness type, pressure transmitting type, cooperation and negotiation type, incentives type and so on at all levels and all kinds of intergovernment to form the correlative legal system.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Basin; authority; river system space; territorial space; legal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