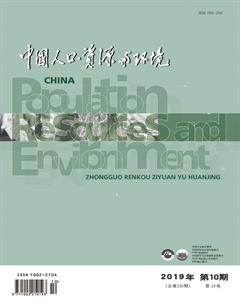建立“绿色发展”的法律机制:长江大保护的“中医”方案
摘要 《长江保护法》已列入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并已启动了立法工作。但各方面对《长江保护法》的性质定位、价值取向、制度架构等一些关键问题还缺乏基本共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建设需要“中医”方案的理念,《长江保护法》的制定也需要通过对涉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进行“体检”,发现各种“风寒”症状、找到“经脉”淤堵点、研究“脏腑”调理方,确保出台一部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引、以“治未病”为价值取向的高质量法律,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良法善治”提供基础。本文认为:①已有涉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立法涉及多层级、多机关、多法律关系,各种规范的出台背景、价值取向、核心内容、制度体系缺乏协同性,所导致的权利冲突是造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恶化的制度原因,必须妥善解决。②解决现存的权利冲突,需要为长江保护专门立法,而为长江立良法的前提是确定长江保护法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目标,应通过法律语言的转换,具体化流域安全、流域公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价值取向。③长江保护立法是在一定价值取向指引下对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等立法资源的配置过程,从立法技术和方法上 ,应注重优化立法资源,厘清长江保护法的基本概念,合理借鉴国外经验,明确立法技术路径;按照发展与环境综合决策原则,合理配置政府事权,建立实现“绿色发展”决策体制;建立以实现绿色发展为目标的多元共治机制,广泛鼓励公众参与。
关键词 长江保护法;权利冲突;立法价值取向;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 D922.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10-0001-10 DOI:10.12062/cpre.20190702
2018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这要作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先手棋”[1]。并明确要求在对母亲河做一次大体检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从源头上系統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整体预案和行动方案,然后分类施策、重点突破,通过祛风驱寒、舒筋活血和调理脏腑、通络经脉,力求药到病除;要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空间管控单元,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做到“治未病”,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阐释了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价值观,也说明了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方法论。将“中医”方法运用到法律上,需要对涉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各项法律制度进行“体检”,发现各种“风寒”症状、找到“经脉”淤堵点、研究“脏腑”调理方,为正在制定的《长江保护法》提供法理支撑,确保出台一部以中医整体观为指引、以“治未病”为价值取向的高质量法律,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良法善治”保驾护航。
1 母亲河生态环境之痛:法律何以解忧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在重庆召开第一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长江经济带建设“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以来,中央和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在强化顶层设计、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通过出台《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及10个专项规划完善了政策体系;扎实开展系列专项行动整治非法码头、饮用水源地、入河排污口、化工污染、固体废物,基本形成共抓大保护的格局;采取改革措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势头,长江经济带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超过了45%;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聚焦民生改善重点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长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2018年,生态环境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进行了暗访、暗查、暗拍,对长江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体检”,在约10万km的行程中,发现了许多沿江地区污染排放、生态破坏的严重问题,一些地方并没有真正改变粗放的发展模式,在环境治理方面能力不足明显。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当务之急是先“止血”,抓好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2]。
1.1 长江保护法目标明确
吕忠梅:建立“绿色发展”的法律机制:长江大保护的“中医”方案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年 第10期2019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长江保护修复的目标是:到2020年底,长江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的国控断面比例达到85%以上,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的国控断面比例低于2%;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比例达9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高于9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行动计划》提出了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整体方案:“以改善长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长江干流、主要支流及重点湖库为突破口,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两手发力,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突出工业、农业、生活、航运污染‘四源齐控,深化和谐长江、健康长江、清洁长江、安全长江、优美长江‘五江共建,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执法,落实各方责任,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确保长江生态功能逐步恢复,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奠定坚实基础。”为此,必须“强化长江保护法律保障。推动制定出台长江保护法,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全面系统解决空间管控、防洪减灾、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航运管理、产业布局等重大问题提供法律保障”[3]。这表明,《行动规划》不仅为长江生态修复建立了目标导向,而且也提出了明确的立法需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长江保护立法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两手发力”“三水共治”“四源齐控”“五江共建”的要求转化成为有效的法律制度。
1.2 长江保护立法共识尚未达成
长江保护法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类项目,已列入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并已启动立法工作,成立了由全国人大人口与环境资源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组成的《长江保护法》领导小组,制定并通过了《长江保护法》的立法工作方案[4]。这意味着《长江保护法》的制定已真正进入“快车道”。但如何做到立法既要快些、更要好些,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5]。
实际上,近两年有三个承担相关研究的课题组以专家建议稿的方式提出了长江保护法草案建议稿,从不同角度设计了长江保护法的制度体系①。今年,《长江保护法》立法领导小组各参加单位也在努力工作,开展了多项立法调研、理论研讨和征求意见工作。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各方面对《长江保护法》的性质定位、价值取向、制度架构等一些关键问题还缺乏基本共识。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应得到妥善解决。否则,既可能影响《长江保护法》的立法进程,更会影响《长江保护法》的立法质量。虽然《长江保护法》的立法指向非常明确——为保护长江立法,但对如何在我国已基本建成的法律体系中确定《长江保护法》的“定位”是关键,否则无法妥善处理《长江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与任务;虽然立法的本质是与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关的各种利益的博弈与协调,但对各种利益的判断与选择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否则无法建立符合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所需要的法律秩序;虽然长江保护修复的各种政策指向、经济方法、技术措施、监管目标已经明确,但《长江保护法》不能把各种政治、经济、技术、管理手段简单“搬家”,否则无法形成符合法律运行规律的理性制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长江保护法》的制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需要这部法律,而是我们制定一部什么样的《长江保护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6]。
1.3 长江保护立法的不同思路
如果说,任何立法都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切一刀;那么,对《长江保护法》而言,切好这一刀却十分不易[7]:一是长江保护立法作为流域立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没有“位置”[8],如何在立法依据较为欠缺的情况下确定长江保护法的定位,需要慎重考量;二是长江大保护的“两手发力”“三水共治”“四源齐控”“五江共建”综合性立法需求,与我国现行的分散式立法模式存在冲突[9],如何在立法基础十分薄弱的现状下创新立法思維,需要勇气担当[10];三是长江保护立法的制度体系建构缺乏相对成熟的法学理论,如何从法理上和逻辑上解决长江保护立法的制度设计,需要法律智慧[11]。
面对“长江病”,从法律上也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一种是“西医”方案,针对已经产生的长江生态恶化问题,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标准,限制甚至禁止各种可能影响长江生态环境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最终将既遏制长江生态恶化的趋势也扼制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这显然不能体现“绿色发展”的理念,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另一种是“中医”方案,根据长江生态恶化的现实状况,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在以最严格制度保护长江的同时,通过实施长江经济带空间管控单元、实行生态修复优先的多元共治等方式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长江经济带的关系,既突破生态环境问题重点实现“药到病除”,也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做到“治未病”,这才是我们的期待。
其实,长江经济带的现状表明:生态环境恶化是“病征”,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搞大开发是“病因”,缺乏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和系统性治理理念是“病根”,因此,按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方式,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必须运用“中医”的辨证施治和系统调理方法,把脉问诊开“药方”。从法律上看,要拿出一套“中医”方案,必须首先认真梳理涉及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保护的各项权利,发现权力配置的“寒热征”、找到权利运行的“淤堵点”,然后才可能辨证施治,提出“祛风驱寒、舒筋活血”的运行机制策、开出“调理脏腑、疏通经脉”的流域立法方。
2 长江病的法律之因: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权利冲突 法律上的权利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具有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之间,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权利之间的不和谐或矛盾的状态[12]。权利冲突既有同类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不同类型权利之间的冲突[13]。产生权利冲突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实质是权利背后的价值、利益冲突。从立法的角度看,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前提是对冲突的权利进行价值识别、判断和选择,在确定价值判断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明晰权利边界、确定权利顺位等方法,以解决权利之间的矛盾问题[14]。 制定一部高质量的长江保护法,前提是对长江经济带建设所涉及的各种权利是否存在冲突以及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①。
2.1 水资源开发利用权利冲突具有世界普遍性
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环境要素和劳动对象,是法律上权利最密集且最容易产生权利冲突的领域,水权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中最为复杂的权利体系[15]。 尤其是水作为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具有明显的流域特性且与所处地理位置的生物种群、气候条件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独特流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共同孕育了人类的不同文明[16],因此,与水资源利用有关的权利冲突也呈现出明显的流域特性。
纵观人类的水资源利用史,水的资源属性与利用方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丰富多元,各种权利也相伴而生。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以后,农业的灌溉需要对水资源开始了建水库、修水坝、打水井等控制和管理性利用,为了保障这种利用的独占性和排他性而产生了设定用水秩序、平衡用水利益冲突的需要,“河岸权”[17]得以产生。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水资源利用方式不再局限于农业灌溉,将水作为土地附着物的“河岸权”无法满足水资源利用多元化的需要。于是,逐渐产生了独立的水权利,如先占优先权、取水权等新的权利,水权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18]。但是,这些权利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基础上的私权,较少涉及公共利益[19]。进入20世纪以后,科技的不断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人类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认知更加全面、更加多元化,在对水资源的控制与管理更加强化的同时,也加速了对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一方面,人类对水的利用从水量扩展到水能、水域空间、岸线、水环境容量、河床砂石、河道航道、水生动植物等各个方面,并不断突破水资源的时空束缚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以对水资源进行管控,进而延伸出了对水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模式及权利[20],包括水资源利用在内的综合性权利——发展权②诞生[21];另一方面,水资源的污染与破坏日益加剧,水质性缺水、工程性缺水、生态性缺水问题如影相随,对个人权利的绝对保护导致公共利益的损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水危机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①,要求保护健康环境的环境权②逐渐成熟[22]。这些不断出现的新变化使得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权利冲突不断涌现,对传统的水资源利用秩序造成剧烈影响。
2.2 长江流域资源开发利用的權利冲突具有特殊表现形式 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兴水利除水害是历朝历代政府最重要的职能,虽然很早就有了涉及水资源利用的《田律》,规定了遭受水旱灾害必须报告,以及禁止在春天捕鱼等内容,但主要是刑法,私法意义上的水权在中国传统法律中没有出现[2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水利是农田的命脉”(毛泽东同志为“红旗渠”题词)的指导思想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围绕农业发展所进行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也主要是由政府组织。从法律上看,我国是公有制国家,实行自然资源全民所有制,根据宪法和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③;但在立法上一直没有明确宪法上的“国家所有”与民法上的“国家所有”的关系。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如土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取水权、渔业捕捞权、渔业养殖权等民法上的用益物权制度并不明确,我国在立法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水权体系[24]。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下,长江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两个突出特征:一是长江流域资源实际上成为中央各部门行政权的标的,长江流域资源开发利用权的取得、行使、终止都是采取许可、划拨、确认、收回等行政性手段。二是横跨大半个中国的长江流域资源实际上为地方占有并使用,流域开发利用权并未真正受到国家所有权的制约,中央和地方对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及其利益呈共享关系。这实际上是长江流域资源开发利用“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法律原因。
现行相关立法中,与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国家法律既有《水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和《水土保持法》等“涉水四法”,也有《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节约能源法》《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在行政法规层面有《防汛条例》《河道管理条例》《长江河道采砂条例》《水文条例》等行政法规,在部门规章层面有《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长江流域大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办法》《长江流域省际水事纠纷预防和处理实施办法》《长江水利委员会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初步建立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污染防治、防洪减灾、水土保持、节水与水资源配置和调度、河道资源管控、流域水事纠纷处理等多项制度。从理论上讲,这些法律法规都应该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依据,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法律的赋权可在不同空间对不同形式的资源利用其不同功能,应该可以形成各得其所、和谐融洽的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秩序。但因为这些立法涉及多层级、多机关、多法律关系,各种规范的出台背景、价值取向、核心内容、制度体系缺乏协同,各种权利间的关系在缺乏必要统筹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清晰界定,必然导致实践层面的诸多法律冲突。经过对涉及长江流域事务管理的30多部法律授权的梳理,我们发现长江流域管理权分别属于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其中在中央分属15个部委、76项职能,在地方分属19个省级政府、100多项职能[11]。这种状况极易导致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权利冲突:一方面是“法律打架”,各种法律规定相互各主体在依法依规行使各自的权利时无法有效控制其外溢性影响,使得基于权利的不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出现相互矛盾甚至剧烈的冲突,进而影响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秩序的稳定。这些冲突在法律层面表现为权利的不和谐和矛盾,在事实层面表现为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结果相互抵牾甚至抵消。
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不同主体的权利界限不明确,权利间的关系不清晰,导致冲突不断。在流域层面,《水法》建立了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也在具体制度中对流域机构授予了制定流域综合规划、水功能区水质监测、新建排污口审核、水量分配和应急水量调度、取水许可审批等权限。但是,《水法》多处使用“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的表述,但未明确水行政主管部门与流域管理机构权限的划分标准或者适用条件。在地方层面,《水法》第12条第4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但没有明确不同层级水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权限”的划分方式及其相关程序,导致各地方“三定方案”规定职责权限差异很大。在中央各部门间,存在许多重复授权、交叉授权、空白授权,使得规划编制、水量与水质统一管理、水工程管理与水量调度、水道与航道管理等方面的权力出现了诸多矛盾和冲突[11]。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水污染防治法》与《水法》都做了相应规定,但两部法律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虽然都使用了“统一管理”的术语,但生态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统一监管的职权与水利行政部门对水量与水质统一管理的职能之间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①;虽然都设置了流域管理的相关制度,但其授权范围与权力行使方式缺乏协调与衔接,两部法律所指称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和“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并非同一机构②;导致区域管理中开发利用的“实”与流域生态保护中无人负责的“虚”现象大量存在。长江流域有特殊的生态系统,其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与历史上形成的开发利用方式和产业布局直接相关,在与长江流域资源保护有关的制度方面,还存在着流域整治、水能资源开发与保护、航运与渔业发展统筹、长江沿岸入河排污指标分配、排污总量控制、洲滩与岸线利用与管理等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真空”[11]。这导致了一些制约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大问题:长江上游主要是支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无序;中下游较为普遍的存在河道非法采砂、占用水域岸线、滩涂围垦等行为,蓄滞洪区生态补偿机制缺乏;河口地区咸潮入侵现象有所加剧、海水倒灌和滩涂利用速度加快;跨流域引水工程的实施,导致流域内用水、流域与区域用水矛盾日趋显著[11]。
正是由于法律上的权利配置呈现出区域权利强与流域权利弱、流域资源开发利用权利大而实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权利小而虚的巨大反差,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为追求自身的发展目标而忽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导致了“长江病”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核心在于通过界定权力边界、畅通权利运行机制,妥善消除各种权利之间的冲突,实现长江流域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协调发展。
3 消弭权利冲突之根:确定长江保護立法的价值取向 法律具有行为规则和价值导向的双重功能,任何立法活动都不是单纯的规则制定过程,而是通过立法活动表达、传递和推行一定的价值目标或价值追求。如果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是法律上的权利严重冲突导致的事实后果,缺乏专门的长江立法是客观原因,那么,为长江立法尤其是立良法的前提是解决立法的价值观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要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做法。有的同志对生态环境保护蕴含的潜在需求认识不清晰,对这些需求可能激发出来的供给、形成的新的增长点认识不到位,对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路径方法探索不深入。一定要从思想认识和具体行动上来一个根本转变”[1]。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推动长江经济带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长江保护法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利益的取舍、规则的设计都必须以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目标,这个目标可具体化为流域安全、流域公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价值取向。
3.1 确立价值取向是长江保护立法的内在需求
从立法活动的规律看,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外部强加于立法者的,而是由立法这一特定的实践活动的品格所决定,其本质是人类在立法时对利益追求的取舍[25]。立法的价值取向的首要功能是明确这个立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长江保护法是针对长江流域的立法,其核心是把过去的以部门和区域为主的法律具体化为针对长江流域问题的法律,它既与原有的国家以部门职责分工为主的条条立法不同,也与地方主要以所辖行政区的块块立法不同,是既跨部门也跨区域的立法(我将长江保护立法喻为“横切面”立法,它是我国过去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层次中所没有的一个中间立法层次,法学理论对于流域立法的研究非常有限)。按照长江经济带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目标,长江保护法的主要任务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解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法治抓手问题,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建立长江流域的功能、利益和权力的协调和平衡机制;三是建立新的适应流域治理变革所需要的治理体制机制[9]。这意味着长江保护法必须处理好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流域与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法律传承和制度创新的关系,面对这样一种新的立法形态、复杂的立法任务,迫切需要形成普遍认同和追求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目标并用以指导整个立法活动,以保证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博弈、权衡和选择的方向一致、判断一致、结果一致。
明确的立法价值取向,可以在出现法律追求的多个价值目标出现矛盾时,通过价值界定、价值判断来完成最终的价值选择。这既包括立法者是否能够对该项立法的应然价值予以接纳和接受;也包括当存在多重价值目标时的价值取舍和和价值目标重要性的排序[22]。长江保护立法在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由于长江保护立法的“横切面”属性,必须跨越传统民法、刑法、经济法的界限,综合运用各种法律调整手段,融法律规范、国家政策、政府行为规制等目标于一体,其应然价值是什么尚存巨大分歧(目前各方面提出的长江保护法立法建议存在从定位到结构、从价值到制度的巨大差异,就是对应然价值缺乏共识的现实写照),立法者应接受或接纳何种价值目标亟待明确。由于长江保护法是围绕开发利用和保护长江水资源的各种社会关系展开,原有的可适用于长江流域的法律众多,这些立法的价值目标多样,也许就单个立法来看都十分正确,但适用的结果却因多重价值目标之间的矛盾而导致权利严重冲突,如何对这些不同立法的价值目标进行价值取舍并明确价值目标重要性的排序,也是必须尽快加以解决的问题。
3.2 安全、公平、可持续发展应成为长江保护立法的基本取向 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目标要求与生态环境的严峻现实之间的张力看,制定长江保护法的根本目标是确保不因长江经济带建设而导致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崩溃。换言之,如果没有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就没有长江经济带。但现实的情况是,长江流域所面临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依然存在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流域的整体性保护不足、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加剧。生态系统破碎化,大量的生态空间被挤占;自然岸线的过度开发;水土流失问题严重。二是水污染物排放量大,治理水平有待提高。长江每年接纳的污水占全国总污水排放量的2/3,单位面积的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值的2倍;部分支流污染严重,滇池、巢湖、太湖等湖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比较突出。三是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矛盾突出,长江资源环境严重透支。非法采砂屡禁不止,自然河道破坏严重;水电资源过度开发引发环境问题突出;矿区分布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高度重叠。四是环境风险的隐患多,饮水安全保障压力大。主要干支流沿岸高环境风险工业企业分布密集;危险化学品运输交通事故引发环境污染风险增加。五是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绿色发展相对不足。上中下游各个地方加快发展的意愿非常强烈,都希望布置工业区,布置沿江城市,重工业沿江集聚并向上游转移的势头明显。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制定的长江保护法,必须统筹考虑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关系,把生态修复放在压倒性的位置,真正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在立法原则上强调“保护优先”,为长江经济带开发利用设置生态红线、资源底线、经济上限。这些要求在立法上,应体现为安全、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
从安全、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看,在长江保护立法中,安全是基础价值,公平是基本价值,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价值。长江经济带建设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如果可以将对长江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简化为以“水”为对象的人类活动,但“水”本身却不简单,至少涉及到水生态、水岸、水路、水系、水质、水源等多个方面,从满足人类生存角度看,需要处理好生活水、生产水、生态水的关系;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需要协调上下游、左右岸用水、管水、排水的秩序;从自然生态角度看,需要面对水多、水少、水脏、水浑等灾害。为长江流域这样复杂的巨大系统建立能够满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需求的法律制度体系,必须将流域生态安全作为首要的基础性价值,任何有害于生态安全的开发利用活动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乃至禁止,否则,长江经济带将无所依托。在保障流域生态安全的基础上,各种开发利用长江流域资源的活动必须确保公平,在法律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长江流域东、中、西部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利益诉求,保证资源配置公平和权利保障公平,确保长江经济带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利益为全流域人民共享,能够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流域安全和流域公平的最終目标是为了实现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双重和谐法律关系,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确定了长江保护法的安全、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才可能将“以改善长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长江干流、主要支流及重点湖库为突破口,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两手发力,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突出工业、农业、生活、航运污染‘四源齐控,深化和谐长江、健康长江、清洁长江、安全长江、优美长江‘五江共建”的要求转化为有效的法律制度;也才可能保证长江保护法实现“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全面系统解决空间管控、防洪减灾、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航运管理、产业布局等重大问题提供法律保障”的立法任务。
只有确立了安全、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才能对现有的涉及长江流域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各种法律制度进行评估和梳理,明确有利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权利(权力)配置原则,建立以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目标的体制机制,完善能够针对长江流域特殊生态系统的法律制度。
4 长江保护立法之方: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法律机制 长江保护立法是在一定价值取向指引下对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等立法资源的配置过程,从立法技术上看,对立法资源的配置,既要追求一定历史限度内的公平,又要优化利用立法资源,以实现最大的立法效益与效率,坚持以良法促善治的高质量立法水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经济带应该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一是要深刻理解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内涵。共抓大保护和生态优先讲的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是前提;不搞大开发和绿色发展讲的是经济发展问题,是结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侧重当前和策略方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调未来和方向路径,彼此是辩证统一的。二是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三是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发挥农村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1]。实际上,长江保护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将这样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转化为法律制度,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法律机制。
4.1 优化立法资源,厘清长江保护法的基本概念,合理借鉴国外经验,明确立法技术路径 针对我国目前流域立法定位不清、立法少、理论支撑不足的现状,深化立法基础性概念、基本法律关系识别、法治类型构造等问题研究。立足流域空间的自然单元、社会经济单元与管理单元等多元属性,界定流域的法律属性,奠定长江保护立法的基础概念与逻辑起点。明确流域法律关系的特殊构造与具体类型,通过流域空间的法律化和法律的流域空间化构造,为长江保护立法构建“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认真研究域外流域立法的发展变迁规律,合理借鉴相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将域外流域立法所经历的传统法调整、现代流域立法产生和流域立法的综合化历史,法律上的流域空间逐步具备独立性、逐步推动水事立法体系整体性和综合性迈进的立法经验,以独立和综合性流域立法容纳和调整日趋复杂的流域法律关系的实践效果等,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尤其是长江流域实际予以扬弃。
深化对长江保护立法的理性认识,在检视我国现行的以部门为主导的分散立法模式、以中央和地方立法为主的直线性立法方式所存在的弊端和问题的基础上,认真研究长江保护立法的技术路线。采取“线性”立法和“横切面”立法并重方法,根据长江流域的多要素性(自然、行业、地区),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复合交融性等特点,充分考虑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的关联性、与经济发展的同构性、流域治理开发保护与管理的特殊性,从产业聚集、国土空间、水资源配置等多方面设定绿色发展的边界、确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性制度,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回应长江流域特殊的区位特征、特殊流域特性与特殊水事问题对立法的现实需求。
采取由立法机关直接立法或委托第三方提出立法草案方式,克服行政部门主导的立法弊端,以利于在立法中按照流域生态系统规律,把水安全、防洪、治污、港岸、交通、景观等问题一体考虑,综合运用私法和公法手段,建立长江流域资源统一配置、统一监管制度,切实解决沿江工业、港口岸线无序发展的问题,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布局、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确保长江流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对“权利——权力”的合作性制度安排,建立流域治理与区域治理相互协作、流域圈与行政圈的有机融合的法律机制。在流域发展与保护方面,统筹考虑科学利用水资源、优化产业布局、合理配置港口岸线资源和安排一些重大投资项目,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局部发展与流域整体保护的关系方面,将长江流域所涉的不同省份、区域,上下游、左右岸的不同主体、不同利益诉求纳入统一的法律制度,形成协同、协调的法律机制。从公共行政的效率性与合法性两个维度考虑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等政策目标通过合理方式进行有效的法律制度转化和建立法律与政策有机衔接机制,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在流域层面合理划分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部门事权、社会组织事权,实现政策与法律的有机统一,对长江流域事权的划分做出系统性、科学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为建立多元共治的长江流域治理体系提供法律依据。
4.2 按照发展与环境综合决策原则,合理配置政府事权,建立实现“绿色发展”决策体制 立足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权利冲突严重,尤其是权力配置缺乏协同与协调机制的现实,深刻认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寻找解决方案。针对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环境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政府决策过程缺乏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充分考虑,以及在政策和法律实施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利益的忽视、扭曲和不对称性的问题,按照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原则,梳理现行立法中涉及的多重社会“合法”利益的冲突并进行合理的选择、协调和平衡,按轻重缓急进行筛选和排序,进而列出可能解决的政策方案及战略选择,以及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价、调整与优化,形成综合决策过程。通过法律方法要求政府决策、计划、规划等决策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实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事前预防与源头控制,以替代以往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被动性事后补救、末端控制方法。
根据长江流域法律空间化和法律的流域空間化构造设想,改变既有立法的一元空间观,将长江流域视为“水系空间”。以法律方式消除过去事权配置存在的流域层级事权虚化或弱化、仅针对单一“水”要素及缺乏长江流域特殊针对性事权配置、片面强调事权关系的单向服从等问题。在长江保护立法中注重从层级、内容、空间、性质四个维度,注意通过识别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特殊性以确定事权的“范围”,进而在政府间进行事权配置。以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国土空间布局和长江经济带功能定位及各项任务为指向,建立“以水为核心要素的国土空间”理念并合理配置事权。从体制建设的角度,为中央、流域、地方三个层级分别配置相应的事权,重点是重构长江流域管理体制,为流域管理主体配置相应的流域层级事权。从机制建构角度,建立流域规划、水安全保障、生态保护与修复、水污染防治、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五类基本法律制度;从解决长江流域的“点”、“线”、“面”问题角度,设计专门法律制度。在各级各类政府间配置权威型、压力传导型、合作协商型、激励型等四类事权,形成配套法律制度。
通过有效的事权配置,建立良性的环境行政综合决策运行机制。通过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其领导的决策内容、程序和方式提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明确要求,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建设目标在决策层次上的法律化、制度化和具体化,确保在决策的“源头”(即拟订阶段)将“绿色发展”的各项要求纳入到有关的发展政策、规划和计划中去,为贯彻执行阶段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机制,要求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进行广泛的合作,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贯彻执行有关的政策与计划时,各部门通过相互协调、积极配合,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以有效防止各部门之间“争权夺利、推诿责任”,堵塞执法漏洞,不致再出现“有权的无力管、该管的没有权”的异常现象。通过事权配置,建立有效的决策监督体制,将各部门及其领导的决策行为置于长江保护法的监督之下,以有效防止相关部门滥用职权、超越职权,或躲避法律、逃避责任的行为发生;在决策者违反法律或构成犯罪时能够依法及时追究法律责任,敦促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依法行政,增强长江保护法的权威性,维护法律统一与尊严。
4.3 建立以实现绿色发展为目标的多元共治机制,广泛鼓励公众参与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26]。在长江保护立法中,采取“超常举措”,开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保护,最主要的方法是建立政府、社会、公民个人多主体参与、有序衔接的“小政府、强政府、大社会”共同治理模式。
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为共同利益,在法律上构建政府、社会、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维度、开放性共治系统,以对话、竞争、妥协、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共治机制,将多主体治理与协作性治理统合起来。确认政府之外的个人、企业、家庭以及各类社会组织机构的治理主体地位,倡导综合运用行政力量与其他社会力量、开展多种方式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并有效预防和化解由长江流域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等行为主体在长江流域多元治理中的不同职能定位和作用,以增强政府和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可能性、合作可行性以及合作效果为目标,克服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公地悲剧,建立政府与社会继续协作的兼容接口或连接点。针对长江大保护需要从单一行政性主导到多元共治的现实要求,建立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相关制度,确保“多元共治”体系下的环境信息公开、决策透明、环境责任主体明确,在政府主导的环境决策机制中明确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建立“多元共治”框架下的宣传教育、监督、风险评估与预警、风险沟通与冲突识别、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高度重视公众参与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作用。建立长江大保护的广泛公众参与和环境民主机制。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鼓励公众以个人或者参与社会组织的方式亲身参与,及时了解和掌握长江流域的环境质量状况,预防和应对有损自己和他人生态环境利益的环境违法政策;及时反映或反馈对政府决策的意见建议,加强公众与执法部门之间的了解与支持,减少消除相互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以通过法律的运行促进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强长江保护法的普及与教育,保证长江保护法的遵守与执行。
(编辑:于 杰)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C/OL]. [2018-10-19].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13/c_1122981323.htm.
[2]韓正. 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问题整改 齐心协力把共抓大保护要求落到实处[N]. 人民日报,2019-03-26(3).
[3]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 [2019-03-30]. https://www.sohu.com/a/291573996_99964894.
[4]程立峰. 将长江保护法纳入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C/OL].[2019-03-3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9/c_1124212522.htm.
[5]沈家本. 历代刑法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239-2240.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43.
[7]吕忠梅.长江保护法立法不易,立良法更重要[N]. 第一财经,2018-11-12.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9]吕忠梅,陈虹.关于长江立法的思考[J].环境保护,2016,44(18):32-38.
[10]吕忠梅.长江保护立法并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N].澎湃新闻,2019-03-12.
[11]吕忠梅.寻找长江流域立法的新法理——以方法论为视角[J].政法论丛,2018(6):67-80.
[12]王克金.权利冲突论——个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2):43-61.
[13]郭明瑞.权利冲突的研究现状、基本类型与处理原则[J].法学论坛,2006(1):5-10.
[14]张平华.权利位阶论——关于权利冲突化解机制的初步探讨[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6):32-45.
[15]崔建远.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J].法学研究,2002(3):37-62.
[16]吕忠梅,等. 流域综合控制: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机制重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9.
[17]王灵波.论美国水权制度及其与公共信托制度的区别与冲突[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2):186-191.
[18]崔建远,彭诚信,戴孟勇.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27-229.
[19]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J].中国法学,2001(2):91-102.
[20][英]史蒂文·米森、休·米森.流动的权力——水如何塑造文明?[M].岳玉庆,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334-336.
[21]汪习根.发展权法理探析[J].法学研究,1999(4):14-22.
[22]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J].法学杂志,2018,39(01):23-40.
[23]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J].文物,1976(5):1-6+99-100.
[24]吕忠梅.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36(6):106-115.
[25]吴占英,伊士国. 我国立法的价值取向初探[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3):10-15.
[26]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06-24(1).
Establishing a legal mechanism for green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Medicine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LV Zhongmei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Beijing 100811, China)
Abstract 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was listed into the lawmaking pl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2019 and the lawmaking work has starte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basic consensus on the nature, choice of values, framework of rules and other key issues of this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edicine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propos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Xi Jinping, the drafting of 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needs a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all laws and rul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o find the symptoms of ‘colds, the blocking places of ‘passages, and the adjustment methods for ‘internal organs for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the adoption of a law of high quality and guided by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values of curing the patients before the diseases develop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basis of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ollowing views: ①The incumbent rul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hierarchy of legal rules, adopted by different agencies, and applicable to different legal relations. There is no coordination as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s, choice of values, essential contents, and the system of rules. The conflicts caused by this lack of coordination is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s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ecosystem. This problem must be solved. ②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specia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The prerequisite for making a good law for Yangtze river is to ensure the choice of values for this proposed law. The of notion of ‘ecosystem first and green development proposed by SecretaryGeneral Xi Jinping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legal terms and embodied in the legislative values of catchmentwide security, catchmentwide fairness, and catchmentw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③The drafting of this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is a process of allocating legislative resources such as rights, obligations,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 to legislativ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optimization of legislative resources, to clarify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to reasonably learn the lesson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o specify the legislative roadmap. This law should reasonably allocate the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and establish a green development mechanism under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 decisionmaking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This law should establish a multisector governance mechanism with the goal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strongly encourage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conflict of rights; legislative choice of values; green development
① 据了解,目前已有不同研究团队提出了长江保护法草案建议稿,包括吕忠梅团队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基础上提出的《长江法草案(专家建议稿)》;环境规划院王金南院士团队在国合会课题研究基础上提出的《长江保护法草案建议稿》;长江水利委员会委托的“长江法立法研究”课题组提供的《长江保护法草案建议稿》。
① 本文为了行文方便,未对“权利”和“权力”进行明确区分,主要着眼于两者存在的一致性——追求一定利益为目的,都有相应的法律上的规定和限制要求等。实际上,在法律上,权利与权力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一方面,权力以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权利为目的;权利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等。另一方面,一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行使。
② 1970年,塞内加尔首任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提出了发展权的主张,他认为:发展权是所有个人和全体人类应该享有的自主促进其救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全面发展并享受发展成果的人权。此观点提出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被学者称之为“第三代人权”,在一些国际法文件中也得到了体现,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第2条指出:“人是发展的主体,因此,人应该成为发展权利的解决参与者和受益者。……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策,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这意味着,发展权应该是一项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权利。
① 水危机一直上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据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全球有近一半人口,约36亿人居住在每年至少缺水时长达1个月的地区,其中亚洲约占四分之三。而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增至57亿人。目前人类每年消耗4 600 km3的水资源,有7成用于耕作,2成用于工业,1成当为家用。报告称,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变化等因素,全球用水需求量在过去一百年内增加了6倍,并且该数值仍以每年1%的速度持续增长。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全球水循环将不断加剧,较湿润地区普遍变得更湿润,较干旱地区变得更干旱。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应聚焦“更环保”的政策,改善水资源的供应与质量。
② 20世纪50年代前后,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损害人群健康事件频繁爆发,其严重后果震惊世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68年7月30日通过第1346 (XLV)号决议,建议就人类环境问题召开一届联合国会议。1968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398 (XXIII) 号决议,人类环境质量的恶化可能会影响到“基本人权之享受”,故决定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目的是“鼓励各国采取旨在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以及补救和防止其受损害之行动,并对此提供准则”。号召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关于公民主张在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及其法律依据的研究和讨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环境权的各种学理主张。1972年,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如期召開并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该宣言原则一宣告:“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着尊严和幸福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环境的基本权利,并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环境的庄严责任。” 这被视为是环境权的标志性定义,也正式开启了环境权的实践。
③ 《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水法》第3条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① 《水污染防治法》第9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交通主管部门的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污染水域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农业、渔业等部门以及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水法》第13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② 《水法》第12条第3款规定:“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 《水污染防治法》第26条:“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工作机构负责监测其所在流域的省界水体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并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的,应当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机构。”矛盾;另一方面是“依法打架”,各执法主体越权执法、选择性执法、扭曲执法等问题不断,权利的行使与保障难以顺利实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