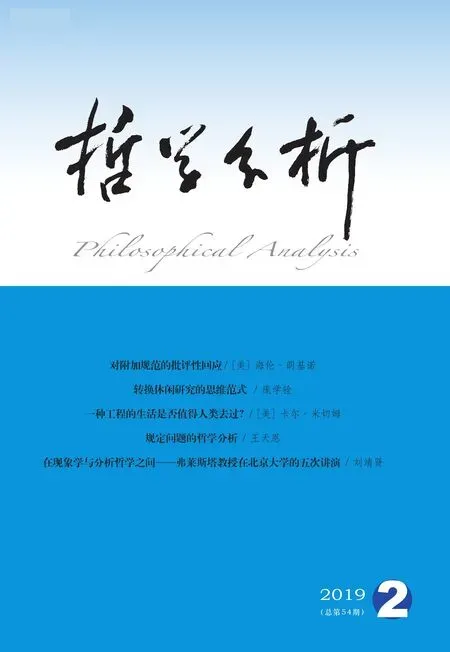对技术的现象学反思之进路
——兼谈人工智能a
汤 炜
近代以来,在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之下,人类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快速而深刻的转变。这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现代阶段,其特征性质被称为现代性。它表现为自然科学主义的观念形态和工具理性的技术化进程。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得现代人对其充满信心的同时也感到隐隐不安。现代战争的恐怖、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人被异化为机器和工具,只是现代技术自我扩张背后的贪婪和自我毁灭倾向的预兆。同样的矛盾感受也体现在人们对新近崛起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中。人们面对人工智能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对于技术的突飞猛进感到无比兴奋,好像人工智能即将改变整个世界和历史进程;一是迷茫和恐惧,不知道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这两种态度都可以在回顾现象学家对于技术的反思和批判中得到解 答。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认为欧洲科学主义的错误在于将普遍理性狭窄化为客观主义理性,将自然主义和数学化的视域作为现象显现的唯一方式强加于一切现象和事物之上。后期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继承胡塞尔批判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胡塞尔的局限性。他认为胡塞尔由于其理性主义的认知视野的局限性,尚未触及技术的更深的本质。技术的本质是存在(Being)在其开显和遮蔽的双重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特定揭示方式即“框架化” (enframinga后期海德格尔的术语,英文为enframing,指技术世界中事物以某种整体方式的齐整的秩序呈现。)。但海德格尔并没有详细论述存在如何具体地通过此在的参与使得技术在现代实现和显现出来。而真正回答这一问题并超越和突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是法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亨利指出,现代技术性只有在生命现象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理解,即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是生命在其呈现方式(即文化)中表现出的一种自我否定的特定样态——野蛮主义。至此,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亨利,现象学对技术主义的批判达到了其最终完成形态。
本文运用现象学对技术的思考讨论了人工智能技术,回答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两种态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状况已经证实了,由于非对象性的内在显现的生命是一切事物包括技术本身显现的源泉和先验条件,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技术对象化生命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热潮不但折射出技术主义对生命的否定和异化态度,还内在隐含了现代技术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技术扩张进一步侵入现实世界,并将人的生命活动驱逐出生命借以实现自身的劳动领域。只有恢复被技术社会忽视的生命现象的先验地位,让技术重新回到生命并为之服务,技术主义危机才可能被克服。
一、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反思
胡塞尔的一般现象学理念贯穿于他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当中。在其晚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中他对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都作了详尽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b要区分科学和科学主义,前者是人类面向自然的研究性实践活动,后者则不是具体科学活动而是某种整体性和物理主义的哲学主张或形而上学。当科学家声称世界是完全物质性的物理世界时,他实际上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在说话。批判科学主义并不等于批判科学。这一批判继承了他在《观念I》中提出的一般先验现象学的思想,即纯粹意识或先验自我作为一切现象显现的先验条件是世界中一切对象显现的根源和基础。先验自我或意识对于世界,总是有某种理解和某种意义的构造和生成。世界作为意识对象不是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所说的脱离意识现象的客观独立的物质存在,而总是作为意识对象已经向意识显现出来的世界,是先验自我或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构造物。现代科学主义宣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是客观的和绝对的,不依赖于任何意识和文化。
但胡塞尔指出,现代科学主义这个充满意义的视域仍然是在欧洲文化的历史中逐渐产生的,是先验自我意义构造的产物。他认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即客观主义和量化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伽利略。伽利略已经提出,唯一真实的存在是独立于人的感官在其之外的数学性和观念性的自在物质世界的。如果说在古希腊哲学那里,数学作为纯粹观念性的对象是超越于这个现实世界,那么从伽利略开始,这种观念性的存在又重新被拉回到现实世界,成为其内在本质。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了现代应用几何学。古代的人们已经在测量土地等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了几何学,但这种几何学并没有试图脱离人们在其中生活着的感性世界,没有试图将自然本身数学化。a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pp.21—23.直到现代应用几何学的产生,空间和自然才被认为是纯粹的数学性物质对象,是一个遵循数学化普遍规律的物质总体。而一旦掌握了这些数学性规律,世界被认为是可以以数学的方式进行计算和操纵的。
这种物理主义和数学主义的理念对近代哲学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的笛卡尔、霍布斯和洛克等认为,空间属性是物质对象的唯一属性或第一属性,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是独立于人的感知的。而人对自然的直接感性认识和属性如颜色、气味等是第二属性,是人的感官主观加上去的。这样,在物理唯物一元论之下,无法被还原为广延性物理实在的感官知觉现象连同它们的根源(即精神领域)被排除到实在之外。现在它们被看作不同于客观实在领域的“主观领域”。这种“主观领域”后来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精神实体”的表述下,成为现代心理学的经验性研究对象。bIbid., p.60.由于现代科学只承认物质性这种唯一的实在,人的精神或意识被还原为物质运动的副现象。因此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间被建立起因果联系。这意味着任何心理活动作为主观的副现象都被理解为物质性生理过程。这种现代心理学的基本预设使得它用物质过程来理解心理现象,如用自然科学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关系的方程式来研究心理现象。胡塞尔指出这种倾向早在洛克的思想中体现出来。cIbid., p.85.而后来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则更加直接地喊出了“人是机器”的口号。在自然科学的物理主义和数学性视域下,人最终被异化为物,一切精神生活的可能性都被取 消。
这引出了一系列的困难。由于人的心理或精神领域被异化为相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领域,那么随之出现的就是主观的心理如何能够认识客观的自然。这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难题。心灵和物质两个彼此分离的对象如何可能产生可靠的认识关系?胡塞尔指出,近代哲学认识论的两种观点即唯理论和经验论均无法解决这一产生于欧洲科学视域的难题。唯理论由于局限于狭隘化了的数学性视域的内在原则最终将完全脱离直观和现实世界,而退化为符号主义和技术主义,成为纯粹的智力游戏。由于无法解释科学知识中不可或缺的范畴对象的来源,经验论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主义,并陷入相对主义从而摧毁了客观知识的可能性。a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pp.86—88.技术主义和心理主义这两个极端都起源于伽利略将自然的数学化。
不管现代科学危机有多少表现形态,对于胡塞尔而言,其根源是对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的精神领域的遗忘和排斥。这种遗忘使得自然科学把数学性观念世界看作绝对的和唯一的存在,并用它来取代和排斥真实显现的具体世界和生活世界。解决当代科学危机的方法是:从物理主义和数学主义的狭隘理性,回到一切意义构造的源泉,即先验自我。现代科学在依照其视域不加反思地迅猛发展时却遗忘了自身的历史,遗忘了自身由之发生的源初精神领域。只有一种先验现象学才能够克服技术主义对于先验的精神领域的遗忘,从而承担起拯救西方哲学中的普遍理性的理念的任务。
二、海德格尔对技术性的反思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性的批判紧密关联于他对存在的意义的一般追问。存在是个别事物显现的先验条件,但其本身不是存在物。前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此在生存结构分析为基础来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从而将自然科学看作把此在的衍生性的“在手”状态唯一化的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只关注世界之中的个别存在物而忽视了此在的生存性以及使得存在物显现出来的存在自身,以静态的、空间化的方式看待自然和世界。这与胡塞尔的看法多有接近之处。但后期海德格尔由重视对此在的分析作为基础转向直接面对存在自身揭示。这时他认为现代技术的危机是存在本身在人类历史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样态和揭示方式(revealing),而不是任何人类个体的创造发明。此在只是参与并进入存在作为真理和自由所打开的开放领域,从而让其中被揭示的事物自行显现自身。对他而言,现代科学仅仅重视对世界之中的具体存在者即物质对象的研究和改造,反映出人类对使技术显现出来的前提即存在作为真理的自我揭示的忽视。这种忽视本身体现了此在与存在的特定关系,仍然是存在的显现样态。技术的本质不可能在各种物质对象的研究中得到回答——技术的本质本身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b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San Franciso: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3, p.311.
那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呢?海德格尔不认同胡塞尔的观点,即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将数学性视域强加和投射在世界之上造成的。技术的本质并不存在于数学性的现代物理学的应用之中。恰恰相反,现代物理学的产生以技术的本质为前提。技术在当前世界的流行并不是由于某种理论性错误造成的,它体现的是历史现阶段此在的共同的整体性视域,某种与存在的调适关系。海德格尔追问,为什么现代数学可以如此完美地被应用于各种科学技术之上?这正是因为数学和现代技术内在分享了某种共同的本质,而这才是技术的本质。它使得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能够很好地结合。a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pp.326—327.海德格尔反对把现代技术看作理性的工具,而认为它自身已经反映了此在和存在的关系。技术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它已经体现在此在和自然、世界和他人的关系之中。它体现为:科学主义之下文明将一切事物都看作一种可以加以控制、提取、存储和分配的资源。河水被看作电能的存储库;动物被看作肉类产品的资源库;土地被施加化肥成为榨取产量的对象;人类本身也被看作可以产生利润的人力资源。技术的本质是“挑战” (challenging)。它表现为,人类开始挑战和攻击自然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甚至挑战自身。“异化劳动”正是技术对人的挑战的表现。挑战性的技术,是一种自动扩张不受任何个体控制的“框架化”。
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是存在本身开启的,是一切技术性对象显现的先在条件。它早在伽利略提出数学化自然理念的时候,就已经内在于其中却隐而不现。实际上只有在对自然进行计算、操纵、控制的动机下,现代数学才可能产生。只是在后来科学技术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技术的本质才清楚地被人们看见,从而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总是同时以开显和遮蔽、真理和非真理的双重方式向此在显现的。在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存在所打开的揭示领域作为科学对象显现的视域和前提却被此在遗忘和遮蔽。这也使得此在与存在的关系和揭示方式的其他更为源初的可能性被阻碍,技术性成为事物显现的唯一方式。bIbid., pp.332—333.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思考此在和存在的关系,从而能够理解这种关系,然后才可能对之作出正确的回应。
海德格尔以其天才的直觉超越了胡塞尔的理性主义视域,指出了技术的本质源自存在的显现且体现为“框架化”和“挑战”。他已经注意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挑战中所呈现出的具有攻击性特征的整体视域是技术本质的更深含义。但他没有能够说明存在如何使得此在接受并参与技术的整体揭示方式,特别是存在如何具体地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自我显现为具有攻击性特征的技术主义。这说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抽象的和不够具体的。而这些问题只有在亨利的生命现象学中对现象学一般理念进一步彻底化后才能得到回答。
三、技术主义作为野蛮主义
亨利在《野蛮主义》一书中基于他的生命现象学思想对现代科学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指出其对生命的显现的忽视和排斥。在其主要著作《显现的本质》中,亨利指出:传统的哲学包括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都只注意到了一种显现方式,即对象的显现。亨利继续追问,对象的显现是不是达到了现象显现最源初的方式。现象学从胡塞尔开始就意识到显现的对象不能脱离“向谁显现” (显现的主体极)而存在。但无论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还是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的此在作为一切事物显现的先验条件,都只是指向了世界之中的对象的存在,还没有超出意向性的范畴。作为主体的意识或此在作为对象显现的先验条件,其自身显现的方式还没有得到正确理解。亨利指出,主体自身的显现作为生命现象不同于对象的意向性显现。作为活着的生命个体,我们无时无刻不内在地直接体验着自身的活动、思想、情感。这种自身体验既不需要观察也不需要思考。以非意向性方式显现的生命现象之中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因为它是自身显现——显现和显现者都是生命自身,没有任何距离。
因为生命的显现是完全内在的情感性感受印象。我们无时无刻不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情感——快乐或悲伤、爱或憎恨。生命内在的自觉自知性决定了它的“不可见性”,即不可能成为自身的对象,无论是观察的对象还是思考的对象。当我处在快乐或悲伤中,我沉浸在其中而无法跳出来观察它;当我拿起水杯喝水时即使我闭上眼睛不作任何反思我也知道自己在喝水。任何对象性活动、一切可见的对象的显现总是以生命的自我感触作为其深处的隐秘源泉和基础。如果我不是一个能感受和觉知到自身的有生命的能看和能听者,我就无法看到任何事物或听到任何声音。科学知识作为一种智性的观念化对象能够为我们所理解和掌握同样也以我们的生命为前提。对于一个生物学学生来说,科学知识并不能教会他如何获取课本上的科学知识——翻书、转动眼睛、思考等活动是人作为一个自觉自知的生命体自发地、不假思索地进行的。aMichel Henry, Barbarism, translated by Scott Davidson,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pp.11—12.
在《野蛮主义》的第一章,亨利基于生命现象对文化进行了一般性定义,并随后对技术性这种现代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形态进行了本质性考察和定位。亨利指出:“‘文化’是生命的自我转化和成长,是生命以之来持续地转化自身以达到更高的实现和完整性形态的运动。”判断某种文化是高级还是低级、文明还是野蛮,取决于这种文化能够允许生命自我实现和发展到何种程度。aMichel Henry, Barbarism, p.5.生命更高级的发展需要促生出更高的文化形态:“出自内在需求天性的需要,产生了文化成熟形态:艺术、伦理和宗教”。bIbid., p.19.亨利指出,技术主义之所以被称作“野蛮主义”是由于它压抑生命,只允许其发展到最低形态,从而显示出它是文化的最低形态。科学技术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虽然出自生命,却否定和排斥生命自身。这使得技术主义成为一切文化中限制和压迫生命的极端形式。这回答了海德格尔所发现的现代技术的本质的挑战性特征从何而来的问题。这种暴力只有在生命和自身的内在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
那么,现代科学主义是如何否定和排斥生命的呢?前文已讲,科学主义的特征是认为世界的一切感受性的特征即其眼中的“第二性质”都是非实在的。它们被自然科学主义排除在存在和真理之外,被看作偶然、虚幻和主观的。但是,生命的自我显现就是一种非对象性的内在感受性。世界之所以呈现出各种感性特征,是由于世界的显现作为向生命的显现总是以生命为前提——世界总是呈现在生命的内在情感印象之中。这就是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为什么总是以感性的方式呈现——它们或者美丽,或者丑陋。而这种情感感受性,正是生命和自然的源初连接方式。自然总是人化的、感性的自然。作为纯粹客观的不被任何生命所感受到的物质对象如果存在的话,是无所谓美和不美。因此亨利指出,取消世界的感受性特征,是以取消生命自身为前提的。cIbid., p.17.胡塞尔指出的欧洲科学的本质特征即客观主义的实质在亨利的思想中得到了阐明,那就是排斥和否定生命。
尽管如此,生命自身由于是一切显现的先验条件,不可能因为被排斥而真正消失。科学主义之下排除一切生命感受性特征以后的世界仍然以某种生命感受的方式呈现为虚无和绝望。英国学者拉特克里夫在《存在性感受》一书中指出,纯粹科学的物理世界在生存上是无法被忍受的。一个只有力、能量、原子,没有任何情感、色彩、气味、温度的世界是彻底虚无的。包括科学家在内没有任何人能够忍受在这样的世界中哪怕是待上片刻。“幸运的是,机械论式世界的倡导者并不生活在其中。如果他们生活其中,他们经历到的非真实感会让他们瘫痪,从而无法认同任何理论。”dMatthew Ratcliffe, Feeling of Being:Phenomenology, Psychiatry and the Sense of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92.另外有一些精神病理学家指出,纯粹科学的世界和精神分裂者的世界是很类似的,它们都被剥夺了意义,一切生命之物都变成了死的物质。eIbid., p.290.
至此,海德格尔所发现的现代技术的挑战性或暴力性特征,在亨利的生命现象学里得到了本质性的阐明:技术主义的暴力性来自其对生命的否定和排斥。由于将生命排除在自身的视域之外,作为自然科学之本体论基础的现代形而上学只能看到世界中的物质对象。如果说古代的科学仍然是为了生命服务,是为了满足生命得以延续的基本的生理的需要。那么在现代科学主义之下,由于生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情感、伦理和爱不再是科学家所关注的目标,它们永远不可能在伽利略式的数学性科学空间中的物质对象(原子、分子、电流)里呈现出来。a有学者认为伽利略的量化自然与生命是兼容的,如生态科学致力于保护和服务于生命。对这一质疑的回答是:要区分科学和科学主义、技术和技术的本质。保护生态和生命的意愿出自生命情感性的内在感触,与自然科学主义的视域无关。从伽利略式的纯粹物质性自然中不可能得到情感性的诉求,如“要保护生命”这样的命题。伽利略式的科学世界彻底排除生命后,生命与世界源初的情感性联系被切断了,生命的爱、悲伤和对善恶的伦理直觉不再指导科学进行的方向。脱离生命后的科学开始只为了技术而技术,不再服务于生命。某种技术被研究出来的唯一理由是:它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便这种技术可能会让生命毁灭。现代技术的扩张,开始成为一种盲目的癌症式的扩张。这种扩张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情感,它寻求一切的可能性。
《科学美国人》近年曾经报道过一篇关于大象行为研究的科学新闻,它很好地体现了科学主义之下生命遭到排斥和否定的特性。非洲某国家为了控制象群的年龄结构,每过几年便会将其集中对其进行“修剪”。其中年龄过大的老象会被屠宰。没多久便发现象群开始产生行为紊乱,原本温顺的象群开始没有任何理由地攻击和残杀其他的动物,变得充满敌意和暴力性。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找到其背后的原因,科学家对之进行了科学观察和研究。研究成果最后发表在某权威的自然科学杂志上。其结论是:年轻的大象是通过年长的大象来学习正确的行为方式的,年长的大象从象群中消失,于是没有大象去教导那些年轻大象正确的行为,这就是象群行为紊乱的原因。
科学主义对生命的彻底无视在这个事例里充分表现出来。象群的科学管理者最初的动机是美好的,希望能够控制象群的年龄结构从而使之年轻化和保持健康活力。虽然屠杀大象是一种野蛮的暴力行为,但是由于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某种在生物学和社会学看来是正确的目的,它看起来也变成了合乎科学理性的。这里大象仅仅被看作自然界中的某种生物体,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看作由物质组成的某种聚合体。管理者看重的是这种物质体的自然属性,如年龄、性别、个体密度等,所有这些可以通过科学观察、测量和控制的数据。大象的情感则由于其无法显现在这些外部数据中从而无法被科学地观察,是不被考虑在内而被彻底忽视的。很明显,象群的暴力性行为是由于其群体中的年长成员被屠杀而引起的愤怒。但情感这种内在体验,在伽利略式的数学性空间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显现的。象群之所以遭到冷漠的暴力杀害,是因为它们被看成非生命的物质对象。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更说明了他们对生命的忽视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大象作为一种生命个体也是有情感、会痛苦的。科学家用现代学习理论解释象群行为异常的事实说明:大象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能够接受外部信息输入,然后向外部输出信息和行为的类似计算机一样的机器系统。生命被否定和排斥的最终结果是暴力、屠杀和漠视。
四、技术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学术讨论和各国政府投资的热点。许多人对此充满了乐观,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能够制造出具有与人类同等智力甚至是具有独立的情感意志的机器人。本来只对生命体有效的概念(如道德伦理),也被讨论是否能够应用在机器人之上。换言之,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是:生命能不能通过科学的对象性的、逻辑的、形式化的方法制造出来。在神学传统中,人是被造的,他的生命来自上帝的创造。人类如果能够通过技术创造出自己的生命,那无疑就拥有了和上帝同样的能力。这样,人工智能在现代重现了《圣经》中“巴别塔”的隐喻。人工智能的乐观主义观点认为,人的内在意识、生命完全可以还原为某种信息流和逻辑过程,内在不可见的情感生命可以被完全对象化,从而被还原为各种对象性的表征符号和规则等。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口号,在现代以“机器是人”重现。
至于这一愿景能否实现,要考察人工智能在近代的发展概况。在《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发展前景》一文中,成素梅总结了在过去几十年里人工智能范式转变的过程,即从早期的符号主义范式转向后期的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范式。a成素梅: 《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发展前景》,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12期。作为强人工智能理论代表的符号主义范式认为,人类的心理过程和内容完全可以被还原为物理符号系统。机器只要足够全面地对人类语言概念进行形式化,即能拥有人类意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心理活动的一切意义被看作是通过语言概念体现的。因此只要充分形式化所有这些概念和它们之间的逻辑规则,就能够实现强人工智能。
这一观点遭到美国现象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的反对和质疑。后者的观点在随后符号化人工智能的失败中得到了证实。b同上。德雷福斯主要依据的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思想,即此在与世界打交道的一般正常样态是不加反思、完全沉浸在情境中的“上手状态”。这种状态中的活动是自发的,体现出创造性的实践智慧,被称作“意会知识”。意会知识通过反思变成明言知识的时候,会失去技能和直觉。分离的、遵守规则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我们的行动和感知的基本方式,熟练的专家是不遵守规则的。a成素梅、姚艳勤: 《哲学与人工智能的交汇——访休伯特·德雷福斯和斯图亚特·德雷福斯》,载《哲学动态》2013年第11期。在德雷福斯观点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开始转向立足于解决具体问题、强调机器与环境交互而非理解的弱人工智能范式,以及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b成素梅: 《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发展前景》。
但专注于与环境具体互动的人工智能,也不可能达到人类专家的“上手”的高度自发的实践智慧程度。人类在处于与环境互动的沉浸状态中之所以有各种直觉反应,是因为他具有内在生命,能够觉知自身的存在,具有意向性,而机器不可能有。即便是被符号主义视作意义的载体的语言概念也不是形式化的,而是充满丰富的感受性含义。这是因为语言总是生命的语言,出自生命不可见的情感感受的中心。这也是为何语言本身不是固定的概念符号集合,而会随着人类的生命感受和活动的增长而生长,新的词汇也会随之而出现。当语言中的生命感受被剥离而成为物理符号,语言概念就失去了一切含义。然而人工智能的这个转向在哲学上意义重大,它标志着自然科学将生命对象化的努力的失败——生命的意义活动无法被还原为以逻辑规则相联的概念符号的集合。现在人工智能被理解为智能性的高度复杂的机器反应系统,而非具有内在理解能力的意向性。
即使认识到人工智能不可能成功地将内在生命完全对象化,技术的危险仍然存在,只要伽利略式的否定一切内在生命感受的科学主义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科学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并如此行动,它就变成了技术。”cMichel Henry, Barbarism, p.42.亨利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表现出一种趋势,即它像癌细胞一样扩张。一种新技术得以被实现,仅仅是因为它是可能的,而对一切非技术性之物即生命漠不关心。“独立于一切连接和所有的整体性和目的性的总体,技术向前进发,像一支星际火箭,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或者为什么。”dIbid., p.55.
成素梅指出:“‘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正在颠覆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与工具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工智能把技术创新的目标从解放体力转向解放智力。”e成素梅: 《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发展前景》。人类的体力和智力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也意味着人类的身心活动从劳动中被驱逐出去。如果说在早期的技术活动中人的身心活动总和技术过程融合在一起,那么人工智能则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和技术彻底分离。这种分离也意味着技术进一步被非人化——人彻底放弃了对技术的掌控而从中撤离。如计算机被设定入“自学习”的进化程序。随着不断升级其应对策略,程序员也无法预知其最后的进化结果。技术现在彻底占据了生命用于发展和实现自身的实践领域——劳动。人的思想从机器的程序化活动中撤离出来,不再能够知晓机器程序运行的过程和结果。这也是人们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的原因,即生命的活动领域完全被无名的、无情感的自动运作的程序所占据。这是生命和技术彻底分离后被驱逐出大部分现实领域后的失控恐惧。
机器没有生命,只是盲目地遵循预设的算法和“目的”,遵循代码完成一系列随机试探、刺激—反应、加权评估、条件判断等过程,在求解空间中寻求一切的满足目标方程式的可能性。这种计算对每种可能性的善或恶都漠不关心。波斯特洛姆提出的曲别针的例子说明了这一危险:“如果一种人工智能系统被设置为使曲别针的产量最大化,那么,这种人工智能系统很可能具有无法满足的胃口,不断地获取物质和能力,走上首先将地球、然后将整个可观察宇宙的大部分都变成曲别针的道路。”a杜严勇: 《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载《哲学动态》2016年第9期。技术主义的本质表现在技术仅以自身为目的,对生命漠不关心。这种危险并不是幻觉。我们知道,互联网上的计算机病毒就是自动运作引发大规模破坏的程序。幸运的是,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虚拟空间无法延伸到现实世界。但正在发展的人工智能就是虚拟程序打通现实世界的通道——人工智能学家正努力让程序能够“识别”和“处理”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对象,使程序技术能够延伸到现实世界而使之现实化。人工智能的成功发展将使技术跨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虚拟世界的严格遵循数学和形式逻辑的技术性观念空间被用于处理现实世界。不难设想,照目前的状况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高度“智能”的全自动战争机器人,其能“识别”物理世界中的生物并执行摧毁程序,体积小且能高速移动并躲避危险,能自动“寻找”能源并“寻找”材料3D打印复制自身……最可怕的是,它不需要任何人类思想的干预,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情感,一切在预先内设的计算机程序下运作。
危险还表现在,技术不仅在一切领域排斥生命,而且试图否定生命,将生命还原和异化为非生命的技术对象。前面象群管理的例子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写照。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已证实内在生命无法被对象化,人工智能的狂热反映出流行的科学文化仍然相信并渴望我们内在的生命感受可以完全还原为对象性的技术过程。伽利略式科学主义仍然在试图将生命排斥在最后的存在之外:“科学已经将活着的先验自我,还原为伽利略空间中的无生命对象,还原为不能感受、思考、诉说任何东西的神经元网络。”bMichel Henry, I Am the Truth: Toward a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 translated by Susan Emanuel,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74.在《我是真理》的结束之处亨利指出,现代人被科学看作一种能够接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感知机器。由于在现代认知科学之下意识被看作信息流的输入输出和加工过程,虚拟现实技术被认为可以完全取代真实的世界。如在虚拟现实中受训的飞行员接收到各种仿真影像,他的每一次摇动控制杆、发射弹药以及敌机被击中的爆炸,都被合成出来,并不断被重复,以便他在真实的空战中能够接受同样的影像输入、同样的动作重复。虚拟环境越是做得无法和真实现实区分开,就越能够使其训练获得成功。a亨利在《我是真理》中的结论部分使用了这个例子。生命被还原为一连串的信息流和数据流。那么只要制造出这种信息流,人的生活就被认为可以完全复制。甚至有一天,人们能够和高度仿真的智能机器人一起生活、组成家庭、享受性生活和情感交流。一切情感被看作脸部肌肉的收缩、皮肤颜色的改变、声音的高低变化……那时候,现实和幻想将不再被区分。“疯狂是不可能再区分表象和现实。在这里就是在一系列的模拟影像和组成现实的类似的影像中进行区分的不可能。人被还原为影像,没有感受的木偶和自动机器,并被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bMichel Henry, I Am the Truth: Toward a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 p.275.
五、结 论
从胡塞尔认为技术的本质源自欧洲科学的数学性和客观性视域和预设,到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存在在人类历史现阶段显现出的“挑战”和“框架化”,再到亨利认为技术的本质是生命的自我排斥和否定,现象学对技术性的反思呈现出内在的继承和不断深化的过程。三位现象学家都认识到,现代技术的危机源于对精神性领域的遗忘,尽管对这种精神领域的理解有一定差别而被称作先验自我、存在或生命。现象学要反对和批判的不是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和技术,不是要回到没有科学的原始社会,而是要批判伽利略式的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看作绝对唯一的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科学主义从伽利略开始把生命排除在真理和存在之外。这一排斥和否定生命的内在本质,是科学主义自身无法看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说存在在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中使得科学对象显现出来的同时也是存在自身的遮蔽过程。人工智能的发展代表着技术主义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开始进一步侵入现实世界并在其范围内排斥生命活动。克服危机的关键在于恢复一切技术从中而来的又被其排斥和否定的生命现象的先验地位,让技术接受生命的指导,让它不再以自己而是以生命为唯一的目的,为生命服务。
——论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时间观的继承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