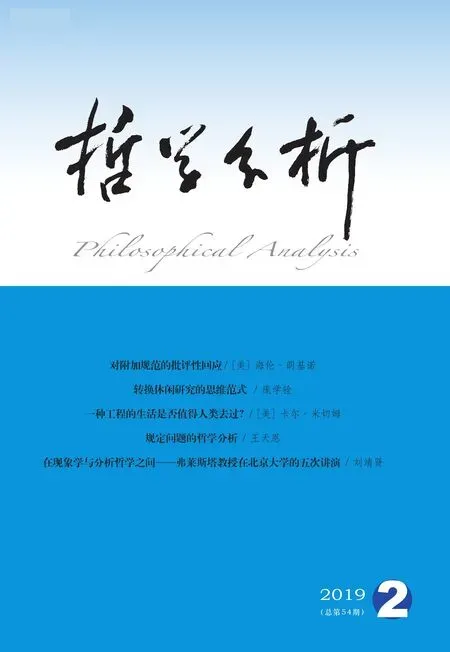整理杨祖陶先生遗著过程中的学术收获a
舒远招
2006年,杨祖陶先生在进入80岁时出版了根据格洛克纳本翻译的《精神哲学》首译本,后又根据“理论著作版”20卷本改译《精神哲学》,且在将近90岁高龄之际奋力撰写《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这种纯粹高洁的学术情怀和“只要一息尚存就笔耕不辍”的工作态度感天动地,杨先生的精神永恒!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2017年1月22日,他刚刚完成约十万字的初稿,还来不及修改就撒手人寰了。承蒙萧静宁师母信任,本人有幸承担遗著的整理工作。面对凝结杨先生心血和生命的遗稿,我的心情是沉痛的,总有一种感动和思念在心头浮现。唯愿先生在自由而永恒的精神世界中安息,也希望先生在天国能知晓遗著顺利出版的消息。
整理杨先生的遗著是一个切身了解杨先生写作方式和风格的机会,更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正是在整理遗著的过程中,我不仅有机会拜读萧静宁师母提供的约十万字的遗著打印稿,而且需要仔细地将这份遗稿与杨先生翻译的《精神哲学》 (杨先生在写作《指要》时,主要依据和引用的是他自己翻译的、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文首译本)加以对照,个别有疑问的地方,还需要参阅《精神哲学》的德语原文。由于遗著对客观精神哲学的解读参照了《法哲学原理》,我因而不得不参阅《法哲学原理》 (遗著引用的是范扬、张企泰的合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除了《精神哲学》和《法哲学原理》,遗著还引用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逻辑学》(《小逻辑》)《自然哲学》 《宗教哲学讲演录》 《哲学史讲演录》等多部著作,以及早期的一些有关精神哲学的论著。遗著与这些著作的相关性,也促使我阅读这些著作中与遗著内容相关的部分。
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我在《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的“整理附记”中已作了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想谈谈在遗著整理过程中获得的三个方面的学术收获。
一、更深刻地认识到《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特色
在整理杨先生的遗著之前,我早就知道黑格尔的《哲学全书》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的简称)的第三部分是《精神哲学》,也知道杨先生根据格洛克纳版翻译的首译本在2006年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后来,他根据“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 (20卷)的第10卷(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编辑的《哲学全书的第三部分精神哲学及附释》)重新翻译的译本,也收录于张世英先生主编、他任副主编的《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并于201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并没有认真阅读过杨先生的译本,因而对黑格尔《精神哲学》这部著作的认识也很肤浅。在我的印象中,《精神哲学》只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一个纲要,而黑格尔对精神哲学的更详尽的阐释,是在诸如《精神现象学》 《法哲学原理》和各种《讲演录》中展开的。我还以为,既然只是一个“纲要”,也就不可能包含鲜明的特色,不会包含原创性的内容。而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出版《精神哲学》的中译本,似乎也“印证”了这个观念:黑格尔的这部著作并不很重要,因而不值得加以特别关 注。
然而,在将杨先生的遗稿与黑格尔的上述著作、尤其是《精神哲学》加以对照的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自己原先的一些想法是肤浅的。正如杨先生所言:精神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对象是人,是人的精神或具有精神的人,人的精神虽然以自然为直接前提,因而最终也以逻辑理念为最初的前提,但它作为逻辑理念和自然这两个各有其片面性的东西的统一,却是逻辑理念和自然的根据和真理,是它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实现。“精神哲学的对象在黑格尔哲学中的这种地位,也就是它成为一门最高的哲学科学的根本原因。它的这种地位,加上上述精神的那种具体性,也就是它之所以是一门最高的、最困难的哲学学科的根据所在。”a杨祖陶:《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舒远招整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人们也许会认为,杨先生上面这段话仅仅提到了“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还未必就是对《百科全书》中的《精神哲学》这部著作重要性的肯定。不过,在2006年《精神哲学》首译本的译者导言中,杨先生对“精神哲学”之重要性的阐释,也就是对《精神哲学》这部著作之重要性的明确指认。他说:“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既是我们全面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深入把握黑格尔有关历史、美学、宗教、哲学等讲演录的纲,尤其是我们了解黑格尔主观精神哲学的唯一专著。黑格尔精神哲学所蕴藏的无数‘珍宝’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财富,光彩夺目,永不减色。”a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导言”第47—48页。显然,这段话中所说的“精神哲学”,其实就是指《百科全书》的第三部分《精神哲学》,即《精神哲学》中的“精神哲学”。正因为如此,杨先生才把“精神哲学”视为我们全面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并视之为黑格尔有关历史、美学、宗教和哲学等《讲演录》的“纲”。对《精神哲学》中的“精神哲学”的重要性的肯定,就是对《精神哲学》这部著作的重要性的肯定。
在上面这段阐述《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的段落中,杨先生不仅指出了《精神哲学》构成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重要环节,而且特别指出了两点:其一,《精神哲学》“是我们把握黑格尔有关历史、美学、宗教、哲学等讲演录的纲”;其二,它“尤其是我们了解黑格尔主观精神哲学的唯一专著”。通过认真阅读和学习《精神哲学》 《法哲学原理》等著作,我逐步对以上两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首先,作为整个“精神哲学”的“纲要”,《精神哲学》一书确实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这尤其体现在对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阐述上。
黑格尔在这两个部分用笔不多,但确实以极为精练的语言,勾勒出了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运动的主要环节,从而构成了《法哲学原理》和有关历史、美学、宗教、哲学等《讲演录》的“纲”。显然,对于不能全面阅读黑格尔哲学著作的读者而言,通过阅读《精神哲学》的这两个部分来获得对黑格尔客观精神哲学和绝对精神哲学的大致了解,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杨先生在《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中也告诉我们:尽管《精神哲学》中有关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阐述与《法哲学原理》以及历史、美学、宗教、哲学等《讲演录》中的阐释大致对应,但《精神哲学》作为“纲要”依然有一些不同于这些著作之处,因而显出自己的特色。如果拿《精神哲学》中的客观精神哲学与《法哲学原理》相比,就会发现有一些标题的表达是有区别的。例如,在《法哲学原理》中,“抽象法”的第三个环节叫做“不法”,而在《精神哲学》中叫做“法与不法”;《法哲学原理》中关于道德的三个标题是“故意与责任”“意图与福利”“善与良心”,《精神哲学》中相应的标题则是“故意”“意图与福利”“善与恶”。其实,不只是标题有所不同,在内容上,《精神哲学》对客观精神的一些阐述也富有特色,如对于康德所说的善或义务的内在矛盾的揭露,对世界历史的深入探讨等。同样,尽管《精神哲学》对绝对精神的论述比较简略,而关于艺术、宗教和哲学的《讲演录》则是对《精神哲学》相关内容的扩充和发挥,但正如杨先生所说,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哲学》中有关艺术、宗教和哲学的论述缺乏独到的内容和特色。例如,《精神哲学》对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作出了详细论述,深入地阐明了哲学的概念思维方式与宗教的表象思维方式的区别;又如,它提出了关于哲学的三个“推论”,即从逻辑理念到自然再到精神、从自然到精神再到逻辑理念、从精神到逻辑理念再到自然的“推论”,由此表明黑格尔实际上把《哲学全书》所论述的三个东西(逻辑理念、自然、精神)都当作“推论”的中介,由此可以构成三个不同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最大特色是对主观精神作了极为详尽的阐述,以至于杨先生认定它是我们了解黑格尔主观精神哲学的“唯一著作”。
对于杨先生的这一判断,我一开始也没有充分的认识,总觉得《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可能也有对主观精神的论述,但当我按照杨先生的提示对《精神哲学》和《精神现象学》加以比较时,发现《精神现象学》对主观精神的论述极为简略,而《精神哲学》则把对主观精神的阐释当作自己的重头戏,以至于占去了全书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可见,黑格尔确实是想在自己的《精神哲学》中,把原先在《精神现象学》中尚未详细展开的内容详加阐述。
在《精神哲学》2006年首译本中,除绪论有32页外,论述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总共78页,而论述主观精神的则有280页。在主观精神哲学中,论述“灵魂”的“人类学”有171页,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篇幅,这说明黑格尔又把主观精神哲学的重心放在人类学上。相对而言,论述“意识”的“精神现象学”所占篇幅较小,它大致是《精神现象学》有关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的论述的简写和撮要。黑格尔对专门研究“精神”的“心理学”也很重视,其篇幅是“精神现象学”的一倍。按照杨先生的说法,黑格尔之所以重视心理学,是因为他对当时心理学的进展和现状极不满意,因此,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就表示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对心理学的问题“详加阐述”。
正因为《精神哲学》的重头戏是主观精神哲学,所以,杨先生在《精神哲学》2006年首译本的译者导言中阐述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意义时,就特别强调了主观精神哲学的意义。他指出,黑格尔把主观精神哲学称为“一般心理学”,也就是说,包括“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在内的主观精神哲学不是对人的心理现象作经验科学的研究和描述,而是作哲学的研究,黑格尔因而从实体和主体、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的哲学高度来考察人的一切心理现象,但并不因此而忽视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而是十分的重视,甚至还谈到要建立一门叫做“生理心理学”的学科。杨先生由此认定,黑格尔的这个广义的、一般的“心理学说”“其实是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等著作所开启的心理学在近代发展的一个里程碑”a黑格尔:《精神哲学》,“译者导言”第46页。。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心灵哲学几乎涵盖了黑格尔主观精神学说的主要内容”b同上。。杨先生还特别指出:黑格尔把千里视、心灵感应等特异心理现象作为其主观精神学说的研究对象,而对这类现象的哲学思考也是现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a杨先生虽然主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但他很关注现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其论述中,引用了高新民教授的《现代西方心灵哲学》 (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在阅读《精神哲学》的过程中,我发现黑格尔在人类学中对“灵魂”问题的讨论,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例一:黑格尔在一开始论述“自然灵魂”时,就谈到了“自然的质”,他不仅论述了由太阳系行星运动所引起的气候的差异、季节的变换和一日各时段的周转及其对灵魂的影响和作用,而且谈到了地理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人的种族、乃至同一种族的各民族的性格、心理素质的差异。黑格尔在此明确反对了种族主义,而且对西欧各民族的性格作了精彩的比较。不仅如此,他还看到灵魂的个体化会导致“个体的主体”的出现,即出现“个体灵魂”,由此探讨了个体在天性、气质和性格方面的差异。
例二:黑格尔在论述灵魂的自然变化时,还对“年龄的自然进程”作出了非常精彩的论述。所谓年龄的自然进程,是指从童年、青年、成年到老年的进程所引起的意识或心理状态的变化。黑格尔认为在童年阶段,人的心理是与外界环境相和谐的,意识尚未具有独立性;在青年时期,人总是带着理想展开生活,因而经常感到主观理想和客观环境的冲突;在成年时期,人的意识和心理达到成熟,因而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而到了老年阶段,理想破灭,总是生活在对昔日生活的留恋和怀念中。后来,施蒂纳受黑格尔的影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旧约:人”的部分,在论述创世纪和人的生活时,和黑格尔一样谈到了儿童、青年、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专门作出评点。
例三:在论述了“睡眠与觉醒”这种自然的变化之后,黑格尔花费了大量笔墨论述“感受” (die Empfindung),并发表了有关感受的许多精彩见解。在他看来,当灵魂进行感受时,它在自身内发现的是直接的、被给予的东西,但同时这个东西已沉入其普遍性之中,就是说,是一个其直接性被否定而从观念上建立起来的东西。换言之,感受是精神在其无意识的和无理智的个体性中模糊活动的形式,在此形式中,一切规定性都还是直接的,按其内容来看还是未发展的,因而属于精神的最特殊、最自然的特性。正因为如此,感受的内容还是受限制的,转瞬即逝的。他指出,一切出现在精神的意识和理性中的东西都在感受中有其起源(他显然吸收了感觉经验论的思想因素),但由于感受是多变的,因此,他和康德一样反对把感受当作道德原则的基础。就是说,他反对把感受或者建立在感受基础上的心情(Herz)当作用来辩护某个东西是宗教的、道德的、真的、正义的等形式。也正是在论述感受的这个部分时,他提出了建立“生理心理学” (eine psychischen Physiologie)的主张。他看到了人的各种感官对于心理活动的作用和意义,认为不能撇开各种感官来理解心理现象。他和近代许多认识理论家一样,把感受分为“外部感受”和“内部感受”,认为前者的内容来源于外界事物,而后者则源于我们的内心活动。由此出发,他还进一步细致地区分了外部感受和内部感受的各种具体形式。
例四:在论述“感觉灵魂”时,具体而言,在论述“在其直接性中的感觉灵魂”时,黑格尔不仅论述了包括“自然地做梦”“母腹中的孩子”“个体对其守护神的关系”等“生命的形式上的主体性”,而且论述了“感觉灵魂的实在的主体性”。他不仅对“做梦”等心理现象给予了关注(这与后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有相似之处),而且特别论述了灵魂的病态或疾病。在他看来,正如身体会生病一样,灵魂也会发生疾病。灵魂的疾病与身体的疾病密切相关,且具有多种病态形式。他谈到了梦游、强迫性晕厥、女性青春发育期、妊娠状态等,甚至谈到了“舞蹈病”,以及临终状态。黑格尔还研究了人们(如奥地利医生梅斯梅尔)称之为“动物磁力”的心灵状态。当时,人们发现可以利用“动物磁力”来进行催眠,他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由“动物磁力”所引起的种种催眠状态与自发产生的灵魂疾病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不过是由催眠师以特殊的方式使被催眠者的灵魂生命中原本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方面达到彼此分离和破裂而造成的。黑格尔还详细考察了灵魂疾病的各种形式,如所谓金属占卜者和水占卜者的“特异功能”、出现在强迫性晕厥尤其是梦游中的幻觉、千里视之类的神奇预感或内观、对他人心灵状态和身体状态的千里视、心灵附体等。黑格尔的这些研究,不仅与后来的精神分析学说有许多一致之处,而且也值得当代心理学给予关注,因为他不仅分析了各种心灵疾病,而且批评性地考察了心灵的各种“特异功能”。
例五:在论述“感觉灵魂”中的“自身感觉”时,黑格尔对灵魂的“疯狂”状态作出了详细考察。他把疯狂视为与身体密不可分的一种“精神病”,由此阐发了一系列关于疯狂的深刻观点。他认为,疯狂并不意味着理性的完全丧失,但确实包含着心灵活动的冲突和错乱。他还对疯狂作出了详细的分类:第一种类型或主导形式包括了痴呆、精神涣散和蠢态;第二种类型或形式就是真正的“傻”;第三种类型或形式就是“癫狂” (发疯)。他还谈到了疯狂的治疗,认为治疗的方法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但要以精神的方法为主,而精神治疗的关键是要把疯子的残余理性当作治疗的基础,因此治疗者要尽量获得疯子的信任和尊重。这些论述,显然与关注精神疾病的当代精神科学具有同样的主题。
上述例子,都取自《精神哲学》中的“人类学”部分。由此可见,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哲学确实包含了极为丰富的、迄今仍未过时的精彩内容。在以“意识”为对象的、篇幅较小的“精神现象学”部分,黑格尔的论述尽管只是《精神现象学》有关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的论述的简写和撮要,但也有其独到之处。例如,《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中都有关于自我意识的论述,而且其思想大致相同,但《精神哲学》对自我意识的论述更加简明、清晰。在这里,黑格尔对自我意识概念作出了清楚的界定,指出自我意识作为意识的“真理”和“根据”,其表达式是“自我=自我”,意指抽象的自由,或纯粹的观念性。该表达式虽然只表达了抽象的自由,但宣告了绝对理性和自由的原则,因为理性和自由就在于我在同一个意识中拥有自我和世界。这个构成精神之原则的自我和客体的统一,最初只是以抽象的方式在直接的自我意识中存在着,而尚未被抽象的自我意识所认识。所以,抽象的自我意识总是把自己与意识对立起来。要克服自我意识的这种抽象性,自我意识就必须经历欲望的自我意识、承认的自我意识和普遍的自我意识三个发展阶段。黑格尔对“承认的自我意识”的论述十分精彩,他用极为明快的语言阐释了《精神现象学》中有关自我意识的承认理论。同样独立的自我意识是如何为了争取对方的承认而展开生死搏斗的,这种搏斗又如何以不平等的主奴关系的出现而告终,主奴关系最终又是如何辩证转化的,在此转化中奴隶对于主人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陶冶事物的劳动又起着何种作用,黑格尔的阐释都十分精当。他还指出,通过上述辩证运动,自我意识终于相互承认对方为独立自由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普遍的自我意识。总之,《精神现象学》对自我意识的论述要比《精神哲学》中的论述远为晦涩,我们完全可以参照《精神哲学》中的相关论述来重新审视《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理论。
由于杨先生对《精神哲学》中的主观精神哲学的解读,重点落在“人类学”上面,因而他并未花更多的篇幅来讲解以“精神”为对象的“心理学”,而是简要地勾勒了这个“心理学”的要点。从杨先生的叙述来看,这个“心理学”的发展线索也十分清晰:首先是被叫做“理智”的理论精神,包含直观、表象和思维三个阶段;接着是实践精神(意志),包括实践的感觉、冲动和任意、幸福三个环节;最后是作为理论精神和实践精神之统一的自由精神。在这里,黑格尔也表达了不少洞见。例如,一般认为理论精神(理智)不像实践精神(意志)那样主动,而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他说,理智诚然还是处在直接性中的精神,它首先“发现”一个给定的、现成的内容,但理智的任务却在于使这个外来的客体失去其被给予的、个别的、偶然的形式,而将之建立为它自己的东西,使它成为主观的、普遍的、必然的、理性的东西,从而表明自己是主动的或能动的。针对“理智是受限制的东西,而意志不受限制”的观点,他指出:意志其实可以被宣布为更受限制的东西,因为它在不断地同外部进行抵抗的物质、同现实之物的排他的个别性进行斗争,同时还面对着他人的意志。他在论述“表象”时,把回想、想象力和记忆当作表象的三个环节,并且将想象力区分为再生的想象力、联想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生产性的)想象力三种类型。此外,他对“实践的感觉”“任意和冲动”以及“幸福”的论述都很简明,弄懂他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
总之,包含“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在内的主观精神哲学蕴含极为丰富的内容,也最能体现《精神哲学》的特色,其中含有无数有待我们深入挖掘和品味的珍宝。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以为《精神哲学》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纲要,而应该在承认它是一个纲要的同时,还要像杨先生指出的那样,将之视为我们了解黑格尔主观精神哲学的“唯一著作”。
二、更准确地认识到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尤其是道德思维方式的批评
近几年来,我主持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康德道义论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着眼于对康德道义论的各种批评》 (项目编号:13JJD720007)的研究,因而不得不关注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在后世受到的各种批评,其中包括黑格尔的批评。在整理杨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我也特别留意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尤其是两人在道德思维方式上的区别。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是从肯定康德伦理学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出发的。他在《小逻辑》中指出:康德在其实践哲学中将他在理论哲学中否认了的东西——意志自由——证明为正确的,康德哲学的这个方面给康德哲学“获得了巨大的好处”a黑格尔:《小逻辑》,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康德的主要贡献是批评了他那个时代盛行的道德哲学,即以人生幸福为目标的幸福论。由于幸福被理解为人的特殊偏好、愿望、需要等的满足,这就把偶然的、特殊的东西当成了意志及其实现的原则。于是,康德就用“实践理性”去对抗这种自身缺乏坚实立足点而为一切任性和情欲大开方便之门的幸福主义,从而说出了一个有普遍性的、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的意志规定的公设。这个“公设”就是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基本原则即无条件的“定言命令”:你要按照你能够同时意愿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康德宣称理论理性(知性)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但现在却明确肯定实践理性的积极的无限性,认为意志具有以普遍的方式,即以思维的方式自己规定自己的能力,而这不过就是对意志自由的肯定。
康德和黑格尔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道德原则并因而反对感觉(情感)主义的。康德认为幸福论或利己主义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多变的感觉的基础上是不可靠的,黑格尔完全赞同这一见解。他在《精神哲学》中论述“感受”(Empfindungen)时指出:虽然一切出现在精神的意识和理性中的东西都在感受中有其起源,但感受是精神在其无意识的、无理智的个体性中模糊活动的形式,其内容是有限的和转瞬即逝的。属于我们的意志、良心、性格等,要比感受和感受的全体(心)远为坚强和稳固。他写道:“说心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这当然是对的。然而感受和心并不是用以辩护某个东西是宗教的、道德的、真的、正义的等的形式,诉之于心和感受要么就只是说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要么就反倒是些不是无可非议之谈,这个道理本身是无需人提醒的。”a黑格尔:《精神哲学》,第98页。他反对把多变的感受和心当作善、伦理和宗教的标准。在《法哲学原理》中,他也反对把主观的满足(个人幸福)当作人的行为的实质意图,反对把客观的目的(道德、善、正义)仅仅当作达到主观满足的工具,声称这是“一种恶毒而有害的主张”b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6页。。
但是,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并不完全满意,而是对之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批评,就是指责它是一种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写道:“着重指出纯粹的不受制约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并把它作为义务的根源,这诚然很重要,又意志的认识——多亏通过康德哲学——只是通过它的无限自主的思想,才获得巩固的根据和出发点……这诚然也很真确,但是固执单纯的道德观点而不向伦理的概念过渡,就会把这种收获贬低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把道德科学贬低为关于为义务而尽义务的修辞或演讲。”c同上书,第137页。他认为,从康德的道德观点出发,不可能形成内在的义务学说。我们可以从外面采入一些材料,借以达到特殊的义务,但从康德的无矛盾性的普遍形式要求,不可能过渡到特殊义务的具体规定;即使在考察行为的这种内容时,该原则也不包含决定该内容是不是义务的标准。而一切不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反倒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得到辩解——它们可以通过康德提出的无矛盾性测试。总之,如果应该为义务而不是为某种内容而尽义务,这在黑格尔看来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的同一,它排斥了一切具体内容。
黑格尔不仅明确指责康德的伦理学是一种形式主义,而且揭示了康德伦理学的内在矛盾。例如,他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 (道德)时,就把康德伦理学作为包含一系列内在矛盾的“道德世界观” (die moralische Weltanschauung)加以批评。他认为,在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中,自我意识仅仅接受义务的约束,把义务当作自己的绝对本质,但在自我意识之外,却又存在一个独立于它的自然,这个自然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这就是说,道德世界观是由道德的自在自为存在与自然的自在自为存在的关系构成的,它一方面假定自然与道德彼此独立和互不相干,另一方面又假定具有这样的意识,它知道只有义务具有本质性而自然全无独立性和本质性。“道德世界观”包含道德与自然这两个环节的发展,而这两个环节又处于上述完全矛盾的假定的关系中。
黑格尔还指出,康德首先假定了把义务当作绝对本质的能动的道德意识,而这个道德意识却知道义务的履行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即感性欲望的满足或享受,也就是说,德行与幸福很可能并不一致,由此出现有德之人不能享福而无德之人享受幸福的不合理的情况。此时,道德意识要求不考虑履行义务是否会带来幸福,而只要求出于义务而履行义务。但尽管道德意识强调在履行义务时要全然放弃对于幸福的考虑,却并不真的就完全放弃了幸福。在至善论中,康德提出配享幸福的人理当享受幸福,认为只有德福相称才是圆满意义上的至善,由此便设定了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和谐。当道德意识设定了道德与幸福的和谐后,原先被排斥于道德意向之外的幸福,现在又被重新接纳进道德意向之中了。
整理杨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将《精神哲学》中有关康德伦理学包含内在矛盾的论述与《精神现象学》的上述论述加以对照,结果发现: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的论述更加简洁。具体而言,黑格尔在论述善与恶的关系时,集中揭露了康德义务论的多重矛盾。
首先,各种特殊的善或义务彼此冲突。黑格尔认为,康德对善的规定是模糊的,由此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彼此对立和冲突的善和义务。但由于它们都是善,因而又“应该”彼此和谐一致。它们每一个都是特殊的,但作为善和义务本身却是绝对的。显然,黑格尔根据善的具体内容看到了善的内在冲突,并且认为各种具体的善的相互冲突最终需要统一在绝对的善之中。由此出发,他试图凭借主体的“辩证法”来解决义务的彼此冲突问题。
其次,特殊的善与普遍的善不相一致。每个独特的主体都在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或福利,并将之当作自己的本质目的和义务,但在普遍的善或目的中,这些特殊的利益或福利就不应该是关键因素。在康德那里,特殊的善与普遍的善之间的和谐一致仅仅是偶然的,但它们却“应该”和谐一 致。
再次,是善与恶相互对立。每个具有特殊利益的主体都有可能使普遍的善成为对自己而言是特殊的东西,并因此使之成为一种“假象”。如此一来,该主体就可能把普遍的善作为达到自己特殊利益的工具,或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牺牲普遍的善,由此陷入恶,这就造成了善与恶的对 立。
最后,主观目的与客观世界不相和谐。在康德的义务论中,除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外,外部客观性(客观世界)也构成了与意志的内在决定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因此,不仅这个外部世界是否与主观目的相一致,即善是否在这个世界里得到实现,恶是否在它里面无效,统统是偶然的,而且主体是否在这个世界里找到自己的福利,即善的主体是否在它里面成为幸福的,恶的主体是否成为不幸的,也同样是偶然的。康德又主张:世界“应该”让善行在它里面得到实现,并满足善的主体的特殊利益;对恶的主体则不仅不给予满足,反而“应该”使恶消灭。
可见,自为存在着的意志对“善”的特殊性的规定活动所引起的深刻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对康德而言,善或义务始终只表现为一种“应该”,而无法顾及它在客观现实中的具体实现;而对黑格尔而言,这些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不能站在单纯主观主义的立场上左冲右突,而是要在一种伦理的立场上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正是在这里,体现了康德的道德思维方式与黑格尔的伦理思维方式的巨大区别。在黑格尔看来,要解决康德伦理学中的上述内在矛盾,就需要把康德的“抽象知性”的思维方式转换为思辨的理性思维。黑格尔在批评康德理论哲学时曾指出:尽管康德的理论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超出了近代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但它最终依然停留在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割裂之上,因此,康德最终也只是停留在知性思维的层次上,而未进展到把矛盾当作客观事物的本质这一思辨的理性思维上。因此,他对康德理论哲学的超越,就是要突破康德批判哲学的上述局限,运用思辨理性来实现主观与客观、现象与自在之物、有限与无限之间全面而彻底的统一。同样,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也是从批判康德的抽象知性(理智)思维方式入手的,他认为,如果坚持抽象的知性思维方式,就会要么陷入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要么陷入一系列的自相矛盾,因此,必须用更高级的思辨的理性思维来取代康德的抽象的知性思维,以便真正扬弃康德伦理学的一系列内在矛盾。
那么,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的思辨思维是怎样的?它与抽象的知性思维有何区别?对此问题,黑格尔在《小逻辑》中的“逻辑学的进一步规定和划分”部分曾有清楚的回答。在他看来,逻辑的东西就形式而言有三个方面:一是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二是辩证的或否定性理性的方面;三是思辨的或肯定性理性的方面。这三个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个部分,而是每个逻辑上实在的东西的一些环节,即每个概念所包含的不同环节。a黑格尔:《逻辑学》 (《哲学全书》第一部分),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2页。知性思维停留在各个固定的规定和它们彼此的差别上,在它看来,这样一种有局限的抽象的东西是自为地持续存在的和现实存在的;辩证的环节是这些有限规定的自我扬弃,是它们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思辨的思维“则把握了各个对立的规定的统一,把握了包含在它们的分解与过渡中的肯定东西”b同上书,第160页。。可见,所谓思辨的理性思维,实质上就是正视和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的思维。
当我将《法哲学原理》与《精神哲学》加以对照时,发现黑格尔对于道德(die Moralität)的阐释非常清楚地体现出了对康德的抽象知性思维方式的超越。
例如,在“故意和责任”部分,黑格尔主张把行为与行为的后果统一起来,反对将两者割裂开来的“抽象知性”。他说:“论行为而不问其后果这样一个原则以及另一个原则,即应按其后果来论行为并把后果当作什么是正义的和善的一种标准,两者都属于抽象理智。”a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0页。Verstand,一般译为“知性”,这里被译为“理智”。只问行为本身而不计后果,这是康德的观点,因为定言命令所要求的,就是要把行为本身当作目的,而完全不考虑行为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而以行为后果来决定行为价值的主张,正是康德明确反对的后果论(幸福论、功利论)。黑格尔从思辨的理性思维出发,反对将行为本身与行为后果割裂开 来。
又如,在论证了行为与其后果的思辨的统一之后,黑格尔在“意图和福利”部分继续论证了行为与其动机(意图、目的)的统一。在行为与其动机的关系问题上,一些人认为行为的价值就在行为本身,根本无需考虑行为的内在动机,而康德从“唯动机论”出发,认为行为的道德价值完全由行为的内在动机决定。黑格尔主张将两者思辨地结合起来,反对在两者之间制造鸿沟。他写道:“近人特别对行为常常追问动机。以前人们只不过问,这人是否正直的人?他是否在尽他的义务?今天人们却要深入到他的内心,而且同时假定着在行为的客观方面和内在方面——主观动机——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所以更高的观点在于在行为中求得满足,而不停留于人的自我意识和行为的客观性之间的鸿沟上,不过这种鸿沟的看法,无论在世界史中或个人的历史中都有它的一个时期的。”b同上书,第124页。可见,他反对片面割裂客观行为与主观动机的做法。
再如,黑格尔在“意图和福利”部分进一步论证行为动机的两个方面即主观动机(实现福利、幸福)与客观动机(实现善、自由、正义等)的统一:一方面,就主观动机而言,每个人都希求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热情;另一方面,善和正义也是行为的一种内容,并构成行为的客观动机,这种内容不是纯粹自然的,而是由个人的合理性所设定的,“以我的自由为我的意识的内容,这就是我的自由本身的纯规定”c同上。。黑格尔还从自由的角度对这两个方面作出了规定。他说,主观的、形式的自由就存在于自然的主观定在中,即在需要、倾向、热情、私见、幻想等中具有较为确定的内容,而这种内容的满足就构成福利或幸福。由于幸福的种种规定是现有的,故它们不是自由的真实规定。自由只有在自身目的中,即在善中,才对它自己来说是真实的。但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是否有权给自己设定未经自由选择而仅仅根据主体是生物这一事实的目的?他回答道:“但是人是生物这一事实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合乎理性的,这样说来,人有权把他的需要作为他的目的。”d同上书,第126页。这表明,他是把人的合理需要当作一种权利来加以维护的。黑格尔在此明确批评了抽象知性(理智)把行为的客观目的(善、自由、正义)与主观目的(福利、幸福)割裂开来的做法。他说:“由于个人自己的主观满足……也包括在达成有绝对价值的目的之内,所以要求仅仅有绝对价值的目的表现为被希求或被达到的东西,以及认为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在人们希求中是相互排斥的这种见解,两者都是抽象理智所作的空洞主张。”a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6页。
在《法哲学原理》的“善和良心”一节中,黑格尔对善的界定最为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思辨理性思维。对他来说,善不再像在康德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抽象形式的道德法则所指向的对象,而是普遍的意志概念与特殊意志相统一的理念。在这个统一中,抽象法、福利、认识的主观性和外部定在的偶然性,都作为独立自主的东西被扬弃了,但它们本质上仍然同时在其中得以保持。所以,善就是实现了的自由,是世界的绝对的最终目的。黑格尔所说的这个“善”,相当于康德在上帝公设之下所说的“至善”。他还进而指出:“善不是某种抽象法的东西,而是某种其实质和福利所构成的、内容充实的东西。”b同上书,第132页。福利没有法就不是善,同样,法没有福利也不是善。于是,善就被黑格尔规定为“合法的福利”,康德的单纯形式的道德法则就容纳了福利或幸福这个感性的内容,康德义务论与幸福论各自的片面性,也就被扬弃了。
总之,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谓的“纯粹实践理性”依然是一种“抽象知性”,而他对康德伦理学的超越,说到底是他的思辨的理性思维对康德抽象的知性思维的超越。通过思维方式的这种提升,黑格尔把康德所固执坚持的一些规定性与其相关的对立面思辨地统一了起来,从而实现了由康德片面的道德世界观向更高的伦理世界观的过渡。
三、认识到了黑格尔的直观思想对费尔巴哈直观理论具有直接影响
在整理杨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我还惊喜地发现:尽管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把自己的哲学与谢林哲学的根本区别,归结为从“概念”出发来界定“绝对”(das Absolute)和从“直观”出发来界定“绝对”的区别(黑格尔把“绝对”定义为“概念”,而谢林将之定义为“理智直观”,并将“艺术直观”视为“理智直观”的最高形式),但黑格尔其实也有自己的直观理论,而且他对直观的理解还与谢林的理解有相似之处。
黑格尔是在主观精神哲学的心理学部分论述“理论精神” (理智)时,提出类似于谢林“理智直观”的直观概念的。他把此处所说的直观与通常的感性直观相区别,认为这是具有理性内容的、结合各种规定为一个整体的直观。换言之,这里的直观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感性直观”,而是类似于谢林所说的“理智直观”,它“浓缩”了“我们关于外部自然、法、伦理和宗教内容的一切表象、思想和概念”a黑格尔:《精神哲学》,第256页。于自身之中。黑格尔说,这种直观“是一种为理性的确实性所充满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对象具有这样的规定:它是一个理性的东西,因而不是一个割裂为好些方面的个别东西,而是一个总体、一个诸规定的充实的集合体。早先谢林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谈到过智性的直观。没有精神的直观只是感性的、仍然外在于对象的意识。相反地,充满精神的直观把握住对象的纯真的实体”b同上书,第262页。。黑格尔在此明确提出了类似于谢林的“理智直观”或“智性直观”的直观,它就是“充满精神的直观”。这种直观所把握到的,是对象的“纯真的实体”或“真正的本质” (德文Wesen一词既有“独立存在的实体”之意,也有“本质”的含义)。
我同时发现,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曾关注到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充满精神的直观”。例如,他在第48节中探讨“感性直观”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由此可见,既然只有为思维所规定的,才是真正的直观;反过来说,也只有为直观所扩大所启发的思维,才是真实的现实界的思维。”c《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9页。在这里,费尔巴哈着重论述的是后一个方面,即真正的思维是离不开直观的,它需要由直观加以扩大和启发,但他毕竟也承认:只有为思维所规定的直观才是真正的直观。而这个“为思维所规定的直观”,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充满精神的直观”。
进一步看,费尔巴哈所说的“感性直观”其实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谢林和黑格尔所说的“理智直观”或“智性直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广义上来理解他的“感性直观”概念。在《未来哲学原理》第38节中,他谈到了可以直观到“真实的、神圣的实体(本质)”d同上书,第171页。的艺术官能,并将之视为一种感性的官能。在第40节中,他又谈到了以“神圣的实体(本质)”为对象的宗教直观,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最高的、神圣的实体,官能,“乃是感性直观”e同上。。可见,他实际上把指向“真正的、神圣的实体(本质)”的艺术直观和宗教直观,都归结为“感性的直观”。
在第41节中,费尔巴哈提出感官的对象不只是“外在事物”,也包括“自我”本身。他还指出:“一切对象都可以通过感觉而认识,即使不能直接认识,也能间接认识,即使不能用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也能用有训练的感觉认识,即使不能用解剖学家或化学家的眼睛认识,也能用哲学家的眼睛认识。”f同上书,第173页。在这里,费尔巴哈把“感性直观”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普通的、平凡的感性直观,它直观近在眼前的东西;二是借“解剖学家或化学家的眼睛”所进行的“自然科学的直观”;三是用“哲学家的眼睛”进行的直观,它要比“自然科学的直观”更高级,能够直观到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关于费尔巴哈的这一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从“自然科学的直观”出发加以考察,他们把这个“自然科学的直观”叫做“二重性的直观”,很显然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直观”恰好介于“普通的、平凡的直观”与“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并具有二重性。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从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第42节的论述来看,他之所以求助于“自然科学的直观”,是为了解决“本质和现象之间、原因和结果之间、实体和属性之间、必然和偶然之间、思辨和经验之间的差别”b《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上卷),第173页。。
对于上面这段话中所提到的“高级的哲学直观”,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方法,但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方法,费尔巴哈至多只提出了高于普通直观的“二重性的直观”。人们或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高级的哲学直观”理解为“对于工商业作为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及其力量的直观”,即对人的本质化过程的直接领会——它不仅仅是“看”和“直观”,而且要求“做”和“行”;c参见邹诗鹏:《何谓马克思“高级的哲学直观”》,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或者理解为“被镶嵌在感性活动中的看到事物之真实面目的直观”d参见郑争文:《马克思恩格斯的“看出事物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之比较》,载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办:《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这种观点是与《未来哲学原理》中的原文相矛盾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评费尔巴哈求助于“自然科学的直观”即“二重性的直观”,而且就像批评费尔巴哈求助于“类的平等化”一样,明确批评费尔巴哈求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他们写道:“……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类的平等化’。”e《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157—158页。此译文中的“最高的直观”是“高级的直观”的误译,其实就是指前面提到的“高级的哲学直观”。
关于马克思如何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评费尔巴哈的直观主义,邹诗鹏和郑争文的观点为什么不能成立,本人在即将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方法吗?——与邹诗鹏教授、郑争文副教授商榷》一文中展开探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想强调指出:费尔巴哈所说的“感性直观”业已包含了谢林所说的“理智直观”或“智性直观”,也包括了谢林所说的“艺术直观”和“宗教直观”,当然也包含了黑格尔在《精神哲学》中所说的“充满精神的直观”,这些以事物的“真正本质”为对象的直观,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因此,不能将费尔巴哈的“高级的哲学直观”误解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或方法。
在整理杨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我的学术收获当然不仅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但仅仅通过以上陈述,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出我的收获是巨大的。这一整理工作不仅使我更好地了解到杨先生的翻译风格,而且使我更深入地把握了《精神哲学》的内容;不仅使我更好地理解了《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色,理解它与黑格尔其他著作的异同,而且使我更好地认识到康德伦理学与黑格尔伦理学的关系,以及黑格尔的直观理论与谢林和费尔巴哈的直观理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