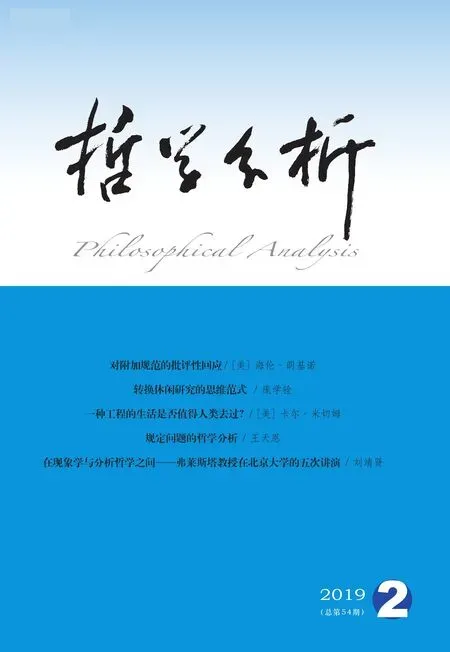权利与启蒙
——康德对革命的双重拒斥
方 博
虽然在理论哲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理论还被马克思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但是在实践领域,康德对政治革命的拒斥却是极为坚定明确的。在《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权利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以下简称为《权利学说》)中,康德明确声称,“针对国家的立法者并不存在人民的任何合乎正义的反抗”,因此“人民有义务忍受最高权力的即使令人无法忍受的滥用”b本文对康德文本的引用依据的是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版的《康德全集》: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von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Berlin: De Gruyter, 1902—,VI 320。后引只在文中注明页码。。同样的观点在此前的《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合于实践》 (以下简称为《论通常的说法》)中也已经清楚地表达过并在一系列反思中被重申。康德对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的这样一种断然否定的态度毫无意外地遭致了诸多尖锐的批评,比如赫费(Otfried Höffe)就将其视为康德法哲学中的错误观点之一aOtfried Höffe, „Königliche Völker “: Zu Kants cosmopolitischer Rechts-und Friedenstheorie, Fankfurt/M: Suhrkamp Verlag, 2001, S. 24.,而拜瑟尔(Frederick Beiser)则更为激烈地指责康德背叛了自己的激进的权利原则并将此归结为康德对普鲁士王权的愚忠bFrederick Beiser,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 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6.,在康德研究中,类似的观点并不鲜 见。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暂且抛开关于这一观点自身在自由主义的叙事传统中是否政治正确的争论,仅仅从学理上去考量的话,那可以说,康德的这一主张在其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中是逻辑自洽的。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康德对革命的拒斥是建立在充分的论证之上的,在他的学说中实际上包含着对革命的双重拒斥,即基于权利概念的拒斥和基于政治实践的拒斥。在法哲学的层面,康德从权利论证的角度指明了所谓的积极抵抗权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到辩护,因为其将会从根本上消解作为一切权利的现实性的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并因此与权利的概念直接相矛盾。而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康德则进一步论证了通过暴力革命并不能如革命者所期待的那样建立起全新的理想秩序,因为其并不能带来人的快速的启蒙,而后者恰恰是制度的持续革新与良序运行所必需的条件。就此而言,只有基于人的启蒙之上的改良才是实现人的权利的唯一合乎理性的现实路径。
一、抵抗权的可能论证进路
对革命权或积极抵抗权的拒斥当然不是什么新的观念,相反,这是从主权概念产生伊始便一直与之相纠缠的老命题。当博丹在《共和六书》中将主权明确地定义为“国家所特有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权力”之时,就明确强调了它是“针对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c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edited by Julian H. Frank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从这一定义出发,一种可以暴力反抗主权者的权利在逻辑上就不可能与主权概念相容。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博丹在其著作中也留下了一些口子,即强调主权者对权力的行使不应违反神法、自然法甚至是其与臣民之间的契约,但他既未为这一观念上的约束提供任何可以实践的措施,亦未承认臣民有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免除政治服从义务的权利。从博丹自己的理论立场来看,他在《共和六书》中事实上已经偏离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自然法传统,而更多地采纳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即将立法的主权视为权利的普遍来源而非相反。aDan Engster, “Jean Bodin, Scepticism and Absolute Sovereignt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7, No. 4 1996, p. 491.当然在这里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博丹自己对此问题持有什么样的立场,而是他在这一态度上的保留实际上全面地反映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对抵抗权的各种论证范式:神法论证、自然法论证和契约论论证。
与之相比,霍布斯则更为决绝地摒弃了残留在博丹思想中的这些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关于抵抗权的思想。在《利维坦》的一开头,霍布斯就否认了国家的任何神圣的起源,而明确宣称其“是用技艺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b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因此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神学的术语和隐喻,甚至我们还可以承认他的国家理论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叙事结构上的相似性,但他所理解的国家已经完全是世俗的和理性的,并没有为所谓的神法论证保留任何余地:关于国家的论证无需引入或预设任何具体的神学命题作为某个必备的论证环节。而霍布斯虽然仍然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但也仅仅将它们视为指引愿意寻求和平的人们摆脱自然状态的一些理性规则,它们并不构成可以指导或者约束主权者行使权力的超实证规范,自然也就不可能证成一种反抗最高权力的权利。霍布斯同样反驳了基于主权者与臣民之间的服从契约之上论证臣民的有限服从义务的思路。在他看来,在社会契约论的模式中,主权者虽然是通过社会契约获得权力的,但他不可能作为契约当事人与臣民缔结契约,“否则他就必须将全体群众作为一方与之定约,要不然就必须和每一个人分别定约。将全体群众作为一方与之定约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那时还不能成为一个人格。要是有多少人他就订立多少单独的信约,那么在他有了统治权之后,那些契约就无效了”c同上书,第134页。。在国家状态之中,主权者本身就是判定契约效力的最终的依据和裁决者,契约只能存在于平等主体之间,因此一种能够约束主权者的契约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中世纪的臣服契约与近代国家理论中的主权概念互不相容。康德后来在一则反思中精确地将这一反驳概括为“在主权者与社会的成员之间不存在契约”(XIX R 7759)。
可以说,霍布斯全面反驳了在博丹那里所残留的论证暴力反抗主权者的权利的可能进路,从而确立了拥有不受限制的至高权力的主权者的地位,但他以自然权利为起点论证国家的必要性的理论进路却同时为抵抗权的论证开启了另外一条进路,即基于自然权利的论证。在霍布斯看来,每个人在先于国家的自然状态之中都拥有自我保全的自由,这是唯一的自然权利和个人的行动决策的最高原则,其普遍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性和情感倾向之中,人们正是为了自我保全的目的才建立国家并无条件地服从于主权者。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之下以自我保全为目的的自由必然是恣意的、无规定的,虽然从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状态意味着这一自由通过被公共权力所抑制转化为法律下的自由,但既然自我保全始终是人的行动的最高原则,这就在逻辑上留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国家权力的行使危及了个人的生命,那个人就可以免除对国家的服从义务甚至反抗国家,因为自我保全是每个人不可放弃的自然权利。“如果有一大群人已经不义地反抗了主权者或犯了死罪、人人自知将因此而丧生,那么这时他们是不是有自由联合起来互相协助、互相防卫呢?当然有,因为他们只是保卫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不论有罪没罪的人都同样可以做。他们当初破坏义务时诚然是不义的,往后拿起武器时虽然是支持他们已经做出的行为,但却不是一种新的不义行为了。如果他们只是为了保卫人身,便根本不是不义的行为。”a霍布斯:《利维坦》,第 170 —171 页。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关于自然状态和国家的理解上与霍布斯有极大的不同,但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对革命的权利的论证正是基于同样的进路:以自然权利来论证革命的权利。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人生而拥有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由此派生的自然权力,即对侵害这些自然权利的行为自主进行裁判和处罚的权力。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就是让渡自然权力给政府以保护其自然权利的过程,这一目的本身就设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从目的上它不能超出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限度,从手段上它不能超出人民所能转让给它的自然权力的范围。社会契约所表达的同意构成了人民的政治服从义务的基础,因此政府权力的行使一旦超越了必要的限度就构成了违约,人民就有权免除自身的服从义务,甚至反抗政府。正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所明确表达的:“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需再予服从,而只有寻求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b洛克:《政府论》 (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9页。由霍布斯和洛克所开启的这一进路构成了自然权利学说论证抵抗权的基本范式,因此康德在自然权利学说的语境之中若想坚持自己拒斥革命的立场,首先就必须令人信服地反驳这一论证。
二、第一重拒斥:权利的逻辑
康德并没有像其他保守主义的思想家比如伯克那样诉诸历史进程中超越人的理性的智慧为现存的秩序辩护。c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州、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页。相反,他首先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一个基于理性权利的进路之上的论证:我们在逻辑和理论上无法证成一种暴力反抗现存的最高立法权力的权利,因为后者的存在恰恰构成了一切权利得以成为可能的现实基础,因此暴力推翻现存的最高立法权力,无异于消解了权利的一切现实性基础并最终否定了权利的概念。这构成了康德反对政治革命的最为基本的理论理由。
康德的反驳的出发点是:自然状态之中并不存在任何确切的权利。与霍布斯和洛克不同,康德并不认为自然权利就是每个孤立的个体在自然状态之中就能够拥有的确凿无疑的权利。正如黑格尔后来在《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中所批评的,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自然权利学说对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规定仅仅基于某种经验的任意性,而未能为偶然的东西与必然的东西之间的界限提供一个先天的判定标准。aG. W. F. Hegel, Hauptwerke in sechs Bände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9, Bd. 1, S. 425.在康德看来,我们只能从理性的先天立法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的自然权利,它们相对于实证权利所指的只是“基于纯粹的先天的原则之上”(VI 237)的权利,换言之,它们是与理性的先天原则相符合的、处于普遍的外在立法之下的每一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都应当拥有的权利。在康德的法哲学之中,构成论证的规范性起点的是一种天赋的权利,它所指的是这样一种“自由(对他人的强迫的意愿的独立性),只要其与每个人的自由依据一条普遍的法则能够共存,就是这一唯一的、原初的、每个人凭借其人性即被赋予的权利”(VI 237)。康德也将其称为内在的“我的”和“你的”,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这并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更为关键的是,即使我们承认每个人凭借其人性都应该先于国家而拥有这样一种自由,它也并非自足的。人生而应当拥有的并非恣意的、无规定的自由,而是能够与他人的同等自由共存的外在行为的自由,但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个体首先就无法确定自己的自由的边界,因为这一边界是理性所无法先天地认识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共存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始终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的那些主观的条件,就是康德所理解的权利:“权利是这样一些条件的总和,在其之下每个人的意愿与其他人的意愿根据一条自由的普遍法则可以被联合起来。”(VI 230)权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共存成为可能的条件,而每个人作为与他人生活于共同的时空之中的经验存在者,他自身的实存和持存都意味着,他在他的行动之中必然要排他性地占有某些外在于自身的东西,并因此与他人处于潜在的冲突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共存因此并不能像几何学那样通过划定人的行动空间就得到实现,而是首先要确定人对外在的东西的权属,这就是所有权,而在康德看来,这在自然状态之中恰恰是不可能的。
康德的这一分析首先揭示了权利的本质,它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愿的关系,是为了界定“我的”和“你的”而产生的。对于卢梭意义上的孤立无依的自然人而言,权利的概念毫无意义。而霍布斯所赋予自然状态中的人的那种恣意的、无规定的自由,从根本上就不符合权利的定义,这种自由的实现非但不能在共同生活的人与人之间建立起行动的边界,反而使得人与人必然地陷入权利的争端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霍布斯而言,从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状态并非自然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或实现的过程,反而是自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公共权力所抑制的过程,这就埋下了公民状态之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无法得到裁决的冲突的根源。与之相比,洛克从一开始就没有将自然权利所包含的自由理解为恣意的自由,并且通过自然权利与自然权力的区分避免了霍布斯所遭遇的困境。但洛克从一开始就将自然状态视为“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a洛克:《政府论》 (下篇),第5页。,这固然部分源自他对人性的乐观假定,但更为根本的是出于他对权利的本质的错误认识。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独立于所有其他人的意志而仅仅通过自己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对外在物的权利,这意味着他将财产权视为人与物的关系。洛克在这里实际上混淆了纯粹物理意义上的占有和具有权利意义的占有,即康德所说的经验占有和理智占有之间的区别。自然状态中的人诚然可以通过劳动在物理上占有某一外在物并排除他人的染指,但这一物体一旦脱离他的直接控制,他便没有任何依据再去排除他人的占有和使用了。具有权利意义的占有必然是一种即使并不在物理上控制某物也能约束他人的意愿和行为的排他性的权利,正如康德所指出的:“当我(在语言上或通过行为)宣称我希望某个外在的东西是我的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宣称,所有其他人都必须避免染指我的意愿的对象”(VI 255)。所有权的实质就是通过单方的意思表示去约束所有其他人的行为,而这在自然状态之中恰恰是不可能的。只有存在共同的外在立法的地方,个人的单方意愿才能以共同的立法权力为中介获得这样一种约束性。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国家之中,所有权才是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的共存也才是可能的,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国家状态就此成为实践理性的一个无条件的定言命 令。
自然状态的这一缺陷并非出于人的认知的欠缺,也与对人性的善恶假定无关,而纯粹是在缺乏共同的外在立法的情况下在人的共同生活的实践中必然存在的问题,因此也就不能期待当人们的认识进步到几乎穷尽了理性法的所有先天规定之后,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到时候人们就不再需要国家了,相反,在康德看来,国家必须“永久存续”(VI 326)。对于洛克来说,通过暴力反抗政府从而重返自然状态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自然状态虽有诸多不便,但已然是一个自由的完备状态,但对自然状态的这一理解事实上建立在他对所有权的实质的错误认识之上。对康德来说,重返自然状态是理性所绝对禁止的,因为这消解了权利的一切现实性基础,而堕入了一个“权利的真空状态(status iustitia vacuus)”(VI 312)。自然状态仅仅是人基于其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格应当拥有却无法真正拥有自由的状态,因此理性为了实现其所赋予每个人的自由,必然要向所有人颁布一条无条件的法则:“脱离自然状态!”(exeundum e statu naturali) (XIX 243)任何试图赋予个体以积极抵抗权的规则都必然与这一条法则相矛盾,因此都不可能在理性面前得到辩护,所谓的积极抵抗权无法通过自然法或自然权利得到论证。
在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之内保留一种暴力反抗最高权力的权利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也不可能以合乎权利的方式被执行,正如康德所指出的:“为了使人民有权反抗,就必须存在一条允许人民的反抗的公共法律,这意味着,最高的立法在自身之内包含着一个规定,自己并不作为最高的立法而存在,并使得作为臣民的人民在同一个判断中成为人民所臣服的主权者,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而这一矛盾通过这一问题将会立即凸显:谁应当在这一人民与主权者的争端中担当法官呢?(因为从权利的角度来看,他们毕竟总是两个不同的道德人格)这表明,人民希望在自己的事务上担当自己的法官。”(VI 320)康德在此实际上是重申了霍布斯的主权概念和一个关键的问题:谁来判断(Quis judicabit)?而霍布斯虽然并不认可国家权力需要受自然权利的约束,但他将自我保全视为人的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却会在逻辑上造成政治秩序的悬置甚至解体:在一个死刑判决中,国家有权力以暴力保证判决的执行,而被告也有自由为了自我保全以暴力反抗这一判决。在康德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仍然停留在自然状态之中,“当每一个人都仅仅依据他自己的判断和运用他自己的力量去追求他所认为的权利的时候,他所处的就是战争状态”(XIX R 7945)。洛克当然也不认同将判断的资格因此是反抗的权利授予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因为这将意味着政治秩序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一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作为集体的人民。“如果在法律没有规定或有疑义而又关系重大的事情上,君主和一部分人民之间发生了纠纷,我以为在这种场合的适当仲裁者应该是人民的集体。”a洛克:《政府论》 (下篇),第156页。但洛克在此很显然预设了一个实体性的人民概念,而并没有为此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论证:超越现行的法律制度所设定的程序,人民如何能够作为一个集体表达和贯彻它的意志?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恰恰是通过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立法权力,一群人才能聚合为人民。如果人民自身就是主权者,它当然有权去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但在这一情境中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抗最高权力的权利。
对抵抗权问题的进一步追索必然会触及政治理论中所通常存在的依据理论建构的理想国家与现实存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霍布斯和洛克都将个体对国家的服从义务归于社会契约所表达的同意,因此社会契约构成了政治权力的正当性的来源。而霍布斯通过将主权者置于契约当事人之外而捍卫了主权的绝对性,使得对政治权力的正当行使的约束成为不可能,但既然将同意视为统治的正当性基础,他就得面对依约建立的政治性国家与通过暴力建立的自然国家之间的对立问题。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事实上摒弃了绝对主权的概念,并提供了关于理想的政治秩序的一个范本,但他仍然需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统治的正当性需要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那我们该如何面对现实中那些并非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或者其制度并不完全符合这一契约的国家?在一个依据理论建构的理想国家之中,讨论人民的反抗权是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面对经验和历史之中的那些必然存在缺陷的国家。
洛克实际上为国家的开端设置了一个基于特定的自然权利之上的最低限度的门槛,并将那些没有达到这一门槛的国家统统剥夺了正当性。但这一视野中的国家只能是现代国家,国家的产生似乎仅仅是一个现代历史的事件。与之相比,康德则更倾向于将国家的发展或人的权利的实现视为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并因此对那些即使在当下的正义视野之下仍然不够正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但康德并没有就此放弃理想政治的信念,他并不接受霍布斯的君主不会对臣民行不义的命题,在《论通常的说法》中他就明确指出:这样的命题是“极其可怕的”(VIII 304)。在其法哲学中,康德致力于为人类的共同生活提供一个基于理性的先天立法的规范性基础,并借助一个假定在理性上会得到所有人共识的原初契约的理念,推导出完全合乎理性的共和国的理念以及一个世界公民主义的全球法治秩序。康德承认存在一些我们能够据以评价现行的国家权力的运行是否合乎正义的超实证规范,但并不能就此否定经验和现实中那些不符合原初契约的理念的国家的统治的正当性,因为这两者在论证上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在康德看来,社会契约并非一个经验事实,也不能构成公民的政治服从义务的依据。通过服从于共同的立法权力从而摆脱自然状态是实践理性基于人的权利的实现的理由而颁布的定言命令,因此政治服从义务的基础并非个体的同意,而是理性自身的要求。但理性要求个人所服从的并非像赫费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完全符合原初契约的本体国家(respublica noumenon)aOtfried Höffe, „ Königliche Völker “: Zu Kants cosmopolitischer Rechts-und Friedenstheorie, S. 24.,因为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作为“一切公民制度的永恒规范”(VII 92)为存在于经验中的现象国家(respublica phaenomenon)提供借以观照自身的不完善性并由此持续改善自身的范 本。
借用康德的范畴表,如果说在国家状态与自然状态之间是模态的差别:权利的有与无,那在不同的统治形式之间则仅仅是量的差别:权利的多与少。任何经验和历史中的国家,不管其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只要能够通过普遍生效的立法界定了人与人之间的“我的”和“你的”,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权利,因此即使尚未具备充分的合义性(Rechtmigkeit),也已经具备了可以要求公民的政治服从的合权性(Rechtlichkeit)。aRobert Spaemann, “Kants Kritik des Widerstandsrechts”, in Materialien zu Kants Rechtsphilosphie, hrsg. von Zwi Batscha, Frankfurt/M: Suhrkamp Verlag, 1976, S. 348.正如康德在《论永久和平》的一个脚注中所说的:“这就是理性的许可法则,它们允许一个带有非正义的公共权利状态得以延续,直至它要么自己成熟起来,要么通过和平的手段被引向成熟而足以变革一切:因为任何一个合乎权利的(rechtliche)的制度,即使仅仅在细微的程度上是合乎正义的(rechtmäßige),也要好于没有制度,后一种命运(无政府主义)是过于急促的改革所将遭遇的。”(VIII 373)人的权利的实现并非始于现代国家,虽然现代国家的确是人们在那个阶段所能够获知的实现人的权利的最佳模式,但在现代国家出现或被普遍建立之前,个人的权利在前现代的政治秩序之中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实现。康德很清楚,政治秩序的历史开端并不建立在人为建构的社会契约之上,相反,在历史中其往往是由暴力行动所促成的,但这样的秩序一旦被建立了,就其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或民族已然身处其中并由此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权利的现实秩序而言,也就构成了他们唯一能够以合乎权利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其理性权利的出发点。从人的权利的现实化的角度来看,自然状态而非暴政才是人所应当无条件避免的政治的“首要恶”bWolfgang 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Immanuel Kants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 Paderborn: WBG,2007, S. 374—375.,因为它是权利的真空状态,意味着权利的彻底丧失。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才会主张:“服从于现存的国家权力,不论其源出何处!”(VI 319)但这里对抵抗权的拒斥并非出于秩序的理由,而归根结底是基于权利自身的逻辑。
但康德所禁止的仅仅是暴力的反抗,因此也为某些非暴力和非强制的反抗保留了空间。虽然在他看来臣民只有通过言论进行反对的权利,但行动上的服从也并非绝对,政治服从义务仍然有其界限。首先,并非在所有秩序,而是只有在某种权利秩序中,个体才负有政治服从的义务。比如在奴隶制中,因为被彻底剥夺了权利主体的地位而被当作纯粹的物看待,奴隶也就不应当承担包括政治服从在内的任何义务。在《权利学说》中,康德明确否认了“人与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存在者之间的权利关系”(VI 241),所以在奴隶制下奴隶暴力反抗奴隶主的可辩护理由并非奴隶拥有暴力反抗奴隶主的权利,而是奴隶并未负有服从奴隶主的义务。其次,即使是在某种权利秩序之中,个体的政治服从义务仍然有可能受到内在道德的限制。在理性的立法中,法律义务与伦理义务当然是不存在冲突的,但是实证法义务与伦理义务的冲突却是完全可能的。在《权利学说》的附录中,康德就对设定服从义务的定言命令给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表述:“服从于对你们拥有权力的最高当局(在一切不违背内在的道德的事情上)。”(VI 371)但在这种义务的冲突之中,尤其是当实证法义务的履行会侵犯到第三者的时候,个人应该如何行为?内在的道德规范并不能取消人的外在的服从义务,暴力的反抗当然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个人在这种情境中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以违背道德的方式履行实证法义务,要么以违反实证法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方式去遵守伦理义务。康德当然会赞赏后一种选择,但在这里反抗仍然不是一种权利,因为对伦理义务的遵守并不能在法律上构成要求责任豁免的抗辩理由,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通过个人牺牲去克服遵守伦理义务的外部障碍却会赋予这一行为以更高的道德价值。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康德对积极抵抗权的拒斥实际上与当代政治哲学所主张的公民不服从是可以兼容的,因为公民不服从恰恰要求通过“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良知的然而是政治的行动去违抗法律”a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itce, 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64.。
三、第二重拒斥:政治的进路
康德对政治革命的拒斥当然首先是因为革命作为一种彻底消解政治共同体的存在的极端行动在逻辑上与权利概念无法兼容,这一点在他的法哲学中已经得到了很明确的表达。而在康德研究中往往会被忽视的是,在这一拒斥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康德的更进一步的与经验和历史相关的考虑:以革命的方式往往很难超越既有的历史条件飞跃式地建立起革命者所期待的与现存的秩序迥然有别的理想政治秩序。康德在他的法哲学中的确致力于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和现实的政治秩序提供一个由先天的—形式的权利原则所构成的规范性基础,但他并非一个无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而退居孤寂的书斋单纯在头脑中编造人类社会的理想图景的哲学家,因此在他对政治革命的反对中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出于政治的—实践的原因的考虑。但并非如人们通常所可能误解的那样,康德是被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恐怖所惊吓,从而在革命的问题上倒退回了保守的立场。事实上,康德对政治革命的反对态度在大革命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政治的—实践的层面,这一主张与他的政治改良主义的启蒙方案紧密相关,这构成了康德反对政治革命的第二重理由。而这一方案的雏形在康德于大革命之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业已被勾勒了出来,比如同发表于1784年的《世界公民意图中的普遍历史理念》 (以下简称为《普遍历史理念》)、《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以下简称为《什么是启蒙》)以及发表于1786年的《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等。
我们为什么不可能通过革命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治秩序?其原因首先在于,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对正义以及理想的政治秩序有一个整全的认识。绝对完善的政治秩序作为一个理念既不构成我们的理论认识的对象,也不可能通过实践在经验层面上被彻底实现,这与康德对理性理念作为调节性原则的规定相一致。虽然在法哲学中他试图基于理性的先天立法为人的自由的共存推导出一整套先天的权利原则的体系,但这一体系就其是先天的而言也只能是形式的,其中并不包含能够直接规范我们的行为和政治行动的完整的规则,而只有将这些形式的原则与具体的经验条件相结合,我们才有可能获知具体行动的规则。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权利概念并没有为自身提供任何对行为的指引。它必须与对世界状况的解释结合起来,唯有如此,它才能变成一个政治行动的方案。”aDieter Henrich, “Über den Sinn vernünftigen Handelns im Staat”, in Über Theorie und Praxis hrsg. von Dieter Henrich, Frankfurt/M: Suhrkamp Verlag, 1967, S. 35.这样的一个具体行动的方案(通过权利概念与具体的经验条件的结合而获得)要成为可能,至少要同时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作为对象条件的具体的经验情况和作为主体条件的将规则的形式与质料相结合的能力。而恰恰是因为对这两方面条件的要求,使得完善的政治秩序只能在历史进程之中被逐渐揭示出更为全面的面貌,而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被认识到。
从对象方面来看,由于现象世界的经验的杂多性,先天的权利原则需要应用于其上的经验情况永远也不可能被穷尽,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无法构建一个可以将所有的经验情况都归摄于其下的规则体系,甚至也无法去估测我们离一个现实可能的最完善体系还有多远。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针对理念国家在现象世界的实现所说的:“人性必须停留于其上的那个最高的程度将是什么,因而在理念及其实施之间必然留下的那道鸿沟会有多大,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当加以规定的,这也正因为它就是自由,而自由是可以超出任何被给定的界限的。”(III B 374)在《权利学说》中,他在谈及必然要将其在经验中的应用同时考虑在内的完整的权利体系之时,也坦诚我们“所能期待的仅仅是接近于体系,而不可能达到体系自身”(VI 205)。而这种接近只能是循序渐进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先于经验或脱离经验就能获知在经验情况之中能够进一步实现人的权利的具体条件,而只能在变动的世界之中通过与新的经验情况的结合持续地拓展我们对合乎理性的政治秩序的认识,在此意义上,现存的经验世界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的进一步认识所无法一步跨越的出发点。
与作为认识对象的经验的杂多性相对应的是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这一有限性不仅体现在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可能性界限去认识绝对的无条件者,还体现在人的包括理性和判断力在内的各种禀赋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康德虽然强调理性作为“我们的思辨的一切权利和主张的最高的法庭”(III B 697),但对于每一个现实的个体或群体而言,能够主张其运用的普遍有效性的成熟的理性并非一种现成的能力,其毋宁说是“一个仍然需要去获得的和人为的能力的理念”(V 240)。在《普遍历史理念》中,康德就很明确地指出:“理性并不依从本能而自行起作用,而是需要尝试、训练和教导,以逐渐地从一个见识的阶段进步到另一个阶段。”(VIII 19)这一过程就是人的启蒙,康德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人在历史中的持续启蒙与政治制度的持续革新的相关性,即理性的持续进步需要体现在外在的客观的政治秩序之上并在一个个世代之间传承。因此正如维兰特(Wolfgang Wieland)所指出:“不仅仅因为现实世界的生活条件的持续变迁,即使仅仅考虑到每一条普遍规范的应用所需要的条件,所有的实证法都已经指向了这一点,它们只能持续地被形成。”aWolfgang Wieland, “Kants Rechtsphilosophie der Urteilskraf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 52,H.1, Jan.-Mar., 1998, S. 20.形式的权利原则所要应用于其上的经验的杂多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我们首先在认知的意义上就不可能获知一个完全合乎理性的政治共同体的现实形态,因此只能在经验的历史中通过对现存的政治制度的持续改良去不断逼近,却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在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中,康德对人的自由在经验中的实现已经持有了一种历史的和生成的理解,而这种立场通常被归为费希特后期和之后的黑格尔所特有b贝克:《费希特和康德论自由、权利和法律》,黄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27页。,甚至是黑格尔在批评康德的形式主义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
但仅仅出于认知的理由仍然不足以反驳革命作为一种改进业已落后于时代的政治秩序的手段的有效性。我们无法超出既存的经验而获得对一个完善的政治秩序的现实形态的整全认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认识到比现行制度更为合理的政治秩序的现实形态,而意在克服现行制度业已暴露出来的巨大缺陷的政治行动并不需要以我们的前一种认识为前提。即使是在黑格尔的语境内,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夜幕降临才会展开它的双翼,但依据他对现存的事物与现实的事物的区分,理性仍然可以通过现存的事物在思想中把握到政治秩序的更具现实性的形态。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为之辩护的君主立宪制很显然并非当时的普鲁士体制。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的法与国家哲学要高于德国当时的政治状况。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而这种错位的另一个原因是:即使德国仍然停留在旧制度的经验和迷梦之中,在国家间的交往日益紧密的世界历史时代,英法两国的政治实践也已经提供了新的经验,并揭示了现代政治的原则和可供参考的具体规则。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考虑权利的问题而仅仅着眼于有效性的话,革命是否可以成为建立更为合理的政治秩序的一个可考虑的选项?如果我们可以站在康德的立场之上替他回答的话,答案应该仍然是否定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是否应该实现现代政治的原则以将自身在政治上提升到与时代同步的水平,关键在于:(1)在与旧制度相伴随的各种历史条件的约束之下,如何能够一如革命者所预期的那样建立起新的制度?(2)即使新的制度在形式上通过革命被确立了,其如何能够良序运作?
虽然在康德所设想的理想国家中,进行统治的将是法律自身,但这始终是一个理念,在经验世界之中,任何法律体系都是不完善的,也始终是不自足的,因此任何时候都需要人的政治实践作为补充和驱动,政治的规范性目的正在于实现权利的概念。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管是制度的可预期的革新还是制度的良序运转,都需要政治实践的主体具备某些特定的品质。在《普遍历史理念》中,康德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人作为动物都需要一个主人,否则其将不可避免地滥用自己的自由,但主人本身也是动物,也需要一个主人,“不管他是求之于一个个别的人也好,还是求之于为此而选出来的由若干人所组成的集体也好”,问题都依然存在。(VIII 23)不可暴力反抗的主权是政治共同体的构成性要件,但这样一个至高的权力只能掌握在人手里,因此始终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统治者也是人,这是所有的政治理论都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在康德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统治者身上,而在于人民自身。他在此明确诉诸人民的普遍的启蒙,并坚信“它必定会把人从其统治者们的自私自利的扩张计划下拯救出来,只要他们能懂得自己本身的利益。而这种启蒙以及随之而来的启蒙了的人们对于自己已经充分理解到了的好处所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的一种衷心的同情,就必定会一步步上升到王座上来,并且甚至于会对他们的政体原则发生影响”(VIII 28)。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进一步阐明了人民的启蒙何以能够遏制主权者滥用权力的冲动并自下而上地推动制度的持续改进。在该文的附录中,康德提出了公共性原则作为调和道德与政治的分歧的手段,他所诉诸的正是这样的实践的检验,即当我的一条不正当的准则被公之于众,“必然会不可避免地激起所有人对我的意图的反对”(VIII 381)。他在《系科之争》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敢公然宣称,他根本不承认人民有任何反对他的权利,人民只能把自己的幸福归功于将之恩赐于他们的政府的仁慈,而且臣民对这一反对政府的权利(因为这一权利自身中包含着允许反抗的概念)的一切妄言都是荒谬的,甚至是可罚的?——其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公开的宣告会激起所有臣民对他的反对。”(VII 86)诉诸人民的公开的反对,实际上已经对人民的启蒙提出了要求。人民不仅要有能力认识到特定的规则和决策的不正义性,而且要有足够的动力和勇气进行公开的反对,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权力的滥用并推动秩序的持续改进。人民必须有觉悟和能力积极参与共同体的塑造,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这正是《判断力批判》的那个著名的脚注所表达的:“人们在新近发生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彻底成为一个国家的事情上通常用有机体这个词来恰如其分地指称市政制度等等及整个国家体的建立。因为每个成员在这样一个整体中当然应该不仅仅作为手段,而是同时也是目的,并且就其共同促成了整体的可能性而言,每个成员借助于整体的理念反过来又依据他的地位和功能得到了规定。”(V 375)
当康德将调和政治与道德的分歧的希望寄于所有人的反对之时,并不意味着他容忍任何积极抵抗的方式。他在《论永久和平》的附录中借以说明公共性原则的应用的第一个例子正是对积极抵抗权的驳斥,人民对主权者的反对的方式因此只能是非强制和非暴力的。在《论通常的说法》中,在反驳了人民有暴力反抗国家元首的权利之后,康德随即指出人民还有一种不可离弃的反对权利,即对公共法律和政治决策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是“人民权利的唯一守护神”(VIII 304)。而在此前的《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一文中,他同样将表达自由视为“在一切公民的负担之下仍然留存给我们的唯一珍宝,只有凭借它才能抵御这一状态的灾祸”(VIII 144)。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康德会将表达自由以及建立在这一自由之上的公共领域视为理性的实存之所在,而他在政治的意义上对这一自由的论述所关注的始终是政治服从的界限,以及在服从之时如何始终保有更进一步实现人的权利的可能性的问题。《什么是启蒙》里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的区分正是对此给出的一个解答:理性的私下运用意味着在权威领域的服从,而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意味着在公共领域的自由批评。康德主张公民应该有“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VIII 37),因为正是在这一无损于政治服从义务的自由之中,他看到了人的持续启蒙以及由此推动制度的持续改进的可能性。通过理性的公开运用,一方面是公众在公共领域之中持续地自我启蒙,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获得了政治批判的力量,促使最高权力不得不进行政治改良以维持他的“立法的威望”,即韦伯意义上的民众的正当性信念。a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Mohr, 1972, S. 122.在《权利学说》中,康德明确指出在代议制中人民有一种消极的抵抗权,可以通过他们的代表去反对不正当的法律和政治决策。而如果人民的代表一直怠于行使这一反对的权利,这将表明“人民已经腐化了”(VI 322),他们已经失去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监督代表们尽责履职的能力。以启蒙不足或再度腐化的人民为基础的共同体,即使出于某种偶然的机缘在形式上建立了好的制度,也会不可避免地重新滑向专制主义。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英法两国的政治实践是否揭示了现代政治的原则,而在于德国人是否有能力去促成这些原则的持续实现。启蒙并不简单等同于知识的占有,知道某些原则并不等于有能力通过自我思考和公共参与去实现这些原则。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组织形式的民主制度的良序运行尤其需要有能力和意愿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监督权力的运行的公民,这只有通过启蒙才能达到——启蒙所要造就的正是有能力和勇气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
而在康德看来,人的启蒙恰恰不可能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虽然启蒙要求个体的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要求“人的内在之中的革命”(VII 229),但内在的革命并不能通过外在的革命来促成,尤其是这里所要求的并非单一个体的启蒙,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普遍启蒙。康德充分意识到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启蒙所将遭遇的困难。对于个体而言,在习惯了他人的照料之后,要从近乎本性的懒惰和懦弱之中摆脱出来并学会自主思考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充满了危险的,而只有依托于公共领域,启蒙才是可能的。只有在公共领域之中,个人才能被激发出主动运用自己的理性的积极性,也只有在与他人的沟通之中,个人才能学会如何进行普遍有效的思考。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被深深地嵌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只能与同时代人一起在交互影响和自我反思的关系之中逐渐地自我启蒙。启蒙并非某个单一个体的事情,而是一项公共的事业,这也就注定了它是“一件困难的而且只能缓慢完成的事情”(V 294)。而革命虽然在权利的意义上会造成一种断裂的状态,但并不会像后来的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可以造就一个新的开端a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被特定的传统和偏见所束缚的人们不可能通过革命就能一下子建立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正如托克维尔后来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所表明的,人们误以为是大革命的产物的许多思想、情感和制度,恰恰是旧社会的残余。b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页。在《什么是启蒙》里,康德事实上就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公众只能缓慢地通往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推翻个人的专制和贪婪心或权势欲的压迫,却不可能带来思维方式的真正改良,相反,新的偏见将会和旧的偏见一起成为毫无思想的大众的桎梏。”(VIII 36)激进的暴力革命不仅无法把控自身的走向,即使它取得了成功,也无法塑造新社会所需要的主体,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很难通过一场暴力革命建立起全新的秩序,而这直接与卢梭的革命观相对立。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明确地表达了革命对人性和习俗的改造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这几乎是一个已经被腐化的民族能够获得新生以配享自由的唯一希望,虽然这一作用也是建立在诸多的偶然性之上的。“正如某些疾病能震荡人们的神经并使他们失去对于过去的记忆那样,在国家的经历上,有时候也并不是不能出现某些激荡的时期;这时,革命给人民造成了某些重症给个人所造成的某些情形,这时对过去的恐惧症代替了遗忘症;这时,被内战所燃烧着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又从死灰中复活,并且脱离了死亡的怀抱而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c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页。卢梭在这里表达了一种浪漫主义的革命观,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际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塑造全新的社会主体:“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而康德很显然并不认同这样的革命观,在他看来,暴力革命非但不能让人摆脱旧的偏见而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反而会将人们抛入更深的偏见和对立之中,并因此不可能成为建立并维持全新的制度的主体,这构成了他反对革命的第二重理由。
四、结论
由此可见,康德对革命的拒斥并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对现实政治的妥协,而是包含着深思熟虑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合起来也就指向了一个以启蒙为核心的政治改良主义的方案,这一方案以在经验层面上实现一个合乎理性的权利秩序为目标,但其方式只能是渐进式的,正如康德在《权利学说》中所总结的:“如果它不是革命地,通过一个跳跃,即通过暴力地推翻迄今所存在的有缺陷的宪法——(因为这将会瞬间导致所有权利状态的解体),而是通过逐渐地依据固定的基本原则的改良而被尝试和被实施的话,那这一理念能够引导我们持续地接近最高的政治的善,接近永久和平。”(VI 355)人们当然可以进一步质疑康德关于持续改良的可能性的设想是否太过于乐观,尤其是在某些统治形式下持续的政治改良最终必然会要求政体原则的根本变更,改良这时就会触及无法逾越的限度。但是从权利论证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积极抵抗权的确很难获得辩护。唯一可能的辩护方式或许是像马克思那样,彻底摒弃权利的话语,转而从社会历史运动的角度去理解革命的必要性。但这对于西方近代以来以权利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而言,将会是更为致命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它的规范性基础的彻底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