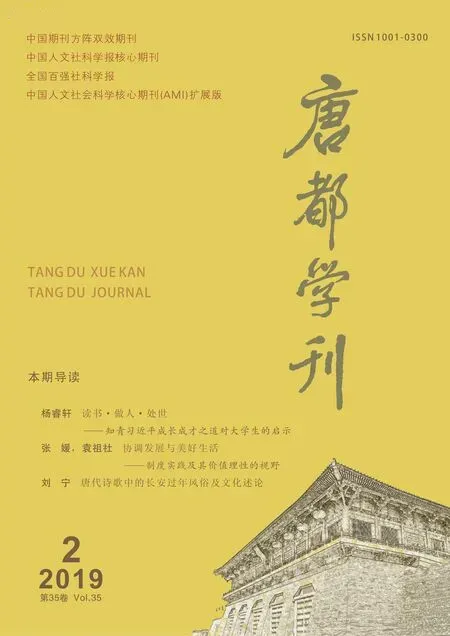程颢仁学对先秦仁学思想的超越与发展
刘君莉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在宋明理学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理学开创者之一程颢先生那里得到了独特的发展与诠释。本文以程颢的“仁学”为研究视角,试图说明以下问题:第一,程颢如何诠释“仁”;第二,程颢仁学对先秦思想的发展;第三,程颢仁学的理论困境与价值可能。
一、程颢论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众所周知,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提出“二程”思想之异同且开创了“理学”与“心学”二派[注]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程明道与程伊川”一节;对二程异同的解读以及二者作为理学、心学先驱的观点,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五十二章继续坚持并称为“道学的奠基者——二程”。,这基本得到学界的公认。近些年,相关研究认为“二程”思想从根本上有很大的差别,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除了理论形态与侧重点有所区别之外,二者在本体论上并无差别。但就明道先生与伊川先生的仁学思想来讲,二者也多有不同,陈来先生谈及二者关于仁的区别时,认为“程颢的仁说思想主要有三:以一体论仁;以知觉论仁;以生意论仁”[1]19。对于程颐的仁说,陈来先生认为:“惟公近仁;爱人非仁;仁性爱情。”[1]21所以本文承续学界此种研究现状,重点论述程颢的《识仁篇》中的仁学思想。
钟泰先生在论及明道“识仁说”时认为“明道教人,每单提仁字,故《语录》中有言仁处最多,而莫备于吕与叔(大临)《东见录》所记。后世因号之为识仁说”[2]206。明道所传文献不多,但谈到仁的地方不少,诸如:
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3]15
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3]15
观鸡雏此可观仁。[3]59
切脉最可体仁。[3]59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3]74
仁者无对。[3]120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3]120
以己及物,仁也。[3]124
人之一肢病,不知痛痒,谓之不仁。[3]366
上文陈来先生认为,程颢的仁说主要思想有三者应是由此总结而来,就此三者来讲,最能体现程颢仁说的是“以一体论仁”,这一思想在后人称为《识仁篇》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为有之,又安得乐?”[3]17由此可见,第一,程颢没有用爱释仁,而是以“生”作为“仁”的基础,如同医家所说那样无生机、无感觉便是“不仁”。关于这一点,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会看到程颢的《识仁篇》对“仁”的论述有别于儒家“以爱释仁”尤其是偏重以“孝悌”释仁的传统。第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或者说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这一点,我们又可以看到程颢受庄禅思想的影响而有别于先秦儒家的仁学思想。第三,仁者无对。尽管在《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一》中有记录云:“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3]121“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阴长则阳消,善增则恶减。”[3]123但在《识仁篇》及《明道先生语一》中明确提出“仁者无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明道的“仁学”思想继承了《易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传统,在对具体“仁”的解释上则与先秦时期的“以爱释仁”有所不同。下面我们追溯一下明道以前对“仁”的解读,由此可以看出明道对“仁学”的发展。
二、程颢仁学对先秦仁学思想的发展
众所周知,“仁”作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传统思想的核心地位似乎毋庸置疑,“以爱释仁”曾是儒家思想的主流,而且“孝爱”占据了很大的分量,逐渐形成了“立爱自亲始”的传统。
(一)以爱释仁作为儒学思想主流
1.孔子以“爱人”释仁
《论语》一书中虽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记载,但“仁”字出现达105次,孔子以“仁”为贵,承继并创新了“仁”的内涵,通过对《论语》中先后出现的“仁”字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语境中,孔子对“仁”有不同的解答,也有学者据此认为孔子并未对“仁”进行确切的定义,张岱年先生对此持相反的见解:“我认为孔子确实曾经给出关于‘仁’的明确界说”[4]。其主要依据是《论语·雍也》中子贡问仁时孔子的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种对仁的诠释含义深远,意味隽永。《论语》中其他条目关于仁的解析都不及此条全面深刻,而且唯有此条用了“夫仁者”,其他多处论仁,并未用“夫”字。
通过对《论语》中先后多次出现的“仁”字进行解读,大体上可将“仁”的解释分为三大类:“循礼”“力行”“爱人”。“循礼”的释义主要来源于《论语·颜渊》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条目,但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中记载孔子对楚灵王的评论:“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由此可以推出“克己复礼为仁”并非是孔子对仁的诠释,也并非是孔子的发明,孔子只是发挥并承继了“古志”。至于“力行”更是原来的观念,唯有“爱人”的观念是孔子的创见并力为凸显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何为“爱人”?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又将其简明扼要概括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孔子认为“循礼”“力行”最终也要归向“爱人”。区分“爱人”观念在儒家里面是有具体指向和次序的,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强调“爱”,不可因为都有此主张而模糊其差别,“爱”的来源、对象、次序往往是不同的,这才是关键,而这正构成了不同宗教的界限。
2.“以爱释仁”作为儒学主流
孟子绍述孔子,在《孟子·尽心上》中对于“以爱释仁”表述得更为明确:“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指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第三十》中说:“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董仲舒详细地解说了“什么是爱人并阐释了在行为上如何去爱人”。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北宋的周敦颐和张载进一步承继了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张载在《正蒙·中正》中提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
上面谈及,程颢、程颐对“仁”有不同的看法,程颢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颐则认为“仁者,公也”;南宋哲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学而》中对仁的解释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尤其是其《仁说》对“仁”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清代哲学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中提出:“仁者,生生之德也。”综上可知,仁最基本的含义是“爱人”,虽然不同思想家对“仁”有不同的看法,但只是扩大了范围,并未从根本上否定“爱人”的要义。而且我们发现,儒家的“爱”有很明确的次序,那便是“亲亲、仁民、爱物”,由此逐渐形成了“立爱自亲始”的传统。
(二)仁爱向“孝悌”观的演进:“立爱自亲始”
1.《易传》中的“天人合一”对“爱”观的影响
以《易传》作为文本依据。《序卦》中有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表达了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关系产生的次序,类似的说法还有《系辞下》中“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关涉人类的起源,中国经典文献中关于人与世界的生成是“化生”模式,这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没有创造主的位置。至于父母、子女的关系,在《易传·系辞上》载:“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并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大学》中也说道: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种由天地而生万物的模式,逐渐演化成“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由“男女构精”而“万物化生”,因此,夫妇进而父母作为“生”的角色被确定下来;从属性上天尊地卑,随而产生男尊女卑之关系。《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可见,由“天地”“阴阳”而仁义的大致思路。正是在这样的思路背景下,儒家仁爱的观念不可能产生像Agape那样,是来自神的;首先的爱是敬畏神、尽心尽性爱神;儒家认为人之产生,来自父母,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天地有阴阳,人类有男女,正是基于阴阳之道,男女进而夫妇进而父母来繁衍人类的,所以爱的首要次序是“亲亲”。
2.“立爱自亲始”所奠基的“仁爱”观
据《诗经·生民》记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此处的“生民”是为了“禋祀”;在《圣经》中也涉及对上帝的“祭祀”问题,而且有专门的“祭司”,但这里我们需要做出澄清,同样是“祭祀”,一个是对“祖先”(其实是人),另一个则是针对“独一真神”,这是不同的。就如同上面提到的中国语境中关于“不朽”的问题一样,这不是“灵”的问题,而是死在他国还是死在己邦的问题,叶落归根,魂归故土,有后人祭祀怀念这便是“不朽”了;同样,还有“民先神后”的问题,还有“民为神主”的问题,确切地说,中国文献里不是没有“人与神”的问题,不是没有“不朽”的问题,但是中国古人都给予了一种“人言”而非“圣言”的解读,都给予了一种“此岸”而非“彼岸”的解读;不是没有爱,而是说,这爱不是来自上帝或者“神”“造物主”,这爱来自人伦,源于双亲,《礼记·祭义》中有详细的记载:“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这里至少涉及两个问题:爱的起源与爱的差等。正是从爱的差等中反映并推出爱的起源,孟子所言的“亲亲仁民爱物”更是凸显了这种关系,爱是从父母开始的,“立爱自亲始”“百善孝为先”,“孝”在中国的思想世界里不仅是一个伦理观念,也是一种“立己之学”“成人之学”,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中,人并非来自上天,而是源于父母,化生万物时“天地不仁”因此是没有爱的,人伦演化,礼乐形成,依据人伦孝悌,人与人产生了爱的关联。而在西方语境中,却与此不同,是在神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了爱;这也决定了各自的道德哲学中最大的道德律令是爱人还是爱神的问题。
在《礼记·问丧》中有这样的记载:
或问曰:“杖者以何为也?”曰:“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则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处也。堂上不趋,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儒家过于看重人情这是不争的事实,儒家所建构的社会被称为“人情社会”,这似乎也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建制形式,大抵与儒家对世界和人的生成方式理解有关,自然万物是阴阳化醇的结果,人类繁衍是“男女构精”的结果,父母抚养孩童“三年免于父母之怀”,因此父母过世当为其“守丧三年”,这些都是“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这些基本上构成了儒家“仁爱”观的范围与主流。由上可见,程颢的仁学对先秦仁学有所突破。
(三)程颢仁学对先秦仁学思想的发展
程颢仁学对先秦仁学思想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注重天地万物之生意,而不仅仅限于“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先秦思想的核心特征之一,但是儒家的演进逐渐更侧重“人情”,由此而有“立爱自亲始”的偏重,尤其是孟子对“亲亲仁民爱物”次序的确立,这些在张载及程颢那里都有所打破,无论是张载的“民胞物与”还是程颢的“与万物浑然同体”,都是对先秦儒家过于注重“亲情”的推进。第二,“孝悌”非“仁”,这在程颢和程颐那里都明确区分开了“孝悌”与“仁”,认为“孝悌”只是“为仁之本”而不等同于“仁之本”[3]125-183,这一思想被朱子继承下来。而在先秦时期,尤其是在孟子那里,仁与“亲亲”几乎有着“等同”的关系,而且他将“仁—孝悌—仁政”联系起来,此种建构在程颢那里没有见到。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应当说是对先秦“仁学”的放大和拓展,毕竟在孔子那里“爱人”并没有明确说明“人”的范围与次序,而程颢建基于“天地之大德曰生”来立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应当说是可贵的,至少有利于避免孟子所确立的“亲亲仁民爱物”的自悖性结构。第三,“仁者无对”思想将“仁”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本体论地位,这在先秦时期是没有的;先秦时期具有此种表述的概念是“道”,而程颢则基于他对“仁”的新诠释而提出“仁者无对”是空前的,仁由此而达到了与“道”同等的地位,而且也只有在这一层面,“仁”在儒家思想的范畴体系中才处于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在《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一》中有记录云:“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3]121“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阴长则阳消,善增则恶减。”[3]123程颢明确提出“仁者无对”,虽然他对此没有明确地论述与展开,但就此命题的新颖性与独创性来讲,无疑是对先秦传统的另一种创造性诠释。
三、程颢仁学的价值困境及其重建可能
程颢对先秦时期的“仁学”思想虽有上述难能可贵的推进,但就其当代价值言,依然面临如下困境:
(一)仁学理解上的泛化
如果说“以生意论仁”是对《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传统继承,那么“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则更近于道禅而非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程颢在《二程遗书》卷2上中说:“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在《答张横渠先生书》中明确提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内外”“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两忘也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3]460-461这些都有浓郁的道禅味道。陈来先生在评价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时说:“程颢的仁说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它不像张载的《西铭》那样具体地表达为亲亲、仁民、爱物,表达出以爱为基础的伦理情感,从而难免流于泛言和抽象,这就无法清楚地与墨家的‘兼爱’、名家的‘泛爱万物’、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等其它一体说区别开来。”[1]21钟泰先生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明道何以悟及于此,要得力于禅学为多。夫‘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及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及所谓法无有比,无相待故也(六祖语)。”[2]207
程颢出入佛老数十年所受的影响,自然并非说佛老不可以借鉴汲取,而是“与万物同体”“自然而然”乃至“两忘”的说法毕竟是对儒家根本思想的偏离。而且,结合此说的当代价值来讲,它似乎更多的是佛道意义上的“浑然”与“无为”,而没有现代社会那种“天人和谐”“尊重他者”的意识,这构成了程颢“仁学”之当代价值的一重困境。
(二)家国同构的悖论
程颢的仁学超越了孟子“仁—孝悌—仁政”的结构,注重仁的本体性与开放性。在仁与孝的关系上,就所见到的文献来讲,程颢对“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的解释是“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3]125。倒是程颐遵循了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观点说:“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3]310而程颢的视域更宽阔了,在《陈治法十事》第四事中,程颢说:“庠序学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者也。”[3]453可见程颢对于“修齐治平”模式的认可,但此种家国同构的模式却有难以避免的自悖性困境:它无法建构社会共同体,而是走向共同体的解构。因为确立一个社会共同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一,共同的价值观;其二,价值观无悖于社会共同体。毋庸置疑,儒家是满足第一个条件的,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较为深远的“三纲五常”,儒家的问题在于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儒家的价值观是“家族”的而非“社会”的,是类似于“宗族团体”而非“社会共同体”。这是儒家致命之处,“孝悌观”是儒家仁爱观的核心,但“孝悌观”是家庭伦理,最终形成的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士绅社会,无法建立起法律至上的公民社会、城邦社会。正是基于此,我们说儒家仁爱观存在家国同构的悖论,这构成了程颢“仁学”乃至整个儒家“仁学”的第二重困境。
(三)“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与“他者意识”
上述的两重困境对建构程颢“仁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形成了很大的阻力和障碍,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现代张力,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的价值标准已被当今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取而代之,关涉人际交往,不论亲疏远近,人人平等,尊重他者显得尤为重要,程颢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为出发点,提出“浑然与万物同体”,类似于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彰显了对他者之平等与尊重。以“浑然与万物同体”释“仁”,些许契合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尽管在程颢的语境中不可能淡化更不可能打破“亲亲仁民爱物”的次序,但“与万物同体”则可以推出“人—我—他”间的共有价值,而且可以推出“同理心”与“同情心”,这是一种价值建构的可能性路径。在此意义上,明道“仁者无对”这一思想具有明显的现代意味,“无对”便是“绝对”,任何文化体系下的“绝对”都具有类似于本体的地位与作用。这样,基于“与万物同体”的对“他者意识”人权的尊重成为首要价值,这是第一原则;现代社会正是在此原则上建立起了公民社会,注重民主、法制皆是源自对个体“他者”人权的尊重。
综上所述,程颢以“一体释仁”,在“注重天地万物之生意而非血缘亲情”“孝悌非仁只是为仁之本”“仁者无对”三个方面有别于先秦儒家以“孝爱释仁并与仁政”同构的“仁学思想”。就学理上讲,这是对先秦仁学的继承与推进;其缺点在于受道禅影响颇深,有流于“无为”“两忘”的危险。就其现代价值来讲,“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及“仁者无对”的思想可以作为基于中国思想语境建构现代价值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