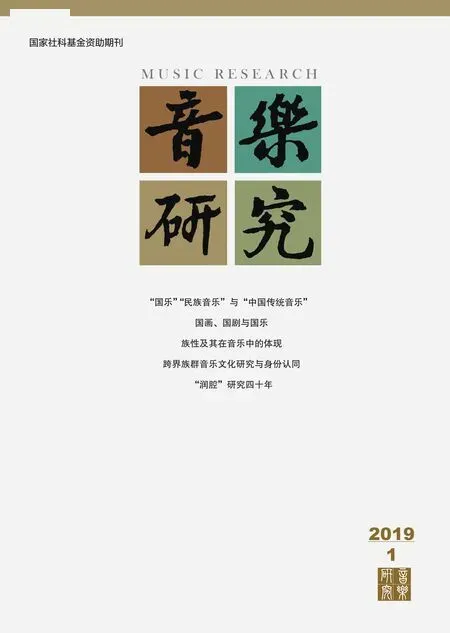乐器、身体与文化认同
——以安达组合演奏的冒顿潮尔为例
◎魏琳琳
音乐作为一种复杂的符号形式,有着自身固有的、多重的特征(诸如旋律、节奏、节拍、音色、音质和结构等),这些符号形式作为文化认同研究的基础和表征,为认同的多重性提供了音乐学层面的元素。当音乐作为一种表演、一种语境时,它似乎为表达不同语境中的多重认同,提供了丰富的舞台。①蒂莫西·赖斯著,魏琳琳译《民族音乐学中音乐与认同的反思》,《音乐探索》2014年第2期,第53页。乐器作为一种器物,是音乐的象征性表达,是一种预期目的的物质实现,是人类活动中音乐普遍存在的证明。在对乐器的研究中,有一种尚未引起注意的现象,即研究乐器扩展人体产生声音的能力,以象征的方式与身体接触,通过乐器在不同文化中的使用方式,从而表征文化认同。
安达组合是近年来中国蒙古族音乐走向世界的民族音乐组合,他们的音乐及表演形式,在保持自身传承与文化身份的同时,将全球化理念融入其中得到了海外受众群体的高度认同。乐队组合中所使用的乐器(包括马头琴、拖布秀尔、冒顿潮尔等)都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其中冒顿潮尔(Modonchoor)因其特有的音色在蒙古族音乐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本文通过乐器与身体的互动及民族志个案的描述,关注冒顿潮尔作为一件世界性乐器、广义跨界族群的产物,通过不同表演语境中表演者的个性化表达体现了现代民族的文化诉求,从而彰显不同程度的认同阶序关系。
一、身体互动语境中的乐器
乐器是身体的延伸,它可以提供一种身体的实践,一种创造声音的身体空间的扩张。它是一种旨在创建共鸣的装置,一种与更大的人体共鸣体有着交集的共振体设计。乐器是身体的外在表象与符号,它更是身份认同作为一种观念的表达,演奏者通过乐器将身份认同加以表征。
谈及乐器与身体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回顾器官学。器官学来自于生物科学,起源于“有机科学”这个词语。在音乐学语境中,曾经被普雷托里亚斯(Praetorius)在其著作中用来指乐器。20世纪40年代,“器官学”曾一度出现在音乐学领域,但对分类和类型学的关注往往集中于乐器的物理属性,而社会功能则被划分到民族音乐学领域。玛格丽特·卡托姆(Margaret Kartomi)在《关于乐器的概念和分类》中从世界范围内考虑乐器的分类历史和文化维度,从变量中关注乐器的分类现象。②Margaret Kartomi, On Concept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Musical Instrumen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虽然器官学关注分类和分类学,但其自身的身份是不稳定的。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系列的精选报告》中,苏德·维尔(Sue De Vale)将器官学作为一种“利用多学科的技术和方法”对“动态系统网络”加以阐明和扩展,这些可扩展的框架包括乐器的物理尺寸、历史轨迹、声学特性及社会背景等。③Sue Carole De Vale, Organizing Organology." In Selected Reports in Ethnomusicology", Volume 8:Issues in Organology, edited by Sue Carole DeVale, 1-28.Los Angeles: UCLA Press, 1990.维尔指出,乐器研究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缺失是显著的。随着以上学者对乐器研究多维方法的呼吁,笔者认为我们对乐器研究的态度应该从全景概览到敏锐的民族志研究,通过对乐器本体及音乐形态的分析,讨论身体互动关系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正如王建民教授从人类学的立场上审视艺术品和工艺品时,提出从器之体(材质)、器之形(形制)和器之用(社会功用),延展到器之性(社会文化属性)、器之礼(制度、仪式和秩序)、器之神(信仰崇拜)、器之品(格调)、器之美(审美)、器之韵(精神意涵)、器之情(情绪情感)等不同方面,以及与器物打交道的人在不同场景中如何处理和变通进而引申出“道”。④王建民《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第5页。
冒顿潮尔起源于游牧文明,目前世界上约二十多个国家使用类似的吹管乐器,其名称、材质、开孔则有所差异: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⑤中国主要流传于内蒙古、新疆阿勒泰等地区;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在下文中简称“图瓦”。三个地方从名称称谓上较为相近:中国叫做“潮尔”(Choor),蒙古国叫做“楚尔”(Tsuur)。图瓦叫做“苏尔”(Shoor),哈萨克斯坦叫做“斯布孜格”(Sybyzgy),土耳其叫做“内”(Ney),巴士几内亚叫做“库拉乙”(Kurai)。⑥据青格乐介绍,常用的“冒顿潮尔”其术语存在很多争议,“冒顿”译为“木质的”,顾名思义是用木材制作的潮尔称为冒顿潮尔,其他材质制作的也可能有着不同的名称,准确地称谓应该是“吹奏潮尔”或“潮尔”。但是由于学术界较为统一习惯性称为冒顿潮尔,所以,本文为了便于表述,统一将乌梁海风格的潮尔用“冒顿潮尔”表述。从材质上看,该乐器最初选用红柳或幼嫩的落叶松苗,或者选用一种类似芦苇,较为坚硬的空心植物——潮尔草(jiaala)制作,后来慢慢改用木质、竹质,发展到现今铜质制作。从开孔及调式上看,中国和蒙古国的冒顿潮尔普遍吹奏五声调式,管身开三音孔;哈萨克斯坦“斯布孜格”有三音孔,也有五音孔;图瓦“苏尔”有四音孔或五音孔;土耳其“内”或巴士几内亚“库拉乙”可以吹奏七声调式,管身开一系列不均匀的三音孔或五音孔。安达组合冒顿潮尔乐手青格乐改良的冒顿潮尔为平均五孔等间距,这种平均孔的冒顿潮尔实现了自由转调,一支潮尔能吹奏出七种调。
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族群共享着这一同类吹管乐器,但冒顿潮尔特有的人体所发出的低音声部与乐器吹奏声音一起产生的双声关系,形成了蒙古族所特有的“乌梁海潮尔风格”⑦冒顿潮尔结合人体与吹管乐器同时发出双声是蒙古族所特有的,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乌梁海潮尔风格”。。土耳其的“内”、巴士几内亚的“库拉乙”在吹奏时则不需要人体喉咙发出持续低音,完全依靠气息经过口腔时气流的角度来决定音色,如果气流被垂直送入,则会发出乐器本身的音色;如果气流被倾斜送入,则会发出较为厚重的沙哑及泛音的音色。
乐器与人的身体、器官之间的关系是乐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几乎所有的音乐都是有形的,都是与身体相连的。⑧Jacques Attali, No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usic.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正如布莱金(John Blacking)认为“乐器与人是分不开的。乐器与人体接口的方式可以提供被赋予它对文化角色的洞察力。”演奏者在演奏乐器的过程中,身体需要与乐器进行互动,这种互动类似于布莱克所描述的:“一种互动和运动的普遍模式出现,这种模式通常与文化体验有关,它是由身体内部形成的,并通过能量流的模式来监控,这种模式超越了演奏者有意操纵的企图。”⑨John Blacking,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 edited by John Blacking, 1-28.London an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当然,冒顿潮尔在身体与乐器互动之前,必须充分意识到气息是动力源。虽然冒顿潮尔与其他吹管乐器一样运用气息,吹奏潮尔所耗费的气息量要远远超出吹奏其他任何管乐器所用的气息。冒顿潮尔将所运用的气息称为“tugjiye”⑩“tugjiye”译为气沉丹田。,演奏者吹奏乐器前首先要找到“tugjiye”,将气息拖长。吹奏的难度不在于气息量的大小,而是控制。据青格乐介绍,这件乐器并不要求拼命用力地吹奏,音的高低与气息的强弱大小关系密切,如特别松弛、饱满地吹奏会发出较低的声音,稍微用力便可以发出较高的泛音。同时,吹奏时候对气息的要求在于持续性,运用气息讲述一句完整的话,刻画出一副完整的具有空间感、立体感的画面。⑪个人访谈,青格乐,2018年7月1日。
身体的互动主要集中在气息、喉咙、舌、齿、唇的协调。演奏者首先将乐器顶住门牙,根据个人习惯放在嘴的一侧(左、右),将舌头顶住下颚,在吹奏之前运用气息经过喉咙的振动发出一个持续低音(基音),然后再经过胸腔、鼻腔、口腔,使气流从上颚和舌头中间穿过送到管内,使人声的持续低音与吹管的旋律同时发出双声音响。这里要说明的是,找准牙齿跟舌头的准确位置难度很大,舌头、上颚是气流经过的部位。同时,由于冒顿潮尔与身体的密切关系,演奏者需要通过改变嘴型及气息的变化从而吹奏出五声调式基础上的偏音fa、si。当然,冒顿潮尔在演奏中要区分基音与泛音的运用,即便基音与泛音同时进行,每个人的演奏也存在差异性,往往会在演奏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感觉和需要决定对基音与泛音的选择。在访谈中,青格乐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位冒顿潮尔吹奏者一定要有一把属于自己的乐器,适合自己身体的潮尔,必须要自己首先了解这件乐器,要有制作乐器的实际理念,并且使潮尔的吹奏养成惯性,制作适合自己的潮尔,每个人的牙齿与呼吸都不一样,你要习惯了一把潮尔后,你就要爱护自己的乐器。⑫个人访谈,青格乐,2018年1月15日。
可见,演奏者与乐器之间形成了身体、内心深处的对话与互动,他们通过身体、器官感知乐器,乐器是身体感知的一部分,其音高、音色受到身体气息、气流强弱的影响,源于与生理的密切关系,但也会受到心理的影响,正如赖斯谈到个人自我认同的界定时指出,认同是关于个人自我认同的基础,对于个人是一个心理问题。⑬同注①,第50页。它是一种内心深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的体现。同时,蒙古族通过特有的双声演奏技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表达了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族群认同。
二、音乐表演语境中的乐器
除了谈及认同所具有的归属感和自我理解特征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音乐实践在多重、多层次认同相互联系中的作用。安达组合在全球化、现代化、历史变迁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表演语境与历史空间,在长期的表演实践中传承着蒙古族传统音乐,同时基于曲目、音色等需要,他们会选择跨界族群使用的乐器体现着身份的多重建构。在这种复杂多变流动的文化认同变迁之中,他们实现了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
杨民康谈及音乐文化认同的概念时指出,应该依据文化与音乐的两重标准,允许存在主位和客位的两种视角。其中从主位文化持有者对该类研究对象——音乐或音声产品持有的观念认识出发,根据他们对研究对象的体验、识别、认定和创作表演行为及其音乐产品的性征来确定该项音乐文化认同事件的性质。⑭杨民康《“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研讨专题主持人语》,《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8页。演奏者对于乐器的选择是由文化实践者根据场景进行的,不同的表演语境决定不同的音乐行为。青格乐作为安达组合冒顿潮尔的演奏者和打击乐手,凭借自己对冒顿潮尔的理解,根据乐队整体音色、表演形式以及曲目演绎等需要选择形制与开孔适合的乐器,甚至会为了某首作品量身制作所需的潮尔。比如在合奏中,他会选择“库拉乙”“内”,而较少使用冒顿潮尔。问及原因在于,冒顿潮尔特殊的双声音色进入到乐队组合中,会产生一种不协和的音响效果,再加上冒顿潮尔本身通过人体气息所发出的双声相对较弱,从音量上无法与马头琴、托布秀尔等乐器抗衡。下面笔者列举一首安达组合作品《苏和的白马》,青格乐为了这首曲目煞费苦心,专门制作、购买了几支潮尔,聊到这首曲目,他说:
这首曲子的音准在合奏中总是出问题,我最理想的是常用的一件木质的“内”,但是音高还是偏高。马头琴用定音器定音是440赫兹,而我这件乐器是按照442赫兹制作的,本身从音准上就有偏差。如果演出现场有音响、话筒等扩音设备,我更加对音准没有把握。如果现场我一个人吹奏,不需要太多考虑音准、调式调性,反而可以自由发挥,但是大家合作时我必须考虑音准等。在合奏时,我吹奏的第一个音非常重要,如果偏高,整首曲子都会偏离。马头琴定弦是固定的,但是我没办法制作成固定的冒顿潮尔,那样的话,我的嘴完全不能动。冒顿潮尔偏偏又需要通过嘴和嘴型的变化来控制音高。所以,这首乐曲对我来说,非常有难度,对音准的要求也非常高。⑮个人访谈,青格乐,2018年7月24日。
在《苏和的白马》这首乐目中,需要马头琴、托布秀尔、低音马头琴、冒顿潮尔、吉他、打击乐等多件乐器的配合,合奏中势必要求音准,而且这种“音准”在平时的排练与现场演出中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基于整体乐队统一要求,青格乐只好将自己的潮尔固定音高,气息控制到他所说的“变态”程度,这样势必会磨灭冒顿潮尔的个性与即兴性,吹奏时要求演奏者的嘴形与气息非常精准,不得有任何变化和偏差。为了解决当下出现的问题,青格乐想了很多办法,换了几支潮尔,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音准的问题。于是,他决定专门制作一支按照440频率定音,且管身下面的几个孔为平均孔,上面的音孔向上移动的特殊潮尔。谈及这首曲目音准的时候,青格乐谈道:
这首曲目冒顿潮尔是从引子之后的旋律进入,对我吹奏第一个音的音准要求特别高,只要我一张嘴,便决定了整个段落是否偏离。长期因为这样的问题搞得我有些心理阴影,但是乐队组合的要求是正确的,我非常理解。考虑到整体效果,我必须做出调整,暂时放弃冒顿潮尔的个性。因为冒顿潮尔这件乐器灵动性很大,只要调整一个音孔,别的曲子就用不了,只好专门为了这首乐曲制作一支。这首曲子第二段落转入快板时又会出现一个特别难度的把握,需要有一个半音的转换,这就要求有很高的演奏技巧。⑯个人访谈,青格乐,2018年7月24日。
出于音色、和谐关系的考虑,安达组合所建构的蒙古族音乐风格既体现了自身的差异性,又认同包容着游牧文明的共同性。然而,一个音乐系统不只是特定的价值取向或社会背景的反映,而是一个社会文化、经济、思想和政治的公共表述,它是由个体或团体的身份认同构成的,通过音乐表演(包括乐器表演)来创造。它们以某种方式将音乐作为一种自然产物或扩展个体和社会文化的认同。
爱德华·弗雷姆(Edward M.Frame)讨论在沙巴地区一件乐器被三个土著群体所使用时指出,在不同的乐队组合、不同的舞蹈风格、节奏、调音中可以找到各自的差异性,某些特定的乐器在个体社群中使用,而不被其他社群所分享。⑰Edward M.Frame,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of Sabah", Malaysia,Ethnomusicology, Vol.26, No.2 (May,1982), pp.247-274.同样,冒顿潮尔特殊的乌梁海风格在蒙古族族群中使用,凸显着蒙古族特色与族群身份,基于此,青格乐专门创作了独奏曲《圣山》,演奏时运用冒顿潮尔特有的演奏法进行演绎。该乐曲区别于传统冒顿潮尔之处在于曲目短小,旋律多由四小节反复之处,并且在乐曲长度上有所延伸,同时结合冒顿潮尔的音色、音域以及空间感,将基音、泛音以及双喉音三种音色完整地呈现给听众,给人一种画面感与镜头感,可以想象山谷、湖水、圣山以及在湖面上的倒影,引发人们对自然的联想。
冒顿潮尔由于不同材质(木质、竹质、铜质)、孔距、不同演奏法所发出的不同音色以及演奏者状态、情绪、现场音响设备等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因此在乐队组合的演奏方式(独奏与合奏)上要经过仔细地思考。这些显性的音乐表征可以标识族群身份,正如托马斯·图里诺(Thomas Turino)在对秘鲁高原三种形式的社会认同进行研究时提到,一个小型乐器——恰兰戈(Charango,类似于小型吉他)可以表达一种或其他认同的归属感。当音乐家们敲击一个平面、金属弦质的乐器时,他们表达自己对土著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他们在一个圆形背面、尼龙弦质的乐器大概三分之二位置进行演奏时,他们则表达了一种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并且置身于阶层认同之中……并且,表演者开始时会演唱一种典型的印度劳动歌曲,组合成一组waynos⑱waynos:这是当地一种最重要的混血流派。,最后结束于克里奥罗华尔兹。这种单独或独立的表演是对秘鲁高原地区土著居民可用的一种、两种或三种多重身份而言的归属感。⑲Thomas Turino, "The Urban-Mestizo Charango Tradition in Southern Peru":A Statement of Shifting Identity, Ethnomusicology, Vol.28, No.2 (May, 1984), pp.253-270.
安达组合根据表演语境、受众群体以及表演形式对乐器加以选择,他们会合理地将冒顿潮尔特有的音色与双声演奏风格安排到独奏中,凸现自己的蒙古族身份与族群认同,体现着有别于其它族群的差异性,彰显乌梁海蒙古族特有的音乐风格。而在合奏中出于音色、音准的要求,巧妙地替换同类乐器(库拉乙或内),包容游牧文化的共同性,这种替换是在游牧文化的共同性与包容性之中做出选择。因此,在这样的民族志个案中,认同所涉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得到了很好地彰显。
三、文化认同语境中的乐器
20世纪70年代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关于身体人类学的讨论其“主要关注点在于不同社会语境中身体外部的文化进程与产品”⑳同注⑨。。乐器通过与身体的互动,在不同的表演语境中体现着文化的进程与产品,体现着社会文化属性(诸如文化认同、历史记忆与表述、社会阶层),体现着器物与天地、自然、人的关系。
进一步来说,乐器与人类交集的不同方式可以为洞察文化角色提供视野。苏·卡罗尔·德瓦雷(Sue Carole DeVale)指出“一个声音乐器是一个全息图,它可以被旋转和从许多角度看,它包含了社会和文化的本质。”㉑Sue Carole DeVale, "Organizing Organology.In Selected Reports in Ethnomusicology", Volume 8: Issues in Organology, edited by Sue Carole De Vale, 22.Los Angeles: UCLA Press, 1990.艾略特·贝茨(Eliot Bates)结合田野个案讨论社会生活中的乐器。㉒Eliot Bates, "The Social Life of Musical Instruments",Ethnomusicology, Vol.56, No.3 (Fall 2012), pp.363-395.阿里·吉哈德·瑞希(Ali Jihad Racy)认为乐器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是多方面的,提出了关于乐器研究的两种普遍模式——适应性与特质性。适应性的解释总是将乐器看作是器官的实体,即对不同的生态性变化和审美现实的反映,从而发展成为一种与地方声音观念、视觉符号学等相关的演奏技法。这种适应性的解释可以使音乐文化(包括表演者、乐器制造者、听众以及音乐形式)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并且可以识别出乐器的地方属性。㉓Ali Jihad Racy,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East-Mediterranean Mijwiz",Ethnomusicology, Vol.38, No.1 (Winter, 1994), pp.37-57.维罗尼卡·道布尔迪(Veronica Doubleday)介绍了四个“乐器与性别”相关的个案。文章以不同的方式论述乐器研究中的性别手段,强调性别的建构会受到乐器演奏者的影响。作者认为,乐器从意义与权力范围视角看是重要的文化人工制品,所有的表演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权力的轨迹。㉔Veronica Doubleday, "Sounds of Power: An Overview of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Gender", Ethnomusicology Forum, Vol.17, No.1 ( Jun., 2008 ), pp.3-39.
通过上述对海外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当今的民族音乐学学者已经不再将乐器单纯作为物质层面的器物,而是更多地关注文化层面以及所彰显的文化认同。正如蔡灿煌教授提出乐器学研究的新视角强调乐器及其音乐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群或国家、人与跨国社群或全球化的关系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乐器如何能有效地串联或进一步意识到音乐本身以及其演奏者的性别、身体的认同。㉕蔡灿煌《乐器、音乐与人际关系:乐器学研究的发展与现今趋势》,《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87—94、103页。笔者认为不仅要批判乐器的概念化,而且要评估那些可以补充和扩大对乐器理解的方法,以及它们与人类及其世界的关系。乐器本身的表现性源于对生物行为和审美结构的文化理解。正如凯文·达维(Kevin Dawe)认为,“在社会建构和意义上,乐器的形态通过它们的形制、装饰和外部特征来揭示,作为它们所服务的音乐家群体的价值、政治和审美的体现。它们既是物理的、隐喻的、社会建构的,也是物质的。”㉖Kevin Dawe, "The Cultural Study of Musical Instruments".In The Cultural Study of Music, Edited by Martin Clayton.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乐器本身的形态既是物理的,也是社会结构的。蒙古族通过其音乐舞蹈、乐器的使用强化自己的族群认同、区域文化认同和自主性。在此过程中,乐器、表演更是一种文化,冒顿潮尔以加强对声音和音乐的文化想象空间的方式来演奏。同时,它作为古老的乐器代表着一种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符号,该符号也是来自于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表征,最终,这种符号的象征具有特殊的意义与本土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正如笔者文中所说,音乐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必然是寻求民族音乐学分析的中心,从而进一步解释音乐传统的本质。
冒顿潮尔在蒙古族音乐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标识着古老的蒙古族音乐文化,不同表演风格、曲目、乐器的类型作为文化身份选择的影响元素,从蒙古族文化、游牧文化中汲取、形塑着一种模式。在以上个案中,认同的阶序与层次得到很好的表现。冒顿潮尔在与人的身体互动过程中,标识着身份认同。作为匈奴后裔、阿尔泰语系民族所共享的同类乐器,尽管名称、形制、材质、开孔等概念存在差异,但是其背后体现了广义的跨界族群认同;而从现代民族角度讲,蒙古族民族认同往往体现着一种对现代族群的文化诉求,安达组合的每场演出、每位乐手在不同表演语境与实践中,通过独奏形式强化着蒙古族族群身份;通过合奏形式强化着跨文化、跨界族群的文化认同,他们巧妙地寻找蒙古族元素,彰显多重音乐文化认同。这些个性化的表达有可能形成了基于民族(中国蒙古族)新的认同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现代民族的文化诉求。㉗该观点受到杨民康教授对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启发,他认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可以从广义和狭义方面加以区分,广义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即指跨地域性(区域性)历史族群的研究,属次生文化层;而狭义的跨界族群比较研究则主要涉及现今于同一广义族群内部,按山区、平坝、河流等地理条件自然分布的,较小规模和体量的跨国境地域性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参见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与身份认同——以中国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的比较研究为例》。
余 论
以上民族志个案从文化认同视角关注乐队组合中的乐器,乐器本身的形制、演奏法、对声音的控制、音色、音律等因素,在跨界族群表演实践中凸显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往往为了表征自我认同、族群认同,甚至涉及广义的跨界族群认同。当我们谈及音乐认同层级时,往往在族群之外更加凸显个性与差异性;而在族群内部则更加强调共性与认同性特征。
当我们将音乐看作一种民族、跨界族群的要素,一种表征与符号的时候,乐器(包括演奏法)可以体现出融合交流借鉴的一方面,但同时也会划分出明确的边界。正如笔者曾讨论过蒙汉杂居区不同族群演奏者通过选用不同的“顶弦”“按弦”四胡演奏法可以标识族群身份。㉘魏琳琳《蒙汉杂居区四胡演奏与族群认同研究》,《民族艺术》2018年第2期,第111—116页。当然,这里所谈及的音乐艺术层面的边界在音乐中没有明确的区分。蒙古族庞大的潮尔体系(弓弦潮尔、呼麦、吹管冒顿潮尔等)以及特有的双声系统,尽管通过乐器以及人声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其原理是相通的,即通过人的身体器官或乐器同时发出两种声音。安达组合的表演,无论手持乐器,还是他们的服饰、语言,都标识着特有的蒙古族族群身份,马头琴、冒顿潮尔这些乐器特有的音色沟通着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对话,彰显着对游牧文化、跨界族群的认同。
正如前文已提及王建民教授列举的器之体、形、用、性、礼、神、品、美、韵、情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他强调“器”与“道”的相通性,这里的“道”强调其观念层面,这种观念是运用于“器”之中的,“器”可以表达观念,观念实现了认同。同时,“器”本身也变成了认同的一种形式与象征性的资源。乐器既是一种技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一种塑造其演奏者的器物,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它反映了与器物相关的信仰崇拜、格调、审美以及情绪情感的“道”。㉙同注④。
当然,除了乐器本身,身体也是一种“器”,它是观念的表达,是文化的观念和态度塑造的结果。身体不仅仅存在于生理层面,在艺术活动中是一种与观念衔接的对文化与观念的表达,更是一种认同的表征。我们意识到乐器、身体、文化、观念、认同之间的联系,才有可能实现对器物的人类学探索。在以往的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乐器研究往往较少与人的身体、表演语境以及文化认同加以结合。因此,在冒顿潮尔的讨论中,人体需要被视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身体各器官的相互配合,借助不同材质、不同开孔的冒顿潮尔达到从独奏到合奏,从模仿自然的生活到基音、泛音的发音,从个体到团队的完美配合,从而实现与自然、神灵、自我的对话。本文从广义走向具体,勾勒出一副冒顿潮尔的清晰画面以便关注它与自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