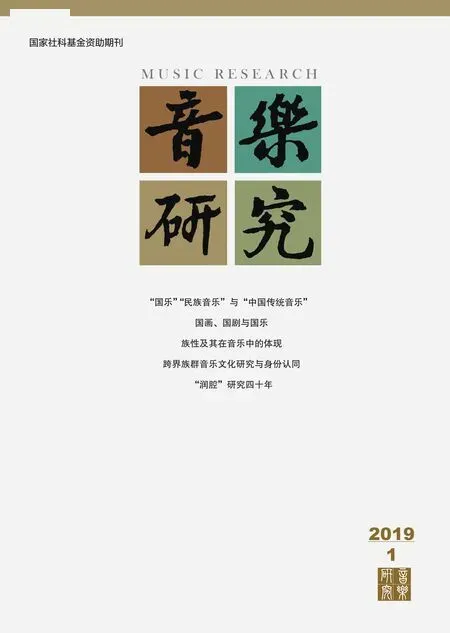国画、国剧与国乐
文◎彭 锋
中国乐派是近来中国音乐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如何从理论上界定中国乐派?如何在实践上壮大中国乐派?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鉴于不同门类之间的艺术问题可以相互启示,不同时代的艺术问题有一定的共性,我想借助考察20世纪上半叶关于国画、国剧与国乐的讨论,来回应当前有关中国乐派的某些问题。
一、国画与国剧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经历与西方竞争中的节节败退之后,中国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洋务运动的失败,让国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是科学技术能够解决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国人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是社会制度能够解决的;中国的落后可能是文化的落后,是文化落后导致的人的落后。这是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照中,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在绘画上找到了自信。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指出:“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故我国之建筑、雕刻之术,无可言者。至图画一技,宋元以后,生面特开,其淡远幽雅实有非西人所能梦见者。”①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原为佚文,刊于1904年2月《教育世界》69号,《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1997年版,第158页。王国维这里所说的“美术”,其实就是“美的艺术”,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艺术。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利害性。中国文化强调经世致用,不利于追求无利害性的艺术的生长。但是,绘画是个例外。中国绘画达到的境界,远远超出西方绘画之上。王国维的这种看法不是孤例,同时代的不少学者都有同样的看法,特别是一些留学海外的中国人,对于国画优越性的体会更加深刻,由崇拜西画,转向了珍爱国画。借用宗白华的话来说,许多中国人留学西方之后没有变得洋派起来,反而变得保守甚至顽固了。②宗白华《自德见寄书》,载《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中国人之所以在绘画上找到自信,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绘画正在经历一场剧变,由再现的古典绘画,走向表现的现代绘画。对于西方绘画的这场剧变,中国书画及其理论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正如包华石(Martin Powers)指出:“唐宋理论家的‘形似’与‘写意’的对比是通过宾庸和弗莱直接影响到欧洲的现代主义理论而在现代形式主义理论的建构中起着关键作用。”③包华石《中国体为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第144页。国画之所以被推崇,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它是先进的,尤其是符合西方现代艺术潮流。
在国剧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情形。1920年代中期,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等留美学生在纽约发动了一场“国剧运动”。除了投身于戏剧实践之外,他们还努力为国剧寻找理论支撑。受到绘画中的写实与写意的区分的影响,余上沅将国剧的美学特征概括为写意,将西方古典戏剧的特征概括为写实。写意戏剧与写实戏剧之间的区分,类似于写意绘画与写实绘画之间的区分。余上沅发现,西方现代戏剧有由写实走向写意的趋势。由此,余上沅等人在1920年代中期发动“国剧运动”,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融入现代形式主义艺术的潮流之中。余上沅将现代形式主义艺术称之为纯粹的艺术,并且认为“中国的各种艺术,至少是趋向于纯粹的方面”。④余上沅《旧戏评价》,载《余上沅戏剧论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151页。关于余上沅写意戏剧观的详细讨论,见拙文《重思余上沅写意戏剧论》,《戏剧艺术》2019年第1期。推崇形式性、纯粹性和写意性的中国艺术,对于西方艺术走出写实的束缚具有重要的启示。与余上沅一同提倡“国剧运动”的赵太侔就非常自信地说:“现在的艺术世界,是反写实运动弥漫的时候。西方的艺术家正在那里拼命挣脱自然的桎梏,四面八方求救兵。中国的绘画却供给了他们一支生力军。在戏剧方面他们也在眼巴巴地向东方望着。失望得很。却不曾得到多大的助力。”⑤赵太侔《国剧》,见余上沅编《国剧运动》,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第10页。
经过上述简要考察发现,国画和国剧都是在与西方艺术的对照中确立起来的。如果将西方的艺术简单地分为古典和现代,与国画与国剧对立的不是西方现代艺术,而是西方古典艺术。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上半期对于国画和国剧的提倡,既是回归传统,又是展望未来。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融合视为未来艺术的方向,这是20世纪上半期部分中西方美学家的共同看法。
二、国乐的确立
与国画和国剧的情况类似,国乐也是在与西方音乐的对照中确立起来的。国乐的确立与国剧差不多同时,稍晚于国画。1930年吴希之在《乐艺》杂志发表《中国乐艺界概况》一文,对当时中国音乐界的情况做了全面的描述。文章写道:“最近十余年来,朝野人士,渐觉国乐的重要,大家起来振臂疾呼,努力整理。”⑥吴希之《中国乐艺界概况》,《乐艺》1930年第1期,第54页。由此推算,对国乐的提倡,大致始于1920年。吴希之在文章中还提到,作为礼乐之邦的中国,音乐传统历史悠久,但也承认这个传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以致国乐有遗失殆尽的危险。发扬国乐的重要标志,是国乐正式成为高等教育的科目,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艺术专科学校都将国乐列入正科。与国乐相对的是外来音乐。吴希之将外来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大约始于元朝初年,不过只是限于教堂内部,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第二个时期是晚清派至海外的留学生,有人在学习政治和科学之余,为西洋音乐所吸引而改学西洋音乐。不过,这个时期学习西洋音乐的人数极少,产生的影响也不大。第三个时期“是西乐输入时代,大约是十余年来的事情”⑦同注⑥,第55页。。只有到了第三个时期,西乐进入学校,才产生了广泛影响。西乐的第三个时期与提倡国乐的时间差不多重合。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西乐的冲击与对照,对国乐的倡导还不一定会提上日程,对国乐的认识还不一定清晰。
对于国乐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一种比较极端的主张,认为国乐只是中国本位音乐,乐曲、乐器、演奏方法等都必须是中国的。比如,上海的霄霏国乐会就持这种主张。他们的立场是:“惟有绝对摒弃洋化,专从事于国有乐器乐曲之搜寻研究,综合各派,集合专家,以分工合作精神,寻求一代表的音乐,以求中国本位的音乐之发扬,在世界艺坛另树一帜。”⑧佚名《沪霄霏国乐会发扬中国本位音乐》,《科学的中国》1937年第9卷第8期,第24页。我们可以将这种主张称之为“国粹论”。
与国粹论不同,更多人认为国乐需要改进,尤其是需要以西洋音乐作为榜样。但是,在对待西洋音乐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主张循序渐进,借用西洋音乐逐级改造国乐。另一种态度主张全面吸收西洋音乐的精华,无需固守国乐落后的乐器与不合时宜的乐曲。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之为“渐进论”,将后者称之为“激进论”。陈振铎在《谈谈国乐与改进国乐》一文中,就表达了渐进改良国乐的主张。陈振铎主张国乐并非理想的音乐,我们应该用西洋音乐作为改造国乐的榜样,但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洋音乐,“必须按着次序,级进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踢翻了搬进西洋货来,尚不是根本办法:根本办法是先从改变中国民情入手。”⑨陈振铎《谈谈国乐与改进国乐》,《女师学院期刊》1933年第2卷第1期,第4页。陈振铎还提出了许多改进国乐的具体办法,有些是音乐内部的事务,有些涉及更加宏观的社会改造和国民改造。总之,按照陈振铎的构想,借助西洋音乐来改进国乐,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按照音乐、教育、社会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
与陈振铎不同,应尚能的观点更加开放和激进。在应尚能看来,与西洋音乐相比,国乐的落后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他反对一味崇尚西洋音乐,但是主张照单全收西洋音乐的精华,用它们来改造落后的国乐。应尚能说:“西洋音乐的精华,我们不妨采纳,西洋的乐器,亦不妨接受。这是节省我们自身的精力,何乐而不为?反过来,一味的崇拜我们落伍的乐器和不合时代的乐曲,也是大可不必的事。”⑩应尚能《提倡国乐》,《青年音乐》1942年第1卷第2期,第3页。对于国乐的界定,应尚能也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他说:
现在谈国乐的,颇不乏人。然而意见却各各不同。有的说凡是本国乐器所奏的,都该是国乐。……更有的说中国人所作的乐曲,一定是国乐,尤以歌曲为必然,因为歌词是中文,其曲焉得不是国乐?……我们看音乐应该从它的内容着眼。《梅花三弄》是在二胡上奏出《梅花三弄》,钢琴上弹出来,还是《梅花三弄》……至于中国人所作的乐曲,亦必视内容而后决定它是否国乐。作曲的方法,尽管是西洋的,只要曲中所发挥的,都能代表中国的人或中国的事,那就该称这种的乐曲为“国乐”,并且不需要问是钢琴谱或是琵琶谱。⑪同注⑩。
根据应尚能的界定,国乐与乐器无关,与作曲家和演奏家无关,与作曲和演奏方法无关,唯一的要求是“代表中国的人或中国的事”。鉴于音乐本身比较抽象,不像绘画、雕塑、文学、戏剧、电影等具备较强的叙事功能,是否“代表中国的人或中国的事”并不容易鉴别。因此,以能否“代表中国的人或中国的事”作为衡量国乐的唯一要求,对于国乐的约束有些过弱。
三、杨荫浏的国乐观
杨荫浏对于国乐的看法非常特别,既不同于国粹论,也不同于渐进论,还不同于激进论,或者说既有国粹论的部分,也有渐进论的部分,还有激进论的部分。杨荫浏对于国乐的看法非常独特,上述三种主张都无法将其囊括在内,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论”。鉴于这种多元论主张非常重要,我们这里列单节加以讨论。
1942—1944年,杨荫浏在《乐风》杂志分三次发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长文,全面阐述了他的国乐观。杨荫浏开篇即对国乐做了这样的界定:
国乐全部的事实,决不是某一点理论,某一种乐曲,某一种乐器,或某一样技术所可以代表的。从纵的方面说,我国有史以来,凡有音乐价值的记载、著作、曲调、器物、技术等等,都是国乐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从横的方面说,中原以及边地各省各市各村各镇的音乐材料,和曾与、正与、或将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的他国音乐的材料,也都是国乐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⑫参见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4页。
杨荫浏对于国乐的界定,采取了历时和共时两种角度,他称之为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所有跟音乐有关的东西,都是国乐的内容。从共时的角度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与音乐有关的东西,都是国乐的内容;甚至他国音乐也可以是国乐的内容,只要它们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由此可见,杨荫浏对于国乐采取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将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的他国音乐也纳入国乐的范围,这种看法可以说比应尚能的激进论更加激进,因为“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比“代表中国的人或中国的事”的约束力更小。
杨荫浏的激进论,在他关于国乐将来地位的前瞻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杨荫浏看来,将来只有音乐,没有国乐与西乐的区别。将来的音乐是融合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音乐。从将来的音乐的角度来看,“国乐的独到的价值,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之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国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化之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取这样观点来看国乐,便可以觉得拒绝世界音律,拒绝世界乐器;拒绝在国乐曲调上作配合和声的尝试等等,都非但是不必要的事,而且也是国乐前途充分发展的障碍。”⑬同注⑫。从这些论述来看,将杨荫浏的国乐观归入激进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杨荫浏并非纯粹的激进论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极端的国粹论者。杨荫浏对于国乐为什么会持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国乐观是流动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之间还有很强的因果关系。杨荫浏对国乐的激进论看法,主要表现在未来这个时间维度上。也就是说,从未来的角度看,人类只有音乐,没有西乐与国乐之分。但是,这并不等于现在就没有这种区分。为了未来更好地融合到世界音乐的大家庭之中,我们现在要坚决维持国乐的身份,要维持国乐与西乐的区别。如果现在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不突出国乐的特性,国乐就有可能完全被西乐所吞没,而失去将来与世界音乐交融的机会。对此,杨荫浏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论述:
原因是如此,交融的不同文化因素,因交融以前各因素,独立基础的强弱,和它准备工夫的充分与否,会形成种种不同的交融结果。全无基础,全无准备的因素,在基础稳定,准备充分的因素之前,会全被压倒,而形成被并吞被消灭的现象。以国乐而论,当前的情形是如此: 我们自已还没有充分准备,世界音乐的力量却已非常强大。我们若再不准备,便只有让整个世界音乐,逐渐地来淘汰或排挤了这仅存的一些国乐成分。因此,我们必须准备。但准备的当儿少量的渐次的发见、归纳和发展,似乎很难抵挡得住世界音乐磅礴的潮流。因此,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之下,我们应当给与国乐过度的注意。中西音乐的界限,最后或许不应当被重视的,这时候,却不得不暂时被重视。国乐中的某种工具,我们虽明知它将来必被淘汰,这时候却因为还有非它不成的媒介作用,不得不坚持保守着,暂时不容放弃。⑭同注⑫,第5页。
杨荫浏之所以能够持有完全不同的国乐观,原因在于他对国乐采取了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看,而不像单纯的国粹论者、渐进论者、激进论者,采取静态的眼光看国乐。当然,至于将来的音乐是否像杨荫浏设想的那样没有国乐与西乐的区别,这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但是,将来的音乐与现在的音乐一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国乐观,这是没有疑问的。考虑到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的交往变得更加容易,联系更加密切,没有民族、国家和地域之分的音乐或许真有可能成为现实,杨荫浏对于未来音乐的构想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总之,采取动态的眼光来看国乐,比采取静态的眼观来看国乐,要更加合理。
杨荫浏之所以强调现在“应当给与国乐过度的注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要在将来的世界音乐中保留国乐的份额。杨荫浏之所以强调在将来的世界音乐中要有国乐的份额,一方面源于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独特的多元音乐观。这种独特的多元音乐观,不仅体现为动态的、发展的国乐观,更重要的体现为对国乐的广度的强调。
杨荫浏强调,研究国乐既要有深度,又要有广度。所谓深度,主要指的是历史的深度,也就是要尊重国乐的历史事实。“国乐的基础,更是在过去的事实,而绝不是现在或未来的无中生有!”⑮同注⑫,第7页。正因为如此,杨荫浏特别强调国乐史实的整理与发掘,而不是随意的改编和创作。在整理和发掘国乐史实的时候,要做到将自己当作透明的玻璃,不去掩盖和歪曲历史事实。所谓广度,指的是理论、乐器和乐曲的多样性。对于国乐界固守某一派别、某一乐器、少数几个曲调的现象,杨荫浏给予了批评。“不看见多数,不能领略少数,离了整个,不能真正认识各个;没有见到整个的广度,便很难达到各个的深度。”⑯同注⑫,第8页。“看不见多数曲调的好处,便听不出少数曲调的短处;没有较广的来源,得较高的认识,便无从评判;无从评判便无从深刻。”⑰同注⑫,第9页。杨荫浏这些一般性的论述,不仅适用于音乐,也适用于其他门类的艺术,而且对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和胸襟的开阔都有重要的启迪。杨荫浏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派别观念到了极端,在整个园地中,便只见得有一个自己,对他派毫无善意。与更丰富的周围隔绝了,与信仰的同志们疏远了,结果,是自己牺牲了快乐的团契权利,放弃了广大的发展可能、走入精神孤立之途,是虚骄,是仇恨,是悲哀,是绝望,将何等的不幸。”⑱同注⑫,第12页。基于对广度的强调,杨荫浏还得出对于国乐要采取谨慎去取的主张。对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乐来说,这种主张尤其重要。杨荫浏注意到,根据某种原则,对音乐加上删减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他主张要尽量多保留,少删减,或者不删减。在论证这个观点时,杨荫浏也采取了发展的历史观。他说:
所取视点不同,所建成之原则,往往相异。取某种观点,淘汰了某事,在淘汰的时候,主张淘汰的人,每觉有充分的理由。一旦社会的趋向改变,后人的造诣不同,所取观点,随之改易,便难免不追思既被淘汰的往事,而为它的被淘汰惋惜,然以前的淘汰极易,以后的挽回极难。在历史悠久,材料复杂的我国文化中间,更不能不加以特别的审慎。⑲同注⑫,第15页。
杨荫浏的这种主张,与当代哲学对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的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普特南的观点,对于我们究竟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没有最终答案,任何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都因为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具有价值。⑳Hilary Putnam, Renewing Philosoph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89.由于我们的趣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被当作不好的音乐今后有可能被当作好的音乐,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任何音乐都会因为丰富了人类音乐大家庭而具有价值,都应该得到保存。杨荫浏明确反对为了满足“自己平凡的预期”,将前人“个性显然,妙有独到的乐句”,改成“不好不坏的柔驯的乐句”㉑同注⑫,第15页。。保持音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仅有利于国乐未来融入世界音乐的大家庭中,而且对于音乐本身也是一件大好事,因此对音乐了解得越多,对音乐的理解越深。
四、国乐的困难
国乐与国画和国剧一样,都是在与西方相应的艺术形式的对照和竞争中确立起来的。但是,国画的表现明显比国乐自信得多。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王国维等人在20世纪初提倡国画,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的,而且因为它是先进的。余上沅等人仿照国画,也为国剧找到了自信。但是,国乐没有这份自信。我们见到的更多是如何借助西洋音乐来改造国乐的议论,几乎没有见到用国乐去改造西洋音乐的主张。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西方艺术的原因,也有中国艺术的原因。
从西方艺术来讲,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现代主义运动,在美术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现代主义运动在西方美术中造成的断裂,在西方音乐中似乎不那么强烈。这与音乐和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关。根据古德曼的研究,绘画和音乐可以作为艺术语言的两极的代表。绘画代表不可分节的密度语言,音乐代表可分节的清晰语言。绘画不可记谱,音乐可以记谱。绘画与音乐在语言上的区别带来了它们之间的一系列差异。比如,绘画是一级艺术和单体艺术,音乐是二级艺术和多体艺术。作为一级艺术的绘画,通常是由画家完成的。作为二级艺术的音乐,在作曲家完成创作之后,还需要演奏家的二度创作。音乐作品可以被演奏,同一个音乐作品可以有不同的演奏,因此就演奏来说,音乐是多体艺术。绘画作品不能被临摹,即使画家本人临摹自己的作品也会被视为赝品,因此绘画通常只有一幅,是单体艺术。㉒Nelson Goodman, Languages of Art,Indianapolis:Hackett, 1976, pp.112-119.
正因为音乐与绘画之间的这些不同,导致音乐在20世纪的断裂没有绘画那么深刻。如果就作曲来说,20世纪的音乐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得到演奏的弥补,因为音乐家仍然可以演奏以前的乐曲,但是画家不能临摹以前的作品。音乐家演奏以前的作品是正当的,画家临摹以前的作品是不正当的。音乐记谱法完善以后,西方音乐家留下了大量作品,特别是19世纪浪漫主义大师创作的鸿篇巨制,已经足够演奏家们去诠释。甚至在19世纪就有人感叹音乐创新已经接近极限,作曲家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将已有的音乐片段进行新组合而已。比如,约翰·密尔在1873出版的《自传》中就感叹,他从音乐中获得的愉快,总是因为似曾相识而褪色。要保持在音乐中获得的愉快不被似曾相识减弱,就需要创新。但是,在密尔看来,音乐组合是可以穷尽的。他承认,他为这种想法所苦恼。更让他苦恼的是,他发现有限的音乐组合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被音乐家们发现了。㉓John Stuart Mill, Autobiography (1873), Part VCrisis in My Mental History.One Stage Onward.https://www.utilitarianism.com/millauto/five.html
密尔关于音乐家穷尽了音乐的可能性而导致音乐终结的想法,启发了一百年后的丹托提出艺术的终结,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丹托这里所说的艺术,主要指的是绘画。在丹托看来,绘画之所以会终结,就是因为画家将绘画的全部可能性都实现出来了。㉔Arthur Danto, “Approaching the End of Art,” in Arthur Danto, The State of the Art,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ress, 1987, pp.202-218.关于约翰·密尔的音乐终结思想的讨论,见pp.202—203。尽管密尔关于音乐终结的思想比丹托关于绘画终结的思想早了一百年,但是终结论对于音乐的冲击远远没有对于绘画的冲击那么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音乐是二级艺术和多体艺术,即使有关音乐的可能性被作曲家全部穷尽,只是表明关于音乐的作曲终结了,不能表明音乐的演奏终结了。在作曲终结之后,音乐仍然可以在演奏中延续下去。但是,绘画终结之后,绘画不能在临摹中延续下去,因为对于绘画的临摹被认为与艺术无关。正因为如此,绘画面临的终结危机远远多于音乐。
20世纪初绘画面临的危机是受到照相技术的冲击,与丹托后来讲的艺术终结情况不尽相同。受到照相技术冲击而造成的危机,只是波及写实绘画。为了摆脱照相技术带来的写实绘画的危机,西方画家和美术理论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在中国写意绘画中找到了让绘画继续存在的理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写意绘画被推到了现代绘画的前沿,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绘画的先进样式。但是,西方音乐由于没有遭遇像绘画那样深刻的危机,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似乎并不继续更新他们的音乐和相关理论。
西方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没有像西方画家和美术理论家那样关注中国,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音乐和音乐理论的某些不足。与国画被西方艺术爱好者和艺术机构广泛收藏不同,国乐很少有途径传播到西方去。这与绘画和音乐的存在方式不同有关。绘画有物质载体,便于保存和传播。在录音技术没有发明,尤其是记谱方式不够完善的时期,音乐只存在于现场表演,不利于保存和传播。另外,尽管现代艺术教育在中国是20世纪初开始才逐渐建立起来,在此之前包括美术和音乐在内的各门类艺术都是以师徒相授的方式进行传承,但是书画领域的艺术家不都是工匠或者民间艺人,而是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文人,他们不仅创作出了趣味高雅的作品,而且能够对作品做出深刻的理论阐释和概括,形成了独特的绘画理论和丰富的画论文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历史长度来说,中国画论不亚于任何一种文字中的绘画理论。丰富的绘画作品和绘画理论,为西方人研究和理解国画提供了条件。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西方学者都开始注意研究、整理和翻译中国画论。翟里斯1905年出版的《中国绘画艺术史导论》,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和美术界对中国绘画和相关理论的强烈兴趣。㉕Herbert Allen Gil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05.黄宾虹和邓实编辑的《美术丛书》于1911年出版,以及随后的多次再版和增订,带动了中国学者自己对国画理论的研究。
但是,国乐就没有这么幸运。与国画相比,国乐作品和国乐理论都要贫乏得多。尽管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礼乐文化非常灿烂,也留下了《乐论》《乐记》等音乐理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徐上瀛的《溪山琴况》体现了很高的理论水准,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对于古琴及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有关国乐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局部的,没有发生全局性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国运衰落,国乐散落民间,从业者以民间艺人居多,很少有人能够对自己从事的音乐做出理论解释和总结。总之,因缺乏物质载体而不便于保存和传播,再加上理论研究的薄弱,是在与西方艺术对照和竞争中国乐没有国画自信的原因所在。
五、写意音乐是否可能?
国画在与西方绘画的对照和竞争中之所以能够具有优越感,不仅源于作品丰富、理论深刻、趣味高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画找到了高度凝练的理论概括,即写意。这种概括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在于能够更好地突出国画的独特性,而且便于传播。它的缺点在于难免以偏概全。国画形式和风格丰富多样,写意只是其中一种样式。即使对写意做最抽象的理解,即不将它理解为一种风格,而将它理解为一种精神,它也不是全部国画的共同追求。因此,用写意来概括国画,一定会付出牺牲国画的丰富性的代价。但是,在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中,越是高度凝练的概念越具有传播效力。将国画中固有的文人写意与匠人工笔之间的对照,西洋绘画中固有的古典写实与现代表现之间的对照,整合为中国写意与西方写实之间的对照,这就很容易让人将中国文人写意与西方现代表现联系起来,既提升了西方表现绘画的趣味,又赋予了中国文人绘画现代性。国画的优越感,来自写意的高雅趣味和表现的现代性。国剧沿用国画的方式,借助写意与写实的对照,在与西方戏剧的对照和竞争中获得了优越感。
我们能否采用同样的方式为国乐找到自信?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按理适用于绘画和戏剧的方式,也应该适用于音乐,因为既然它们都归属于艺术,就会有同样的特征。但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首先,“艺术”这个概念的约束力本身就不是很强。我们今天使用的“艺术”概念,是在18世纪欧洲确立起来的,艺术之中应该包括哪些科目并非固定,常常会因时代不同和文化不同而有所不同。㉖关于现代艺术概念的确立的详细考证,见PaulKris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 Ⅰ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2, No.4 (Oct., 1951), pp.496-527.PaulKris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Ⅱ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3, No.1 ( Jan., 1952), pp.17-46.既然如此,被归入艺术之中的科目,就不一定有共同的本质;它们也有可能是根据家族相似关系而被归结为一类。同时,当代分析美学的研究表明,不同门类的艺术可能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地位。比如,绘画是一级的、单体的艺术,音乐是二级的、多体的艺术,文学是一级的、多体艺术,等等。㉗参见拙文《艺术为何物?——20世纪的艺术本体论研究》,《文艺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21页。由此可见,适用于绘画和戏剧的道理,不一定适用于音乐。
无论用写意来指称音乐的方式还是境界,都会碰到同样的困难,那就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用写实来指称音乐都会显得非常古怪。如果没有写实音乐作为对照,写意音乐就难以成立。换句话说,写意音乐之所以难以成立,原因在于写实音乐不能成立。这与用写意来指称电影所遇到的困难刚好相反。不能用写意来指称电影,原因是电影在根本上就是写实的。如果音乐在根本上就是写意的,无论国乐还是西洋音乐就都是写意的,写意就无法标明国乐的特征。
还有不借助与写实的对照来界定写意的方式吗?一定会有。就绘画中的写意来说,与写实的对照也不是其获得意义唯一的途径。如果不与写实对照,写意也有意义,那么写意音乐就有可能成立。事实上,我们的确能够感觉到有些音乐是写意的,尽管我们很少感觉到哪些音乐是写实的。另外,我们用写意来指称某些音乐似乎并不古怪,尽管用写实来指称音乐是古怪的。这说明我们还有其他途径来确立写意的含义。比如,写意也可以指操作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国乐的记谱方式是否让国乐的演奏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呢?另外,对于写意绘画,经常用虚与实、似与不似之间来形容,写意音乐是否也存在虚与实、似与不似之间的问题呢?只有在澄清诸如此类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明确写意音乐的含义,才能判断音乐是否可以是写意的。
六、余 论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回顾20世纪初有关国乐的讨论,对于我们今天提倡中国乐派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已经看到,在20世纪上半期与西方艺术的对照和竞争中,国画和国剧比国乐要成功和自信。它们成功和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找到了自身的核心概念即写意,通过将西方传统绘画和戏剧归结为写实而实现了对它们的超越,进而越过西方传统艺术,直接对接新兴的现代艺术。遗憾的是,我们对于国乐的精神内涵研究不够深入,没有找到它的核心概念,在与西方的对话和竞争中,没有自己的明确面貌,更谈不上对西方音乐的启迪和拯救了。杨荫浏在国乐的史料整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国乐的理论总结和提炼方面留下了遗憾。杨荫浏已经认识到明确国乐本体的重要性,他说:“乐器、符号甚至乐律和技术,都不过是国乐表现或流传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国乐真正的本体。若国乐确有它真正的本体,国乐曲调确有它内在的特性,则必不会因在小提琴上奏出,而变成了西洋曲调;必不会因等比律的应用,而失掉了它原来神情的重要部分。”㉘同注⑫。但是,遗憾的是,杨荫浏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
陈振铎在谈到国乐相对简单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国民性的不同,他说:“中国国民性乐,是基于喜礼让、轻名利、爱和平、重情义上,故其意味清平和蔼,雅而不亢;不像近代一部分西乐之多于过分刺激的东西。类似我们听了身心不安过于刺激的近代西方乐艺,是否合于乐以主和,怡人心神的原则,尚是问题。”㉙陈振铎《谈谈国乐与改进国乐》,《女师学院期刊》1933年第2卷第1期,第2—3页。陈振铎还试图借助与绘画的对比,概括国乐的审美特征,他说:“其实乐的有无和声,仅不过是所取材料的色彩浓淡问题,不是音乐本身上有无毛病的好坏问题。譬如作画,用笔细密,渲染工致的浓厚色彩油画固然可以绝妙;但是着笔高简,遗貌取神的寥寥三两笔淡墨水画,也未尝不可以妙绝。让我再就实际方面来说:这种高简清淡的东西,在今日的中国,也许比较用处多些。因为我国国民对情节过于高深或变化过于复杂的音乐,能领略者尚鲜。”㉚同注㉙,第3页。陈振铎在国乐中体会到了和、清、雅、简、淡等审美特征,在古代乐论中多有论述,特别是《溪山琴况》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总结,只是没有得到现代音乐理论研究者的关注而已。陈振铎在水墨画中发现的那些审美特征,完全可以用写意来概括。水墨画与国乐之间在审美上的相似性,表明用写意来概括国乐的审美特征不是没有可能。
一旦从理论的高度把握了国乐的审美特征,有关国乐的创作、表演和教育领域中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就有了方向,国乐对于世界音乐的启示和贡献就可以凸显出来。如果这样的话,中国乐派就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学术概念。就像国画在20世纪上半期那样,不仅因为它的中国性而且因为它的现代性而受到推崇。在21世纪上半期,中国乐派也将不仅因为它的中国性而且因为它的当代性而受到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