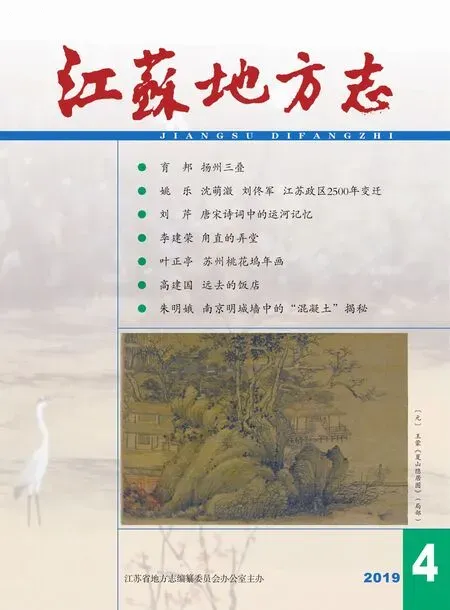老地名中的另类乡愁
◎ 凌 子
消逝的杜公漾
这是个早已不存在的“漾”,消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事实上,是硬生生给抽干的。那时,仿佛还以粮为纲,围湖造田余热未歇。“人定胜天”,本来就浅水位的杜公漾不知怎么就被牛气冲天的“革命泵”(好像叫“圬工泵”),夜以继日,围追堵截,消灭了。
抽干后,周边村民欢欣鼓舞,摸鱼捡蚌捡捞沉浮物。一时间,我等十来岁顽童也跃跃欲试。一边脚踢洪荒塘钉,一边难得一窥老渔民用钓枪在淤泥中逮起“千年神龟”。为排除最后的积水,漾中央开挖了一条深深的河沟,那等于是在海底再挖海沟。集聚的水湍急,急水中的鱼厉害,但“革命泵”力大无比加劲抽,以致人们只能站立深沟边,眼睁睁看着鱼儿被吸进泵口,好不沮丧。
杜公漾抽干后,先是划分给生产大队种田。但不知怎的,就是长不成可收获的稻谷。原来,湖底淤泥有些为小粉土,细腻与板结,如淀粉沉淀。我们特别爱这样的土,雨后,粉刷瓷结,脚踩上去,不粘,更不会硌脚。稻谷不见丰收,遂改开鱼塘。这时,改革开放的号角隐隐吹响。杜公漾位于吴江黎里,系江浙沪腹地,乡镇企业油然而生。世纪之交,干脆任其荒废,同时又百废待兴,来个咸鱼翻身、鲤鱼打挺,一半“集约用地”成为小微企业大本营,一半“回土复耕”成为大农户驰骋地。辗转反复,再也找不到荡漾的水印了,也无需多情寻觅所谓乡愁了。
关于杜公漾,我惊诧,地方史志中始终轻描淡写,不多记一笔。查阅清代《黎里志》,即便名士徐达源也只是一笔带过,想来那时司空见惯。历史上,包括黎里在内的太湖流域,大背景“水天一色”,河荡潭漾,星罗棋布。水如梦魇,压迫着地方,也激发起一方水土的抗争热情。新中国成立后大兴冬季水利会战,让水乡泽国“首当其冲”。塘中筑坝,湖边围田,填河栽秧……不亦乐乎!
回到记忆中的杜公漾,真个浩瀚、壮阔,那是我童年的“气蒸云梦泽”,是嬉戏与网罗食材的广阔天地。漾中波光粼粼,村中炊烟袅袅。有雾气的时候,烟树远村云山,朦胧一片;天朗气清时,则尽可大做白日梦,诗与远方历历在目。可以说,我仅有的一点哲理与诗情,就是在杜公漾畔,若即若离酿就。
杜公漾抽干之际,屁孩们只有兴奋,只有水泊初聚义的快感。每天都去报到,都要以各种理由“轧闹猛”。我们疯狂,从上到下哪个干部群众不亢奋,用日后风行的“打了鸡血”作比喻,歪打正着。大人们是机会难得、假公肥私,捉鱼啊。小孩们是看热闹,无意中“瞎猫撞着死老鼠”,或踩到一水产品,或捡拾起一件小器物,喜出望外啊。
杜公漾荡漾时,水面辽阔,水清澈。夏日午后,酷日当空,非但没有构成威胁,反而给戏水的孩子带来无限希望。那样,水就不凉;那样,就可以久久地在漾中“伏波”。浅滩硬底,水草依稀。膝盖微屈,水面刚好齐脖颈。惬意地闭起眼,柔波如轻纱细浣,说不尽的温柔。有时竟至飘飘然欲眠,梦亦呈水晶般透明。水乡的孩子识水,水也识童心。城中与今天的孩子是不会有这样的享受。顺水推舟、顺手牵羊,更多时候,我们会在“伏波”之余,把手探入水草丛或伸进水沫吞吐的浅滩石隙——那里躲藏着小鱼虾,呆萌。尤其是虾,一只只如齐白石笔下所现,中看又中吃。
不敢走远方,也不敢游走得太远。童年流连处,其实不过杜公漾之一角,近水楼台,向阳花开。稍涉远,陡然一“百慕大三角”,深不可测,水极寒。那里发现过很多神秘东西,据说还发现过亚洲象骨骼化石。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父亲,做木工,漾抽干后,于旁通的深水荷花池底挖得一巨鳖,斩食之,日后蹊跷事不断。
“杜公何许人也”,永远猜不透。杜公漾消失了,我们长大了,远走高飞。
有趣的地名误解
我的小学与初中一二年级是在家门口的乡校读的,七八位老师大多为代课教师。小学采用复式班教学,基本用本地“土话”。语文课相对高大上,用洋泾浜普通话。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吴江地方不大,方言却千差万别。东边芦墟人听“西横头”横扇人讲话,不啻与西域外交使节打交道。那时,“西横头”人总摇着船,夏季载着西瓜、腌大头菜,近年关载着胡葱、白菜、萝卜,沿太浦河东来叫卖。
黎里靠东边,黎里话也是这个村与那个村不太相同。尤其是隔着太浦河,“河南话”对我们“扎网港”而言,又是外来语。
由此,我一直搞不清许多“物事”——普通话中叫什么,汉字写作什么。这样的苦恼,伴我成长,且纠缠回忆,至今不灭。不知怎的,扎网港的发音极含糊,叫法又独特,想找到对应词汇,有时真困难。如“构树”,极卑微的一种树,司空见惯,但就是不明白学名是什么,因为我们叫它“国树”。再如“东边西边”,我们称作“东海西海”,明明与水不搭界,与海十万八千里,但一直这样叫过来叫过去。
最头疼的是地名。已过“知天命”的我,因为搞地方史料关系,经常查阅一些旧志地图。看着上面的标名,好多时候诧异。如“西姚港”这个地名出现眼前时,我竟不明白那正是我少年时期常去做客的“西海港娘舅”家。感谢早已消失的“杜公漾”提示,让我恍然大悟,尽管是在西边,正确的标注不是“西海港”而是“西姚港”。近期接到一位老人电话,声称要写回忆录,欲索我编辑的《吴江文史资料》参考。老人是几经辗转知晓我的手机号,远兜远转,终于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原来,他是我父亲辈,与我还有依稀的姻亲关系。一个地名报出来,令我恍惚——梓树下。
梓树下,何其沧桑又诗意,不由联想起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我不知道,这个村的形成,是否也与历史上的战乱、迁徙有关。远的如张士诚起兵、太平军“长毛”烧掠,近的如日寇扫荡、解放初期“土改”。无论如何,这个地名之于我印象相当深刻。那是因为童年时,我跟着祖母出远门走亲戚的极致就是此地。一直以来,苦于写不出准确地名。依读音记为“紫熟屋”,那也是穷尽所能,用想象与排除法得出的最佳选项。你想,屋后的茄子成熟了不是紫红色吗?《红楼梦》中刘姥姥的村庄不也如此景象吗?看到真正答案后,恍若隔世。祖母去世三十年了,按俗语云,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大批的村庄消失,“桑梓”之情无从寄托。我知道,“梓树下”名虽犹存,然面目全非也。当年到“梓树下”做客,一定还要顺路串另一家亲戚门,近在咫尺,却不是同一村。那地名好记也好写,叫“清风桥”,名副其实要走过一座桥,一座高大又结实的木桥。今天对照区划图,竟发现写成“青风桥”,不伦不类,不得其解。推想,要么是“清风”,要么更有可能是“青枫”——与“梓树”呼应。发展是硬道理,任性的背后是谁都不在乎——割断了史脉,文字仅为符号标签。此种情形,一如当年“扎网港”的孤陋寡闻,依音想当然。
再提两件陈年芝麻事,同样有关地名写法。一究竟是“火烧浜”还是“虎啸浜”;二究竟是“浒泾弄”,还是“虎径弄”。两个地名问题皆出自黎里,我的家乡。小时候,柴垛集结,冬季失火不少见。一失火,烙印难以抹去。因而,我们认同“火烧浜”命名。至于“浒泾弄”,也顺理成章。“浒”水边也,河网交织,舟行为主,入黎里镇口,原来就有一条小河叫“箭泾”。如此,两者仿佛可以定论。
然而,一部《吴江县志》与清嘉庆《黎里志》,挑战“定论”。史志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虎突至永安圩民家,众逐之,伤三人一毙。往来田间两昼夜,居民大恐,鸣之官。守备张光玉率兵下乡,虎已去,不知所之。”明清之际,吴江尚系水乡泽国、野旷天低。虎之出没,虽可信,然明明白白见诸正史,还是霹雳一声。另有民间传说,康熙初年,不知从何处而来一虎,骚扰黎里,逡巡“浒泾弄”,最后被毙于不远处的一土洞。此土洞在禊湖道院,名“伏虎洞”。如果关联起来演绎,虎当由野地窜来,地缘上对应的“火烧浜”可能真的为“虎啸浜”(新出版的地方区划图,即以此标示);而一步之遥的“浒泾弄”或许慑于虎威,曾叫做“虎径弄”。但历史远比想象丰富,比推理更合理或更不讲逻辑。真实情形,无从考证。
文史觅桑梓。最后,荡开一笔,追寻一下黎里与扎网港两个地名踪印。黎里古称梨花里,三里市河穿镇而过,故又有“黎川”雅称。清代大才子袁枚曾来黎里访名士徐达源(即清嘉庆《黎里志》作者),作诗《黎里行》云:“吴江三十里,地名梨花村。我似捕鱼翁,来问桃花津……”扎网港是黎里的一个自然村,也称撒网港,依河聚居,历史上可能就是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吴江人徐崧与友人合著《百城烟水》,中有一诗,赫然记载儿时随父“授徒黎川之撒网港王氏”情形:“黎里人家尽水乡,谁家聚族此推王……场上积薪高过屋,港边晒网半沿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