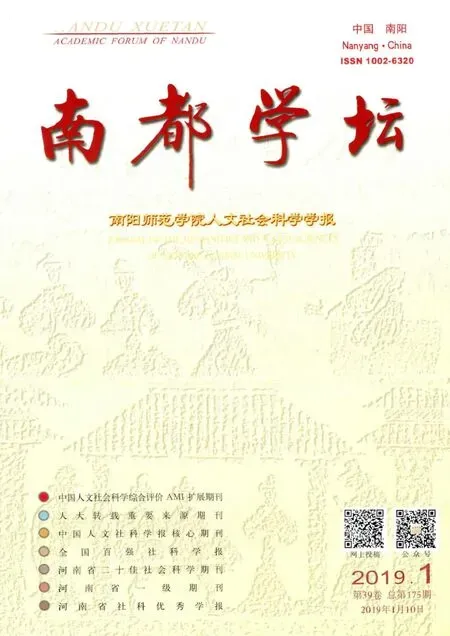吴梅村书写的南明政权及其批判
陈 岸 峰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一、前言
甲申之变后, 清兵略定中原,迅即南下,由西线入蜀,公元1647年,张献忠于凤凰山阵前中箭身亡。至于东线兵马,则以豫亲王多铎为主帅,剑指南明。公元1645年,清兵渡过长江,弘光帝先观戏、酣饮,再于二鼓后仓皇出逃[1]213,旋即被俘,南都迎降。
在弘光政权灭亡后的几年,吴梅村的创作力达到顶峰,书写了一大批关于社会动荡离散的作品,格调凄楚苍凉。此中,其有关南明政权兴亡的作品,既有深沉的个人感慨,又史实详尽、史识深邃,足供后人了解南明政权未能如东晋与南宋般支撑半壁江山反而迅速倾覆的原因。
二、新君人选之争
其时,清廷政权尚未稳固,清兵尚未渡江,故南京的明朝大臣均急于谋立新君以稳定半壁江山,并图恢复。
新君的人选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为福王朱由崧,一为潞王朱常淓。朱由崧乃明神宗之孙,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崇祯的堂兄。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破洛阳时,老福王朱常洵死难,小福王朱由崧逾城逃脱;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三日壬戌,怀庆府夜变,他与母亲走出东门,却“弃母兵间,狼狈走卫辉府依潞王”[1]1。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朱由崧获封为福王。就继位的资格而言,福王与崇祯的血统最亲,然而他昏庸懦弱、沉溺酒色,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早已知悉一切,便指出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1]6《明史》更指史可法曾向马士英指出福王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注最先指出福王有“七不可”的是张慎言、吕大器及姜曰广。[2]7017[3]178。然而,马士英却以“七不可”之书用凤督印印之成案,史可法遂受制于马士英[3]179。
此外,在朝的东林、复社中人均反对拥立福王,原因在于其祖母郑贵妃当年有夺嫡之嫌,即因所谓的“国本之争”[4]211[5]而曾受到东林党的攻击,彼此嫌隙极深。由此,东林、复社中人恐怕朱由崧一旦上台会翻历史旧案,故而倾向于拥立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称其“贤明当立”[2]7017。作为复社盟主的吴梅村在《银泉山》中,便曾猛烈批评郑贵妃的种种乱行。其中“覆雨翻云四十年,专房共辇承恩顾”指的便是郑贵妃恃万历之宠而祸乱后宫。“玉椀珠襦散草间”之说,犹见郑氏生前之贪婪奢侈,“云是先朝郑妃墓”一句,则颇有不屑之意。“宫人斜畔伯劳啼,声声为怨骊姬诉”两句之“宫人斜”亦称“内人斜”,乃秦朝都城咸阳埋葬宫女之所在,“伯劳”乃生性凶猛之小型雀鸟,此乃刺郑贵妃之恣行威怒、草菅人命,犹如晋国惑君乱政之骊姬。至于“尽道昭仪殉夜台,万岁千秋共朝暮。宫车一去不相随,当时枉信南山锢”四句,则在于责其于万历死后不殉[注]《明史·后妃传》载,郑贵妃薨于崇祯三年七月,葬银泉山。[2]3538;而“移宫事迹更茫茫”更是斥其意图怂恿万历废掉太子而立其亲生儿子福王朱常洵。
吴梅村在叙述福王遭难的《洛阳行》中,亦讽及郑贵妃:“我朝家法逾前制,两宫父子无遗议。廷论繇来责佞夫,国恩自是优如意。”[6]41-42其中,所谓的“家法逾前制”,乃以万历之宠爱郑贵妃母子而引发的政治风波而言。诗中还以汉高祖刘邦与戚夫人比喻明神宗与郑贵妃,并用戚夫人谋立赵王刘如意不遂之典故,再一次指斥郑贵妃夺谪的阴谋。此诗用典甚多,“少室峰头写桐漆,灵光殿就张琴瑟”典出《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原诗写的是卫文公迁都于楚丘后筑造宫室、广植树木之事。椅、桐、梓及漆均为木名,朱熹注曰:“四木皆琴瑟之材也。”[7]“桐漆”乃指从少室山采桐与漆以兴建宫殿,“张琴瑟”指大张歌舞,可见讽刺。卫文公广植树木乃振兴国家,而福王采伐树木则为营建宫殿以图享乐。诗中还以鲁恭王修建灵光殿模拟福王大兴土木。另外,诗中“倚瑟楚歌”典出葛洪《西京杂记》,“百子池”典出干宝《搜神记》,“鸿飞四海”典出《史记·留侯世家》,以上典故之运用,既蕴含讽刺,亦可见吴梅村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
福王就藩河南期间,贪财失德、鱼肉百姓,吴梅村在《绥寇纪略》中记载:
福王大婚费三十万,营洛阳府第二十八万……上所遣税使矿使数十人,月有奉,日有进,广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宝石,豫章磁,陕西异织文毳,蜀重锦,齐、楚矿金、矿银,他搜括赢羡亿万计,名人主私财,入贵妃掌握,拟斥十之九以资王……上为下诏,賜庄田四万顷,所司争之力,得减半……乘传,列旌旗笳吹,所至索舆皂饩廪无算,田之良楛,租之多寡,胥悬其口,常过汝州擅杀人,山东、江、楚之间,富家忧攘夺,农夫疲供亿,天下骚动。[4]211-212
郑贵妃恃宠乱制,福王则胡作非为、祸害河南,而万历放纵自若。福王与民争利,甚至影响到军饷供给:
其请福府食盐也,于洛中设州邸阁,中使至淮扬,支王盐一千三百引,干没要求辄倍。中州旧食河东盐,有令旨,非王店所出不得鬻。淮商开中既诎,晋引复滞,九边军饷无所资。[4]212
由此可见,万历溺于私情而忘天下之安危,变乱实由此际而起。再观《明史》的相关记载基本如出一辙,只多了一小段:
及崇祯时,常洵地近属尊,朝廷尊礼之。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2]3649-3650
两代福王的共同嗜好便是闭阁饮醇酒、玩弄妇女及倡乐,他们耗尽天下而搜括来的财富,最终为李自成所获,“以号召宛、洛,附从始众”[4]265。吴梅村在《绥寇纪略》中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攻河南,有营卒勾贼以致城陷,李自成汋福王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4]214。在《送周子俶张青琱往河南学使者幕六首》其五,吴梅村叹曰:
极目铜驼陌,宫墙噪晚鸦。
北邙空有骨,南渡更无家。
青史怜如意,苍生遇永嘉。
伤心谭往事,愁见洛阳花。[6]329
吴梅村再一次以赵王刘如意比喻受宠的福王,又将“甲申之变”比作西晋的“永嘉之乱”,因为后来拥小福王而成立的弘光政权似乎颇有划江偏安而治的迹象。当李自成兵陷洛阳、老福王死难的消息传回京师时,吴梅村在《洛阳行》里曰:
今皇兴念繐帷哀,流涕黄封手自裁。
殿内遂停三部伎,宫中为设八关斋。
束薪流水王人戍,太牢加璧通侯祭。[6]42
吴梅村在《绥寇纪略》中亦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福王遇害后崇祯的反应:
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日……上发御前银一万,坤宁宫四千,承乾宫三千,翊坤宫三千,太子一千,又慈庆宫懿安后一千……以慰恤福藩世子。[4]215
崇祯酷待臣下、刻薄边将,却在此际为作恶多端而又窃财于民、富可敌国的福王之死而再度浪费金钱,可见其不知轻重、徇私忘公。这再一次得见崇祯之昏庸自私,重宗室而轻臣下[4]209,溺于小我之亲情而忘天下大难之将至。吴梅村在《洛阳行》的最后几句慨叹:
帝子魂归南浦云,玉妃泪洒东平树。
北风吹雨故宫寒,重见新王受诏还。
惟有千寻旧松栝,照人落落嵩高山。[6]42
此诗由皇宫之恩宠而至嵩山落日作结,物是人非、悲凉至极。至于“受诏还”的“新王”,即小福王朱由崧劣迹败行甚多,然而掌握军队实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却“独念福王昏庸可利”[1]6,于是联络刘泽清等大将,抢先将福王迎至南京,胁迫群臣拥戴:
马士英既借四镇以迎立,四镇亦遂为士英所结。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无能为矣。[3]180
四镇均受制于马士英,而有心为国的史可法则因在迎立福王一事上而失势并备受孤立,至于以封爵拉拢四镇,则益令四镇骄横。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福王称监国,十五日就位,以“弘光”为年号。弘光政权的建立,其立朝方针为“讨贼复仇”。政权建立不久,便于江淮一带设立四镇:刘泽清驻淮安,管辖淮安等十州县;高杰驻泗水,管辖徐州等十四州县;刘良佐驻临淮,管辖凤阳等九州岛县;黄得功驻庐州,管辖滁州等十州县。四镇的任务乃护卫南京,剿灭河南、河北一带的流寇,并伺机恢复中原。弘光政权幻想如东晋或南宋一样,划江而治,因此对清廷并未做认真的防范,甚至建议双方合剿流寇[4]478-494。
朱由崧就位后,荒淫无道[1]156-157,昏庸程度较其父老福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明史》记载:
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擢至兵部尚书,巡阅江防。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2]3651
关于朱由崧的拥立者马士英,《明史·奸臣列传》评曰:
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划,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2]7941
至于阮大铖,本为阉党,曾于崇祯初年被废斥,其人品为公论所不齿。崇祯中期,他在南京力图复用,复社的陈贞慧、吴应箕等则起草《留都防乱檄》对其进行揭露与声讨。然而,阮大铖乃马士英之房师,遂被举荐为兵部右侍郎,此举被指摘为:
从来小人当国,止狥一人之私昵,而不顾天下之是非;止弄一时之威权,而不顾万世之公论。[1]43
吴梅村斥之曰:“阮怀宁由逆阉之余孽,乘国难以窃政。”[6]1013由此可见,弘光政权从建立之始,新君人选已种下祸根,且已集结了前朝党争之余绪,奸佞在位,日伺报复,大事焉有可为?
三、“中兴大业”的失败
弘光初立,吴梅村于五月廿九被任命为少詹[1]16。在《甲申十月南中作》一诗中,吴梅村对弘光朝表现出热切的期盼:
六师长奉翠华欢,王气东南自郁盘。
起殿榜还标太极,御舩名亦号长安。
湖吞铁锁三山动,旗绕金茎万马看。
开府扬州真汉相,军书十道取材官。[6]137
表面上兵强马壮,王气郁盘,且有如史可法辅佐,就连弘光帝为享乐而兴建的宫殿与游船,吴梅村亦误以为乃开国盛事,并将之比拟为唐初的“太极宫”与三国孙权之御船“长安”号。吴梅村又于《读史杂感十六首》其一中曰:
镇静资安石,艰危仗武侯。
新开都护府,宰相领扬州。[6]96
吴梅村在此以击败前秦大军并中兴东晋的谢安与六次北伐的蜀相诸葛亮比喻史可法,期望弘光政权能在史可法的带领下,北御强敌、恢复中原,借此以寄托其对弘光“中兴”的热切期待[1]11-14。
然而,弘光政权刚建立,便谬政频仍,先是刘宗周上陈不应胡乱封爵:
无故而施之封典,徒以长其跋扈。以左帅之恢复也而封,高、刘之败逃也而亦封,又谁为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随之;外廷既封,中珰随之。[3]196[1]46
此中,最荒谬的是弘光政权竟将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于军前为监军太监举行生日宴会而死于清军铁蹄之下的吴阿衡谥为“忠毅”[3]245。此外,又有所谓的“南渡三疑案”:一是大悲狱案,苏州僧人大悲与潞王朱常淓认作本家,1645年冬,大悲由苏州至南京,弘光帝疑其替潞王争夺帝位而前来刺探消息,将其下狱致死[注]大悲的身份相当复杂,或自称烈皇、齐王、定王、潞王之弟,或称休宁王朱世杰,又或言非大悲,而是大悲之行童。张廷玉等的《明史》卷308;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卷8;夏燮的《明通鉴》附编卷1(《考异》);谈迁的《国榷》卷103;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南略》卷3(《大悲假称定王》条);陆圻的《纤言》下(《大悲和尚》)等,皆有不同的记载。;二是皇妃童氏案,弘光帝逃难时,在开封结识了周王府中的宫人童氏并有染,弘光即位后,童氏来投而遭拒,并将其下狱致死[注]此相关论述,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南略》卷3,第185—187页,187—190页;谈迁的《国榷》卷104;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卷9;夏燮的《明通鉴》附编卷2上;陆圻的《纤言》中《童氏》;邹漪的《明季遗闻》;留云居士辑的《明季稗史续编》;钱等著的《甲申传信录》第267页,均有所记载。;三是伪太子案,太子朱慈烺久无消息,忽于1645年春据传来到南京,查为假冒而下狱[注]相关论述可参阅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南略》卷3,第174—181页;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第64页。南炳文先生据《明季遗闻》与《小腆纪年附考》(卷9)之记载而明确指出“这个所谓北来的太子,实系假冒”。详见南炳文的《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这些案件均非同小可,特别是关于太子朱慈烺的真假问题,若处理不当,既直接损害弘光帝的形象,亦势必影响其统治威信。然而,弘光帝及马士英、阮大铖等根本无视事件的严重性,以至酿成左良玉以太子案为借口而举兵“清君侧”,从而导致弘光朝迅即倾覆。
其时,弘光政权的文臣武将大多贪赃枉法,贿赂公行之事不绝如缕,对此,吴梅村在《读史杂感十六首》其二做出抨击:
莫定三分计,先求五等封。
国中惟指马,阃外尽从龙。
朝事归诸将,军输仰大农。
淮南数州地,幕府但歌钟。[6]96
“国中惟指马”乃以赵高之指鹿为马以喻在马士英主政之下的弘光政权,文官只图进官封爵、纵情享乐,武将则骄横跋扈、苟且偷安,此亦可见于吴梅村《读史杂感十六首》其七的“江州陈战舰,不肯下浔阳”和其八的“已设牵羊礼,难为刑马心”[6]98。“牵羊礼”指的是金国的受降仪式,俘虏赤裸上身,披着羊皮,颈上系绳,被人牵引;“刑马”指的是古代结盟之杀马歃血,立誓为信,吴梅村在此讽刺弘光朝之文臣武将均已准备投降,根本没有立誓北伐之决心。吴梅村又刺曰:
北寺谗成狱,西园贿拜官。
上书休讨贼,进爵在迎銮。
相国争开第,将军罢筑坛。
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6]96
此诗讽刺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之兴狱倾陷东林人士,贿赂成风、贪图逸乐,毫无北伐之志。“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指的是奉命北上议和的左懋第为清军所执,不降而诛[1]275-277,在此以其如苏武般的节操反讽苟且偷安的马士英、阮大铖之辈。吴梅村又刺曰:
御刀周奉叔,应敕阮佃夫。
列戟当关怒,高轩哄道呼。
监奴右卫率,小吏执金吾。
匍匐车尘下,腰间玉鹿卢。[6]97
在此以《南史》中周奉叔的刚烈勇猛与阮佃夫的贪鄙弄权构成对比,以歌颂左懋第的忠贞不屈,暗讽马士英、阮大铖二人的腐败弄权。吴梅村在《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又直接抨击马士英、阮大铖和高杰、左良玉的猖狂跋扈,以及百姓遭受军队之骚扰:
江南昔未乱,闾左称阜康。
马阮作相公,行事偏猖狂。
高镇争扬州,左兵来武昌。
积渐成乱离,记忆应难详。[6]25-26
此诗作于顺治十年(1653)吴梅村赴京途中,马士英、阮大铖行事猖狂,高杰、左良玉兴兵作乱,多少年后,百姓仍忘却不了弘光朝文武大臣的腐败与荒唐。李清转引述其同年吴应恂所见左良玉麾下士兵之暴行:
左良玉兵半群盗,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贿,用板夹爇之,肥者或脂流于地。又所掠妇女,公淫于市,若入舟后,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则身首立分。[8]
吴应恂是崇祯辛末年(1631)的进士,又是李清的同年,且是楚令,所言必不虚。从这则数据可见,左良玉纵兵扰民,如此军队如何能抗击李自成的大顺军以及清廷的铁骑?而作为南明的军队,不爱护百姓,反而作恶多端、鱼肉百姓,实令人发指。如此军队、如此朝廷,怎会不败?唯一具有复国意识的便是史可法,吴梅村在《扬州四首》其二叹曰:
野哭江村百感生,斗鸡台忆汉家营。
将军甲第橐弓卧,丞相中原拜表行。
白面谈边多入幕,赤眉求印却翻城。
当时只有黄公覆,西上偏随阮步兵。[6]396
兵火连年、民不聊生,吴梅村由“斗鸡台”而感慨西汉周亚夫之“细柳营”的不复存在。史可法虽有北伐之志[1]192,但在“白面谈边多入幕”的局势下,孤立无助、难预机枢,只能“拜表”外出督师扬州。“赤眉”指曾为流寇的高杰,高杰乃陕西米脂人,本为李自成同乡、部下,后降明[2]7005。至于“当时只有黄公覆,西上偏随阮步兵”,指的是黄得功奉马士英之命抵御左良玉。吴梅村还有《白门遇北来友人》与《有感》两首,抒发了他对中原沦丧的悲哀,及对弘光朝之荒谬的讽刺:
风尘满目石城头,樽酒相看话客愁。
庾信有书谈北土,杜林无恙问西州。
恩深故国频回首,诏到中原尽涕流。
江左即今歌舞盛,寝园萧瑟蓟门秋。[6]136
以被困于北周的庾信与避东汉末年王莽之乱的杜林,惋惜滞留于北方的友人,讽刺马士英、阮大铖诸人之祸乱朝廷。其时弘光初建,而崇祯十七年(1644)冬的江左却歌舞升平,故吴梅村讽刺并哀叹曰:
已闻羽檄移青海,是处山川困白登。
征北功惟修坞壁,防秋策在打河冰。
风沙刁斗三千帐,雨雪荆榛十四陵。
回首神州漫流涕,酹杯江水话中兴。[6]137
神州失陷、举国哀号,而刚建立的弘光帝却沉醉于淫乐之中,所谓的“征北”与“防秋”皆为敷衍了事,朱明王朝的十四陵任由清朝铁蹄蹂躏。至此,吴梅村对弘光政权所谓的“中兴”,已不复期望。
弘光政权的另一谬政,便是恤慰已故逆案中人及其党人,而此中曾被吴梅村弹劾的蔡奕琛更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3]253-258,遂令吴梅村及复社中人深感不安[3]268。不久,马士英、阮大铖辈果然大兴党狱以报复东林党与复社,复社元老周钟以降李自成之罪被杀[注]关于周钟的生平及投诚及其被杀,详见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北略》卷22,第605—607页;《明季南略》卷3,第200页。另见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的《梅村诗话》,《吴梅村全集》卷58,第1141页。,陈贞慧被捕,侯方域与吴次尾逃出南京[9]。阮大铖更捏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名单[2]3434,深文周纳,意图打击东林与复社中人;又做《蝗蝻录》,蝗是蝗虫,蝻是小蝗虫,即将东林党人视为蝗虫,东林党人的子弟参加的复社者则被视为小蝗虫;又将东林党、复社周围的人称为蝇或蚋,做成《蝇蚋录》[注]关于阮大铖迫害复社中人的论述,可参阅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第62页。。其所作所为,毫无大臣之风范,此际不共济时艰,政权未稳却忙于内斗,此即《明史》所慨叹之“日事报复”[2]7941。吴梅村在《〈清忠谱〉序》中叹曰:
甲申之变,留都立君,国是未定,顾乃先朋党、后朝廷,而东南之祸亦至。[6]1216
见弘光朝政如此腐败,吴梅村于是辞职,自称“报国有心,趋朝无力”[6]1126,又在《与子暻疏》中曰:“南中立君,吾入朝两月,固请病而归。”[注]相关论述可参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校的《吴梅村全集》卷57,第1132页;叶君远的《吴伟业生平考辨》,《清代诗坛第一家:吴梅村研究》第14—15页;徐江的《吴梅村研究》第45页。顾湄在《吴梅村先生行状》中曰:
先生知天下事不可为,又与马、阮不合,遂拂衣归里,一意奉父母欢。[6]1404-1405
吴梅村洞悉先机,由此又避过弘光政权之倾覆与如钱谦益般的迎降一劫。
四、弘光帝的荒淫
弘光登基,马士英即奏请:“选淑女以备中宫。”[3]188于是,弘光帝立刻忙于遴选后妃,派出宦官四出“挨门严访淑女”,“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弄得如陈子龙所奏“闾井骚然”;利瓦伊樾亦奏“道途鼎沸”[1]92。
吴梅村在顺治八年(1651)写下《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此诗以恋人卞玉京操琴,记述她自身以及“中山好女”等名门闺秀与卞玉京等青楼名妓各因南明弘光帝选妃与清兵南下的悲惨遭遇。此诗前六句,由“驾鹅逢天风,北向惊飞鸣”开始,描绘卞玉京仓皇逃命之氛围。自“中山有女娇无双”至“青冢凄凉竟如此”,讲述的是中山王后代的徐氏女、祁氏及阮氏的悲惨遭遇。从“万事仓皇在南渡”至“青冢凄凉竟如此”,吴梅村以一系列的淫乱昏君如陈后主、东昏侯即齐废帝萧宝卷以及晋武帝司马炎来讽喻弘光帝,显然是对南明政权的绝对否定。
顺治二年(1645)五月初十,即清兵渡江的第二天,弘光帝慌忙乘马从南京通济门逃亡,文武百官无一知晓,遗下之前忙于征召的一众女子。诗中慨叹又讽刺的是当弘光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未成之时,清军已经南下,三位女子尚未见到君王,就被清军当作战利品,劫掳北去。吴梅村痛斥了弘光帝的荒淫无道及南明政权的荒谬后,又从“我向花间拂素琴”至“携来绿绮诉婵娟”句,转入卞玉京自身在离乱中的叙述,吴梅村借卞玉京之口控诉清兵同样向弱女子施以淫威。为了躲避清兵的掳掠,卞玉京改装逃亡回苏州虎丘之山塘。自“此地繇来盛歌舞”以下,言清军南下,昔日的繁华已成“山塘寂寞遭兵苦”。卞玉京的同伴沙才、沙嫩两姊妹以及董白,也在乱离中化为尘土。
弘光帝每天“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并下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加上“宴赏赐皆不以节”,以致“国用匮乏”,“边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乘时射利,识者已知不堪旦夕矣”[1]104。陈子龙痛陈曰:
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臣甚为之寒心也。[1]93
吴梅村在《读史杂感十六首》其六叹曰:
贵戚张公子,阉人王宝孙。
入陪宣室宴,出典羽林屯。
狗马来西苑,俳优侍北门。
不时中旨召,着籍并承恩。[6]98
阉人王宝孙年仅十余,眉目清秀,犹如处女,他乃南北朝时的东昏侯萧宝卷的玩偶,甚至被留在御榻旁侍寝。王宝孙因恃宠逐渐干预政事,甚至矫诏控制大臣,以至于骑马入殿,诋诃东昏侯。吴梅村一再以东昏侯模拟弘光帝,以揭露其淫乱无行与朝纲不振[1]108-109。
五、弘光政权的崩溃
弘光帝及弘光朝政固然罄竹难书,而其迅即倾覆,则又起于左良玉之“清君侧”行动。左良玉拥有号称百万的大军[4]312,乃南明最为强大的军队,他扼守上游的战略要地武昌。然而,弘光拥立,马士英、阮大铖之用事,则令左良玉大为不满[注]相关论述可参阅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的《吴梅村全集》卷53,第1057页;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南略》卷3,第195—196页,第196—198页,第198—200页。。吴梅村认为原因在于“朋党”:
左武人,初不知所为朋党,既见板矶筑城为西防,叹曰:“西今复何防,真乃我耳。”不免有沿江之计矣。[4]313
侯方域为避马士英、阮大铖而逃出金陵,但其父侯恂则对左良玉有知遇之恩,他向左良玉坦陈马士英、阮大铖之恶行,由此而造成左良玉与马士英、阮大铖之矛盾。后来发生北来太子疑案,朝中争执不下之际,左良玉遂于四月四日以“清君侧”为名,举兵东下。吴梅村在《绥寇纪略》记载:
左以乙酉三月廿六日传檄讨马士英,空国行,自汉口达薪州,火光接天者二百余里。[4]245
内忧外患均未平定,即生内讧。左良玉之东犯,令马士英大为惶恐,立命阮大铖率兵会朱大典巡防江上,又调江北镇将黄得功、刘良佐西进堵击,并令史可法带兵入卫。江北之防因此空虚,清兵遂乘机连下徐州、泗水,渡过淮河。史可法心急如焚要求救援,而马士英却以左良玉之威胁为借口而不允。吴梅村于《扬州四首其三》曰:
尽领通侯位上卿,三分淮蔡各专征。
东来处仲无它志,北去深源有盛名。
江左衣冠先解体,京西豪杰竟投兵。
只今八月观涛处,浪打新塘战鼓声。[6]396
前四句写的是史可法督师扬州,指挥四镇军事。四镇以拥立之功而获封为侯,而其中的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三镇正是驻守淮蔡一带。处仲乃东晋大将王敦,以喻左良玉;深源乃东晋重臣殷浩,以喻史可法[注]清廷亦称史可法为“领袖名流”。见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南略》卷3,第142页《清朝移史可法书》。。王敦起兵于武昌,东下建康,本意欲倾覆东晋政权,吴梅村认为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军东下,迹似王敦而并没有谋反之意,故曰:“无它志。”[注]弘光亦认为左良玉并没有叛逆之意。见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南略》卷3,第202页。殷浩乃东晋清淡名士,曾率军北伐失败,以其喻史可法之殉难[1]203-206。然而,左良玉率军东下至九江时却突然暴毙,军队遂大乱而溃散。吴梅村在《楚两生行》诗序中哀叹:“宁南没于九江舟中,百万众皆奔溃。”[6]246其军队被马士英派来堵截的黄得功部击溃,余部在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的率领下降清。北线的高杰为许定国设计所害[1]157-158,部下或溃散或降清。“江左衣冠先解体,京西豪杰竟投兵”,指的便是清兵渡江,弘光帝出逃,诸臣联名上降表于清兵统帅豫亲王多铎。
当清兵南下时,黄得功却在芜湖一带与左良玉的部下混战,南明江淮防线空虚,清兵迅速攻破扬州,史可法殉国[注]关于扬州之失陷之论述,可参阅南炳文的《南明史》第60—61页。。吴梅村以诗悼之:“阴风夜半扬州月,相国魂归哭孝陵。”[6]167吴梅村复于《读史杂感十六首》其五对弘光帝做出抨击:
闻筑新宫就,君王拥丽华。
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
使者螭头舫,才人豹尾车。
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6]97
以“拥丽华”暗喻弘光帝为陈后主,而以“可怜青冢月,已照白门花”作结,邓汉仪在此对“可怜”二句评曰:“惨不忍闻。”[6]97此处所指乃忙于选妃的弘光帝,不久便于北京被弃市。
六、其他南明政权之失败
弘光政权崩溃后,各地的南明小政权亦陆续遭受重挫: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兵攻陷浙东,鲁王朱以海避难海上[1]293;八月,清兵自浙入闽,隆武帝,即唐王朱聿键遇害;十二月,清兵占领广州,永历帝,即桂王朱由榔则逃往桂林,以后便游弋于西南一隅[注]相关论述分别见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南略》第334—335页,第336—337页,第339—340页,第345—346页,第350页,第351—352页,第362—363页,第364—365页,第374页,第424—425页,第426页,第438页。。最终,永历帝于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为缅甸人所执,献于吴三桂军前,并为其所杀[1]475-483。《清史稿》的记载较为具体,突出吴三桂的弑君行径,康熙元年(1662)四月:“三桂执由榔及其子,以弓弦绞杀之,送其母、妻诣京师,道自杀。”[10]
至此,清朝已控制了中原的绝大部分地区,恢复渺茫。吴梅村作于顺治八年(1651)的《杂感二十一首》组诗,其九、其十两篇叙述时为永历政权主帅何腾蛟的艰难抗战。永历二年(1648)何腾蛟收拾两湖危局,一度形势大振,吴梅村于组诗其九曰“西上祖生仍誓楫,路旁还指旧通侯”[6]165,祖生指祖狄,以东晋名将祖狄之誓揖中流、坚持北伐比喻何腾蛟之谋复湖北;其十曰“十载间关历苦辛,汩罗风雨泣孤臣”“报主有心争赤壁,借兵无力听黄巾”[6]165,其时李自成余部李赤心(即李锦、李过)等接受永历的封爵,虽为何腾蛟所节制,然却不全力协同作战而致溃败,以致何腾蛟被俘并不屈死节[1]389-390;“王孙去国余三户,公子从亡止五人”两句[6]165,既道出永历帝当时的危急态势,又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古谣及晋国公子重耳出亡而终复国的典故,寄托其复明之期望。吴梅村又在《读史杂感十六首》其十一曰:
屡檄知难下,全军压婺州。
国亡谁与守?城坏复能修。
喋血双溪阁,焚家八咏楼。
江东子弟恨,伏剑泪长流。[6]99
此诗写朱大典坚守金华,兵败城陷后全家自焚殉国的壮烈事迹。朱大典乃崇祯朝之大臣,在弘光朝除授兵部尚书,弘光政权倾覆后,朱大典奔返浙江。鲁王、唐王相继自立[1]287,303-304,且又因争正统而同室操戈[1]291,朱大典出于顾全大局而同时接受两王所授的大学士与督师的职衔,一心抗敌。公元1646年,清兵欲由浙入闽攻隆武帝(唐王),朱大典死守金华三个月,击杀清兵数万,城破后全家自焚殉国,金华全城被屠[6]99。吴梅村《读史杂感十六首》其十二叙述隆武政权兴亡始末:
听说无诸国,南阳佳气来。
三军手诏痛,一相誓师哀。
鲁卫交难合,黥彭间早开。
崆峒游不返,虚筑越王台。[6]99
“无诸国”,指的是秦、汉之际闽越王无诸,以喻身在闽地的唐王(隆武帝)。唐王(隆武帝)原封地在河南南阳,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刘秀起兵便在南阳,吴梅村以唐王比拟光武,可见厚望。隆武帝即位之初,亲撰诏书,语极痛切,天下激励,人心振奋。然而,将相不和,“一相誓师哀”指的是他所极力推崇并曾在崇祯朝营救过的黄道周,此时为隆武政权首辅,孤军出征却不久败亡[1]314-321。其时,鲁王朱以海在浙江以监国名义抗清,唐、鲁二王政权本应同仇敌忾、协同作战,但却因争遂正统之名号而被清军逐一击破,唐王殉国,鲁王逃亡海上。鲁、卫皆为周室同姓之国,以鲁、卫喻唐、鲁二王,既切合以宗周喻朱明,尊明之意亦存其中。鲁、唐不协,主要责任是在两王朝中大臣的正统之争,尤其两王麾下大将如郑芝龙、方国安,不顾大局[1]330-331,故以黥布、彭越为喻。唐王(隆武帝)为清兵所俘杀,吴梅村以黄帝游崆峒不返之典故,喻其殉国。最后六首是写唐王(隆武帝)、鲁王、桂王(永历帝)三支力量前后抗清的事迹[注]关于南明的抗清论述,可参阅钱穆的《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第825—827页。,褒贬强烈,故清代通行诸本均没收入,唯赖宣统三年(1911)董康所刻的《梅村家藏稿》[注]相关论述可参阅阚红柳的《〈梅村家藏稿〉文献史料价值评析》,载《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48页。,方得以保存。
《读史杂感十六首》其十三写鲁王部将在浙南闽北的抗清战事,其十五写金声桓于江西反正,其十六写姜曰广于南昌兵败殉难[1]392-393。其十四写桂王的永历政权在湘、桂、川、粤的抗清战争,当时在湖广、巴蜀一时出现军势大振的气象,吴梅村热情赞美抗清将士:
计出游云梦,雄风羡独醒。
连营巴水白,吹角楚天青。
五岳尊衡峤,三江阻洞庭。
故家多屈宋,应勒武冈铭。[6]100[1]383-386
永历元年(1647)何腾蛟联络李自成余部,策划由湖南、巴东两路出兵,进窥湖北,意图收复武昌,故吴梅村赞以“计出游云梦,雄风羡独醒”;而“连营巴水白,吹角楚天青”,则是形容此次军威之盛大;“五岳尊衡峤,三江阻洞庭”两句,衡峤即南岳衡山,湖南当时在永历政权范围之内,以五岳应尊南岳衡山为喻,指天下应共尊永历政权;“故家多屈宋,应勒武冈铭”两句,楚地本是屈原、宋玉的故乡,楚中多才,吴梅村认为应当大书勒石以铭刻将士之赫赫战功。《杂感二十一首》组诗的第十六首写四川战事,第十七首悼念史可法殉国,第十八首嘲讽吴三桂,第二十一首叙述瞿式耜在明朝因党人案下狱,其后在桂林抗清[1]348-349,363-364,失败而殉国[1]428-432。第十九首叙述孔有德叛明降清并率军南下攻占桂林杀害永历政权的大学士瞿式耜:
蓬莱阁上海云黄,用火神机壁垒荒。
本为流人营碣石,岂知援卒起萧墙。
戈船旧恨东征将,牙纛新封右地王。
辛苦中丞西市骨,空将热血洒扶桑。[6]167
“萧墙”之祸指孔有德叛变于山东登州,起因在于孔有德违抗赴援宁远、锦州的军令,于崇祯六年(1633)投降清朝,并为清朝带去了红夷大炮(“用火神机”)及其制造与使用技术,增强了清兵的战斗力[注]相关论述可参阅韦庆远的《西洋火炮──明朝最后的救星与克星》,载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的《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至于“本为流人”以下四句,指的是孔有德原是驻守皮岛的都督毛文龙的部将,毛文龙以皮岛为据地,自海上出击以牵制清兵,然而自崇祯二年(1629),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后,孔有德即投奔登州[注]相关论述可参阅可参阅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的《明季南略》卷16,第436页《附记孔有德遗事》;樊树志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70页。。崇祯四年(1631),孔有德叛变并与明军战于山东,崇祯六年(1633)孔有德战败后,便由登州出海投降清朝。“戈船旧恨东征将”,指的是孔有德曾为明朝东江镇帅毛文龙部下,“右地王”本为匈奴王号,在此用以喻孔有德接受皇太极的封爵。“辛苦中丞西市骨”指的是瞿式耜,写他虽一腔热血撑住危局[1]397-398,然却终被孔有德献予清廷而被弃市。忠臣之悲惨下场与降清叛将之狰狞面目,在此强烈对照之下,更见“甲申之变”后抗清的残酷过程及不同的人性。
七、结语
以上论述可见,吴梅村创造性地以组诗形式拓展了诗歌的纪史功能及书写空间,《读史杂感十六首》,实际上就是一部南明痛史。弘光政权的荒淫无道以及其他南明小政权之内讧以致败亡,偏安无望、恢复无谋,君无道而臣无能,对此,吴梅村在诗中做出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至于忠臣勇将以及抗清民众,吴梅村则热情歌颂爱憎分明。可惜的是,各个南明小政权均纷纷溃败,令吴梅村及众遗民余生均陷于亡国的无尽悲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