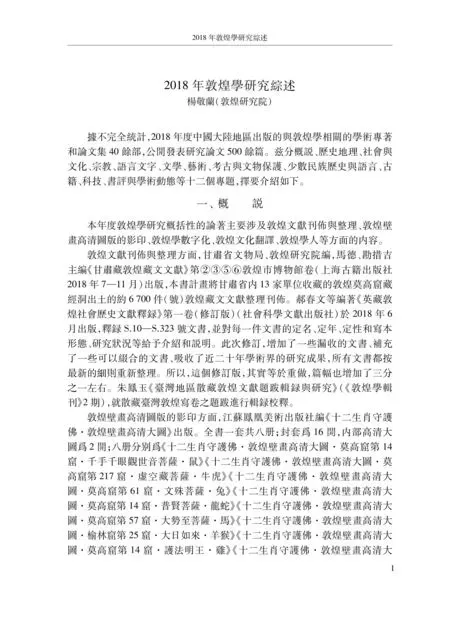敦煌飲食文化研究綜述
劉艷燕(敦煌研究院)
敦煌飲食文化研究,既是敦煌學研究的一個分支,也是中國飲食文化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敦煌石窟壁畫中,保存了許多飲食方面的形象資料,從耕作、播種、打碾到宰殺、各種宴飲等,在敦煌壁畫上都有反映。而魏晋、十六國時期敦煌以及附近嘉峪關、酒泉等地的墓室壁畫中,也有一些反映宰殺、宴飲、飲食品製作的磚畫以及出土的飲食器具。另外敦煌藏經洞出土的6萬多件文書中,保存了大量敦煌人飲食生活的第一手資料。它們反映了敦煌人從飲食結構、食物加工、飲食品種、飲食風俗、節日食俗、飲酒習俗等方面的内容。同樣,敦煌飲食文化受西域或更遠的國家和周邊民族的影響,顯示了多元文化的特點。研究敦煌飲食文化是對中國古代飲食文化研究的極大補充、完善和發展。對這些珍貴資料的整理研究,不僅拓展了敦煌學研究領域,也極大推動了中國古代飲食文化的向前發展。回溯敦煌飲食文化的研究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初步探索期(1980—1999)、蓬勃發展期(2000—2009)、深入研究期(2010至今)。本文擬對多年來敦煌飲食文化研究史以時間順序進行梳理,以便給學界提供較爲詳實的敦煌飲食文化研究相關的歷史成果、研究現狀、信息資料等。
一、 初步探索期(1980—1999)
敦煌飲食文化的研究較敦煌學領域的其它研究工作而言,起步較晚,涉及研究這一領域的專家也爲數不多。自20世紀80年代初,才有少數學者在論著中提到敦煌飲食文化這一命題。
1983年,施萍婷《本所藏〈酒賬〉研究》(《敦煌研究》1983年創刊號)主要依據敦煌文物研究所所藏歸義軍時期的《酒賬》文獻卷子,研究了歸義軍時期的禮儀、酒的計量單位和歸義軍與當時西北各民族地方政權之間的關係,是較早涉及到敦煌酒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作品。1988年,王進玉《敦煌壁畫中的糧食加工工具》(《農業考古》1988年2期)依據敦煌壁畫中的形象資料,就圖中所出現的石磨、足踏碓等糧食加工工具及其有關的問題作了梳理探討,指出敦煌壁畫中的一些加工糧食的場面,表現了歷代人民生産生活的真實情況。1989年,高國藩《敦煌民俗學》對敦煌的民間飲食風俗做了簡單的介紹,給敦煌飲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信息資料。隨後到90年代初期,敦煌飲食文化研究逐漸興起,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並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1990年,王賽時《唐代的寒食風俗》(《民俗研究》1990年3期)指出,寒食是唐代八大節之一,尤其受人們的喜愛。敦煌文書中就有關於寒食節日習俗的記載。王冷然的《寒食篇》,反映出唐人對寒食節的重視,活動呈現多樣化,也是我們研究寒食節日習俗文化重要的史料依據。
1991年,譚真《敦煌古藥方〈神仙粥〉剖析》(《敦煌研究》1991年2期)本文對敦煌古藥方《神仙粥》進行了全文釋録並對此藥方做了剖析。依據《神仙粥》是《呼吸静功妙訣》之附屬藥方从文字體上分析,大約是北宋初期寫本,早不過五代時期。古藥方《神仙粥》在醫食同源,藥物特性、藥理功能、炮製比例及服用方法等方面都具有科學性,對現代中藥配方及療法具有指導意義。暨遠志《唐代茶文化的階段性——敦煌寫本〈茶酒論〉研究之二》(《敦煌研究》1991年2期)本文結合文獻和考古材料,對唐代茶文化的演變軌迹分爲三個階段進行了論述。第一階段,陸羽《茶經》階段(公元780年以前);第二階段,敦煌寫本《茶酒論》階段(公元780年—824年);第三階段,以法門寺茶具爲代表的階段(公元825—907年)。敦煌寫本《茶酒論》經考證,確認是唐代貞元元和年間的作品,而且,這個寫本中涉及到唐代的茶酒文化,記述了780年以後唐代茶文化的新變化。
1992年,黄正建《敦煌文書與唐五代北方地區的飲食生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1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主要從敦煌文書中的飲食資料入手,來揭示當時中國北方地區的飲食生活,開創了運用敦煌資料研究中國飲食文化之先例。敦煌文書中有關飲食生活的文書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各種帳目,包括食物帳、入破曆、會計帳等。這些帳目大多都是晚唐五代時期寺院的收支帳目。還有一類是流行在敦煌的字書,這些資料爲研究唐五代的飲食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1995年,鄭炳林《唐五代敦煌釀酒業研究》將敦煌酒業置於唐五代時期敦煌社會經濟的大背景之下,闡述了敦煌社會的特點。指出唐五代時期敦煌經濟繁榮昌盛,釀酒行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氣象,飲酒習尚也非常盛行。1996年,盛朝暉《“細供”考》(《敦煌學輯刊》1996年2期)主要依據敦煌文書記載,對“細供”重點招待哪些人物、用於哪些場合進行了考證。指出“細供”主要用於三種場合招待重要的客人,第一類是外交使節,第二類是祭祀賽神用,第三類是招待一般督造官員及工匠。“細供”一詞反映出歸義軍政權對待邦交、祭祀活動的重視。因人而異,招待的規格檔次不一,因事而又有所不同。1997年,季羨林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薈萃了百年來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其中有高國藩、譚蟬雪、李正宇等先生撰寫的數十條與敦煌飲食研究有關的詞條,介紹了敦煌飲食文化的相關基本知識。
1998年,高啓安《釋敦煌文獻中的梧桐餅》(《敦煌學輯刊》1998年1期)主要依據敦煌文獻及現實生活中當地居民的做餅習慣對梧桐餅作了全新的解釋。指出敦煌文獻P.4909卷中“又造梧桐餅面壹斗”中的梧桐餅,就是用梧桐泪和麵所造的餅。而P.2058背《驅儺詞》中的“一升梧桐泪”也是爲了用它來和麵做食物驅趕鬼的。梧桐餅的出現,説明敦煌人在一千多年前就知道了用梧桐碱來發麵製作食物的方法。1999年,高啓安《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敦煌學輯刊》1999年1期)指出唐五代至宋的敦煌,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在經濟上以當地獨立的體系爲主,其量制和量器呈現出有别於中原的特殊複雜狀況。其特點主要是: 一是在承襲唐中央政府頒佈的量制法規的同時,民間通行大斗制,個别的量制與傳統觀點有所不同。二是由於受吐蕃統治過半個多世紀,又使用吐蕃的量制。三是特殊的計量方法,如馱,既有傳統的“漢馱”,也有吐蕃的“蕃馱”。四是酒的計量方法有其獨立的體系。高啓安、索黛《古代敦煌人的飲食》(《絲綢之路》1999年1期)指出隨著敦煌飲食資料的發現和研究,使我們有機會瞭解到一千多年以前,敦煌人當時的飲食習慣,究竟怎樣吃、吃什麽。敦煌地處西北,有着比較早的農業開發史,文中對敦煌古代人愛吃的食品種類、麵食烹調方法、蔬菜和水果及飲酒習俗等都做了全方面的闡述。高啓安、王璽玉《唐五代敦煌人的飲食品種研究——敦煌飲食文化研究之三》(《敦煌研究》1999年2期)指出唐五代敦煌人的飲食品種,除了近三十種餅以外,還有其他不少的非餅類食物,有炒麵、冷讓、冷淘、水麵、飯、油麵、粥(粥、漿水粥、白粥、米漿水)、灌腸麵、煎膠麵、饊飯、粽子、煮菜麵、鬚麵等,它們和各種餅一起,構成了敦煌人主要的加工食物品種,是敦煌人膳食結構中最主要的部分,一些食物的出現,反映了敦煌食物加工技術的進步和發展。高啓安《唐五代敦煌僧人飲食的幾個名詞解釋》(《敦煌研究》1999年4期)指出唐五代敦煌的僧人飲食,是敦煌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僧人飲食在敦煌飲食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敦煌社會經濟類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寺院的賬籍文書,其中與僧人飲食有關的資料相對豐富,因而保存了不少當時敦煌寺院僧人的宗教儀式飲食、節令飲食、日常飲食等方面的資料。其中有幾個特殊的用語和名詞,它們是討論僧人飲食的前提。該文依據敦煌文書對唐五代敦煌僧人飲食的幾個特殊名詞和用語進行了考證,這與研究僧人飲食戒律、造食用途、食物來源等有密切關係,也是探討僧人飲食必先搞清楚的前提。
二、 蓬勃發展期(2000—2009)
進入新世紀,敦煌飲食文化研究得到了學術界更廣泛的關注,敦煌飲食文化研究也取得了非常矚目的成果,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良好局面。
敦煌文獻中與酒有關的材料説明,作爲東西文化交通的咽喉要道,敦煌有著悠久的釀酒歷史,有着深厚的酒文化積澱,飲酒習俗是敦煌飲食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敦煌古代的飲酒習俗很盛,酒在敦煌人的生活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各種活動都少不了酒,如宴會、祭拜、招待使節、婚喪、慶典等。
在敦煌飲酒習俗研究方面,近年來,高啓安對敦煌古代的飲酒習俗進行了更進一步的論述,發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章。如2000年,高啓安《唐五代敦煌人的飲酒習俗述論》(《敦煌研究》2000年3期)指出敦煌人飲酒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敦煌幾乎各社會、各階層的人均飲酒,寺院的僧人、尼姑也不例外。敦煌人的飲酒方式既有“喧拳”,也有文雅的籌令。敦煌人愛喝酒,敦煌酒的銷量很大,除了敦煌有悠久的造酒、飲酒傳統外,也與敦煌所處交通要道有關,往來的商旅和使節影響着敦煌酒的供求關係,還與敦煌糧食産量相對富裕有關。高啓安《古代敦煌人的飲酒方式和酒量》(《中國西部風采叢書·隴原酒業風采》,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文對敦煌人的飲酒方式及喝酒的酒量進行了論述,指出敦煌人喜歡飲酒而且喝酒豪爽,酒量普遍很大。高啓安《唐五代敦煌人的宴飲活動述論》(《西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3期)指出唐五代時期的敦煌人,有許多宴飲活動,這些宴飲活動的名稱也很特别。一般在歸義軍招待周邊政權的使節、某項工程完工、社人聚會、節日慶祝、迎送首長等儀式和活動中舉辦。這些宴飲活動不僅是一種集中、大規模的飲食活動,也是調解人與人之間關係、增加社團和社會群體之間交流的重要手段。
2001年,高啓安《從莫高窟壁畫看唐五代敦煌人的坐具和飲食坐姿(上)》(《敦煌研究》2001年3期)、《從莫高窟壁畫看唐五代敦煌人的坐具和飲食坐姿(下)》(《敦煌研究》2001年4期)主要依據敦煌壁畫中的形象資料研究了唐五代敦煌人的坐具,並對他們的飲食坐姿進行了探討。指出飲食方式是飲食文化的重要内容,它除了與生産方式密切相關外,還與飲食器具的發展、飲食制度等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是飲食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進食者的坐姿是構成飲食方式的重要環節。唐五代至宋時期出現在飲食圖上各種坐具,這些傳統坐具無論其功能和造型均有分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發展和創新。坐具的變化和這一時期人們的飲食坐姿以及飲食制度相適應。
2002年,高啓安《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靈口之店推磨圖”之我見》(《敦煌學輯刊》2002年1期)指出敦煌莫高窟第61窟著名的五臺山圖中的“靈口之店”圖,歷來被學術界認爲是“推磨圖”,本文否定了這一傳統觀點,認爲這是一幅“杠子壓麵圖”。高啓安《敦煌文獻中的“草子”爲“沙米”考》(《敦煌學輯刊》2002年2期)指出敦煌文獻中多次出現了一種可以食用的“草子”,經過對其顔色、形狀的分析、對比、考證,認爲這些“草子”正是今天城裏人喜歡的“沙米”。高啓安《唐五代敦煌的飲食胡風》(《民族研究》2002年3期)依據敦煌文獻和敦煌壁畫的資料,從食物原料、飲食品種、飲食器具、飲食禮儀、胡姬酒肆、飲食結構等方面探討了唐五代敦煌地區飲食中的“胡風”現象,進一步討論了敦煌地區“飲食胡風”濃重的原因和特點,以及其在中西飲食文化傳播中的作用。
在敦煌僧人飲食研究方面,敦煌作爲古代的佛教文化聖地,敦煌僧人飲食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敦煌僧人因獨特的地域因素,又具有不同於其他地方僧人的飲食習俗。敦煌社會經濟類文書中各寺院的帳籍,大多都與飲食有關,因此,記載僧人飲食的資料不僅多而且很詳細具體。這些文書資料是瞭解敦煌地區僧尼宗教和社會生活的重要材料。如高啓安《唐五代敦煌僧人飲食戒律初探——以“不食肉戒”爲中心》(《敦煌佛教藝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趙紅、高啓安《唐五代時期敦煌僧人飲食概述》(《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下)》),這兩篇文章探討了敦煌僧人的飲食戒律和飲食文化。僧人由於受佛教儀軌、戒律以及傳統文化影響的原因,其飲食與世俗人有着很大的區别。因此,就飲食而言,僧人是區别於世俗人的不同群體,僧人的飲食分爲日常飲食、節日飲食和其他飲食活動三部分。敦煌僧人的日常飲食除了應當遵守的戒律外,和敦煌俗人相差不大,但在佛事節日期間僧人的飲食活動則更加豐富。在宗教節日活動中,寺院和僧人就是主辦者和主要參加者,活動和飲食也是形式多樣。敦煌僧人飲食作爲特殊的飲食者群體,和正規敦煌社會的飲食生活緊密相關,他們的飲食生活是構成敦煌人豐富的飲食生活的重要篇章。通過對敦煌僧人飲食特點的研究,可以使我們瞭解其日常生活、寺院的管理甚至一些佛教流行的特點、佛事活動的内容及狀況。
在敦煌飲食文化開發研究方面,高啓安《淺議敦煌飲食的開發》(《敦煌研究》2002年第6期)、李正宇《敦煌飲食文化研究開發的若干思考》(《敦煌研究》2002年6期)都探討了開發和利用敦煌飲食文化資源的問題。指出敦煌飲食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甘肅的寶貴文化遺産。敦煌飲食有著巨大開發價值,開發敦煌飲食,是振興甘肅經濟和西部大開發的迫切需要,是對敦煌文化的挖掘和繼承。敦煌飲食應當成爲敦煌文化産業化鏈條中重要的一環,成爲甘肅的名牌和視窗。開發敦煌飲食要在“文化”上做文章,珍惜和保護好“敦煌”的牌子。傳統飲食文化的開發必須堅持去僞存真、推陳出新的方針,必須符合現代人文精神,結合現代人的飲食習慣和文化心理,從原料、口味、製作方式、名稱、進餐形式等方面進行嘗試,形成地方飲食品牌。
2003年,高啓安《敦煌文獻中的“鬚麵”——我國最早的掛麵》(《揚州大學烹飪學報》2003年1期)指出學術界一般認爲成書於元代的《飲膳正要》中的掛麵是記載掛麵最早的文獻。但作者通過對敦煌文獻的梳理,認爲敦煌文獻記載了一種被稱作“鬚麵”的食物,它比《飲膳正要》的記載早了好幾百年,這應當是中國最早的掛麵。高啓安《敦煌飲食研究札記三題》(《蘭州商學院學報》2003年2期)指出敦煌文書中將釀造酒、醋、醬稱作“臥”,還將用油煎炸食品稱作“煮”。從文字學的角度,探討了這兩個字的本義及其演變過程,並利用敦煌文獻資料,糾正了學界對“點心”一詞的誤解。高啓安《唐五代敦煌的宴飲坐向和座次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003年2期)指出敦煌壁畫中有數十幅宴飲圖像,這些圖像不僅提供了宴飲場合、宴飲座制會食狀況、會食人數等信息,而且反映了當時宴飲的方位坐嚮、男女、座次等尊卑觀念。
2004年,高啓安繼續致力於敦煌飲食文化的研究,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先后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敦煌飲食探秘》和《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兩本專著。特别是《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一書,是他完成敦煌飲食文化研究博士學業的論著,也是他多年傾心飲食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多年來,他通過對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壁畫中大量的飲食資料全面、系統地整理,結合傳統史料中的飲食資料及現今河西、甘肅乃至整個西北地方的飲食現象,分别從食物原料、飲食結構、飲食加工具、食物品種和名稱,宴飲活動、宴飲坐具、坐姿、婚喪儀式飲食、飲酒習俗、僧人飲食以及飲食胡風等十個方面,探討了唐五代時期敦煌人飲食文化的方方面面,極大地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2005年,汪受寬《河西古酒考論》(《敦煌學輯刊》2005年2期)通過對史料記載和出土文獻的梳理考證,指出先秦漢初,河西就有造酒的傳統。漢唐時代河西美酒融合中外,品種多樣,品質上乘,被皇家官宦、文人騷客所贊賞。直至清代,酒泉酒還被譽爲天下一等名酒。本文較爲詳細地闡述了歷代河西諸種美酒的名稱,及其來歷傳説、製作工藝、口味特色等,是一篇較全面考論河西走廊酒業發展史的專題文章。李正宇《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聽飲酒——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5年3期)從酒戒鬆弛這一個特定角度著眼,揭示敦煌佛教的世俗化性質,爲敦煌佛教研究及中國佛教史研究推開一扇新的視窗,指出佛教雖重視酒戒,不允許僧尼飲酒,但8世紀後期至11世紀,敦煌僧尼普遍飲酒,而官府、僧司、民衆則對此視爲正常,無所非議,表明這一時期的敦煌佛教不禁飲酒。
2007年,安忠義、强生斌《河西漢簡中的穀物考》(《魯東大學學報》2007年4期)主要依據河西出土的漢簡資料,對漢簡中出現的穀物種屬做了考證和辨析,並説明它們在農史上的重要地位,既豐富了河西史的研究,也豐富中國農史的研究。河西漢簡中出現大量的穀物名稱,河西地區的考古中也發現了大量的穀物實物,這都是研究古代河西農業發展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重要資料。
2008年,安忠義《敦煌文獻中的酒器考》(《敦煌學輯刊》2008年2期)對敦煌文獻中所提到的三種酒器榼、曲卮與叵羅做了較爲詳細的考證。榼是一種中國傳統的盛酒器,而曲卮和叵羅都與唐代傳入中國的粟特金銀酒器有關,由於後世這些器物已經不多見,對於它們的形制有諸多誤解。高啓安《甘肅古代飲食名品拾遺》(《敦煌研究》2008年5期)指出甘肅地處絲路中段,歷史悠久,文化厚重,産生了許多聞名於華夏的菜肴和食物品種,這是地方的珍貴文化遺産。
三、 深入研究期(2010至今)
近年來,敦煌飲食文化的研究不斷拓展,把敦煌飲食文化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傳播及周邊的少數民族飲食文化結合起來,進行多元文化的深入探索。如高啓安《裕固族早期飲食文化研究——以〈肅鎮華夷志〉爲主》(《敦煌研究》2010年1期)指出《肅鎮華夷志》是裕固族重要的歷史資料,其中記載了不少與裕固族生産、生活有關的資料,這些資料,反映了裕固族早期飲食的狀況,是研究裕固族歷史和文化的重要史料。
2011年,趙小明《敦煌飲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2期)從道教辟谷與敦煌飲食文化、道教服食養生與敦煌飲食、道教節日、祈賽活動中的飲食等方面探討了道教對敦煌飲食文化的影響,揭示敦煌飲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高啓安《絲路名饌“駝蹄羹”雜考》(《西域研究》2011年3期)本文對絲路名肴“駝蹄羹”的來歷,名稱及烹飪方法進行了闡述。“駝蹄羹”,即以駱駝足掌爲原料烹飪的美食佳餚,出現於魏晋時,唐代以後逐漸被推崇,被認爲是上等肴饌而受到許多文人騷客的吟誦,元代被列入“八珍”。塞外駝蹄成爲中華知名肴饌,這也是絲綢之路飲食文化交融的結果。高啓安《唐五代時期敦煌的宴飲“賭射”——敦煌文獻P.3272卷“射羊”一詞小解》(《甘肅社會科學》2011年6期)指出敦煌文獻P.3272《丙寅年(公元966年)羊司付羊及羊皮曆狀》中的“射羖羊”一事,發生在正月期間歸義軍衙内宴會後一次賭射活動中,作爲賞賜利物的一隻山羊的支破記録。認爲敦煌人在較隆重的宴會期間也舉辦賭射活動,來娱樂慶祝。解梅《唐五代敦煌的胡酒》(《蘭臺世界》2011年24期)對胡酒的盛行之風、品種及傳入途徑進行了分析,唐五代敦煌作爲國際化的大都市之一,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尤其是胡人雲集、胡風盛行,其中頗具代表的胡酒不僅豐富了當時敦煌的酒類品目,還成爲東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證。
2012年,俞曉紅《敦煌變文〈茶酒論〉校注商補》(《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1期)本文對《敦煌變文校注》《敦煌變文選注》等對《茶酒論》所作的校理疏釋中,存在一些問題提出了看法,就其中的35則校釋提出商補性意見。高國藩《唐宋時期敦煌地區商業酒文化考述》(《藝術百家》2012年3期)對盛唐至宋初敦煌酒文化的市場化進行了分析,特别對吐蕃奴隸主統治下酒文化的特殊性做了側重的分析。文章認爲奴隸制時期的敦煌酒文化是停滯的,只有民族英雄張議潮結束吐蕃佔領以後,敦煌商業酒文化才得以恢復發展並繁榮起來。高啓安《唐人宴飲程序概觀——以〈遊仙窟〉爲中心》(《形象史學研究》2012年1期)指出由於史料的缺乏和記載材料較少,我們對長期以來古代宴飲程式、主客位置、上食先後、飲酒過程等,没有系統的研究。著名的唐代傳奇小説《遊仙窟》小説以十娘迎接、招待張生進而成就兩人愛情的故事爲綫索,却以大段的文字描述了唐代宴會的概貌,反映了古代的宴飲位置、尊卑坐向、宴飲程式等,使我們對唐代宴飲活動有了一個較全面的瞭解。
2013年,高啓安《“羖羊”及敦煌羊隻飼牧方式論考》(《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3年2期)指出羖羊是敦煌乳品的主要提供者,“羖”即家山羊。羖羊肉味鮮美,也受到古代敦煌人的喜愛,是敦煌人主要吃的肉食品之一。敦煌文獻也寫作“骨力”。羖羊在羊群中不僅起領頭作用,也爲牧人提供乳品,敦煌牧業經濟中,“羖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僧海霞《唐宋時期敦煌地區藥酒基酒考》(《中醫雜志》2013年2期)對唐宋時期敦煌地區藥酒配方進行了梳理,認爲對這些方劑的系統分析,可以見證唐宋時期藥酒發展狀況,以引起民衆對敦煌醫藥文獻及民族特色文化的關注,從而促進民族醫藥事業的發展。僧海霞《唐宋時期敦煌地區藥用醋考》(《中醫雜志》2013年14期)指出唐宋時期的敦煌地區,醋的品類衆多,名稱各異,其中麥醋是藥用醋的主流。文章認爲醋在古醫方中臨床應用很普遍,醫方中使用的各種稱謂,是不同歷史時期或者同一歷史時期的不同習慣表述。其中部分名稱已超出南北朝時期醋所界定的概念範圍,個别名稱被後世誤判,是因爲它自身的佚失及其在實踐中被廣泛取代等因素。
2014年,高啓安《吐魯番出土“草編粽子”名實辨考》(《吐魯番學研究》2014年1期)對吐魯番出土的“草編粽子”這一名物進行了考證,對學術界定名的“草編粽子”給予否定,提出了新的觀點。日本大谷探險隊曾於吐魯番古墓葬中採集到一件連綴的草編物,有學者稱之爲“粽子”,並以此作爲西州出産稻米之證據。作者認爲此物並不是所謂的粽子,其淵源應爲香囊,是香囊文化在西州傳播的見證。它只是農家所編的一件小飾品,或懸掛於家中,或佩飾於兒童,已經不具備香囊的功能,更不能把它當作爲“粽子”。僧海霞《唐宋時期敦煌醫用粥探析》(《中醫雜志》2014年12期)指出粥自古以來都是人們生活中最常見的食品。中國古代食粥這一特色飲食文化,至唐宋時期達到空前興盛,其具體應用及使用特色在敦煌遺書中有所體現。敦煌遺書中所載諸多醫用粥,分别以原料、濃度、顔色、温度、味道等不同因素爲選取標準,具體應用於服藥、養生、助藥力、助胃氣、療疾及病中調護和初愈調養中,其所體現出的辨證思想至今仍可借鑒。2015年,高啓安《中國古代的水煮方便食品: 棋子麵與掛麵》(《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1期)依據敦煌文獻和其它史料,對中國古代的水煮方便食品棋子麵與掛麵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並對這兩種食品的名稱、形狀及製作烹飪方法、發展傳承等作了較全面的介紹。
在敦煌飲食文化研究人物述評方面,王祥偉《高啓安先生與敦煌學研究》(《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3期)、馮培紅《高啓安與絲綢之路飲食文化研究》(《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3期)、何宏《高啓安與〈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南寧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均是對高啓安先生在敦煌飲食文化研究中取得的成果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指出高啓安先生的治學之路最初是從敦煌文獻入手,專攻敦煌飲食文化研究。他的博士學位論文曾獲得蘭州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其研究課題獲得了國家文物局、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的資助,爲敦煌學研究開闢了一塊新的領域。此後,其飲食文化研究範圍逐步拓展至絲綢之路中國段,是國内在此領域研究中貢獻突出的學者之一。
陳静《敦煌寫本〈茶酒論〉新考》(《敦煌研究》2015年6期)指出敦煌寫本《茶酒論》應爲七個寫本,並不是學術界一直認爲的六個。其中四個寫本抄有作者姓名,但作者姓名的寫法不一致。結合唐代茶文化發展狀況,可以推斷《茶酒論》的創作時間約爲800—805年之間。從傳寫特徵看,《茶酒論》寫本是民間一些有文化的底層人士,出於個人喜愛,隨手抄寫,留爲自用的。解梅《唐五代敦煌酒具考略》(《蘭臺世界》2015年33期)指出飲酒之風濃郁是唐五代宋初敦煌飲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飲酒離不開酒具,作爲酒文化載體的酒具成了當時人們日常的必備用具。敦煌文書中所提及的酒具名目繁多、形制多樣。
2016年,高啓安《嘉峪關魏晋墓壁畫四炊具圖像名物研究》(《第二届中國古村鎮保護與利用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年)依據嘉峪關魏晋墓壁畫,結合墓葬出土文物以及同時期出土的明器陶灶(鬼灶)上諸多炊具、餐飲具乃至附屬用具模印圖像,考證了古代河西地區人們的飲食結構、飲食風俗和飲食概況。文章指出體現飲食製作乃至飲食文化特色的,不光是特殊原料、烹飪方式和美味的飲食品種,那些有别於他處的飲食製作過程,有時也顯現在不起眼的炊具以及附屬器具上。高啓安《漢魏“鬼灶”上一器名物考索》(《形象史學研究》2016年1期)指出墓葬出土之“鬼灶”是研究漢魏時期飲食文化的主要形象資料。文章從灶面上的炊具、餐飲具及出土區域、器形、時代特點等方面進行了論證。安忠義《敦煌文獻中幾種食器考辨》(《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6年3期)對敦煌文獻中所提到的四種食器牙盤、樏子、楪子與槐子做了較爲詳細的考證。文章認爲牙盤是寺廟中用來盛放佛前供品的器具,因盤底有足而得名;樏子是一種中間有許多隔檔的盤子或盒子,即明清以來的攢盒,今天的全盒;槐子是一種帶柄羹斗,長柄大頭;楪子即是今天使用的餐具碟子。
2017年,高啓安《“髓餅”來歷及流變》(《吐魯番學研究》2017年2期)本文探討了“髓餅”原料添加方式、烤制用爐以及添加糖蜜、早先流行於北方等因素,由此可以判定髓餅與胡餅、蒸餅等,均爲漢代傳入中國的一味外來食物。高啓安《胡瓶傳入和唐人注酒方式的改變》(《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1輯,2017年)指出“胡瓶”是一種特殊的盛容器,因其形制從西亞、中亞傳來,所以中原人給它起了一個反映傳入地、流行地和使用者民族屬性的名字“胡瓶”。因胡瓶的傳入,唐人的飲酒和注酒方式發生了變化。可見,胡瓶是中西飲食文化交流的一個明顯例證,飲食器的交流也是東西飲食文化交流中重要的體現。穆瑞明、曾維加《佛教和道教的“厨經”研究》(《宗教學研究》2017年2期)指出佛教和道教均有厨經,佛教有敦煌寫經《佛説三厨經》《佛説停厨經》以及在敦煌寫經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高野山寫經《佛説三停厨經》,道教有《老子説五厨經》。雖然天厨思想在中國、印度都可追溯各自的源頭,但就這些厨經的内容和結構來看,道教的厨經邏輯順暢,而佛教的厨經却問題較多。文章通過比較佛道兩教的厨經,研究天厨思想的内涵、佛道厨經的同異之處以及佛道厨經的具體方法,最後總結出厨會傳統演化的社會學景象。
2018年,高啓安《絲綢之路上傳來的酒中奇葩——“羊羔酒”再申》(《晋陽學刊》2018年6期)指出“羊羔酒”是將動物脂肪原料釀入酒糟後發酵的一種酒,其最早流行於西方可薩人當中,後傳入中國,與中華傳統釀酒方式融合釀造而成。“羊羔酒”傳入内地的時間爲唐代,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原的佳釀之一,在古代一直深受飲酒人士的歡迎。這與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有關係,因此而成爲宋代宫廷法酒之一。直到清代,雍正皇帝仍對此酒贊不絶口,並指定爲進貢的美酒佳釀。余力《轟動世界的敦煌飲食文化》(《甘肅農業》2018年18期)指出敦煌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外來文化因素的影響,敦煌飲食也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古代敦煌人的食物原料以農業、牧業産品爲主,以一定的採集、狩獵食品爲補充,是較爲完善的食物結構體系。
總之,敦煌飲食文化研究是舉世矚目的敦煌學領域裏拓展出的一條新的課題方向。敦煌飲食文化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多年來其研究領域的學者們孜孜不倦、刻苦鑽研,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對敦煌飲食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探索,不僅推動了敦煌學研究的發展,也將極大推動中國古代飲食文化研究的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