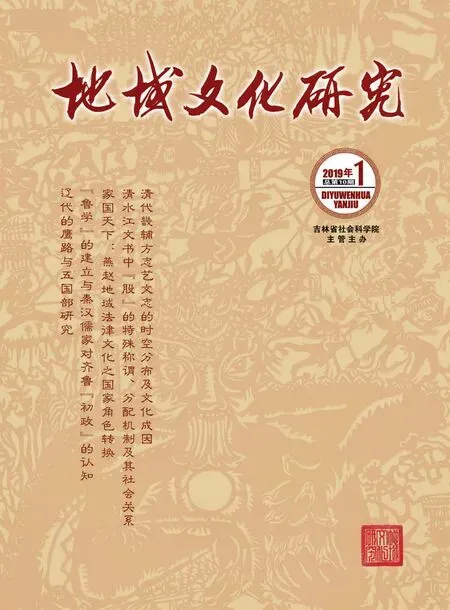“鲁学”的建立与秦汉儒家对齐鲁“初政”的认知
张沛林
《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①(东汉)班固:《汉书》卷88《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618页。
“鲁学”“齐学”及《公羊》为“齐学”与《谷梁》本“鲁学”的称法即源于此。《汉书》中的这一段话,除在学史上提供了两个名词以及概念外,其蕴含的历史及当时人的观念讯息也是十分丰富的。
首先,汉宣帝初即位时,距汉高祖刘邦建国已有一百余年的时间,“齐”与“鲁”这两个西周初开始存在的诸侯国早已灭亡。虽然,在西汉也曾多次有同名的诸侯国设置,但其辖区频繁变更,已和两周齐、鲁旧国地域的范围大不相同了。大抵“齐”“鲁”在西汉中期只作为地域名存在,这里的“鲁学”“齐学”是一例,又如《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往往直接表明经师是“齐人”或“鲁人”。可以说在西汉中期的人心中,“齐”“鲁”仍然可以算作界限清晰。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文中“宜兴”一词最值得关注。“宜兴”的原因绝不是谷梁子与韦贤等同为“鲁人”,也不完全是皇帝有所私心或偏好,而群臣附和。因为这两点原因都不够“冠冕堂皇”,不可以对严肃的政治与当时和政治有极大关联的经学给予合理交代,只可能是他们口中的“鲁学”在某些方面较“齐学”有真正的“优势”,才可以成为“宜兴”的理由。为说明这种“优势”的必要性,这里权做一个简单假设:孔子是鲁人。孔子的学说在鲁地发源,孔子的弟子也多为鲁人。任凭“齐学”先师在当时有多么高的权威,如果“鲁”地有孔子最纯正的学问,“鲁学”是得到至圣孔子的真传,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那么“齐学”也必须让“鲁学”一头。“宜兴鲁学”才能正式成为一个可议的官方议题,随之才能以皇帝的旨意使《谷梁》成为官学。该“假设”并无佐证,但可以显示“鲁学”的“宜兴”,也就是其较“齐学”的“优势”,必须有在群体中高于个别权利的学理支持。
以上就《汉书·儒林传》中这一段重要记载的两点“言外之意”作了初步的论述。而今日读者如果对西汉政治及经学有一定了解,在阅读这一段话时,并不需经过深入的思考便可以意识到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这样的论述似乎同于“鸡肋”,但其关涉到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根本问题。问题的提出就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假如在春秋、战国时,齐、鲁二国尚在,如果谈两国学术,毕竟可依据当时存在的国家或当时国内的学者划分。而西汉中期时谈“齐学”与“鲁学”,空间、时间的凭据已减弱,学问也随几代学者的探求发生转变。且韦贤所指的“鲁学”,并非是单纯的地域学术概念,已经转换为孔子之后“《春秋》学”或“经学”上的概念。①“齐学”“鲁学”或可移为《诗经》学上的《齐诗》《鲁诗》,但就《儒林传》中语,韦贤等人的话专就“春秋学”提出。时间与地域都不再完全适用,“鲁学”的提出实在使人生疑。
根据上面的怀疑,需要探究的重要问题可以概括为:韦贤等人对“齐学”“鲁学”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如何认识的,其区别两者是当以“齐”“鲁”地域划分?还是以学风和释经方法划分?还是以《公羊传》及《谷梁传》中具体不同的观点学说划分?或者可以说是韦贤等人在鲁国灭亡、地域变更的情况下是如何建构“鲁学”的,“鲁学”与“齐学”是否在西汉中期时真的可以成立?
一
韦贤等人是否就“齐学”“鲁学”有相对具体的认识,因文献缺乏,我们已经不能了解当事人的具体说法。但就其当时情形,他们对两个概念的提出,是为治国当以“王霸杂之”的汉宣帝,情感上突然对并不太看好而又需利用的“经学”产生的一些可贵倾向提供依据。这也体现了历史的“或然性”:假如卫太子不曾好《谷梁》,假如当时《谷梁》传习者依然同先师申公一样言论不得皇帝之心,同先师瑕丘江公一样口讷败给董仲舒,两个概念的提出及汉中后期《谷梁》学兴盛一时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存在。
但“无中生有”对任何人,尤其对身为政治家和学者是较难的事情,重要观念尤其是使某些方面历史轨迹有所改变的观念一定有其学理上的基础。即便这些概念是如今人常说的固化的片面的“贴标签”,其“不准确”也是概念的某些方面不可以和事实相符合,但不准确的“标签”一定是根据某些与事实相合的方面而“贴”出的。讨论“鲁学”“齐学”,就是要找到这些与历史相合之处。
作为相对的概念,“差异”应最先讨论。两个“学”的不同,从两个“名词”上看,关键在于“齐”与“鲁”的差异。作为单纯的地域来谈,其差别明显。虽同在东方,“齐”临海而“鲁”为内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空间的差异也许会对民风、民俗产生影响。这方面区别,学者们从考古、历史、民俗与人类学等诸多方面已有充分研究。这里仅就为后来史家及学者眼中关注的“齐”“鲁”,也就是经过人为“改造”或“重构”后的“齐”“鲁”再做一些考述。首先来看齐国: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①(汉)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85页。
又,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②(汉)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20页。
以上两段,司马迁以不多的语言,将齐国建国时姜太公治国的政策及在西汉初他亲身到齐国体验的感受作了陈述。太公的“因其俗”与司马迁体察到的“其天性也”形成了互证,清楚地表明了齐国的“俗”在周初至汉初近八百年中基本未有大的改变。但太公“修政”不是无作为,“简其礼”表现了周人的制度在有些方面还是在齐地推行开来。只是作为推测来谈,“礼”不施于庶人,这些制度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的改变,以适用于行政的要求及齐国国政与周的对接。在社会进程发展较迟缓的时代,八百年而在下的民氓还是保持着“天性”则完全有可能。而司马迁的亲身印证,体现出他“实践史学”,应为“实录”。
有趣的是,司马迁在《鲁周公世家》中将“齐太公”和“鲁伯禽”做了个对比: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③(汉)司马迁:《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35页。
《史记》中的这一段,作为齐、鲁“初政”与对后来齐鲁文化特征的重要证据,近代以来学者多有引述,已属“老生常谈”。其中文字是司马迁根据古史籍“转译”,或是据传说书写,周公三人的语言明显不同于《尚书》中一些篇目的佶屈聱牙与周初青铜器上铭文的简古。非当事者原话,基本可以确定。而对史料中具体情境与人物对话可靠性的怀疑,并不影响对该事的大致情况与在历史中的真实性。从日后齐、鲁的文化名人及风格,如“齐谐”“稷下”、孔子以及汉高祖灭项羽后“独鲁不下”等情况,“初政”内容对国民性格、操守以及文化诸多方面确有巨大影响,是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初政”的不存在。“初政”也是讨论“齐学”“鲁学”在孔子之前最为重要的文化“基因”。而更为重要的是,不论在司马迁的眼中,还是《史记》中的“周公”,他们将“齐”“鲁”的未来发展都系在了这个“初政”上,也就是系在“初政”的执行者齐太公与鲁伯禽身上。
作为先秦及汉初观念上的“学”,多半是讨论如何治理国家的。诸子学说的分野,也常是因对治国不同观点产生的分歧。或许“名家”“阴阳家”等将一部分关注点放在了事物的名称与性质上,但可以断定,诸子学大多数是针对或指向政治之学的,“如何治国”是“学”的核心。而我们要讨论的“齐学”与“鲁学”虽是在“学”的观念上已有转变,也就是由儒家转入经师,“政治之学”转入“经典之学”的时期提出的,但其“学”的前提毕竟是“齐”“鲁”,“初政”是一个重要来源。在文献中,也就是在史籍书写者及观念提出者对历史的回顾与重新构建中,我们讨论的“齐学”与“鲁学”,要从考察学者对“初政”差别及齐太公、鲁伯禽差别入手。因为对同一历史状况,人们的思想有所不同,文献书写者的态度和文献中对人物及事例的书写会有所转变。史学家重视的是实录,而儒者经师重视的是信仰。
《说苑·政理》: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①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9页。
上引《说苑》中这一段明显与前引《史记》中一段所说是同一件事,而观点却完全相反。抛却这段话的时间性、书写者与《史记》中相关内容做一个对比,②应说明的是,《说苑》是西汉末刘向所编辑的,刘中垒向来以博闻见称,其编纂书籍材料来源自皇家及群臣藏书,但终究难以确定某一则的来源。观其编纂的《战国策》等书,所述与历史多有乖违,其虽然为“文献学之祖”,但处理某部文献的方式我们也不能确定。同样,我们并不能知道刘中垒在编纂这段话中有没有改写,其反映是谁的观念不可知,但大体是儒家的。其重点在周公对太公、伯禽的评价。首先《史记》中相对简略,对于“治国”的优劣,周公肯定了太公的“简易”③裴骃《史记集解》载有两种不同的本子:徐广曰:“一本云‘政不简不行,不行不乐,不乐则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简不易;有近乎简易,民必归之’。”但两本大义都相近。,而对未来的预测是鲁必然居于齐下,或可以说鲁当为齐臣属。而《说苑》所载的恰恰相反,首先,对“治国”优劣的评价者变成了文献的书写或改编者,他(们)认为,齐不如鲁,太公不如伯禽,差别在于“王者”还是“霸者”,而文中的周公只是做了对未来的预测。
《史记·齐太公世家》:“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就在这第五世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而“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齐国的确乱了。鲁国虽中间有魏公弒幽公,但十世懿公为武公少子,为周宣王所喜爱而命为太子,即位后被其兄括的儿子伯御所杀,周宣王杀伯御而立孝公。司马迁对宣王的悖礼与鲁乱的后果用一句话作结:“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对照史籍记载,《说苑》中周公的“预言”是惊人的准确。
很明显,《说苑》中的一段话是被修改过。而修改者应为刘向之前的儒家学者。对比《史记》,齐国与鲁国的“初政”优劣得到了逆转,并通过周公的“预言”对齐、鲁的国史给予佐证。儒家经师是青睐鲁国的“初政”的,对这种“王道”初政的认同,促使他们修改史料。推至“鲁学”与“齐学”,在儒家看来,“鲁”在其“基因”中自有优越之处。
二
儒家经师对比齐、鲁的“初政”,自然伯禽为优。那么鲁国“初政”的执行者伯禽在汉儒心中,尤其是在没有同齐太公对比时的确切评价,则体现了“鲁”与“鲁文化”在汉儒心中较为准确的定位。
中国古代学者对于自己推崇的先贤,往往进行“神圣化”的塑造,赋予“预言”能力便是其中一种方式。对比《史记》《说苑》两则材料,《说苑》中的周公是“神化”了的。而《史记》中的周公并不可以说是“神”,只是作为一个出色且有预见性的政治家出现。①在这里,不能说《史记》便是丝毫不差的实录,这与前面提到司马迁写齐国风俗为实录不同,它是具体的人物对话,来源于传说或古代文献,无法进行实践验证。
书写者及改编者的目的各不相同。《说苑》神化周公是借其口评述“齐”“鲁”优劣。而还有一种是将文献中“对手”双方都“神化”的处理,如文献中有关于对周公和齐太公齐鲁政治优劣的对话:
《吕氏春秋·长见篇》: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②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55页。
这则材料还见于《淮南子·齐俗训》《韩诗外传》《汉书·地理志》等古籍中。文字虽异,大旨相同,这里不再引列原文。综合上面《说苑》《史记》的材料,可以看出“齐”“鲁”的“初政”问题在战国、秦汉之际讨论较为普遍。《吕览》周公、齐太公皆被神化:太公以为“鲁削”与周公以为“齐非吕氏”,预言都十分准确。文献中二者似乎“势均力敌”,周公稍稍胜出。而其想表达的是治国“尊贤上功”与“亲亲上恩”之异,亦应出自儒家手笔。此段情况与《说苑》相似,这里不为论述“齐”“鲁”,是为引出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否所有人皆可被当作圣贤而“神化”,伯禽是否具备这个资格。
在《说苑》中周公被神化,在《吕览》中周公、太公望都被神化,因在历史上他们都为王佐之才,所以在传说中有被“神化”的资格。只是有资格的人中谁需要被“神话”由文献书写者决定。老子可以“化胡”,孔子是“儒童菩萨”。不论出于什么目的,“资格”必须具备,而小小的人物或许在后世文献中能飞上云端作仙人,却不能作“全知”高等的神。
伯禽作为鲁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人物,鲁国的“初政”由其完成,鲁国民风、民俗甚至“鲁学”都和他脱不掉关系,他有被神话的资格吗?从文献中看,这类情况几乎没有,而夸赞的情况是存在的。
《毛诗·駉小序》:《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垧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③阮元等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08页。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举兵欲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鲁好义而民戴之,好义者安,见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④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7页。
《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子思曰:“可。”公曰:“为之奈何?”对曰:“茍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
兴也勃矣。”①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5页。
以上三则材料,或是赞鲁僖公学伯禽,或以周公、伯禽并称,或独赞伯禽,都是夸赞的实例,但至于“神化”的形象则没有。而文献中存在大量的周公“教训”伯禽的内容:
《史记·鲁周公世家》: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②(汉)司马迁:《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85页。
《韩诗外传》卷三: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衣成则必缺纴,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措,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诫之哉!其无以鲁国骄士也。”③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7-118页。
《韩诗外传》及《史记》中这两段恰与前引《史记》《说苑》的情况相近,都是讲同一件事而内容有差异。不同的是,《韩诗外传》出现应在《史记》之前。那么《史记》没有采信《韩诗外传》中周公自“吾闻德行宽裕”至“诫之哉”的一大段话,有可能两者都有相近的史料来源,《韩诗外传》有所增添,也有可能是司马迁删去,这里不做讨论。但《史记》所不取的一段确实“夸张”,引《诗》谈《易》大似东周儒士。不论语言的多寡,两段话都没有丰富伯禽的形象,文献的书写者意图或在记周公的思想,或借周公之口说话,伯禽的用途只是叫周公论道不“自言自语”而已。伯禽被“教训”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文献中可长可短。短者如《吕览》中一语,④《吕氏春秋·贵公》:“伯禽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非受周公“教训”的如《说苑》中有成王教训伯禽⑤《说苑·君道》:“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撙节安静以籍之。谏者勿振以威,勿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伯禽总是一个淡化了形象的被“教训”者。
孟子谈“圣人”,在伯禽之前有伯夷、伊尹,在其后有柳下惠。相较于这些人,其事迹确实不显。伯禽绝非乏善可陈,他的鲁国“初政”是将宗周礼乐文化在东方推广开来,在后世儒家眼中有大功劳。但伯禽是执行者而非创制者,他时常被“教训”而或恭敬地执行,没有“神化”的资格也没有“神化”的必要。假如文献中对伯禽有了形象的描述,那么也是为了在对比中完成抬高他父亲周公的目的。
《荀子·尧问》:伯禽将归于鲁,周公谓伯禽之傅曰:“汝将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对曰:“其为人宽,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周公曰:“呜呼!以人恶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彼其宽也,出无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窭小也。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彼争者均者之气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浅也。闻之曰:‘无越踰不见士。’见士问曰:‘无乃不察乎?’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彼浅者,贱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语女: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吾于天下不贱矣;然而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之士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者千有余人,于是吾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于十人与三十人中,乃在百人与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为之貌,下士吾厚为之貌,人人皆以我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后见物,见物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鲁国骄人,几矣!夫仰禄之士犹可骄也,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①王先谦:《荀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47-651页。
《荀子》中这一段话较长,大部分还是周公的言语。与前引《韩诗外传》《史记》状况不同:伯禽虽并未出场,但终于有了“为人宽,好自用,以慎”的形象。但随之便得到了周公的否定。伯禽的三个在常人眼中的“美德”,引起周公感叹:“以人恶为美德乎?”这一句如何解读,以前的释读者或认为很简单,不予说明。或认为“恶”是名词,整句当理解为“把人坏的地方当作美德”,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从整段话可以看出,伯禽的三个“美德”及周公所说的都是针对治民、取士的问题,而非泛泛地谈治国。何况这三个“美德”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恶”的。这里的“以人”是用人之义,如《荀子·大略篇》:“上臣事君以人”。而“恶”是疑问代词,如《荀子·礼论篇》:“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整句话当理解为:“(为人宽、好自用、以慎三点)在用人上哪里是美德啊”。这句话作为一段的转折,伯禽的“美德”与周公见识又形成对比。如文中的周公是以“道”德人的,对待士人也是灵活的采取不同态度。相比周公“两边不住”的“中道”“中庸”,伯禽的“美德”也偏向了一边,不那么完善灵活。
前贤的“神”与“圣”,也同样遵循着“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原则,伯禽文献中的形象在与周公对比中得到了体现:伯禽并未理解透彻作为圣人的父亲的“教训”,而保守谨慎地在鲁国推行着“宗周文明”。最明显的例子,在《汉书·古今人表》,《表》将人分九品,周公列在上上圣人,师尚父在上中仁人,而伯禽竟在第五等中中。与其一品的历史名人还有齐桓公②管仲在上中仁人,对比下见班固对齐桓公功绩的归属意见。、吕不韦等,明显可以看出在汉儒心中对伯禽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普通人。
三
伯禽是鲁文化形成中关键的人物,上文主要谈西汉人对他形象的认识。而更为关键的是孔子对鲁的看法。《论语·雍也》: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先贤多以为孔子就时事而言,如包咸注:“言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贤,周公圣人,今其政教虽衰,若有明君兴之,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其中虽谈到周公、齐太公差别,但却一律肯定。
《论语集注》: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程子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孰不以为齐胜鲁也,然鲁犹存周公之法制。齐由桓公之霸,为从简尚功之治,太公之遗法变易尽矣,故一变乃能至鲁。鲁则修举废坠而已,一变则至于先王之道也。”①(南宋)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0页。
朱子注并引程子说,稍稍进了一步:对齐太公的态度,从儒家角度稍有贬损,更强调了“初政”的差别。也就是对《论语》中这一句话的解读,从圣贤的差别,转变为王政与霸政的差别。问题在于,时事与初政在这句话中,到底分别有多重的比例?《论语·八佾篇》所说的“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这恐怕也并非一变即为“道”的鲁政现实。而《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子路》: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参考《论语》中以上二语,更可以得出,孔子对某国政治的评价,虽不能说一点也不顾及现实,但“探源”的意思是较多的。孔子说齐桓公“仁”,说“齐桓公正而不谲”,鲁僖公虽然是“作颂贤君”,但依然不可以与齐桓相比,怎么可以说春秋时是“齐一变至于鲁”。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中,当是“初政”的因素较多,太公“简政”一变为伯禽之政,伯禽一变或能至于周公的“郁郁乎文哉”。结合前面所引战国至西汉的文献,伯禽不能与周公相比,“鲁”的“初政”与周政相比打了折扣,孔子的话也是重要的印证。同样实行周政,伯禽还是和周公有差异的,孔子或有意或无意,也参与进这种对历史及文化形象的构建中。
历史中真实的状况无法完全复原,但在文献中,伯禽的“形象”及其“初政”给鲁人在秦汉时期人心中留的印象也可以通过文献反映出来。在讨论这个问题前,需要强调的是个体虽然接受着周围文化环境的浸染,但还是有差异的。说齐国人都还保持着天性,但也应有纯谨之人,如荀子弟子浮丘伯。与荀子的其他两位著名弟子李斯与韩非,对此浮丘伯学《诗》是多么“不通达”,其所传《诗》学日后还被称为“鲁诗”。鲁国也并非无狂肆之人,如孔子的老友原壤,《论语》中载其箕踞等待孔子,《礼记》载其母死而敲椁木而歌,简直“大逆不道”。但只要不针对个体,文献书写者便总喜欢归类:
《史记·扁鹊列传》: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②(汉)司马迁:《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361页。
上引《扁鹊列传》的记载是对事实的绝对化,风俗、习惯的特点即成为地域整体人物的特点。诸子书中常将一类性格归到一国人的头上,如“齐人有一妻一妾”,宋人“守株待兔”“揠苗助长”而郑人“买椟还珠”,或荒唐或愚蠢。但在不同学派学者眼中,则有不同的看法:
《韩非子·说林上》: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徒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髪。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①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01页。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少者侍长者饮,长者饮亦自饮也。一曰。鲁人有自喜者,见长年饮酒不能釂则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见长者饮无余,非斟酒饮也而欲尽之。②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16页。
儒家眼中鲁人的“规矩”,在韩非子看来,则稍为愚蠢,不知世事,不懂变通。而史家纪实,如《史记·货殖列传》:“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徧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③(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50页。又“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游侠列传》:“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④(汉)司马迁:《史记》卷124《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40页。则记载鲁人虽有一些观念上的转变,但始终应是学文学、以儒教的。而有时“鲁人”的出场,也表达了一些态度,从而也反映了“鲁人”在史家眼中的形象。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则可以是以半虚构的形象出现,如《史记·吴起列传》中的“鲁人或恶吴起”,《史记·叔孙通列传》中的“鲁有两生不肯行”。
上文就“齐、鲁初政及其在文献中的评价”“文献中伯禽形象”及“周季与秦汉文献中鲁人特点”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较准确的还原“鲁文化”在西汉儒者心中的定位,从而说明“鲁学”在他们心中的位置。综合来说,通过对《说苑》等文献的分析,伯禽在汉儒心目中的定位得以初步的还原,鲁国的“初政”是严格依照周礼推行的,文献中伯禽的形象又被战国、西汉儒家塑造成谨慎且稍显教条的。伯禽虽远不及吕尚,其“初政”也未达到周公治下的高度,但其行“王道”毕竟比行“霸道”优越,“鲁”高于“齐”就是在这个方面”,但也并非尽善尽美。
而上文曾就孔子在两概念提出中的影响做过一个猜测,但无论如何,说《公羊》是“齐学”则代表其不是纯正孔子之学,在当时都会引起反感。况且“齐”与“鲁”并提比较,从上文征引的文献看,秦汉人有较固定的问题意识,便是“初政”及其后来影响。
还原了西汉儒家心中“鲁”的位置,再来看韦贤等人所谓的“鲁学”。
《汉书·儒林传》: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⑤(东汉)班固:《汉书》卷88《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618页。
从上引《儒林传》事可见,所谓“鲁学”压过“齐学”而能大兴,还要靠在具体的“经义”论辩中取胜。但这只作为“程序”,“宜兴鲁学”恐怕是作为“鲁人”的私意,作为迎合宣帝的意旨,而结合西汉人心中“鲁”与“齐”对比中的优越,而为达到兴起《谷梁》的一个借口。如同当时汉武帝选择《公羊》一样。或许韦贤等人以更近“王道”的“鲁学”劝谏“霸王杂之”的汉宣帝,但无论目的如何,“齐学”“鲁学”在韦贤等人那里,算得上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概念。
四
以上考量了秦汉儒家对齐、鲁“初政”及伯禽的认识与建构,可以说这是战国、秦汉人的固有话题,韦贤等对“齐”“鲁”优劣认识在“初政”上是较为清晰的。就此前“齐”“鲁”的对比常在“初政”上,而经学上韦贤等是首次提出,移置《公》《穀》二传说法比较含混。那么为什么“齐学”“鲁学”是建立在这种固有“王”“霸”之分的认识上,而不是在西汉中期“齐学”“鲁学”本来就因地域有界限清晰的区别呢?也就是“鲁学”与“齐学”是否能在西汉中期实际的学术环境中得以成立。
蒙文通先生以为“鲁学谨严,齐学驳杂”,“齐学之党为杂取异义,鲁学之党为笃守师传”,“就汉世言之,则鲁学谨笃,齐学恢宏,风尚各殊者,正以鲁固儒学之正宗,而齐乃诸子所萃聚”。①详见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4-85页。蒙先生将“齐学”“鲁学”说的泾渭分明,其方法则是抓住史料中一二语或一两例扩充到全体。如刘歆有“义各相反”一语,蒙先生则以为“《公羊》与《谷梁》反异”云云。作为不同著作,其“反异”是正常的。按今《公》《穀》传文,其相同者也很多,如何定义这种“反异”?又如《汉书》载申公以训诂教《鲁诗》,最为近真,而辕固生及韩生采杂说,以此则知“鲁学谨严,齐学驳杂”,则是从一个例推广到全体。
蒙先生的方法是先接受了“齐学”“鲁学”两个概念,然后向其中填充内容,这种方法的错误在于先成立“概念”再套用“实际”。上文引《史记》并谈到,两国“初政”对两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两国民风有所不同。
《管子·大匡》:“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粮,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②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1页。
《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③(东汉)班固:《汉书》卷51《贾邹枚陆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53页。
如上,从一些文献中确实反映出战国秦汉时不同地域人的性格不同。鲁人较保守,齐人则较开通。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假若曲解狂、狷的意思,正好可以拿来比喻“齐”“鲁”人的性格。且上文也曾引及《扁鹊列传》,证明各地爱好不同,如今人常谈湘、川人爱吃辣,而东南爱吃甜,都属这类。是将地域的大众喜好,或大多数人风俗及文化、性格在语言及文献上表达的绝对化。对于风俗,虽然一定有特例,但泛言无妨。可是因为学者数量是有限的,且分类要求严格,对学派的归类是应避免这种浮泛的方法。学派中的所有学者都应在主要学说或方法上相同相近才能定为一类,其余若师承、地域等方面都难以作为统一标准,何况西汉经学,前后变化巨大,考量“齐学”“鲁学”应当是严格的。
首先就所谓“齐学”“鲁学”的代表看:
《史记·儒林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①(汉)司马迁:《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66页。
申公作为《鲁诗》《谷梁春秋》学史上较关键的人物,忽略司马迁特意提及的“老”字,②这里的“老”字或是马迁有意书写的,因年老可使人沉稳。其性格确实同于鲁人性格。以一语谈力行治国,与所谓“齐学”代表董仲舒动辄千言的《三策》是有所不同。《鲁诗》则纯以训诂传,无《传》。察《汉书·艺文志》,数家独《鲁诗》无《鲁传》。申公的学问,确实像蒙文通先生说的那样谨笃。
但在西汉中期,也就是汉宣帝即位前后一段时间,是学术变化的关键时期,学问风气与汉初又大不相同。就“鲁学”一词的提出者们看:史高史料寡少。韦贤虽位至丞相,《汉书》特为立传,但只是交代其为瑕丘江公弟子,为“邹鲁大儒”。可能是因为政治成就较高,对其学术少有谈及。有据可依的是夏侯胜,《汉书·夏侯胜传》:“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灾异事暂且不谈,这里只看《尚书》学。西汉《尚书》多源自伏生,伏生传张生,张生传夏侯始昌,夏侯胜的《尚书》学若归类当属“齐学”。而蒙文通先生则以为大小夏侯《尚书》为“鲁学”。小夏侯是夏侯建,《汉书》载其“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则又属蒙先生所说“齐学之党为杂取异义”类。如此看,“鲁学”的代表学者有完全符合条件,如申公。有的竟符合“齐学”特点,如大小夏侯,可见蒙先生的分类与实际情况的矛盾。
再就时代学风的变异,也就是“灾异学”看:
《汉书·眭弘传》: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③(东汉)班固:《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153-3154页。
上引《汉书》眭孟被杀一事,《五行志》等亦有记载。一方面眭孟的确迂腐,不知执政者的底线。两个迂腐儒生凑在一起上书,且是卑微的学者,并非权臣,竟然想让皇帝“禅让”。何况眭孟所说的“先师董仲舒”,就曾因言“灾异”而被汉武帝下狱“警告”。眭孟犹不以先生为前车之鉴,这恐怕并非偶然,而是“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实在深入人心,成为学者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是信仰,并不以为忌讳。元凤三年(前78)至宣帝即位不到十年,因此事警戒,学者们或许不再“口无遮拦”,但学风业已形成,迥异于武帝之初。所谓的“鲁学”,若在这种学风下毫无改变,不主动添加些所谓“齐学”作风,则绝不能适应现实需要。
察《汉书·艺文志》,也有如《谷梁外传》这类的著作出现。《谷梁》属蒙先生说的“鲁学”,如何能有《外传》?《汉书·五行志上》:“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①(东汉)班固:《汉书》卷27上《五行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17页。“传以《洪范》”当作“傅以《洪范》”,颜师古注:“传字或作傅,读曰附,谓附着。”刘中垒以《洪范》述《谷梁》,完全为顺应时代学风,将《谷梁》推向一个高峰。如谨守师法,又如何以《谷梁》推“灾异”?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申公《谷梁》学是申公之学,刘向《谷梁》学是刘向之学。两者《谷梁》学尚且不能相合,何况将西汉经学简单分为“齐学”“鲁学”。
上文曾谈到,如果讨论西周、春秋以及战国时鲁国具体的“鲁学”,为鲁地学人做一个“学案”,从鲁国存在的角度说,不论其内部有什么不同的派别,“鲁学”是合理的。这种合理不是学派,而是以人及存在的国家地域划分。西汉中期提出的“鲁学”与“齐学”,作为概念,它首先必须在当时儒家与经学的范围中得以普遍适用。如翼奉、匡衡、萧望之同学于后苍,传《齐诗》。按理说三者都应该属于一个“学派”,但翼奉上书动辄言“灾异”,而匡衡多言礼制、经济,萧望之多谈政事而偶言及“灾异”。个人偏好差异还算明显,所以经学内容的多样性与学者的差别恐怕难以用一种固定学派的标准分类。
又,概念的成立,必然要有现实合理的因素。如西汉常见的“经学”“经术”等词,在先秦并不多见。如果可见,也与西汉的含义不同。西汉的大量出现,是因为实实在在有共同承认的“经学”“经术”存在,并且常常使用,所以见于文献的数量自然很多。“齐学”“鲁学”则不同,在韦贤等人提出前,没有人提出相同的说法,甚至其后的西汉末东汉之时也很少出现。从此侧面也可得知这两个概念的真实性。
以上,就秦汉儒家对齐、鲁“初政”及伯禽的认识与建构与“齐学”“鲁学”是否在西汉中期时真的可以成立两个问题作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韦贤等人提出“齐学”“鲁学”两个概念依据了战国以降儒家对齐、鲁政治“霸道”与“王道”的认识,政治意图较强,而并不符合实际学术情况。西汉《谷梁》学作为一门前后变化的学问,也不可将其视为所谓的“鲁学”。今天讨论经学史上“齐学”“鲁学”的意义,恐怕并不如“齐文化”“鲁文化”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