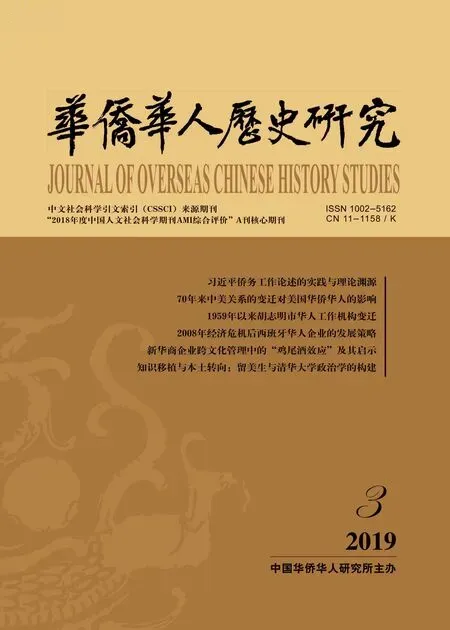另类的守望者*
——国内外跨国留守儿童研究进展与前瞻
王 晓,童 莹
(1.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2.福建社会科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1)
20世纪60年代以降,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世界人口的跨国流动呈现汹涌澎湃之势。据统计,2017年全球约有2.58亿人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占全球总人口的3.4%。[1]这意味着,世界上每30人中便有一个是国际移民。然而,受限于劳工合同及僵化的移民制度,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衍生出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跨国留守儿童。数据显示,摩尔多瓦31%的儿童(0至14岁)其父母至少有一方远在异国他乡;[2]在墨西哥,每25个儿童中就有1人的父亲移民美国,11个孩子中便会出现1个可能在15岁之前其父亲就已跨国流动;[3]由于政策对跨国迁移的鼓励,在菲律宾的跨国留守儿童人数更是高达900万,占整个青少年人口的27%。[4]中国的跨国留守儿童至今虽然并无一个精确的人口统计,但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移民海外,其数量一直处于急速增长的状态。以福建省闽江入海口处的福清、长乐、马尾、连江等传统侨乡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拥有外国国籍的跨国留守儿童就有2万人之多。[5]
与广受关注的国内留守儿童不同,跨国留守儿童具有一定的自身独特性。首先,他们受到的时空撕裂更为严重,与父母分离的时间更早、更长,空间距离拉得更远,而且受到诸多行政障碍的限制,导致家庭教育主体长期缺席,思想和情感培养都处于真空状态。其次,他们与父母分处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之中,甚至有些先是在国外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学校教育才回到故国,身上有着明显的文化张力。正因此,跨国留守儿童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处境不利的边缘群体。然而,这一“另类的守望者”的现实遭遇并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同样的重视。无论是学者规模还是研究成果的丰富性和深入性,国内对留守儿童的探讨远远滞后。在国内,跨国留守儿童是潜在的侨务资源,通过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并解决其成长困境,能有效提升未来一代华侨华人的向心力。有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和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展望,为进一步深化认识我国跨国留守儿童乃至农民工留守儿童提供参考。
一、国外的研究现状
半个多世纪以来,南北半球之间日益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工移民,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跨越国界,迁移到发达国家和地区。面对随之而来的数量庞大的跨国留守儿童,相关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关注重心放在了父母跨国迁移行为对留守儿童造成的诸多影响上。然而,几乎在每个领域,已有研究都存在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
(一)身心健康
儿童健康对家庭结构和组成的变化十分敏感。[6]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父母因跨国迁移而缺席家庭生活,会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琼斯(Jones)等学者指出,父母移民国外的孩子遭受情感问题的可能性是非移民家庭同龄人的两倍。[7]苏亚瑞兹·奥罗斯科(Suárez-Orozco)等人也发现,经历过跨国留守的孩子有更高和更明显的焦虑和抑郁症状。[8]在斯里兰卡,相关研究发现,母亲的跨国迁移造成留守儿童尤其是青少年 普遍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时常感到孤独和悲伤。[9]另有研究强调了父母的连续移民对亲子关系的极大破坏,并发现时间似乎并不能起到完全有效的修复作用。[10]摩尔根(Morgan)和他的同事甚至认为这种不良的心理状态会波及未来,通过考察伦敦的加勒比移民,他们发现精神疾病与早期的亲子分离存在显著关联。[11]
近年来,鉴于女性移民异军突起,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相比父亲,母亲的缺位是一个更大的风险因素,更有可能引起留守儿童的身心困扰。比如,通过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不同形式跨国家庭中的儿童进行比较,乔丹和格拉哈姆(Jordan & Graham)发现母亲移民国外的孩子比生活在其他家庭中的孩子更容易感到沮丧和无助。[12]留守期间,虽然直系亲属或朋友、邻居等扩大家庭成员可能会帮助填补护理不足问题,但总的来说替代工作是不充分的。当妻子迁移时,丈夫要承担更多的照顾角色,面临更大的压力,于是很多人开始酗酒和吸毒,以此逃避监护责任。[13]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情感支持,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风险大增,逐渐变得孤僻和冷漠。[14]而且,母亲角色退出后,年长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可能会承受更重的负担,她们凡事必须自己拿主意,同时还要照料兄弟姐妹。[15]马祖卡托(Mazzucato)等人发现,女性移民在为留守子女争取稳定的照顾安排方面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孩子们被迫不止一次地更换监护人,而护理人员的频繁变化只会导致儿童健康状况变得更差。[16]当然,也有学者将父亲的角色放在与母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德·斯奈德(De Snyder)的报告认为,当丈夫移民后妻子不得不独自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由于身心承受更大的压力而产生抑郁和被遗弃的恐惧,留守儿童很容易受到波及,从而造成他们不良的身体反应。[17]斯克米尔(Schmeer)的研究则发现,当父亲不在时,移民家庭可以利用的资源锐减,孩子生病的几率要比父亲在家时高出39%。[18]
然而,也有大量的文献表明,跨国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并不比非移民家庭的孩子差,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更好。巴蒂斯泰拉和康诺克(Battistella & Conaco)在菲律宾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移民子女的心理问题比正常家庭的孩子差很多。通过标准的测量方法,移民儿童的社会焦虑略高于非移民儿童,但在孤独程度上,两类孩子的得分几乎是一样的。[19]相似的结论也出现在撒哈拉以南的诸多非洲国家,在那些地方,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孩子对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的适应能力,因此完全不会把父母移民与病耻感联系在一起。[20]
(二)教育状况
大量证据表明,父母参与国际移民提高了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有效保证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对留守儿童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墨西哥的一项研究指出,只要留守儿童不把移民看作是未来经济成功的可替代路径,父母的跨国迁移将对他们的教育表现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21]在戴维斯(Davis)看来,移民汇款可以让孩子免于家庭劳作,从而消除接受正规教育的结构性障碍。[22]在菲律宾,留守儿童经常被移民父母安排进教育条件更好的私立学校,至少在小学阶段,与非移民儿童相比,他们的学校表现更好,能够获得更高的分数和更多的奖学金。[23]爱德华兹和尤瑞塔(Edwards& Ureta)的研究发现,移民汇款能够大大降低留守儿童辍学的风险。数据显示,对城市中的一至六年级学生而言,有接受移民汇款的儿童比其他孩子的辍学率低54%,六年级以上低27%;对农村孩子来说,相比之下低25%。[24]
但是,移民汇款并不能抵消父母缺席对留守儿童造成的心理伤害。[25]而不良心理反应的积累,则很容易转化成逃学、学校问题行为及普遍缺乏完成学业的动力。[26]尤其是在跨国迁移的早期阶段,由于移民工作的不稳定性,汇款时断时续,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因为移民与原生家庭逐渐失去联系而中断。[27]莫兰·泰勒(Moran-Taylor)在危地马拉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移民父母本来都打算定期向原生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但在实际生活中,支付减少乃至断绝联系的现象并不罕见。[28]如此,留守儿童很可能会被迫辍学去找工作或帮忙做家务。[29]阿尔卡拉斯(Alcaraz)等以2008年的经济危机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墨西哥移民家庭入学率与美国汇款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汇款收入的锐减导致了童工数量的显著增加和学校出勤率的明显下降。[30]然而,有意思的是,另有学者发现在移民汇款大量涌入的社区,留守儿童入学率却依旧不增反降。究其原因,相关学者认为,经济移民的巨大成功使这些社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笼罩性的移民文化,在其影响下,孩子们期望追随父母的脚步而成为未来移民,他们因此会低估当地的教育价值而提前终止学业。[31]
(三)社会行为
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对跨国留守儿童社会行为的关注要远少于身心健康和教育状况。即使这样,学者们的观点仍未达成统一。其中,部分学者坚持认为,父母跨国迁徙并不必然会导致留守儿童社会行为失范。或者说,与非移民家庭孩子相比,跨国留守儿童的社会行为如果不是表现更好,至少也不会差得太多。比如,菲律宾的一项研究显示,父母迁移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及价值观和精神品质的传递乃至形塑并不十分重要,在家的监护人可以成功填补父母不在身边时的角色空缺,在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下,他们通常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与其他家庭成员相处得也很好。[32]对留守儿童发生吸烟、喝酒和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而言,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证据表明,父母移民与此并无显著关联。[33]相同的结论也存在于泰国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对719户农村家庭的对比考察,认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跨国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发生率更高。[34]
对此,有很多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相关研究之所以未能发现移民与非移民子女之间的差异,深层原因在于敏感事件或情绪未被充分报道。实际上,父母移民与儿童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35]一项有关泰国的研究显示,父母陪伴成长可以有效降低15~19岁的青少年吸烟、喝酒和婚前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36]在洪都拉斯、墨西哥和萨尔瓦多,父母外出致使留守儿童不满情绪高涨,从而造成一些人混入青年帮派或接触容易得手的毒品。[37]克劳福德·布朗(Crawford-Brown)在牙买加的研究表明,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跟母亲接触或经历多次监护安排变化的留守青少年,表现出行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在被监禁之前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问题青少年大约占了80%,其中92%的人经历过两到六次监护安排的变化。[38]
(四)亲子沟通
受制于地理空间的隔离,跨国移民父母面临着向留守在家的子女提供情感关怀的挑战。为了保持跨越国界的亲密关系,移民父母通常采取两种应对方式:一种是商品化的物质连接,一种是基于现代通讯技术的虚拟连接。一项斯里兰卡的研究发现,在海外从事家政服务的母亲,为了弥补自己的缺失,会尽力给孩子带去物质上的好处。孩子虽然不得不经历亲子分离带来的困扰,但由于得到了商品化的爱,能够承受住这些苦难。[39]尤其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父母在离开本国后仍然能够承担照顾孩子的大部分责任。对移民父母来说,长途通讯技术大大提高了他们在远处施加影响的能力,可以对孩子的饮食、家庭作业和纪律问题进行微观管理,重塑了他们作为有效父母的角色。[40]更重要的是,有研究发现,通过这种虚拟的跨界看护,留守儿童会对父母的迁移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并逐渐意识到父母的巨大牺牲。[41]他们因此不会对父母怀有怨恨,也不会有被抛弃的感觉。[42]
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物质还是虚拟连接,都不足以跨越跨国分离造成的沟通障碍,尤其是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情感层面。身体的疏远为日益增长的情感分离铺平了道路,物质连接很可能使亲子关系变成一种干瘪的金钱转移关系。[43]虽说长距离通讯能在其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非所有的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沟通费用,经济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跨国关系的维持能力。[44]而且,有学者认为,远距离通讯完全弥补不了实际的身体接触或眼神交流所提供的亲密关系。[45]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父母身体缺席和跨国电话成为例行公事时,孩子会变得漠不关心。越南的一项研究表明,除非有提示,不然已经习惯了跨国分离的孩子不会再提及缺席的父母。尽管大多数孩子在被要求的时候仍然会通过电话与移民父母交谈,但他们对同一类问题的重复谈话越发失去兴趣。甚至那些年长的孩子还把移民父母通过电话等表达爱和关心的手段看成是一种遥控和监督。如此一来,可直接语音交流的通讯设备反倒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对成长中孩子的祝福。[46]
二、国内的相关探讨
我国的跨国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侨乡。历史上,这些地区便存在着高频率、大规模的跨国移民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移民人数更是逐年增长。与之相伴而生的是,跨国留守儿童在东南沿海大量涌现,而且有往内地反向扩散的趋势。然而,国内学界对此没有做到应有关注,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均指向农民工留守儿童,跨国留守儿童遭到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其实,“留守儿童”一词于1994年被一张首次使用时,原本指的便是跨国留守儿童群体。[47]只不过后来因为受到声势浩大的农民工跨区域迁移的影响,农民工留守儿童受到了政学两界更为广泛的重视。截止到2018年10月9日,笔者以“留守儿童”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期刊库中检索发现,研究农民工留守儿童的文章竟然高达1万余篇,而对比鲜明的是,有关跨国留守儿童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仅27篇,且大多属于宏观、抽象的一般性论述,真正有深度的经验研究只有寥寥10篇左右,这显然与跨国留守儿童作为“特殊中的特殊群体”[48]的地位极不相称。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依据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
(一)跨国抚养原因
从移民及其家庭的主观态度看,跨国抚养并不是一个理想选择。之所以如此,胡启谱认为主要受三方面的影响和推动:第一,移民父母自身的处境使国外抚养困难重重,尤其是对于那些非法移民父母,他们在社保和工作方面存在诸多不平等待遇,根本没有能力和时间照顾孩子;第二,国内抚养不仅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照看条件,而且还有益于整个家庭的和谐团结;第三,签证手续、交通通讯及侨乡相关服务业等外部环境的改善,也大大减轻了跨国抚养的阻力。[49]除以上三方面原因外,有学者还发现,中华文化传统、规范和家庭期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提到隔代照顾时,几乎超过一半的移民父母都认为这是一个预期习俗的延续。于是,让孩子回到过去的文化中,实现大家庭的愿望,同时也能解决儿童保育议程,便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50]
(二)成长与发展困境
这方面的研究根据视角不同又可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问题视角,集中考察跨国留守儿童所遭遇的成长困境与主要问题表现。何毅指出,受限于家庭环境、学习需求和发展方式的影响,跨国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更少、更程式化,日常亲情互动严重缺失,家庭教育残缺,人格发展受阻,抑郁寡欢、脾气古怪,在人际交往中有明显的自卑感,对学习也普遍缺乏动力。[51]此外,文峰发现,因为身份特殊的缘故,跨国留守儿童还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困顿,对未来选择感到迷茫。[52]于是,很多孩子过分沉迷于网络,有的甚至走向极端化,最终扭曲了人生方向。[53]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另有学者持较为乐观的看法。谢履羽认为,受益于物质条件的提高及移民父母对亲子沟通的重视,跨国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处于正常水平,并未因父母缺席而受到损害。[54]
第二类是比较视角,主要探究跨国留守儿童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尤其是心理和行为的差异。在这方面,大部分研究认为,与其他类型的留守儿童相比,跨国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最差,亲社会行为最少。刘艳飞在比较了省内留守、省际留守和跨国留守三种类型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后发现,跨国留守儿童比另外两种类型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更明显的敌对、偏执、人际敏感、抑郁、焦虑、适应不良和情绪不稳等症状。[55]一项有关朝鲜族跨国留守青少年的研究指出,非留守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水平都明显高于跨国留守青少年,同时由于朝鲜族是父系社会,父亲外出的负面影响比母亲更大。[56]赵定东等则将跨国留守儿童与犯罪富裕型留守儿童和一般富裕型留守儿童进行对比,发现其他两者的心理健康皆比跨国留守儿童要好,相对孤独感更轻,安全隐患更小。[57]潘玉进等的研究表明,跨国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远不如国内留守和非留守儿童,使得他们在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等人格各维度上的得分显著要低,而违纪更多。[58]然而,潘佳丽等的研究却显示,虽然跨国留守儿童的社交问题比国内留守和非留守儿童更严重些,但在其他问题行为上,三者并无太大差异,反倒是在群体内部,因为性别和年龄的不同存在明显的区别。[59]
(三)产生的社会影响
陈日升通过对“小美国人”的实地考察,发现跨国抚养对地方社会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首先,移民汇款提升了寄养家庭的经济状况;其次,移民父母更加关注家乡的各项基础建设和文化教育发展,从而整体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和办学质量;再次,基于照顾留守儿童形成的服务行业间接地为移民迁出地引进了青壮年劳动力,有利于优化当地的人口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最后,由于跨国留守儿童的侨眷身份,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拥有的还是外国国籍,在政治和法律上对当地政府提出了如何正确应对中外关系的新课题。[60]高哲运用跨国主义理论对跨国抚养期间的跨国主义联系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虽然跨国留守儿童系未成年人,尚未完成基本社会化、独立拥有资源,但由于特殊身份的缘故,其跨国主义联系超越了家庭内部的经济及情感界限,具有国际政治及社会交往方面的内涵,是促进家庭成员及中外联系和交流的纽带。[61]
三、已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一)主要特点
不难看出,学界围绕跨国留守儿童已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并产生了不少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已有研究有如下典型特征。
一是研究对象主要以幼小儿童为主,或者未做任何界定,笼统地将所有年龄层的留守儿童都纳入考察范围,极少量涉及青少年群体。二是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心理健康和教育表现两大领域,其相关成果几乎占了跨国留守儿童研究的半壁江山,其他方面的探讨稍显薄弱。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以问卷、量表为工具的定量分析占统治性地位,只有极少数采用的是访谈、观察和体验等质性研究方法,而将跨国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则是众多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点。四是在研究视角上,绝大部分学者站在客位的立场,视跨国留守儿童为父母移民的被动受益者或受害者,只有极个别学者注意到了留守儿童在移民决策中的能动作用。五是在研究水平上,由于国内学界过分重视农民工留守儿童而忽视跨国留守儿童,导致研究的丰富性和深入性均落后于国外。学者们并没有真正挖掘跨国留守儿童区别于农民工留守儿童的特有属性,依旧将其作为普通留守儿童来看待。
(二)存在的问题
1.主体性丧失与群体无相①“无相”本是一佛教用语,意指心无所住,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的精神状态。这里借用其本意,即没有行迹、没有具体形象,用来指跨国留守儿童被高度抽象化,使人们看不到其主体性的一种研究结果。
前文述及,定量分析在跨国留守儿童研究中占据绝对核心位置。学者们多抱着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泛用技术化的资料收集工具和统计分析方法。这种研究路径虽然可以快速抓住跨国留守儿童与其他不同类型儿童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但同时,跨国留守儿童本身也极易被模式化、简约化,沦为没有血肉,没有人生经历、情绪体验和主观能动性的抽象研究客体。其结果是,跨国留守儿童集体失语,我们只看到父母移民对留守儿童产生的影响,却唯独看不清留守儿童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本来面目及其对留守生活的能动反应。
值得留意的是,近年来国外学界正在经历一个学术转向,即不再视留守儿童为消极的接受者,相反将他们看成是自己生活的积极参与、建构与阐释者。相应地,研究视角也正在从局外人的立场切换到儿童自身的内部视角。相关学者认为,尽管父母移民导致了留守儿童生活受限,但通过抵抗、韧性和改造的策略,他们完全能够成为有意识的能动者和自身发展的代理人。[62]通过对墨西哥农村的田野调查,德雷比(Dreby)发现,作为家庭中没有权力的成员,孩子对移民的决定几乎没有影响,但他们往往会以负面的行为和态度表达不满,以此与父母讨价还价,最终影响家庭的迁移轨迹。[63]也有学者曾以加勒比4个留守儿童的生活故事为个案,深度考察过儿童对父母移民与自己跨国留守的理解。[64]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于还原留守儿童活生生的本来面目,重塑儿童主体性价值甚大。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只占很小比例,相互之间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理论对话。
2.过程与结果呈混乱局面
(1)研究对象界定不明
明确清晰的概念界定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但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跨国留守儿童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尚缺乏统一、明确的界定。
首先,跨国留守儿童别称众多,五花八门。国内学者多称之为“洋留守儿童”“洋留守华裔”“侨乡留守儿童”“华侨留守儿童”“海外留守儿童”等,国外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卫星儿童”。其次,有关跨国留守儿童内部的细分类型,不同学者间也远未能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跨国留守儿童特指在国外出生,已经取得了外国国籍,但因为移民父母忙于事业无暇他顾或为了学习中文等目的,被送回国内抚养的孩子。[65]但另有学者也将国内出生,父母于其幼年时远赴海外而被迫留守家中的孩子归入其中。[66]再者,不同研究所指的跨国留守儿童的内涵和外延差别甚大,尤其在留守儿童的年龄方面,标准明显不一。
(2)研究过程缺乏规范
首先,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随意。对若干质性研究来说,学者只是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介或实地访谈获取几个个案资料便展开主观评议,并没有真正深入到留守儿童的生活予以整体式理解,资料碎片化,结论空洞无物、泛泛而谈。而且,由于报纸网络的报道和他人评价多是负面导向的,从而致使研究者很容易夸大跨国留守儿童自身的问题。而对定量研究而言,又普遍存在研究设计简单化、抽样方法不科学等问题。有些学者甚至对问卷设计、抽样过程及结果检验只字不提,研究结论难免会产生偏差。
其次,研究内容重复现象普遍,缺乏成果之间的相互借鉴与积累。许多国内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很少会去回顾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更不会主动与前沿理论观点进行对话。正因此,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国内研究都远滞后于国外学界。目前,国内学者对跨国留守儿童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心理健康和教育问题两大方面,且大部分文章都是靠一些零碎资料或简单的统计分析拼凑而成,内容杂乱并多有雷同。此外,研究视角和叙事方式仍是问题式的,缺少理论关怀。
(3)研究结论南辕北辙
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父母跨国移民对留守儿童的影响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相差甚远,甚至有时针锋相对。其中有些是客观存在,因为跨国留守儿童所处的国家不同,面临的政治社会文化有异,问题表现自然会有差别。但问题恰恰在于,面对同一背景下的跨国留守儿童群体,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仍会相互抵牾。这种矛盾决定了研究人员有必要转换视角,寻求其他替代性解释。
四、未来国内研究的可拓展之处
在国内,跨国留守儿童虽然客观存在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则比较晚近,甚至可以说至今都还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因此,与农民工留守儿童相比,跨国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明显滞后。鉴于此,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及存在问题的挖掘,提出几点可以在未来研究中拓展的地方。
(一)研究对象
截至目前的跨国留守儿童研究基本上是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幼小儿童身上,或是直接不加区分,将所有年龄层的孩子视为同质化的个体进行泛化的统一考察,比较缺乏对青少年群体单独、深入的关注。然而,研究人员应该知道,青少年正值青春期,也正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节点,极易受到家庭结构变化及周遭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他们即将完成基本社会化,准备或已经开始作为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面临着比幼小儿童更多、更复杂的成长与发展问题。因此,未来研究的焦点可适当从幼小儿童转向青少年群体。此外,在已有的比较研究中,比较的对象多限于农民工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与其他不同国家、不同类型儿童(如流动儿童或父母离异儿童等)进行比较,探寻其间的共性与差异,以了解不同形态的父母分离对儿童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注重的是作为群体而非作为个体的跨国留守儿童,客观上造成了跨国留守儿童集体失语并丧失主体性。对此,新儿童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和普劳特(James& Prout)的意见或许可以借鉴。他们认为,儿童作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应该从其自身进行理解,因此人类学民族志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研究方法。[67]人类学民族志主要采用主位取向的研究策略,尤为强调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倾听他们的声音并移情理解。未来研究可遵循此路径,选取若干典型侨乡或学校作为田野调查点,融入跨国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活及其人际交往圈子,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同时实施无结构深度访谈,以了解其真实的生活状态及内心感受。
(三)研究内容
近年来,由于我国人口大量地跨国迁徙,跨国留守儿童数量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开始作为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研究主题和内容也需进行新的拓展。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是跨国留守儿童的教育期望和成就动机。当一对父母决定迁移时,背后最大的推动因素往往是希望给留守在家的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教育机会。[68]尤其是随着海外移民父母自身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子女教育更成为他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已有研究虽多有涉及跨国留守儿童的教育表现,但对他们的教育期望和成就动机并未做相关深入探讨。他们对待教育的态度如何?是否会受移民文化的影响而在主观上轻视教育价值?其成就动机又是什么?是否与父母的殷切期望保持一致?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明。
第二是跨国留守青少年的人际交往与社会参与。与幼小儿童不同,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个体往往具有脱离家庭及成年人掌控的内在诉求。在他们身上,家庭的影响功能趋向弱化,家庭外因素的作用逐渐增强。其中,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承担了关键一环,是青少年认识自我、他人及社会的最主要形式和途径。作为他人眼中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的特殊人群,跨国留守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鲜明特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留守青少年的正常社会化发展与身心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三是跨国留守青少年的职业期望与职业适应。由于受到父母跨国迁移和当地移民文化的影响,出国成为大部分跨国留守青少年的主要人生目标。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辍学后马上会被父母带去国外参加工作,更多的则是到家乡附近几个重要的城市打工,目的是先闯一闯外面的世界,为出国做准备。对这样一个受跨国移民实践影响至深的群体来说,其职业认知是怎样的?他们选择职业的价值标准有什么特点?那些已经辍学并开始工作的人,是否很好地适应了职业发展的需要?这同样是未来研究所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四是跨国留守青少年的婚恋与家庭观念。婚恋与家庭观念是个人应对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根本价值取向及道德选择,也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成长于特定社会与家庭环境中的特殊群体,跨国留守青少年在这方面的表现有何特点?尤其是,在移民文化的作用下,他们的婚姻家庭之路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轨迹?又会出现怎样的难题?这亦需要予以集中探讨。
第五是跨国留守青少年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内容。由于具有潜在或正式的洋身份,以及会受到身居海外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跨国留守青少年身上普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中外文化张力。因此,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否会表现出独有的特征?他们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和认可自己所生长的国家和耳濡目染的传统文化?在其群体内部,是否会因为政治身份归属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至今学界仍无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亟需进行探索性调查和深入探究。
最后是跨国留守儿童对家庭及地方社会的反向影响。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特定社会和家庭背景对跨国留守儿童造成的影响,相对忽视了跨国留守儿童对家庭及地方社会的反向作用。尤其是随着跨国留守儿童群体的扩大,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留意他们所遭遇的问题与困境的同时,也要深入研究其带给家庭及地方社会的新挑战。
[注释]
[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2017, p.1, http://www.unmigration.org/.
[2] Vanore M., Mazzucatob V., Siegela M., “‘Left behind’ but not Left Alone: Parental Migration & the Psychosocial Health of Children in Moldov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132, 2015, pp.252-260.
[3] Jenna N., “ Migration and Father Absence: Shifting Family Structure in Mexico”, Demography, Vol.50, No.4, 2013,pp.1303-1314.
[4] Parreñas R., “Long Distance Intimacy: Clas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Vol.5, No.4, 2005, pp.317-336.
[5] 冯军、王磊:《留守的“洋娃娃”》,《新京报》2012年12月6日。
[6] Fomby P., Cherlin AJ., “Family Instability and Child Well-be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2, No.2,2007, pp.181-204.
[7] Jones A., Sharpe J., Sogren M., “Children’s Experiences of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as A Consequence of Migration”,Caribb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3, 2004, pp.89-109.
[8] Suárez-Orozco C., Bang HJ., Kim HY., “I Felt Like My Heart was Staying Behind: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amily Separations and Reunifications for Immigrant You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Vol.26, No.2, 2011,pp.222-257.
[9] Save the Children in Sri Lanka., “Left behind, Left out: The Impact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of Mothers Migrating for Work Abroad”, 2006, p.14, http://www.savethechildren.lk/.
[10] Smith A., Richard NL., Johnson AS., “Serial Mi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hildren of Caribbean Immigrants”, Cultural Diversity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Vol.10, No.2, 2004, pp.107-122.
[11] Morgan C., Kirkbride J., Leff J., et al., “Parental Separation, Loss and Psychosis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 Case-control Stud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Vol.37, No.4, 2007, pp.495-503.
[12] Jordan LP., Graham E., “Resilience and Well-being Among Children of Migrant Parents in South-East Asia” ,Child Development, Vol.83, No.5, 2012, pp.1672-1688.
[13] Hewage P., Kumara C., and Rigg J., “Connecting and Disconnecting People and Places: Migrants,Migration, and the Household in Sri Lanka”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101, No.1, 2011, pp.202-219.
[14] Senaratna BCV., “Left-Behind Children of Migrant Women: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and Strengths Demonstrated”,Sri Lanka Journal of Child Health, Vol.41, No.2, 2012, pp.71-75.
[15] Parreñas R., “Children of Global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Gendered Wo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7.
[16] Mazzucato V., Cebotari V., Veale A., et al., “International Parental Migr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hildren in Ghana, Nigeria, and Angol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132, 2015, pp.215-224.
[17] De Snyder VNS., “Family Life Across the Border: Mexican Wives Left Behind”,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15, No.3, 1993, pp.391-401.
[18] Schmeer K., “Father Absence Due to Migration and Child Iillness in Rural Mexico”,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69, No.8, 2009, pp.1281-1286.
[19] Battistella G., Conaco MCG., “The Impact of Labour Migration on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A Study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the Philippines” , Sojourn, Vol.13, No.2, 1998, pp.220-241.
[20] Cebotari V., Mazzucato V.,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of Children of Migrant Parents in Ghana, Nigeria and Angola”,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42, No.5, 2016, pp.834-856.
[21] Kande W., Kao G., “The Impact of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on Mexica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5, No.4, 2001, pp.1205-1231.
[22][37]Davis J., “¿Educación o desintegración? Parent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s Education in Western Guatemala”,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48, No.3, 2016, pp.565-590.
[23] Yeoh BSA., Lam T., “The Costs of (im)Mobility: Children Left Behind and Children Who Migrate with a Parent”,Perspectives on Gender & Migration, 2007, pp.1-37.
[24] Edwards AC., Ureta 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EI Salvad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72, No.2, 2003, pp.429-461.
[25] Cortes P., “The Femi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World Development, Vol.65, 2015, pp.62-78.
[26] Adams CJ., “Integrating Children into Families Separated by Migration: A Caribbean-American Case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Distress and the Homeless, Vol.9, No.1, 2000, pp.19-27.
[27] Menjivar C., Davanzo J., Greenwell L., et al., “Remittance Behavior among Salvadoran and Filipino Immigrants in Los Angeles”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2, No. 1, 1998, pp. 97-126; Amuedo-Dorantes C., Pozo S.,“The Time Pattern of Remittances: Evidence from Mexican Migrants” , Well-being and Social Policy, Vol.2, No.2,2006, pp.49-66.
[28] Moran-Taylor MJ., “When Mothers and Fathers Migrate North: Caretakers, Children, and Child Rearing in Guatemal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35, No.4, 2008, pp.79-95.
[29] Frank R., Wildsmith E., “The Grass Widows of Mexico: Migration and Union Dissolution in a Binational Context” ,Social Forces, Vol.83, No.3, 2005, pp.919-947.
[30] Alcaraz C., Chiquiar D., and Salcedo A., “Remittances, Schooling, and Child labor in Mexico”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7, No.1, 2010, pp.156-165.
[31] Davis J., Brazil N., “ Disentangling Fathers’ Absences from Household Remittance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Cas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Guatemal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Vol.50, 2016,pp.1-11; McKenzie D., Rapoport H., “Can migration reduc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Mexico”,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24, No.4, 2011, pp.1331-1358.
[32] Yeoh BSA., Lam T., “The Costs of (im)Mobility: Children Left Behind and Children Who Migrate with a Parent” ,Perspectives on Gender & Migration, 2007, pp.1-37.
[33] Choe MK., Hatmadji SH., Podhisita C., et al., “Substance Use and Premarital Sex Among Adolescents in Indonesia,Nepal,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Asia-Pacifi c Population Journal, Vol.9, No.1, 2004, pp.5-26.
[34] Jones H., Kittisuksathit S.,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Findings from Rural Thaila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Vol.9, No.6, 2003, pp.517-530.
[35] Bryant J., “Childre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A Review of Evidence and Policies”, 2005, p.7, http://www.unicef.org/irc.
[36] Choe MK., Hatmadji SH., Podhisita C., et al., “Substance Use and Premarital Sex Among Adolescents in Indonesia,Nepal,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Asia-Pacifi c Population Journal, Vol.9, No.1, 2004, pp.5-26.
[38] 转引自Dillon M., Walsh CA., “Left Behind: The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of the Caribbean Whose Parents Have Migrate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Vol.43, No.6, 2012, pp.871-902.
[39] Ukwatta S., “Sri Lanka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Overseas: Mothering Their Children from a Distanc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Vol.27, No.2, pp.107-131.
[40] Madianou M., Miller D., “Mobile Phone Parenting: Reconfigu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lipina Migrant Mothers and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 New media & Society, Vol.43, No.3, 2011, pp.457-470.
[41] Dreby J., “Children and Power in Mex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69,No.4, 2007, pp.1050-1064.
[42] Mazzucato V., Cebotari V.,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Ghanaian Children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Vol.23, No.3, 2017, pp.1-14.
[43] Boccagni P., “Practising Motherhood at a Distance: Retention and Loss in Ecuadori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38, No.2, 2012, pp.261-277.
[44] Vertovec S., “Cheap Calls: The Social Glue of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Global Networks, Vol.4, No.2, 2004,pp.219-224.
[45] Skrbiś Z., “Transnational Families: Theorising Migration, Emotions and Belonging”,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29, No.3, 2008, pp.231-246.
[46] Hoang LA., Yeoh BSA., “Sustaining Families across Transnational Spaces: Vietnamese Migrant Parents and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Asian Studies Review, Vol.36, No.3, 2012, pp.307-325.
[47] 一张:《“留守儿童”》,《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45期。
[48] 陈美芬、陈丹阳、袁苑:《侨乡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心理研究》2014年第3期。
[49] 胡启谱:《福州侨乡跨国抚养原因研究》,《科教导刊》2015年第11期。
[50] Bohr Y., Tse C., “Satellite Babies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 Study of Parents’ Decision to Separate from Their Infants”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Vol.30, No.3, 2009, pp.265-286.
[51] 何毅:《侨乡留守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浙江青田县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0期。
[52] 文峰:《侨乡跨国家庭中的“洋”留守儿童问题探讨》,《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
[53] 王佑镁:《“跨国寄养”背景下我国农村侨乡留守儿童媒介素养研究》,《现代远距离教育》2013年第4期。
[54] 谢履羽:《海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亲子沟通状况的关系研究》,《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55] 刘艳飞:《东南沿海留守儿童类型及心理健康状况比较——以福州连江为例》,《福州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
[56] 朴婷姬、秦红芳:《朝鲜族海外留守青少年自我概念、家庭结构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东疆学刊》2011年第3期。
[57] 赵定东、葛颖颖、陆庭悦:《富裕型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问题探析——基于浙江省若干区域的调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8] 潘玉进、田晓霞、王艳蓉:《华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资源与人格、行为的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59] 潘佳丽、李丹、张雨青:《海外初中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心理研究》2011年第3期。
[60] 陈日升:《福建亭江的“小美国人”:一个跨国寄养的新移民子女群体》,《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61] 高哲:《浙江侨乡地区跨国抚养的跨国主义联系研究》,《中国市场》2017年第34期。
[62] Hoang LA., Lam T., Yeoh BSA., et al.,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Changing Care Arrangements and Left-behind Children’s Responses in South-east Asia” ,Children’s Geographies, Vol.13, No.3, 2015, pp.263-277.
[63] Dreby J., “Children and Power in Mex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69,No.4, 2007, pp.1050-1064.
[64] Olwig KF., “Narratives of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Home and Identity in Globalised Caribbean Famil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25, No.2, 1999, pp.267-284.
[65] 乔志华:《恩平的“洋留守儿童”问题一窥》,《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9期。
[66] 夏凤珍:《试析对“洋留守华裔”华文教育的路径选择——以浙江重点侨乡青田县为例》,《八桂侨刊》2015年第1期。
[67] James A., Prout A.,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Oxon: Routledge, 1990, p.207.
[68] Victor C., Valentina M.,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of Children of Migrant Parents in Ghana, Nigeria and Angola,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42, No.5, 2016, pp.834-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