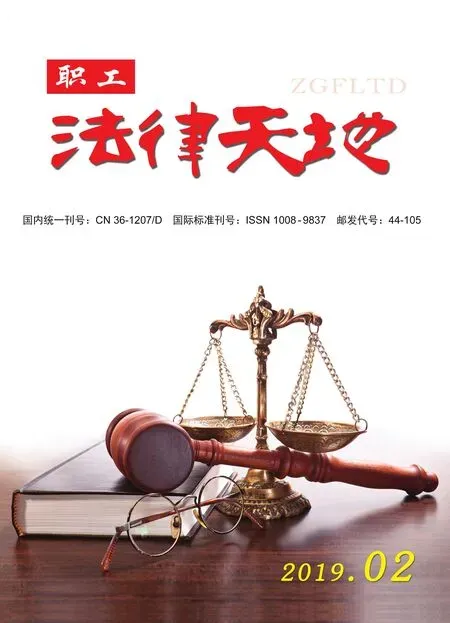捐助法人治理结构在我国的发展
姜云腾
(150080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一、“捐助法人”称谓的由来
《民法总则》第九十二条规定: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以及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等统称为“捐助法人”。纵观各国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都不曾查阅到“捐助法人”一词,该称谓原系我国个别学者所创设,用以代指大陆法系国家中“财团法人”的概念。
在《民法总则》编纂之前,关于我国基金会等公益法人在法人分类中的称谓是否采“捐助法人”一词,在理论界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类:第一类学者认为《民法总则》在法人分类上还是应该固守大陆法系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模式,基金会、宗教寺庙等公益法人应为财团法人项下的公益性财团法人亦或宗教财团法人,但不包括以私人利益为目的和中间目的的财团法人,故我国民事基本法的立法应沿用大陆法系国家通用的“财团法人”一词。第二类学者认为既然我国立法一直没有采用“社团法人”的概念,单独使用“财团法人”的概念就显得不甚协调,再者“财团法人”一词会使一般公众难以理解,易与西方国家营利性质的财团所混淆,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所以采“捐助法人”一词比较符合我国国情,也更能为我国大众所理解。梁慧星教授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就曾建议将我国的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将“捐助法人”置于“非营利法人”之下。
从目前来看,现行的《民法总则》采用了“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三分法的分类模式,将基金会法人等公益法人以“捐助法人”的称谓规定于“非营利法人”的项下。
二、我国捐助法人的性质
捐助法人制度写入《民法总则》,使原本游离于法人分类之外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以捐助法人的形式在《民法总则》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关于捐助法人的性质,理论界通常将其定性为传统民法理论上的“财团法人”,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只能将财团法人作为类似参照物来研究我国的捐助法人,而不能将二者等同,我国的捐助法人有其独特个性。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的捐助法人还是多由《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所规范,这些规范通常都给予了捐助法人高度的自我决策权,严格来说其不像财团法人一样是完全的“他律法人”,而是“自律法人”。
三、我国捐助法人治理结构的历史演进
追溯我国捐助法人的历史发展,可以以《基金会管理办法》等几部法律法规的出台为界,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行政管控型”的治理结构
第一个阶段为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的出台,确立了捐助法人“行政管控型”的治理结构,从外部管控来说,主要依托于归口登记、三重负责、分级管理、行政备案这四项具体措施;从内部治理结构来说《基金会管理办法》在其第三条中规定了基金会的建立必须要有章程、管理机构和必要的财务人员。此法颇有计划经济的色彩,用国家的行政化来管理基金会法人,完全阉割了基金会私主体的法律属性。
2.“ 行政管控向法人治理型转变”的中间模式
第二个阶段为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确立了捐助法人“行政管控向法人治理型转变”的中间模式,从外部管控来看,行政对捐助法人的管控力稍有减弱,从《基金会管理办法》的四项措施变为“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和行政备案”这三项措施;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法人治理型的萌芽初现,具体表现在建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的二元治理结构,其中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理事会为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拥有修改章程、人事任命以及决定重大事项的权力;第二十三条对理事的任职资格做出了限制,具体为消极资格排除、近亲阻却和有限报酬等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基金会须设立监事并明确了其监督理事会、提出质疑建议或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权力。虽然《基金会管理条例》确立了捐助法人的内部治理结构,但究其根本也是一部行政法规,所以其确立的内部治理结构也只是有限的内部治理。
3.“ 法人治理型”的治理结构
第三个阶段是2016年《慈善法》的正式实施,使得捐助法人在治理规范上首次突破了行政法规的层级,获得了法律层级的支撑,向法人治理型的治理结构转变。从外部治理规范来看,其一,降低了准入门槛,“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没有了审查权,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其二,减少了事前准入的防范机制通过检查评估以及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等事中事后措施来对基金会进行监督。从内部治理规范来看,《慈善法》在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慈善组织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及章程,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明确决策、执行、监督三方面的职责权限,开展慈善活动。
最后是2017年10月《民法总则》的施行,捐助法人被纳入到了《民法总则》所确立的法人分类模式,加之上述提到的《慈善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捐助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由“一般法加特别法”调整的规范格局,这也标志着其完成了由“行政管控型”治理结构向“法人治理型”治理结构的最终转变。
通过对我国捐助法人治理结构历史演进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捐助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其总体的趋势是“行政管控式”的治理结构逐步退位于“法人治理型”的治理结构,严格的外部监管逐步退位于宽松的内部制衡,纵向的行政立法体系逐步退位于横向的以捐助法人制度为基础的私法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国捐助法人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是“行政管控式”的治理结构逐步退位于“法人治理型”的治理结构,但是也不能对我国当初“行政管控式”的治理结构予以全盘否定,其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选择,有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加之,“行政管控式”的治理结构和“法人治理型”的治理结构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笔者认为一个良好的捐助法人治理结构应该在外部行政管控和内部自我治理之间进行合理的尺度选择,行政管控的目的在于“防弊”,内部自我治理的目的在于“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