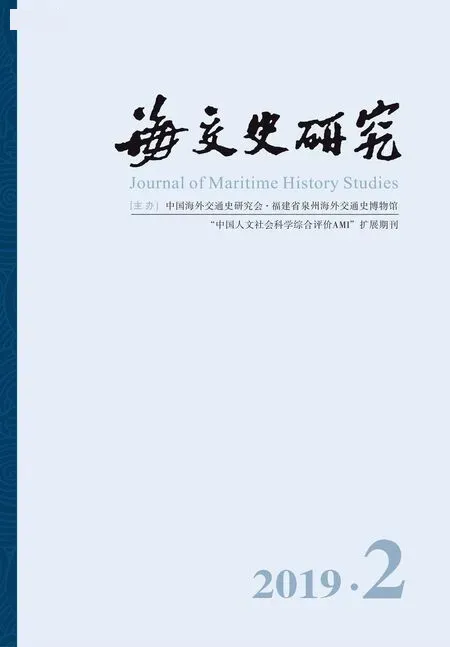“航海文献与中外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综述
林 瀚
中外航海文献的发掘、收藏、整理与出版,一直是东西方海外交通史研究持续关注与不断推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一领域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航海针路簿、涉海碑铭、海洋舆图以及闽粤侨批等民间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焦点。一批批珍贵的民间航海文献得以整理出版,也为推进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为进一步发掘和深入研究航海资料,丰富“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领域研究,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主办,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联合承办的“航海文献与中外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于2018 年10月15日至17日在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召开。
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闽南师范大学、南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温州大学、海洋出版社、中国航海博物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博物馆及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近30人提交了论文,参加会议的还有社会人士及泉州地方相关单位的专家等。
一
开幕式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海洋出版社编审刘义杰主持,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陈尚胜教授、《海交史研究》新任主编谢必震教授、泉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兼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研究员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陈尚胜在致辞中指出,航海文献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在大数据时代,对航海文献进行整理和校勘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14日在联合国讲话的基本精神,在泉州这样一个中外文化汇聚的海上丝路港口城市来探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问题,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现实意义都是很重要的。
《海交史研究》新任主编谢必震表示,201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恰逢泉州海交馆建馆6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多年来,海交史研究的学者在“一馆一会一刊”模式的促进下成长,一馆一会一刊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收获成果的田园,是学术出彩的舞台。2019年《海交史研究》将改为季刊,改版后的《海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都将进一步提升。他还表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奋斗的时代,值得大家为之努力。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指出,海交馆作为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在发展会员、沟通专家学者、组织学术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海交馆也因为有研究会强大的研究力量作为学术支持,在加强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自身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海交馆的年轻学者参与了大量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从中得到了锻炼,不断成长。由于研究领域的合作关系,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共同承办。今后,研究会、海交馆还将扩大和其他相关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为推动中国海交史研究贡献力量。
二
本次研讨会分六组进行报告与评议,与会学者分别就海路针经、海洋图像、南海及印度洋海域、东亚海域、造船技艺、侨批文献等诸多学术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对话。现就各文所论要点概述如下:
(一)海路针经与海图专题研究
海路针经作为古代航海舟师在传统木帆船时代重要的航行指南,不仅是无数舟师火长长期航海经验的积累,也是古代海外交通航海成就的概括。海图则是直观反映着人们对海洋、海上贸易路线以及海权意识的认知。随着历代海路针经的整理出版与海图的不断发现,这一议题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
单丽(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在《异源杂流:海道针经的撰述与流传》一文中,重点探讨了海道针经的产生、流传以及散布过程,认为原始海道针经的母本极有可能是多源的,在其形成后的流传过程中,也不拘于单种扩散及传承方式,而是基本处于一种交相汇流的杂流状态,其内容也会因抄录之人的个人取舍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汪前进(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论文《<顺风相送>航海名词术语系统分析》,通过系统研究《顺风相送》的文本,将此书的航海名词术语初步归纳为十三类:针路簿名称、海洋地貌术语、海洋水文术语、海洋气象术语、船舶术语、方位术语、时间术语、航路术语、操作术语、位置术语、测量术语、祭祀术语与评价术语等。
李彩霞(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在《<顺风相送>南海存疑地名及针路》一文,利用谷歌地球、百度地图等现代先进的测距技术手段,辅以明清以来海外交通史籍的佐证,对《顺风相送》一书中的南海外洋存疑更路及地名进行辨析;并提出可用《指南正法》与《顺风相送》相互比对校勘,这不仅可为存疑针路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更正与改进,同时也为《顺风相送》的版本流传和成书过程提供新的思路。
林瀚(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日本藏<长崎和兰支那海针路志>的推介与解读》,主要介绍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长崎和兰支那海针路志》钞本,通过将该钞本所涉航线予以整理公布,并解读其航线范围﹑记录针路的方式﹑所引东西方航海测量术等内容,初步考订其著述年代,认为该钞本对研究中西方航海技术在东亚海域的交流及航海针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连心豪(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清代漳州月港海上丝绸之路重构——从<送彩(船)科仪>和<安船酌献科>说起》,利用伦敦大英图书馆所藏《送彩(船)科仪》和《安船酌献科》等民间科仪本所记海员配置及航线,参照其他中外文献资料,试图以此部分重构清代漳州月港海上丝绸之路。
刘义杰(海洋出版社)在《试析<更路簿>中的南海更路》一文,通过对20多种《更路簿》进行释读,将《更路簿》中的作为起航港和中转港的港湾分为海南岛本岛港群、南沙群岛港群和海外中转港群,并将更路分作东海(西沙群岛)更路、北海(南沙群岛)更路和海外更路,东海更路和北海更路统称作南海更路,通过对南海更路进行梳理,力图将通过南海更路的纷繁多姿来展示数百年来我国渔民在南海开创的那段久远而又现实的历史面貌。
阎根齐(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福建移民与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渊源》一文,通过对海南渔民部分《更路簿》持有人迁琼始祖进行梳理,发现以福建莆田为主;在比对多种《更路簿》所使用的方言、抄写、句式等特征后,认为海南《更路簿》最初应是由福建渔民落籍海南时传入,或经舟师、商人经过海南岛时传播,而后版本又经与当地航海实践相结合,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海南渔民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的总结。
周运中(福建省福龙中国帆船发展中心)的《牛津明末航海图与<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一文,将牛津大学藏明末航海图与《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所及航线进行对比,认为航海图与之关系密切,且东洋部分多参考《指南正法》。
陈国威(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明代郑若曾<万里海防图>中“两家滩”考析——兼论雷州半岛南海海域十七、十八世纪域外交往史》一文结合田野调研与文献资料,以明代郑若曾等所绘《万里海防图》中的“两家滩”为考察对象与线索,对雷州半岛南海区域十七、十八世纪对外交往的相关情况进行梳理分析,认为雷州半岛除了在国家海防位置上占据一席之位外,在南海商贸圈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羽离子(钱健,南通大学文学院)与陈亚芊(南通大学文献研究所)在《初考晚清绘制渔海全图以宣的活动》一文中,重点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面对列强占海侵渔的局面,如何以渔权保海权的抗争,通过考察《渔海全图》的绘制过程,参展1906年意大利世界博览会情形,并推测其图绘内容,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绘制渔业海图,体现了古老中国对渔权、海权的觉醒。
(二)南海及印度洋海域专题研究
随着考古调查发掘材料的整理,以及学者研究视角不断向外拓展,使得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推进,旧材料在新研究视角的重新审视下,也获得新的认识。
吴春明(厦门大学)的《中国早期文明的“南海”》一文,以汉文史籍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印证,通过对环南海树皮布史前石拍及异形玦饰的空间分布与形态类型进行分析,以及对这些技术的跨海传播等例证的考察,认为南海不仅是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东西二洋”航路的核心海域,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中国四方”“四海之内”之多层、差序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留下了特殊的历史记忆。
杨晓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在《<诸蕃志>“南毗国”条地理补释》一文,通过明初《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以及元代《岛夷志略》等文献的参读互证,对《诸蕃志》“南毗国”条地名进行考释,指出南毗及其属国以放置在印度西南海岸为宜,并认为南毗国属国的地域范围以印度西南海岸的克拉拉地区为主,不能远及印度西北海岸;至于印度东南海岸,也可能在南毗国控制之下。
王小蕾(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女神信仰·海洋社会·性别伦理 ——对水尾圣娘信仰的性别文化考释》一文,尝试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从涉海人群的实践行为和心理积淀出发,对发源于海南岛清澜港,而后影响辐射的范围遍及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水尾圣娘信仰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各个时期水尾圣娘信仰的性别文化意涵加以探究,概括其在构建南海海洋社会性别伦理中的作用。指出对这一海洋女神信仰性别文化意涵的解读,不仅可以体现海洋环境对涉海人群身份定位及社会关系的影响,更能够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触摸南海海洋文化历久弥新的生活气息。
(三)东亚海域专题研究
东亚海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辐射范围,这一海域间不同国家的人群往来异常频繁,双向乃至多向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也构筑起严密的东亚海域交流网络,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深耕的重要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与会学者通过深挖新史料、利用新视角,取得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胡梧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海之昆布”:唐代东亚昆布的产地、传播及应用》一文,通过对中日韩相关文献的梳理,考辨了唐代东亚昆布的基原形态,并就其产地与流转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唐代东亚昆布主要分布于渤海国南海府、龙原府、安边府,新罗良州东莱郡,日本陆奥国等沿海地域,其传播路径主要由新罗和渤海国向唐朝输入,而日本则并未向唐朝输出昆布。就昆布在唐代东亚各国的应用也略有不同,在唐朝主要用作药材;在新罗和日本主要作为食品,也兼做药材;在渤海国则被视为珍贵食品,且已了解其药用价值。
马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新论》一文,通过发掘新史料与对旧史料的重新解读,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洪武中日“倭寇外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指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与邻邦交往,需要从多角度考察双方交往的动态过程,认为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这对于我们重新考察和理解东亚国际秩序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刘永连(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与学生冉晓旭在《从朝鲜汉文文献看东海与南海区域之间的沟通》一文中,通过朝鲜半岛汉文典籍的记录,考察朝鲜士人对南方海洋的认知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指出东亚海域的海商、使臣、海盗等群体为其提供东亚诸国及南海各国的信息,这不仅加深我们对近世东亚海洋文明内涵的理解,也进一步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
陈颖艳(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日本古代画作中的唐馆》一文,以保存于日本长崎、神户等地的古代画作,通过大量绘制精美且有形象的图像资料,分析讨论长崎唐馆的管理与格局,华商对日贸易物品种类,以及华人居住唐馆的日常与节庆习俗,生动再现了唐馆内部景观与华人生活情景。
谢必震(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与吴巍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在《试论海疆史料在新修方志中的运用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方志编纂具有官方文件的性质,十分重要。文章通过对地方志书编纂中遗漏我国重要海疆史料这一问题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进行客观分析,认为以往的志书对于东海、南海的疆域表述,受历史条件的局限,缺漏甚多。新编地方志书应该将古人缺漏的海疆历史资料,譬如钓鱼岛与南海岛屿等史料,客观如实地补充完善,为我国在领海主权争端中提供历史证据和法理依据,以利于我国的对外斗争。
张永钦(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的《陈侃的<使琉球录>为现存最早的琉球使录原因新探》一文,从明代的历史背景、社会事件以及使者的个人情况等方面探析陈侃的《使琉球录》为最早的册封使录的原因。
陈琰璟(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的《零和博弈:1622年荷葡澳门之战新考》一文利用多种语言文献进行互证,将1622年荷葡澳门之战置于更为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之中,力求厘清该战役的前后发展脉络,文章指出在这场军事行动中,由于荷兰在战略、战术以及备战等诸多环节中均存在严重不足,使之成为荷兰人最终失利的原因。
刘啸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衰落的舞台——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佩里舰队眼中的澳门》一文,通过对19世纪中期美国海军佩里舰队中随行人员笔下的澳门记录进行排比对照,指出他们观察下的澳门,更多是美国人眼中(或文化印象中)的澳门。他们将彼时的澳门简化为几个“澳门符号”去理解和观察,澳门本身的角色只是历史和政治的舞台。佩里舰队人员眼中真正的主角,是澳门这个舞台上的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即衰败没落的老旧帝国和如日中天的新兴帝国在澳门如何表现,之所以如此观察,则恐怕与彼时美国崛起之初的国际地位和扩张心态有直接关联。至于生活在澳门这个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保持着独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于佩里舰队人员而言更多只是一种文化猎奇的观察物件而已。
(四)传统造船技艺专题研究
舟船作为沟通海陆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载体,其产生、样式、尺寸、修造工艺等一直是船史学界关注与讨论的重点,不同样式的船只适航于东西方不同的海域,海上的交流不仅包括物产、情报及文化,同时也包含不同技术的交流与书写记录。本次会议共收到三篇船史论文,分别考订了多重船板、郑和宝船尺寸及传统船钉的种类及使用。
袁晓春(蓬莱阁景区管理处)的《<马可·波罗游记>与“华光礁Ⅰ号”宋船的比较研究》一文,以“华光礁Ⅰ号”宋朝沉船六层外板的发现,分析其工艺与功用,并认为学界应该重新审视《马克·波罗游记》记载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科学与史料价值。
胡晓伟(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郑和宝船尺度考——从泉州东西塔的尺度谈起》一文通过分析泉州东西塔所用度量单位“丈”,认为有必要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郑和宝船所用度量单位“丈”。文章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明史·郑和传》之郑和宝船与《明史·和兰传》之荷兰船尺度所用度量单位“丈”提出新的解读,同时参照明清时期红夷大炮的实物尺度,推导出三者所用度量单位1“丈”≈1.6米,并据此换算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为70.4米、宽“十八丈”为28.8米。此外,就洪保墓志所提到的“五千料巨舶”,作者也认为不是长度超百米的郑和宝船。
黄东伟(泉州舟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传统海船船钉演变探析——以田野调查与考古发现为讨论中心》一文中,就目前所出版的沉船考古调查报告以及地方文献资料对传统船钉的叫法各异的情况进行梳理,作者通过对我国沿海进行实地走访调查,重点分析了古代至近现代海船修造中不同船钉的种类、形制、打制工艺、防锈处理及使用方式。
(五)其他海洋专题研究
除了以上专题之外,与会学者还就海洋景观、潮汕侨批、涉海人物、海洋历史资料汇编等议题做了讨论与对话。
曹瑞冬(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灯塔的景观叙事与中国的地理想象(1856-1936)》一文指出灯塔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既是人类视觉和意识的焦点,也是特定社会经济构成的意义和记录,并能以图像为中介将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关系转化为叙事形式。文章以灯塔为中心,通过探索景观叙事的历史演进过程,着重讨论人与景观在互动过程中所展现的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认知与想象。
陈思伟(华南师范大学)的《从stoma到stena:古代希腊罗马人对曼德海峡的认识》一文,从时间纵向的角度梳理古代希腊罗马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探索的历程,通过利用古典作家的著作,考察公元前后人们对海峡的地理位置、名称、宽度等方面的了解程度,并从认知方法的角度分析导致模糊或错误认识产生的原因。
陈贤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学生吴联珠在《大时代与小人物——宋嘉锐侨批书信所见一个潮汕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1922-1965)》一文中,通过整理广东澄海冠山乡宋嘉锐家庭保存完整的290封侨批书信,从一个普通百姓家庭的生活细节和情感起伏再现20世纪上半叶大时代变迁与小人物际遇的互动牵扯;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并思考侨批书信作为家庭私密性文件这一文献类型的价值与局限。
李国宏(石狮市博物馆)在《吴鉴行迹编年述略》一文中,通过爬梳文集、地方志、碑铭等文献的记载,按编年记叙,简要勾勒了元代海外交通史研究中重要的历史人物吴鉴的行迹、交游及著述情况。
陈彬强(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海上丝绸之路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评介》,认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具有收录齐全、编排科学、作风严谨等优点,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汇编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有力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发展,并为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汇编整理工作提供很好的经验借鉴,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和使用价值。
三
本次学术研讨会虽然规模不大,但仍涉及针路簿、航海图、造船技术、航海信仰、涉海人物等诸多领域,涵盖的范围也包括南海、印度洋及东亚海域。与会学者发掘了新材料,利用新方法,获得新见解,展示了中外文明跨越海洋的交流与互鉴的辉煌历史。本次会议论文水平之高、涉及范围之广,足以反映近年来中外航海文献的研究成果与学术水平。
研讨会分六组进行报告与评议,与会学者在交流与讨论中绽放了思想的火花,不仅拓宽研究的视角,也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讨会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多为目前国内海交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海交史研究》主编谢必震在闭幕式上在对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逐一进行点评,认为虽然与会人数不多,但论文精湛。他认为,本次的研讨会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无论从史料还是角度上都力求创新;二是年轻学者的研究力量在壮大,这是好现象;三是研究的角度多维度多层次;四是史料的分析透彻、扎实。
相信通过本次“航海文献与中外交流互鉴”学术研讨会,结合新近发现的航海文献和出土文献,充分吸收国内外学界的理论与方法,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历史研究,为航海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产生积极而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