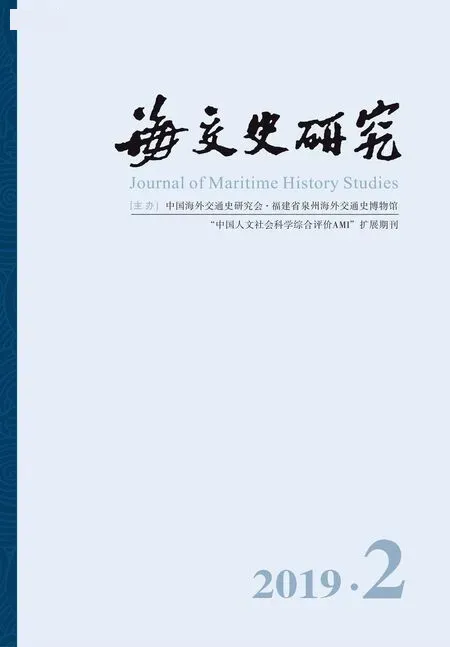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发展和探源
陈政禹
中国沿海自古便有“送船”习俗。所谓“送船”,是指通过将特制小船漂流入海或焚化的方式来送走灾祸或祈求神灵庇佑。其表现形式有两种:—是以竹草制成仿真的船型,糊以彩纸,内置神像和各类仪式用具,醮毕抬至水边焚化,以祈求平安,称为“游地河”。二是以真船装载纸扎的神像和各类供品,延请道士做醮后,放送入河或入海,又称“游天河”。[注]据清代林豪所撰光绪《澎湖厅志》卷8《杂俗》记载,进行“送船”仪式的“船”在制作完成后,“或择日付之一炬,谓之游天河;或派数人驾船游海上,谓之游地河”。“送船”习俗在江浙沿海的具体表现形式为“送彩船”“送纸船”“送大暑船”和“送法船”(水灯)等,在闽台沿海则表现为“送王船”。
关于“送船”习俗的产生和传播,国内外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学界目前在“送船”习俗的来源、传播路径以及“送船”习俗的宗教属性方面尚存争议;而且研究关注的焦点多集中闽台地区的“送王船”,有的学者甚至指出类似于“送王船”这种“送船”形式为闽台地区独有[注]姜守诚:《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载《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254页。。这就使得对“送船”仪式的研究难以深入全面。事实上在江浙沿海也存在着大量的“送船”习俗,对它们的分析和探源有助于拓宽“送船”习俗的研究领域,丰富“送船”习俗的研究内容。同时,“送船”仪式多发生于海陆交界地带,仅从海洋或是陆地方面解释其成因和发展都难免偏颇,对“送船”习俗的探源应从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两方面综合考虑。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江浙地区的“送船”习俗为研究对象,从海陆文化交融这个角度考察“送船”习俗的来源,以求对“送船”习俗有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江浙沿海的“送船”习俗
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江浙便有 “祠沙”这种习俗,即“送彩船”。据北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丁丑,辰刻……,而后至沈家门抛泊。……申刻,风雨晦冥,雷电雨雹欻至,移时乃止。是夜,就山张幕,扫地而祭,舟人谓之祠沙。实岳渎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为小舟,载佛经、糗粮,书所载人名氏,纳于其中,而投诸海,盖攘厌之术一端耳。”[注](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页。由上可知,从江浙出发的船队途经沈家门时遭遇风浪袭击,船员抛锚举行“祠沙”祭海仪式,每船都会制作一木质小舟,在其中装载佛经、粮食以及船员名单,随后将小船投入海中漂流而去,以寄望送走厄运,人船平安。徐兢此次奉使高丽的出发港为浙江的明州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的缘故,出海的水手多从海船出发地招募,因此“祠沙”应为随船的江浙水手依照其家乡风俗而举行的“送船”仪式。由此可以推断,宋代在浙江沿海一带居民中就有“送彩船”祈求平安的习俗。
在浙江温州沿海有“送纸船”的习俗,“送纸船”又称“大送船”。在光绪年间(1875-1908)出版的《吴友如画宝》中,有关于这项活动的图文记载:“瓯郡,自入秋后瘟疫流行,久而不息。九月九日,当道宫绅建水陆道场,迎神出巡,计七昼夜。……水中纸扎大号船一艘,二号船四艘,载以金箔银箔,储以日用器具,凡三十六行应用之物,无一件不精,无一物不备。至十五日亥时,送至北门外大江中焚化。”[注](清)吴友如:《吴友如画宝》第三册,《风俗志图说(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页。1895年的《申报》也对“大送船”仪式进行了叙述,“逐疫预备纸船一大只,放在庙中,启建罗天大醮七昼夜,一俟迎神驾回,恭送圣船出朔门外,顺潮出口焚化”[注]载《申报》1895年9月15日,第8051号。。《申报》中的记载与《吴友如画宝》大致相同,而且更详细地指出,送船焚化的地点在河流的入海口附近。
在江浙沿海的“送船”习俗中,台州沿海的“送大暑船”习俗延续至今。“送大暑船”活动可以追溯到清代。据《清稗类钞》记载:“同治时(1862-1874),临海县民以频岁有疠,过大暑不瘳,乃为送船之会。船与常舶无异,用具如桌椅床榻衾枕,食物如鸡豚鱼虾,甚且刀矛枪礮之足以备盗者亦有之。……大暑前数日,建道场,至大暑送之,俗呼为大暑船。”[注](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74页。今天的“送大暑船”活动基本沿袭了清代的做法,据《椒江市志》对当代“送大暑船”仪式的描述:“大暑船,每年一度,渔民集资做一、二丈长小船一只,船内置猪、羊、鸡、鸭、米、水缸、扛灶等物品。于大暑日点上香烛,集体诵经送船,如船顺潮漂入海洋,则为大吉大利。如船出海门关后,遇猛烈东风不能东进,涨潮时又回关内,则为不祥之兆。”[注]陈志超:《椒江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29页。
在江浙沿海每逢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即“地藏开眼”日有“送法船”仪式。“法船”又称“水灯”,一般是用竹条搭成各种形状的灯架和船架,然后裱糊上白纸,点缀各种彩色纸图案。“送法船”活动在清代便流行于江苏沿海一带。据雍正《江浦县志》记载:“僧舍设斋荐亡,夜放水灯,曰盂兰盆会,是月值大尽,谓地藏开眼,僧家以纸为法船,乡人纳禇钱寄船焚化,谓上法船。”[注](清)项维正:《(雍正)江浦县志》卷1《风欲》,清乾隆重修本,第138页。“法船”一般放入与大海相通的河流中,有驱疫去灾之意。在江苏的海州沿海,有“放河灯”的习俗,应为“送法船”仪式中的一种,人们用芦苇竹片扎成纸船,装上纸钱,点上油灯,放入河道漂流,从而送走灾祸。[注]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 ·民俗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8页。
综上所述,江浙沿海历史上存在四种“送船”仪式,分别是“送彩船” “送纸船”“送大暑船”和“送法船”仪式。“送船”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仪式中都涉及江海、木船或纸船,以及瘟疫灾厄这几个重要元素。从送船形式上看,它们与“送瘟”仪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看作“送瘟”仪式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表现。
二、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源流探析
(一)仪式流程
“送瘟船”至少在北宋时就已见于内陆的两湖地区。如北宋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提到:“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擢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注](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6页。这种以“草船浮水”进行 “送瘟神”的巫术仪式可视为江浙沿海“送船”活动的雏形。
北宋庄绰的《鸡肋篇》记载了宋代湖南澧州地区的“送瘟船”仪式,其仪式流程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的“送彩船”仪式类似。[注]徐兢在宣和六年(1124)奉使归来的第二年,即1125年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鸡肋篇》则成书于绍兴三年(1133)。两书的成书年代相差无几,因此所描述的“送船”习俗应同时代存在于两湖地区和江浙沿海,而沿海的“送船”习俗来自于两湖地区的可能性更大。“澧州作五瘟社,旌旗仪物皆王者所用,惟赭伞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轻木制大舟,长数十丈,舳舻樯柁无一不备,饰以五采。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事之类为状,以载于舟中,浮之江中,谓之送瘟。”[注](宋)庄绰:《鸡助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2页。文中的“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事之类为状”与“送彩船”中的“载佛经、糗粮,书所载人名氏”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知,宋代沿海“送彩船”禳灾的习俗应来源于两湖一带的“送瘟船”习俗。
早期的“送瘟”仪式应主要由道士来完成,元末明初时编纂的道教类书《道法会元》中就收录了现存最早的遣瘟送船科仪文本——《神霄遣瘟送船仪》。其中记载了瘟疫醮的起源、流程、神祇、法令及疏文等诸多内容。这些仪式流程与今天江浙沿海地区盛行的“送船”仪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神霄遣瘟送船仪》中“焚船”部分谈到“送瘟”的去处时有“行莫回头,去毋转面,张帆鼓浪,齐等楚岸之舟”[注]《道藏》第30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l页。的内容,历史上的“楚地”大致是指两湖流域一带。这与《岳阳风土记》和《鸡肋篇》中记载的“送瘟船”地点大致相同。因此,《神霄遣瘟送船仪》可以看作是对两湖地区“送瘟船”仪式的系统记录。
《神霄遣瘟送船仪》中记载的“送瘟船”仪式内容大致如下:
步虚,咒水洒净。毕,默念:天无氛秽,地绝妖尘。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一如告命。
次炷香启告云:九天之上,惟道独尊。……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六天洞渊大帝,伏魔天尊,神霄启运诸大祖宗真君,……同赐来临,受今关白。辄以香茶,表诚供养。
献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以令结造华船,敬神伸拜,……请起瘟司行化王神卦,中占出一切等鬼,请上华船,受今拜送。……令人捧船于患室,或厅上,仍具酒牲祭仪于船所在,然后祭献。香烟散彩,瑞气浮空,……手焚香重申奉请,神霄真王大帝,洞渊三味太一天尊,法府上圣高真祖师,帅将本家,香火司命六神,降赴船莚。……再焚信香虔诚奉请,天瘟地瘟二十五瘟神君,天蛊地蛊二十四蛊神君,天瘵地瘵三十六瘵神君,降赴华船,受今拜饯,次焚信香虔诚奉请。……辄敷文疏,上渎圣聪。
宣疏。文疏敷宣,圣聪必鉴。……今有某结造茅舟一舫,请迎瘟部众神,出于十字路头,虔以三牲酒礼,敬伸祭送,用保平安。……请离此席,毋辄趑趄。奉送行轩,遨游前迈。
焚船。存前光后暗。送神舟出门,到化船所。念云:神本无私,默运感通之理。人能有请……。一切鬼神,以今奉为。某特备酒牲凡仪,敬伸祭奉,仰惟洋洋在上,济济齐临……。以净水洒于祭仪上,念化食咒曰:天洞天真,玉液成琼……。备以画船,装载经幡钱马等仪,敬伸焚化,奉送。……摄毒收瘟,引领一该之众,流恩降福,甦生数口之家,行莫回头,去毋转面,张帆鼓浪,齐等楚岸之舟……。焚化,望燎左手,飞南斗一座,存六星光芒,炎炎如火,铃之状,念咒曰:火铃炎炽,洞焕八方。万神侍卫,永断不祥。急急如丹天流金火铃律令。[注]《道藏》第30册,第370-37l页。
在整个仪式中, “焚香祷告”这一环节是为请众神仙协助驱除瘟疫。而“献茶”和“宣疏”是将各路瘟神礼送上船。最后“焚船”是将载有瘟神的船焚化,送走各路瘟神。
“送大暑船”仪式与《神霄遣瘟送船仪》记载的“送瘟船”仪式有很多契合之处。据顾希佳对“送大暑船”的考察,大暑船在制作完成后,会在其放置的五圣庙里做道场,由道士来念诵《瘟司御灾治病宝忏》,这类似于《神霄遣瘟送船仪》中的“次炷香启告”。在大暑前一天,人们会去请当地的几个地方神到五圣庙中,又名“迎圣”[注]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载《民俗研究》2001年第4期,第33页。。这和“献茶迎圣”类似。在大暑这一天,地方长官到江边主祭,并当场宣读祭词。然后道士会把“五圣”从五圣庙中请到船上。最后用筏子将大暑船拖到海口烧掉。[注]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37-39页。这就如同《神霄遣瘟送船仪》中的 “宣疏”和 “焚船”环节。关于“送大暑船”与“送瘟船”习俗的联系,清代文人俞樾就有注意到:“余从前客休宁汪村时,每年四月间,有打标之俗,亦所以逐疫也。糊纸为船,无物不具,但皆以纸为之耳。焚之野外,云送之游西湖,俚俗相沿,可发一噱。……临海之船,竟是真船,宜其灵异更著矣。”[注](清)俞樾撰,徐明霞点校:《右台仙馆笔记》卷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2页。俞樾记载的“糊纸为船,焚之野外”的习俗应为“送瘟船”习俗。他认为内地的瘟船习俗和“送大暑船” 俚俗相沿,只不过内地的“送瘟船”是糊纸为船,而沿海的“送大暑船”用的是真船。
除了大暑船外,温州沿海的“送纸船”仪式也与《神霄遣瘟送船仪》所记载的相似。据清代钱塘孙雨人的《永嘉闻见录》记载:“永嘉晴雨无常……。瘟疫流行,民间必互相敛钱建道场,作佛事,或三日或七日。预设大纸船一只,内实纸钱冥帛无算。俟佛事毕,将船载至海口,用大木板置纸船于上,点火焚之。乘风入海。不知所往。群以为瘟鬼送去,疾可愈矣。”[注](清)张宝琳:《永嘉县志》卷6,《风土志》,清光绪八年刻本,第579页。由上可知,温州沿海的“送船”仪式和“送瘟船”仪式一样,也有类似 “焚船”环节中的“装载经幡钱马等仪,敬神焚化”。又据1891年《申报》对“送纸船”仪式流程的描述:“就东瓯王庙大殿设罗天醮七昼夜,纸扎大小神船五艘,舁四大天将、陈府、杨府、庄济、勇南王、府县城隍诸偶像到坛,并奉东岳忠靖王像出游,事毕送船出北门。”[注]载《申报》1891年11月6日,第6662期。可知,“送纸船”是在东瓯王庙进行,其仪式流程为先将制作的纸船安置在庙前。后居民将府县城隍、勇南王、庄济王、忠靖王等塑像抬到东瓯王庙,再由主法道士率领醮坛司事,由三清传令忠靖王驱逐瘟疫。届时忠靖王开始巡行四方,到各街巷驱瘟收疫。这些仪式流程与《神霄遣瘟送船仪》中的描述相似,奉东岳忠靖王像出游其意义在于收瘟与祈安,相当于《神霄遣瘟送船仪》中的“宣疏”环节,最后“送纸船出海”和“焚船”的内容也与《神霄遣瘟送船仪》中“送神舟出门,到化船所”的记载相符。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江浙沿海的“送大暑船”和“送纸船”与《神霄遣瘟送船仪》在流程方面有以下几个相似点:第一是按真船的比例制作瘟船,船上放置纸扎的瘟神;第二在道士做法后举行巡游仪式;第三是瘟船巡游时有“驱瘟之神”一起巡游;第四是瘟船送到江河入海口,众人将船焚化后随风入海。鉴于《神霄遣瘟送船仪》是已知的最早出现的遣瘟科仪文本,因此它们都可能是由《神霄遣瘟送船仪》发展而来。
由上可知,江浙“送船”仪式不仅与内陆“送瘟船”仪式的流程基本类似,而且在禳灾除祸、保境安民的核心宗旨方面也与其一脉相承。
(二)祭祀内容
江浙“送船”仪式在内容方面也体现了“除瘟”的寓意。古人多以“米”代表天花,“杂豆”则代表麻疹。因此将代表瘟疫的米豆抛于流水中,以表达将瘟疫驱除之意。如《艺文类聚》引《龙鱼河图》曰:“岁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头少许发,合麻子豆著井中,祝敕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温鬼。”[注](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53页。这里的“合麻子豆著井中”是为了防止伤寒等瘟疫,说明汉代就有以粮食辟瘟神的传统。明代《武陵竞渡略》中更有将桃符、兵罐掷于水中的记载。“桃符能杀百鬼,乃攘灾之具。兵罐中所贮者米及杂豆之属。”[注]《古今图书集成》之《端午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36页。可知在明代端午竞渡这种“断瘟”仪式中,也有将米豆抛于流水中的内容。[注]江绍原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认为端午竞渡为公众禳灾方式中的一种;姜守诚在《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一文中也认为端午竞渡出于逐送瘟疫的本意。本文这里就不再做赘述。
江浙“送船”仪式中也多在船中装米、豆等粮食。如“送彩船”中会在小船中“载佛经、粮食”,这里的粮食有贿赂鬼神,以求航海平安的意义,但笔者推测最初应从代表瘟疫的米豆发展而来。大暑船中粮食的瘟疫象征意味更明显。如清人俞樾提到大暑船上,“米谷豆麦,备御之具如刀矛枪炮无一不备;惟盛米之袋甚小,仅受一升,而数则以万计,皆村民所施也,……又福建某处有卖米之牙行,一夜有叩门以米来售者,担夫数十人至船中起其米,达日而米未尽。米袋大如五石瓠。……天明视之,则小如碗耳。有父老识之曰:‘此临海大暑船中米也。’即日疫疠大作”[注](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12,第212页。。由上可知,大暑船中的米相当于瘟疫,当船上的米回到城中,就会导致城里瘟疫发作。
“送法船”仪式中也有置粮船中的内容。崇祯《松江府志》记载了江苏沿海的“送法船”习俗,“(七月)晦值三十日,相传为‘地藏开眼’。又寺僧造纸船,……男妇多以钱、米、豆、麦、棉花少许,寄置其中为趁船,以祈生方西渡。至夕,作梵事而焚之”[注](明)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明崇祯三年刻本,第693页。。可知在“送法船”中也装有米豆等物,这里的米豆虽是作为鬼神的祭品,但其原意也应是禳灾除瘟。综上分析,江浙沿海“送船”习俗在仪式内容方面的“除瘟”特征明显。
(三)神灵和传说
早在晋代(265-420)便有记载瘟神的《女青鬼律》与其后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女青鬼律》成书约为公元4世纪,其中有“五方鬼主”的记载:“东方青炁鬼主姓刘名元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南方赤炁鬼主姓张名元伯,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炁鬼主姓赵名公明,领万鬼行注炁之病;北方黑炁鬼主姓钟名士季,领万鬼行恶毒霍乱心腹绞痛之病;中央黄炁鬼主姓史名文业,领万鬼行恶疮瘫肿之病。”[注]《道藏》第18册,第250页。从文中可知,在晋代便初步形成了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钟士季和史文业的五瘟神架构。大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420-589)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也有记载:“又有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李公仲、史文业、钟仕季、少都符,各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注]《道藏》第6册,第41页。根据《女青鬼律》和《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关于刘、张、赵、钟、史五位神祇的记载,可以推断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五瘟神”的神位和神格就已形成。
成书于明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了宋元以来民间的神道风俗传说。其中对“五瘟神”的来历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此是五名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上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注]阙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江浙送暑船仪式中供奉的“五圣”其原型应为历史上的“五瘟”之神,据“送大暑船”仪式中五圣庙内做道场的道士所吟诵的《瘟司御灾治病宝忏》手抄本记载:“五圣原为江西省安庆府浮洋(梁)县人,结义五姓,张、刘、赵、史、钟,兄弟同科,得中五进士出身。”[注]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43-44页。其中“五圣”的姓名与“五瘟神”相似,因此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在“五瘟神”的基础上衍变而来。[注]据2015年7月21-23日笔者在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所做的田野调查,清代葭沚一带大暑前后瘟疫流行,因此当地居民将原本作为瘟神的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史文业、钟士贵奉为“五圣”,以求祛病消灾。这也说明江浙“送船”仪式中的传说与瘟神传说的故事内核基本一致。
除了传说的相似性外,“送船”仪式中供奉的神灵也与瘟神相关。其神灵多有为民服瘟的经历。如“送纸船”仪式中的核心神灵为忠靖王。忠靖王即江浙一带居民信仰的温元帅温琼,传说中他为救民而取瘟药自服,因此受到广泛敬拜。据《平阳县志》记载:“王读书玄帝行宫,……一日斋居闻剥啄声,启视则二青衣童捧箧衍,云是瘟药千丸,奉上帝敕投之井,疠此一方人,君行高幸无饮此,王闻疾,探丸仰天,面北罄吞尽药,须臾腹痛面青,顿易前相,是盖以一身而拯万姓之命者说。”[注](民国)符璋:《平阳县志》卷47《神迹列传》,民国十四年铅印本,第1896页。可知温元帅因救民服瘟药而亡。笔者推测,“温”与“瘟”谐音,在《神霄遣瘟送船仪》中,“元帅”多指押送“瘟神”赴船的神灵,如“天符都天正元帅、地符押瘟副元帅”[注]《道藏》第30册,第37l页。等,因此“温元帅”意谓驱逐各种瘟疫的大元帅,这本身就寄托着一种除瘟的意愿。
闽台地区“送王船”中也供奉有驱瘟神王爷,如作为王爷之一的池王爷。据《泉州市区寺庙录》中的记载,池王爷名梦彪,为开封人,唐高祖时任太守。在任时与化为士人的瘟神结为朋友。一日,瘟神告诉他奉玉帝之命要在其地传播瘟疫,池王爷将药骗来倒入自己口中,为民而死,全城百姓因感其德而建庙祭祀。[注]泉州市区道教研究会编:《泉州市区寺庙录》,泉州: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1996年,第114页。
可见,江浙沿海“送船”仪式中的传说是在“五瘟神”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成,“送船”中涉及的神灵也与内陆瘟神相关,这充分说明仪式中的“送瘟”因素。
综上所述,江浙沿海的“送船”仪式与古代“送瘟船”仪式相比,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衍变,但其外在形式、科仪流程及核心内涵等方面都还保留着“送瘟船”的影子。
三、江浙其它地区的“送瘟船”活动
在江浙的内陆地区,也有大量“送瘟船”活动,可以看做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雏形。如在扬州地区,每当夏季瘟疫流行,会抬都天神像巡游,“彩纛经过之处,观者争以茶叶钱米抛掷船内,谓之送瘟船”[注]《驱疫染疫》,载《申报》1895年8月21日,第8023号。。在江苏盱眙,五月初五日,人们会扎上纸船,并抬上降福菩萨像巡游,居民届时会将米豆等类粮食撒在船内。最后,将纸制瘟船投诸淮河,如果船顺水下行,则无瘟疫。[注]齐涛:《节日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95页。
在杭州地区,每逢瘟疫,则“建醮坛,礼斗诵经,以禳疫疠”,并“每晚请元帅令箭一枝,巡行街坊一次,名曰搜瘟,圆满之夕,并备纸船纸马,用元帅文牒至各处焚化”[注]《西泠禳疫》,载《申报》1895年9月14日,第5047号。。这里的元帅也是温元帅温琼。在浙江内陆的丽水地区,有抬温元帅巡行的拖船节。据《遂昌县志》:“社后卜吉设醮作乐,呼拥鼓吹,升温元帅周巡四隅,以童子作优伶状,高升而行,谓之台阁。拖船于市,以逐疫。”[注](清)胡寿海:《(光绪)遂昌县志》卷11,《风俗》,清光绪二十二年刊本,第1169页。“拖船”亦称“瘟船”,指运送瘟疫恶鬼的船只,因仪式中船需在地上拖行故称“拖船”。“拖船”的队伍巡遍主要街巷后,会在河边将“拖船”火化,表示温元帅已将一切瘟神鬼魅全部赶出本境之外,从此合境平安。
从江浙内地的“送瘟船”祭祀中可以看出,这里“船”只是作为瘟神乘坐的工具,其中以纸和竹木制成的“纸船”为最多,与今天江浙沿海地区流行的“送船”习俗相比,两者的基本程序极具相似性,故二者之间存在地域上的承接关系。江浙腹地的“送瘟船”可看做中国内陆“送瘟船”仪式与江浙沿海“送船”仪式之间的“过渡型”。今天江浙沿海的“送船”仪式更为繁复,当系在海洋环境下沿海居民根据自身需要不断增衍所致。
四、“送船”习俗在沿海的演变
由上文可知,江浙沿海“送船”习俗源自于内陆的“送瘟船”习俗。与内陆的“送瘟船”相比,其意义和内容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异,但“送瘟”的核心仪式和内容都没有改变。如今沿海“送船”仪式中的“瘟”已是指代航海中的各种危险,“送船”向攘灾的祭海方向发展,成为了海洋渔民的特色习俗,其功能从“驱除瘟疫”延伸到了保护航海平安,仪式中的瘟神也被赋予了海神的功能。
在江苏沿海的海州湾,“送彩船”成为渔民送走厄运,保障海上平安的特殊仪式。渔民的海船如果在海上受了损伤,尤其是在海上出事死了人,归来后要用纸做一小船放入海中任其漂流,意为原来出事的船重新成为清洁的船只。否则,这条船第二年就不能出海作业。[注]江苏省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连云港市志》(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2563页。
在浙江的海岛地区,“送纸船”已成为渔民的常态,只不过仪式的规模和船的大小进行缩减。如在浙江象山东门岛,岛上人如果遇到瘟疫,就会做一只小木舟,在退潮时让它漂走。小木舟大约长1.5米,船上设有棚帆,并有用纸扎成的人物和长枪等,木舟之中还会放上做饭的锅和油盐。“送船”当夜人们会到城隍庙“请酒”,摆上一桌酒和菜,以求鬼魅吃过以后早早离开。[注]刘铁梁:《东门渔村的神庙祭祀与村民合作》,载《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以此来保障出海的安全和捕鱼的顺利。
在“送船”习俗中受海洋文化影响最明显的应是“送大暑船”,今天的“送大暑船”习俗已经成为台州沿海渔民渔休节的一部分,制作精美的大暑船与其说是驱除瘟疫的载体,不如说是渔民对渔业丰收的期盼。一些渔民甚至已经忘记“送大暑船”驱瘟的原意,认为“送大暑船”是为了向东海龙王朝贡,从而使生命财产减少损失。[注]政协浙江省椒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椒江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第131页。
江浙沿海的“送法船”,即“放水灯”活动如今也在海岛渔民中盛行开来,并演变成为一种祭海仪式。在地藏王诞辰日这一天,温州洞头海岛的每个渔港岙口都会请来道士在滩头作法,然后点燃水灯,让潮水把“瘟神”送出远海,以祈求村境平安,渔业丰收。[注]洞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洞头县文史资料 》第3辑,1993年,第69页。在舟山群岛,每逢中元节,渔民也会在海上“放水灯”,焚烧冥币,送走野鬼,以保出海平安。[注]《中国海岛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岛志·浙江卷》,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年,第467页。
“送瘟船”中的驱瘟神,在渔民的需求下,也被赋予了海神功能。在浙江台州沿海流传着许多关于“五圣”在海上帮助渔民解除险情、送水送粮的传说,类似于闽台一带渔民关于妈祖的信仰传说。[注]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31页。在每年农历“送大暑船”这一天,来自浙江温岭、玉环、路桥、临海、三门等沿海地区的渔民都会汇聚到浙江台州椒江江边祭拜“五圣”。[注]顾希佳:《中国节日志·渔民开洋谢洋节》,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62页。在送船仪式中一些瘟神的位置如今也被海神取代。如在浙江沿海苍南县的“送纸船”仪式中,妈祖充当了驱瘟神的角色,制作的仿真大船会先放置妈祖宫庙前,再请和尚诵经,然后将祭品装入纸船内,一起送到海边焚烧。[注]金亮希:《苍南与妈祖信俗情缘》,载《海峡两岸·传统视野下的妈祖信俗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328页。浙江花岙岛的“送水灯”仪式则在圣母娘娘庙前进行。渔民在庙前沙滩上施放水灯,祈求天后娘娘保佑海上船只太平。[注]黄浙苏:《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相似的情形还有闽台的“送王船”习俗,在今天的台湾,“送王船”中的王爷已转变其功能,“成为渔民崇拜的海神”[注]严安林编:《台湾神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今天江浙沿海“送船”习俗在仪式方面更多地体现了海洋宗教仪式的成分,与内陆的“送瘟船”习俗相比,船从瘟神乘坐的工具变为海洋船只的象征,表现了沿海居民在海洋环境中,根据自身的心理需求对“送瘟船”这种内陆习俗进行的再创造。但在这种再创造中也基本承袭了“送瘟船”的仪式构架,以船送疫入海的核心内容没有变,整个仪式表现出海洋习俗和陆地习俗相互交融的特点。这说明“海洋世界不是封闭的社会人文系统,始终和陆地世界发生互动的关系”[注]杨国桢:《论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载《中国海洋报》2005年7月26日第3版。。
结 论
通过对江浙沿海“送船”仪式的考察,我们对“送船”仪式的来源、传播途径和宗教属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送船”习俗的来源方面,学术界目前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航海者在航行中的“送彩船”是“送船”习俗的基础和来源。[注]如李玉昆认为“送王船”仪式源于古代航海者放小舟、彩船之举。(李玉昆:《略论闽台的王爷信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9-127页。)毛伟以闽台王爷信仰中的“送王船”为例,说明“送船”源于古代“送彩船”这种航海者善待遇难者的仪式。(毛伟:《闽台王爷信仰的人类学解读》,载《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56-163页。)廖大珂则以厦门的“送王船”为例,说明航海者在旅途中祈求神灵保佑海上平安的“送彩船”是“送船”仪式的基础和来源。(廖大珂:《略论厦门的“送王船”信仰》,载《海洋文化与福建发展》,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年,第229-235页。)另一种观点认为“送船”习俗源于古代攘瘟除疫的“送瘟”习俗。[注]如杨国桢认为“送船”习俗虽然与海有关,但其本意是“送瘟神”。(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姜守诚以闽台“送王船”习俗为例,说明两宋时期江淮及两湖流域民众中流行的“祀瘟神”与“送瘟船”是“送船”习俗的雏形。(姜守诚:《试论明清文献中所见闽台王醮仪式》,第249-255页。)顾希佳认为浙江台州沿海的“送大暑船”习俗源于“送瘟神”习俗。(顾希佳、陈志超:《从大暑船到渔休节——台州湾渔民信仰民俗嬗变的考察》,第29-53页。)第三种观点认为“送船”习俗源自佛教盂兰盆会法事中的“送法船”。[注]如蔡亚约和杨英杰认为早期的“送王船”来自于“放水灯”仪式。(蔡亚约:《闽台送王船》(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3年,第36页;杨英杰:《中外民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6页。)文海则指出浙江台州的“送大暑船”实际上是“放水灯”的发展和演变。(文海:《流变的民俗——葭沚民俗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从江浙沿海“送船”仪式的流程和神明传说中可以看出,“送瘟船”应是江浙“送船”仪式之滥觞,二者存在纵向上的演化关系。
在“送船”习俗的传播路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樱井龙彦认为“送船”原本起源于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后来沿着河传到内陆地区。[注]樱井龙彦:《关于在环东海地域使用船的“送瘟神”民俗》,载《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第60-68页。这种“送船”习俗源自沿海的观点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注]如王国宇认为“送船”习俗是通过沿海的古越族带到内陆的。(王国宇:《从民俗文化看水族的源流》,《百越史论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92页。)除此之外,持 “送彩船”说的学者也自然倾向于“送船”习俗源自沿海。而持 “送瘟”说和“送法船”说的学者则倾向于“送船”是从内陆向沿海传播的。从江浙沿海“送船”习俗的发展传播路径中可以看出,沿海“送船”仪式发源内陆的“送瘟船”,其传播途径应是从内陆到沿海,随着海洋文化因素的增加,瘟神逐渐具备了船神和海神的性质,最初仅是作为瘟神交通工具的“船”也被赋予了保护海上船只航行平安的含义。
在“送船”习俗的宗教属性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送船”仪式的起源与佛教信仰有密切关系, 而与瘟神信仰无涉。[注]廖大珂:《略论厦门的“送王船”信仰》,第230页。持“送法船”说的学者也将“送船”视为佛教盂兰盆会法事的流变,而持 “送瘟”说的学者则认为“送船”仪式的道教成分居多。[注]如学者姜守诚认为“送船”仪式来自道教神霄派的遣瘟送船仪。(姜守诚:《明代《武陵竞渡略》检视闽台“送王船”习俗的历史传统》,第75-87页。)从江浙沿海“送船”仪式的佛道属性中可以看出,“送船”的法事活动以道教仪式为主,其中涉及的神灵也多为道教神灵,但同时也伴有佛教的因素,如“送船”仪式有时由道士主持,和尚诵经[注]据2015年7月23日笔者在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所做的田野调查,“送大暑船”仪式在五圣庙由道士主持,但当放船时,有和尚与佛教信徒口念佛号送船;此外,一些信徒把去五圣庙迎接“五圣”称为“接佛”,可见“送大暑船”仪式中的佛道界限并不明显。,这说明了“送船”仪式佛道兼容的特性。
综上所述,“送船”仪式乃系内陆“送瘟船”仪式和海洋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今天的“送船”既是人们对于送走灾祸,合境平安的期望;也是为了给危险的海上航行寻求一种超乎自然力量的庇护。这说明民间信仰中的习俗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而是不断演变的,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