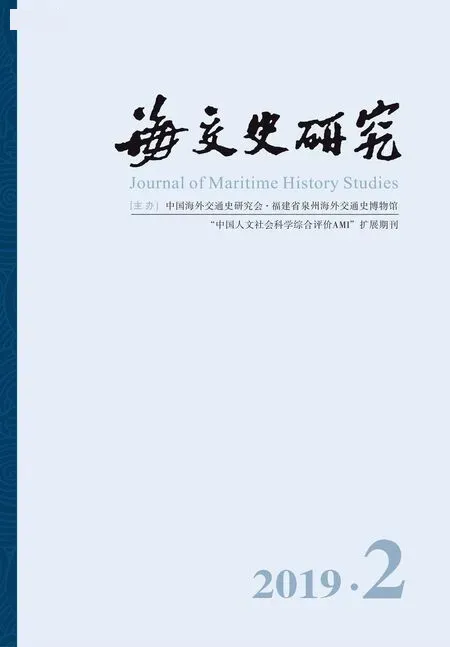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中的倭寇描写及明代史观析论*
郭尔雅
在描写倭寇的文学作品中 ,陈舜臣(1924-2015)的《战国海商传》堪称是从“重商主义”的角度进行切入的代表之作。《战国海商传》是陈舜臣以16世纪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贸易的海商(史称“倭寇”)活动为中心所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明代的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明政府以及当时的海禁政策和相关举措的一系列时代局限性,呈现出一种较为客观中正的倭寇观、海禁弛禁观以及商业观。而正是由于对明政府本身的局限性的认识,陈舜臣在小说中又虚构一个以“曾伯年”为首的反明势力集团和一个以明代藏书家范东明为原型的退隐士大夫,让他们对明代的商业和政治做了一系列的思考与设想,乃至为了其理想中的商业环境和政治环境做出一系列与政府政策相悖甚至相对抗的行动,反映出作者自身独特的明代史观以及贸易观、政治观。
一、从重商主义立场出发彻底否定明朝的抑商政策
在《战国海商传》中,陈舜臣对于明朝的政治进行全面的否定,这种否定,上至帝王下至官宦,包括政令律法,甚至国家体制都包含其中。而这样彻底的否定,则为其后续的“倭寇”描写与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对于帝王,陈舜臣写道,正德帝即位后生活放纵,设建豹房,“起初因为喜爱异邦的音乐,在豹房集结了各地的音乐家”,后来则用来“蓄养西藏、伊斯兰、欧洲、东南亚等不同民族的人种”,宛如一个“巨大的人种展览会场”[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东京:讲谈社文库,1992年,第134页。,供自己游乐之用。而小说中的新吉就曾被蓄养在豹房,因而对正德帝极为了解:他是一个对异国充满着强烈憧憬的人,但“只是没头没脑地叫嚣着大海大海,但他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去往大海,他连他自己也不懂得。”[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第137-138页。陈舜臣以设建蓄养不同人种的豹房来表现正德帝的荒淫。事实上,明朝确实是历史上封建帝王与豪门贵族豢养动物的最鼎盛时期,京城内也多建有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鹰房等饲养动物的场所。历史上对正德帝所建豹房的用途也是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它是正德皇帝荒淫享乐的场所,也有学者认为豹房是正德帝治理朝政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总部。但无论如何,“豹房”确如其名,是蓄养豹子的,如朱国祯《涌幢小品》便有“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注](明)朱国祯撰,王根银校点:《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涌幢小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页。等关于豹房养豹的记录。从中可以见出养豹耗资巨大,这也或可证明正德帝的生活放纵。但史料中并无陈舜臣所说的正德帝在豹房蓄养各色人种的记载。
同时,《战国海商传》对于明朝国政腐败、贿赂成风的状况也有所表现。小说写道,嘉靖十八年,日本贡使上京之际,新吉认为:“北京的风纪与腐败的正德末期相比,也并无改善。”[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160页。而嘉靖帝则只求长生,故令大臣作青词以献,善写青词者方能得到重用。《明史·宰辅年表》统计显示,嘉靖十七年(1538)后,内阁14个辅臣中,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更有因不愿作青词而被流放的大臣,这使得朝臣皆以学写青词为业。善写青词的严嵩便极得皇帝信任,有野心的官员于是纷纷向严嵩聚拢,朝廷上下,贿赂成风,严嵩根据官员的贿赂金额多少选用自己中意的人,其中赵文华更是与严嵩结为干亲,从通政使升任工部侍郎。他们甚至利用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进行敛财,对他们来说:“北方的阿勒坦汗和南方的倭寇是明国最大的问题,而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敛财时机。”[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东京:讲谈社文库,1992年,第286页。范东明在供职工部时,就因阻止严嵩之子严世蕃贪墨公产而被廷杖。陈舜臣写道,在这个时期,“世人皆知,被廷杖的都是正义之士”[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26页。,而遭受廷杖也成了刚正之士警醒世人的唯一方式。就连日本贡使也深谙明朝官场的贿赂之道,宁波争贡之役便是由于细川氏以大量金银贿赂市舶司贸易监督官太监赖恩,获得优先贸易权,造成大内氏的不满而引发的。中国的海商集团更是与朝廷官员交往密切,小说所写的以李光头、许栋为首的新安贸易集团便通过贿赂朝廷官员以及宦官,拥有对日走私贸易的主导权。对于沿海商人与朝廷官员通过贿赂关系的勾结,作者借佐太郎之口说道:“非合法贸易商在朝廷看来就是“海贼”,至此,大部分海贼都向朝廷行贿,北京的宫廷一旦收受贿赂,就不再将其当作海贼。然而这种情况一旦被扭转,大部分海贼无法进行贿赂,他们便只能变成真的海贼,北京又会怎么做呢?应该会使用武力,开始大规模的取缔。”[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281页。显而易见,贿赂不仅成为一种普遍通行并且行之有效的潜规则,似乎也变成了维持走私贸易与朝廷海禁政策之间微妙平衡的手段。此外,海商、沿海豪族以及朝廷官员之间也形成一个行贿受贿的链条,海商以走私贸易的巨大利润引诱沿海豪族投资以人、船等财力和影响力,而后,沿海豪族以银钱上通朝廷官员,影响朝廷决策。就如陈舜臣所批判的:明国从下到上,层层贿赂,“这已是既成的秩序,虽然是坏秩序,可当事者却并不自觉”[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280页。。
除皇帝的昏聩、朝臣的勾结贿赂之外,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对明廷的政令乃至政体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关于海禁政策,作为一个商业主义的主张者,陈舜臣必然是支持海上贸易、反对海禁的,因而他在小说中对明廷严行海禁的举措自然颇多指摘,也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种种不解和不满。而且,陈舜臣认为明朝所面临的“南倭北虏”的忧患,便是起因于朝贡:“由于南北的对外纷争,使得明国疲于应对,国力大为损耗。北方是蒙古族,南方是日本人,虽然入侵的民族不同,但问题却同样都是明朝所说的朝贡。”[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400-401页。此外,他对明朝政治体制的质疑与批判,更是超越时代局限:“因为现在是完全的皇帝独裁制,皇帝想怎样便能怎样。然而我们不能保证一个皇帝永远是明君。只有对于明君,皇帝独裁制才是好的,但是,如果遇上昏君,就不好说了。因此,需要确立一个皇帝虽然拥有权力但也不能破坏的体系,那就是‘法’。”[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15页。
明朝政治固然腐败,然而陈舜臣在小说中的描写也是极具倾向性的,他对皇帝偏听偏信、官员腐败贿赂的批判,最终还是指向了与他最关心的海上贸易相关联的海禁政策上。在他的描写中,官员的贪腐与皇帝昏庸独裁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便体现在海禁政策的严苛和对海外贸易的管制打压之上。事实上,对于海禁政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朝贡贸易,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学者,只要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时,必定是持贬斥态度的。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在中国产生的必然性。
在欧洲,如埃里克·琼斯《欧洲奇迹》所说,由于肥沃的土地在地理分布上缺乏连续性,故而在分散的土壤肥沃地区形成了分散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从而形成欧洲多元的政治体系,而诸多独立的政治体系之间都存在着强烈的竞争性,同时也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这就造成西方重视商业利益并在竞争中谋求生存的国际贸易观,也使得“重商主义”成为西方各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基本思想。[注]参见[英]埃里克·琼斯著《欧洲奇迹》,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85-120页。重商主义主要是以国家强大为指向,以货币(金银)为财富的象征,以对外贸易为获得财富的重要途径,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国家致富的经济思想。其中重商主义所坚持的国家干预实质上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商人开拓国际贸易甚至以武力进行贸易扩张的支持之上。
而中国却很早就实现了统一,邻近小国也完全不具备与之竞争的能力。同时,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属性使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很低,这使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秉持着“重农抑商”的基本思想,坚持以农为本而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国际贸易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通过 “怀柔远人”来建立“华夷秩序”的一种政治手段,使得朝贡贸易成为维持“中国”与“四夷”关系的基本方式。与西方贸易扩张中的暴力与不平等性相对,中国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和平的关系往来,它不依靠武力征服,而是以他国对中华帝国的文明与商品的需求为保障的。通过朝贡贸易,朝贡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国则由此确立其宗主国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到了明代,中国甚至将所有贸易都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下,使得朝贡贸易成为唯一合法的贸易方式,因为朝贡贸易的本质不在贸易而在政治,所以中国不仅不支持商人进行海外贸易,甚至多番禁止,明代的海禁政策便是基于此而产生的。对此,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所谓的朝贡贸易,其实只是中国官员与外国贡使合力编演的“构建合法性和贸易欺骗的帝国游戏”,他们通过藩属使节的叩拜礼节与朝贡行为维持其“王朝对内权威的合法性”,藩属也因为由于贸易利益而非常乐于参与到这一欺骗游戏之中。[注][英]约翰·霍布森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此外,作为一个农本主义社会,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政府也必定会为了将大多数人附着在土地上而控制商人的规模、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商业活动,而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相比是更不可控的商业行为,所以政府必定会加以控制。
而陈舜臣作为一个出身商人之家,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影响并在自由贸易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面对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必定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对明朝的抑商政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将反明势力的起因完全归结到明朝对商人的限制之上,认为“这是对他们(明政府)轻视商人的惩罚,他们将为这个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贸易事业看得等同乞丐,就得受到相应的惩罚”。[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54页。显然,陈舜臣对商业贸易的态度是深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重视对外贸易、政府支持并保护商人进行国际贸易乃至贸易扩张是西方“重商主义”的重要内容,这也是陈舜臣在《战国海商传》中对海外贸易所持的基本主张和对政府的基本期待。所以说,陈舜臣对明代海禁政策的批判以及由海禁政策所引发的对明朝皇帝官员的贬斥,都是以“重商主义”为心理前提,或者说他至少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站在现代自由贸易的立场之上对明代贸易体系进行批判。
二、“反明”势力及“曾伯年”形象的虚构与作者的海上贸易观
在《战国海商传》中,陈舜臣基本遵循历史的脉络推进小说的情节发展,而他所安插的历史之外的人物与情节,则是反映其思想的重要道具,也是我们去究查其思想的重要线索。在小说中,陈舜臣虚构了一个以“曾伯年”为首的反明势力集团。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曾伯年”其人,而且这个反明集团也并不像历史上惯见的反政府势力一样靠武装夺取政权,而是主要通过商业利益的拉拢来扩充集团的势力,通过商贸活动对抗当权的统治,从而达到撼动甚至推翻明政府的目的。当然,他们的反明集团也并非没有武力装备,但那只是为了商战的需要。在商战或贸易中以强大的武装为后盾来达到震慑对手的目的是这一时期的商贸集团惯用的方式。小说从没有出现“曾伯年”集团与他所反对的政府官宪真刀实枪地正面对抗的场景,他最多只是怂恿他所拉拢的日本武装海商与政府为战。陈舜臣这样的设置,这样的描写,究竟目的何在?他想要借此表达什么呢?一方面,在作为“重商主义”者的陈舜臣看来,商业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足以抗衡甚至颠覆其政权与统治的存在;另一个方面,以商业为战的反明势力的设置,也是陈舜臣借以表达他对政府压制商业极端不满的方式。
由《战国海商传》可知,“曾伯年”本是泉州某名门的家主,明成化八年(1472),专管琉球进贡贸易的泉州市舶司被移往福州之后,泉州日益凋敝。为重振泉州,他曾向朝廷上书,请求再设市舶司,以失败告终。而新安(安徽、浙江、江西三省)商人却通过贿赂宦官,获得了与日本的贸易权。这使得“曾伯年”对明朝政府彻底失望:“朝贡形式以外的对外贸易都是非法的,这是明国的国是。但沿海各地的通商活动却极为繁盛,这些通商都属于走私贸易,是官宪取缔的对象,然而所谓的取缔,也不过是像想起了就应付一下一样,处于半公认的状态。这都是贿赂的结果。”而这样的贿赂,“已是既成的秩序”[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280页。了。至此,“曾伯年”走上了对抗明朝政府之路。虽然小说借“曾伯年”之口为其反明之路设置一个看上去极为合理的逻辑线条,即明朝政治腐败,整个国家从下到上,层层贿赂,皇帝昏聩,偏信奸臣,官员相互构陷,良臣蒙冤而死。然而追根究底,他走上反明之路的动因,依然是其增开市舶司、扩展海外贸易、兴盛泉州经济的设想破灭,到底还是商业利益的驱动。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之下,小说中“曾伯年”以整饬国家秩序的姿态,集结受当时明政府迫害的人,意图推翻明政府的统治。这其中,有受其祖先牵连而不能享有正常明人待遇的蒲氏一族,有因妨碍太祖统一天下而不被允许在陆上生活的陈友谅军团后人“九姓渔户”,以及比其他地方都负有更重的税金的苏州张士诚的后代。而他们动摇整个国家的砝码,便是商业,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与商业相关。他们利用发动商战、操控商圈的行动,对明朝的政府发起挑战并形成影响。为达成这一目的,“曾伯年”集团首先所做的,是以生丝为筹码对以佐太郎为首的日本海商的拉拢。“曾伯年”垄断了作为对日贸易主要输出品的生丝与绢织,这使得中国市场上以对日贸易为主的新安商贸系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海贼王直、日本海商佐太郎等也都因主要输出品被垄断而大受影响,于是佐太郎等人前往九日山,与“曾伯年”进行商谈。“曾伯年”借机拉拢佐太郎,将生丝与绢织全部交给他,但交换条件是他必须加入与新安商人的商战,并担任商战的总大将,对新安商人进行彻底的打击。于是,生丝与绢织从佐太郎手中开始流通,而“在生丝的买卖中,出现新的面孔,这意味着在一直以来的新安系商人之外,又出现一些小商人,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新安系商人的市场占有率显著减少。”[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322页。这里说的“小商人”,事实上就是“曾伯年”安插在生丝贸易市场上用以排挤新安商人的棋子,他们持有“曾伯年”供给的源源不断的均衡价格的生丝。“为了打击这些小商人,许栋及其背后的新安商人大规模地囤积生丝。然而不管怎么买进,生丝的市价都没有上涨。不仅如此,不知哪里一直在大量地供应着价钱便宜的生丝,这些小商人们一点都不困扰。而在小商人们抛空之后,生丝的价格突然大幅跌落。新安商人损失惨重。”[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322-323页。
“曾伯年”对新安商贸集团的打击,一方面是因为此前新安集团通过行贿获取对日贸易权的行为破坏曾家在泉州增开市舶司的计划,但更重要的,则是“曾伯年”意图通过打击新安商人来对朝廷施加影响。因为他深知新安商人在暗中与明廷至少是与宦官勾结紧密,如果新安商人的商权被夺,他们必定会再次借助明廷的力量打击对手。而这一次,“曾伯年”早有预谋地将佐太郎推到与新安系商战的前线,以生丝为饵诱其作商战的总大将,而他自己则隐藏在日本武装海商之后谋划布局、发号施令。同时,佐太郎的日本海商集团此前又与王直有所勾连,较之日本出身的佐太郎,王直对中国市场以及新安系统的了解自然更深入。所以在商战中,往往是王直与新安商人进行正面交锋,佐太郎则负责生丝的供给以及接受传达“曾伯年”的指令,这样一来,“世人都以为双屿帮的首领是王直,是他得到日本人和葡萄牙人的支持,掌握着事情的主导权。但是被看成首领的王直,实际上却并不觉得自己是首领,他只是按着佐太郎的指令行事。”[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323页。事实上,佐太郎也并不是指令的真正发出者,“买、卖、静观,佐太郎只是遵从着这样简单的指令行事。……一有指令,佐太郎就会告知王直。”[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322-323页。所有指令的发出者,其实都是“曾伯年”。但在新安系看来,与他们进行对抗的却是王直以及王直勾结的日本人,这也就暗合了历史记载中“倭寇”的构成成分。而新安商人通过贿赂请求明廷打压的对象也就变成了王直的海贼集团及日本武装海商,亦即明朝官方所说的“倭寇”。朝廷原本就有海禁政策在前,沿海私商,尤其是日本的武装走私海商本就是严厉打击的对象,加之那些收受新安集团贿赂的宦官对决策者乃至皇帝的怂恿,让明政府发兵出剿“倭寇”并不困难。这便是“曾伯年”策划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明政府若为此施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会动摇政权的基础,尤其是当下并不稳固的政权,这有可能导致明政府的衰亡。”[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282页。事实上,朝廷也确实因此派朱纨出剿倭寇以及他们盘踞的双屿港。但由于王直与佐太郎得到“曾伯年”送来的消息而提前迁出,双屿之战对他们并无任何损伤,反倒是新安私商集团因为贿赂之后的有恃无恐而迁入了双屿港,以至损失惨重。
整个行动环环相扣,从朝廷的决策到新安系商人的心理,从让政府出兵以动摇国基到将日本武装海商拉入自己的集团,“曾伯年”称得上是算无遗策。其实,佐太郎也一早就知道自己被“曾伯年”利用,而且他也深知:“对手不仅是新安商人,还有这个国家的主人,明王朝,一个巨大的国家。”[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282页。但是为了能够获取生丝以及生丝贸易中的利润,佐太郎依然走入了“曾伯年”的计谋与布局之中,这也明确地表达日本海商的立场,即为了商贸利益,不惜与整个明王朝对抗。而“曾伯年”集团也正是抓住日本武装私商以经济利益为上的心理,诱使他们与新安商人乃至明廷对抗。当然,如果将小说所写的以佐太郎为首的日本海商集团等同于史料中的“倭寇”,并站在政治角度去衡量的话,陈舜臣的这一描写不免有混淆倭寇的入寇本质,推诿倭寇劫掠行为的嫌疑,但正如笔者在《从“海商”到“倭寇”——陈舜臣〈战国海商传〉的重商主义倭寇观》一文中分析的,陈舜臣是站在商业主义的立场上看待倭寇的,因此小说也会处处显示出商业至上的观念。这一点也反映在“曾伯年”反明势力的所有行动中,他通过对生丝的垄断和适时的抛出将包括新安商人和王直、佐太郎的海商集团在内的整个生丝市场玩弄于股掌之中,乃至借此引发政府的军事行动,以达到动摇其政权的目的。当然他也如愿完成了对日本武装海商集团的拉拢,使日本海商成为其对抗明朝廷的前阵,也为策动日本武装海商进一步自发地向明朝廷发起战争催生可能。
而后,“曾伯年”集团所做的,便是获取沿海住民的支持,并彻底击碎民众对朝廷与官兵本来就所剩不多的信任。此时,以佐太郎为首的日本海商和以王直为首的中国海商都已经因为对日生丝贸易的利益与“曾伯年”的反明势力捆绑在一起,而“曾伯年”也正是试图通过掌控沿海商贸实现其推翻明政府的政治目的。他们意识到,“与官宪为敌,我们的对手是巨大的,几乎与“天下”等身,为了与此相对抗,我们必须尽可能增加我们的同伴”,而沿海的民众因为 “贫穷,渴望交易所得的利益的零头,当然就做了海商的伙伴”,“海商赚到钱,住民们也就有得赚”,于是,“金钱分散到他们那里,但官兵一来,就夺去那些钱财,官兵就是那样地强取豪夺”,这使得沿海住民“憎恨索取贿赂、为了威吓而严加取缔海商的官兵”。在官府的压榨和海商的拉拢之下,沿海住民自然会靠向海商集团,成为海商们“可供依恃的壁垒”。[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46页。而且,“曾伯年”集团对住民的拉拢,不仅表现在沿海,还延续到内陆,不仅表现在贸易中,还运用于与官府的战争中,“从沿海到内陆,加入我们的住民越来越多。……内地住民与我们结为同伴,与官宪之间的战争已经愈演愈烈”[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上),第53-54页。。
按照《战国海商传》所写,烈港之战后王直率倭寇攻打乍浦的行动,实则仍是由“曾伯年”集团所操控指挥的。他们作战的目的,依然是为了通过获取住民的支持而达成动摇明政府统治目的:“伙同住民——要动摇明王朝的统治,这是他们必须保持的基本姿态”[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165页。。为了伙同住民,他们首先便是粉碎民众对官府的信任。他们焚烧官有建筑物,闯入富豪家放火抢掠,激怒官府,使官兵对他们出手,“他们让住民们看到,四十个船男一拿着武器,明兵便仓皇而逃的情景,这无非是想要告诉住民,平时压榨他们的官兵实际上是何等的无能,一点都不足为惧”。而在平湖知县罗拱辰率数百官兵赶来乍浦之时,日本船又及时撤退了。因为“此次的目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告诉住民,明王朝的官宪是不可靠的。这一目的已经达到”[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167-170页。。而由于倭寇的四处焚烧抢掠,“明王朝会不得不因此而扩充武器装备,造成赋税加重,从而导致人心离散。”在这种情况下,而他们则“对住民施以恩惠。这是作战的根本目的。在乍浦收买粮食的时候支付数倍于市价的价格,也是因为遵从这一方针”。[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158-159页。
“曾伯年”的反明集团通过商业利润的引诱和对官民矛盾的激化将沿海住民乃至内陆百姓拉拢至自己一方以壮大势力,这样的设置其实也是符合明嘉靖年间的社会现状和历史规律。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本主义国家,百姓是最看重安定,只要政府官宪值得信赖,日常生活有所保障,他们是不会参与更不会发起动乱的。但是在小说所写的嘉靖时期,皇帝崇道,内阁纷争,宦官专权,厂卫横行,对于百姓来说,更重要的是皇室、官僚以及地主各阶层都剧烈兼并土地,以至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皇庄更是数不胜数,而农民则因为失去土地而沦为佃民。更有甚者,地主阶级还千方百计将自己应该负担的赋税徭役转加摊派给农民,加之政府的财政危机,朝廷又增加赋税,致使农民重荷难负甚至被迫背井离乡、辗转流亡。而对于沿海住民来说,朝廷的海禁政策使得他们的远海渔业以及在沿海贸易中的获利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他们向武装私商靠拢,这一状况反映在《战国海商传》中,便是迫于生存压力的沿海住民和内陆百姓对“曾伯年”反明势力的支持。
事实上,在嘉靖年间,有记载的农民起义就先后爆发了四十余次,此外,因缺饷而发生的各地兵变也有二十余次,想必也正是这些起义与兵变的记载为陈舜臣设置反明势力提供摹本。然而明嘉靖历史上的起义和陈舜臣所写的反明势力是有着极为本质的区别。陈舜臣设置的反明集团所处的社会阶层应该是商人,他们是通过商业利润来扩大集团势力和人员,通过商战来进行反明活动的。在中国,虽然重农轻商是封建社会的主流,但到了明代,政府对商人的法令制度以及商人的生存环境都是相对宽松的。明朝开国之初施行一系列恤商政策,例如对商税的征收:“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注](清)张廷玉:《明史》卷81,《食货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5页。并且还扩大了商税的免税范围:“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注](清)张廷玉:《明史》卷81,《食货志五》,第1975页。到永乐年间,明成祖又进一步扩大了免税范围:“凡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 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注](清)张廷玉:《明史》卷81,《食货志五》,第1975页。
这使得商人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加之明中期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手工业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的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的繁荣,各地奇珍异货的引诱和商业利润的刺激使得上至皇帝官僚、下至士卒百姓纷纷涌入经商浪潮,致使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普遍蔓延于整个社会。与此同时,士人与商人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商人习儒、追慕文雅、与士人交往渐密,甚至通过科举或者捐纳等经济手段跻身仕途,而士人中“弃儒就贾”的也不在少数。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商人手中集聚着大量财富,社会地位也有很大的提升,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进行反政府行动的充分理由与动力。事实上,明嘉靖年间确实也没有商人发动起义的文献史料记载。明朝甚至中国历代的起义与变乱,因发动者的身份不同有各种各样的名目,但不管是农民起义、士兵哗变、邪教作乱、土匪强盗、商贩作乱乃至民族纷争,其发起的原因无外乎日常生活难以为继或是巨额利润的驱动,当然其中也不乏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变乱。他们攻城掠地、抢盗库兵、释放囚徒,甚至设置百官、自立为王,达到不小的规模,但从没有一个反政府武装集团如陈舜臣所写的那样是为了替商人张目、建立一个政府保护之下的和平贸易环境而走上反动之路。因为那并不符合明代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语境,也就是说,在农本主义的中国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孕育出像西方那样在政府支持之下的海外贸易制度。“曾伯年”的反明集团所秉持的政治理想,只能说是陈舜臣基于自己在西方社会构成的影响之下赋予他们的的理想化设置。
三、“范东明”的形象虚实与作者的明代政治观
陈舜臣作为一个受西方体制影响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也明显将这一观念融入小说之中。在“曾伯年”的反明势力之外,他在明代著名藏书家范东明这一历史人物的原型之上进行加工,借范东明之口表达自己受西方社会体制影响形成的政治见解,并为范东明所建的天一阁赋予藏书之外的政治功用。小说写道,范东明为官十五六年,痛感明朝官场腐败、拉帮结派的现象,故此萌生退隐之心,并借为父丁忧之机建造藏书楼天一阁,想要将其作为一个国家法制化的研究所,让人们从书中汲取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而他为世人所熟知的酷爱书籍的形象,其实不过是为了免遭当权者的猜疑。
而历史上的范东明(名范钦,1506-1585)为官之时的确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曾因顶撞武定侯郭勋被廷杖下狱,最终在任职兵部右侍郎时遭弹劾“回籍听参”。回乡之后为了收纳其经年藏书,建天一阁。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之一,是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它为中国古代的藏书事业包括《四库全书》的编修以及书楼的修建提供有效借鉴,也是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因而对于范钦其人及其所建天一阁的研究众多,也有不少学者亲自登阁为其编撰书目。我们由此可知,天一阁藏书主要包括历代善本碑帖、各地方志以及一些借由官场之便所得的官书等内部原始资料,其功用便是藏书,也有学者认为它是范钦与友人的交游宴饮之所,但没有任何资料与研究可以证明天一阁具有陈舜臣所说的研究国家法制化的功能,甚至天一阁的藏书中关涉国政法制的书目也极为有限。而范钦的归隐也只是迫于被弹劾的无奈之举以及对官场失望之后的独善其身,并不是像其所刻画的那样是为了将国政法制化的蓄势待发。此外,范东明在小说中仅仅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帮助日本海商新吉与青峰救出佐太郎,第二次便是在佐太郎的会面中表达自己对国政的看法,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范东明亲近并帮助日本海商、批判明朝政治以及海禁政策的立场,然而,与其说这是范东明的立场,不如说是陈舜臣自己的立场。我们由天一阁所藏的明嘉靖刻本《范司马奏议》可知,范钦在任职兵道备和巡抚南赣时,外剿倭寇,内防动乱,终因剿抚倭寇有功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注]参见范钦:《范司马奏议》,明嘉靖刻本,第1-4卷。而被陈舜臣表述为海商、并与王直勾结的佐太郎等人,在明朝官方看来,就是倭寇,范钦对他们施以援助并与他们相交甚笃的可能性应该极小。另外,陈舜臣让范东明对明朝的“皇帝独裁制”作一番议论:“因为现在是完全的皇帝独裁制,皇帝想怎样便能怎样。然而我们不能保证一个皇帝永远是明君。只有对于明君,皇帝独裁制才是好的,但是,如果遇上了昏君,就不好说了。因此,需要确立一个皇帝虽然拥有权力但也不能破坏的体系,那就是‘法’。”[注][日]陈舜臣:《战国海商传》(下),第15页。
在陈舜臣的笔下,范东明是一个对国家政治敢于批判、对皇帝极权与法治的关系有所思考,甚至为建立理想中的“法”的体系乃至法制化的国家而付出行动的人。从对范东明的言谈举动的设置之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西方的社会制度、国家政体及其对权力的认识对陈舜臣的影响。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便对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充满警惕与戒备,亚里士多德在它的《政治学》中,通过对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政制的研究之后指出,与只依靠君主一人智虑的君主政体相比,由贵族集团或一部分人共同参与政治的共和民主政体更为可靠,而只有“法治”才是让人们平等参与政治的方式。他说:“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遵循这种法治的主张,这里还须辨明,即使有时国政仍须依仗某些人的智虑(人治),这总得限制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虑。”[注][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7-168页。这种以法律来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论调贯穿着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的始终。而他们对法律的依赖与对权力的忌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们对人性本恶的认识,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注][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第71页。在他看来,放肆地追求权力是比盗窃、寻欢等为饥寒与情欲所驱使的犯罪严重得多的最大的犯罪,而人一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会堕入对权力的放纵。因此他们将法律作为利器,来遏制人性、制约权力。而中国则不同,无论是儒家的性善与礼教治国主张,还是法家的性恶与制度治国主张,其最终都归结到通过对人性的教化和顺应去加强君主的权力。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研究焦点最后都会落到君主的身上,而权力对国家与社会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最后也都被归结到君主的品行修养上。人们坚信,同样的制度,尧舜用之则治,桀纣任之则乱。孔子也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注]刘兆伟译注:《论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89页。也就是说,人们把所有的权力都心甘情愿地奉于君主之手,而后又将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寄望于君主的盛德仁风,唯一能够制约帝王的,只有所谓的“民心”与“天命”,而这只是一种隐形的制约。这与“西方对政府权力久怀猜疑”[注][美]郝大维、安乐哲著:《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3-137页。,通过法治来限制统治者从而限制权力的做法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而陈舜臣让一个在整套儒家学说与君权权威的思想中为学、出仕的明代士大夫质疑皇权、质疑国家政制,并以藏书楼为名私自建立一个将国家法制化的机构,这是不符合历史逻辑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如果说陈舜臣虚构的“曾伯年”的反明势力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对明政府的统治产生质疑并进行反明行动,是作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倾向的潜移默化,那么他对范东明的形象加工则是直接在明代典型士大夫的身上嫁接一个具有西方政治观念的头脑,一个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尤其是明代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的头脑。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自秦汉以后均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在这种政体中,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世袭罔替的君位,君权更是不受制约、凌驾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任何权力之上的绝对权力,君主是集行政、立法、司法权于一身的。在行政权上,皇帝本身就是全国的行政首脑;立法权更是归于皇帝;对于司法权,皇帝则通过种种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到了明代,皇权专制更进一步加强,在皇帝的绝对统率之下,建立起一整套体系完备的司法机构,而皇帝不仅直接掌控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三个主要的中央司法机关,还通过三法司之间的权力分配和牵制来加强对其的控制,以此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此之外,明代皇帝为了严密监察司法官吏的活动,在唐宋御使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又设置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的监察机构,使得整个国家的监察权乃至司法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然而,皇帝仍然不能完全放心这些直接受命于他的司法机构和监察机构,于是另行组建由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及内行厂组成的厂卫特务机构,使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并赋予他们直接行使司法权的权力,开始对全国的特务统治。皇帝亲掌锦衣卫,而厂卫则交由整日侍其左右的心腹宦官统治,以达到将举国上下朝廷内外的官民动向皆收于眼底的效果,这一举措更加巩固了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在将一切权力都奉于君主并指望靠君主仁德的文化心理基础上,面对昏聩无德的君主,士大夫所能做的,除了顺从与劝谏,最多的便是彻底失望之下的辞官归隐。事实上,小说中的范东明便是选择归隐,而历史上的“范东明”甚至连主动辞官归隐都未能做到,而是被弹劾回籍。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以皇帝不能顺应天命民心为由而发起的反政府武装势力,但是他们也只是想要朝代更迭、皇权易位,而后重新将最高权力交与下一任君主。他们没有思考国家政体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更没有重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的意识。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尝有也。”[注]梁启超:《文集之九·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载《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0页。小说所写的明代,中国依然自恃居于天下之中,等待四方来朝,而没有与其他国家其他政体进行比较的意识,当然也无从比较,当时中国对西方政治方面的著述尚无译介,时人对政治的思考自然也只能局限在当时的、唯一的政治体制之内,他们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质疑国家政体并企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能力。而陈舜臣将范钦拔高到一个能够摆脱时代限制、对皇帝独裁制加以批判、对法制国家的建设提出构想并通过修建天一阁将其付诸实践的高度,同时也为天一阁赋予了超出其藏书功能的政治化功用,毋宁说这是陈舜臣借由范东明所表达的自己对明朝政治的思考,或者说是陈舜臣自己在西方政治三权分立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政治观念。
由上分析可见,在《战国海商传》中,无论是以“曾伯年”为首的反明势力的设定中所反映的海外贸易观,还是以藏书家范东明为形象所表现出的政治观,明显都是超时代、超历史语境的,表现作者陈舜臣在其“重商主义”和商贸自由思想的立场上对明代的商业政策以及包括“倭寇”在内的商业活动的思考,也是受西方政治体制和观念影响的陈舜臣对明代政治制度和历史现象的思考。其中不免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些视角的局限性、立场的僵硬性,尤其是对明代政治与海禁政策缺乏同情的理解,忽略其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环境之下这些政策与措施的历史必然性。陈舜臣《战国海商传》所表现的历史观与我们通常的历史观、特别是倭寇观的差异,为中国读者认识倭寇提供另一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