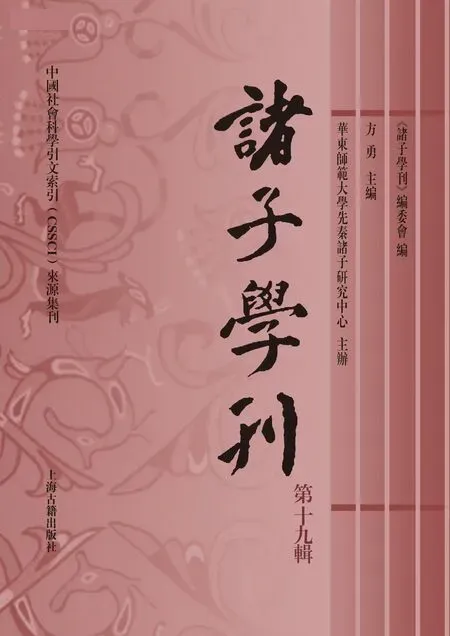梁啓超: 先秦諸子亦有 “教智之言”*
——梁啓超認識論思想簡論
蔡志棟
内容提要 “新民子”梁啓超充分結合先秦文獻,從認識對象、認識的基本過程、認識論的環節和認識能力等方面入手,全面地討論了真理何以可能的問題。對於整個認識過程,梁啓超結合《詩經》,將認識對象區分爲自然世界和人類世界。從這個基本區分出發,他批評了先秦法家在歷史觀上的態度,突出了歷史領域人的自由意志的積極作用。梁啓超認爲,認識自由的起點是實踐,他高度贊賞清代顔、李學派的“因行得知”論。在真理問題上,梁啓超也嚴厲地批評了朱熹的真理觀,主張回歸孔、孟的真理論。他認爲,真理也即認識自由的獲得不以知天下之事無巨細爲前提,而以認識主體自身特長之所在爲轉移。换而言之,即便在某一領域獲得正確的認識,也可謂獲得了認識自由。認識自由絶非要求你認識全天下所有事。在認識論的環節上,結合先秦諸子,梁啓超對科學方法論的内在環節、演繹法和歸納法、假設和驗證,以及群己之辯等,均有所涉及。對於認識能力,梁啓超除了對於一般的理性、經驗等表示其觀點之外,還討論了直覺、判斷力等當時不爲人所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 梁啓超 真理 先秦諸子 認識論 顔李學派
在晚年所作《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的演講中,梁啓超指出,“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横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説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絶對的不能承認。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説是有現代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没有反科學的精神”(1)梁啓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吴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六集),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0頁。。這段話明確地點出了梁啓超判斷先秦科學思想的基本立場。
他還認爲,墨學充分地討論了認識論的諸多問題:
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矣,《墨經》而已矣。《墨子》之所以教者,曰愛與智。《天志》《尚同》《兼愛》諸篇,墨子言之而弟子述之者,什九皆教愛之言也。《經上》《下》兩篇,半出墨子自著,南北墨者俱誦之,或述所聞,或參己意以爲《經説》,則教智之言也。《經》文不逾六千言,爲條百七十有九。其於智識之本質,智識之淵源,智識之所以浚發運用,若何而得真,若何而墮謬,皆析之極精,而出之極顯,於是持之以辨名實,御事理,故每標一義訓,其觀念皆穎異而刻人,與二千年來俗儒之理解迥殊别,而與今世西方學者所發明,往往相印,旁及數學、形學、光學、力學,亦間啓其扃秘焉。蓋嘗論之,《墨經》殆世界最古名學書之一也。(2)梁啓超《〈墨經校釋〉序》,《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五集),第3100頁。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先秦思想在認識論上毫無瑕疵。梁啓超指出,先秦思想缺乏邏輯思想“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3)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236頁。。
這一切均構成了我們討論梁啓超認識自由思想與先秦諸子關係的基本背景。
一、 主客、知行與有限的真理
認識自由的獲得,離不開對認識過程和認識環節的探討。在這個意義上,討論認識過程和認識環節就是在討論認識自由。
對於整個認識過程,梁啓超首先將認識對象區分爲自然世界和人類世界。他認爲,自然界存在着必然性或者説規律,可以通過實踐獲得知識。這個觀點是以事理統一爲本體論前提的,所謂“有物有則”。梁啓超認爲先秦時代的《詩經》表達了這個思想。他説:“《詩經》説:‘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是事物,‘則’便是理。(以秉持爲經常曰則,以各如其區分曰理。)‘則’存於‘物’中,舍事物而言理,便非聖賢所謂理了。”(4)梁啓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五集),第3146頁。
不過,這是梁啓超比較籠統的説法。在“有物有則”的論述中,嚴格地説,“何謂物”這個問題没有得到有效的闡釋。“物”既可以是自然界之物,也可以是人類世界之物(梁啓超分别稱之爲“自然系”和“文化系”(5)梁啓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六集),第3356頁。),後者往往表現爲歷史和文化。事實上,梁啓超認爲人類歷史之中並無“則”(規律、必然性)的存在。他説:
因果是什麽?“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於是命甲爲乙之因,命乙爲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作“必然的法則”。(科學上還有所謂“蓋然的法則”,不過,“必然性”稍弱耳,本質仍相同。)“必然”與“自由”是兩極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們既承認歷史爲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其理甚明。(6)同上,第3354頁。
雖然我們可以説歷史既是人類自由意志創造的,又受着必然性的支配,兩者之間並無矛盾,因爲所謂自由意志並不是對必然性的違背,而是嚴格的遵守。這段話反而反映出梁啓超在自由意志和歷史必然性之間非此即彼的僵化思路;但是,就其本身而言,這段話還透露了一個信息: 要區分自然界和人類世界。兩者所適用的規律是不同的。(因此,所適用的認識方法也不同。這點下文會展開。)
從這個基本區分出發,梁啓超批評了先秦法家在歷史觀上的態度。他認爲,法家的最大目的,在“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這是錯誤地將自然界的法則運用到人類世界之中。因爲所謂的“必然”指的是有一成不變的因果律存在,它可以協助我們預料將來。其情形就像一加一必爲二,氫氧化合必爲水也。梁啓超的批評理由還是將必然性和自由作出嚴格區分:“夫有必然則無自由,有自由則無必然。兩者不並立也。物理爲必然法則之領土,人生爲自由意志之領土,求必然於人生,蓋不可得,得之則栽人生亦甚矣。”(7)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
如果换一個角度看以上言論,梁啓超似乎在否定作爲對必然性認識的自由。因爲他明確認爲必然性和自由是對立的。雖然他説的是人類世界如此。可是如果將此觀點擴展出去,其意思似乎也是在説,“自然系”存在必然性,但没有自由;“文化系”存在自由,但没有必然性: 因此,我們即便討論自由,也和必然性無關。從這個角度看,本文對於梁啓超自由觀的討論值得質疑。不過,這種指向本文合法性的批評未必成立。因爲梁啓超在此所説的自由主要指的是自由意志,而非我們作爲一種規範性研究框架的認識自由。
梁啓超認爲,這種認識自由的起點還是實踐。他高度贊賞清代顔、李學派的“因行得知”論。(8)梁啓超《顔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五集),第3116頁。
《大學》裏面説:“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梁啓超認爲,這句話解決了“人的知識從那裏來呢?我們用什麽方法才能得着知識呢”(9)同上,第3114頁。這些問題。相比於歷史上宋明理學等思潮的解釋,梁啓超認同顔、李學派的解釋。顔習齋的解法如下:
李植秀問“格物致知”。予曰: 知無體,以物爲體,猶之目無體,以形色爲體也。故人目雖明,非視黑視白,明無由用也;人心最靈,非玩東玩西,靈無由施也。今之言致知也,不過讀書、講問、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須跪拜周旋,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譬如欲知樂,任讀樂譜幾百遍,講問思辨幾十層,總不能知,直須搏扮擊吹,口歌身舞,親下手一番,方知樂是如此。是謂“物格而後知至”。……格即“手格猛獸”之格。……且如這冠,雖三代聖人,不知何朝之冠也,雖從聞見而知爲某種之冠,亦不知皮之如何暖也。必手取而加諸首,乃知如此取暖。如這蔽蔬,雖上智老圃,不知爲可食之物也,雖從形色料爲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箸取而納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後知至。(《四書正誤》卷一)(10)同上。
梁啓超認爲,顔習齋的解釋,將“致”字當作《左傳》裏“致師”的“致”字來解,當作《孫子兵法》裏“致人而不致於人”的“致”字來解。引致知識到我跟前,叫作“致知”;知識來到了跟前,叫作“知至”。這段話的要點在於肯定“知識的來源,除了實習實行外是再没有的”(11)同上,第3115頁。。他否定了先天知識的存在:“習齋以爲,書本上説這件事物如何如何,我把這段書徹頭徹尾看通了,這種知識靠得住嗎?靠不住。别人説這件事物如何如何,説得很明白,我也聽得很明白。這種知識靠得住嗎?靠不住。憑我自己的聰明,把這件事物揣摩料量,這種智識靠得住嗎?靠不住。要想知識來到跟前(知至),須經過一定程式,即‘親下手一番’(手格其物)便是。换而言之,無所謂先天的知識,凡知識皆得自經驗。”(12)同上。
這裏的曲折在於,梁啓超通過肯定顔、李學派對《大學》“格物致知”論的解釋,表達了自己的認識起點甚至是知識的檢驗標準的觀點,這個起點或者標準就是行(實踐)。不過,具有才子氣味的梁啓超在用語上並非十分嚴格。今日我們會説,經驗也區分爲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梁啓超所説的讀書以及聽他人傳授指的是間接經驗,而自身的揣度則類似於内省。所以,嚴格地説,梁啓超是在主張知識都來自直接經驗。但是,仔細的區分之下我們會發現,實踐和直接經驗還是具有某些差别。在某種意義上,内省經驗也可以是直接經驗,雖然在此梁啓超力圖否定内省的重要性,但就直接經驗本身而言,它顯然包括内省經驗。從這個角度看,梁啓超的措辭比較疏漏。但其基本意思還是比較清楚的: 知識來源於實踐,並且以實踐作爲評判標準。
認識過程以獲得真理而暫告完成。和在知行關係問題上否定宋明理學,回歸先秦儒學一樣,在真理問題上梁啓超也嚴厲地批評了朱熹的真理觀,主張回歸孔孟的真理論。
梁啓超認爲,真理也即認識自由的獲得不以知天下之事無巨細爲前提,而以認識主體自身特長之所在爲轉移。换而言之,即便在某一領域獲得正確的認識,也可謂獲得了認識自由。認識自由絶非要求你認識全天下所有事。這個思想很重要。
在論述方式上,梁啓超也借助對顔、李學派的評論來達成如上論點,而顔、李學派則通過回歸先秦的文本來闡述其思想。當然,當梁啓超引用顔習齋的觀點時,已經表明他對顔、李學派這種觀點的認同。
朱熹追求的是全面的真理,要求掌握所有的知識,以爲這才是真理:“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朱子語類》卷十五)(13)轉引自梁啓超《顔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五集),第3116頁。
對此,梁啓超批評道:“朱子這種教人求知識法,實在荒唐。想要無所不知,結果非鬧到一無所知不可。何怪陸王派説他‘支離’呢?”(14)同上。他同意顔、李學派對朱熹的批評。李恕谷説: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教學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大學辨業》)(15)同上。
很清楚,李恕谷對朱熹的批評正是以回歸先秦儒家的思想爲表現的。他的意思是,真理並不要求遍知一草一木,而是根據自身的特性有所知即可。後者在如下言論中表現的更明顯。顔習齋曾問一門人,自度才智如何?那人答道:“欲無不知能。”習齋説:
誤矣。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後世菲資,乃思兼長,如是必流於後儒思著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無能,其實一無知也。(16)梁啓超《顔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五集),第3116頁。
梁啓超認爲,以上言論表明,“顔、李對於知識問題,認爲應該以有限的自甘,而且以有限的爲貴”(17)同上。。所謂“自甘”某種程度上也就可以看作是獲得了真理之後的自由狀態。這種狀態自有其長處,主要表現爲從認識主體自身的特點來考慮認識自由問題。如果完全繼承朱熹的觀點,雖然其精神可嘉,但不僅事實上做不到知曉天下所有之事,而且還會嚴重挫傷獲得真理之後的自由感。因爲,按照那種全面的真理觀,没有達到生命盡頭、宇宙盡頭那一刻,人是不可能獲得認識自由的。從這個角度看,顔、李學派有限的真理觀(按照顔習齋的説法,其思想源頭爲孔、孟)使得認識自由成爲可能。
然而,顔、李學派的這個洞見又深受其狹隘的實踐觀所束縛。梁啓超正確地指出,顔、李學派認爲“想確實得到這點有限的知識,除了實習外,更無别法”(18)同上。。從以上引文也可以看出,顔習齋認爲書本知識和内省知識還是可以達到朱熹的全面真理的——“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19)同上。。也就是説,顔、李學派對全面的真理的批評具有一定的正確性,但是,其理由卻站不住腳。其實,不僅直接經驗不可能達到全面而無遺漏,間接經驗和内省知識也不可能做到包羅萬象;所謂的包羅萬象很可能只是内省知識的幻象。
梁啓超繼承顔、李學派而又超越之。他認爲真理不僅是有限的,也是經驗和思辨的綜合。梁啓超沉痛地批評純經驗論者説:
今之論人論事者,一則曰經驗,再則曰經驗。夫經驗誠可貴也,非經驗無以廣儲俗識,而俗識實學識所取資也。雖然,苟無相當之學識,而唯日日馳逐於經驗,則經驗之能致用者有幾?是故有萬不可犯之原則而貿貿然犯之者,有極易遵之原則而落落然置之者,故往往用心甚善,用力甚勤,而反招惡果。惡果相襲,猶不省覺,甚則歷受惡果之煎迫,猶不肯認爲自招也。(20)梁啓超《良知(俗識)與學識之調和》,《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四集),第2393頁。
雖然梁啓超的這段話直接針對的是晚清民國時期“論人論事者”,但如果聯繫上文顔、李學派的基本觀點,此話顯然也可以指向他們的完全經驗論。梁啓超認爲,完全經驗論導致的很可能是種種“惡果”,也即没有實現認識自由。反過來看,認識自由之實現,需要學識和經驗的綜合。梁啓超承認學識也來自經驗,但是,它對經驗也有反作用,此即指導經驗能够真正致用。
梁啓超對顔、李學派知行關係論的糾偏某種程度上已經涉及認識的内在機制了。此爲下文討論的内容。
二、 認識的環節
寫作了《歐遊心影録》且喊出“科學萬能論破産”的梁啓超自然並不迷信科學,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將科學知識作爲知識的典範(21)嚴格地説,這裏所説的科學是自然科學。不過,從某種角度看,梁啓超也是陷入了某種自我矛盾。他認爲“文化系”的對象不完全適用歸納法,但是,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他認爲清代的考證學家充分地發展了科學方法,其中的核心就是歸納法。但是,衆所周知,考證學指向的,本質上是“文化系”的内容。如果我們執着於這個矛盾,梁啓超的認識論思想便似乎一無所是。但是,我們還是相信雖然梁啓超常常“不惜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他還是貢獻了關於認識論的很多洞見的。本書之立論並不在於尋找先賢的疏漏,只要有一得之見,皆會進入我們的討論範圍,哪怕這些洞見會被論主自身否定掉。。當然,正如上文所言,梁啓超將世界分爲“自然系”和“文化系”,認爲這兩種認識對象在某些方面涉及的認識環節和能力是不同的。如果將兩者綜合起來,或許可以看出梁啓超所判斷的認識環節和能力之大概。
科學一定意義上是認識真理的典型表現,所以從科學方法之中可以看出認識的各個環節。
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論述清代諸老的考證學方法時較全面地展示了他對科學方法的理解。雖然在這本著作中他没有論及先秦諸子和這些科學化了考證學方法之間的聯繫,但是,由於這些資料能够展現梁啓超科學方法的概貌,構成了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基礎,故予以簡述。
梁啓超認爲,清代諸老之所以能够在考證學上取得巨大成績,根本原因就在於貫徹了“科學研究法”,其中分爲“注意”“虚己”“立説”“搜證”“斷案”“推論”六大環節。他説:
然則諸公曷爲能有此成績耶?一言以蔽之曰: 用科學的研究法而已。試細讀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現此等精神。吾嘗研察其治學方法: 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過之處,彼善能注意觀察,發現其應特别研究之點,所謂讀書得間也。如自有天地以來,蘋果落地不知凡幾,唯奈端能注意及之;家家日日皆有沸水,唯瓦特能注意及之。《經義述聞》所厘正之各經文,吾輩自童時即誦習如流,唯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學問上能有發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觀察之後,既獲有疑竇,最易以一時主觀的感想,輕下判斷,如此則所得之“間”,行將失去。考證家決不然,先空明其心,絶不許有一毫先入之見存,唯取客觀的資料,爲極忠實的研究。第三曰立説,研究非散漫無紀也,先立一假定之説以爲標準焉。第四曰搜證,既立一説,絶不速信爲定論,乃廣集證據,務求按諸同類之事實而皆合,如動植物學家之日日搜集標本,如物理化學家之日日化驗也。第五曰斷案。第六曰推論。經數番歸納研究之後,則可以得正確之斷案矣。既得斷案,則可以推論於同類之事項而無閡也。(22)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6頁。
其中第三“立説”、第四“搜證”和第五“斷案”其實也就是假設和驗證:
科學家定理與假説之分也。科學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經過假設之階級而後成。初得一義,未敢信爲真也,其真之程度,或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爲近真焉,而憑藉之以爲研究之點,幾經試驗之結果,寢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達於十分,於是認爲定理而主張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爲假説以俟後人,或遂自廢棄之也。凡科學家之態度,固當如是也。(23)同上,第36~37頁。
以上所論不僅展示了清代考證學家的研究方法,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展示了科學方法論的内部環節。
不過,梁啓超認爲與考證學聯繫在一起的科學方法具有兩大不足:
1. 其研究對象爲歷史上的文本,而不是自然界。“本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惜乎其用不廣,而僅寄諸瑣瑣之考據。……故曰其精神近於科學。”(24)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273頁。只是“近於”,而非“便是”。
2. 側重於歸納法,忽視了演繹法。梁啓超認爲,清代考證學家的治學方法“純用歸納法”(25)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62頁。。他將歸納法的内在環節也加以展示,從而豐富了科學方法論。
夫吾固屢言之矣,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種程式始能表現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特别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於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係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意見,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爲定説。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凡今世一切科學之成立,皆循此步驟,而清考證家之每立一説,亦必循此步驟也。(26)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62頁。
雖然在此梁啓超在措辭上似乎將歸納法和科學精神完全等同起來了,但這並不意味着梁啓超本人忽視了演繹法。事實上,他對清代的研究方法有一個批評,此即忽視了演繹法:“清學正統派之精神,輕主觀而重客觀,賤演繹而尊歸納,雖不無矯枉過正之處,而治學之正軌存焉。”(27)同上,第105頁。不過,從這種措辭中,也可以看出,梁啓超較多地認同歸納法,而對演繹法並不高度贊賞。
這當然和梁啓超對演繹法的認識相關。一般認爲,演繹法所能得到的結果是確定無疑的,但梁啓超指出,演繹法所遵循的大前提本身是值得質疑的,因此其推論未必確實。比如“凡人皆有死,我是人,所以我也會死”的演繹推論,梁啓超指出,“若使‘凡人皆必死’之大前提有絲毫不確實,則‘故我亦必死’之一斷案,亦將不確實。寢假有人焉,以特别試驗,而見有若干少數不死之人,則安知我不在彼少數者之内也?故倍根以爲此種論法,導人於武斷之途者也。”(28)梁啓超《子墨子學説》,《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335頁。
梁啓超認爲歸納法反而能够尋得真理。比如“我也會死”這個結論,可以采用歸納法研究:“今以歸納法研究之,而見夫墨子死也,孔子死也,孟子、荀卿死也,宋牼、禽滑厘死也,亞里士多德、倍根死也,乃至往古來今之人無一不死也,於是而凡人必死之一前提,乃爲鐵案而不可移,而故我必死之一斷案,亦可以自信。此其術之所以爲進步也。”(29)同上。“故演繹法只能推論其所已知之理,而歸納法專以研窮其所未知之理。”(30)同上,第336頁。梁啓超認爲,在歸納法的問題上,西方以培根爲代表,而中國早在先秦時期墨子就提出了相關的觀念。“倍根氏所以獨荷近世文明初祖之名譽者,皆以此也。而數百年來,全世界種種學術之進步亦罔不賴之,而烏知我祖國二千年前,有專提倡此論法以自張其軍者,則墨子其人也。”(31)同上。
梁啓超對歸納法和演繹法的認識不無商榷之處。
從創造新知識的角度看,歸納法似乎比演繹法好;然而,這並不能認爲演繹法不能創造新知識。以上文“凡人皆有死”的演繹推論爲例,“我會死”當然包括在這個大前提之中。可是,當我們通過演繹法明確將“我會死”這個命題突出,某種意義上也是創造了新知識,即將隱含在大前提中的内涵加以揭示。
從推論的必然性的角度看,無疑歸納法所得是蓋然的,演繹法所得是必然的。從這個角度看,當梁啓超説“而見夫墨子死也,孔子死也,孟子、荀卿死也,宋牼、禽滑厘死也,亞里士多德、倍根死也,乃至往古來今之人無一不死也,於是而凡人必死之一前提,乃爲鐵案而不可移”(32)梁啓超《子墨子學説》,《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336頁。,他錯了。從那麽多歷史人物之死不能遽然推導出“凡人必死”。如今,歸納法不能得到必然性,這個認識已經是常識了。
不過,從梁啓超自己所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真理的獲得需要歸納法和演繹法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我會死”是以“凡人皆有死”爲前提,但這個前提的獲得離不開歸納。事實上,梁啓超在解釋墨子的“三表法”時明確認爲,“三表法”説明的是演繹法和歸納法的結合才是探尋真理的途徑。
梁啓超綜合了墨子論及“三表法”之處,認爲它分爲三法,第一法和第二法又分爲甲乙兩種:
第一法:
甲—考之於天鬼之志
乙—本之於先聖大王之事
第二法:
甲—下察諸衆人耳目之情實
乙—又徵以先王之書
第三法: 發而爲刑政,以觀其是否能中國家人民之利(33)同上。
梁啓超認爲,這三法之中,第一法之甲,第二法之乙,皆屬於演繹法;第一法之乙,第二法之甲,與第三法,就是歸納法。“是故墨子每樹一義、明一理,終未嘗憑一己之私臆以爲武斷也,必繁稱博引,先定前提,然後下其斷案。又其前提亦未始妄定,必用其所謂三表、三法者,一一研究之,而求其真理之所存。若遍舉之,則全書五十七篇中,無一語非是也!”(34)同上。换而言之,梁啓超認爲,雖然正如其前文所説,墨子已經有了和培根相媲美的歸納法思想,但在真正進行推理時,他貫徹的是綜合了歸納法和演繹法的“三表法”。换而言之,雖然在具體的推理個案中所得的結論未必爲必然,但是,至少梁啓超認爲,墨子結合演繹法和歸納法來進行推理,可以使得結論更加嚴密,走向真理。
梁啓超認爲,歸納法和演繹法綜合的思想不僅體現在墨子那裏,而且也體現在儒家的《大學》裏面。他認爲,所謂“格物致知”就是講的演繹法和歸納法的結合。他説:
俗識者,恃直覺與經驗之兩種作用而得之者也;學識者,恃概括分析與推定之三種作用而得之者也。例如磨剃刀使薄則犀利,平峻阪使紆則易登。此兩事者,由俗眼觀之,截然不相蒙;由學者觀之,則一事而已,即物理學上鋭其鍥子之理也。學問之天職,在分析事物,而知其組織之成分,然後求得各種事物共通之點,概括綜合之以尋出其原則,復將此原則推之凡百事物,所謂格物致知,所謂一以貫之者,於是乎在矣!(35)梁啓超《良知(俗識)與學識之調和》,《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四集),第2392頁。
這裏,梁啓超對於直覺和經驗似乎有所不滿,稱之爲“俗識”。然而,我們可以暫且不管這個,而從下面的言語中可見,格物致知便是從分求通,然後再用此通用的原則規範其餘事物。這就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結合。
但是,梁啓超認爲,相對於培根而言,雖然《大學》也涉及了歸納法和演繹法等認識環節,不過在實證這一點上比較欠缺。他説:
綜論倍根窮理之方法。不外兩途: 一曰物觀,以格物爲一切智慧之根原。凡對於天然界至尋常至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觀,當有自主的精神,不可如水母目蝦,倚賴前代經典傳説之語,先入爲主以自蔽,然後能虚心平氣,以觀察事物。此倍根實驗派學説之大概也。自此説出,一洗從前空想臆測之舊習,而格致實學,乃以驟興。如奈端因蘋實墜地而悟吸力之理,瓦特因沸水蒸騰而悟汽機之理,如此類者,更僕難盡。一皆由用倍根之法,静觀深思,遂能製器前民。驅役萬物,使盡其用,以成今日文明輝爛之世界。倍氏之功,不亦偉乎!朱子之釋《大學》也,謂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論精透圓滿,不讓倍根。但朱子雖能略言其理,而倍根乃能詳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實行之;朱子則雖言之而其所下工夫,仍是心性空談,倚虚而不征諸實。此所以格致新學不興於中國,而興於歐西也!(36)梁啓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説》,《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392~393頁。
由於朱熹詮釋的文本爲《大學》,所以這段材料也能爲我們所用。换而言之,梁啓超認爲《大學》的格物致知不能走向空談心性,而應該征諸實際。
事實上,梁啓超明確表示,中國先秦以來的一大弊病就是物理實學之缺失。不僅《大學》如此,諸子百家皆有此病。他指出:“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然有録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唯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絶。唯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爲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37)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236~237頁。
當然,必須强調的是,梁啓超並不認爲培根代表了現代認識論思想的高峰。因爲他雖重視實驗,但缺乏假設的環節。而從前文可知,梁啓超認爲假設和驗證應該是認識論的重要環節。在此,他主張需要引進笛卡爾。他認爲,朱熹在某種程度上反而表達了要重視假設的思想。他説:
笛卡兒嘗語人曰:“實驗之法,倍根發之無餘藴矣。雖然,有一難焉,當其將下實驗之前,苟非略窺破一綫之定理,懸以爲鵠,而漫然從事於實驗,吾恐其勞而無功也!”此言誠當。蓋人欲求得一現象之原因,不可不先懸一推測之説於胸中,而自審曰: 此原因果如我之所推測,則必當有某種現象起焉。若其現象果屢起而不誤,則我之所推測者是也;若其不相應,則更立他之推測以求之。朱子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故實驗與推測常相隨,棄其一而取其一,無有是處。吾知當倍根自從事於試驗之頃,固不能離懸測。但其不以此教人,則論理之缺點也。故原本數學以定物理之説,不能不有待於笛卡兒矣。(38)梁啓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説》,《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393頁。
意思甚明。
假設和實驗,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演繹法和歸納法的結合的另一種運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認識主體自身所提出的假設擴展到群體中去得到檢驗。這種檢驗,一方面當然離不開實證,另一方面也可以是理性的辯駁和維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認識環節也包含了群己之辯。
早在《變法通議》中,梁啓超就提出了認識過程中的群己之辯的環節。他説“群之道,群形質爲下,群心智爲上”(39)梁啓超《變法通議》,《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38頁。,“道莫善於群,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40)同上。。這個觀點一直伴隨着梁啓超。多年以後,他還認爲“合衆人之識見以爲識見則必智,反是則愚”(41)梁啓超《論商業會議所之益》,《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三集),第1327頁。。
衆所周知,群道是中國素來的話題,荀子就對此作出了很好的説明。但是,梁啓超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論述群道的,而荀子則是從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角度來加以言説。事實上,梁啓超采取的論證也讓我們看到了荀子的痕迹。梁啓超説:“虎豹獅子,象駝牛馬,龐大傀碩,人檻之駕之,唯不能群也。”(42)梁啓超《變法通議》,《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第38頁。這不正是荀子“義論”的首句嗎?(43)荀子説:“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 分。分何以能行?曰: 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强,强則勝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争,争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荀子·王制》)此即荀子之“義論”。
换而言之,梁啓超充分地認識到真理、認識自由的獲得是以群己之辯爲基礎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注重認識過程中的群己之辯,並非意味着他完全以人數之多寡作爲判斷真理的標準。他認同顔、李學派的觀點:“習齋説:‘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所同,不隨聲也。’(《習齋言行録》卷下)”(44)梁啓超《顔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五集),第3112頁。梁啓超似乎重視是非而不論異同。這兩種判定真理的標準之間的差别是,前者是包含了更多的判斷真理的標準,而以符合論爲主。後者則主要分爲兩種: 一種是以前人、聖人的言論爲標準,一種是以多數人的言論爲標準。嚴格地説,這兩者作爲判斷真理的標準都是有不足之處的。但是,梁啓超對於認識機制的複雜性的認識也有不足之處。因爲即便是是非論,也包含着某種異同論。無論是符合論還是效果論,都離不開多數人。
可見,群己之辯絶非要求認識主體含糊其辭,而是更加要求其堅持自己的主張。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也就是思想自由的表現。因此,群己之辯也就涉及理性的辯駁:“思想是要自由的,但卻不能囫圇,卻不能模棱,對於和自己不同的見解,必要辯駁,或者乃至排斥。辯駁、排斥,不能説是侵人自由,因爲他也可以照樣的辯駁我,排斥我。”(45)梁啓超《戴東原哲學》,《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五集),第3142頁。這也就意味着放棄歷史上某些霸道的做法:“我們不贊成韓愈的態度,因爲他要‘人其人,火其書’;不贊成董仲舒的態度,因爲他要‘絶其道,勿使並進’。”(46)同上。其中顯然包含着對先秦思想自由狀態的肯定以及對後世大一統思想格局的批評。
三、 認 識 能 力
以上所論科學方法論的内在環節、演繹法和歸納法、假設和驗證,以及群己之辯等,主要涉及認識論的環節。在認識的過程中,不僅需要討論認識對象、認識的基本過程、認識論的環節,還涉及認識能力等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梁啓超除了對於一般的理性、經驗等表示其觀點之外,還討論了直覺、判斷力等當時不爲人所注意的問題。
關於直覺,上文曾指出梁啓超認爲,直覺與經驗構成的是“俗識”,理性的歸納法和演繹法構成的是“學識”。雖然他認爲“俗識”也是“學識”的基礎,但他更多地對“俗識”持輕視、批評態度(47)梁啓超《良知(俗識)與學識之調和》,《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四集)第2392頁。。但是,嚴格地説這是在“自然系”裏面對直覺的立場,在“文化系”裏,則要重視直覺。他説:
現代所謂科學,人人都知道是從歸納研究法産生出來。我們要建設新史學,自然也離不了走這條路。所以我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極力提倡這一點,最近所講演《歷史統計學》等篇,也是這一路精神。但我們須知道,這種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簡單説,整理史料要用歸納法,自然毫無疑義,若説用歸納法就能知道“歷史其物”,這卻太不成問題了。歸納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許多事物相異的屬性剔去,相同的屬性抽出,各歸各類,以規定該事物之内容及行歷何如。這種方法應用到史學,卻是絶對不可能。爲什麽呢?因爲歷史現象只是“一躺過”,自古及今,從没有同鑄一型的史迹。這又爲什麽呢?因爲史迹是人類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絶對不會從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學家正相反,專務求“不共相”。倘若把許多史迹相異的屬性剔去,專抽出那相同的屬性,結果便將史的精魂剥奪净盡了。因此,我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進一步。然則把許多“不共相”堆疊起來,怎麽能成爲一種有組織的學問?我們常説歷史是整個的,又作何解呢?你根問到這一點嗎,依我看,什有九要從直覺得來,不是什麽歸納演繹的問題。(48)梁啓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六集),第3353頁。
可見,梁啓超已經認識到歷史學研究當中直覺的重要性,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梁啓超完全否定科學方法在歷史學裏面的地位,至少他承認整理史料還是需要科學方法的。
問題的另一方面是,以上言論反映了梁啓超的某些偏見。在科學研究領域,並非只有歸納法和演繹法、假設和驗證、理性的討論等環節。歸納所得的結論,即從具體的事例到抽象的結論之間的跳躍,假設的産生,甚至驗證方法的尋得,直覺也在發揮作用。對於這點,其後賀麟説的相當詳盡。
與直覺處於類似神秘地位的是判斷力。
梁啓超認爲,判斷力的養成需要三個前提:“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步,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智識;再進一步,還要有遇事能斷的智慧。”(49)梁啓超《爲學與做人》,《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六集),第3333頁。其中最關鍵的是第三步。梁啓超認爲,常識和學識的堆積並不能産生判斷力。因爲“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才懂這一件,那麽,碰着一件没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便手忙腳亂了。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50)梁啓超《爲學與做人》,《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六集),第3334頁。梁啓超雖然没有對何謂判斷力作出明確界定,但是,從這段話中可見,判斷力就是對於没有學過的特殊事務的應對能力。
在哲學史上,對判斷力作出巨大貢獻的是康德。康德把判斷力區分爲規定性的判斷力和反思性的判斷力,前者和認識論密切相關。他指出,“如果把一般的知性看作規則的能力,判斷力就是把事物歸攝於規則之下的能力,即辨别某種東西是否從屬於某條所予的規則(cssus datae legis所予規則的事例)之能力。”(51)[德] 康德著,韋卓民譯《純粹理性批判》,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頁。從這個角度看,梁啓超和康德所説的判斷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針對的都是特殊的事物。不過,康德同時指出,“判斷力卻是只能得到練習而不能得到教導的一種特殊才能”(52)同上。。换而言之,康德認爲判斷力不可學。與之不同,梁啓超比較籠統,他認爲判斷力是可以培養的,除了以上三個步驟之外,還需要培養總體的智慧。“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才能養成呢?第一件,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着實磨練他,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那麽,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我都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自然不至於惑了。第二件,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着實將養他,叫他變成清明。那麽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從容,很瑩澈的去判斷他,自然不至於惑了。”(53)梁啓超《爲學與做人》,《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六集),第3334頁。顯然,這種總體的智慧其實也就是科學方法的運用和内化。
梁啓超認爲,判斷力是智育的核心。他批評當時的教育不僅忽略了情育和意育,而且最致命的是,“至於我所講的總體智慧靠來養成根本判斷力的,卻是一點兒也没有”(54)同上,第3335頁。。他認爲,先秦時代儒家所提出的“知者不惑,仁者無憂,勇者無懼”之“三達德”中,“知者不惑”説的就是智育。判斷力的養成真正達到了這個目標,實現了先秦儒家的追求——“以上所説的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知者不惑”(55)同上,第3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