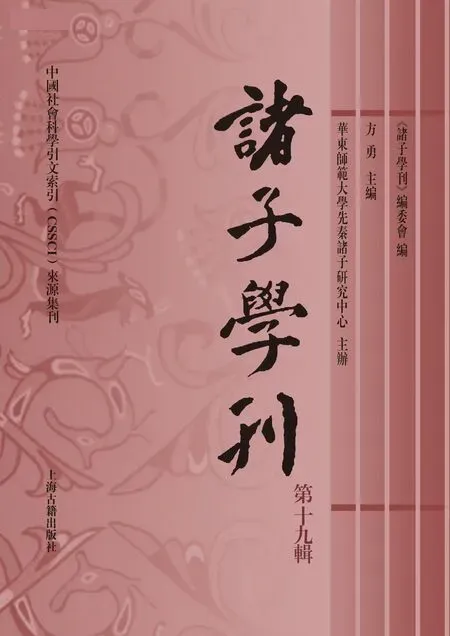諸子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從解讀到闡釋
——論諸子學研究的深化與提升
劉韶軍
内容提要 諸子學深入研究的一個必備條件是對諸子書的文本進行深入細緻的解讀與闡釋,爲完成好這個任務,首先必須按歷史主義的精神做到忠實於文本原意,同時還要有現代主義的意識,能據時代的要求對諸子原書的文本之中包含的豐富思想内涵進行現代性的闡釋。其次,要在闡釋學的理論指導下,對諸子書的文本做到從本然到應然的深入闡釋,以求完整地探尋其中的思想義理。再次,對諸子思想學説中提出的主張和觀點進行闡釋與解讀時,要充分注意其中具有的理據,以求證實這些主張與觀點的可靠性。最後,要把分散的各家諸子的研究整合爲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不再分割這個思想整體,這樣才能看出不同的諸子之間的關係與差異,從而更爲深入地認識諸子的思想。
關鍵詞 諸子 文本 思想 闡釋
諸子學的研究在現代條件下,從根本上説,應該從傳統的諸子學研究進步到現代的諸子學研究。欲達這一目的,從研究諸子傳留下來的著作文本的角度看,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注意。這就是本文題目所説的——從解讀到闡釋的問題。
我所説的解讀,是對諸子著作文本的閲讀性理解,即認真地一字一句地對諸子著作文本進行閲讀並做到徹底地理解。其要求是忠實於諸子著作文本的本意或原意,且儘量完整準確地閲讀並理解。我所説的闡釋,則是在對諸子著作文本的解讀的基礎上,對諸子所論述和提出的種種問題從現代條件更爲深入地進行分析論述。其要求是超出諸子當時的觀點、主張,使諸子所論及的問題在現代觀念與理論的基礎上得到深化和提升,不再停留於諸子當時的思考層次。
解讀是諸子學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是必不可少的步驟。闡釋是諸子學研究的提升與發展,也是當今學術研究需要創新和深化的地方。在現代條件下對諸子學的研究,必須從過去比較重視的解讀層次上升進化到闡釋的層次,這才可以稱爲現代的新的諸子學研究,而與歷史上的舊的諸子學研究區分開來,而這也正是現代的新的諸子學研究必須完成的任務。
從解讀到闡釋,在我看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説明: 在研究的時代性上,要做到從歷史到現代的提升與發展;從對諸子著作文本的内涵理解上,要做到從諸子所論的内涵之本然到所關涉的問題的内涵之應然的提升與發展;在諸子思想的分析上,要做到從諸子當時的觀點與主張的理解與總結到對這些觀點與主張的理據(理由、根據、邏輯等)做出論證與分析的提升與發展;在諸子的相互關係上,要做到從對個别的諸子的研究到全部的諸子的整體性研究的提升與發展。而這四個方面的探討,有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把對諸子學的研究從一般化的解讀性研究提升到更爲深刻和完整的闡釋性研究上來,由此促進現代諸子學研究的進步。
以下就這四個方面分别予以説明與論述。
一、 從歷史到現代
所謂歷史,就是歷史上的諸子所處時代及其學術在思想文化上的整體背景以及諸子在這樣的歷史條件與背景下對所關注的種種問題的論述及其觀點與主張。簡單地説,就是諸子的思想觀念在歷史上的原本狀態。所謂現代,就是今天的學者研究歷史上的諸子時所處的時代及其學術在思想文化上的整體背景。諸子的歷史情況,是必須首先研究清楚的。現代學者研究歷史上的諸子的思想,則必須與現代的實際情況緊密聯繫,不能使現代學者對諸子的研究脱離現代社會的種種情況,要把諸子學中包含的種種問題放到現代社會的視野中進行全新的審視與分析研究。
在學術研究的方法與觀念上,存在着歷史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區分。根據英國所出版《楓丹娜現代思潮辭典》(1)[英] A.布洛克、O.斯塔列布拉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譯《楓丹娜現代思潮辭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第265~266頁有對“歷史主義”的解釋:“本來指一種研究方法,强調所有歷史現象的獨特性,認爲對每一個時代應該按照它自己的觀念和原則來加以解釋。從反面説,對人過去的行動不應該按照信仰、動機和對歷史學家自己所處時代的評價來加以解釋。”
這種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與觀念是拒絶研究者根據自己的信仰、動機和時代觀念來解釋歷史,只按歷史當時的觀念來解釋歷史。而此書第364頁有對“現代主義”的解釋:“在神學上,指的是根據對《聖經》的考據和科學發現的結果以及對現代文化的條件等方面的考慮來使教義現代化的運動。”
所謂神學,是指神學研究,即對基督教義的學術研究。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正相反,不是局限於歷史當時的觀念以解釋歷史,而是要求研究者根據新的研究成果和現代文化的觀念來解釋教義,使之現代化。初看二者不可調和,各執一義,其實可以統一。這是因爲對歷史(包括歷史上的諸子及其思想學説等)的解釋以研究和弄清楚當時的真實情況(即歷史上的諸子所論説的本意或原意)爲基礎,但不能停留在這一步,還應根據現代的條件與思想觀念和理論學説來對歷史(即諸子當時所論説的思想内容)進行更進一步的深入的分析與考察,以求發現其中的合理内涵與不合理的成分,並根據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對歷史上的諸子的思想學説進行現代化轉化和加工,把其中的合理内涵用現代學術的思想理論加以更高層次的論證與闡釋,使之成爲可以爲現代社會服務的思想資源。因此歷史主義的研究是整個研究的基礎與第一步,但不能説是學術研究的全部與終止處,在歷史主義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應把它放到現代社會條件下進行審視,做出學術上的研究分析、判斷與評價。這就要用到現代主義的觀念和方法。所以説此二者初看是矛盾與對立的,但仔細從整個學術研究的過程與要求來看,則二者都不可缺,而應互補以相輔相成。
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的序言中把史學分成幾種(2)參見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7~9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1999年重印本與該版一樣。: 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哲學的歷史。
原始的歷史,是直接記録歷史的方法,反省的歷史主要爲批判的歷史和各種專門史,如藝術史、法律史、宗教史等。所謂批判的歷史,已經是研究者用自己的思想觀念來對歷史進行分析評判,相當於前面所説的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據黑格爾説,反省的歷史中的批判的歷史有一個特點,即“著史的人”用他的“鋭利的眼光”,“從史料的字裏行間尋出一些記載裏没有的東西”。黑格爾説,法國人的歷史著作中多有這類研究的成果,“貢獻了許多深湛和精闢的東西”,而德國人則把它上升爲“高等的批判”,即研究者過度使用了自己對歷史的批判(也是一種闡釋),黑格爾反對這種高等的批判,認爲它們“不過是就荒誕的想象之所及,來推行一切反歷史的妄想謬説。……就是以主觀的幻想來代替歷史的紀録,幻想愈大膽,根基愈是薄弱,愈是與確定的歷史背道而馳,然而他們卻認爲愈是有價值”。可知,歷史主義是必要的,現實主義則不能過度使用,否則就會走向妄想謬説而與真實的歷史背道而馳,這是没有價值的。
黑格爾作爲德國人,認爲反省的歷史還不够,他提出了哲學的歷史之方法。所謂哲學的歷史,本質上就是對歷史進行哲學的思考,思考世界歷史各大事變的推動者或指導者(或稱爲領袖),思考歷史是怎樣由精神和理性所領導、指導、推動的。他認爲哲學的歷史不是研究歷史的“純屬外表的綫索,不是那種浮而不實的結構,而是探討歷史中各種事實和動作的内部指導的靈魂”。可知哲學的歷史也是一種反省的歷史,只不過反省的高度上升到哲學的層次,要爲歷史的發展找出其背後的哲學原理性的東西。但這仍屬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因爲研究者所憑藉的哲學學説與觀念,都是研究者的時代所具有的,是與所研究的歷史(包括諸子的思想學説)不一樣的。
總起來説,反省的批判的歷史的研究方法,都是研究者根據他的時代的思想理論學説和觀念等來對歷史進行分析觀察與評價,本質上都屬於現代主義的方法。只不過不能過度,不能不顧歷史的事實之根基。在諸子學的研究中,也應如此。
不管怎樣,歷史主義與現代主義這兩種方法論與思想觀念,對於現代的諸子學研究是有重要啓發意義的。我們既不能只顧追究諸子的理論學説思想觀念的歷史真實與原貌,也不能憑着研究者主觀的想法來對歷史上的諸子學的豐富内容進行没有根基的幻想式評判與分析。而應把這二者適當地結合起來,用歷史主義的觀念研究清楚諸子思想内容的本來内涵(本意),用現代主義的觀念方法徹底闡釋諸子的思想學説所涉及的重大學術問題。用前者作扎實的根本,用後者作創新的研究。這就是歷史與現代的結合,就是從歷史走向現代的應有之含義。
二、 從本然到應然
歷史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結合,是從歷史的不同階段及其發展變化的角度來看問題的。而從本然到應然,則是從解釋學的角度來看問題的。
所謂本然,是指諸子在歷史的特定時段所論説的思想内容之本來意旨。所謂應然,是指諸子所論説的思想内容中包含的問題應當怎樣分析論述與解決。本然,是歷史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應然,是現代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本然與應然表明歷史與現代在本質上是統一的。
美籍華人學者傅偉勳在1987年冬季號《知識份子》發表了他提出的“創造的解釋學”,主要是討論如何解釋中國古代思想的認知方法問題。傅偉勳的“創造的解釋學”,是從現代西方闡釋學衍生出來的變種,是結合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實際而生發出來的思想闡釋方法。此種方法比傳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有獨到的可取之處,值得瞭解。而他所説的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研究,正可用來説明今天所討論的諸子學的研究。
傅氏提出的解釋學的基礎是哲理解釋時的觀點轉移之理。所謂“觀點轉移”,就是對古代思想家的原典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因此現代的研究者對古代思想家的原典不能局限於它的原有思想進行説明,而要對其原有思想的深層結構進行發掘,要突破原有思想,發展到客觀的解釋學的描述層次。傅氏的創造的解釋學分爲五個層次:
實謂層次,即由研究者弄清楚原思想家的著作原文及字面意義,這一層次還不能瞭解原思想家實謂之後的哲理内容。因此必須超過實謂層次而進至第二層次: 意謂層次。
意謂層次,是要研究者弄清楚原思想家在實謂層次之後意謂什麽。實謂與意謂間存在着距離,原思想家也不一定能解決他意謂了什麽。故研究者要推敲探索,以澄清隱藏在實謂之後的意謂。但在意謂層次,人們很難取得一致的意見,即不可能獲得純客觀的瞭解和解釋。如何對所謂的意謂而由不同的研究者形成的不同解釋進行判斷?這就必須進到更高的層次: 藴謂層次。
藴謂層次,是指原思想所言説的東西可能藴涵了什麽?爲此研究者必須系統地瞭解對這一思想家的歷史上形成的解釋傳統。以研究《論語》的哲理藴涵爲例,首先要遍查自魏晉時期何晏《論語集解》直至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歷代的重要注釋書,以瞭解整個解釋史上的主要内容和學者們不同的解釋方法,由此爲基礎,才有可能發現《論語》可能藴藏的種種哲理深義。通過藴謂層次的探索,才能克服意謂層次上的主觀片面的淺陋之見及其解釋方式,然後才可以進至更高的層次: 當謂層次。
當謂層次,就是研究者超越已有的解釋史,而由自己判定歷史上的各種解釋的價值所在,包括認清其中的正確的説法與錯誤的説法,這被稱爲“當謂判斷”。在當謂判斷的面前,將逼使原思想家説出他本應説出的話。爲此必須能在其原有思想的表面結構之下發掘出其深層結構,由此即可進至必謂層次。
必謂層次,就是超越原思想家的思想意境,達到“由我(即現代的研究者)爲他(即古代的思想家如諸子)開創的思想傳統説出什麽”的層次。所謂由我爲他説什麽,即指由現代的研究者爲歷史上的諸子等思想家説出他們未曾説出的思想,也就是在歷史上的諸子的思想學説的基礎上説出他們的思想中所包含的更深層次的意旨。
從實謂、意謂、藴謂、當謂而到必謂,這就是傅氏“創造的解釋學”的主要見解。他的意思是説對古代思想家如諸子的研究要在思想内涵的闡釋上不斷深入,論證出一層層更爲深奧而不顯現的思想。但這種層層深入的闡釋學,基礎還是諸子著作文本中的本來含有的意旨,此後的層層深入,都不能離開也不能違背這種本來含有的意旨,只是在這些本來的意旨的内涵中不斷深化思考而把所涉及的問題從較浅的層次闡釋到較深的層次。這也正是從歷史向現代的發展和演進。如果没有這種發展和演進,也就不可能形成綿延數千年而不斷的學術解説史和思想闡釋史。
然而我們可以不必按照傅氏所分的五個層次來看這個問題,完全可以把它簡化成兩個層次,即本然與應然。本然是諸子當時所論説的思想内容之本來情況,應然是現代的研究者對諸子所論説的思想内容進行深入分析論證後形成的應該怎樣的認識與論述。只對諸子思想内容的本來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在諸子研究上還是不够的,只能説是諸子研究的第一個階段的任務。在完成這個任務之後,還要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分析研究,以探求諸子在他們的論説中提出的種種重要問題及其解決方法,達到應該如何正確解決這些問題的地步。
如在老子思想的研究中,在本然層次,我們可以根據《老子》的文本分析出其思想主旨是主張聖人式侯王以自然無爲的觀念來治理國家和天下,不要像當時的現實中的侯王那樣從個人私欲出發而不顧人民死活的竭澤而漁式的統治。但對現代的研究者來説,弄清楚這一本然的情況還不够,還要繼續根據現代社會的條件與思想理論來探討這個聖人式侯王自然無爲以治國的問題,是不是合理的、可行的?是不是還有不充分的地方,還有不切實際的地方?如果其中有合理的成分,有可行的因素,則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又應如何根據這樣的思想來治國理民?這些問題就都屬於應然層次,需要現代的研究者根據現代社會的實際情況來從理論上予以闡釋和論證。
其實這種情況,在《老子》解釋史上已有例證。如近代的嚴復,曾寫有《老子評點》,在其中他根據近現代西方學術的思想理論,對老子思想進行了與歷史上的解釋都不一樣的新闡釋,如他在翻譯赫胥黎《天演論》時,認爲斯賓塞所説的“治”,根本意旨就是“任天”,這就是黄老道家所説的任乎自然(“猶黄老之明自然”),而這種“任天”(任乎自然)不是單純哲學觀點,而是對於人類社會及其發展進步有着重要意義的一種規律——“凡人生保身保種合群進化之事,凡所當爲,皆有其自然者,爲之陰驅而潛率”(3)見嚴復譯《天演論》,科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22頁。。
他又把“任天”的“天”與《老子》的“天”聯繫起來,認爲就是順乎自然的進化:
凡讀《易》《老》諸書,遇“天”“地”字面,只宜作“物化”觀念,不可死向蒼蒼摶摶者作想,苟如是必不可通矣。(4)見嚴復《老子評語》第七章,嚴靈峰《老子集成》本。
而《老子》五章説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就是指聽任自然(任天),嚴復認爲《老子》此章所説,正是“《天演》開宗語”,而遵循這一思想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即“法天者,治之至也”(5)嚴復《老子評語》第五章評語。。基於這樣的理解,嚴復認爲《老子》第五章的王弼注,最符合西方的進化論之旨:“此四語,括盡達爾文新理,至哉王輔嗣。”(6)同注③。這裏所説的“四語”,是指王弼爲《老子》五章“天地不仁”所作注:“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
類似的例子在嚴復《老子評點》中還有很多(7)參見劉韶軍《嚴復〈老子評點〉與西方思想》,《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1年第6期。,這説明嚴復對《老子》的闡釋已從《老子》所説的“本然”向他所理解的“應然”提升,而他理解的“應然”,則來自他所處的時代,即他所處的“現代”所提供給他的學術思想。這又説明,所謂應然,又是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需要不同時代的學者不斷地研究和探索。
我在研究《太玄》時,需要對《太玄》的思想進行解釋。因爲宋代的蘇軾説過,揚雄的《太玄》不過是“以艱深文淺易”,照此説來,《太玄》就没有什麽深刻的思想内容了。但是如果按照從本然到應然的研究方法來探討《太玄》中的思想内容,就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在研究中,我曾論述過自古以來就爲人們經常討論的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即根據闡釋學的認識,文獻的文本作爲表達思想與更多内容的載體,與所要表達以及所包含的内容之間並不是完全相等的,也就是説,古代思想家(諸子)的著作及其文本所承載的思想内容遠遠多於文本字面所能表達的意思,而這正是中國古人早就説過的,並非我的新見。《周易·繫辭》載夫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這説明由文字所組成的“書”,不能完全表達作者所要説的話(言),作者所要説的“言”,也不能充分表達他的思想(意)。這並不是説“意”完全不可見,而是説僅靠“言”不能充分瞭解“意”,要充分瞭解“意”,就要超出“言”,進行更爲深入的思考與分析。所以《繫辭》又説“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所謂的“盡意”,就是通過“象”來充分理解其“意”,不是説“象”本身就能完全表達出其“意”。所謂的“盡”,要靠人的思維和分析來完成,僅靠“象”是不能自動“盡”其“意”的,不然的話,人的思考與分析也就不必要了。
言不盡意,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是一個重要命題,注重思辨的學者對此都非常重視,如《莊子·天道》説:“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書”由“言”和“語”組成,而“言”與“語”的寶貴在於它所表達的“意”,但“意”不能完全由“言”來傳達。一般人只重“書”和“言”“語”,不知“書”和“言”“語”不足以表達“意”。真正可貴的不是“書”和“言”“語”,而是“書”和“言”“語”之外的“意”,即郭象注釋時所説的“其貴恒在意言之表”。“意言之表”即言語之外的“意”。《莊子·外物》又説:“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也是説“言”與“意”不是簡單相等的,需要另外思考獲得其“意”,而且能得“意”的人非常難得,所以才希望有這種人出現而與之交流。
在魏晉玄學時代,人們仍然關注這一問題,如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説:
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在“言”與“意”之外又提出“象”,“象”不是“言”,但性質上與“言”差不多,都有可見性,都是用來表達“意”的,即所謂“出意”。不管是“象”是“言”,讀者最終是要通過它們來得“意”,“象”與“言”是得“意”的媒介,但不能等同於“意”,其完整的“意”在“象”與“言”之外,當然“象”與“言”本身也表達一定的“意”,但不是全部的“意”,所以達到得“意”的目的之後,“言”與“象”都不再重要,都可以忘掉,這與莊子的思想一致,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認同的一種思維方法與目標。
與王弼同時的荀粲也説:
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藴而不出矣。
認爲“意”是“理之微者”,是在“象”之外的,而且是“藴而不出”的,所以僅靠“象”或“言”是不能直接獲得的,必須通過人們的思考才能獲知之。
在闡釋諸子思想的“本然”時,已有“言不盡意”的問題,而要闡釋出“應然”層次的内涵,就更應注意“言不盡意”的問題。這説明要對諸子思想闡釋到“應然”層次,必須對“言不盡意”的“意”有更深刻的理解。歷史上的諸子之“言”有不盡的“意”,這是諸子當時已有的“本然”之“意”,而在現代的研究者看來,諸子的“言”與“意”又是不完整的,還需要現代的研究者從中發掘更深更多的“應然”之“意”。
如筆者在注釋《太玄·中首》的“初一”的贊辭“昆侖旁薄,幽”、測辭“昆侖旁薄,思之貞也”時,首先把其中的文本從訓詁上弄清楚,即: 昆侖同渾淪、混沌、渾沌,原義爲渾沌未分,茫茫一團。此處用爲動詞,意爲籠括一切,混沌一體。旁薄同旁魄、旁礴,言廣博宏大,此用爲動詞,謂混同籠括。幽,幽隱不現。唐代王涯注:“幽者,人之思慮幽深玄遠也。”
在此基礎上説明《太玄·中首》初一的本然之意,是謂賢人之思籠括一切而幽隱未現,他人對此是未之知的。根據《太玄》排列組合的規律,初一爲“思之微”,即人的思索之始萌微弱階段。由此可知這裏説的“昆侖旁薄,幽”,是説賢人君子之思,此時尚處於始、微狀態,故曰幽。但此時的思是無所不包的,故曰“昆侖旁薄”,意謂其思籠括一切事物,但幽隱不現,不表現出來,外人並不能知曉其人所思的内容。
揚雄又在《太玄·文》中引用《中首》此句另加解釋,綜合起來,其意更明。《文》説:
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
曰:“賢人天地思而包群類也。昆諸中未形乎外,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故曰幽。”
又説:“昆侖旁薄,大容也。”
“昆侖旁薄,資懷無方也。”
這都證明揚雄的意思是説賢人之思籠包天地萬類,大容資懷,無方無盡,然而其思昆(混)於中心而不現於外,獨居獨思,幽隱難漏。這正是古代哲人深沉思索世界根本之道的寫照。要對揚雄這一説法進行闡釋,還不能停留在此一步,於是又根據黑格爾的説法加以進一步的闡釋,以求出其中的“應然”之意。
黑格爾在《小邏輯》第三版序言説:“愈徹底愈深邃地從事哲學研究,自身就愈孤寂,對外愈沉默。”又説:“以謹嚴認真的態度從事於一個本身偉大的而且自身滿足的事業(Sache),只有經過長時間完成其發展的艱苦工作,並長期埋頭沉浸於其中的任務,方可望有所成就。”(8)[德] 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0頁。
黑格爾的説法,與《太玄》此語甚爲相似。由此可以證明揚雄所説的話,其應然之意蓋謂古人的哲學思考籠括一切,獨思不現,憂樂兼之。可是現代人往往鄙薄古代人思想的籠統含混,認爲那種思想有欠清晰,不够完滿。其實,世界的根本之道,古人無法説清楚,現代人也無法説清(9)正因爲如此,所以西方20世紀的哲學轉向,就從思考論證哲學的本體問題轉向到論證這類問題的語言學和邏輯學上來,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思想家從二千多年的思想史的實踐中認識到,對於哲學的本體論問題是無法説清楚的。而他們之所以如此,又是因爲哲學家們論述問題時的語言和邏輯還存在着不少没有解決的問題,所以要從語言學和邏輯學上尋找突破。。古代人的這種廣含概括性的思考,所注重的是世界和事物的本質大道,而不是糾纏於問題的細枝末節,可以説這正是哲學思考的特性。若皆清晰具體,那就不是哲學的方法與理論,而是具體科學的研究與理論了。如老子的道、揚雄的玄、黑格爾的絶對精神等,人們可以給它一個具體的形象、細節的描摹和準確的規定嗎?所謂世界的本質、物質、規律諸語,也都不是可以具體想見其形象的。但它們是客觀存在的,普遍有效的,同時又都是抽象的。若無籠括一切的思考,怎會認識到這一類籠括一切的根本之道?哲學既是對於一切存在(包括物質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的普遍本質的思考,從根本上説,就不能不是這種籠括一切的思考。古代人早在幾千年以前已對世界萬物的普遍本質進行了深刻思考,得出了卓越的結論,時至今日,人們仍然不能推翻它們,只能予以補充、糾正,或予以更精緻的解説而已。譬如現代人批評老子的道,但現代人並不能否認世界存在着一個根本之道——無論説是本質,説是規律都無不同——存在於客觀之中並發揮着作用,道是客觀的,無論物質和精神都是客觀存在的,道是超越二者之上的更大的範疇,不可拘於更低的觀念去限定它。
現代人還認爲古人的思想是直觀的,其實直觀就是哲學的抽象方法,對客觀世界及其根本規律的認識,不用抽象是無以見之的。如“道”這類概念,誰能不用直觀抽象的方法而直接具體地看到它?又如對於萬物的認識,也必須是抽象直觀的方法才能得出這樣的概念。透過物象而探索其内其後的不可具體而見的道理,這是一種深思,離了抽象和直觀,也是無法完成的。
通過這樣的闡釋,就把揚雄《太玄·中首》所闡述的哲人思考的特點揭示出來了,而這是《太玄》並没有直接説明的,只是用一種特定的古代語言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而現代人可以通過其他不同的理論學説來對《太玄·中首》的這一思想進行闡釋,由此説出其中的應然之意。
從本然到應然,應該是現代諸子學研究上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研究者從更廣泛的學科理論與思想方法予以實踐,不能局限於某種固定的學科體系進行單方面的研究與分析。而且所謂應然的闡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時代與社會的發展進步,隨着各學科的學術研究不斷發展而逐步成熟和完善起來的。但這一任務則不是不可懷疑的,也是必須由現代的研究者們努力去從事和完成的。
三、 從主張到理據
在現代的諸子學研究中,還要注意一個問題,即從主張到理據的問題。所謂主張,是指諸子著作文本中提出來或論述到的各種思想觀點及其主張。所謂理據,是指這些思想觀點及其主張中的理據。理據分爲兩個方面,一個是理由、依據,一個是根據理由和依據闡發爲思想觀點與主張的邏輯。理由與依據,在諸子的論説中可以根據其文本而找出,但邏輯則是文本不能充分説明的,所以必須由研究者根據諸子論説的著作文本加以分析,從中析出諸子闡述自己的思想觀點主張時的内在邏輯。
對諸子論説的主張中含有的邏輯的分析與證明,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必須要研究者具有扎實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相應的豐富知識。邏輯本身是現代西方學術中非常重視的一門學科,而這在中國歷史上的諸子學者那裏並没有清楚的概念。但他們在闡述自己的思想觀點和主張時,仍然遵循着一定的邏輯,不然就無法得到讀者的理解與贊同。
但這種邏輯往往是隱性的,並没有像現代邏輯學那樣給出明晰而完整的邏輯推理過程以及使用概念時的内涵定義與外延説明。因此研究者在這種不給予充分的邏輯證明的思想觀點及其主張面前,必須經過研究者自己給予嚴密清晰的邏輯分析。
只有把諸子論説的思想觀點及其主張中含有的邏輯梳理清楚,才能對它的思想觀點及主張的理由與依據給以明確的認定。而這兩方面的考證與梳理,是現代研究者研究歷史上的諸子的思想觀點與主張時必須完整予以分析與思考的,不能隨意缺少和捨棄之。
因此,仔細地完整地分析與論證諸子思想主張中的理據,是現代諸子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而且是難度很大的問題。需要研究者具備足够的思維訓練和知識儲備。
而對諸子思想觀點及其主張的理據的深入全面的分析梳理,又是使現代學者研究歷史上的諸子時從歷史到現代、從本然到應然所不可或缺的步驟。尤其是對諸子思想的應然層次的研究,如果能從諸子的思想主張的理據入手加以疏證,才能保證關於諸子思想主張的應然的研究的可靠與準確。
筆者在2001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地精魂——楚國哲學》中曾分析了范蠡的行動哲學的思想主張,重點探討了范蠡的行動哲學中的理據與邏輯。
范蠡是楚國人,他和朋友文種到越國幫助勾踐治國、用兵、復仇,他並没有把自己的思想主張寫成一部著作,而是通過與勾踐的對話而不斷表達出來的。根據他與勾踐的對話,我們知道他提出的治國主張是三項原則(10)所據文獻資料是《國語·越語》《吴語》的相關内容。:
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
爲什麽他認爲治國需要三項原則,他馬上解釋其中的理由: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這説明他認爲治國者必須解決三方面的問題,國與天、國與人、國與地。他的這一主張的理由是: 一個國家的存在與安全,在古代社會條件下,是與天、人、地三者密切關聯的,三者都是國家存在與安全的重要因素,一個都不能忽略和輕視。
作爲現代的研究者來説,如何分析其中的邏輯呢?
對於天,首先應該理解爲自然環境及自然規律。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正確認識國家所處的自然環境以及自然環境發展變化的根本規律。因此,在處理國家與天的關係時就要以持盈爲第一原則。所謂持盈,就是道家老子所説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以及“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就是滿,治理國家要符合這個國家所處的自然環境所給予的條件,不能不顧這種自然條件而一意孤行。這是持盈的一層意思。不欲盈,就是治國時要讓各項措施不達到極端盈滿的程度,包括不能富貴而驕,要能功遂身退等。這都是持盈和不盈滿的原則的規定,治國者必須遵守之。所以范蠡認爲治國時處理與天的關係,要遵守持盈即不欲盈的原則。
范蠡在爲越王説明持盈與天的道理時,針對越王欲搶先進攻吴國的想法,認爲越王的這一決定是不符合持盈原則的,其理由與根據是“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其中的邏輯是: 人的作爲不能與天(自然)的規律相違背,天時不到,有些事就不能做。在這裏,還把國家與人的關係問題一併説明了。治國者做事要符合“天時”,即自然客觀環境的條件與形勢。不能不顧天時情況而盲目有所作爲,采取一些冒進的行動。這是治國要持盈與天的理由,其根據就是天時。而同時又要顧及到人的問題,所以又説“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是不可取的。把與天和與人兩個因素綜合起來考慮,越王想搶先對吴國采取進攻行動,既不符合天時,也不符合人事的條件。人事的條件就是“人事不起”的意思。放在這裏,作爲范蠡主張的一個要素,其邏輯是: 治國者要做某種事,必須得到人們的回應與擁護,才能把這件事做成做好。如果人事不起,即人的因素還不够,那麽即使天時已到,也是不能貿然采取行動的。
如果既不合乎天時,又不合乎人事條件,就盲目采取行動,那就是“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由此可知范蠡持盈的主張的理據就是既要不逆於天而合乎天時,又要得到充分的人事方面的條件,使治國者的行動與國民的意願相“和”。這樣看來,范蠡的治國主張之理據在於國家及其行動與天、人的相互關係,其邏輯在於治國及采取某項行動必須符合天時條件與人事條件,若不符合,就不能貿然采取任何行動,尤其是對外用兵這種對於國家來説特别重大的行動。
范蠡治國主張中的持盈與天的原則,本質上是與老子的思想一致的,如《老子》説“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等,這又説明范蠡治國主張的持盈原則的理據之一是道家的老子思想。他之所以以道家的老子思想作爲自己幫助越王治國以求向吴國復仇的決策的理據,其中的邏輯是他已認真研究過道家老子的思想及其中的主張與邏輯。這也可看作范蠡治國主張的理據與邏輯的來源之一。
此處范蠡還明確説明了“持盈者與天”原則的根本理據是“天道”: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所謂天道,就是自然規律。自然事物如果滿盈就必然會有溢出的後果,而溢出就是平衡狀態的破壞,是自然界對一切滿盈狀態的懲罰。所以治國者要遵守盈而不溢的天道,即把滿盈保持在不至於溢出的程度,從而避免溢出的災禍。根據這一理據,范蠡的邏輯就是: 因爲天道盈而不溢,所以人的做事(包括治國)就要“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進一步闡釋之,就是人道要與天道一致,不能違背天道。前面明確説天道如何,後面則省略了“人道”二字,而説“盛而不驕”等。這裏面的邏輯就是人道必須符合天道,必須遵守天道。
如果進一步進行分析,還可以看出范蠡這些主張中的更深的邏輯: 天(自然)是無情的,所以它能按照天之道行事,而人是有情的,所以人往往不能保持冷静而科學的態度,讓感情主宰了自己的行動,因此人(治國者是人)在成功之時和盛滿之際,非常容易産生驕矜之心,不能保持與天道的一致,而做出不正確的行動。唐代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正是告誡唐太宗不要做出或延續不合乎天道的驕盈之行,可以説是這一邏輯的實際例證。魏徵勸誡太宗的十條,並没有説明其理據,如果聯繫到范蠡的持盈者與天的主張,就可以説這就是魏徵《諫太宗十思疏》的理據。
范蠡在論述“持盈者與天”這一治國主張時,已涉及“與人”的問題,但那還是作爲“持盈者與天”原則的輔助性理據,而在定傾者與人這一治國主張中,則主要説明“與人”原則在治國上的理據與邏輯。“定傾者與人”這一原則主要用於形勢危殆時,這與持盈者與天的理據與邏輯是有所不同的。持盈主要還是要治國者在國力相對盈盛强大時不要頭腦發熱而驕傲狂妄自大,從而不顧後果地盲目地采取重大行動。而定傾者與人原則,則主要是用於挽狂瀾於既倒,穩定即將傾覆局勢的,這正與持盈時的國家狀態相反。所以要闡釋“定傾者與人”的主張,可以發現其主要理據是國家處於虚弱狀態。
所謂定傾,是指國家就要傾覆,如何挽救國家的危急。處理這種情況的原則就是“與人”。其理據就是靠人的因素來挽救國家的傾覆危亡。因爲國家已處於傾覆危急狀態,實際上是因爲没有做到“持盈者與天”的原則,才會有這樣的後果,所以這時的要務是靠人力來挽救國家的危難,而不能再靠天時。其邏輯就是: 挽救國家傾覆危急,只能靠人力來補救天災造成的禍難,因爲此時國家的危難已不能再靠天時來扭轉了。
范蠡還説明了“定傾者與人”的具體辦法,即如何靠人力挽救國家傾覆危急:“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
這樣看來,定傾者與人的邏輯也就清楚了: 當時越國敗於吴國,這就是越國的傾覆危急。要挽救這一禍難,既然不能靠天時,只能靠越國的人力,但這時的靠人力並不是再靠越國的士兵來與吴國作戰,而是靠越國的其他人的力量來挽救越國亡國的更大災難。所以,要向大兵壓境的吴國暫時表示屈服,以示弱的姿態,要求與敵人媾和,以换取生存的餘地,然後再圖後計。這時的與人之措施,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包括越王本人也需要到吴國去爲人質或做更卑賤的事。用越國的人來做這些事,才能保住越國不被滅國,這就是范蠡“定傾者與人”原則的邏輯。
定傾者與人所以能够成功的邏輯還在於: 一是可以讓對方得到滿足,並利用人性中的憐憫心,使之一時心軟,不斬盡殺絶;二是由此可使本國獲得最後一綫的生存可能性。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越國存在並且在將來不斷努力而謀求東山再起。
范蠡治國的第三原則是“節事者與地”,其理據之一,是如《史記·越王世家》的《索隱》所解釋的:“與地”是因爲“地能財成萬物”。定傾是靠人力保住了國家不被滅亡,之後還要努力奮起,以求復仇。怎樣才能達到這一目標?范蠡的理據是靠地的生成萬物的能力來使越國重新復興而變强。地能財成萬物,這是中國古代的常識,所以范蠡以此作爲復興越國的根本辦法,而依靠地能財成萬物的理據,其可行之路是“事”,“事”指越國存國之後應該做什麽。
他把所要做的“事”與“與地”聯繫起來的邏輯説得非常清楚:
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
即土地能容納萬物,給萬物提供生存生長的空間,對萬物一視同仁,無偏無愛,使萬物各自生長,又各有其用。這裏面還有一層邏輯,即告訴越王勾踐,要想東山再起,反攻吴國,一定要有充足的物資基礎,而大地就能提供所需的各種物資。
但如何用大地提供的各種物資,並不是光憑蠻幹就能奏效的,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則,所以范蠡又來説明人應如何利用萬物:
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
而這又是范蠡主張“節事者與地”的内在邏輯所在,即: 萬物可以爲人所用,但人不可違背自然規律而用萬物。所謂自然規律就是范蠡所説的“時”和“事”。萬物的生長都按一定的時節,這就是自然的規律。人用萬物,必須“不逆天時”,不可急功近利,不可揠苗助長,要等萬物按照自然的時節(此即所謂“時”),按照自己的生長規律,完全生長成熟之後(此即所謂“事”),才可加以利用。所以人對萬物的態度,應該是“自若以處”。自若就是自如,自如以處,就是在籌備所需要物資的過程中,一定要不急不躁,按照萬物的自然生長成熟過程,循序漸進,按部就班,不得妄動。
順其自然,也不是一味地等待,啥事不幹,人們要在順乎自然規律的前提下積極組織人力,發展生産,以豐富大地的物資:
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根據這種邏輯,范蠡讓越王勾踐努力調動越國一切勞動力從事人的生産與物的生産,逐漸積聚物質財富與人力資源。堅持一段時間,就能恢復國力,實現復仇大業。
生産發展了,物資豐盛了,人力充足了,是不是馬上就可向吴國發動反攻而大舉開戰呢?並不是這樣簡單。“節事”原則還包括第二層内容:
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則撫民保教以須之。
這裏的邏輯是: 時勢的發展終會走向它的反面,比如原來吴勝越敗,吴强越弱,這是時勢的一種形態,但不會永久如此,事物的發展到達一定的極點,就會向反面轉化。越國在聚集民力,發展生産之後,就會逐步由弱到强,雙方力量對比就會逐步發生變化。這就是“時將有反”。時勢雖然終有反向轉化的趨勢,但要采取行動,則還要等待對方國家内部出現可乘之隙。因爲越國由弱到强,吴國不一定由强到弱,它還具有一定的實力,所以越國雖然力量增强了,與吴國相比,還是勢均力敵,不能貿然開戰。這就要等待吴國内部出現毛病,給越國以可乘之機。這就是“事將有間”。間即間隙,即對方可以鑽的空子。事情的發展,總是這樣的,所以説是“天地之恒制”。恒制可以理解爲常規。作爲一國君主,能知這樣的客觀常規,按照客觀常規進行決策,采取行動,才能得到“天下之成利”。如果對方内部尚未出現裂痕縫隙,没有可乘之機,則己方只能“撫民保教以須之”(須即等待)。這時的撫民保教,就是繼續做好己方的工作,使準備更爲充足,力量更爲强大,待到時機一來,就能在決戰中處於更爲主動有力的位置。
根據范蠡這些説法,可以看出“節事者與地”的邏輯包括“節”與“地”兩個方面,而“節”與“地”又都包含着主觀與客觀兩方面的涵義。
節,一方面是指事物發展的時機或時節,這是客觀方面的涵義,另一方面則是行事有節,不可只按主觀意志,不顧客觀形勢,要順乎事勢的發展,不可超前也不可滯後,等待事物走向反面,等待事物轉化。這是主觀方面的涵義。
地,一方面是指土地包容萬物,爲萬物的生存與生長提供條件,這是客觀方面的涵義。另一方面,是要順乎土地的特性,利用土地産生萬物的客觀規律,通過人的勞動而生産各種物資。這是主觀方面的涵義。
節事原則的另一個邏輯在於: 節事和與地都不是一次性的措施,不可能一勞永逸,二者都是長期的活動,需要持之以恒地進行下去。因爲要讓事物走向反面,促進事物出現轉化,不是一兩次行動,在短時期就可以完成的。生産也好,國家實力的增長也好,都要無限次反復進行,要長期堅持,才會得到成效的。
范蠡節事者與地原則的最大理據在於: 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土地是最爲重要的生産資料,是産生一切物資財富的源泉。一個國家要想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物質基礎。平時的國計民生,要靠土地所産生的物資財富,戰時的軍需戰備,同樣也要靠土地産生的物資財富。而其可行的邏輯在於: 在危難形勢下,通過“定傾者與人”的原則,獲得了苟延殘喘以圖恢復的機會,下一步的任務就是恢復實力,以圖反攻取勝。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靠以土地爲基礎的農業生産,這就是范蠡節事者與地的理據,而如何實現節事者與地原則的種種做法,就包含了這一原則的種種邏輯。
本節以范蠡治國三原則的主張,説明了如何分析其中的理據與邏輯,由此就可以充分解讀范蠡的思想,而把這些思想主張放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就可以從范蠡所説的本然提升到應然,而這樣的分析就能爲現代的諸子學研究提供有益的成果作爲可以參考的資源,這樣才能使現代的諸子學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四、 從分散到整體
分散,是指諸子既爲多家,所説所論都是分散的,並没有集中起來合成一套有系統的完整的思想學説及其觀點主張。這是歷史上的諸子的著作文本及其思想的存在形態之最大特點。
整體,是指現代研究者研究歷史上的諸子的思想學説及種種主張時,不應受這種分散形態的制約,而應通過種種現代的學術研究的科學手段與方法,把諸子的著作文本及其思想學説及主張視爲一個整體,而在資料處理上和内容研究上把處於分散狀態的諸子的著作文本及其思想學説整合爲一個有機的整體。可以按照諸子所論問題爲綫索,把諸子的著作文本及其思想學説與主張等加以資料整理,而使分散的諸子論説綜合爲一個整體,這樣在研究其中的思想内容時,就能融會貫通,把表面分散而實際爲同一問題的諸子學説聯繫起來加以研究與闡釋,這樣就能使對各個諸子的單獨研究提升到整體研究而形成更高更深的視野與見解的層次,避免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的現象,避免盲人摸象的弊病,因此,這是現代諸子學研究必須重視的一個問題。
有關的詳細論述,筆者已經撰述了《論“新子學”的整合研究及其拓新意義——以〈莊子〉研究爲例》的文章,刊登在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辦的刊物《諸子學刊》第十六輯上,有興趣者可以參閲,此處就不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