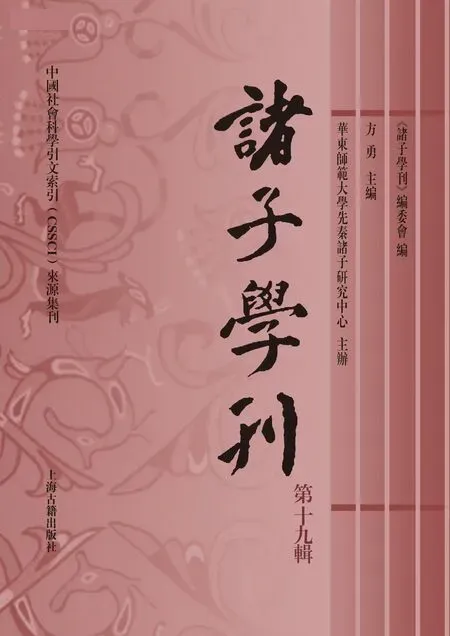宋元金華義理子學探微*
李小白
内容提要 宋元金華學人以融合匯通的姿態對待各派學術,自覺運用義理觀念對子部書籍進行解讀。由於金華學人大多具備理學背景,在闡揚義理的宗旨下,他們對傳世子書重新加以甄别、取捨和詮釋,儒家義理觀念不但成爲統攝、駕馭子學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還在某種程度上使子學走向了義理化的道路。
關鍵詞 義理子學 詮釋 義理 婺學 宋元
婺州(今金華地區)地處浙東,梁朝稱金華郡,隋朝始稱婺州,“唐初爲婺州,又改東陽郡。宋爲保寧軍,元至元十三年,改婺州路”(1)宋濂《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497頁。。兩宋之際,中原文獻南移,婺州名儒接踵,人文薈萃,有“小鄒魯”和“東南文獻之邦”的稱譽。域内“山川之美,人物之盛,風俗之善,爲浙東諸郡最”(2)康熙《金華府志·序》,《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49册,上海書店1993年版,第2頁。,當地人文、自然景觀交相呼應,境内府縣壤地相連,加之北通杭州,便於物資、人員及文化交流,使金華自南宋以降便是士人聲氣互通的集中地。婺學的構成,先是在南宋經金華吕祖謙、唐仲友及永康陳亮等三人各自所創性理之學、經制之學及事功之學奠其基,再由“金華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許謙於宋元之交傳下朱學嫡脉,婺學由此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理學色彩。由金華學人開出的婺州學脉,“自東萊吕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3)宋濂《宋濂全集》卷三十九《題蔣伯康小傳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64頁。,儒學師教風氣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漸次生成。入元之後,婺學更是形成約四代的以師緣爲中心的學脉授受關係,加强了婺學内部的文化聯繫和對外的文化輻射,使婺州成爲真正意義上的東南文獻之邦。子學作爲傳統的四部之學,在婺學濃厚理學色彩的影響下,也有一個義理化的發展過程,這是學界較少注意到的問題(4)歐陽光《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文史》1999年第49輯)及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就婺學以師緣爲脉絡形成的代際關係進行了詳細論述。但從整體角度論述宋元之交金華士人的行止去就等問題仍需參考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及鄒艷《月泉吟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論著。學界較多地從儒家經學、理學等方面論述金華之學,此類著述已有相當的積累。由於子學隱藏於理學的話語場域背後,學者對婺學的子學面向有所忽視。其中,從理學角度論述金華子學問題的專論,僅有方勇《莊子學史》第二、三册(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的部分内容具備參考價值。黄靈庚《宋濂融貫衆説集婺學之大成》(《江南文化研究》第5輯,學苑出版社2011年版)部分内容涉及了金華諸子學,惜其論述不多。。本文就此論説,疏謬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 宋元婺州學人的子學論説
義理子學是一種以理學爲研究子學的指導思想,具有“以理闡子,以子證理”的子學闡釋特色。伴隨着宋代理學的發展,理學對子學的滲透越來越深入。經史兼修的理學家們對子部書籍的論述,深化了近世諸子學的文化内涵。經由理學家對子學的闡釋,子學被納入義理的範疇進行討論。儘管宋元子學哲理性内容得以充實,但子學原有的個性特徵卻遭掩蓋。受元代重視融合匯通的學風影響,子學隨理學“流而爲文”,轉而成爲儒學的附庸。這點在婺州這種區域文化重鎮表現得較爲典型。
如所周知,宋代學術門户較之元代要嚴格得多,不過在經歷了朝代更迭和統治族群變動之後,整個學術的發展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動。原有的學術門户被打破,學人提倡文道並重,主張融合匯通和轉益多師。士人的學緣關係因此得以交叉和發生變異,各派學術團體也呈現出複雜、多元的特點。元代學術也較多的以融合匯通的面目示人。理學上調和、融匯朱、陸成爲潮流,學人吸收各家學術特色,參合變化,打通門户壁壘,轉益多師,選擇了不同於宋人門户謹嚴的學術取向(5)查洪德《元代理學“流而爲文”與理學文學的兩相浸潤》,《文學評論》2002年第5期。。南宋金華學人中以吕祖謙、唐仲友、陳亮等三人成就較大,“宋南渡後,東萊吕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出於一正;説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家”(6)宋濂《宋濂全集》附録二《潛溪録》卷四《經籍考》,第2720頁。,“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吕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吕氏爲得其宗而獨傳”(7)黄溍《黄溍集》卷十一《送曹順甫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婺學又經朱熹弟子黄幹門人“金華四先生”擴大規模,入元後,當地士人大多受朱、吕之學影響,彼此又因親緣、鄉緣、師緣、友緣、政緣等結成複雜的交際網絡,如戴良所言:“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姻親而托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遊從,或以友朋而密邇。”(8)戴良《戴良集》卷七《祭方壽父先生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頁。元代婺州作家群基於這種同門、同里、姻親、同宦等交遊關係,加上轉益多師,打破了原先門户森嚴的師緣結構,使婺學呈現出區域文化整合會通的典型特徵(9)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第22頁。。
不但如此,舉凡元代文學、子學與理學之間,都有融合匯通的態勢。婺州理學“流而爲文”和子學義理化都可視爲這一趨勢發展的結果。清人黄百家評元代金華之學“流而爲文”現象時説,“金華之學,自白雲一輩而下,多流而爲文人。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又言及元中後期以至明初婺學文人化趨勢,“北山一派,魯齋、仁山、白雲既純然得朱子之學髓,而柳道傳(柳貫)、吴正傳(吴萊)以逮戴叔能(戴良)、宋潛溪(宋濂)一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10)黄宗羲《宋元學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727頁。。在這樣的背景下,元代婺學在各個方面都以理學爲思想指引,理學觀念順利融合到子學相關論述之中。我們將南宋吕祖謙與陳亮關於子書的議論拿來,對比元代婺州學人的相關子學論述,從中不僅可以看到子學義理化的發展脉絡,還能得窺元人對子學富於創造性的論述。
(一) 吕祖謙與陳亮針對《文中子》的討論
《文中子》一書是隋人王通門人記載乃師言論的子學著作,“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因是書存世版本互異,陳亮“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以爲王氏正書”,爲《文中子》一書厘定篇次。陳亮從事功的角度對此書内容進行了分析,指出王通“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王通的影響力有限,直到北宋才由程頤發揚其潛德,“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陳亮隨後從《春秋》學的角度論證義利之辨,感慨“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11)陳亮撰,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卷二十三《類次文中子引》,見《鄧廣銘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頁。!從序言可知,陳亮本人對《文中子》一書揄揚有加。
吕祖謙對此並不贊成,他認爲陳亮在《文中子序引》中所言“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尤其針對陳亮所説《文中子》“荀揚不足勝”,“孔孟之皇皇,蓋有迫於此矣”,再有“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等説法,“此類恐更須斟酌”。吕氏分别就此予以辯駁,先討論陳亮言論所用文字是否妥帖的問題,“蓋荀揚雖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又就“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中的“迫”字提出“似未穩”的意見,又將書中所謂“續經之意”拈出,指出范仲淹將世人“誠不足以知之”的内容“忽得之於久絶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並對陳亮對此書的“論次筆削”,“定爲王氏正書”的自信有所質疑,認爲這樣做“蓋非易事,少遼緩之爲善”(12)陳亮撰,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卷二十三《附·答陳同甫書》,見《鄧廣銘全集》第五卷,第200頁。。
陳亮對自己的見解頗爲自信。他“以《中説》方《論語》,以董常比顔子,及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是讀《文中子》者的通病,指出書中模仿《論語》,比類顔子之處,“往往過多”,這説明此書因爲是弟子抄録王通言論而成,其中某些内容如“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説》者抄入之”,目的是“將以張大其師”,卻因此弄巧成拙,“不知反以爲累”(13)陳亮撰,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卷二十三《書類次文中子後》,見《鄧廣銘全集》第五卷,第200頁。。就是因爲原書内容多由摻雜其他内容而成,影響到了學者對《文中子》本書的理解。陳亮對此進行説明,言外之意是説吕祖謙並不能真正理會自己編次《文中子》的本意。
吕、陳二人關於子書的討論,涉及個别子書的版本流衍、文獻辨僞、思想闡述等方面的問題。從陳氏的言論可知,他仍是堅定的以儒學爲立場評判子部書籍,吕祖謙甚至要比陳亮更進一步地維護儒學的尊嚴。陳氏從《春秋》大義的角度分析先秦諸國征戰的歷史背景,而吕氏則就陳氏某些“似未穩”的判斷予以合乎儒家立場的批評。上述内容都反映出吕、陳二人關於子部書籍的基本態度。
(二) 元代婺州學人的子學叙述
元代學術異於其他時代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文倡於下”和“融合匯通”思潮特點。元朝統治者漢文化水準低下,政府在文化上的作爲相當有限,社會治理和思想管控處於較低水準,又因爲長期不舉行科舉,南方士人仕進之途狹窄,士人學在民間,“學道本於經,而旁通曲究”者較爲普遍,學術活動較爲自主(14)許謙《跋潘明之所藏吾丘衍書素書》,《全元文》第25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頁。。在這種較爲自由的學術風氣影響下,婺州學人對子學的叙述發生了某種異於前代的轉移。
在朱學嫡傳許謙筆下,道家莊子與佛家空性之説擁有同等價值,理學家傳統的批判語調發生變化,“學唯爲己……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遊戲,假莊生之寓言”(15)許謙《回潘縣尉啓》,《全元文》第25册,第8頁。,“知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暢。稽理亂,鑒興亡,涉百氏,獵騷莊”(16)許謙《復張子長文》,《全元文》第25册,第13頁。。在此處,諸子與《離騷》、佛家等無差别。我們瞭解到,由元入明的義烏王禕曾論及元代儒學之盛,指出婺州學者金履祥、許謙師徒都可被納入一流的理學家之列,“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17)王禕《擬元儒林傳論》,《全元文》第55册,第771頁。金履祥論及子學的内容儘管較少,但其義理化的史論則“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家”(18)許謙《上劉約齋書》,《全元文》第25册,第21頁。,延續了朱熹、陳亮、吕祖謙的義理化史學思維。金履祥筆下所及諸子著作也視同材料和佐證,並無太多發揮。從其批判司馬光、劉恕等人的史著觀點來看,金履祥對諸子著作持有保留意見,“顧其(指司馬、劉二人)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説,是非既謬於聖人,此不足以傳信”(19)許謙《通鑒前編序》,《全元文》第25册,第37頁。。
從其門人許謙的文章來看,所作文章,注重文采,斐然可觀,語涉老莊或者是模仿老莊文意的文章不少,但他作爲理學家的立場並未因此發生改變,“道備於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20)許謙《跋潘明之所藏吾丘衍書素書》,《全元文》第25册,第39頁。。結合時代背景來看,元初江南士人在經歷了破國亡家之後大多不願仕進,遺民意志較爲突出。士人隱遁於老莊哲學之中,以前賢自況,抒發遺世獨立的隱逸情懷。許謙爲躲避官府對他的徵召,寫出頗具莊子文意的遁詞,“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莫寄於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鸇之虞;方且搶然而飛,嘎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蓋其樂放曠而畏拘檢也”(21)許謙《上宋經歷書》,《全元文》第25册,第16頁。。再有,直引《莊子》文句婉拒徵召,“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干青霄,薄飛鵬,不爲蜩鷽之也幾希矣”(22)許謙《上李照磨書》,《全元文》第25册,第17頁。。
類似許謙這樣經歷過宋元鼎革的故宋遺民,寧願在殘山剩水中以道自適,也不願接受元廷的辟舉。這種情況在元初江南頗爲普遍,如浦江遺民方鳳與吴思齊、謝翱等人曾仿照科舉程式,組織以“春日田園雜興”爲主題的詩歌聯賽,將儒道合一的代表陶淵明作爲吟詠對象,表達不仕新朝的遺民立場。他們的精神源泉來自老莊,這也能回答爲何許謙慣於引用《莊子》作爲他婉拒官府徵辟的理由。莊子的精神哲學成爲這一時期支撑婺州學人的精神支柱。元初遺民群體寄情山水詩酒,四處遊歷,聯絡故交,借此抒發因個人遭際而産生的憤懣與艱於治生的無奈。這一時期的金華作家,多有借老莊、禪理排遣的詩文,如方鳳的一些詩句,“人生本來浮”“大觀物物齊”“吾心太虚闊,倘然萬象具”以及“盆歌疏達慕莊生”“手把南華讀一過,詩思徒湧如春波”,甚至有“不惜逍遥投杖屐,何妨磅礴解衣冠”的曠達文句(23)方鳳著,方勇輯校《方鳳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8、39、48頁。,着實可見莊子的精神已然融貫於方鳳的生活世界,成爲他能够從破國亡家的切己苦痛中挣扎而出的精神動力。
歐陽光認爲,分析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構成,可結合師緣關係劃分爲四代,首代以方鳳爲盟主,謝翱、吴思齊等人爲核心的故宋遺民作家;第二代則是入元後成長起來的方鳳門人群體,其中以黄溍、柳貫爲核心,包括吴萊、方樗、方梓等輩;第三代婺州學人臻於鼎盛,湧現出以宋濂爲盟主,包括王禕、胡翰、戴良等核心成員的婺州作家;第四代則是以宋濂弟子寧海人方孝孺爲盟主的一批學人(24)歐陽光《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文史》1999年第49輯。。徐永明在此基礎上,按照代際關係,分别開列出婺州作家群的簡歷,便於勾勒彼此複雜的交遊關係(25)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第4~8頁。。隨着故宋遺民的陸續凋零,婺州二代學人崛起,金華學脉完成代際過渡。其中像黄溍、柳貫、吴萊等人活躍於元代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他們的社會身份發生轉化,遺民性降低,加之元朝重開科舉,許多人不僅接受了元朝的官職還不遺餘力地推行所謂“盛世文學”,婺州文風因之發生改變。
元人重視反思宋亡教訓,對理學的空疏有深刻認識,“以學術誤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辭以自解矣”(26)謝枋得《疊山集》卷六《程漢翁詩序》,《四部叢刊續編》本。,“道學之名立,禍天下後世深矣”(27)郝經《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全元文》第4册,第158頁。。元人批評理學空疏,提倡經世之學的文章不勝枚舉。整個元代的文化政策與政治環境以實用主義爲立場,理學所謂天理性命之説並不爲統治者所欣賞。學者變爲文人是大勢所趨,越早與政治結合的學術流派,其文人化也就越早。即便是堅持隱居不仕的婺州學人,一旦其後學預備參加科舉或走入社會,流爲文人也是不可避免的。理學在元代與其他學問相互浸潤,原本相比於理學地位較低的其他學問如諸子之學的地位由此抬升。元代中後期士人研習子部書籍漸成風氣,如柳貫,從其“幼有異質,穎悟過人……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可知柳貫於子書不廢研習,經史子集全然不廢的博學傾向似已成爲婺州學人的共識。柳貫重視化用子書内容入詩文之中,入詩者,如“吹萬豈其情”,“太上乃忘言,吾歸抱吾素”;入文者,如其與危素的書信中所談,“願一求之群聖人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形之歌詠,自然適夫性情之正矣”,明顯可知柳貫以儒家典籍爲根本,參合諸子,廣覽博收,充分進行經子互動的義理化子學觀念。他仍是基於理學的立場,理學爲體,諸子爲用,目的是借經子互動進入所謂“光明博大之域”(28)柳貫《柳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13、363頁。。所學内容雖然龐雜,卻是柳貫進入理學“光明博大之域”的重要手段。諸子等學在此語境下是作爲“術”的角色而存在,並非柳貫心中的“道”,道術關係本不對等,明顯可知其立論的目的所在。
吴師道關於子書的若干學術筆記值得重視。吴氏的子學觀點一本於朱子,“吾之所信,則有朱子之評在”(29)吴師道《書揚子後》,《全元文》第34册,第196頁。,並“因朱子之言”爲立場,評析諸如《子華子》《荀子》《揚子》《文中子》《太玄經》等子部書籍。吴氏評析此類書籍的基本方法是從文獻本身出發,參合諸如二程、朱熹、葉適等人意見,分析所見文獻的版本及其内容是否“牴牾乖剌”。舉吴氏辨析《子華子》一書爲例,吴師道先引朱熹《與杜叔高書》稱《子華子》一書有“非常可笑者”,專意“考朱子疏辨其可笑之實”,而對那些認爲《子華子》一書“爲是者之枉錯其心”,爲此吴師道先從朱子、晁公武二人以爲是宋代士人僞作的原因出發證僞,“因其中多《字書》淺謬也”。《字説》本爲王安石所撰,由於其中有較多臆測牽强的解釋,頗遭學界詬病。但吴師道並未從文字本身考辨此書,而是選擇就《子華子》所涉内容進行辨僞,“愚謂其僞之顯然易辨者,孔子遇程子傾蓋見《家語》,子華子説韓昭僖侯見《莊子》”,二事經吴師道分析後,指出“戰國去孔子世遠,二人而合一;苟以《莊子》爲寓言,則陸德明云魏人者,必非妄也”。此時,吴師道將葉適異於常人的觀點拿出,説葉適“最尊信”此書,對古人所非者,葉適則以爲正確,這令吴師道很不解,“不識其何説也”。再如此書的後序作者,及文中所引《吕氏春秋》的内容,吴師道判定爲“依托爲之”,“剽掠可以驗也”,最終證實朱子所言的正確,“輒因朱子之言而摭其遺”(30)吴師道《題子華子後》,《全元文》第34册,第130頁。。不過,四庫館臣提供的意見同樣值得重視。四庫館臣肯定此書爲後世所造,但不同意前人一概否定的極端態度,“今觀其書,多采掇黄、老之言,而參以術數之説”,儘管在成書時,作者故意“掩剽剟之迹,頗巧於作僞”,但整部書與儒家觀點頗爲相合,“然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詭於聖賢。其論黄帝鑄鼎一條,以爲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土階一條,謂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雖稍涉曼衍,而縱横博辨,亦往往可喜”。是書“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托其名於古人者”,最後肯定此書的價值,“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彩,辨其贋則可,以其贋而廢之則不可”(31)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子部雜家類,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07頁。。
我們也注意到吴師道會自覺按照理學的觀點分析子書,如其對《荀子》的判讀就反映了這一點。吴氏“因讀《史記》諸書紀荀子歲月而有所疑”,參考唐仲友關於荀子年歲和《荀子》一書的考定,並不以爲然。唐氏所考荀子年歲,“蓋立一説”,吴氏批評唐氏關於“性惡”的説法,“唐論澀縮而不敢盡,末謂李斯、韓非非師之過”,認爲唐氏“大本已失”,“何其異也”,最終上升到從“心術之微,固可即此而見矣”的義理角度進行批判。
從更明確的義理角度分析子部書籍的婺州學人,當以吴萊爲典型。宋濂在《浦陽人物記》中提到吴萊的子學修養,“翻閲子書百餘家,辨其正邪,駁其僞真,援據爲的切可傳。四方學者一時多師之”(32)宋濂《宋濂全集》卷九十六《浦陽人物記》,第2269頁。。吴萊善於從經史並重的立場辨析諸子,他的立論依據一出於史,所以顯得證據確鑿,頗具説服力。如其討論諸子生成的歷史背景時説:“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唯磨厲其舌,肆爲讒説,莫之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唯以利害相勝。”不僅得出“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的感慨,還倡議對諸子之學僅作瞭解其人其事即可,不必深究其文,“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33)吴萊《吴氏戰國策正誤序》,《全元文》第44册,第40~41頁。。吴萊的經學修養奠定了他考察先秦諸子的基礎,這點要結合其學問出處來講。吴萊學問的根柢在《春秋》經,較專注於史事考辨,“年二十四,以《春秋》舉上禮部……著書有《尚書標説》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説》《胡氏傳考誤》未完”,從中可知其學問出處(34)宋濂《宋濂全集》卷九十六《浦陽人物記》,第2270頁。。
儘管吴萊對先秦諸子持保留意見,但從其行文與閲讀來看,明顯可以感受到先秦諸子對其文風的形成所産生的影響,“年未冠,以朝廷有事倭夷,撰《論倭》千七百言,議論俊爽,識者謂有秦漢風”(35)同上,第2269頁。。吴萊所作《形釋》《改元論》《秦誓論》等論文,從其文氣、語言、風格等角度考察,秦漢文風對其影響頗深,側面反映出吴萊對先秦諸子的熟悉程度,符合傳記之中對其諸子閲讀史的記載。例如吴萊頗不贊成南宋以降士人諱言或倡言兵法的兩歧態度,“縉紳逢掖之士,浸恥言兵,兵日弱矣”。一是“苟取古人之糟粕,而强謂我知兵,是即趙括之不知變也”,二是“以孫、吴、韓、白韜略機權而言兵”,對兵家從權謀機巧討論兵法的方式不能苟同,要求“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提倡“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36)吴萊《新安朱氏新注黄帝陰符經後序》,《全元文》第44册,第61頁。。吴萊還試圖調和儒家與諸子之間的關係,先是回顧“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横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爲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的歷史背景,指出後世學者“或欲援儒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儒”的做法,不僅混淆了學派之間的區别,還造成後世引諸子思想入儒學典籍的做法。實際上,吴萊從古今人物共通的觀念角度,説出“必也,天下人心之義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内外,雖欲一混而大同之,亦可也”,意圖從義理的角度調和諸子内在的矛盾(37)吴萊《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全元文》第44册,第71頁。。吴萊這樣説似乎僅限於口號,其本人並没有提出妥善方式解決經、子之間的内在分歧。
吴萊充分意識到先秦各國紛紛推行富國强兵戰略的目的,各國對鼓吹施行仁政的儒家學説並不在意,“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説”(38)吴萊《讀公孫龍子》,《全元文》第44册,第127頁。。在吴萊看來,荀子之學也因其靈活調整策略而成爲子思、孟子所譏諷的“小儒”,“猶習於戰國之俗,而不純於堯舜周孔之道”,“或言王,或言霸,或言强國,務使世主擇焉以爲政,則又時變其道,以曲從之”。這種靈活的方式尤爲吴萊所不齒,“道可變乎?是徒苟冒而寙惰,繆學而飾説,既病乎人,且厲己也”。吴萊承認“戰國之世,去聖日遠,而諸子之説紛起。私意揣摩,强辨相勝”,結果導致“荀卿子號爲儒者,而未純於聖人”,荀子弟子輩又“自叛”於儒,“視儒者之學,輕而非也。亦陷於刑名、法術之末”。吴萊認爲荀子應對這一狀況的出現負責,“荀卿子亦不爲無過也哉”(39)吴萊《讀韓非子》,《全元文》第44册,第127頁。!韓非師從儒者卻自陷於法家之説,荀子作爲其師,應負有一定的責任。而且,還認爲荀子遠離了孔子之道,“至於荀卿,則知一返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爲惡,豈不遠吾聖人之道哉”(40)吴萊《讀孔子集語》,《全元文》第44册,第128頁。!
吴萊對先秦子書有着深刻的閲讀體驗,並能就所讀内容作出相應判斷。這種判斷也是基於維護儒家固有的對文王、武王仁義形象而做的辯護。如其就《吕氏春秋》中談到“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王即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就此提出與《史記·伯夷列傳》中不同記載的疑問,“由是伯夷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隨即通過排比史事,尋求《吕氏春秋》與《史記》不同記載的合理化解釋,而所謂合理化解釋類似從義理角度的推論,前提認定武王派遣召公奭、周公旦二人與殷人微子、膠鬲的結盟爲真,以此證明伯夷歸周的合理之處。儘管吴萊是從史事排比的角度論證此事,但分析其内在旨趣則明顯可以感受到理學家特有的思想律動。
吴萊關於先秦子書的論述,試圖從自身的生存情景中尋求對先秦歷史情境的真實理解,所以我們看到吴萊的關於子書的閲讀貫徹了“辨其正邪,駁其僞真,援據爲的切可傳”的原則,其中史學考辨的内容占了多數,所得出的結論也因其充分論證而顯得較爲可信(41)宋濂《宋濂全集》卷九十六《浦陽人物記》,第2269頁。。很明顯,吴萊試圖通過辨析先秦子書賦予理學一種外向型的價值取向,在閲讀和評價子部書籍等問題中取得與理學内在觀念的某種契合。尤其在承襲吕學經史並重的學術理念的基礎上,以史學辨析的方式,尋求一種通過社會和禮儀制度的變遷,表達從無序走向普遍秩序的社會關懷。這是吴萊試圖以學術的道德實踐性統合先秦諸子,實際上也是義理化思維在其子書閲讀過程中的顯著印記。
針對先秦諸子進行義理分析是金華學人的典型判讀方式。作爲婺學的集大成者,宋濂相關文章的内在脉絡較爲明確地貫徹了這一點。實際上,宋濂的理學修養遠超其文學成就,但他的理學家面目卻往往被文名所掩蓋,不過從其“吾心與天地同大,吾性與聖賢同貴”一語便可知他的理學根柢(42)宋濂《宋濂全集》卷九十《自題畫像又贊》,第2138頁。。方孝孺對乃師也有這樣的評價:“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絶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43)方孝孺《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先生像贊》,見黄靈庚校點《宋濂全集》第5册,第2544頁。梳理宋濂所屬的學緣關係,宋濂兼祧吕學、朱學、事功之學等學脉,可視爲婺學的集大成者。宋濂本人對先秦諸子的意見及其個人子學著作,是討論他在子學義理化方面的重要參考。
我們注意到,婺州學人一般將性理之學作爲評價戰國諸子的標準,以此衡量諸子彼此間自相矛盾的説法。柳貫、黄溍、吴萊等人以六經爲立場的子學評判標準影響到了宋濂。柳貫主張爲學應“求之群聖人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44)柳貫《柳貫集》卷十三《答臨川危太樸書》,第363頁。。黄溍從經學角度評價其他學問的立場更爲堅定。宋濂曾與同學論學時回憶黄溍的學術立場,“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即黄溍)嘗言之”,而且所謂“聖人之文”,亦即“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45)宋濂《宋濂全集》卷三《華川書舍記》,第75頁。。在此立場上,宋濂强調“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46)宋濂《宋濂全集》卷二十三《白雲稿序》,第471頁。,經學構成了宋濂思想的基本底色,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考慮到宋濂思想譜系的複雜性,他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反思個人的學術歷程,在涉及子學的認識方面有必要在他更爲複雜的思想圖景中展開。宋濂59歲時曾説:“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爲事,自以爲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踰四十,輒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踐之。五十以後,非唯悔之,輒大愧之;非唯愧之,輒大恨之。”(47)宋濂《宋濂全集》卷二十四《贈梁建中序》,第492頁。宋濂年少時熱衷古文辭,於書無所不讀,三十歲以後轉變學問方向,年近五十對自己又有了更爲清醒的認識。對比他的自傳,明顯可以看出宋濂學問轉换的輪廓,先是以六經大義作爲“存心”“著書”“言談”的根本,中年後轉换到服氣養生的道家之學,期間對佛教也有深入研究,用作韜晦之資(48)宋濂《宋濂全集》卷十六《白牛生傳》,第294頁。。
宋濂融合佛道思想入文便是這一思路的直接反映。對待道家學説,宋濂將之納入所謂“列仙之儒”的範疇予以解釋,“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書》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修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蜎子與夫兵謀之書,咸屬焉”(49)宋濂《宋濂全集》卷八《混成道院記》,第162頁。。至於説佛教,宋濂三十二歲便有“閲盡一大藏教”的特殊經歷。他的佛學修養遠超同儕,並爲當時知名禪僧千岩元長所贊許,二人結爲方外之交長達三十餘年,“締爲方外之交垂三十年……雖纏於世相,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最深”(50)宋濂《宋濂全集》卷七十三《普利大禪師塔銘》,第1755頁。。
宋濂分别在48歲、49歲遭遇戰亂時完成了《龍門子凝道記》和《諸子辨》兩書。有學者指出此書並非單純意義上的辨析諸子著作真僞的作品,而是反映儒家心性之學,講究修身養性,傳承金華學脉的代表作(51)黄靈庚《宋濂的闡述性理之作——〈龍門子凝道記〉〈諸子辨〉辯證》,《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從這個意義上説,宋濂所作兩書的目的是借論述諸子學的形式,闡發自身的儒學精神,也就是子學義理化的另類表達。宋濂在《諸子辨》文末題記中説:“作《諸子辨》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别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儒家者言。”(52)宋濂《宋濂全集》卷七十九《諸子辨》,第1915頁。宋濂辨析諸子,將諸子與儒學之間親疏遠近的關係作爲排列、評價子書價值高低的標準,目的是闡述性理,從而服務於儒學。分析《諸子辨》也能清楚地看到這一意圖。
《龍門子凝道記》一書頗具子書性質,以至於四庫館臣列此書爲“道家言”。顯然四庫館臣没有充分理解這一時期理學思維下子書義理化的時代特徵,僅就字面意思便作出了判斷。宋濂追求從儒學大義的角度理解六經和所讀典籍,從其“年近五十,絶不事方策,日唯熙熙,仰觀俯察,若有所自樂者”(53)宋濂《宋濂全集》卷九十五《龍門子凝道記》,第2236頁。,這種化有形之典册入無形之心性體悟之中的做法,不正是理學家心性之學的典型要求嗎?這一時期的宋濂,心性之學已臻於爐火純青的境界。所寫《龍門子凝道記》《諸子辨》二書,正是宋濂心性之學的典型呈現。舉若干實例進行論證,如其在《龍門子凝道記》卷末題記所言:“皆一時念慮所及之言……當求聖人之遺經,益精研而箋記之,以贖前者不知妄作之罪。”(54)同上,第2238頁。明人徐禮分析宋濂的學脉傳承之後,所言更爲透徹:“觀其自謂濂、洛之學,鼎立爲三: 武夷之學,則主於知行;廣漢之學,則嚴於義利;金華之學,則自下學而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其一也。其所憂則有之,憂之如何?如孔子而已。觀其在龍門之日,著書立言,有及乎此,雖若不敢以斯道自任,亦見其有不得而辭者矣。”(55)徐禮《龍門子凝道記序》,《宋濂全集》第5册,第2708頁。宋濂以儒家性理之道自任的態度不僅昭然若揭,而其理學家的精神底色更是顯而易見。
至於説《諸子辨》的性質,歷來有所謂“辨僞”和“明道”兩歧的説法。實際上,所謂辨僞之説並没有深入瞭解宋濂撰寫此書的真正意圖。如果從宋元以來金華學脉的發展角度看待,《諸子辨》作爲一部“衛道之書”而非“辨僞之書”的性質就顯而易見了。“《諸子辨》一書並無辨僞之意,它所講的‘辨’,並非真僞之辨,而是儒家的正宗思想與諸子‘邪説’之辨,是以儒家思想爲旨歸,決定對諸子的存留取捨,使道術咸出於一軌。”(56)王嘉川《布衣與學術》,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07頁。宋濂辨析諸子的立場昭然若揭。宋濂使道術咸出於一軌的意願,因爲得到朱元璋的支持,而落實到明初的國家改革活動之中,明初國家意識形態的强化與金華學人這種理念存在明確關聯,值得從朝代更迭與士人思想觀念存續的角度予以深度闡發。
二、 婺州學人子學闡釋的義理特徵
諸子著作在金華地區的收藏與閲讀相當普遍,反映了子學在當地具備的良好基礎。宋元之際胡長孺曾提及地方府州縣學大多藏有子部書籍,“郡縣之學皆有尊經閣,以藏群經,與凡訓詁注釋之書,以及諸子、史論、文集亡慮數千萬卷,少者亦數千百卷”(57)胡長孺《尊經閣記》,《全元文》第13册,第544頁。。胡氏所言不無誇張,但從元朝公私藏書的情況來看,元代藏書量遠超前代,萬卷以上的藏書家,北宋有28家,南宋有30家,元代有37家,見於文獻的藏書家,北宋62家,南宋64家,元代則有72家(58)劉洪權《論元代私人藏書》,《圖書館》2001年第4期。。士人對子書的閲讀也呈普遍趨勢,許謙曾不無自得地描繪當時士人的讀書生活,“學唯爲己……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遊戲,假莊生之寓言”(59)許謙《回潘縣尉啓》,《全元文》第25册,第8頁。。元人讀書較少功利心,學在民間,更能體會讀書之樂,涉獵也就更廣,對子部書籍的閲讀與理解趨於多元,但整體而言,理學思維下的子書詮解是主流,從而有助於區域性文化思潮的分析成爲可能。
宋元金華義理子學特徵主要表現於以下幾點:
其一,以經學爲基礎,統御子學。與宋濂同在黄溍門下的王子充,在其華川書舍中,“上自群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不過王子充這一讀書方式並不爲宋濂所支持。宋濂從“文”與“道”的角度論證如果致力於諸子之文將會對“先王之道”産生不利影響,“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殊”,然後從管子、鄧析、列子、老子、墨子、公孫龍子、莊子、慎子、申子、韓非子等作文特點出發,指出戰國世變之下“文日以多,道日以裂”,“各以私説臆見嘩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爲文”,達不到宋濂所謂六經之文的標準。批判諸子之文的同時,宋濂提出了作文標準,“故濂謂立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宋濂的觀點得自黄溍、吴萊等人,在他們看來,性理之學視角下的諸子之學,遠不能達到“聖人之文”的經世效果,後世學習諸子之文的作家面對“聖人之文”,“不無所愧”,此外還高揚道統,推舉理學,“上下一千餘年,唯孟子能辟邪説,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唯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60)宋濂《宋濂全集》卷三《華川書舍記》,第76頁。。義理化視角下,諸子之學站到了儒學的對立面,宋濂的這種觀點接續了自宋初邢昺《論語疏》中“異端,諸子百家之書”的立場。
從北宋中期以後興起的以儒家義理爲導向,闡發古代典籍的思潮,較早地出現在史學領域。采用義理甄别史料,並將諸子思想作爲靶向進行批評,即便是司馬光也不能例外。司馬光曾在《史剡》“由餘”條提及秦穆公曾用由餘之言,施行戎狄之策,意圖避免因爲實行禮樂法度而導致的“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的局面,采用戎狄之法,“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最後達到“遂霸西戎”的結果。但司馬光則將經學義理的觀念投射到這則史料上,不僅貶低秦穆公采用胡俗,成就秦國霸業的歷史作用,“治人國家,舍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司馬光將老莊後學作爲攻擊的目標,猜測“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61)司馬光《傳家集》卷七三《史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司馬光直接認爲此事是老莊之徒的虚構,本身就暴露了他論證過程的臆斷之處,與史學求真的立場相悖。這種主觀性的推測,不僅罔顧了由餘所言内亞遊牧部族首領與臣屬之間“淳德、忠信”的真實關係,還有意識地將諸子作爲立論的反面對象,從中可見到北宋儒者對待子學的態度。子學不僅被義理所統御,還是以反面的角色出現。
近代蜀中劉咸炘曾批評:“宋人之於史,本偏重於議論,孫(復)、石(介)、胡氏(瑗)之習既深入人心,而晦翁之學又行於世,故空持高義,以褒貶人品,而不察事勢,乃成宋、元以來之通風。”(62)劉咸炘著,黄曙輝編《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23頁。由史學領域興起的義理化風潮,經過南宋浙東史學的代表,如吕祖謙、葉適等人提倡,經史合併,同歸理學指導。金華學人對子學的研究同樣受這一趨勢波及,子學義理化或者説是經學思維下觀照的子學因此得以展開。從前文對金華學人子學論述的相關梳理來看,子學義理化真正意義上在金華學人中鋪陳開來是在元代,尤其是從金華學脉的第二代人物如柳貫、黄溍、吴萊開始。
義理子學的發展,吴萊可以作爲典型案例進行分析。王東認爲義理史學的興起,與《春秋》學的盛行密切相關(63)王東《宋代史學與〈春秋〉經學——兼論宋代史學的理學化趨勢》,《河北學刊》1988年第6期。。吴萊的學術背景中,《春秋》經扮演了重要角色。吴萊關於部分先秦子書的論述,不僅用義理甄别子書的内容,還將義理作爲判讀、組合和詮釋子書的標準和指導思想。秉持儒家義理,用以判讀先秦典籍,在宋元學人之中頗爲常見。皮錫瑞曾指出,宋人解《尚書》,“專持一理字,臆斷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與其理合者,即以爲是,與其理不合者,即以爲非”(64)皮錫瑞《經學通論·書經》,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71頁。。元代理學流而爲文,突破了宋代學術門户森嚴的情況,理學家轉變角色而爲文人的情況相當普遍(65)查洪德《理學背景下的元代文論與詩文》,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8頁。。這種文人化的轉變儘管有許多時代原因,但由於突破了前代理學自設的藩籬,學者爲提升文章技巧,不得不廣爲涉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宋代以來束縛子書閲讀的理學化主張。宋元學者,尤其是與政治較爲疏遠的金華學脉,重視經學,采用義理統御其他諸學的基本主張並未改變。金華學人認爲子部之學的研讀必須是學者治經而有餘力方能爲之。强調六經重要性的論述,在金華學人的文集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其二,運用義理的觀點闡釋子學,子學成爲儒學的附庸和抨擊對象。宋元金華學人對理學的堅持是一貫的,他們强調義理的存在,閲讀子部書籍也是以義理爲立場,進行多種角度的闡釋。有《春秋》學背景的吴萊,本就注重從義理史學的角度看待先秦歷史。在討論諸子著作何以生成的歷史原因時,吴萊首先注意到“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的歷史背景,從義理的角度批評“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唯以利害相勝”而罔顧義理的做法。把當時流傳的儒學拿來作對比,指出孔孟之學“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册,充衍洋溢,遠而未斬”,因此之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甚至孔門“言語”一科因爲子貢等儒門後學傳播廣泛,對名家、縱横家等輩頗有影響,“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弟代、厲之流”,批評他們的“讒邪之説,罔知義理,而傎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入,固有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感慨“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66)吴萊《吴氏戰國策正誤序》,見《全元文》第44册,第41頁。。這種不但認爲子學與儒學有着派生關係,還從根本上對諸子學術予以貶低的態度,在金華學人中頗有市場。前文宋濂對同門王子充也讀子書的批評態度便是由此而來。
經過宋元學者對子學的閲讀和批判,理學對子學的滲透達到相當程度的自覺。元代理學流而爲文,理學家文人化的趨向相當明顯,金華學人强調從六經的角度作文,宋濂在《六經論》中强調“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天理、人心與六經因此論而達到統一。對諸子文獻的閲讀,宋濂采用考察著録源流,關注材料的來源與流衍變化,對諸子思想内容、文字風格乃至相關史實等内容予以辨僞和評價,其系統的考辨無不是基於性理之學,將儒家義理作爲評判諸子著作的唯一標準。實際上,宋濂對諸子著作的考察,與其説是辨僞的,不如説是借辨析諸子之機,宣揚儒家性理之説,他的《龍門子凝道記》和《諸子辨》透露出的思想主旨正是以此爲基礎(67)黄靈庚《宋濂的闡述性理之作——〈龍門子凝道記〉〈諸子辨〉辨證》,《浙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諸子之學應在儒家經學、理學之下是宋濂的基本態度,“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烏足以爲經哉”,經的地位自不待言,“無所謂學經者”,可以爲聖爲賢,無論是面對政事、富貴、貧賤、患難都能遊刃有餘,“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凖”(68)宋濂《宋濂全集》卷十二《經畬堂記》,第226頁。。經子關係中,子學明顯是作爲對比和批評的對象。
金華學人還將子學的研究與道德修養進行聯繫,他們筆下的子學問題表現出倫理化的傾向。以理學家自況的金華學人認爲,先秦諸子由於背離儒家的倫理觀念而天然地具備了道德“原罪”。這種問題集中凸顯在於諸子的“重利輕義”問題上,“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唯以利害相勝”(69)吴萊《吴氏戰國策正誤序》,見《全元文》第44册,第41頁。。“當戰國之時,士多以遊説縱横、攻戰刑法之説行……儒墨並稱,百家雜説混淆之矣”(70)吴萊《孟子弟子列傳序》,見《全元文》第44册,第53頁。,高揚儒家仁義之説,以此貶低戰國士人的攻戰刑法之説,“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吴、韓、白韜略機權而言兵”,指出“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71)吴萊《新安朱氏新注黄帝陰符經後序》,見《全元文》第44册,第61頁。。依據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説法(72)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524頁。,對待子學中大量强調功利主義的内容,理學家們無不强調從“明道正誼”的角度立論,强調對經學的堅持,反對將時間精力投入到子書的閲讀研究之中,這種觀點在明初方孝孺那裏得到强化,他僅僅是選取子書中某些符合儒家義理的内容,其他的都要燒掉才甘心,如其《讀鄧析子》一文就説,“予擇其可取者二百言著於篇,餘皆焚之”(73)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四《讀鄧析子》,寧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頁。。修養的道德化和功利訴求的完全對立,借由理學家們的一貫强調而走向了極端。
餘 論
理學經過數代人的努力,經史、經子關係皆被賦予了一套帶有儒家義理的價值觀念,組成了中國文化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宋儒試圖將義理加諸他們所要處理的任何問題之上,表現出强烈的懷疑精神和變革心態,從而有别於漢代以來的儒學研究範式。子學本身具備的思想内涵在與理學家所秉持的義理觀念接觸時,諸子原本的思想内涵被掩蓋和改造,甚至在儒家義理的語境下被理學家樹立爲批判的對象。這是經子、經史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的地方。宋代以後的子學,已經是被理學涵化之後的子學,勉强可以稱之爲義理子學。義理子學把原來的子學個性進行了改造,這一特性在宋元金華學人之中有明顯的反映。義理子學是理學家自覺地依據儒家義理觀念,對子部書籍進行甄别、取捨和詮釋,借子書闡明義理,以義理統御子書或將子書進行義理化的批判。金華學人通過對義理與子書内容的往復印證,增强其對義理的體認與理解,從而堅定義理作爲個體生命價值重要支撑的内涵作用。金華一脉學人對子書的詮釋活動,不但明確了子書之於自身價值世界的關係,還能透過這種批判性的精神活動確立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價值體系的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