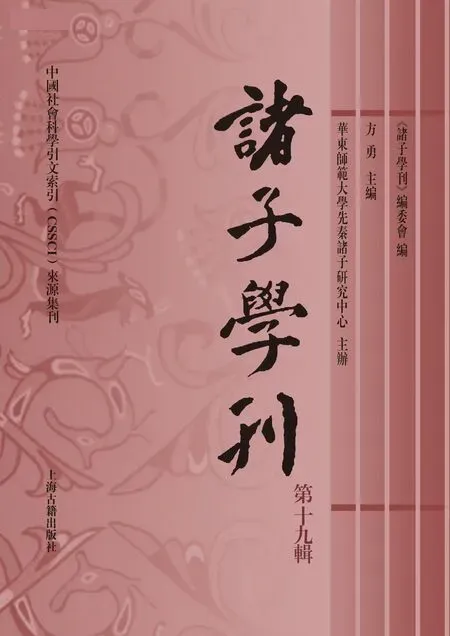“類稱”與“特例”的統一: 先秦諸子的求道之思
陳衛平
内容提要 哲學作爲“類稱”來説,中西哲學具有共同的理論内涵,這就是探討宇宙人生的普遍性原理和探討人類最根本的價值理想問題,中國哲學的最高概念“道”正體現了這樣的理論内涵。就中西哲學作爲“特例”而言,它們的理論内涵則各具特性,康德的哲學思辨聚焦於如下四個問題: 我能知道什麽?我應當做什麽?我能期望什麽?人是什麽?先秦諸子同樣探討了這些問題。即“聞道”“遵道”“志於道”和“成人”之道;這裏略以康德爲參照,論述先秦諸子的求道之思,體現了“類稱”和“特例”的統一。
關鍵詞 類稱 特例 諸子 康德
引 言
中國哲學作爲現代學科從誕生於“五四”時期起,就存在着發生學上的糾結: 用來自西方的“哲學”詮釋中國傳統的思想内容,這樣的“哲學”還具有中國民族特性嗎?如果否認中國傳統思想具有與西方“哲學”相通的理論内涵,中國傳統思想將無法在世界哲學的智慧長河中顯示價值。爲了解開這個糾結,張岱年曾指出,應當“將哲學看作一個類稱”,是包含了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特例”的“總名”(1)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序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頁。。以哲學爲“類稱”的前提,是哲學作爲“類”的共同屬性和本質規定是什麽。這實際上就是何謂哲學的問題,對此儘管有不同回答,但在以下兩點是有共識的: 一是探討宇宙人生的普遍性原理,一是探討人類最根本的價值理想問題。作爲西方哲學典型代表的康德集中展示了這一點。他以思考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表現了前一方面,而“三大批判”的論著則表現了後一方面。中國傳統思想則把這兩個方面歸之於對“道”的求索。熟稔傳統儒學的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哲學家西周,在首先把philosophy翻譯爲“哲學”時,正是這樣以“道”來闡釋何謂哲學:“論明天道、人道,兼立教之方法,稱ヒロソヒ—譯名哲學。”“東土謂之儒,西洲謂之斐鹵蘇比(philosophy的音譯——引者注),皆明天道而立人極,其實一也。”(2)轉引自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的現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0頁。這裏的天道和人道指向的是關於宇宙人生普遍原理,而立教和立人極指向的是確立最高的價值原則。先秦諸子之“道”正是如此。《莊子·天下》,把諸子作爲“道術將爲天下裂”的産物,所謂的“道術”,既是對天下萬事萬物之“宗”(根源)、“精”(精微)、“真”(本質)即宇宙人生本原的探究,又與重建“内聖外王之道”的價值理想相聯繫。就是説,諸子都試圖從不同方面把握宇宙人生的根本性、普遍性之“道”,從不同價值取向彰明内聖外王的價值之道。這意味着哲學作爲“類稱”來説,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具有共同的理論内涵;就兩者作爲“特例”而言,它們的理論内涵則各具特性。哲學的認識宇宙人生普遍性原理和追求真善美價值理想,展開爲一些具體的問題。康德把自己的哲學思辨聚焦於如下四個問題: 我能知道什麽?我應當做什麽?我能期望什麽?人是什麽?(3)前三個問題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第四個問題在《邏輯學講義》中提出。作爲中國哲學根基的先秦諸子同樣探討了這些問題。這借用孔子的話語,就是“聞道”“遵道”“志於道”和“成人”之道,它們構成了先秦諸子的求道之思,由此奠定了中國哲學的基本傾向。這裏略以康德爲參照,論述先秦諸子的求道之思,體現了“類稱”和“特例”的統一。
一、 “聞道”與“我能知道什麽”
康德的第一個問題,是對人的認識活動的思索,如他説的純數學和純自然科學何以可能,即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何以可能等。這在西方哲學是認識論或知識論問題。先秦諸子將認識論與倫理學結合在一起,與康德的認識論和自然科學緊密相關有所不同。孔子主張以學與思而“聞道”,作爲最早的教育家,考察知識如何形成無疑是題中之義。對此他提出了很多影響深遠的觀點。如開篇首章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論語·學而》),認爲完整的認識過程離不開認識(學)和實踐(習)的相互作用;同時在這相互作用中,體會到由成就君子而獲得的人生愉悦;因而此章最後説“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這表明孔子既從闡發認識的過程來考察認識論問題,又將此與認識主體的德性培育相聯繫,顯示出認識論和倫理學結合。此後的孟子、荀子同樣如此。孟子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而“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就是説,認識性與天道,必須盡心即充分發揮理性思維的作用;而盡心的過程則是對天賦的道德“良知”予以自覺反思的過程,“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因此,“學問之道”是盡心即理性思維過程和求其放心即道德自覺過程相融合之道。荀子否定有天賦“良知”,但他也很重視心的理性思維作用,稱心爲統帥耳目感官的“天君”(《荀子·天論》)。但是,“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解蔽》),事物存在着矛盾的兩個方面,而“心術”的通病是只見一面而不見另一面;要去除這樣的“公患”,就需要重視認識主體之“心”的道德修養,“以仁心説,以學心聽,以公心辯”(《正名》)。可見,認識論和倫理學在荀子那裏也有着内在聯繫。
先秦其他諸子的“聞道”之思,同樣體現了認識論與倫理學的内在聯繫。墨子説“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墨子·明鬼下》),以衆人耳目的感覺經驗,作爲判斷事物是否真實存在的認識之道。墨家以“利”爲善(義),以“害”爲惡(不義),而利與害則訴諸喜悦和厭惡的直接感覺,“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得是而惡,則是害也”(《經説上》)。可見,墨家重視感覺經驗具有認識論和倫理學的雙重意義。老子也説“聞道”(《老子》四十一章)之詞,然而“道常無名”(三十二章),作爲萬物普遍原理的“道”,不是名言、概念所能把握的;要認識“道”,必須洗滌心靈這面鏡子,使其毫無污染的瑕疵,“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十章)。這是回歸嬰兒純净初心般的厚德,“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五十五章)。顯然,“道常無名”也是認識論和倫理學的結合。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指出,“緣道理以從事”(《韓非子·解老》),要求認識一般規律(道)和特殊規律(理);而其法家思想正是“道理之言”(《難勢》)。言此道理則涉及道德品性,如苦樂與利益的關係,“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苦”(《六反》);如私情與公正的關係,“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飾邪》)。名家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討論“名”與“實”即名稱、概念如何反映客觀實在的認識論問題,但這關聯君臣倫理。“名實無當”會使得“君臣争而兩明”,即君臣相争而各自顯明勢力;“兩明而道喪”(《公孫龍子·通變論》),即認識名實關係之“道”陷於淪喪。
二、 “遵道”與“我應當做什麽”
康德的第二個問題,主要涉及倫理道德領域,即道德律令對人們行爲的規範性以及這種規範的根據等,這在西方屬於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康德的倫理學以不依賴於經驗的“實踐理性”爲基礎,以强調意志自由爲核心。與此有所不同,先秦諸子是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相結合,凸顯了與治國理政的緊密聯繫。孔子對於應當做什麽的回答是“遵道而行”(《中庸》),即以道作爲行爲規範;而禮是體現道的具體規範,因而一旦禮崩樂壞,就會“天下無道”。所以,他强調“克己復禮曰仁”(《顔淵》)。要成爲仁德之人,就必須遵照禮,因爲禮具體規定了什麽可以做和不可以做;循禮而行的過程就是“克己”即個人進行道德修養的過程。禮也是施政行爲的規範。孔子説:“爲國以禮。”(《先進》)深得孔子學説精髓的有子,發揮老師的思想説:“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學而》)認爲先代君王完美的治國之道,就是無論大事小事都依禮辦理,體現了以和爲貴的精神。孔子用禮來規範個人和國家的行爲,奠定了禮儀之邦以及把個人修身和齊家治國平天下貫通的基礎,關切治國理政的經驗世界,體現了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結合。這樣的結合在孟子和荀子思想中更爲緊密。孟子的倫理學以性善論爲核心,認爲人性本善即人具有天賦的仁義禮智之善端。這是人們行爲的基礎,《中庸》稱此爲“率性而爲道”,孟子稱此爲“由仁義行”(《離婁下》)。然而,這不僅是個體行爲的基礎,也是施行良好政治的基礎,由“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孫丑上》)。仁政注重道德教化,孟子以爲這合乎本善之人性,因而必定深得民心,“善教得民心”(《盡心上》),得民心便能得天下。可見,孟子的性善論是仁政民本政治哲學的基礎。與孟子的性善論相反,荀子的倫理學持性惡論,認爲人生而“好利”“好聲色”等,必須用禮義法度予以矯正,此即“化性而起僞”。荀子認爲以此爲基礎才能“循道正行”(《堯問》),形成正確的行爲。這樣的“循道正行”表現於治國理政就是禮法兼施:“聖人以人之性惡……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性惡》)荀子以“性僞合而天下治”(《禮論》)揭示了性惡論與禮法兼施政治哲學的内在聯繫。
先秦其他諸子的“遵道”亦是如此。墨子也説“遵道”(《天志中》),但其“道”即兼愛,“兼之爲道”(《天志下》)。墨子以愛人如己爲普遍的倫理原則,“天下人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兼愛上》);實現兼愛的辦法是“交相利”,即利益對等互報,如《詩經》所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在實踐上以“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兼愛下》)(4)孔子説:“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孟子説:“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孟子·離婁下》)他們與墨子上述觀點明顯不同。來擔保投桃報李的兑現。兼愛之道是針對天下如何由亂而治所提出的,墨子試圖以此改變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的大亂局,達到社會全面“和調”(《兼愛中》)。因此,從政治哲學上講,“兼者,聖王之道”,即“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兼愛下》《兼愛中》)。“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就是老子的“遵道而行”。這被稱之“爲無爲,事無事”(六十三章),即效法道之自然無爲而行事。從倫理學角度而言,“爲無爲”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三十八章)。以無意於人爲地執着道德規範爲最高的道德即“上德”。從政治哲學角度來説,“爲無爲,則無不治”(三章),這就是“治大國如烹小鮮”(六十章)。儘量減少干涉民衆,如同烹燒小魚不要多翻動一樣。韓非以法爲道。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他把人們的行爲軌於法令比喻爲“隱栝之道用也”(《顯學》),就像用隱栝把彎曲的木材矯正爲筆直。而其能够奏效,則以倫理學上的人性論爲根據: 以好利惡害爲“人情”即人性(《八經》),法令正是“因人情”而用賞罰“二柄”使得人們趨利避害。
三、 “志於道”與“我能期望什麽”
康德的第三個問題,實際是人生理想問題,“期望”即理想。康德以“至善”的道德作爲最高的人生理想。但他認爲道德與幸福在塵世生活中很難一致,德福統一的至善的人生理想只存在於宗教的彼岸世界。而先秦諸子的人生理想則具有現實世界中獲得德福一致的向度。孔子説的“志於道”,就是確立人生理想。他又説“志於仁”,把統攝道德之“仁”作爲終身追求的人生理想,“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仁,顛沛必於仁”(《里仁》),無時無刻都執着於仁。人生理想最根本的是直面生命意義的生死問題,爲了求仁的不惜犧牲生命,“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衛靈公》)。之所以不惜生命的代價,因爲“志於仁”正是人生之樂。孔子由此贊揚顔回能够長久地“不違仁”,而其他人很難做到,即使“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就是説,志仁成仁的人生理想體現了道德與幸福的現實統一。這同樣體現於孟子、荀子的人生理想。孟子以實現王道仁政爲人生理想。王道仁政的重要内容是制民以恒産,讓百姓“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由此聯繫孟子的“居仁由義”(《盡心上》)和“與民由之”(《滕文公下》),可以看到王道仁政的人生理想在義利之辯上是以民衆之利爲義,因而視百姓的憂樂爲憂樂,“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梁惠王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梁惠王下》)。這表明在孟子那裏對民衆的現實關懷,既是人生理想的道德原則,又是人生理想的幸福所在,此即“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盡心上》)。荀子的人生理想是“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王霸》),由注重實際功業的霸道發展爲以德服人的王道。成就霸道自然要講究功利,但“利克義者爲亂世”(《大略》)。因此,上王下霸的人生理想在義利之辯上是“以義制利”(《正論》)。荀子認爲這樣才能得到現實的幸福,“先義而後利則榮,先利而後義則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榮辱》)。這意味着德福的統一體現於把道德原則(義)作爲達到榮通(名譽顯貴)的手段。當然,這樣的幸福幾乎是以實際功利爲内涵了。可以説,孔孟和荀子分别從精神超越層面和實際功利層面回答了現實人生的德福統一何以可能。
先秦其他諸子“志於道”的人生理想各有不同,但追求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德福一致則是同樣的。墨子以兼愛爲道,其“守道”(《修身》)就是篤守兼愛之道的人生理想,它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下》)爲旗幟,試圖去除三大“民之巨患”,即“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非樂上》)。這樣的人生理想源自大禹。墨子稱贊大禹“形勞天下”,爲天下百姓治水而不辭勞苦;强調墨家必須“以自苦爲極”,“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自苦利他的人生理想,墨子既視其爲自己的道德追求,“獨自苦而爲義”(《貴義》),也視其爲自己的幸福所在,“愛人利人以得福”(《法儀》)。莊子的人生理想是“遊心於物之初”(《田子方》),即“遊心”於道,因爲道爲萬物的初始。“遊心”於道是要破除世俗所有束縛,使心靈像道那樣超越一切而自由自在。《大宗師》中,女偊在回答南伯子葵“道可得學邪”之問時,説明“遊心”於道,首先是“外天下”即遺忘世事,其次是“外物”即抛棄各種名利得失的計較,再次是“外生”即無慮於生死;於是心境“朝徹”即如朝陽一般明朗洞徹。而被世俗桎梏的人生,精神上昏暗茫然,“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齊物論》)!兩相對照,“遊心”於道的精神自由“得至美而遊乎至樂”(《田子方》),是完美至樂的人生理想。這與鄙視世俗利益誘惑的節操相一致。楚威王以厚幣相位禮聘莊子,莊子説: 不要玷污了我!我寧願像條魚遊戲污泥濁水中“自快”即自得其樂,求得精神愉快即“以快吾志”(《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以法爲道,其人生理想是通過變法改革,鼓勵耕戰,實現富國强兵,以此作爲成就統一諸侯各國大業的憑藉,取得三王五帝那樣的名望:“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乘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面對變法改革的重重阻力,“孤憤”之情鬱積於韓非胸中。不過,齊國改革家田成子的故事使其有所排遣。田成子改革終有成效,百姓歌舞慶頌,“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外儲説右上》)。這意味着韓非堅信自己的人生理想,必將有德於民並獲得爲百姓擁護的幸福感。
四、 “成人”之道與“人是什麽”
康德的第四個問題,從“人是目的”出發,注重何謂理想的人。他的回答是每個人在法律保障下達到享受最大自由的理想狀態。先秦諸子的回答則是在實現人生理想過程中造就理想人格。孔子的“人是什麽”,首先展開於人禽之辨,“鳥獸不可與同群”(《微子》)。“成人”之道正是對何謂與鳥獸相區别的理想人格的回答(5)“成人之道”還指二十而冠的成人禮儀,《禮記·冠義》云“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作爲全面發展的人格典範,是完美無缺的聖人。然而,其所謂“亦可”意味着現實中没有如此聖人,有的是會犯過錯的君子,因此在理想人格的層次上,君子遜於聖人。這樣的人格設定,一方面是强調君子對於聖人的追求只有進行時,没有完成時,始終持有提升自我的超越性;另一方面是强調聖人由君子拾級而上,具有不脱日用常行的現實性。因此,“君子之道”作爲聖人與君子的互補,是在日常生活中成就理想人格,如《中庸》所説“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由近及遠,由低往高,即從身邊事情做起。這就是後來王陽明説的“事上磨練”(《傳習録下》)。由事上磨練而成就的君子人格,與上述“志於仁”的人生理想相聯繫,一方面是把仁内化於心,這就是“克己復禮爲仁”以及種種“克己”的功夫: 一方面是承擔起社會中堅的使命,“仁以爲己任”,“任重而道遠”(《泰伯》)。孔子把這兩個方面概括爲“修己以安百姓”,以此回答“子路問君子”(《憲問》)。這實際上是對君子人格予以了内聖外王的雙重規定。孟子、荀子和孔子一樣,認爲君子之道須落實於事上磨練。因此,孟子反對“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離婁上》);荀子則正面表達爲“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修身》)。但兩者的事上磨練偏向不同: 前者偏向於内聖,後者偏向於外王。這與他們不同的人生理想有關。孟子王道仁政的人生理想以激發個人内在的惻隱之心這樣的善端爲基點,因而君子人格的造就以“存心”即道德意識的涵養爲指向,“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離婁下》)。荀子的人生理想是由霸而王,他推崇“威動天下”的春秋五霸(《王霸》),表明了極爲重視外在的事功。與此相應,君子人格展示了外王的偏向: 一是“法後王而一制度”的安邦濟世,“百家之説,不及後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儒效》),君子把以一統天下爲目標的“後王之道”(《不苟》)作爲言行的標準。一是制宰自然的“君子理天地”(《王制》),這就是“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解蔽》)。
先秦其他諸子“成人之道”的理想人格風采各異,但都是自身人生理想的承擔者。墨家源於俠,又被荀子稱爲“役夫之道”(《王霸》),平民和俠士的情懷是墨家理想人格的底色。“俠”與“義”相聯,墨子説:“萬事莫貴於義。”(《貴義》)其“義”以“力”爲基礎。墨子説: 禽獸的生存無需依賴耕稼紡織,“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非樂上》)。人與動物的不同,在於只有依賴自身力量才能生存。因此,人之“貴義”必須“賴力”。這有兩個方面: 一是譴責“不與其勞,獲其實,以非其所有取之”(《天志下》)即掠取他人所有而歸於己的不勞而獲爲“不義”,偷盜的行爲、貴族的奢靡、諸侯間的攻戰、人際間的以强侮弱等,均屬此列。一是以扶危濟弱爲“義”,如止楚伐宋(6)《墨子·公輸》記載,墨子得知楚國準備攻打弱小的宋國,跋涉十日十夜趕往楚國予以阻止,冒着爲公輸般所殺的危險,指責他助楚攻宋,違背了“義固不殺人”。,如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尚賢下》),顯然,墨家的貴義賴力是其自苦利人的人生理想的人格反映。道家認爲人應當與以自然爲宗旨的道合一,即莊子説的“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秋水》)。這與道合一的過程被稱爲“見獨”(《大宗師》),即體悟到道之“獨”。這從道的獨立無待來説,是人生理想上“遊心”於道的精神自由,“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齊物論》);從道的獨一無二來説,是在人格上以獨特個性最爲可貴,“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在宥》)。後者之“獨”是前者之“獨”的表現,莊子將此稱爲“自得”“自適”(《駢拇》)。見獨自得的人格展現出道家隱士群體的清高形象,“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繕性》)。法家提出了基於歷史進化觀點的理想人格。韓非説,歷史由“上古”到“中古”“近古”,直至“當今”;如果“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因爲死抱住堯舜先王之道者猶如守株待兔(《五蠹》)。這是把與時俱進的“新聖”作爲理想人格,並以此支撑變法圖强的人生理想。韓非深知改革少有勝算,《孤憤》《説難》《和氏》等對此作了冷峻分析,預見自己難逃前輩改革家吴起、商鞅的厄運——“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和氏》),生命和學説俱遭毁滅。然而,“新聖”是“强毅而勁直”(《孤憤》),逆襲而進,置生死於度外。這與上述的“孤憤”之情相交織,産生出改革家慷慨悲歌的人格震撼力和感染力。
從上述康德四個問題與先秦諸子求道之思的簡略比較,不難進一步看到了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既有哲學“類稱”的共性,又有作爲“特例”的個性。同時,先秦諸子的求道之思表現了“道不遠人”的重要内涵,即金岳霖所説“哲學家與他的哲學合一”,“他的哲學要求他身體力行,他本人是實行他的哲學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學的一部分”,“在他那裏,哲學從來不單是提供人們理解的觀念模式,它同時是哲學家内心的一個信條體系”。金岳霖同時感歎道: 西方自近代以來,“哲學家與哲學分離已經改變了哲學的價值,使世界失去了絢麗的色彩。”(7)金岳霖《中國哲學》,《道、自然與人》,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60頁。言下之意,繼承發展中國哲學“道不遠人”的傳統,將使世界哲學的舞臺再現失去的絢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