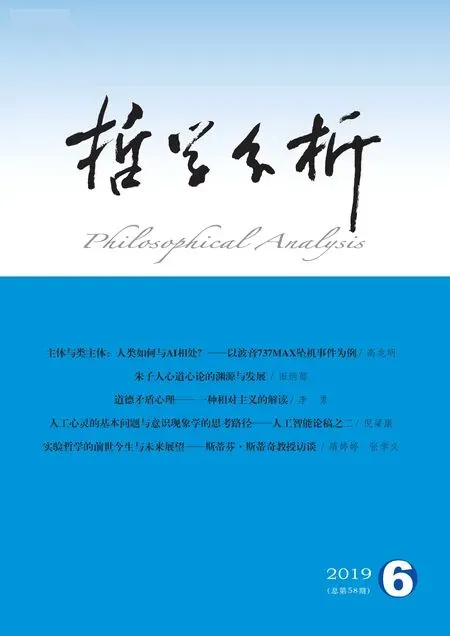政治、意见与真理
——以汉娜·阿伦特的柏拉图解释为中心的考察
乐小军
一
尽管汉娜·阿伦特以政治哲学家名世,但是她在1964 年接受德国记者京特·高斯(Günter Gaus)采访时说她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她也一直避免“政治哲学”这个措词。aHannah Arendt,“‘What Remains?The Language Remains’: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edited by Jerome Kohn,New York:Schocken Books,1994,p.1.这是因为,政治哲学在阿伦特看来是一个缺乏正当性的用语,它关涉的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生活方式。由于存在条件的不相容,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既然哲学与政治无法和谐共存,那么它们之间必定是一场彼此争夺霸权的斗争。斗争的最终结果必定是一方统治而另一方被统治,而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就是哲学支配政治这一模式的固化。阿伦特之所以对这个传统不满,是因为这个传统是从哲学的逻辑模式来理解政治的存在条件,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对政治的偏见和敌视,这一点清晰地呈现在这个传统的创立者柏拉图的哲学中,因此认真对待柏拉图就成了题中应有之 义。
从哲学史上看,哲学与政治的紧张肇始于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定罪,“自从苏格拉底审判,即城邦审判哲学家以来,这里就存在着政治与哲学之间的一种冲突”a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Correspondence,1926—1969,edited by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translated by Robert Kimber and Rita Kimb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2,pp.228—289.。苏格拉底之死“使柏拉图对城邦的生活感到绝望”,因为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好公民却被城邦处死,同时也“使他怀疑苏格拉底学说的某些基本原则”bHannah Arendt,“Philosophy and Politics”,Social Research,Vol.57,No.1,1990,p.73.。柏拉图从苏格拉底向雅典人提出自己的意见(doxa/opinion)并未令城邦相信其清白这个事实中,认识到基于意见的说服(peithein/persuasion)缺乏有效性。“意见”源自dokei moi,它的原初含义是“向我显现”(it-appears-to-me)。cIbid.,p.80.尽管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意见,然而由于每个人在政治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因此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见也是不同的,意见的这种复数性会导致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苏格拉底的意见败于雅典人的不负责任的意见,这个事实使得柏拉图把意见与真理对立起来,并且渴望某种可以用来判断人类行为的绝对标 准。在柏拉图看来,解决哲学与政治之间冲突的办法在于从哲学中而不是从政治中派生出政治标准。dHannah Arendt,“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s”,The Promise of Politics,edited by Jerome Kohn,New York:Schocken Books,2005,p.130.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用来衡量和评价政治领域的标准是一种处于政治领域之外、高于政治领域的超越性的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绝对标准,那么政治领域中的任何事情都会是相对的。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从哲学经验而不是政治自身的经验来检视政治,它是基于哲学的反思而不是真正的政治经验。换句话说,柏拉图是根据哲学家对政治的偏见和敌视来描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比喻”就给出了这种描述。阿伦特把这个洞穴比喻看作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中心eHannah Arendt,“Philosophy and Politics”,p.94.,由此可以想见这个比喻的重要性。当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根据黑暗、混乱和欺骗来描述人类事务领域时fHannah Arendt,“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Age”,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New York:Penguin Books,2006,p.17.,他对政治的态度昭然若揭。哲学家不仅应该逃离这个混乱不堪的领域,而且也不必过于认真地对待人类事务的整个领域。但是,柏拉图仍然把人类事务领域当回事,因为他想用他的理念论来改造政治。aHannah Arendt,“What is Authority”,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113. 也可参见Hannah Arendt,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edited by Ronald Bein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1。柏拉图所使用的eidos 和idea 这两个词的含义基本相同,但是它们的派生方式不同。我们一般把前者译为“形式”(Form),而把后者译为“形相”。汪子嵩和王太庆两位先生认为“理念”的旧译是不对的,宜将idea 和eidos 译为“相”和“型”(参见汪子嵩、王太庆:《关于“存在”和“是”》,载《复旦学报》2000 年第1 期,第28 页)。本文沿用旧译。正如米古尔·阿本索(Miguel Abensour)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暧昧性构成了洞穴比喻的基本结构。bMiguel Abensour,“Against the Sovereignty of Philosophy over Politics:Arendt’s Reading of Plato’s Cave Allegory”,Social Research,Vol.74,No.4,2007,p.958.
对阿伦特来说,洞穴比喻讲述了一个哲学家的生命历程,这个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标志着一个转向,三个转向加在一起构成了灵魂的转向,即哲学家的诞生。第一次转向发生在洞穴中,有一些人从小就居住在洞穴里,他们的腿脚和头颈被捆绑着,以至于他们只能呆坐在同一个地方直视着正对面的洞壁屏幕上的影像。这个未来的哲学家在摆脱了捆绑之后第一次转头看见了照亮洞穴中事物的火。这个火使得他明白屏幕上的影像实际上是真实所是的实物向他显现的。火不仅照亮洞穴中的实物,使它们真实所是地显现,而且也造成了这些真实所是的实物在屏幕上的影像。在这里,阿伦特区分了真实所是地显现和向人的显现这两种显现方式:前者是后者的原型,而后者是前者的影像。向洞穴居住者所显现的影像就是洞穴居住者所熟悉的意见(doxai/opinions),它们会因人所处位置的不同而显现出多样性。cHannah Arendt,“Philosophy and Politics”,pp.94—95.
当这个被阿伦特叫作“孤独的冒险家”的未来哲学家对洞穴中的火和这些真实所是地显现的实物感到不满意而试图找出火的来源和实物的原因时,他第二次转向,发现了一个离开洞穴的出口,这使他来到了理念的王国。所谓理念,是指真正的和纯粹的存在者,它是那些相对的和变化的事物的永恒本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哲学家定义为爱看理念的人,但是观看理念需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有光,这个光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的理念,即照亮理念的善的理念。阿伦特说,这个阶段是哲学家生命的巅峰,但同时他的悲剧也开始了。因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人,他并不属于这个理念王国,他必须返回原先居住的洞穴,然而他在洞穴中不再感到自在。在第三次转向中,他经验了一种从原初的家中被放逐的感觉,如果他试图把他在洞穴外面看到的东西告诉洞穴居住者,那么他轻则遭到嘲笑,重则性命不保。dIbid.,p.95;Plato,Republic,translated by Joe Sachs,Newburyport:Focus Publishing,2007,514a—517a.
我们从上述对洞穴比喻的概述中可以看到,过政治生活就是生活在一个阴暗的洞穴中,里面的囚徒所看到的洞穴墙壁上的阴影仅仅是意见。如若要寻求真理,那么他就必须离开他所居住的洞穴,因为真理不在洞穴中。在柏拉图看来,真理与意见不仅泾渭分明、相互对立,而且它们存在的可见度也不同,真理的领域是完全被光(作为善的理念的太阳)照亮的领域,而意见的领域则是光(火)与黑暗相混合的领域。如果说洞穴代表政治领域,那么政治领域就相当于意见领域,它们与真理领域构成了一个对立面。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显然是用哲学的眼光来看政治的,然而阿伦特提醒我们,拥有这种眼光的哲学家是“如何疏远人类的事务,……他们再也不能在洞穴的黑暗中看见东西,他们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方向感,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所说的他们的共同感(common sense)”aHannah Arendt,“Philosophy and Politics”,p.95.。在这里,阿伦特用共同感来指洞穴居住者的共同意见,以此与哲学相区 别。
共同感与哲学的区别是政治与哲学关系的另一种表述。我们从洞穴比喻中不难看出,成为哲学家的先决条件在于从人类事务领域中撤离从而超越那里的共同意见。按照奈廷格尔(Andrea Wilson Nightingale)的说法,这个旅行去看真理的人最后成为了一个新的人,也就是说静观理念的活动转变了他,给了他一套新的能力、性格和价值,使他对世界有了一种完全新的观点。bAndrea Wilson Nightingale,Spectacles of Truth in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y:Theoria in its Cultural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06,p.116.悖论的是,“看”也是洞穴居住者的唯一活动,他们既不言说(lexis)也不行动(praxis)。阿伦特认为,柏拉图所描述的这些人其实是潜在的哲学家。cHannah Arendt,“Philosophy and Politics”,p.96.我们知道,言说和行动是政治的存在条件,然而柏拉图把人类事务领域看作通向哲学真理领域的准备阶段,这种理解不仅抹杀了政治的意见领域自身的自主性,而且使它受制于哲学的真理领域,这种反政治的立场导致了对政治的人类条件的误解。汉斯—约尔格·西格瓦特(Hans-Jörg Sigwart)分析说,成为一个哲学家和成为一个公民是两种不同的人类存在方式,因为构成这两种存在方式的经验现实的模式是不同的和不相容的。哲学对惊异(thaumazein)的经验是一种单数的人的个人的经验,相反,政治对世界的经验是一种形成意见的复数性实践。dHans-Jörg Sigwart,The Wandering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pp.15—16.简单地说,哲学与单数的人有关,而政治与复数的人有关,因此它们是两种异质的存在经 验。
阿伦特在写于1971 年的《海德格尔的八十寿辰》一文中再次考察了哲学对惊异的经验。阿伦特说,海德格尔曾经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也讲过这种对纯粹惊异的能力,但与柏拉图不同,他还补充说把这种惊异作为人的居所。后面这句话对于反思海德格尔的问题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尽管人们熟悉思想以及与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孤独,但是显然没有人会在那里有他的居所。当惊异压倒我们时,我们就会从人类事务领域中撤离出来从事思的活动,但不久之后我们又会回到人类事务领域。从世界中撤离是思想的前提条件,因为思想只与不在场的东西打交道,这就是思想的“去感觉”特征。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他要固守在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脱离世界的思想的居所中。a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 at Eighty”,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Critical Essays,edited by Michael Murra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pp.299—300.尽管思想要成为可能,它就得从世界中撤退,但是海德格尔却要居住在思想之中。孤独的思想会削弱思想家的共同感,使他迷失在人类事务领域中。就像泰勒斯与色雷斯少女的故事所讲的那样,一个想知道天上事的人却没有看到位于他脚下的东西。bIbid.,p.301.尽管居住在纯粹思想中的宁静生活对于职业思想家来说是充满诱惑的,但是完全切断我们与人类事务领域的关联是很危险的。一旦人间事务将思想家带回他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使他不得不与他陌生的意见世界打交道时,他就会像那个返回到洞穴的哲人一样失去方向感和判断 力。
二
如前所述,尽管柏拉图是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政治,认为人类事务领域是一个需要逃离的晦暗领域,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领域不当一回事。哲学家只关注真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对政治事务不产生任何作用。阿伦特认为,柏拉图写作《理想国》显然是要证明哲学家应该成为哲学王这个观念的合理性,这不是“因为他们[哲学家]喜欢政治,而是因为,首先,这意味着他们不想被比他们自己更坏的人统治;其次,这将给城邦带来完全的宁静和绝对的和平,这当然构成了哲学家生活的最好条件”cHannah Arendt,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1.。哲学家在城邦里的处境和命运要靠他自己来改变,这就要求哲学家返回洞穴,用他在洞穴外面所看到的理念来改造洞穴内的政治,也就是用eidos 来统治doxa。我们知道,eidos 在柏拉图那里属于静观的对象,这种观看理念的生活方式(bios theoretikos)是一种最自足的行动(praxis)形式。对于喜爱看理念的哲学家来说,他最渴望的幸福生活不是返回到洞穴中去当哲人王,而是永远居住在理念的晴空下。现在,哲学家被强迫去过一种洞穴中的政治生活(bio politikos)。由于返回洞穴的人在洞穴中所面临的潜在危险,或者说由于城邦对哲学家的敌视,哲学家需要改变理念的原初含义,以便适应政治的要求和目 的。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对此作了这样的总结:“只有当他返回人类事务的黑暗洞穴,再次与他的同伴生活在一起时,他才需要理念作为标准和规则来指导,通过它来衡量许多不同的人类行为和言说,把这些行为和言说归入同一种绝对的、‘客观的’确定性中,这种确定性也是指导工匠和外行用不变的、永恒存在的模型即普遍的床的‘理念’来制作和判断个别的床。”d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226.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当理念从哲学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时,它的含义也从静观的纯粹存在转变成了标准和规则。阿伦特自己承认,她的这个看法受惠于她的老师海德格尔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中对洞穴比喻的解释。aHannah Arendt,“What is Authority”,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284,note16.她在1956 年7 月1 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明确地说:“当海德格尔说在阐明洞穴比喻中,真理偷偷地被转换成正确性(correctness),因此理念被转换成标准(standards)时,他是对的。”b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Correspondence,1926—1969,1992,p.228.
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阐明这个转变的?按海德格尔的说法,真理在希腊语中是指一种无遮蔽性或去蔽(aletheia/ Unverborgenhei),也就是对遮蔽的东西(letheia)的剥夺(否定前缀a-)。如此说来,非真也就不是现代人所谓的错误,而是一种遮蔽性(Verborgenheit)。任何东西在去蔽即展开之前都是遮蔽的,没有遮蔽就没有之后的去蔽,这就意味着遮蔽是真理(aletheia)的前提条件。遮蔽与去蔽都是存在的基本特征,真理不是纯粹的光明,洞穴中的晦暗的生活也是真理的一部分,真理是遮蔽与去蔽的一场斗争。然而,柏拉图却把真理只看成一种纯粹的和永恒存在的光明,换言之,真理是理念的纯粹的无遮蔽性,而这种纯粹的无遮蔽性只发生在洞穴外面。因此,海德格尔说,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中,“aletheia 受idea 的支配。当柏拉图说idea 是允诺出无遮蔽性(Unverborgenhei)的主宰时,他便向我们指明了某种未曾说出的东西,这就是:从此以后,真理的本质不是作为无遮蔽的本质而从它本身的本质丰富性中展开出来,而是转移到了idea 的本质上”cMartin Heidegger,Wegmarken,Gesamtausgabe Bd. 9,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76,S.230. 中译文参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265 页。译文略有改动。。
用迈克尔·英伍德(Michael Inwood)的话说,在柏拉图那里,aletheia 是在idea的支配下出现的,idea 来自希腊语idein(看)——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它指的是实体的视觉外观(Aussehen)。离开洞穴的囚徒的上升是对他们看理念的一种逐步校正。因此,aletheia 不再是存在者的一种特征,而是对理念的正确地看。dMichael Inwood,A Heidegger Dictiona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9,p.14.在idea(理念)和idein(看)对aletheia 取得优先性中,真理的本质发生了变化,真理变成了一种正确性。eMartin Heidegger,Wegmarken,S.231.海德格尔:《路标》,第266 页。如前所述,阿伦特认为,尽管海德格尔在论证柏拉图是如何把aletheia 转变成正确性这一点上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论证的政治语境,也就是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想把他的理念作为一种超越性的标准或规则应用于政治领域。构成这种政治意图基础的东西从根本上说还是真理与意见水火不相容这个基本论 题。
一旦这种超越性的标准或规则被引入到人类事务领域中,它就成为了人类行动的标准或规则。在阿伦特那里,政治、自由和行动是一组三位一体的概念,“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aHannah Arendt,“What is Freedom?”,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145.行动就是自由的政治行动,它是一种开始新事物的能力。“与制作不同,行动在孤独中是绝不可能的;孤独也就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b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p.188.。行动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中进行的,它完全依赖他人的在场,这意味着行动必定与公共领域相联系,而公共领域内显现的永远是不能被还原的复数的人。这当然不是说公共领域中只有差异性而没有一致性,而是说差异性是一致性的前提。此外,政治上的一致性应该以政治的方式来获得,确切地说,“每件事情都是通过言说和说服而不是通过力量和暴力来决定”cIbid.,p.26.。一言以蔽之,行动对应于复数性这个人类条件,也就是对应于“人们(men)而不是人(Man)在地球上生活,在世界中居住”dIbid.,p.7.这个事实。正因为如此,与制作东西的制作者不同,行动者无法预期他自己行动的后果,“行动的灾难全都来自复数性的人的条件”eIbid.,p.220.。因此,“对于行动的人来说,总有一种很大的诱惑去寻找一种行动的替代品,希望人类事务领域可以逃避行动者的复数性所固有的偶然性和道德上的无责任性”fIbid.。
这种行动的替代品就是制作。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用来作为其哲学关键词的“idea”实际上来自制作领域中的经验,“idea 或eidos 是工匠在开始他的工作之前在他的心灵的眼睛之前必定拥有的模型或蓝图”g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Mind,Vol.1 Thinking,New York:Harcourt,1978,p.104.。制作一定要看一个原型,所有的制作都包含看。比如说,工匠制作一张床,他是怎么制作出来的?首先工匠心里要知道床的样子或理念(eidos),然后他看着床的样子制作出具体的床。政治技艺同样如此,统治者看着正义的理念把正义的事情做出来。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就是根据制作来理解行动的,就像床的模型指导工匠制作一张床那样,正义的理念指导哲人王制作一个正义的城邦。这里需要辨明的是,哲学在柏拉图那里只是纯粹地看(theoria),它不仅自身就是目的,而且是一种最自足的praxis(实践/行动)。与praxis 形成对照的是poiesis(制作),按照特伦斯·鲍尔的说法,它们的区别在于,praxis 是一种自我包含的活动,它自身就是完满的,而不作为一种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相反,poiesis 是指达到一个单独可确认的目的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poiesis是工具性的活动。hTerence Ball,“Editor’s Introduction”,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xis:New Perspectives,edited by Terence Ball,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p.4.由上所述可以看到,当柏拉图把看到的理念作为标准或模型应用于政治领域时,他实际上是把政治活动看成达到某种目的(比如上文所说的“逃避行动者的复数性所固有的偶然性和道德上的无责任性”)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是根据制作经验来理解政治的,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poiesis 对praxis 的取 代。
正是柏拉图所开启的制作对行动的取代,造成了archein(开始/统治)与prattein(行动/实现)之间的分裂。这两个词在希腊人那里原本用来表示同一个praxis 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现在它们却变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archein 是指只统治而不行动,而prattein 则是指单纯执行命令而不统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确保开始者保持对他所开始的事情的完全控制,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它”a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pp.222—223.。这其实是按照工匠和他的材料之间的制作模式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像在制作中工匠统治材料一样,在政治中发布命令的人统治执行命令的人。在柏拉图看来,发布命令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统治自己的人,也就是那些灵魂中理性部分统治欲望部分的哲学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统治他人,因为他们具有自我知识。由此可见,这种以制作为模式的统治理论内在地包含着知与行的分离。比利时现象学家塔米尼奥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根据他的说法,柏拉图提出知而不行的人与行而不知的人这个区分的意图有三:第一,给予poiesis 以特权;第二,使praxis分裂为两个部分;第三,废除公民的phronesis(明智)。由于把公民变成prattein,即确定任务的执行者,因此公民的phronesis 只是一个幻觉,而真正的phronein 是哲学家的theorein。bJacques Taminiaux,“Bios politikos and bios theoretiko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Hannah Arendt”,translated by Dermot Mor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Vol.4,No.2,p.223.信哉斯 言!
三
在明确了真理与意见的对立最终导致制作对行动的取代从而消除了政治这一结果之后,拯救政治的方向无疑在于破除真理与意见之间的对立。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真理与意见的对立已经固化为对人的复数性这个基本政治现象的偏见和敌视,因为真理想要“与显现世界以及构成显现世界的意见相分离,它想成为孤独的和自足的,而不想嵌入复数性中”cIbid.,p.221.。此外,所有真理在它们断言有效性的模式上也都与意见相对立,真理自身就带有一种强制的因素。dHannah Arendt,“Truth and Politics”,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235.一旦拥有真理,就没有了争论和说服的余地,即使上帝也必须同意二乘以二等于四。可见,“从政治的观点看,真理具有一种专制暴君的特征”eIbid.,p.236.,因为真理只与单数的人有关,而政治的最基本特征是它的复数性,因此真理从根本上说是反政治 的。
真理与意见的对立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表征为存在(being)与显现(appearance)的二分法。在柏拉图哲学中,真正的存在属于可知世界,而纯粹的显现则属于可见世界,由此可见,存在与显现的对立是两个世界理论的一种翻版。虽然显现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因为它不是完全虚假的,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存在。真正的存在潜藏于显现的背后,它需要靠灵魂的眼睛才能发现。换句话说,真正的存在是不显现的东西而不是显现的东西,显现的东西是以不显现的东西作为自身的根据,或者说不显现的东西是显现的东西的基础。因此,不显现的东西在等级上要高于显现的东西。阿伦特在《精神生活》中是这样来评论存在与显现之间的这种对立的:“我们的哲学传统已经把某物所来自的基础转变成了产生某物的原因,并给予这个产生的行为者以一种比仅仅满足眼睛的东西更高的现实等级。原因应该比结果具有更高的等级这个信念,可能属于最古老和最顽固的形而上学谬误。”a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Mind(Vol.1)Thinking,p.25.
在柏拉图那里,可见世界就是显现的世界,但它是晦暗不明的意见世界,而真正光明的世界则是可知世界,也就是真理世界。阿伦特明确指出,这个形而上学谬误“不是来自我们对于显现世界的普通经验,而是来自思想自我的不普通的经验”。bIbid.,p.42.这意思是说,柏拉图的可知世界是思想从显现世界中撤离后所居住的处所,虽然这个世界在我们的政治世界中是不显现的,但是它在等级上要高于显现的政治世界。阿伦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真理从可知世界转移到可见的政治世界,从而消除存在与显现之间的二元对立。这显然来自海德格尔的启发。如前所述,海德格尔认为作为aletheia 的真理是在洞穴内而不是在洞穴外发生的,因为真理存在于遮蔽与去蔽的张力中。可知世界中的真理(理念)是纯粹的存在,它只是纯粹的去蔽;可见世界中的意见则处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所以它在被遮蔽的同时又抗争这种被遮蔽。因此,真理的发生地是意见的显现世 界。
在完成了把真理从可知世界转移到政治领域后,阿伦特接下来要做的是把作为aletheia 的真理看作一种向我显现,由于意见(doxa)的原初含义是向我显现(dokei moi),因此我们可以说意见就是通过显现被揭示的aletheia。所谓显现就是指能够被每个人看见和听见,这种被看见和听见构成了我们存在的现实性。显现之所以能够被每个人看见和听见,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公共的政治世界中显现的。在公共的政治世界中,“存在与显现是同时发生的”cIbid.,p.19.。这种向我显现会随我们在政治世界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由于我们是在世界中的存在,我们只能从世界中的某个位置来看世界,而无法采用一种上帝的全景式视角来看世界。又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我们看世界的观点也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的观点,“考虑其他人的意见是所有严格的政治思想的标志”aHannah Arendt,“Truth and Politics”,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p.237.。阿伦特把这种政治思想称作“代表性的思想”(representative thinking):“通过从不同的观点来考虑一个给定的问题,通过使那些不在场的人的立场出现在我的心中,也就是我代表它们,我形成了一个意见。代表的这个过程并不是盲目地采用那些站在其他立场上的人的实际观点,而是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世界;这既不是移情问题,好像我试图成为某个其他人或像他那样感受,也不是数人数和加入大多数人的问题,而是在我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方在我自身的同一性中存在和思想的问题。当我思考一个给定的问题时,我在我心中呈现的人们的立场越多,我就越能更好地想象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将会如何感觉和思想,我代表性思想的能力也就越强,我最后的结论和意见也就越有效”bIbid.,p.237.。由于我们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因此我们作出的判断总是会被某种主观性所规定。要摆脱这种私人条件的限制,我们就得通过想象力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世界。这种代表性的思想要求的是一种不偏不倚(impartiality)的品 质。
由于意见是在我们这个流变的世界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就意见而言的思想也是流动的,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世界的一个部分到另一个部分,穿过各种各样的相冲突的观点,直到它最后从这些特殊性上升到某种不偏不倚的一般性(impartial generality)”cIbid.,p.238.。应该注意的是,阿伦特这里讲的“一般性”不是指某种超越意见领域的普遍性,而是指意见从每一个可能的视角来显现自身,这种视角的多样性对应于人的复数性条件。既然每个人在不同的视角上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都具有有效性吗?罗纳德·贝纳(Ronald Beiner)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说:如果某些意见要说服我们,那么它们就要让我们相信这些意见所断言的东西具有真理。dRonald Beiner,“Rereading‘Truth and Politics’”,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Vol.34,No.1—2,2008,p.126.贝纳的这个质疑想表达的是,意见仅仅是主观的东西,它缺乏某种真理性。尽管意见的主观性是由每个人站在他自己的位置上来看世界这个事实所规定的,但它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它也来自这个事实,即世界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某种对它的所有居住者来说共同的东西”eHannah Arendt,“The Crisis in Culture”,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p.219.。需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域中的真理的本质特征是复数性而不是超越 性。
一谈到意见,人们总不免会认为它与真理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这对于柏拉图来说具有正当性,但是阿伦特并不这样认为。阿伦特之所以反对柏拉图的超越人类事务领域的绝对真理,是因为这种绝对真理取消了我们从一个复数的视角来看世界的可能性。正如科林娜·埃诺多(Corinne Enaudeau)所说的那样,阿伦特试图理解真理的哪种使用会取消政治明朗,相反,哪种使用会保证政治明朗。aCorinne Enaudeau,“Hannah Arendt:Politics,Opinion,Truth”,Social Research,Vol.74,No.4,2007,pp.1029—1030.显然,超越性的绝对真理不仅无法保证政治明朗,而且还会使政治去价值化。阿伦特要寻求的是一种属于政治世界而不是在政治世界之外的真理,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政治的复数性条件——那就是以视角的复数性向我们显现的意见。政治世界中不存在一种意见对其他意见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也没有哪一种单一的视角可以支配其他的视角,各种不同意见和视角之间是一种平等(isonomy)关系。即使我们通过想象力能够尽最大可能地站在所有其他的视角上来看问题,这也并不是说所有其他的视角可以被还原为这个单一的视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政治的复数性条件被消除 了。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全面统治的目标就在于用“一个巨大的人”(One Man of gigantic dimensions)来取代复数的人。bHannah Arendt,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1994,pp.455—466.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最大的偏见就是对人的复数性的敌视,这样一来,这个传统的开创者柏拉图岂不成为极权主义的罪魁祸首?阿伦特说,极权主义的独创性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的行动构成了与我们所有传统的一种断裂”cHannah Arendt,“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s ”,Essay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edited by Jerome Kohn,New York:Schocken Books,1994,pp.309—310.。照此看来,柏拉图哲学不仅不是造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用它的概念框架也无法理解极权主义现象。那么,极权主义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到底有没有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要素(element)和原因(cause)这两个概念。根据阿伦特的解释,要素和原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素本身决不会引起任何东西,如果要素突然结晶成了固定的和确定的形式,那么它们会成为事件的起源”dIbid.,p.325.。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是构成极权主义的要素,而不是形成它的原因。阿伦特的柏拉图解释的目的就在于用“没有被哲学遮蔽的眼睛”eHannah Arendt,“‘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edited by Jerome Kohn,New York:Schocken Books,1994,p.2.来发现那些要素的原初经验,从而恢复被这个传统所抹杀的真实的政治经 验。
——人的美学视野中的阿伦特